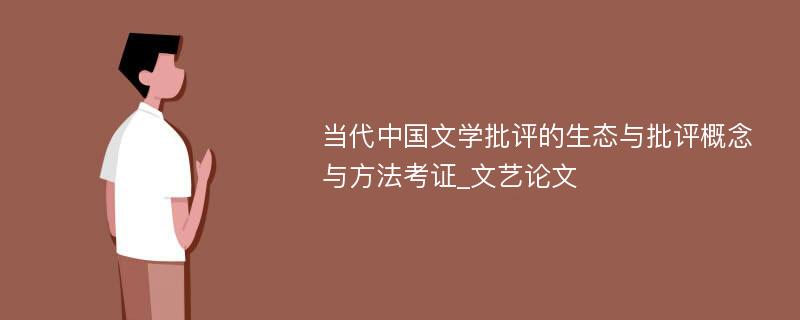
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生态及批评观念与方法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批评论文,中国当代论文,批评论文,观念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精髓是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批判意识,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发扬光大,但就是这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常识,在我们今天的批评界却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时代批评的悲哀,也是几代批评家的悲哀。谁来打捞具有批判精神的文艺批评呢?这或许是批评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正是由于这种危机的存在,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才负有重新建构文化与文艺批评话语体系的责任。除去种种外在因素,我以为这一状况与所谓“后现代批评”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国内理论界有很大关系。正如卡林内斯库所言: 詹姆逊的思想和著述风格要松散得多,而且可以说它表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正经历的严重理智问题。晚近马克思主义最明显地丧失了的,是它早先所具有的方法论完整性,以及使它能从其他各种社会思想模式中被辨认出来的内在历史主义逻辑。今日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似乎乐于甚至是急于采纳任何碰巧在理论上时髦的方法或“反方法”(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最高深形式),却不考虑这种兼收并蓄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参照系的爆裂,而他们却自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① 因此,“后现代批评”对中国“学院派”批评家的巨大影响,对文化与文艺批评向正常轨道回归是一次严重的干扰。笔者只想针对文化和文艺批评领域中存在的弊端进行论述,并针对批评界缺乏基本常识与规范的许多症状做出评判与纠正,以期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同时,笔者也不得不对文艺批评做出一些必要的考释和梳理。如果我们连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都搞不清楚,那么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就将永远陷入“盲人骑瞎马”和“盲人摸象”的泥淖之中,徘徊于濒死的境地。 一、批评词义考释与批评现状 文艺批评在中国古来有之,然而其在今天的理论模式却是从西方引进的。它的内涵与外延在西方历经了几千年的变化与发展,形成了许多思潮和流派,但在中国学界的运用与借鉴中,它的意涵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漂移和改变。尤其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我们像“过电影”那样跨越了从封建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历史过程,但我们的文艺批评始终都没有走出“颂歌”与“战歌”模式的怪圈②。即便是当下充满着铜臭味儿的商业化文艺批评,也正是利用了“颂歌”的批评模式,肆意将交易的利润无限扩大,导致了全社会对文艺批评的不屑。 查阅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笔者发现“批评”和“评论”是在同一个词条下的,试看其中三个词条: critic 批评者,吹毛求疵者(文学、艺术或音乐作品等的批评家、评论家)。 critical ①吹毛求疵的,批评的,评论性的;②善于评论的,从事评论工作的;③附有异文校勘材料的;④危机的、危急的,决定性的、关键的;⑤达到临界状态的。 criticism ①批评、指责、非难,批评意见,指责的话;②(某评论家的)作品评论,评论文章。③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所谓批评是涵盖一切评论的,而评论也包含着批评的职责。而中国的批评与评论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分道扬镳了。 雷蒙·威廉士在考察“criticism”一词的演变过程时谈到: Criticism已经变成一个难解的字,因为虽然其普遍通用的意涵是“挑剔”(fault-finding),然而它有一个潜在“判断”的意涵,以及一个与文学、艺术有关且非常令人困惑的特别意涵……这个英文字在十七世纪初期形成,是从十六世纪中叶的critic(批评家、批评者)与critical(批评的)衍生而来……Criticism这个字早期普遍通用的意涵就是“挑剔”:“处在批评的焦点(marks of criticism)……众矢之的。”Criticism这个字也被用作对文学的评论,尤其是从十七世纪末期以来,被用来当成“评断”文学或文章。最有趣的是,这个普遍意涵——亦即“挑剔”,或者至少是“负面的评论”——持续沿用,终成主流。④ 或许,我们可以从威廉士的论述中看到其中蕴涵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如果这样的溯源还不足以说明批评的本义,那么我们就只能追溯到它的源头——古罗马文艺批评。“古罗马文艺批评是从公元前2世纪中期后随着文学发展的高涨而兴起的”⑤。它的缘起是围绕着罗马文化是否应该吸收希腊文化的意识形态斗争而展开的:“这时的文艺批评关心的主要是与吸收希腊文学成就和在此基础上发展民族文学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如关于希腊文学作品的利用、文体概念、写作手法和技巧、诗歌文体、文学语言问题等。这时的文艺批评主要散见于诗人、作家的各种类型的著作中,因此我们可以说第一批罗马诗人、作家同时也是第一批文艺批评家。”⑥这里起码给我们三点启示:首先,文艺批评应该争论问题,而不是吹捧式的评论,它区别于鉴赏性质的歌功颂德;其次,它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也就是说,政治领域的问题是可以争论的,就像我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最后,也是中国当代文艺批评沦落的关键问题之一,这就是西方的许多批评家同时也是作家,因而他们总是能在创作实践中取得优先发言权,获得足够的资格进行批评。检视中国这六十余年来的文艺批评“家”们,又有几个同时是创作者呢?当然,我们不能排斥有独到见地的大理论家参与文艺批评,但绝不能够容忍那种连作品都没有读懂就指手画脚的批评家大行其道。 诚然,我们不能忽略“罗马文法批评”的存在:“古代存在过三个不同的批评术语,这就是语文家(philologos)、批评家(critikos)和文法家(grammatikos)……关于批评家,亚里士多德曾在《论动物的结构》中说:‘我们认为,只有受过全面教育的人才有能力批评各种事物。’后来‘批评家’用来指对文艺作品进行分析的学者。在附于柏拉图名下的一篇佚名作者的对话录《阿克西奥科斯》(公元前4世纪末)中,‘批评家’系指学校里的高级文学教师,与低级文学教师grammatikos(文法家)相对。塞克斯图斯·恩皮里库斯(公元3世纪后期)曾经根据克拉特斯的看法,对批评家和文法家做过如下界定:‘批评家应该精通于各门属于精神起源的科学,而文法家则仅仅需要知道词语解释、音韵理论等。’”⑦笔者之所以引用这段话,与下文分析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现状有关。而这里笔者要强调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清楚西方文艺批评史自古以来就将“批评家”和“文法家”区别开来。“批评家”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精通于各门属于精神起源的科学”,具有广博的人文知识积累。这一点也恰恰是中国当代批评家无法企及的。因此才会出现一些连最起码的文史知识都不知道,却也能够横行于文艺批评界的“怪胎”。反观我们几十年来的所谓“评论”,恐怕也就至多属于“文法家”的层次。其次,“批评家”担当的是审视与评判的职责,只有这样才能在文艺批评中居高临下地指出作品的优劣与高下。他们的批评文章只有在充分发挥批判的功能后,才能达到文学艺术的审美高级阶段,其中暗含的“审判”意识应该成为文艺批评的自觉。而“文法家”担当的职责则是在作品鉴赏层面的“评论”。作为大众阅读的引领者,“文法家”只是作品的解读者而非批判者。这就划清了“批评”与“评论”的界限,两者所承担的对文学艺术阐释的职责与功能不尽相同。而我们的评论家恰恰混淆了这两者的区别,浑浑噩噩地进行当代文艺批评。说到底,我们只有作为“文法家”的评论者,而鲜有真正具有批判自觉的“批评家”。正是缺少了批判的风骨,我们的文艺批评才会让那些三流乃至十流的作品流布于市、妖言惑众。 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是批评家素养的升华,即从一般性的讽刺指谬的“批评家”上升到有自觉批判意识的文艺“批评家”,这需要大量的人文知识储备,还要具有历史哲学的识见和不畏强权的批判勇气。以伟大的批评家琉善为例: 琉善虽然是一个修辞学家,并且在其早年受到第二期诡辩派的影响,但他终于能以批判的态度克服诡辩派的各种弊端,成为当时一位最杰出的讽刺作家。他的讽刺矛头指向正在瓦解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的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修辞学和文学等。正像他严厉批评他生活时代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宗教迷信一样,他也严厉批评他生活时代的历史著述和文学创作,在这些批评中表现出他的文艺观点……他反对虚假的、美化真实的写作,肯定真实的、非虚伪的文学,号召作家(包括历史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作家)深入地观察生活。他认为:“作家最好写他亲自见到的、观察过的东西。”他认为作家的思想应该有如镜子,真实地反映出所接受的东西,不歪曲、不美化、不改变原貌……他认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要能够独立思考,不趋炎附势,对任何人都无所畏惧,这样才能胜任历史著述的首要任务——如实地叙述事件……史家作史应该能千古流传,而不要追求同时代人的一时激赏;不应用一些传说取悦于人们,而应给后代留下对事件的真实叙述。他认为这就是历史学家应遵循的原则。与这种原则相适应,历史的叙述风格应该平易流畅,文笔简洁,不雕饰,不浮夸。⑧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琉善生活的年代,文体的分类还不很严格,他所说的“历史”包括一切叙述和议论的文体。也许很多文艺理论家会认为这种古老文艺学见解已经过时了,但正是这个朴实的文艺学理论在检验几千年来的世界文学史,尤其是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当我们一直相信文艺创作应比生活更高、更集中、更伟大时,我们却背离了生活的本质,离真实的生活更加遥远了。笔者一直以为作家只能对历史进行真实的摹写,绝对没有篡改和美化历史的权力。像《大秦帝国》这样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作品,非但在文法技巧和艺术造诣层面上乏善可陈,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肆意的践踏和亵渎,却得到了许多“评论家”的高度评价。这不仅表明那些评论家的修养和审美水平出了问题,更可悲的恐怕是他们并不知道批评的最高阶段是既有艺术感悟的灵性,又兼备历史批判的责任,而绝不是政治投机。反观当代文艺批评的历史,我们的批评家哪一次不是踏着雕饰和浮夸的节奏在前行呢?那种能独立思考的批评少之又少,即便有,也往往马上就被投机的文艺批评家剿杀殆尽了。文艺批评一旦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批评的本质就被阉割了。所谓不歪曲历史,往往不止于作家对历史的刻画,更在于批评家的理性分析和深度的哲学批判阐释。 雷蒙·威廉士在谈到“censure”一词的涵义时提到: Censure(责备、严厉批评)。当criticism的最普遍的意涵朝向“censure”解释时,其专门特别的意涵却是指向Taste(品味、鉴赏力),cultivation(教化)、culture(文化)与discriminatin(识别力)是一个意义分歧的字,它具有正面的‘良好的或有见识的判断’之意涵……问题的症结不仅是在于“批评”(criticism)与“挑剔”(fault-finding)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在于“批评”与“权威式的”(authoritative)评论两者之间存在着更基本的相关性:二者皆被视为普遍的、自然的过程。作为表示社会的或专业的普遍化过程的一个词汇,criticism是带有意识形态的……将criticism提升到“判断”的意涵……在复杂而活跃的关系与整个情境、脉络里,这种反应——不管它是正面或负面的——是一个明确的实践(practice)。⑨ 回眸六十多年来的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我们的批评始终停滞在对作家、作品进行鉴赏的层面。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批评家的理论基础和人文修养先天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批评与评论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学活动。前者是融形上与形下为一炉的哲思,而后者却只是一种文法阐释和欣赏活动。也就是说,当“批评”上升到“判断”(即“批判”)的层面时,其批判精神就起着主导作用了。这就是雷蒙·威廉士所说的“带有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式的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当然可以赞颂,西塞罗就声称“文学称赞是对德行的最高奖赏”。王焕生指出,西塞罗认为“对一个杰出人物的颂扬实际上也是对一个民族的颂扬,对一个民族的颂扬可以激励人们为荣誉而奋斗。因此,国家应该尊重诗人,重视文学。西塞罗的上述看法反映了当时罗马社会文学观念的变化……从上面的举例可以看出,罗马上层社会人士也正极力利用文学的这种功能,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求扬名后世”⑩。我们不反对为国家、民族以及英雄歌功颂德,但它只能是批评观念与方法的一种,而且这只是“文法家”的工作范畴。我们千万不能将其当做文艺评论的唯一标准和衡量评论家水平高低的尺度。一个批评家如果像鲁迅批评的“京派”和“海派”文人那样被“官家”或“商家”豢养,他就不可能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同时也就放弃了批评的尊严。六十多年来,我们给作家的待遇让全世界羡慕和瞩目,它在体制层面上就规定了作家和艺术家享有至高的荣誉和权力。在这一体制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只有“歌德派”才能获取更大利益。反躬自问,包括笔者在内的绝大多数所谓批评家,有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鲜血淋漓的现实发出良知的呐喊呢?几十年来由文艺这个政治风云的晴雨表记录下来的痛苦经历,已然将奴性植入了作家和艺术家的血脉,从而使作品丧失了生命的活力。这种精神萎缩同时传导给文艺评论界,使其失去了批判的立场。 其实,不为意识形态操控不仅是作家的品格,而且也应该是批评家的品格。奥威尔曾这样评价法朗士和马克·吐温: 跟马克·吐温相比,那位法国人(指阿纳托尔·法朗士)不仅更博学、更文明、更有审美趣味,而且也更有勇气。他敢于攻击自己所不相信的事物;他从没像马克·吐温那样,总是躲在“公众人物”那可亲的面具后面,甘心做一个特许的弄臣。他不惧怕得罪教会,在重大的争议中——比如,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敢于站在少数人一边。反观马克·吐温,则从来没有攻击过社会确定的信仰,生怕惹上麻烦(《什么是人》这个短篇也许是个例外)。他也一直未能摆脱“成功与美德是一回事”这一典型的美国式观念。(11) 是的,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像马克·吐温这样“甘心做一个特许的弄臣”的人太多了,却很难见到法朗士那样敢于说“不”的批评家。 奥威尔作为欧洲20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之一,他的批评充满着文化批判的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的犀利之处是敢于进行近乎刻薄的批评。他这样评价自己不喜欢的作品:“我所提到的这些书,都是所谓的‘逃避’文学。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形成了愉快的区域和安详的角落,都跟现实生活委实没有多大关系。”(12)这样敢于“吹毛求疵”的批评家在中国非常罕见,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那种躲在意识形态皮袍下的唱诗者,连“公众人物”的面具都不敢戴的发言人,他们早就把批判的武器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奥威尔一贯秉持现实主义的文艺观,他告诉我们:作家的技巧再好、再时尚、再先锋,如果不能忠实于现实,那么其作品就不会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反观文艺界在“十七年”时期兴盛起来的“战歌”批评模式,其理论基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规训。这样的批评模式一旦蔓延开来,就不仅仅是文学艺术的一场灾难,而是一场文化的劫难。这类“批评”一度成为某些批评家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成为“棍棒”的代名词,致使批评界至今仍规避使用这个词。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对“批评”进行正名,试图将“批评”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但我们应该看到,一俟政治文化生态有所变化,这种变文艺批评为政治大批判的模式立马就会死灰复燃,许多靠此腾达的“批评家”无须变脸就可以鸣锣开张、粉墨登场了。 我们需要的是正常的批评,指陈和批判文艺作品中林林总总的思想缺陷和艺术失误。只要不是人身攻击,亮出批判的利剑,大刀阔斧地驰骋在文学艺术的殿堂上,用学术和学理的手术刀来摘除文艺肌体上的毒瘤,保持批判者的本色,唯此才能使批评正常化。当然,批评需要激情,需要引发争鸣,但前提却是需要杜绝“大批判”式的批评文风,使批评回到正确的学术与学理的轨道上来。 不过,在中国的文艺界,一个更加温和的批评术语——评论——开始频繁出现。这三十年来,“评论”甚至已经基本替代了哲学层面的“批评”。于是,文艺界充斥着对一切作品的褒扬。这种风气一俟遇到适合的生存环境,便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严重危害文艺批评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以降,由于消费文化的侵入,阿谀奉承的“评论”开始大行其道,捧杀了作家,捧杀了作品,最终捧杀了中国的文学艺术。看一看艺术品市场的怪现象:假的说成真的、丑的说成美的、恶的说成善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现象比比皆是,这难道不是艺术评论家的功劳?而文学评论家也可以不看原作,只读内容简介,就可以写出一大篇评论文章的现象,早已不足为怪了。“评论”失去了“批评”的锋芒,毫无批判精神可言,跪倒在拜金主义的裙下。没有非难、没有指责、没有吹毛求疵,文艺就没有危机感。当文艺批评成为作家、作品的吹鼓手和抬轿夫,成为金钱的奴仆,死亡的就不仅仅是批评本身,它与文艺作品一起走进了坟墓。 我们倡导正常的文艺批评,但最难的还不是面对强权与文艺的堕落敢于说“不”,而是能够面对自己的朋友和亲人的创作也能够保持批判的姿态。别林斯基临死前对自己培养起来的作家果戈理的严厉批判是批评的伟大典范。果戈理在1847年出版了一本鼓吹恢复农奴制和沙皇统治的小册子,这让别林斯基极为愤怒,并使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奋笔疾书,痛斥果戈理背叛了良知与真理。别林斯基为何如此激动、如此愤慨?就是因为一个批评家的良知和职责让他不得不对自己昔日的朋友发出怒吼。他不能在人民的痛苦和文学的真理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我为中国批评家放弃批评的道德与良知感到悲哀。今天,阿谀奉承的“评论”已经覆盖了大地,却难觅追求真理与良知的“批评”的踪影,这就是中国文艺批评生态的真实现状。 由此我联想到的是,如今中国的批评恐怕更缺乏的是那种对自己同党、同派、同宗、同门、同志、同仁的批评。“党同伐异”易,“挞伐同党”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的“圈子”文艺也是阻碍正常的文艺批评的重要因素之一。殊不知,文艺批评的本质与精魂就在于它永远忠实于对思想和艺术的独特阐释,它的天平永远倾斜在艺术的真理一端,而不受任何亲情和友情的干扰。 如果再不恢复文艺批评的批判功能,我们就丧失了批评之魂。当然,我们不需要“狼嚎”式的“战歌”批评,也不要“莺啼”式的“颂歌”批评,我们需要的是那种建立在科学知识体系上的批评和评论。不做蜷缩在某种指挥棒下的吠者,亦不为带有宗教色彩、放弃怀疑批判精神的批评张目,这应该是批评家遵循的批评法则。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批评家们纷纷抹去了观念的棱角和思想的锋芒,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他们或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成为消费文化的谋利“掮客”,唯独失去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批评风骨。其实,批评家都知道一个常识:如果没有怀疑与批判的精神做导向,没有犀利和独到的批判精神做基础,文艺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当20世纪90年代人们都在高声呼吁“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恰恰丢失了人文学科的灵魂。这是一个“丧魂落魄”的时代,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寻觅那条人文学科的“黄金通道”——在没有批判的年代里寻找批判的武器。“破”是手段,“立”才是根本,试图重建一个有序的批评话语体系,寻觅一种倾向于真理而不屈从于话语权力、追求正义而不臣服于规训的勇气,成为21世纪一代学人的批评之梦。 我们今天的批评要为将来的文艺批评留下历史的底片。当文艺批评抽掉了批判的内涵,变成了一味吹捧的“评论”,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批评死了,而文化也就死了!这其实是一个简单的常识,但要让人们理解它却十分艰难。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它的意涵延展到人类文化的价值底线上来,把人性的诉求和文化的进步作为批评的本义,批判一切阻碍人类文化进步的不合理现象,为建构一个理想的文艺批评体系而努力。不要以为文坛上的“评论”十分热闹,殊不知,它恰恰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失去活力的表征。所以,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才是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要知道,一个社会的进步应该依靠不断洗涤其身上的文化污垢,不断疗治其自身的文化疾病才能健康地成长。 二、“学院派”的“批判理论”与“现代批评”的出路 随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批判理论”成为西方现代批评的重要武器,其领袖人物阿多诺、霍克海姆以及本雅明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政治美学”: 在阿多诺最具挑战性的论点里,他针对当代社会的矛盾,提出了缜密的论证分析,虽然就此而言受惠于马克思主义,但他关注的不是有组织之劳工阶级传统的能动性,而是现代文学与音乐(贝克特、荀白克)里强烈的形式困难和自主性,以寻求反对资本主义的对抗性感受(sensibility)。他和学派里的其他成员认为文化工业会破坏政治意识,并且威胁要吸纳最不妥协的“真正”艺术以外的一切事物。(13) 这种决绝的“批判”意识和姿态几乎成为西方批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批判理论”通过批判社会来提升美学的自我觉醒,对霸权意识形态和媒体操控进行严厉的批判。这一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逐渐为学界所推崇。到了90年代,“伊格顿(Terry Eagleton)指出,批判与批评不同。后者指涉的是位于文本或事件之外的中立有利立场,批判则是在研究对象内部采取位置,试图引出矛盾倾向,并突显其有效特质”。如果这一解释尚不够清晰的话,那么,约翰逊(Richard Johnson)表述得就更加明确了:“我所说的批判是最全面的意思:不只是批评,甚至也不是争论,而是一种程序,藉此可以同时理解其他传统的可能性和禁制。批判牵涉了窃取比较有用的成分,抛弃其余部分。从这个观点来看,文化研究是个过程,是生产有用知识的炼金术。”(14)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陆“学院派”学者纷纷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的缘由。然而这种理论的盛行往往又成为一把批评的双刃剑,利弊都十分明显:对西方“批判理论”的吸纳,一方面使我们能够对西方后现代社会进行有效的批判;另一方面却让我们对中国社会自身的文化弊端视而不见。在批评实践中,“学院派”批评家大量使用空洞理论,并在文章中植入后现代理论家们佶屈聱牙、囫囵吞枣的名词。这些批评家的工作不过是像堂吉诃德那样与风车作战,但却被许多人看作是“横移”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硕果。殊不知,这种“横移”是皇帝的新装,只是没有学者愿意去揭穿事实的真相。因为“学院派”批评家,包括我本人在内,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对时尚的西方理论一窍不通。于是,运用这些西方新理论去评论中国作品的“新批评家”就雨后春笋般出现了,这些“遗传基因”甚至明显地体现在某些“80后”批评家身上。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文艺批评似乎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虚假繁荣的背后,“学院派”批评家开始对作家、作品进行西方批判理论名词的轰炸。这类解读往往很容易被并不懂西方批判理论的中国作家所接受,因为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作家的心灵深处有着世纪末的文化恐惧,一旦有批评家搬弄西方批判理论为中国作家的作品镀上一层“先锋”、“新潮”或“实验”的金箔,作家就欣然接受了这份理论的馈赠,参与了这场“批评术语革命”的狂欢。其实在中国的读者群中,即便是能够解剖“先锋”作品“全尸”的“学院派”批评家也没有领会作家真正在表现什么。况且这种解读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歌德”的层面,很少出现有批判力度的哲理批评。 “学院派”为何会在21世纪突然从文艺批评转向了文化批评呢?追根溯源,一是对文艺创作的失望;二是认为广阔的文化批评更适应“学院派”的学术路径;三是因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没有政治风险。有学者指出: 文化评论是18世纪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产物,也是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兴盛时期的产物。由于市场原则与专业倾向,文化批评家在地位上开始具备独立自主性,而且在媒体、公共舆论的批评与理性论述空间里,拓展对话、辩论及多元思考的余地,将当下的文化生态及其现象当做批评的对象,让读者或听众一起感知或了解切身的文化问题,进而设想其对策或解决之道。从18世纪起,小说就对内在价值、家庭生活、情感伦理、虚拟人物及其共同背景的理解等现代文化现象的向度,以具体写实的语言与再现的方式提出种种形塑组构(configuration)与重新解读(refiguration)的可能性……虽然18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如何操作新闻事件、艺术展览、影像再现,以及“自然”如何日渐荡然无存而成为“工业革命”祭坛上的献祭,都是批评家重点批评的对象,都是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仍有另一个层面,力图采取救赎式的美学政治,以诗去取代已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销声匿迹的宗教——以这种角度进行的“文化批评”,由浪漫主义到新批评,都是某种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15) 而反观中国近二三十年来的文化批评,虽然它在文艺批评界刮起了一股借鉴消费文化理论的批评旋风,但这股旋风并没有对中国文化资本市场做出宏观的理论把握,也没有对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内在价值、家庭生活、情感伦理、虚拟人物”的“形塑组构”进行鞭辟入里的剖析,而是用被“误读”的后现代理论做挡箭牌,去遮掩其批评的空洞和解读的紊乱。这样的批评与美国文化批评有何关联呢?他们失去的正是对工业革命的种种弊端进行深刻批判的批评本质。 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新批评”是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重要一支。这一理论以美国批评家兰塞姆于1941年出版的《新批评》为标志,定义了“现代批评”、“本体论批评”、“反讽批评”、“张力诗学”、“结构批评”、“分析批评”、“语境批评”、“本文批评”、“客观主义理论”以及“诗歌语义学评论”等一系列批评概念,大大丰富了批评的内涵与外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批评”理论进入中国理论界、批评界和文学史界,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观念和文学史观的格局。因此不对“新批评”做出客观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厘清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史上这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化。我们不能只在技术层面上吸纳“新批评”理论,而缺乏对其人文主义批判意识的认识。 无疑,韦勒克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逊于西方任何一位当代文学理论家,他那本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几乎成为文学系师生人手一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该书十分强调以新批评为代表的艺术形式分析的美学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文学性质、功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及总体文学、比较文学、民族文学等各方面的定义和研究,力图廓清文学方法存在的问题。通过大量的资料准备,作者讨论了文学与诸多相邻学科,如传记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的关系,最后建构起自己的一套理论。”(16)为什么韦勒克的文学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有如此大的影响呢?尤其是书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元合一的批评观念与方法,就像灯塔似的引导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因为他的观点和方法不仅适合于欧美文学界,似乎更加适合当代中国的治学语境。这样的理论既注重中国传统义理考据的方法,又旁及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同时也没有通常西方文学理论的枯燥艰涩。更重要的是,其理论的阐释恰恰与这些年中国社会文化结构高度吻合,其对美国资本主义文化发展中的许多弊端的阐释,恰恰成为中国当下文化的一面镜子。可惜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真正吸纳其精华者甚少。 对中国理论界和批评界来说,韦勒克最为精彩的理论无疑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元合一的批评体系。这是提升一个批评家(也是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修养的不可或缺的方法。正像韦勒克和沃伦所说的:“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里欠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17)这段话可谓点到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死穴”。由于学科分工过细,中国文学研究界的这三个领域成为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机构,使得本应该更博学的治学者变成流水线上工匠式的操作工人,在“学院派”的冠冕下做着精致的作坊式的工作。这种学术生态严重阻碍了中国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的文艺批评往往呈现出以下两种模式:首先,“学院派”批评家会从文学史的角度,大量引征文献资料,“掉书袋”成了他们评论文章的主体结构。殊不知,这恰恰背离了文艺批评对于文本应有的独特阐释,使得评论文章被大量引经据典的注释所湮没。我并不反对运用各类古典文献来分析当下的文艺创作,但面对当下文艺作品中那些古人无法遭遇的生活经验,这种“掉书袋”式的批评只能是阉割当代作品中对现实生活的鲜活感受。当然,我并不反对借鉴古人的文学艺术经验,但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文明、文化和文学的变化,对现实问题做出新的读解才是批评的价值所在。我们只有用自己独特的判断来完成批评在当下的工作,才能真正担负起批评家独立思考的批评职责,才有可能使批评起死回生。其次,是那些非“学院派”批评家的评论模式。虽然这类批评家对作家、作品有着较为敏锐的感悟,但是他们的文学评论往往缺乏理论的支撑以及文学史的整体意识,甚至缺乏起码的人文常识。这使得其批评往往停滞在平面化的分析和对作品自说自话的误读中。这些评论家虽有一些才情,却难以将平面化的评论提升到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批评的层面。 此外,针对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重构,“新批评”理论中作家、作品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看法也击中了中国评论家的命门:“不过,作家的‘创作意图’就是文学史的主要课题这样一种观念,看来是十分错误的。一件艺术作品的意义绝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积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18)按照作家的“创作意图”去按图索骥的批评观念与方法,已经成为中国很多评论家的惯性思维。尽管近二十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善,但多数评论家还是习惯首先去揣摩作家写某个情节和细节时的意图。他们不知道批评的“独特的生命”是在批评家的“二次创造”中获得的,对同时代的“大”理论家的看法却很在意。即便那些“大”理论家对文艺评论并不在行,也会有很多的评论家为其批评进行趋之若鹜的“深度阐释”。批评家总是生活在先验的理论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批评弱化的深层次原因。此外,很多批评家不知道作家的“创作意图”其实也是根据某种先验意识形成的。即使他们了解到这一点,他们也会把它视为“深化意图”的理由和资本。因为这些评论家和作家在共同建构着一种只适用于当下的评论和作品,而文艺作品的恒久生命力则被忽视了。回眸几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那些一度被评论家捧红的文艺作品会有一大批被逐出历史的教科书。 不难看出,几十年来之所以“颂歌”流行,皆因中国文艺批评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陋习——评论家习惯于匍匐在作家,尤其是大作家的足下讨生活。仰人鼻息、仰视作品,已然成为一种评论的行规和潜规则。如果说得刻薄些,那就是当今的许多评论家是孵在作家卵翼之下生活的雏鸡,是站在犀牛背上觅食的寄生鸟,是生活在一种体制囚笼中的金丝鸟。 在韦勒克和沃伦看来:“历史派的学者不会满足于仅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观点去评判一件艺术品,但是这种评判却是一般文学批评家的特权;一般的文学批评家都要根据今天的文学风格或文学运动的要求,来重新评估过去的作品。对历史派的学者来说,如果能从第三时代的观点——既不是他的时代的,也不是原作者的时代观点——去看待一件艺术品,或去纵观历来对这一作品的解释和批评,以此作为探求他的全部意义的途径,将是十分有益的。”(19)或许这种批评方法对欧美的历史派批评家来说,是一个并不艰难的选择,而对中国大陆的批评家来说,则是一种奢望。用“第三时代的观点”去看待一件艺术品,的确是可以超越先验的意识形态羁绊,对文艺作品进行客观的评判,但这样的“特权”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因此,克罗齐的著名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便成为许多批评家歪曲和“误读”文艺作品时最响亮的理论口号,也成为许多投机的文化评论家的理论资源。“新批评”的“第三时代的观点”理论为什么没有引起中国理论界足够的重视?其中的奥妙不难理解,因为我们的批评家从来就没有、也不需要文学史的自觉意识与前瞻意识。 中国的当代批评家从来就不要求文艺作品具有的永恒性,而“新批评”的理论则认为: 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相对主义把文学史降为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篇断简,而大部分的绝对主义论调,不是仅仅为了趋奉即将消逝的当代风尚,就是设定一些抽象的、非文学的理想(如新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批评流派的标准,不适合于历史有关文学的许多变化的观念)。“透视主义”的意思就是把诗,把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文学不是一系列独特的、没有相通性的作品,也不是被某个时期(如浪漫主义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蒲柏的时代和华兹华斯的时代)的观念所完全束缚的一长串作品。文学当然也不是一个均匀划一的、一成不变的“封闭体系”——这是早期古典主义的理想体系。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二者都是错误的;但是,今天最大的慰藉,至少是在英美如此,是相对主义的流行,这种相对主义造成了价值的混乱,放弃了文学批评的职责。实际上,任何文学史都不会没有自己的选择原则,都要做某种分析和评价的工作。文学史家否认批评的重要性,而他们本身就是不自觉的批评家,并且往往是引证性的批评家,只接受传统的标准和评价。今天一般来说都是落伍的浪漫主义信徒,拒斥其他性质的艺术,尤其是拒斥现代文学。(20) 因为中国的批评家没有追求永恒的批评意识,所以他们看不到“不适合于历史有关文学的许多变化的观念”。趋奉“当代风尚”成了他们唯一的宗旨和目的。这种流行于英美的相对主义理论被韦氏诟病为“造成了价值混乱,放弃了文学批评的职责”,但是却被一些理论家引入中国后无限放大,成为“学院派”理论批评的滥觞,被这三十年来的文艺理论与文艺批评奉为圭臬。 在中国研究现当代文学的人往往被研究古典文学的“学问家”鄙夷。这种陈旧的“学院派”论调虽然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仍然阴魂不散。殊不知,任何人的研究水平都不是取决于其研究对象,而是取决于他的研究能力和思想深度。韦勒克和沃伦曾指出,“现代文学之所以被排斥在严肃的研究范围之外,就是那种‘学者’态度的极坏的结果。‘现代’文学一语被学院派学者做了如此广泛的解释”,当然也有例外,“在学院派之中,也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捍卫并研究当代文学”(21)。有趣的是,韦勒克对20世纪欧美理论界状况的论述,就好像在描述中国“学院派”研究者的病症。而我们是否要做他所说的那种少数捍卫并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呢?我们是否能够在研究当代作家和艺术家时用自己独特的喉咙发声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韦勒克和沃伦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做的辩护极为精彩,他们认为: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存作家毕生的著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著作可能为他早期的著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的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现存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存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不利的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和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学院派人士不愿评估当代作家,通常是因为他们缺乏洞察力或胆怯的缘故。他们宣称要等待“时间的评判”,殊不知时间的评判不过也是其他批评家和读者——包括其他教授——的评判而已。(22) 也就是说,盖棺论定的研究方法不适用于研究当下的文艺创作,因为研究者的理论和批评本身就是在创造历史,建构有意味的文学史。韦勒克、沃伦所说的那种研究古典文学“十流作家”的现象在中国就是“学院派”混饭吃的科研项目。对那些被文学史淘汰的作家、作品重新大张旗鼓地进行研究,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亵渎。大量的学术垃圾就是由此产生的。 此外,今天中国的文艺界还有一种现象相当普遍,即作家对文学史一知半解以及艺术家对艺术史一无所知。由于中国许多作家、艺术家的文化修养有限,使得他们往往以无视文学史和艺术理论为骄傲,将批评家当作自己的“吹鼓手”和“擦鞋匠”。这一怪现状使得中国的文艺批评也形成了无视文艺发展史的弊病,因为对文艺发展史装聋作哑可以少读些书,这就自然把批评庸俗化和浅表化了。没有文艺发展史的自觉意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就不会深刻。正像韦勒克和沃伦所言: 反过来说,文学史对于文学批评也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文学批评必须超越单凭个人好恶的最主观的判断。一个批评家倘若满足于无视所有文学史上的关系,便会常常发生判断的错误。他将会搞不清楚哪些作品是创新的,哪些是师承前人的;而且由于不了解历史上的情况,他将常常误解许多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批评家缺乏或全然不懂文学史知识,便很可能马马虎虎,瞎蒙乱猜,或者沾沾自喜于描述自己“在名著中的历险记”;一般说来,这种批评家会避免讨论较远古的作品,而心安理得地把他们交给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去研究。(23) 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批评家的通病。换言之,一个好的批评家必须具有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只有以古今中外优秀的作家、作品为参照,批评家才能准确地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而今天的中国有这样的批评家吗? 总之,我在这篇文章中梳理了目前中国文艺批评界出现的种种怪现状,并在理论上分析了造成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可以说,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已经极度堕落,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因此,重建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多元文艺批评体系是目前刻不容缓的时代诉求。 ①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320—321页。 ②参见丁帆、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3页。 ③邱述德主编《英语学习与交际大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30页。 ④⑨雷蒙·威廉士:《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5页,第75—77页。 ⑤⑥⑦⑧⑩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第25页,第81—82页,第313—314页,第93页。 (11)(12)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李存捧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99—200页,第262页。 (13)(14)彼得·布鲁克:《文化理论词汇》,王志泓、李根芳译,台湾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77页,第78页。 (15)廖炳惠编著《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51页。 (16)王治河主编《后现代主义辞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667页。 (17)(18)(19)(20)(21)(22)(23)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页,第35页,第36页,第36—37页,第37页,第37—38页,第38页。标签:文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批判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