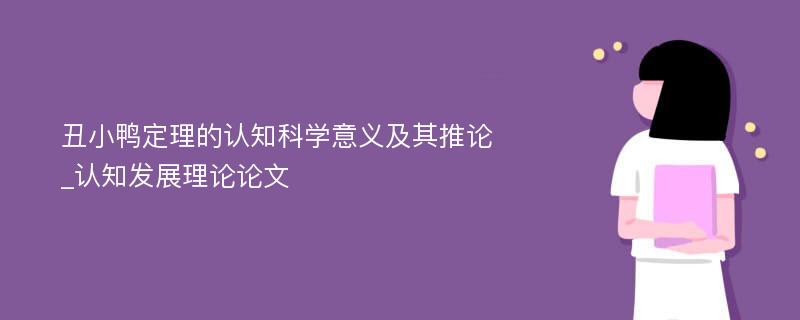
丑小鸭定理及其推论的认知科学涵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科学论文,推论论文,丑小鸭论文,定理论文,涵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9 O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13(2006)04—0049—05
一、指数爆炸与勃瑞姆曼极限
地球上的认知能力资源(头脑资源+计算机资源)是非常有限的,初步估算其总量不超过一个勃瑞姆曼极限10[93]bit。[1] 而解决任何一个实际问题所能投入的认知资源量,要比这一极限小很多。
另一方面,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且平凡的问题,所消耗的认知资源就可能以很快速度趋于无穷,这在认知科学中称为指数爆炸。例如,一个围棋盘有361个交叉点,每个点至少有三个状态(黑子、白子、没有棋子,这里未考虑提劫的复杂性),那么所有可能的棋局数目不小于3[361],这个数远大于勃瑞姆曼极限(因为3[194]≈10[93])。显然,对于指数爆炸系统的认知,绝不能采用无限搜索和穷举的办法,必须寻找“智能化”的投机取巧方式。而生物认知系统一旦在进化中找到了这一方式,则对于非指数爆炸的系统,也有可能广泛运用之。
也就是说,生物认知系统天生就是一种规避指数爆炸的智能系统。它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决不像平面镜子那样忠实可靠。恰恰相反,由于日常事务大都是指数爆炸的,所以认知系统只能以非常简约的方式力图近似地描绘客观事物,认知就相当于对客观事物的“原文”所作的某种“摘要”。
认知科学已证明,限制分类深度,将某些近似的东西看作一类,即有意忽略一类事物相互之间的差异性,是生物认知系统规避指数爆炸的方法论基础。例如青蛙眼睛只对运动物体起反应,对静止物体是看不见的,即使是近在咫尺的食物。这意味着对青蛙而言,静止的事物是同一类事物。
也就是说,判断事物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是认知过程最基础的环节。那么生物认知系统根据什么来作出这种判断呢?
二、丑小鸭定理
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分为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例如,“现在正在下雨”是事实判断,这种判断的正误取决于是否符合后验事实;而“下雨对缓解旱情很有利”是价值判断,其正误取决于是否与某种既定的价值观相符。
认知(Recognition)的基础是一种“再识别”(Re—cognition)。而识别要求把对象与其他对象进行区别。
那么,怎样判断两个对象相同或不同呢?显然,如果按照完全客观的标准进行事实判断,那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即“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仅有类似玻色子或费米子的量子统计对象才是相同的(而这在自然界中属凤毛麟角、“测度为零”)。然而,这种严格的分类标准看似客观、科学,对于生物认知系统却是完全不可操作的,因为以这样的标准来认知任何事物,都会被淹没在指数爆炸的汪洋大海之中。
既然生物认知系统的本质是回避指数爆炸的,那么对事物的分类就不能过细,即往往把一类近似的事物看作相同的,这称作模糊聚类。所以,认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事物间的“相似性”。
认知科学历史上曾有过类似物理学史上莱布尼茨理想的看法,即认为模式之间的相似性存在一个普遍的判断准则,是一种事实判断,它与人的主观偏好无关。然而,20世纪60年代美籍日裔模式识别专家渡边慧证明了“丑小鸭定理”。该定理认为“丑小鸭与白天鹅之间的区别和两只白天鹅之间的区别一样大”。也就是说,世界上不存在分类的客观标准,一切分类标准都是主观的。渡边慧举了鲸鱼的例子说明该定理[2]8—9:按照生物学分类方法,鲸鱼属于哺乳类偶蹄目,和牛是一类;但在产业界,捕鲸与捕鱼都要行船出海,鲸和鱼同属水产业,而不属于包括牛的畜牧业。分类结果取决于选择什么特征作为分类标准,而特征的选择又依存于人的目的或价值观。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幼雏,在画家眼里,丑小鸭和白天鹅的区别大于两只白天鹅的区别;但在遗传学家眼里,丑小鸭与其父亲或母亲的差别小于父母之间的差别。
喜鹊和乌鸦也是如此。就人的喜好来说,喜鹊的叫声和外形总是给人带来愉快的联想,而乌鸦则正好相反。所以,人们喜爱喜鹊而讨厌乌鸦,把喜鹊看成是喜鸟,而乌鸦是丧鸟,归于完全不同的类。但在自然界中,喜鹊和乌鸦不仅同属于生物分类学中脊椎动物亚门的鸟纲、鸦科,而且聚居一地的喜鹊和乌鸦在面临外来猛禽的入侵时,还会携手拒敌,因此也可看作是同类。
按照这一思路,还可举出许多类似实例。一把锁在普通人眼里,只有这把锁的几个钥匙被看作“一类”;但在某些开锁高手眼中,由于其具备用铁丝或木棍开锁的技巧,所以铁丝、木棍与钥匙都是“一类”。又如,在免疫过程中,医生为需要免疫者注射经过灭活的疫苗。在医生和免疫者看来,疫苗与病毒原体不同,疫苗不会像病毒那样引起强烈的病理反应;但对免疫者的生物免疫系统来说,疫苗具备病毒原体的“全部重要特征”,所以想方设法制造出能识别这些特征的“抗体”。
简言之,选择什么准则将事物划为一类或异类,属主观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
三、丑小鸭定理的哲学背景和语言学例证
我们认为,丑小鸭定理的成立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并与如下两个普遍原理有关:
(一)同维异维原理:两个事物总有相同属性,也有不同属性。从相同属性看过去,它们是一类;从不同属性看过去,它们是不同类。人们的价值观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属性重要性的差异上。例如生鸡蛋和煮熟的鸡蛋,外观属性一样但内在属性不同。画家看重外观属性,所以在他们眼里这两个鸡蛋是一类;餐馆里的食客看重内在属性,在他们眼里这两个鸡蛋就不是一类。
(二)(差异的)量变质变原理:随着对事物认知深度的增加,人们对事物的分辨力也随之提高。在低分辨力下相同的某个属性,在高分辨力下就可能不同。认知分辨率的提高会使差异化属性个数增多,无差异属性个数减少。即使每个属性的重要性不发生变化,其对事物差异的总体评价也可能不同,这是量变质变原理在差异认知上的反映。
丑小鸭定理对生物认知系统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它要求生物不能以同样的敏感性对事物进行分类,而要根据价值大小的不同,对不同事物给以不同的分辨率。例如,虽然不同语言对事物的表述能力平均来说不相上下,但基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语言对某些特定事物的分辨率大不相同。在对亲戚身份的识别上,汉语具有最高的分辨率,叔叔、伯伯、舅舅、表叔、堂叔、姨夫、姑夫等等区分很细;但欧美语系在这方面的分辨率就差了很多,如英语对上述“不同的”男性长辈亲戚统一用uncle来表示。这可能是因为欧美地广人稀,亲情相对淡薄,身份不同的亲戚同时相聚的机会不多,所以从降低认知成本的角度,没必要区分太细;相反,中国人多地少,中国人的亲情观念相对于欧美民族要浓厚得多,亲戚交往频繁密切,不同身份的亲戚同时相聚在一起的机会很大。这种情况下,为避免混淆和提高沟通效率,对亲戚身份进行细致区分就十分必要了。在中国,著于公元前的《尔雅》一书中,有关家庭各种关系亲属的名称就有一百多种,其中多数在英语中没有对应词语。
据语言学分析测定[3],英语描绘基本颜色的术语有11个,分别是黑、白、红、黄、绿、蓝、褐、紫、粉红、橙和灰。而巴布亚新几内亚达尼人的语言中,只有两个描述基本颜色的术语,他们只是简单地对明和暗作出了区分。
类似的还有爱斯基摩人对汽车和雪的描述。对于跑车、轿车、卡车、赛车、拖车、翻斗车等等不同的车,爱斯基摩人只用一个词(汽车)来描述。相反,对于其他语言中不细致区分的雪,爱斯基摩人却有20多个词汇来精确描述,他们对雪的分辨能力比使用其他语言的人要高明得多。事实上,人们眼中常见的雪并非完全相同(丑小鸭定理),深厚的积雪可能由一层层不同的雪组成,每次下的新雪的密度、厚度不一,再加上风的吹袭、太阳照射、温度变化,便形成一层层特性不同的雪层,各雪层之间因不同特性而有不同的结合力,这些对雪的承载力大小以及是否会发生雪陷、雪崩是至关重要的判据,需要细加区分。而且,极地爱斯基摩人通常住在用雪建筑而成的“冰屋”中,屋中既不能生火以免把“房子”烤化,也不能过于寒冷(屋外的温度可低至零下50多度),所以通过墙壁上雪的不同形态判断屋里的温度也非常重要。所以,对雪的这种高分辨率认知,对像爱斯基摩人那样天天和冰雪打交道的民族是十分必要的。
四、不确定条件下丑小鸭定理的推论
认知系统在不确定条件下的模糊聚类,也有将概率不同的事物归并为一类的倾向,以回避指数爆炸。特别是认知系统通常会推定某种微小概率的事件肯定不会发生(即认为小概率事件与零概率事件是一类),这是丑小鸭定理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一个自然推论。
对交通事故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我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有10多万,相当于一场惨烈的战争。[4] 对这些事故进行分析,除机械故障和道路原因外,大致可归纳为三类认知差误:一是注意力不集中,例如开车打手机;二是认知疲劳,例如连续开车10多小时;三是忽略了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例如在视野不良情况下超车或拐弯时,未考虑对面或后面有高速来车的可能性。其中第三种原因与丑小鸭定理的推论有关。
事实上,在不确定环境中,认知系统不可能每次都追求绝对的(百分之百)可靠性,往往还要兼顾认知效率。例如,车速快会增加交通事故的概率,但如果所有路段都限速在30公里/小时以下,交通事故固然会少很多,但交通效率却没有了。
中央电视台关于野生动物的“狂野周末”栏目有过这样的镜头:热带雨林里一只鸟栖息在树枝上,树枝旁边盘绕着一条色彩斑斓的大蛇。蛇一动不动,鸟在无忧无虑地鸣叫。突然蛇猛地一扑咬住了鸟,而鸟在几经挣扎后成为蛇的美餐。生物学家对鸟的悲剧给出一个极其简单的解释:鸟的眼睛只对活动物体敏感,看不见静止不动的物体。
鸟(以及青蛙等小动物)为什么对静止物体视而不见呢?显然是为了节约认知成本。事实上,要对静止的环境进行辨识,对鸟而言是一个指数爆炸的认知问题。要达到这样的认知深度,必然要极大消耗鸟的认知能力资源,这样鸟的大脑以及躯干就需增大很多倍,而超过翅膀的承载能力。
另一方面,活动物体对鸟类的生存价值要远远大于静止物体。鸟的食物主要是飞虫和爬虫,其运动特征很容易识别。鸟的主要天敌(老鹰)也是在运动中捕食的。而守株待兔、静止不动的蛇,虽然对个别鸟有很大威胁,但就鸟类而言,被蛇捕食仍然是小概率事件。生物认知系统不去刻意防范小概率事件,在整体上就回避了指数爆炸的困境,虽然个别个体的失败在所难免。
在稳定环境下将某些习惯固化,也是忽略小概率事件从而降低认知成本的一个方法。认知科学中有一个著名的寄生蜂实验。[2]272 寄生蜂繁殖时先在地上挖洞,再捕捉其他昆虫的幼虫麻醉后放入洞中,然后寄生蜂在幼虫旁产卵,孵化出的寄生蜂幼虫便以被麻醉的幼虫为食。在此过程中,研究者特别注意到寄生蜂的一些程式化行为——寄生蜂捕到幼虫拖回洞时,先将其置于洞口一定位置,然后检查洞内无异常时,再把幼虫拖进洞。此时若观察者暗中将幼虫移动几厘米,则寄生蜂从洞里出来后并不直接把幼虫拖进洞,而是重新置于洞口特定位置,再次进洞检查。实验者曾用这种方法让寄生蜂重复这一机械动作达40次之多,表明寄生蜂的这一行为“不过脑子”,已是一种习惯的固化,其意义在于节约认知成本。显然,行为固化忽略了类似被人类实验者蓄意欺骗这种小概率事件。
认知科学认为,对小概率事件的忽略是合情推理的。其合理性在于,事物的少量特征有时足以构成认知该事物的充分条件(在某种满意的可靠性下),而生物在进化中恰好抓住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特征。如狼通过嗅觉认知自己的孩子,小鸭通过“印痕”识别自己的父母,等等。虽然,进化过程中不乏失败的个例,且提高认知深度能够减少失败概率。但是,生物必须在有限资源、有限时间下实现生存目标。目前代代相传的认知习惯可以被认为是在进化过程中,认知系统平衡了认知效率和认知成本的一个较好的方案。
五、生物价值观的固化与再塑
价值观通常可分为随基因遗传的生物价值观和不随基因遗传、后天形成的社会价值观。前者往往在长期进化中固化为某种特定行为、结构或偏好,如认为甜的食物比苦的食物好吃,就是千百年来有毒野果的苦味在基因编码中的体现;后者则在后天经历中形成(也包括后天教育,如“八荣八耻”)。限于篇幅,本文仅对生物价值观进行分析。
(一)生物价值观的结构固化
赵南元在《认知科学揭秘——认识科学与广义进化论(第二版)》中,系统建立了广义进化论理论。其基本思想是,生物的认知系统是长期适应环境不断进化的产物,不同认知系统的差异往往能在主体与环境的相互适应中找到依据。例如对于“树为何不长眼睛?”广义进化论的解释是[2]226—227:
1.眼睛对树的生存价值很小。假设树“看见”有人拿着斧头、锯子朝它走来,它也无法逃走。
2.即使树长了眼睛,也由于自身不能运动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距离感和立体感(有严格的动物实验为证),甚至在眼睛不能自主运动的情况下,由于无法区分焦点与背景,缺少运动视差,眼睛可能也“看不见”东西。
再如蝙蝠的视觉很差而超声回声系统灵敏,是因为其长期居住在阴暗的山洞,视觉的分辨率低且认知成本高,而超声回声则具有优良的时间分辨率,可以构造成高速定位系统。蝙蝠飞行速度极快,为了追捕食物、躲避天敌和障碍,在视觉不能利用的黑暗中,只有采用高速、可靠的超声回声定位手段。如果用普通声音定位,就很容易受到自然界其他声音的干扰,排除这种干扰(即滤波)就要消耗时间而达不到高速认知的目的。因此,虽然超声系统消耗资源很大,蝙蝠在长期进化中仍不得不选择这一系统(由于超声回声不在五种通用感知平台范围内,所以有时也称为“第六感”)。
实际上,认知系统分辨率是其效能的重要指标。已经发现,许多动物都有极高分辨率的认知手段,例如鹰对地面活动物体的视觉、鲨鱼对血腥的味觉(鲨鱼可侦测到水中百万分之一含量的血液并追踪其浓度梯度)、狗对气味的嗅觉、蝙蝠对障碍物和猎物的超声回声定位系统等。同时,动物大多五官残缺不全,以此来节约认知成本。如蛇是聋子且几乎是瞎子,猫头鹰几乎没有嗅觉等。显然,这是生物价值观在认知系统中的某种固化效果。
按照类似思路,还可以大致解释许多用其他理论难以解释的进化现象。例如,人以及所有偶蹄类动物为什么不长三只手、三只眼睛?因为很显然,在独手或者独眼上增加一只手或眼,功能增加很大,前者增加了搬动物品以及诸如旋转饮料瓶盖等对生存极有价值的功能;后者则增加了立体感、测距以及提高视觉分辨力的功能。然而,在两只手和眼的基础上增加第三只,虽然能为人带来一些功能的增长,例如在抱住一个东西的同时拿另一个东西,但这一功能的增长与前一种相比,质与量的价值都小得多,这在经济学上称为边际效用递减。与增加第三只手、眼的成本相比较,自然两只手、眼的选择是最经济的。这一事实的背后显然蕴藏着深刻而丰富的进化价值判断。
为什么章鱼会有很多只手呢?因为章鱼以捕食其他小鱼为生,手越多越有优势,呈现经济学上的另一种规律——边际效用递增。当然多增加一只手的边际成本也在递增,章鱼手的数目最后决定于其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的相称。可以想见,在食物丰富、被捕食者反抗力不强的水域,章鱼的手会较少;而在食物缺乏、被捕食者反抗力较强的水域,章鱼的手会较多。这与实际观察结果一致。
为什么蜜蜂会有5只眼睛(其中3只长在头顶,2只长在头正面)?这也与蜜蜂的生存模式密切相关。据英国《镜报》(2005年11月)报道,蜜蜂是非常勤劳的生物,一只蜜蜂为产出五百克蜂蜜,需要在蜂箱与花朵间来回飞行一千万次。显然这种生存模式要求对花粉极高的认知效率。如果眼睛全部长在正面,对飞行有利而对认知花粉不利(采花粉时正面的眼睛需要闭住);反之,如果全部长在头顶,飞行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进化的结果是在正面和头顶都有眼睛。
(二)生物价值观的行为固化
生物价值观不仅能固化于生物体结构,还能体现于其行为。例如狗与猫合作性的差异[2]133:按照多数人的常识,狗是比较“忠诚”的,而猫是“奸臣”。这是由于狗与猫的食性不同。犬科动物通常捕食比自己更大的动物,像狼群捕食斑马、野牛、野鹿等,只有通过集体合作才能捕到食物分而食之;相反,猫科动物则是单独捕食比自己弱小的动物,如果旁边有别的猫,只是增加了竞争对手。因此,狗的合作性格在进化中得到发展,猫的“独吞”(不合作)性格也在进化中得以固化。
(三)生物价值观的第三种固化:可视化相似
外观相同的两辆汽车,人们通常认为它们是一类;一束鲜艳的玫瑰花,人们很难想象一朵与另一朵的不同;对于陌生的美女,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会有好感,等等。人们的某些价值观似乎先天被锁定在相同的方向上,不受后天经历的影响。而从认知科学来看,这种先天锁定的价值观往往出现在可视化的认知框架下。换句话说,哪些东西看起来(或听起来、闻起来等)是可视化的,哪些不是可视化的,本身也是固化价值观的一种反映。
(四)生物价值观的后天再造
生物在进化过程中,虽然一部分价值观在结构、行为及认知可视化方面得到固化,但仍有大量的价值判断是可塑性的,受到后天环境变化或人为训练的极大影响。例如,苍蝇原是与垃圾腐物为伴的,但澳大利亚因为特别干净,苍蝇所爱好的“传统环境”——脏与臭,在那里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不见了“传统型”苍蝇。不过,苍蝇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找不到赖以生存的垃圾和腐物,也就不得不转而飞向草原与森林,并以那里的植物汁液为食。久而久之,它们的生活习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具有了蜜蜂般的传播花粉的功能。
就自然价值观而言,普通人对猴脸的分辨率远低于对人脸的分辨率,但经过后天训练的动物学家或饲养员则不然;同样是对人脸,职业画家的分辨率也要高于一般的人。
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了人际关系的一个著名学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古今中外学者大都认为,这一伟大思想的普遍性价值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历史时空的藩篱,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准则(据说十字军东征时也援引过这句口号)。但是,我们同样注意到,孔子从来没有说过“己所欲,施于人”之类的话。很有可能,孔子凭借其卓越的洞察力,已经发现了“己所不欲”的先天固化特征和“己所欲”的后天再塑特征,所以明智地没有对“己所欲”问题作过多的探讨。
收稿日期:2006—09—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中国股市的挤出效应及其引致价格暴跌风险的研究”(03SJA79002)的部分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