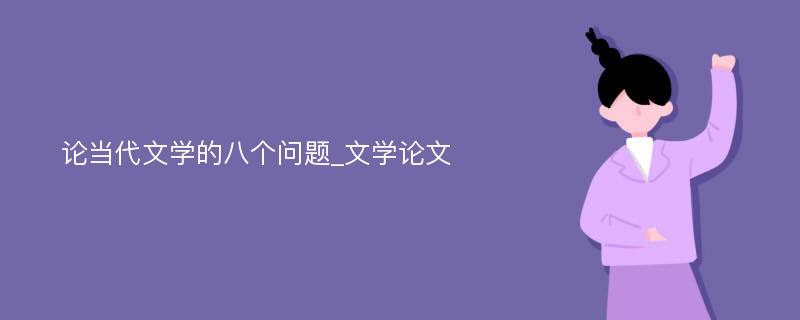
当代文学八题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八题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在还没到出大作品的时候
郜:蒋先生,您平时对当前的文学创作很关心,这次又参加了92-93年度上海长、中篇小说评奖活动,集中看了不少作品。今天能不能谈谈您个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一般印象?
蒋:这次评奖,我觉得我们的小说创作整体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与历史上真正一流的大作品比,还有一段距离。我一直很困惑,在我们国家,群众对文学的期望很高,政府也对文学鼓励有加,社会上设立的各种文学奖名目繁多,大家都希望产生出大作品,为什么就是没有大作品出来?我觉得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基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精神状态不够高,精神面貌不够好,还不到出大作品的时候,没有大作品,不能单纯地责备作家,而应该面对整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素质,进行一番冷静的思考。急是急不出来宏篇巨制的。历史上出现大作品的时代,精神状态都很高涨。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作家,即使当时客观的社会生活很不理想,但他们自己总是表现出强烈的追求与崇高的企慕。所谓发愤著书,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状态要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四人帮”对人对文艺的摧残,确实是创痛剧深。我看,到现在为止,我们在精神文化上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作家在其他方面也许可以说是解放了,但是并没有因为外在的解放,马上就获得了内在的充实和自由。这也许是没有大作品的根本原因。
郜:过去对精神文化的摧残,本质上是人的自我残害,其后果并不是一下子就能看清,就能医治好的。在精神文化的深层,我们也许只能慢慢地去认识去治愈这种历史性的创伤。
蒋:你说得很对。以往破字当头,许多传统的好东西,包括真善美的信念,都一齐破掉了。许多作品,写得固然很不错,但是如果要追问一下作家写这些究竟要告诉人们什么,往往就问不出个所以然。这些作品中作家的精神内核,或许本身就很暧昧,是一件空的东西。比如余华的《活着》,许多人都叫好,我也觉得确实写得很动人,给我的震撼就很大。但是读过之后,静而思之,又觉得很茫然。好像作家写了那么多悲惨的事件之后,并没有说出个什么。整个小说,是一部叫人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的空心的作品。当然,这也许正是余华的特点。他的特点,就是很真诚地写出了我们现代人面对这么多的苦难情景,主体精神上竟然不知所措,因而陷入了一片虚空。这不就是暴露一个文化时代精神上的匮乏吗?问题是,暴露出这种匮乏之后,作家还能干些什么?还应该干些什么?这就不是像《活着》一类的作品可以回答的了。
郜:这最终关系到我们这个时代作家本身的精神素质问题。您刚才讲的历史上出大作品的时代,固然不可一概而论,但是从作家的素质方面看,凡是大作家,都无不以他们自己的写作,反抗各种虚无,竭力修补各种文化上的破损。他们的作品,都是一种价值的积累,信心的积累,都是一个时代甚至文明精华的总结。
蒋: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和文学状况来说,我看主要问题恐怕还是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修复一种传统,恢复这个传统内在的精神气脉。这项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许我们今天的作家,都还只是过渡性的。他们的重要性,他们在历史上的神圣的位置,也许就在于这种过渡性。我说这些话,并不是散布一种悲观情绪。我倒是真诚地鼓励我们的作家在这个过渡时代尽自己的努力最先看到下个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曙光。我想,我们一次一次地评奖,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我们作家的信心,恢复作家自身应有的神圣的使命感。评奖当然是一种外力,关键还在作家自身。
二、我们在语言上真是愧对前辈
郜:我们刚才谈了一些比较抽象和一般的问题,最后把这些问题交给作家,是很合适的。这些问题从创作中反映出来,也只能在创作中一点一点去克服。现在蒋先生是不是谈一些具体问题,比如语言问题?
蒋:我们作家的语言,许多还不够纯正,不够美,缺乏汉语言应有的光彩。当然,语言问题绝不仅仅限于作家,也是我们整个时代和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但作家的语言不纯正,不美,说明这个大问题的严重性。作家应该是一时代一社会运用语言最好的那一批人。“五四”时期那批作家和学者,像梁启超、鲁迅、胡适、王国维、顾颉刚、罗常培、陈寅恪,他们的语言多好!可到了今天,我们的作家在语言上还树不起来。这真有点愧对前辈了。《四牌楼》的语言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有些地方往往暴露出松懈和散漫,语言背后的底气总显不足。王安忆的《文革轶事》,也不错,作家在语言上的探索精神也很可贵。但是她的探索是不是已经很成功了?我觉得还不必早下结论。王安忆的语言很适宜于她那种带有浓厚思想兴趣的叙述,但是这种叙述对语言的运用,有时叫人读得很累,烦不胜烦,语言本来具有的轻松明净没有了,我们好像一下子钻进了语言的牢笼。还有王小鹰的《我们曾经相爱》,我不知道你对她的语言有什么感觉。
郜:不能说不好,但总是缺了点什么。无意之中在迎合社会上一般水平的语言,没有一个提高和锻炼的过程。顺手写来,看似行云流水,但是仔细一回味,就觉得驳杂不纯,是一种溱合性的语言,水份不少。我觉得这也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在许多小说中,我们都有这种阅读上的遗憾。
蒋:我同意这个判断。还有李锐的《旧址》,也很不错的。我看了前半段,觉得作家是花了功夫,也有相当的语言功底,但是读到后面,就差了。前面是一杯浓茶,后面就是变淡了的茶水。语言中的底气还不厚,缺少充沛的活力,所以不能一贯到底。我们谈语言,并不是谈一种抽象的语言。语言的生机和华美自有一种文化的衬托,二者互为表里。语言的松懈、散漫、随便、媚俗、驳杂不纯等等,说到底,还是由于文化底蕴的衰萎不振。
郜:也有另一种极端。有的作家干脆偏离流行的语言常规,在小说中引进大量的俚言俗语,以此激发汉语的生命力。比如何顿的《生活无罪》,就充斥了长沙的方言,还有黑社会的切口粗话,确实够味儿,也自成一体。我看何顿的特点,决不仅仅在于他把个体户和民间底层社会写得活灵活现,还在于他写这个社会时,直接运用了原来就属于这个社会的语言。我们这些习惯于生活中的流行语言的读者,一读之下,觉得有力道,够味儿,也很刺激。何顿的观象当然不是孤立的。刘庆邦、杨争光、莫言等等,都努力要在语言上出奇制胜。但是语言的魅力,也不能光靠这种出奇制胜。俚言俗语要写,正常的语言规则要偏离,但是不能忘记语言的毛病并不只是在语言的平面。如果一味要在语言平面进行这样那样的“陌生化”、“颠覆”、“革命”,奇则奇矣,终归不是治本之策。弄到文不雅训的地步,反而会害了语言。
蒋:语言问题最终还得由作家来解决。我们这些不搞创作的人讲这类问题讲得太多了,也许就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痛。
三、文学应该始终属于民间
郜:80年代活跃过的一批重要的中年作家,不少现在已经搁笔甚至暂时放弃了写作。但是也有许多那一代的作家,比如王蒙、刘心武、张贤亮、陆文夫等,他们的创作仍然贯穿到90年代,有的似乎越到后来,笔力越健。不过,经过80-90年代经济文化的转型,这一辈作家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心态都作了相当大的调整。当然,也有一些老作家明显陷入了重复自己的痛苦处境,时时流露出作为80年代的文学主将在世纪末所特有的悲凉心理与历史沦桑感。对这一辈作家,评论界一度对他们有些冷落,现在好像又慢慢开始注意起他们这一代人特殊的历史位置和创造潜力了。
蒋:这一辈作家其实大多数也不过60岁左右,还谈不上老年,有些人身体精力俱佳,正是做最后冲刺拿出自己一生总结性的作品的时候。不应该总是留恋80年代出现的文学繁荣,还是要面向未来。记得我们上次曾经谈到刘心武在《四牌楼》中流露出来的沦桑感和悲凉感,无可奈何的命运感,当然,还有对文学、对作家、对写作价值的平实冷静的领悟。你说刘心武的心态转换,在80-90年代中国作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我很赞成。这里面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作家一定要通过自己潜心的写作,摆正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
郜:90年代的文学,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弱化和淡化。作家不再漂浮在政治口号或某一流行思潮的平面,而是努力回到民间,在民间社会和民间性的生活世界寻找创作的灵感。这种创作取向使90年代的许多作品比起80年代来,更趋厚实和沉静,同时也因此不再具有那么强烈的时效性和轰动效应,作家在社会中的位置似乎因此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蒋:作家不应该怕自己不被重视。其实被重视,被捧着,对创作一点好处都没有。现在经济文化的转型使整个社会不像以前那样重视文学,我看是好事。人们喜欢文学,应该是出于一种自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宣传介绍。文学应该始终属于民间。我也主张中国作家真正回到民间社会去,回到他自己切身体验的生活当中去,靠一种民间化个性化的写作参与社会生活。我对你们讲的民间化还不太清楚。但是如果真有这么一股趋势,那是文学的希望所在。张炜的《九月寓言》算不算这种民间化的作品?
郜:《九月寓言》是典型的民间化作品。它是用民间的情和意来讲述民间的生活世界。我们过去习惯于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去审视一部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社会信息,所以对《九月寓言》这种民间化的作品,一开始阅读起来,可能还有点不大适应。
蒋:如果换一个角度和价值立场,就好懂了。
郜:的解如此。
四、文化部门的市场意识还不够健全
蒋:不过我看“民间化”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的作家渴望回到民间,因为那里有他的家园和根基。比如张炜,张承志等作家,还有《最后一个生产队》的作者刘玉堂。但也有的作家面对一个日益稳固的民间,反而会发惊。他失去了以前居于庙堂的荣耀,对民间这个新的生活世界又不熟悉,不信任,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把回到民间,看成是前途未卜的“下海”。这也反映了他们对作家民间化的偏狭而庸俗的理解。这种理解已经不是文学性的了。
郜:是一种很现实的算计和筹划。
蒋:我不赞成“下海”。下海的结果,无非多一个商人,少一个作家,在文艺部门贯彻市场经济,并不等于人人下海。关键是我们的作家必须靠自己的写作劳动,靠自己的作品,去接受市场的挑战,就像30年代鲁迅、巴金那些作家那样。那时候,大家都很自然地把作品当作一种商品,当作一种生存竞争的方式,好像谁也没有考虑是否下海的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个“海”,那么作家和普通老百姓都在海中,他并没有什么下和不下的问题,没有什么特殊性。目前的问题,恐怕还是我们的学术文化出版发行渠道不够畅通,讲是讲搞市场经济了。实际上许多地方都没有上轨道。许多出版部门的市场意识还很薄弱,不了解读者的阅读需要,只知道想当然地出一些自以为可以赚钱的书,而一大批有质量的,出了也未必就一定赔本的学术文化著作,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另外,稿费制度一再呼吁要改革,至今好像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些现象其实都反映了目前这些部门市场经济的不健全。
五、“留学生文学”会一步步地有所提高
郜:我发现许多留学生文学的作者都是“老三届”,他们的作品确实融入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生活感受和文化景观,多维度多层次地折射出一代人的经历和灵魂。问题还是这些作者本身的素质。我们往往看到,在这些作品中,尽管反映的生活异常新鲜新奇,但作者流露的情感和认识问题的方式,总是似曾相识。往往人在澳洲和美国,心态和思想水平似乎还滞留在国内,这就很难有思想内核和生活范围真正的突破与创新,整体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本世纪初直至20年代中国留学生关于海外生活的那些作品。
蒋:你刚才提到的老三届问题,我看的确存在,尽管留学生文学的作者未必全是老三届。有些老三届,在国内感到没有出路,以为国外就有。但国外的出路主要是谋生赚钱,所以由此形成的作品,文化起点不可能很高,也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作者,我看并没有因为见了新世面,一下子就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自身的局限有时确实很难打破。比起十九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留学生文学,像梁启超、鲁迅、苏曼殊、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人的作品,那是要差一大截。起点不同,追求也不同。鲁迅那一辈人出洋是要救国救民,现在人出洋,主要是讨口饭吃,救自己,所以一般来说,格调都不甚高。这次王周生的《陪读夫人》,写的不单纯是谋生问题,还突出了中西方生活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差异,突出了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尊严问题,作者写这些,又总是和自己切身的生活经验相联系,所以比一般的同类作品,要高出一筹。我看随着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生活地位的提高,随着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生活地位的提高,随着他们渐渐进入西方国家的高层次文化,冲破打工和做保姆的生活局限,留学生文学会有不断的提高。
六、“新历史小说”不能简单地趋新
郜:这次参加评奖的好几部作品,像《旧址》、《阴阳关的阴阳梦》、《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凝眸》,都可以归入“新历史主义小说”一类。这一类小说共同的特点,是通过对我们熟知的历史进行再叙述或者说重新叙述,打破以往文学中教科书式地演绎历史的旧框框,把文学的灵性注入尘封的往事,同时也从历史中吸取文学灵感。“新历史”与前几年热闹一时的“新写实”几乎同时出现,至今似乎仍然有影响较大的作品不断产生,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刘震云的《故乡相处流传》,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新历史小说。
蒋:历史小说和一般小说不同,首先在于它要有“历史”。没有历史真实,就谈不上历史小说。我觉得“新历史小说”的出发点也许正是要追求一种以往历史小说所没有的历史真实性。当然,所谓历史真实性,并不是要求文学家们像历史学家们那样,用翔实的史料“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但是,另一方面,历史小说在整体神韵和历史感上,又必须和真实的历史相契合,不能太离谱了,不能一点准备也没有,光靠一点捕风捉影的历史知识就大做其历史小说。这里的问题很复杂,我看的小说不多,不好妄评。“新历史小说”的出现也许是件好事,各人情况不同,风格互异,我觉得不应该轻率地干涉作家。托尔斯泰写拿破仑,写法俄战争,就没有按照当时俄国和西方历史学的一般观点去写。他没有在拿破仑是伟人这一点上做文章,而是把他写成一个丑角。写库图佐夫,也不是那么神奇,那么指挥若定,而是一个很平庸的将军,不过偶然之间不自觉地执行了历史和人民的无声的命令,因而成为胜利者。托尔斯泰突出了历史本身的规律,突出了人民的作用,人民的伟大,相反把那些一心要做伟大的人写成玩弄历史最后也被历史所玩弄加小丑。《静静的顿河》写历史也写得很了不起,它没有把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简单化。他写了革命,更写出了革命波浪底下人民生活巨大的潜流,因此显得有历史的深沉和人性的壮阔。我希望我们的“新历史小说”在新的条件下也应当达到这些俄罗斯大作家曾经达到过的高度,不能满足于轻易获得的那顶“新”的桂冠。
郜:在这方面确实应该引起注意。“新历史小说”作家应该不断地追问自己究竟:“新”在何处。跟历史开玩笑也是“新”,但这种“新”的意义是有限的,可能只在一种破,即破除以往同样简单化的历史观。现在有些历史小说,似乎太偏爱把历史加以寓言化和传奇化的处理。历史在这些寓言和传奇式的小说中确实获得了某种崭新的形式,变得简化和轻化了,但是同时,也回避了历史的复杂性和深重性。历史好像变得很容易去写。中国古代的历史小说,确实都有很强的寓言和传奇色彩,但是如果仅仅追求寓言和传奇色彩,仅仅在似是而非的历史之上涂抹一层所谓的文学性,那也不是传统历史小说的正传。
蒋:历史本来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灰姑娘吗?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作家面对生活和历史时有没有直面人生挥洒历史的精神力量。以往写历史的作家,观念很简单,就是贯穿阶级斗争论。但是这些作家确实是心悦诚服地相信阶级斗争论,所以尽管写出来的东西很成问题,但是写的过程中,不能不承认有一股子气势和力量。现在的作家早就不相信以往那种教条化的历史观了,但是自己又树立不起更好的历史意识,所以虽然观念上进步了不少,落笔时反而没有气势和力量,显得松弛疲软。历史小说这个问题,反映了作家主体精神力量和文化积淀青黄不接的窘境。
七、在“伪”的既去“真”的未来之间……
郜:以往诚如蒋先生讲的,我们是破字当头,自残文化。现在作家要想扭转这种局面,不得不破以往的破,叫做“破破”吧。但破也好,破破也好,都不能代替立。这就使我们的文学处处有希望,又处处有遗憾。
蒋:你讲得很对。比如这两年,我们的文学抛开了过去的许多“伪崇高”、“伪现实”、“伪浪漫”、“伪美”“伪真”、“伪善”,这应该是好事。但是抛开这些“伪”之后,留下的空白要用什么来填补呢?就很少思考了。相反。倒是很多作品对丑、恶、卑琐、细碎、甚至肮脏、阴暗的东西津津乐道, 以至于形成一种习惯,好像只有写这些东西,就不“伪”。这次评奖过程中,我觉得《活着》、《老旦是一棵树》、《文革轶事》、《接近于无限透明》等等小说,就存在着这种“伪”的既去“真”的未来的问题。
郜:这和理论界的某种理论导向也许不无关系。近年来,我们许多文章对尼采的“上帝死了”和福科的“人死了”等等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激言,有点不加分析地搬用过来,稀里糊涂地认为凡是从古典人道主义立场讨论当代人的生存处境,都是过时之论,陈旧不堪了。其实就拿反本质论的存在主义来说,情况就很复杂。你能说萨特真的反对关于人的任何本质的规定吗?其实存在主义者反本质主义是有其特殊思想史背景的。他们反本质,只是反形而上学的本质论,并不是要去掉与本质有关的所有东西。“本质”一词,无论萨特还是海德格尔,都经常在肯定的意义上加以使用的。相反,对人的本质各种虚无主义的拒绝,正是他们要竭力反对的。尼彩的“超人”是他所理解的人本质。海德格尔的“此在”也是他理解的人本质。用“超人”和“此在”来解说人的存在,并不是简单宣布人死了,人道主义过时了,真善美无效了,而是要在新的理论语境中对这些古典名词加以新的释义,使其新生,使其不死。生生不息的人的本质,人类世代追求的真善美,真的能够一朝抛弃吗?
蒋:我看抛不掉。一个最切近的事实,小孩子不受任何主义和观念的影响,但小孩子看电视,听故事,首先就要分清好人坏人。分不清好坏,他就看不下去也听不进去。这说明人类对于美丑恶有一种原始的鉴别力,有一种原始的关怀。我们一些大人认为小孩子不懂艺术,只会在好人坏人层次上纠缠不清。其实这了说明了我们大人自己已经失去了这种原始的关怀和鉴别力。人生是复杂的,但有些事情也很简单。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固然天真幼稚;把简单的东西弄得太复杂,那又该怎么讲呢?我总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可能有太多的假恶丑,但整个人类的追求,人类的希望,还是应该寄托于真善美。
郜:有人说真善美是形而上学的虚构,是已经过时了的古典主义时代的理想。其实人的本质力量离不开虚构,离不开理想。一切都实打实,还有人的可能性发展吗?那才叫形而上学,那才是僵化和了无生气。小说之所以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就因为小说是一种虚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卓越的心灵追求超越、追求发展的理想和热情。人不知虚构,人丧失了虚构的能力,就不成其为人了。我们要求能在小说中看到真善美的闪光,并不是叫人无视生活中的假恶丑,而是叫人不管面对怎样的假恶丑,都不要丢失理想和希望,都不要只知下沉而不知上升。
八、百年积德,百年养气
蒋:希望文学更光明一些,更上升一些,这事实上也是对我们人本身的希望。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自己不要那么萎琐,不要那么丑陋,也不要光看到别人的萎琐跟丑陋而一味地哀声叹气,或者做出一副莫测高深的哲人状,对广大读者说一声:“就是这么一回事”,掉头回去睡大觉。我看要文学更光明更上升,文学家自己首先必须有一股正气。曹雪芹、鲁迅都有这股正气,郭沫若、郁达夫好像就不能树立这样的正气。
郜:中国文学中的正气、元气,确实是一衰再衰,一至于今。现在我们的作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根本的问题,但是气之正邪清浊,有时候实在是一种普遍的笼罩力量,对个体来说有其绝对的统治权。一旦形成,就很难转移。
蒋:不过说到底,作家的气还是要靠自己来澄清,来培养,而不能靠别人。别人不能把气吹给你,要靠自己。像孟子那样,善养其浩然之气。比如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形式很好、节奏感很强。你上次分析得很不错,这篇小说的确是写一股受压抑的气无从伸张,愤而不能择路,只好用那种出人意表的方式发泄出来。这样地发泄出来之后,气已经岔了。像老旦的一股气,加上人贩子赵镇,村里其他人,榀能还有作者的一股气,混和在一道,总的来说是一股子浊气和邪气。《废都》更是一股浊气和邪气,还有流里流气。刘心武的《四牌楼》你说是世纪末精英分子的一股衰气和消沉之气,我同意。但是恐怕另外也还有一点玩笑人生的流气在里面。另外,我看不少小说,似乎还洋溢着一股子恶气,痞子气,匪气……
郜:可能还有俗气。
蒋:对,媚俗之气。这种气最要不得,因为其他的气虽然不好,但还是刺激生命的。唯独这媚俗之气,只能沤烂生命。不幸我们的文学,媚俗之气一直很严重。
郜: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也有一股气。这股气被压抑扭曲得曲里拐弯,完全变了形。气本来应该是肯定生命的,在这里却成了否定生命的。朱苏进是满怀悲愤去写的,但客观上也告诉我们人的一股气是如何变得不利于生命。
蒋:这几年形势越来越好,是到了从根本上扶正祛邪的时候了。百年积德,万年养气,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根本的任务。文学家应该当仁不让,率先伸张一种正气。气是中国精神文化的精华和底蕴。一股相沿相承的气是维系民族健康发展的根本。历代文人站得高看得深的,无不一再呼吁文学要养气培气。以往我们太不注意这些了,任凭这气那气冲激摩荡,不晓得自己的一股气该往那里引。“文革”更是抽气,放气,弄得许多人根本就没有气。硬提气,提上来的,也只是一股子毒气、浊气和邪气。所以真要讲养气,我看也不那么容易。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代作家回答。我们各人自己都应该好好想想,再想想。
1994年5月8日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活着论文; 作家论文; 九月寓言论文; 历史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