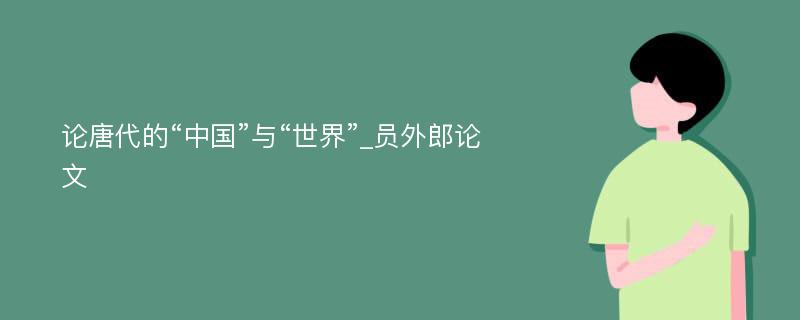
试论唐朝的“中国”与“天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朝论文,中国论文,试论论文,天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华民族”、“华夷秩序”、“中国”、“天下”等问题的讨论,由于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提出,及他所主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版,近十几年来出现了一个高潮。这些问题的讨论,对于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讨论还存在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两头热中间凉”,即研究先秦时期和清朝晚期的相关文章比较多,而研究秦朝以后至明朝的相关文章比较少。这个现象的出现比较好理解,因为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形成的发端时期,清朝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最后形成时期,二者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二是贯穿整体的研究比较笼统,即从整体上研究中华民族和中国形成特点的文章较多,而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研究的文章较少。这个现象也比较好理解,因为目前以研究文章居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也是由单篇文章组成的),而文章的篇幅即决定了不可能对每个历史时期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两个现象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空间。有鉴于此,笔者拟对唐朝的“中国”、“天下”进行探讨。限于篇幅,本文拟主要根据《全唐文》所载各个时期唐朝皇帝的有关诏令德音和唐朝人所撰的政书《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议》,以及新旧《唐书》的有关记载进行探讨。
一、关于唐朝的“中国”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1963年陕西宝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这是西周武王时期的铭文,“中国”的概念应早于西周初年,可以追溯到商朝。《诗经》和《尚书》中也有“中国”一词,如《诗经·大雅·民劳》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可以说,先秦至清代有关“中国”的记载多如牛毛,唐代“中国”一词亦不绝于书。
1.唐代“中国”一词的用法。
唐代“中国”一词的用法大体上可以分为用于前代(包括先秦)和当朝两类。
第一类用法主要用于唐人引用前代的名人名言,议论前代的人、事,或追溯前代的典章制度沿革。《通典》这方面的记载比较典型。如是书卷188 《边防四·南蛮下》引西汉淮南王安上书曰:“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不足以烦中国也。”卷189 《边防五·西戎一》条称:“永嘉以后,吐谷浑兴焉,本辽东鲜卑,晋时数百户,西附于品阴山。属晋乱,遂吞并诸羌,而有其地。至其孙叶延,遂为强国。后魏末,其主夸吕自号可汗,建官多效中国。”这里引用前朝名人名言或议论评价前代人事、追溯前代典章制度,都出现了“中国”二字,而且基本上都是沿袭前人“中国”的概念。
在第二类用法中,主要用于与四夷有关联的人、事,用于与四夷、四方(边鄙)或外来文化对举。如《全唐文·太宗皇帝五·赎取陷没蕃内人口诏》称:“隋末丧乱,边疆多被抄掠。今铁勒并归朝化,如闻中国之人,先陷在蕃内者,流涕南望,企踵思归。”就是以中国与铁勒对举。又如《全唐文·宪宗皇帝三·放免京畿积欠制》载:“疆理宇内,必先于京师;惠绥四方,亦始于中国。”不仅以中国与四方对举,而且套用《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语言。再如《通典·职官二十二·秩品五·萨宝》载:“至天宝四年七月,敕:‘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以中国与外来文化(波斯教)对举。
实际上,在第一类例子中,凡引用“中国”者,也都有“夷狄”(或匈奴、或高句丽、或吐谷浑、或西域、或岭南蛮等等)的字样出现,也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对举。所以,从唐代“中国”一词的用法上看,可以说唐代的“中国”是一个与“四夷”(四方)相对的概念,唐代仍然沿袭了传统的“中国”与“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的观念。
2.唐代“中国”一词的含义。
学术界对于古代“中国”概念的含义研究颇多,为我们理解唐人的“中国”观念提供了借鉴和基础,但有一些说法则可以进一步讨论。学术界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概念、一个文化概念,有京师、中原、民族、文化等含义。如冯友兰指出,“中国”一词在古代文化意义最甚,民族意义最少,国体意义尚无。①翁独健先生认为:“古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② 杜荣坤先生指出:“‘中国’一词……初含有‘京师’、‘帝都’、‘国中’、‘王畿’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③ 陈连开先生认为:“中国一词……大体是殷周指天子所居王城;到春秋战国,指中原诸侯国和实行华夏文化礼仪的诸侯国,既是地域概念,又是文化概念。到秦汉以后,往往指王朝直接管辖区,而以王朝的边疆为‘裔’。”④ 这些认识虽然不是具体针对唐朝“中国”概念而言,但也包含唐朝“中国”一词的含义。
“中国”一词在唐代具有地域、文化、民族等含义,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比如《新唐书·南诏传上》载:“俗以寅为正,四时大抵与中国小差。”《旧唐书·吐蕃传上》载:“国多霆、电、风、雹,积雪,盛夏如中国春时,山谷常冰。”这里的“中国”都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都是地域概念。比如《通典·边防五·西戎一》载:“氐者,西戎之别种……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织布。善田种,畜羊豕牛马驴骡。婚姻备六礼。知书疏,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这里所说与氐错居的“中国”,当然指民族,也就是汉族,而“中国语”则指汉语,“中国”既是民族的概念,又是文化的概念。比如《旧唐书·陆贽传》称:“戎狄之所长,乃中国之所短……所谓乘其弊,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中国之所长也。”这里的“中国”也有文化的含义,而且“夷狄”与“中国”的区分,本来就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是以血缘为界限的。
笔者想强调的是,唐代“中国”还有政权的概念,指“朝廷”或“中央政府”。比如《旧唐书·宗楚客传》载,唐朝宰相宗楚客因受西突厥阿史那忠节的重赂,发兵攻突骑施首领娑葛,监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称:“今娑葛反叛,边鄙不宁,由此贼臣,取怨中国。”这里的“中国”既不是地域概念,也不是文化概念,而是政治权力机构的概念,指朝廷或中央政府。因为突骑施臣属于唐朝,此处称突骑施首领娑葛为“贼臣”,即承认他是唐朝的臣子,他所怨恨的“中国”,当然是发兵攻伐他的朝廷或中央政府。
“中国”一词的地域范围,由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最初的“京师”、“帝都”、“国中”、“王畿”之意或逐渐消亡,或发展扩大,也是没有疑问的。学者一般认为,“中国”一词逐渐发展扩大泛指以中原为核心的地区,或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笔者认为,这个观点大体不错。在唐代,“中国”还可以指称“内地”。唐代皇帝的诏令和赦文中往往有“内地”的用法。如《全唐文·武宗皇帝二·平潞州德音》载:“于戏!朕以四海为家,兆人为子,一夫不获,常所歉然。(阙)不宁每劳轸虑,今逆党已戮,内地无虞,偃戢干戈,谋从此始。”同书卷83《宣宗皇帝三·洗雪南山平夏德音》载:“平夏南山,虽云有异,源流风俗,本实不殊。我国家累圣以来,许居内地,久奉声教,亦立功劳,朝廷抚绥,常布恩信。”都采用了“内地”的说法。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斯坦因S.1344号《开元户部格残卷》。此格称:“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不得入蕃,仍令边州关津镇戍,严加捉搦,其贯属西、庭、伊等州府者,验有公文,听于本贯已东来往。”⑤ 我们知道,唐代的法令有律、令、格、式四种,“格”是其中之一。令、格、式早已亡佚,唯律保存下来。而这一件“格”,是20世纪初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十分珍贵。这件《开元户部格残卷》,将“内地”与“蕃(地)”对举,同唐朝以“中国”与“四夷”、“四方”、“蕃夷”对举相同,可见“内地”与“中国”是等同的。
我们将“格”文内容与《唐律疏议》相关条文进行比较,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这件“格”文规定诸蕃商胡只能到内地贸易,不能到蕃夷之地贸易,违者将遭到边州关津镇戍的捉搦。《唐律疏议》也规定化内华人不能越度关塞与化外人私相交易,违者将根据交易的数额判二年半徒刑至流刑不等。该书卷8 《卫禁》载:“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共化外人私相交易,若取与者,一尺徒二年半,三疋加一等,十五疋加役流。”二者所不同的只是主语及具体惩罚措施。⑥ 唐律的主语“化内华人”虽然未明说,但“【疏】议曰:缘边关塞,以隔华、夷。其有越度此关塞者,得徒二年”。这里的“华、夷”即点明主语是与“夷”相对的“华”。与律文“化外蕃人”相对的应是“化内华人”。我们知道,唐代的“华”与“夷”等于“中国”与“蕃夷”,⑦ “化内华人”等于“中国人”。“化内”又等于“内地”。
这条律文还明确提出了化内之“国”(即中国)的概念及化内、化外之间的“国境”问题。其疏议在解释律文下半部分对华人与蕃夷交易兵器和婚姻方面的处罚规定时有:“越度缘边关塞,将禁兵器私与化外人者,绞。共为婚姻者,流二千里。其化外人越度入境,与化内交易,得罪并与化内人越度、交易同,仍奏听敕。出入国境,非公使者不合,故但云‘越度’,不言‘私度’……因使者,谓因公使入蕃,蕃人因使入国。私有交易者,谓市买博易,各计赃,准盗论,罪止流三千里……又准主客式:‘蕃客入朝,于在路不得与客交杂,亦不得令客与人言语。州、县官人若无事,亦不得与客相见。’即是国内官人、百姓,不得与客交关。私作婚姻,同上法。”这里所谓“蕃人因使入国”之“国”、“国内官人、百姓”之“国”,皆指与“蕃国”相对的“中国”;所谓“出入国境”的“国境”即指“中国”与“蕃国”交界的“国境”。这里“国”(“中国”)与“蕃国”对举,同《开元户部格残卷》的“内地”与“蕃地”对举,亦可见唐朝的“中国”还有“内地”的含义,可以“内地”来指代“中国”。唐朝以“内地”与“蕃地”相对举,与现代以“内地”与“边疆”相对举的方法类似。
有学者认为,“中国”或“中华”一词在统一的时候指全国:“作为地域名称,‘中华’与‘中国’相同”,“‘中华’作为地理名称,大抵也是指郡县地区,以与边陲相对。统一时指全国,分裂时指中原。”⑧ 但唐朝是一个统一的王朝,唐朝的“中国”、“中华”并不指全国。“中国”这个名词真正指全国是在清朝。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界约》称“中国大皇帝钦差分界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索额图”,“中国”第一次作为国体概念出现在外交公文上。不过这个界约并无汉文本。1842年8月29日中英签订的《南京条约》, “中国”一词出现在汉文本上。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成为中华民国的简称,“中国”正式成为国家的代名词。清朝的王绍兰《说文段注订补》纠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夏,中国之人也”的注,称:“案:京师为首,诸侯为手,四裔为足,所以为中国人也。”这是清朝民间认同“中国”一词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名称的代表。可以作为对比的是唐人类似的比喻。圣历二年(699),鸾台侍郎、平章事狄仁杰上表称:“臣闻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内……人有四支者,所以捍头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卫中国也……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国,恐非通典。”⑨ 这里狄仁杰将唐朝统治的范围(天下)比作整体的人,而将中国比作人的头目,将四方(四夷)比作人的四肢。“中国”在这里只是唐朝统辖范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四方(四夷)组合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整体。“中国”不指“全国”,不指唐朝统治的整个范围是显而易见的。狄仁杰的这个比喻与王绍兰的比喻有明显差别,这个差别反映了“中国”概念在唐朝与在清朝的差别。
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一词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用法:“中国一词的狭义用法是指‘万国之中心’、‘天下之中心’而言。”“中国”一词的广义用法,则是指整个国家的领土而言,这是当时(夏商周时期)更为普遍的一种用法。”最后结论说:“综上所述,从国家形成以后,我国古代的国家主权观念、领土观念也随之形成和发展起来,自古以来都把‘中国’作为国家通用的名称,对‘中国’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将其与‘天下’、‘四海’视为同等概念,互相通用。”⑩ 笔者认为上引文有三点不符合唐朝的实际。第一点,唐代“中国”一词并不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唐代的“中国”并不指整个国家的领土而言。第二点,唐代的“中国”概念并不等于“天下”和“四海”。第三点,唐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关于第一点,在上面已经进行了讨论,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3.唐朝“中国”之“中”的含义。
关于“中国”之“中”的含义,学者们有很多解释。一般认为是天下之中,“四海”之中。陈玉屏先生认为,“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11) 但唐人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释。《通典·边防一·边防序》载:“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下引李淳风云:“谈天者八家,其七家,甘氏、石氏、浑天之类。以度数推之,则华夏居天地之中也。又历代史,倭国一名日本,在中国直东;扶桑国复在倭国之东,约去中国三万里,盖近于日出处。贞观中,骨利干国献马,使云,其国在京师西北二万余里,夜短昼长,从天色暝时煮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于日入处。今崖州直南水行便风十余日到赤土国,其国到五月,亭午物影却在南,一日三食,饭皆旋炊,不然,逡巡过时,即便臭败。热气特甚,盖去日较近。其他渐远转寒,盖去日稍远。则洛阳告成县土圭居覆载之中明矣。唯释氏一家论天地日月,怪诞不可知也。”这里所谓“华夏居天地之中也”,即明确指出中国之“中”乃“天地之中”之意。《通典》的根据有二:一是根据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的说法,利用浑天仪、测影仪测算出来的;一是根据历代史书所记中国及东南西北国家与太阳的相对位置推算出来的。李淳风《旧唐书》有传,所载与杜佑《通典》所说略同。李淳风复原了失传了千年的浑天仪,并测出“中国”在天地之中,而且洛阳告成县在天地之正中的位置。李淳风这个结论乃至测量的手段都与西周时相同。据说西周时,周公在阳城(今河南登封)用土圭测量日影,在夏至午时,八尺之表与周围均没有日影,认为这就是大地的中心。(12) 如果说《通典》所根据的李淳风的结论没有超过前人,那么杜佑所根据的中国同直东倭国、扶桑国,西北骨利干国、直南赤土国与太阳方位的比较,则较前人有了一些新的内容。不过,中国人真正认识世界,却是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将《万国全图》传入明朝之后。
4.唐代“中国”的同义词。
张景贤先生说,“自古以来都把‘中国’作为国家通用的名称,对‘中国’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将其与‘天下’、‘四海’视为同等概念,互相通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准确。在唐代,“四海”、“天下”与“中国”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或同义词,唐代与“中国”相同的概念是“中夏”、“华夏”、“中华”、“函夏”等等。
如《全唐文·太宗皇帝一·备北寇诏》载:“自隋氏季年,中夏丧乱,黔黎凋尽,州城空虚。突厥因之,侵犯疆场,乘闲幸衅,深入长驱,寇暴滋盛,莫能御制。”同书卷24“玄宗皇帝五”“命金宪英袭封新罗王制”:“故开府仪同三司使持节大都督鸡林州诸军事兼持节宁海军使新罗王金承庆弟宪英,奕叶怀仁,率心尝礼。大贤风教,条理尤明;中夏轨仪,衣冠素袭。”这里的“中夏”与“中国”同义。(13)
又如《唐律疏议·名例》载:“平赃及平功庸”疏曰:“又问:在蕃有犯,断在中华。或边州犯赃,当处无估,平赃定罪,从何取中?答曰:外蕃既是殊俗,不可牒彼平估”云云。将“中华”与“外蕃”对举。“附录”《唐律释文》卷第三“名例”解释说:“中华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将“中华”解释为“中国”,可见“中华”亦等于“中国”。(14)
再如《通典·边防一·边防序》载:“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是“中国”又称“华夏”。
还如《全唐文·玄宗皇帝二十·册于阗王尉迟伏师文》载:“践义立身,资忠成性,禀崆峒之气,威武右称;慕函夏之风,款诚必尽。”此“慕函夏之风”可以训为“慕中华之风”,是“函夏”等于“中华”,又等于“中国”。
总之,唐代“中国”一词为天地之中之国之义,同义词有“中夏”、“华夏”、“中华”、“函夏”等等。“中国”不代表唐朝实际统治的全部领域,而仅代表唐朝统治的核心地区。那么,什么词语代表唐朝当时统治的实际领域呢?这就是“天下”。
二、关于唐朝的“天下”
关于“天下”一词史书中记载很多,学者们的讨论也很多。学者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如田继周先生说:“当时‘天下’这个概念的含义,也不像我们今日理解的那样广泛,大体上指的是我国当时的领域。今天,我们讲到中国时,往往以‘五湖四海’来形容它或代表它。‘四海’之称在先秦时代已普遍使用了。当时‘四海’和‘天下’的范围,虽然不能说就是我国今日的范围,但却包括了当时的‘九州岛’之域。”(15) 但近年来陈玉屏先生提出不同意见,他说:“此种意见在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按此种意见的见解,先民心目中的‘天下’、‘四海’的具体范围不论做何种描述,都是一个有限范围。笔者认为这个先民所言的‘溥天之下’的范围,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要服’、‘荒服’的蛮、夷、戎、狄,直至地处蛮、夷、戎、狄之外的藩国,不论距离多远,理论上亦均为‘王臣’。先民们的大一统意识讲求‘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记·曾子问》),不能设想他们从理论上承认在他们所处领域之外还有一个天地、一个至尊、一个太阳。至于天子的实际控制与影响范围有多大,对‘王土’和‘王臣’的实际控制程度有多强,那是另外一回事,并不妨碍上述理论的成立。先民正是循此理念来思考问题,来认识天下国家的。”(16) 那么,“天下”究竟是“大体上指的是我国当时的领域”,还是“在理论上是无限的”,或者二者并存,皆有合理成分?我们来看唐人的“天下”就能明白何者为是。
1.唐朝的“天下”。
笔者认为,唐朝的“天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毕奥南先生指出:“先秦‘天下’有广狭二义,广义指所知世界,狭义指王朝及诸夏统治区域范围。”(17) 这个看法对于我们认识唐代的“天下”有借鉴作用。笔者认为,唐朝的广义“天下”应指当时与唐朝有交往的整个世界,狭义应指唐朝的实际统治范围。唐朝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世界帝国,唐朝的所谓“蕃国”,多数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统治下的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是独立于唐朝的外国,这些蕃国都包括在唐朝的“天下”之中,就这一点而言,唐人的“天下”应该具有广义的世界意义。据《唐六典·礼部》记载,唐朝“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这70余蕃包括“三姓葛逻禄,处蜜,处月,三姓咽蔑,坚昆,拔悉蜜,突蹶,奚,契丹,渤海,室韦,龟兹国,疏勒国,于阗国,焉耆国,突骑施,吐火罗,米国,火寻国,骨咄国,诃毗施国,曹国,拔汗那,康国,安国,石国,日本,大食,吐蕃”等等,其中日本、大食、吐蕃、东天竺、西天竺、南天竺、北天竺、中天竺等就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国家。因此,唐朝的广义“天下”应指当时与唐朝有关联的世界。不过笔者认为,唐代的“天下”主要是狭义的概念,这个“天下”主要指唐朝实际统治的范围,这个“天下”具有王朝国家的性质,具体指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下面笔者主要从《唐六典》的记载来考察唐朝官方赋予“天下”一词的含义。由于《唐六典》是一部唐朝官修的政书,由当朝宰相张说、张九龄、李林甫等人主持监修,于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完成,因此,此书完全可以代表唐朝官方的观点。而《旧唐书·百官志》所载此方面的内容和措辞与《唐六典》基本相同,从而亦可以证明《唐六典》所具有的代表性。
《唐六典》主要记载的是唐朝职官的建置和职掌。我们分析考察唐朝中央机构官吏的职掌范围,就能明确唐代“天下”的主要用法和“天下”一词的主要含义。唐朝管理国家事务的中央机构是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一台(御史台)、九寺(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等等。由于篇幅所限,仅举三省为例。据《唐六典》记载,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掌军国之政令……人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次长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门下省首长侍中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尚书省首长尚书令“掌总领百官,仪形端揆。凡都省掌举诸司之纲纪与其百僚之程序,以正邦理,以宣邦教”。是三省的首长和次长所掌范围为“军国”或“邦国”(简称“邦”)。(18) 尚书省作为三省中的执行机构,下领六部二十四司。据同书记载,这六部二十四司中,吏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官吏选授、勋封、考课之政令”,其下四司,吏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司封郎中、员外郎“掌邦之封爵”;司勋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官人之勋级”;考功郎中、员外郎“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户部尚书、侍郎“掌天下户口井田之政令”,其下四司,户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支度国用、租赋少多之数”;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库藏出纳之节,金宝财货之用”;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国之仓庚,受纳租税,出给禄廪之事”。礼部尚书、侍郎掌“天下礼仪、祠祭、燕飨、贡举之政令”,其下四司,礼部郎中“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道佛之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数”;主客郎中、员外郎“掌二王后及诸蕃朝聘之事”。兵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其下四司,兵部郎中“掌考武官之勋禄品命”;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驾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维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库部郎中,员外郎“掌邦国军州之戎器、仪仗”。刑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句覆、关禁之政令”,其下四司,刑部郎中、员外郎“掌贰尚书,举其典宪而辨其轻重”;都官郎中、员外郎“掌配没隶,簿俘囚”;比部郎中、员外郎“掌句诸司百寮俸料、公廨、赃赎”;司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诸门及关出入往来之籍赋,而审其政”。工部尚书、侍郎“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其下四司,工部郎中、员外郎“掌经营兴造之众务”;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虞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泽之事,而辨其时禁”;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从以上引文可见,三省长官及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长官的职掌范围皆为“军国”、“邦国”或“天下”,而以“天下”为多。(19)
从上列三省官员职掌“天下”的范围来看,这个“天下”都是非常具体的。如户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唐六典》在其下载,“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羁縻之州盖八百焉”,“凡天下之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说明这个“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改为十五道), 就是当时唐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地理范围,这个“三百一十五州府、八百羁縻府州”,就是当时唐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州府总数;(20) 这个“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户,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口”,就是当时唐朝统治之下的“天下”的户口(当然还有未被政府控制的户口)。又如《唐六典》载“凡天下观总一千六百八十七所”,这个数字就是祠部当时所掌“天下”道观的总数。再如同书载兵部尚书、侍郎“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其下接载“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这个数字就是当时兵部所掌“天下”军府的总数。再如同书在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之政令”之下接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这个数字就是当时屯田司所掌“天下”屯田的总数。又如同书在驾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传、驿”等之下载,“凡三十里一驿,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所水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陆驿,八十六所水陆相兼”,这个数字就是当时驾部所掌“天下”驿站的总数。又如,同书在水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之下载“凡天下水泉三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有九”,这个数字就是当时水部所掌“天下”水泉的总数,等等。总之,这里的“天下”都是具体的,都是狭义的“天下”,都是指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实际统治的范围,这个实际统治范围就是“十道”(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改为“十五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陇右道、岭南道。这“十道”又分为“三百一十五州府,八百羁縻府州”。
上述“天下”又略等于“邦国”。《唐六典》中职方郎中、员外郎的职掌为“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侯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可见这里将“天下”与“邦国”互换而其意基本不变。又如驾部郎中、员外郎的职掌为“掌邦国之舆辇、车乘,及天下之传、驿、厩、牧官私马、牛、维畜之簿籍,辨其出入阑逸之政令”,这里亦将“天下”与“邦国”交替使用而其意大致不变。再如记述御史台的职掌,“御史大夫掌邦国刑宪、典章之政令……中丞为之贰。凡天下之人有称冤而无告者,与三司诘之”,亦以“邦国”与“天下”互相说明,交替使用。这个“邦国”又略等于“军国”。如前所引,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掌军国之政令”,中书侍郎“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门下省首长侍中“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尚书省首长尚书令“以正邦理,以宣邦教”,三省的首长、次长所掌范围或称“军国”或称“邦国”(简称“邦”),而我们知道,三省首长、次长所管皆为唐朝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所管范围并无不同,所不同的只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为决策机构,尚书省为执行机构,由此可见,“邦国”与“军国”的范围亦略同。
那么,既然“军国”、“邦国”、“天下”三种称呼的意思略同,唐朝为什么要分别称之,其用意究竟何在呢?细细品味《唐六典》、《旧唐书·百官志》等书的措辞,笔者发现,唐朝官方“天下”、“邦国”、“军国”的用法还有一定的差别。这个差别主要体现在,“军国”是最郑重的用法,主要用于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职掌,这大略与中书省、门下省为中央的最高决策机构,其首长职掌出纳王命,地位最崇重,而古代国家最重要的事莫过于祀与戎有关;而“邦国”是更普通的用法,从《唐六典》等记载来看,中书省首长中书令所掌称“军国”,次长中书侍郎所掌称“邦国”,中书侍郎较中书令地位略低,可见“邦国”比“军国”的称呼亦略低。而从“邦国”与“天下”的比较来看,“邦国”更侧重于管理官府官吏的事务和中央事务等层面,如尚书省中,凡掌涉官府官吏的职掌(如都省、司封、司勋、驾部、库部郎中和员外郎的职掌),及管理中央事务的九卿的职掌范围,皆称为“邦国”。“天下”是更广泛的用法,“天下”更侧重于管理地方和百姓的层面(同时也包含管理官吏的层面),如尚书省中,一般掌涉中央和地方、官吏与百姓两方面事务的官员所掌范围即称为“天下”。如尚书省中,吏部、户部、度支、礼部、祠部、兵部、职方、刑部、比部、司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这些部门的官员掌涉中央和地方、官吏与百姓两方面的事务,其所掌的范围即称“天下”。由此可见,“军国”、“邦国”和“天下”这三种称呼的意思或范围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又各有侧重。这三者的用法,并不是史官信手写来或随便称之的,而是大有深意的。
笔者认为,唐朝之所以以“天下”作为其所统治范围的名称,应该主要是沿袭传统的观念。从先秦开始,中国即有以“天下”指代统治疆域的传统习惯。中国是一个特别注重传统的国家,唐朝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王朝的延续,当然要采用传统的习惯称法。另外,唐朝对蕃国的概念界定不清,将两种不同性质的蕃国(唐朝统治下的地方政权和与唐朝并立的外国政权)混淆在一起,也应是唐朝以“天下”指代所统治范围的重要原因。
总之,唐朝的“天下”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而以狭义为主。只承认其中一种是不正确的,只看到它的广义一面或者夸大这一面尤其不符合唐朝的历史。有学者说:“按照纯粹理论上的定位,天下/帝国根本上就不是一个国家,尤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或者说是一个世界社会,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天下是个关于‘世界’而不是‘国家’的概念。”(21) 这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研究中国古代史,得出的结论难免偏颇。
2.唐人“天下”的同义词。
唐代“天下”的同义词除了上举的“军国”、“邦国”、“邦”、“国”等以外,还有“四海”、“海内”和“区宇”(区寓)、“区夏”等等。
关于“四海”。有学者指出,根据《尔雅·释地篇》所谓“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则四海类似四夷”,先秦的“四海与其说确指地理方位,不如讲只是代表先秦时期人们对周边部族分布区域的笼统指称”。(22) 这是有道理的。不过,“四海”的概念后来有所发展和变化,不再单指四夷或周边,而是指包括周边四夷在内的整个“天下”。唐人的“四海”用法即如此。如《全唐文·高祖皇帝一·遣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载:“隋德下衰,政荒民散。九州幅裂,四海瓜分。元元无辜,困豺狼之吻。”这里所说的“四海瓜分”就是指隋朝整个天下的瓦解。同书同卷《每州置宗师诏》载:“朕受终揖让,君临四海,普天之下,同加惠泽。”这里的“君临四海”,指的也是唐朝皇帝统治的整个天下。
关于“海内”。如《全唐文·高祖皇帝一·改元大赦诏》载:“大业末年,纲维废弛,三光改耀,九服移心。既戡定时难,辑和庶绩,一匡海内,再造黎元。隋氏以天禄永终,历数攸在,敬禅厥位,授于朕躬……可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武德元年。”这里将“海内”与“天下”相提并论,可见可以互相指代。又如,《旧唐书·令狐德棻传附邓世隆传》载:“初,太宗以武功定海内,栉风沐雨,不暇于诗书。”《旧唐书·礼仪二》载:“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议其制。”同书载:“上(太宗)曰:‘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这里的“定海内”与“平定天下”、“取天下”是同一个意思,“海内”等于“天下”。
关于“区夏”、“区宇”和“区寓”。如《全唐文·高祖皇帝一·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载:“尚书令雍州牧右武候大将军上柱国秦王世民……廓清区夏,忠孝克彰……今区宇方缉,巩洛犹芜,镇俗治戎,允资望实。”这里的“区夏”、“区宇”都是指唐朝逐鹿中原取得的天下。“区宇”又作“区寓”。如《全唐文·宣宗皇帝三·洗雪南山平夏德音》:“朕君临区寓,深念黎元,凡曰含生,皆同赤子。”这里的“君临区寓”与前所引“每州置宗师诏”中的“君临四海”意思相同,可见都是“天下”的同义词。
三、关于唐朝“中国”与“天下”的关系
前面笔者已经指出,唐朝的“中国”仅代表唐朝统治的核心地区,不代表唐朝实际统治的全部领域;而狭义的“天下”则代表唐朝实际统治的领域,具有王朝国家的性质。唐朝的“中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再就“中国”国家的性质略论之。
关于古代“中国”国家的含义,学者们有许多讨论。如杜荣坤指出:“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型及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23) 张璇如认为:“关于‘中国’的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岛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是不对的。”(24) 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很正确。但也有一些观点不正确,如近年来有学者说:“唐代关于‘中国’称谓,在原有的意义上大为扩展,其中包含有当今主权国家的基本涵义。”(25) 这个观点夸大了唐朝“中国”一词的范围和含义。近代国家的概念有三个基本要素:人民、领土和主权。笔者认为这三个基本要素也可以用来衡量古代中国。以此衡量唐代的“中国”,显然,此时的“中国”,人民仅指汉族,不包括唐朝统治下的其他四夷之民,更不包括历史上属于今中国的其他民族;领土仅指中原内地,不包括四方边疆之地;主权亦无完整的国家主权。所以,此时的“中国”不代表统一多民族的王朝国家,更不具有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它只是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狭义的“天下”则基本上具备了这三个要素,它具有较完整的领土、主权和人民,是唐朝统治范围的代名词,是一个王朝国家或政治实体;而广义的“天下”则是唐朝建立的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以唐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狭义“天下”为政治实体的包容其他国家在内的世界体系和政治秩序。
书讯
张永攀博士著《英帝国与中国西藏(1937—1947)》一书年2007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3万字,分三章。第一章对1937—1947年间英国与印度政府在西藏门、察、洛地区的活动情况,侵入策略与方针,官方政策分歧等进行了探讨。第二章探讨了英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对西藏政治地位的争论。第三章对英国政府干涉国民政府改善与西藏地方关系的活动做了探讨。
该书利用了近年来公布的英国印度事务部档案等较少见的外文资料,弥补了一些前人所未涉及的研究领域,在研究中印边界关系、西藏近代史领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注释:
① 参见安树彬:《从传统天下观到近代国家观》,《华夏文化》2004年第1期。
② 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③ 杜荣坤:《试论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 陈连开:《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与民族》,《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⑤ 郝春文等:《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页。
⑥ 这条律疏禁止“化内华人”越度缘边关塞, 与化外蕃人私相交易(“取蕃人之物及将物与蕃人”);上举格文禁止蕃人到蕃夷之地贸易,规定只能到关塞以内的内地进行交易,律文与格文都禁止在缘边关塞以外私相交易,而允许在缘边关塞以内进行贸易,内容大体相同。
⑦ 《唐律疏议》卷4《名例》亦明确指出“化外蕃人”指的是“蕃夷国之人”,其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疏】议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
⑧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44—245页。
⑨ 《通典》卷186《边防二·东夷下》。
⑩ 张景贤:《论中国古代领土观的形成》,《历史教学》1998年第5期。
(11) 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12) 参见张环宙:《试论“中国”含义的发展》,《湖州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
(13) 《资治通鉴》卷188武德三年(620)二月条载:“突厥颉利可汗承父兄之资,士马雄盛,有凭陵中国之志。”而同书贞观元年九月条载称:“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资治通鉴》在这两处地方叙述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一用“凭陵中国”、一用“凭陵中夏”,亦可见“中国”等于“中夏”。
(14)《唐律释文》为南宋人此山贳冶子所撰,元人王元亮重编,今刘俊文先生将此作为附录,附于《唐律疏议》之后。其释“中华”为“中国”是正确的。
(15) 田继周:《我国民族史研究中的某些理论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3期。
(16) 陈玉屏:《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17) 毕奥南:《天下、四海、中国、疆域、 版图——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2期。
(18) 九寺、五监首长所掌的范围,《唐六典》基本上亦都用“邦国”来说明。
(19) 史书中还有很多称“天下”的记载。如《旧唐书·礼仪四》载:“(贞观)十九年正月,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天下州县等停牲牢,唯用酒脯,永为例程。”“(天宝)十二载七月,诏天下举人不得充乡贡,皆补学生。”“九月,两京玄元庙改为太上玄元庙,天下准此。”“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为太微宫,天下诸州为紫极宫。”《旧唐书·地理志》载:“景云二年,分天下郡县,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之。”“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每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不胜枚举,皆与正文所引“天下”的含义相同。
(20) 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唐朝羁縻府州的数字实际上比《唐六典》所列数字要多,其他如人口、军府、屯田等情况同样如此。不详列举。
(21) 赵汀阳:《“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5期。所引梁漱溟先生观点见《梁漱溟学术论着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32页。
(22) 毕奥南:《天下、四海、中国、疆域、版图——历史语境中的王朝中国疆域概念辨析》。
(23) 杜荣坤:《试论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24) 张璇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之我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
(25) 胡耀华:《对“中国”概念演变及地缘内涵的分析》,《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