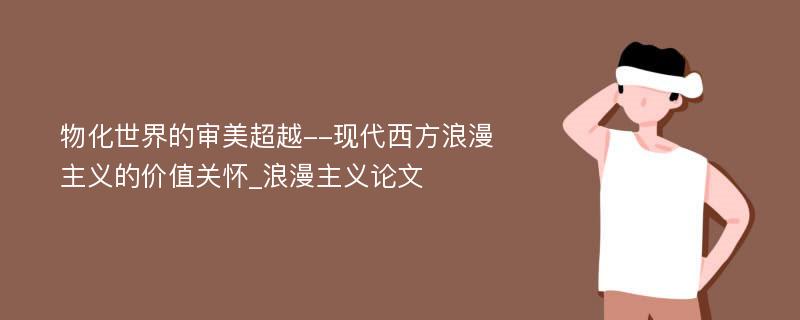
物化世界的审美超越——近代西方浪漫主义的价值关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关切论文,近代论文,价值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诗人海涅曾讲过一个寓言故事。故事说,一个英国发明家在造出一些精妙的机器之后,忽然想到要用人工方法来制造一个人,而且他最终获得了成功。据说他的这个了不起的作品竟完全能像一个人那样举止动作,甚至,在它那皮革制造的胸膛里还具备了和通常英国人的情感相差不远的一种人类情感。它用于表达情感的语言十分清晰,并且就连内部齿轮、磨损器和螺丝发出的杂音,也富有一种地道的英国腔调。总的来说,这个机器人就像一个派头十足的英国绅士,它作为一个真正的人,除了灵魂以外别的什么都不缺了。但这个英国技师却无法给它一个灵魂。而这个可怜的被造物,自意识到这个欠缺以后,便日日夜夜折磨它的创造者设法给予弥补。这位大发明家终于无法忍受那日益迫切的不断请求,于是便丢下机器人仓皇出逃。但这个机器人却立刻坐上一部特快驿站马车追他到欧洲大陆。它总跟在他身后,突然抓住他,哼哼唧唧地对他说:“给我一个灵魂!”(注:《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0页。)
灵魂的匮乏或价值的沦丧作为技术文明的一个负面效应,在近代西方工业化国家似乎是一个可以直接感受到的生活现实,至少对于浪漫主义者来说是这样。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虽然使人们分享到技术进步的好处,但它所建立起来的机械世界,特别是这个机械世界对人的强制性的分割与组织,却又肢解人的健全生命,使之丧失了本该具有的质朴圣洁与青春激情。当眼见着田园变成排污水的工厂,森林变成冒黑烟的烟囱,男男女女变成机器体系的附属部件,有人曾哀叹说:“在这里,文明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则几乎又成了野蛮人。”(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从表现形式来看,浪漫主义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反应是否定性的。科学的成长、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崛起、市场力量的壮大以及商业品味的流行等等,所有这一切被视为工业文明成就或象征的东西,不仅没有激起浪漫主义者的乐观情绪,反而诱发了他们的一种深深的挫折感和失落感。这种挫折感和失落感,用历史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也许太过极端,无法从中引申出对工业文明历史地位的恰切评价。但是,当质疑工业文明的物质成就是否足以确证人的生存意义的时候,那又必须承认,浪漫主义者的叛逆姿态显然有其关切生命价值的正当依据。同迎合工业文明潮流的世俗功利主义取向相反,浪漫主义的一个批判性立场是,人们对物的追求意志越强烈,向外部世界攫取越多,其内在的灵性也就越是容易被掏空。因此,有必要向那些盲目的乐观主义者追问:文明进步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这些代价是否可以用它的好处来抵偿?倘若不能抵偿或不能充分抵偿,那么在一个精神贫困时代,该如何找回我们因世俗所累而丢失了的本真?
这些带有鲜明倾向性的追问使浪漫主义者无法投身现代文明事业,同社会现实和谐相处。他们觉得,如果社会沿着世俗化、技术化、理性化的轨道前进,势必会造成一种“沉于物,溺于德”的景象。这种景象不仅让他们忧心,而且令他们恐惧。于是,在强烈的失落感的驱使下,他们逆时代潮流而行,掉过头去,“转向过去和乌托邦,转向潜意识和幻念,转向不可思议和神秘,转向儿童和自然,转向梦境和放肆,一言以蔽之……转向能把他们从失败的感受中解脱出来的要求。”(注:蒙塞尔:《艺术史的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透过浪漫主义传统,我们可以发现一系列相互缠绕的特色主题,譬如:崇尚人与自然的契合交感,反对技术文明带来的人与自然的分离对抗;坚持本真情感在精神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反对科学理性的妄尊自大;追求诗意的人生,反对沉醉于庸俗商业趣味的市侩习气,等等。将这些主题归结起来,可以称之为物化世界的审美超越。
二
罗素讲:“浪漫主义运动的特征总的来说是用审美的标准代替功利的标准。”(注: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6页。)这个评价十分贴切。依浪漫主义的审美标准来判断,工业文明所塑造的物化世界显然是一个价值颠倒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无法留居的。既如此,对浪漫主义而言,到一方不闻城市喧哗和蒸汽机轰鸣的净土,与自然独对,品味摆脱了世俗纷扰的内心宁静,追寻业已隐退的真人的行踪,便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生存抉择。这种生存抉择使浪漫主义者对前技术文明格外痴迷。靠着诗意的想象,他们消解前技术文明在历史形态上的落后、艰辛与不幸,将其幻化成质朴圣洁的生活样式,从而作为昭示未来的后技术文化理想,推到了工业社会的对立面。由此可以理解,在工业化时代,英美浪漫主义者为什么常常以反潮流的方式进行一系列旨在阐明价值优先性的二元对比。
第一组对比存在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华滋华斯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不饰伪装的清纯朴直,因此,“自然”乃人性的最高衡量标尺。这个标尺的确立意味着,真正的生命原型,应当越过城市、越过在浮躁的现代文明生活中沾染了太多虚伪、庸俗之气的男男女女,到乡村去,到茅舍田野去寻找。这个价值取向使浪漫主义者对象征工业文明成就的城市生活作出了否定性的评价。爱默生说,随着城市人获得越来越多的现代技艺,他同时也失去了原初的本质力量。他有车辆,但失去了双足;他有精致的钟表,但失去了通过太阳准确判断时间的本领。笔记本和图书馆败坏着他的记忆和智慧;知识学问腐蚀着他翻译自然之书奥义的能力。他的财富越积越多,但却成了一个只消化食物的胃;他的生活越来越舒坦豪华,但却遗忘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家。在这个意义上,纵令可以谈论所谓社会的进步,“但进步的人却一个也没有。”(注: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161页。)
第二组对比存在于儿童和成人之间。如果说,自然率真乃人性的最高尺度,那么儿童的幼稚单纯较之成人的老谋深算,便更贴近浪漫主义者心目中的人格理想。因此,在许多浪漫主义者那里,返朴归真合乎逻辑地指向了一种儿童崇拜。照他们的说法,因无知而无邪,因未曾涉世而有一颗澄明之心的儿童,就像是来自天国的精灵。在他们身上,成人的那种支离暴躁的心胸,那种因精明的功利算计而导致的“对外界的不信任感”,都是不存在的。他们的眼神未曾被慑服,他们的心灵健康而完整。因此,圣洁的童心犹如浑然天成的诗,传达着自然的不朽信息,颁布着人性的庄严律法。在这个意义上,用儿童那质朴性灵的纯净之水,来冲刷伴随着所谓文明教养而淤积在成人心中的肮脏污垢,实质上也就是追思人生的诗意,给无家可归的浪子指出一条返乡之路。所以华滋华斯唱出了“儿童本是成人的父亲”的著名诗句。(注:《英国湖畔派三诗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第三组对比存在于情感和理性之间。将儿童视为人生的伟大向导,对浪漫主义来说暗含了一种反启蒙的立场。“人生识字糊涂始”是关于这一立场的通俗表达。它意味着,对成人的虚伪面目的揭穿,逻辑地等价于对启蒙的理性准则的颠覆。按照浪漫主义者的看法,理性准则之所以要被贬斥,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抽象、枯燥、机械、刻板,会使人的生命活力受到压抑和窒息;另一方面也由于,一当与竞争性的世俗潮流相融合,它就既倾向于把外部自然当作财富的源泉来榨取,也倾向于把自己的同类当作谋利的手段来算计。因此,理性谋划在什么程度上表现得精明,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反衬出它的自私与冷漠。浪漫主义者因而强调说,当善作功利盘算的理性的文明人面对受难的同类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时候,要寻找道德良知的真正基础,必须超越理性,诉诸更原始和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情感,就是生命热血,就是永不熄灭的“内心光明”。从某种意义来讲,儿童之于成人的价值优先地位和情感之于理性的价值优先地位,在浪漫主义那里是相互沟通、彼此印证的。它们分别代表了个体生命历程和心理品格构造中的“自然”。
第四组对比存在于艺术和科学之间。浪漫主义者将田园生活、儿童世界和生命情感沟通起来,构设一种至真至纯的自然之境,所凭借的是一种创造性的诗意想象。这种诗意想象不仅使浪漫主义者剔除功利杂质,塑造一个清澈澄明的“小我”,而且将这个“小我”融入宇宙“大道”,追求着一种天人合一的感受方式和生存方式。柯尔律治指出,艺术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媒介物和协调者”。(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这个媒介物和协调者,无论在品格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与实证科学大相异趣的。浪漫主义者认为,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分析精神。由于分析意味着抽象,而抽象总是使实在变得贫乏,因此,科学所建立的世界只能是一个无生命的死寂的世界。这个世界将彩虹拆散,把天使和小精灵驱走,使所有可爱的幻想都受缚于冷漠的物质定律,其刻板僵硬犹如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科学在知识论的范围内排除迷信观念,固然正当;但当它逾越合理限度,将审美感受和诗意想象一并加以扼杀时,问题的症结,就毋宁是在更高的水平上用艺术来为科学解蔽了。解蔽的方式就是要给自然重新“施魔”,显现它隐藏在帐幔下的神奇、秘密和灵光,从而将物质主义的宇宙转化为同人契合交感的活生生的“你”。对浪漫主义来说,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具有双重意涵:自然中有人的生命情感的投射,充满了温馨和爱意;而人则又借自然的清新甘露净化自己灵魂,殚精理道,解粘去缚,返还生命的本真。华兹华斯把这描绘为诗意的纯粹人生:“在这恬静的心绪中,/那高尚的情感引导着我们,/使人们仿佛暂时停止了呼吸,/甚至连血液也不再流动,/我们的肉体已进入酣睡,/好像变成了一种纯粹精神……”(注:《英国湖畔派三诗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第五组对比存在于诗人和庸众之间。浪漫主义者超越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狭隘视界,用审美艺术来构造至真至纯的理想天国,因而必然要确证诗人在价值建构中的优先地位。雪莱说:“一个诗人浑然忘我于永恒、无限、太一之中”,他是真善美的领悟者和体验者。(注: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在华滋华斯看来,诗人的这种独特气质使他超越于庸众之上。他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8-49页。)爱默生则进一步强调,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芸芸众生被世俗的尘埃蒙蔽了眼目,已无法回复到本然的自我。所以,世界就总是期待一个以超人的能力来领悟自然的宝训并将之传授给众人的诗人。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活立言,因而是“一个盟主,处于中心的位置。”(注:爱默生:《自然沉思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页。)在浪漫主义者那里,诗人的这中心位置是作为工业文明的叛逆形象而建构起来的。他抗拒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之风,崇尚精神的高洁和生命的健全,因而就像是一个“鹤立于庸人之中的完人”。这个“完人”讨厌商业社会“恶臭的呼吸”,不看别人的脸色,不留心别人的脚印,不受世俗礼法的束缚,具有一种遗世独立、昂然自恃的高贵派头。事实上,这也就是浪漫主义者给自己的定位。
三
浪漫主义者对审美标准的推崇和对功利标准的颠覆,表明他们强烈感受到了工业文明的兴起所带来的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与饥渴。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这种感受来自一种实际的生活经验,因而有着某种可以理解的历史根据。但令人感兴趣的是,工业化进程相对滞缓的德国也培育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竟不仅比英国人更早,而且更深刻地觉察出了技术文明时代人的生存意义的危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或许答案就在问题的反面:正因为德国人较多乡土气,他们才较少技术中介的阻隔,而与大自然保持了难分难解的神秘交感和血肉契合。因此,他们那充满宗教感和田园诗风的素朴性灵,在觉察出工业化浪潮的蔓延之势后,就不能不随之震颤,并发出一串串跟现代社会不尽和谐的声音。荷尔德林在诗中说:“哀哉!我们的同时代人在黑暗中摸索,仿佛/生活在阴曹地府一般索然无味。光为/自己的事业忙,在隆隆的作坊里/全都闭目塞听,蛮人般地挥动巨臂……”(注:《荷尔德林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5页。)
德国浪漫主义者敏锐地感觉到,工业文明的成长会在双重意义上伤害人的内在灵性。一方面,功利欲求的统治使生活变得贫乏,成为一片“撒过盐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艺术精神得不到培养,它萎缩于利益的桎梏下,“消失在嘈杂的市场中”。(注:席勒:《美育书简》,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37页。)另一方面,知性思维的盛行、技术规则的推广、专业分工的细化,在提高类的总体力量的同时,又从根本上破坏了个体生命原本具有的丰满与完整。人成了束缚于无生命的机械组织中的一个断片。席勒评论道:“永远束缚于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断片了。耳朵里所听到的永远是由他推动的机器轮盘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嘈杂声,人就无法发展他生存的和谐,他不是把人性印刻到他的自然(本性)中去,而是把自己变成他的职业和学科知识的一种标志。”(注:席勒:《美育书简》,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1页。)
不仅如此。在席勒看来,就连把个体联系到机械整体上去的那个细微断片也不取决于人的自主选择,而是由一个公式无情地、严格地规定出来的。这还有什么灵性、诗意可言!出于对这个物化世界的厌恶,席勒返回过去,在古希腊那里发现了人之为人的理想楷模。“希腊人的本性把艺术的一切魅力和智慧的全部尊严结合在一起……他们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注:席勒:《美育书简》,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8-49页。)在他们身上,席勒看到了一种身与心平衡、灵与肉和谐的完美人格。
如果在现象层面作一个对比,那么席勒对“纯真希腊”的追忆较之华滋华斯对乡村生活的眷恋,似乎显示了一种更为厚重的历史感。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一大特色。但是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席勒所谓“纯真的希腊”并不是作为历史事实,而是作为比照现代文明的精神理想设定出来的。一如华滋华斯对田园生活的幻化,“纯真的希腊”对席勒而言也是一种用诗来编织并靠诗来复活的梦境。“美丽的世界,而今长在?/大自然,美好的盛世,/重新回到我们之中来吧!/可叹只有在诗的仙境里面,/才能寻觅你那种神秘莫测的仙踪。”(注:《席勒诗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
由此凸显了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取向。诺瓦利斯在论及这个取向时说,既然时代是一个“沉于物”的功利主义,那代,在新的生活光临之前,必须先有一个诗的裁判日。“诗歌是真正绝对的真实。这是我的哲学的核心。愈有诗性,就愈加真实。”(注:《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3页。)因此,在德国浪漫主义者那里,诗,不再是一种特殊门类的艺术创作,而是一种形而上的价值建构方式,一种发现生活真义的指导线索。它通过激情、想象、直觉和冥思而冲破外在的时空局限,在一种超越因果规律的自由状态中显现一个不可见之域,一个同卑污的现实世界遥遥相对的价值世界或意义世界。
从本质上说,席勒的“纯真希腊”就是这样一个诗化的意义世界。当浪漫主义者以其与大自然的神秘交感,谛听着清泉的吟唱和树木的低语,从奇花异葩的眼睛里读出相思的神情,乃至于在古堡废墟、精灵鬼怪、巫术魔法中咀嚼某种神奇意味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现代文明的功利旨趣、知识旨趣、技术旨趣的拒斥与抗争。勃兰兑斯指出:“诗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个大问题,对于它们深刻的不共戴天的矛盾的绝望,对于一种和解的不间断的追求——这就是从狂飚时期到浪漫主义结束时期的全部德国文学集团的秘密背景。”(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由于以诗的映照去不断加重相形见绌的生活的危机感,德国浪漫主义者具有相当浓烈的遁世情绪。而且,同英美浪漫主义比较起来,他们的这种遁世情绪,少了一份隐匿独处、漫步遐想的悠然自得,而多了一些寂寞无助的忧郁和几近精神分裂的痛苦。为了平复这种痛苦,诺瓦利其告别发出“冒昧光亮”的白昼,唱起了《夜颂》。他觉得,在黑夜中,周围世界都隐没起来,于是人们便得以“走向内心”,沉入令人陶醉的幻想状态:“黑黢黢的夜呀……你展开了心灵的沉重的翅翼……我感到光亮是多么可怜而幼稚啊!白昼的告别多么可喜可庆啊!……夜在我身上打开了千百万只眼睛,我们觉得比那灿烂的群星更具神圣。它们比那无数星体中最苍白的一颗看得更远;它们不需要光,就能看透一个热恋心灵的底层,心灵上充满了说不出的逸乐。”(注: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页。)
按照一种相信历史进步的乐观主义观点,这样一种迷恋黑夜的遁世情绪无疑是消极的。海涅就说,诺瓦利斯的诗艺实际上是一种疾病。对之作出判断,不是批评家的事,而是大夫的事。(注:《海涅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舍勒认为,浪漫心灵“在某程度上总带有怨恨。”(注: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页。)他们对前技术文明的痴迷,不是基于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价值和吸引力,而是基于一种贬损自身时代,逃离自身时代的避世意向。至于他们在艺术幻梦中的迷醉,更说明他们缺乏在行动上重构现实的决心,实乃无力感的表示。这些看法涉及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问题毕竟还有它的另一个方面。最起码,我们不好把浪漫主义者沉醉于艺术之梦看作是纯然的自欺。因为自欺,就本质说来,乃是精神为了某种外在需要而违心地扭曲自己的本然意图。但在这里,情况正好相反。正是为了不自欺其心,德国浪漫主义者才弃绝庸俗的生活现实,主张在诗的国度里纯化人的情感,信护性灵的圣洁。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浪漫派以及整个浪漫主义传统,通过对物化世界的审美超越而保全了一颗形而上的人类价值火种。这颗火种是应该传递下去的,尽管难以指望它在可见的未来形成燎原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