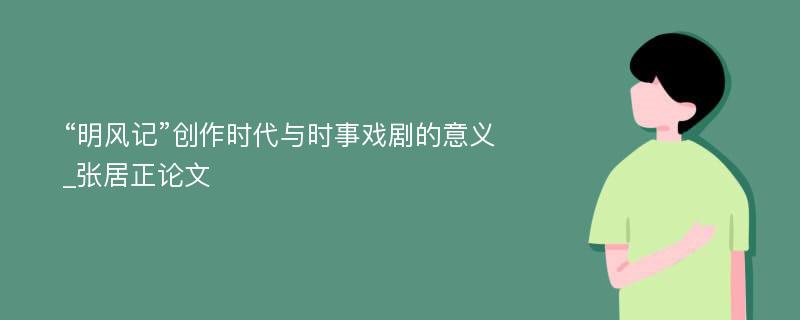
《鸣凤记》创作年代与“时事剧”之义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义论文,时事论文,年代论文,鸣凤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5)02-0054-04 《鸣凤记》历来被视作明清剧坛上“第一部”时事剧,郑振铎称:“传奇写惯了的是儿女英雄,悲欢离合,至于用来写国家大事,政治消息,则《鸣凤》实为嚆矢。[1]李修生主编《古本戏曲剧目提要》也称该剧“是戏曲史上最早表现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的作品”[2]。郭英德《〈鸣凤记〉:时事剧的发韧》、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等均持相似观点。关于它的创作年代,张军德《〈鸣凤记〉创作年代初探》(下简称张文)一文根据《明史》、《万历野获编》等史料中所记载的邹应龙、林润、孙丕扬等人事迹的考证,认为《鸣凤记》并非成于嘉靖时,且进一步考证其创作时间为“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3]。笔者认为,“《鸣凤记》非成于嘉靖时”这一结论是可靠的,相关证据是让人信服的,也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可,如郭英德《〈鸣凤记〉:时事剧的发韧》一文便采用了张文所引的史料证据,结论则比较谨慎,只是称“据以上诸证,此剧创作年代不应早于万历元年”[4]。但是张文的另一观点笔者则不以为然,张文关于《鸣凤记》的具体创作年代的推考是基于对吕天成《曲品》“鸣凤”条的读解,《曲品》云:“(《鸣凤记》)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词调尽鬯达可咏,稍厌繁。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者,即此意也。”[5]张文据此写道:“吕氏认为:‘江陵时’除有《鸣凤记》外,还有《鸾笔记》与之并行于世。我以为更可说明《鸣凤记》不仅不成于嘉靖时,而且可能是在万历初年。”并在最后的结论中写道:“吕天成在《曲品》中暗示出来的《鸣凤记》成年‘江陵时’,与《鸣凤记》本身泄露出来的作品成年‘万历初’是相吻合的。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柄政’,卒于万历十年(1582)。那么,《鸣凤记》之成,应在一五七三至一五八二年之间。”笔者认为,仅就“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一语不足以推导出《鸣凤记》为万历初年的作品,因为《鸣凤记》即使产生于万历十年(1582)之后,即创作时间晚于《鸾笔记》,身为后人的吕天成也完全可以作此表述。 若此,众多论者将《鸣凤记》视作明清时事剧的“开山之作”,并以此来建构时事剧的发展史,恐怕是有问题的。至少,在《鸣凤记》的具体创作年代未清楚之前,这样的观点和论述都不免失之草率。 而且,如果《鸣凤记》果真是产生于《鸾笔记》之后(即使《鸣凤记》真的出现在万历元年至十年间,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那么从当朝人写当朝事的角度看,《鸣凤记》与时政的密切程度远不及《鸾笔记》,作者的政治勇气也相去甚远,这样一来,《鸾笔记》倒有可能才是明清时事剧的“开山之作”。 吕天成《曲品》将《鸾笔记》作者朱濑滨置于“中之下”,与高濂、吴世美、程文修、杨柔胜、全无垢等剧作家同列,吕氏除熟悉高、吴二人外,其余则称“不悉其人,但观词采,悬想才情,亦皆有学有识,可咏可歌。允为中之下”[6]。《鸾笔记》亦列于“中下品”。此外,《曲品》涉及到该剧的资料还有三条,分别是:“朱漱滨,昆山人。”然遍查史料,未见其人。“朱濑滨所著传奇一本”,注云:“此朱上舍为吴复庵作也。记江陵夺情,邹、赵诸公廷杖时事,语多凿凿,可称实录。江陵九原有知,亦当颡泚。”[7]吴复庵即吴中行(字子道,号复庵,武进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大学士张居正为其座师。万历五年(1577),上疏反对居正夺情,言辞激切,与赵用贤、邹元标等上疏者一起被处廷杖,吴受刑最惨,“气息已绝,中书舍人秦柱挟医至,投药一匕,乃苏。舆疾南归,刲去腐肉数十脔,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当时遭廷杖的五人“直声震天下[8],是一件轰动朝野的重大政治事件,朱濑滨正是有感而发,创作了这样一部时事剧。最后,《曲品》在“赐环”条云:“往余见《丹铅录》,载华生事,意甚悲之。今此记描写权佞奸态、丑态毕尽,不减《鸣凤》、《鸾笔》二记。真才士也。”[9]《赐环记》为铜陵人佘翘所作,演宋代华岳事,曾传入内廷,此剧非写时事,吕天成并举三例是因为它们都是描写“权佞奸态”。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吕氏的评价,他称《鸣凤记》“记时事甚悉”,《说文》:“悉,详尽也”,主要是赞赏《鸣凤记》能够比较详尽地描述严嵩专权至倒台期间的时政大事,而称《鸾笔记》则云:“语多凿凿,可称实录”,就忠于史实的角度而言,这一评价明显要高于《鸣凤记》。 可惜的是,《鸾笔记》已佚。除了毁于兵燹等偶然性因素之外,其可能的原因还有:首先,对于张居正之政绩,明人多所肯定,即使当年弹劾张的邹元标在天启间“亦称居正”。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讼居正冤。帝令部议,复二荫及诰命”[10]。《明史》不仅将张居正排除在《奸臣传》之外,而且给予较高的评价和一定的同情,称其“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11]。因此张居正很难和严嵩一样被视作“权佞”,这也可能是《鸾笔记》影响与传播不及《鸣凤记》的原因之一。再者,《鸾笔记》中的主角吴中行与张居正乃是门生与座主关系,虽然吴的行为是激于大义,但以门生反对师长,不免引起非议,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此外,吕天成《曲品》将《鸣凤记》列于“中上品”,高于《鸾笔记》,由于无法一窥原剧的真面目,我们只能推测《鸾笔记》在文字、情节和搬演效果上或逊于《鸣凤记》。 《鸣凤记》能否算是时事剧的“开山之作”,当俟相关资料的发现以作进一步的探讨。其实,在明清时事剧研究方面,首先要厘清概念,什么样的剧作才能被称为“时事剧”?对此,学界大致分为两种意见,有的将“时事剧”之“时事”理解为偏向于民间题材的“时事新闻”[12],更多的研究者则倾向于理解成表现朝廷斗争的“时事政治”,如:“时事剧,是指剧坛上直接反映当代政治斗争的作品”,“时事剧,顾名思义乃记时事之剧,其直接来自于当代的政治斗争,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作为社会现实表征的政治变迁则是时事剧的催生剂。”[13]从剧本演出效果而论,所谓“时事新闻”因主角为市井细民,其社会轰动效应多不如关系江山社稷的“时事政治”,尤其是明代戏曲剧本一般优先在士大夫厅堂“红氍毹”上排演,观剧受众群体中有优先选择权的是现职或赋闲的朝廷官员,他们对“时事政治”的关心远高于“时事新闻”。另外,人们对“时事剧”的理解往往是一个带有褒义倾向的剧类概念,白居易早就提出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口号,其中便隐含了“时”与“事”的价值判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联所折射出的晚明文人对时局的关切与忧心,是与此精神传统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明清时事剧大量涌现的社会与心理背景。 考虑到上述因素,笔者赞同将“时事剧”定义为与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直接相关、反映作者政治立场或理念的戏曲作品,并认为构成一部“时事剧”,应同时具备以下要素: 其一、鲜明的政治性。时事剧本是作家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关系最好的诠释,他们藉此可以更便捷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而这在古代中国显然是一种禁忌。所以此处所指的政治性与作家的政治观点并无多大关系,但不失为一种政治道德立场的强烈宣示,只不过它很难超越“忠孝节义”的话语范围。换言之,几乎所有的明清时事剧都只是披着“时事”外衣的忠奸剧。尽管如此,这件“时事”外衣也并非那么好穿上的,由于“时事”的高度敏感性,在情节组织、人物安排、唱白设计,特别是涉及到与皇帝有关的内容时必须处理得格外小心,要处处凸显其“圣明”,不吝言辞地反复称颂,防止人们将奸臣贼党的乱政与最高统治者的昏庸失察联系起来。像《鸣凤记》开场“龙飞嘉靖圣明君”、“除奸反正扶明主”和结尾“皇明圣治称嘉靖”等颂辞,无论今人看来多么言不由衷和自相矛盾,在当时则是再恰当不过的一种表达,这也可以理解成是作者避祸的一种自我保护。明清时事剧中,“皇帝”并不会上场,但至高无上的皇权阴影则无处不在,事实上,时事剧是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是否与皇帝用人、朝政得失有关,这也决定了其内容总是离不开忠奸斗争的二元对立以及邪不压正的故事结局。 其二、相对可靠的真实性。戏曲创作中,适当的艺术虚构是免不了的,也是合理的,但“时事剧”因其特殊的时代感在真实性方面有着更为严格的要求,“相对可靠”主要是基于作家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认真求实的前期准备。产生于明末的《磨忠记》(现存崇祯间刻本,秀水范世彥撰)一剧虽以魏忠贤、崔呈秀、杨涟、魏大中、周顺昌等天启人物结构剧情,但写魏忠贤本是厉鬼所化,杨涟死后为天下都城隍及群仙勘问阉党等等,皆荒诞不经,祁彪佳评云:“作者于崔魏时事闻见原寡,止从草野传闻,杂成一记,即说神说鬼,去本色愈远矣。”[14]创作者对笔下时事缺乏起码的了解,其作品自然不足以成为“时事剧”。同样是反映与魏忠贤斗争的《喜逢春》(现存崇祯间刊本,金陵清啸生,一作江宁清笑生撰),尽管也有“关公显圣”之类的情节,但对照史书,其内容与史实基本相符,还因如实描写了清兵入侵宁远、锦州的情形于乾隆间遭禁,故可列于时事剧。更能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李玉《清忠谱》,吴伟业在《清忠谱序》中盛赞此剧:“逆案既布,以公(周顺昌)事填词传奇者凡数家。李子玄玉所作《清忠谱》最晚出,独以文肃与公相映发,而事俱按实,其言亦雅驯,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15]虽然不是每一部时事剧都要达到“信史”的高度(也没必要),但是要想打动“时人”,恐怕不得不在可信度上倾注心力,否则无法取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毕竟,“时事剧”首先是写给“时人”看的。 其三、剧中主要角色应为时事人物。照此标准,凡以历史人物为创作对象的概不归入时事剧,像李开先《宝剑记》可以讨论其影射意义(“影射”所指,本身就见仁见智),但不宜将其列入“时事剧”的范畴。又如佚名的《犀轴记》,《远山堂曲品》著录,云:“是记成于逆珰乱政时,借一沈青霞以愧世之不为青霞者。”[16]该剧或有影射之义,然沈炼为嘉靖时人,此作成于天启间,故不应置于时事剧之列。此外,像吴伟业《临春阁》,《曲海总目提要》称“所演临春阁事,隐指福王也”[17],并引其讽喻诗为证,此推断虽不无道理,但也只能归入政治讽刺剧一类,不能视为时事剧。 最后,处于“共时”阶段的时效性。既称“时事剧”,就一定有个时效性的问题,但究竟多长时间内所创作的剧本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是“时事剧”界说最困难的地方。陈大康《明代小说史》在界定时事小说概念时很谨慎地提出“时差的最大范围一般似以十年左右为宜”,时差是指“作品所描述的事件的结束与作品问世之间”[18]。有的研究者在定义“时事剧”时接受了这种界定,也有的研究者提出“时间差为20年左右”[19]。在笔者看来,无论10年还是20年,其实都只是一个模糊的主观判断,缺少足够说明如此划定的充分理由。而且,在实际操作时,又因许多剧本创作时间的难考,使得这样的界定陷入更大的困惑之中。以《鸣凤记》为例,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罢相,嘉靖四十四年(1565),严世蕃斩于市,这是作品描述的主要事件的结束。假设我们认定《鸣凤记》问世于万历元年(1573),则距二事的时间差分别为11年与8年;假设我们认定《鸣凤记》问世于万历十年(1582),时间差则变为21年和19年;假设问世时间更晚,恐怕连“20年左右”都限定不了,那么《鸣凤记》还是不是时事剧都成问题了。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无休止的争论,在时间范围界定上,不必具体到10年还是20年,而应着重考察剧作家的创作过程与剧本所描述的事件或人物是否存在共时与交集,并以此作为判定之依据。像孔尚任曾于栖霞山白云庵访问过明锦衣卫张怡(字瑶星),后以他为原型塑造了《入道》一出中的白云庵道士张瑶星,剧作家与剧本人物原型存在交往关系,则《桃花扇》当属时事剧无疑。《鸣凤记》中的人物孙丕扬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才逝世,而该剧在此之前肯定已经问世,故亦符合这一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学界欲深化明清时事剧研究,当务之急要对“时事剧”的概念进行更加广泛和严肃的讨论。同时,应加大考证相关作品创作年代的力度,包括对作家生平的考证,一时无法确考的,应暂时存疑,而不必仓促纳入“时事剧”的范畴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