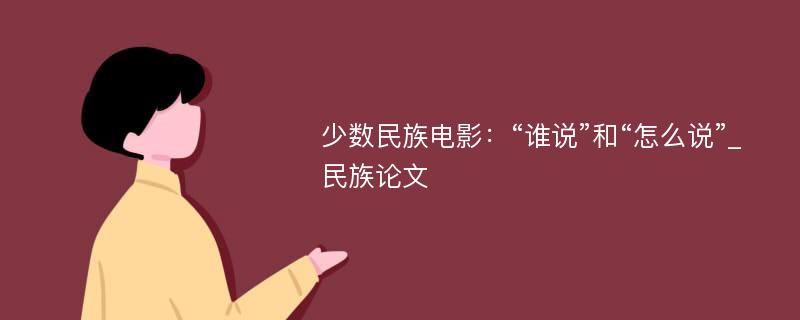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谁在说”和“怎么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谁在论文,少数民族论文,题材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新中国电影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新中国主流电影之外的,堪称“边缘”、多少有些“另类”的独特存在。毫无疑问,它曾经有效地发挥过极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完成了主流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大中华民族”和谐共存,亲如一家的现实之想象性营造。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类电影的存在,使得在今天我们回望新中国电影时并不特别觉得它是单色调。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给新中国电影版图增添了诸多艳丽的色调,像美丽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动人的少数民族民间歌舞、习俗,主流电影中往往要避讳的爱情主题,这些主流电影中经常缺失的东西,却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极为难得地保留了下来。因此,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电影增进了中国电影审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今天,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更是在一个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剧的时代具有保存文化的多样性的独特文化功能。少数民族文化的呈现是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有机组成,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指向民族文化的内部空间,成为一种具有文化认同意义的民族寓言和史诗;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作为多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有机地呈现了新的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我们的国家形象是多元的、容纳差异、多姿多彩而又和谐的共同体。
称这一存在为“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而非“民族题材电影”,既是对既成历史的尊重,也是因为去掉“少数”二字的“民族电影”的称谓在中国电影面向海外,华语电影势头不断崛起的今天会引发歧义有关。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电影”中的“少数民族”,英语中是Ethnic Groups之意,而如果去掉“少数”即Ethnic的修饰,则“民族”会与我们对外常使用的“Nation”和“Nationalism”及相应的“国家电影”、“民族电影”乃至包涵更广的“华语电影”等相混淆。
在我看来,探究今天少数民族电影遭遇的问题,需要考察少数民族电影“谁在说”的问题,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电影中创作主体的问题是很重要的。“谁在说”,还制约或决定着“如何说”。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按“谁在说”的角度,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说话主体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指建国后“十七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
正如论者指出,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题材影片“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动人的爱情表达获得观众青睐的同时,也配合国家意识形态,巧妙宣传了当时的民族政策。这些影片用歌舞仪式、语言、服饰,景观等符号构筑指认性的身份场景,以阶级认同重构他者阵营,在强调各兄弟民族情谊的基础上,顺利地将各族人民团结到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来,巩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①诚如斯言,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电影,在电影的宣传性工具性和快感娱乐性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维持了电影的文化娱乐功能,满足了观众、尤其是作为主流的汉族观众“陌生化”的观影欲望。也就是说,这一类电影在义不容辞地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之余,也有效地发挥了娱乐性功能。这是这些影片家喻户晓、为国人所欢迎的重要原因。甚至像《阿诗玛》、《五朵金花》、《刘三姐》等还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恒久记忆,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名片与审美符号。
从文化功能上看,这一阶段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的想象性再造,因而往往以阶级矛盾取代族裔矛盾,通过阶级矛盾的强化和最终的解决,阐述新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建构统一、和谐、完整的大中华民族的必然性。
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颇具寓言性。达吉无疑有一种身份分裂的痛苦和认同的困惑: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父亲、养育之恩和自小熟悉的生活习俗;一方面是工程师的汉族父亲和骨子里的汉人血缘、遥远的文化指认。但这里的民族矛盾(具体体现于两个父亲之间)在阶级矛盾的大矛盾和大中华的国家期待中得到了化解。最后,父女三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在这里,民族的隔阂、血缘的隔阂都被超越了。这个和谐的多民族家庭,正可视作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隐喻。
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光明使者的汉族父亲对少数民族父亲的宽容大度,达吉经过犹豫困惑之后的认父,双方父亲的和谐并存使得这一对矛盾达成了化解。达吉和谐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两个民族融合的中介和完美融合物。“认父”这一行为则隐喻了少数民族的回归和重新融合,从而完成了安德森认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按安德森的说法,就是“透过共同的想象,尤其是经由某种叙述、表演与再现方式,将日常事件通过报纸和小说传播,强化大家在每日共同生活的意象,将彼此共通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形成同质化的社群。”②
不难发现,在这些少数民族电影,如《山间铃响马帮来》、《冰山上的来客》、《摩雅傣》、《边寨烽火》等中,常常有一个“外来者”的形象。这些外来者一般都是解放军战士、医生、工程师等先进文明的代表者,而少数民族则常常是被“拯救”、被感动、教化的客体,注定要感化、“归来”并皈依于主体的。
第二阶段是新时期以第四代、第五代导演为主体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创作。
我们先从一部第四代导演的影片《青春祭》说起,在这部影片中,摄影机的视点与女知青的眼睛视角常常是合一的。通过摄影机镜头——一种主观镜头,她以一种悲悯而沉痛的眼光俯视被摄对象。如影片中表现她初到傣乡看到傣族男女青年对歌的情景时用了连续的三个镜头:
镜头一:(特写)李纯在看。
镜头二:(远景)反打出李纯之所见——傣族男女青年对歌。
镜头三:(特写)重新回到李纯在看,若有所悟的脸部表情。
旁白(第一人称):真想不到他们表达爱情的方式这么大胆热烈,我们内地的青年是不可能这样的(大意)。
因而在这里,农村边地,少数民族地区是被看的存在,主体并没有与对象合为一体,还是一种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的视角。正因为主体与对象之间拉开了观照的距离,也因为现代文化与傣家少数民族文化的无法填平的文化差异,才使得傣家人的生活显得那么诗意化和纯美。而且即使那么美,也逃脱不了毁灭的命运。最后从情节上看不免牵强的结尾——小村庄被泥石流吞没,其实流露了导演一种“看客”或旁观者的潜意识心理——“此曲只应天上有”。具有边缘性和反现代性特征的傣家少数民族文化,她可以欣赏,但她永远无法融入,因为她不可能成为傣家人,而且这种文化可以欣赏,但却与她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现代性理想相背。正如张颐武所指出的,“《青春祭》是缅怀和思念,又是告别和放弃。傣族的生活给予了女主角自由,但这一自由却是来自于某种边缘的民俗而不具有进入主流社会的意义,因此不可能让人完全投入,甚至最后还弃之而去”。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第四代导演审美理想与现代性追求的深刻矛盾,有一种清醒而又痛苦的启蒙理性精神在其中。
田壮壮拍《猎场札撒》、《盗马贼》的时候,已经知音寥寥,他也相当偏激地说是要为下一个世纪的观众拍片。他通过对边缘蒙昧原始地区少数民族野性生命力的张扬,隐约传达了对一直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一统的、循规蹈矩的汉文化的反思,立意是相当深远的。这些影片作为第五代影片造型美学追求的有机组成,表现出淡化戏剧性传统和叙事因素,强化影像造型并致力于开掘影像语言背后历史文化意蕴和哲理探求。田壮壮的这一文化指向,直到90年代的纪录电影《德拉姆》中仍一以贯之。在这些影片中,当少数民族文化作为理想的乌托邦出现的时候,则更多地承载了主创者对“他者”文化的想象。
与“十七年”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相似,少数民族文化的非主导性文化特征使得编导主创常常在影片中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个“闯入者”的视角。当然,与“十七年”电影不同的是,这些“闯入者”带有更浓重的新时期启蒙知识分子的味道,代表新政权的政治味道,“拯救者”的权威性则淡化了。很多时候,这些知识分子的“闯入者”或“旁观者”,没有了“政治型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权威和自信,连自己都是困惑矛盾分裂和无能为力的。如《青春祭》中感伤涟涟的女知青,谢飞《黑骏马》中汉化或现代化了的知识分子。有意思的是,应该属于“第六代”甚或再后的陆川,在《可可西里》中的文化取向与上述影片也颇为相近,也设置了一个北京来的随队记者的旁观视角。
总之,此一阶段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新时期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贯注了强烈的文化反思和文化批判精神。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电影。
此间出现了一批堪称狭义的、具有原生态意味的少数民族电影,编导演主创均为少数民族,在文化意识、自我意识上均真正以少数民族为主体。这批电影的集中出现,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国家民族电影政策的开明(如国家允许各种资本进入电影生产,从而为一批小成本的,有可能偏离主流意识形态,回避或拒绝“他者”立场的少数民族电影的生产创造了条件)等有关,更与编导人员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精英、传承者和代言人所感受到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强化和表达的需要有关。
在主题意向上,又大致可区分为两种:
其一,是民族自我身份的寻求和确立。文化的认同,往往呈现出文化认同的自豪感与身份确认的豪迈激情。如蒙古族的《东归英雄传》、《悲情布鲁克》、《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以风格独具,在中国动作电影史上已具经典意义的“马上的动作之舞”把蒙古族的历史与生活置于宏大磅礴的气势和辽阔无涯的草原中,进而展现了蒙古民族的英雄形象,既有成吉思汗、忽必烈、渥巴锡汗这样的“一代天骄”大英雄,也有斯琴杭茹那样的没落贵族之后——怀抱坚韧的民族理想而坚执淡定的平民化的“小英雄”。再如藏族的《松赞干布》,以本民族的视角挖掘出了一代藏民族英雄的文化底蕴,改写了以往汉族视角下的松赞干布形象。此类少数民族电影是对少数民族自身身份的追寻和重新书写,少数民族主创人员力求摆脱以往的“他者”视角,从而表现为民族自我意识的苏醒和强烈自觉。
其二是在自豪而平和,近乎原生态地呈现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又对本民族文化的前景表现出某种浓烈的忧思和深深地困惑。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在《静静的嘛呢石》中专注于对藏族人原生态生活的展示,他说,“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经常有一些人用文字或影像的方式讲述我故乡的故事,这些使我的故乡一直以来蒙上了一层揭之不去的神秘面纱,给世人一种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或蛮荒之地的感觉。少数民族成为他者是作为这些人常常信誓旦旦地标榜自己所展示的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反而使人们更加看不清我的故乡的面貌,看不清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不喜欢这样的‘真实’,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来讲述发生在故乡的真实的”。④再如《美丽家园》也以近乎唯美的影像向我们展现了哈萨克大草原的伤感与沉重。影片表现城市与草原的冲突与对立,草原上的人今天开着汽车而不是骑马走向城市,虽然留下“还会回来”的袅袅余音,但这只是一种记忆和想象中的心灵慰藉罢了。
在一些蒙古族电影中,这种痛苦表现得沉郁苍凉甚至给人以撕心裂肺之感。如在《季风中的马》中,世代居住在草原的牧民不得不面临“是草原还是城市”的痛苦选择。草原沙化退缩,牧民无处可居,但城市却喧嚣嘈杂,无法适应,他们面临“失名”的身份认同痛苦。这种两难的痛苦代表了不得不从草原退居城市的蒙族牧民的痛苦与矛盾心态。而从主创的角度看,也不妨说是导演思考自我族群文化存留的痛苦与矛盾心态的影像化表述。此类少数民族电影通过人物内心痛苦的开掘和对本民族与汉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仪式、习俗)与现代、乡土(草原)与城市的矛盾冲突的尴尬处境的表现,引发我们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对民族性、全球性,本土化与现代化等问题的思考。
这一类剧情片虽是虚构的,但在影像表现上偏向于原生态纪实性风格(或者直接就是纪录电影,如《德拉姆》),因而独具文化人类学意义。电影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民族地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保护作用。这是这些少数民族电影被赋予也是主动追求发挥的一个重要功能。近年的《长调》(蒙古“非遗”长调)、《鲜花》(哈萨克“非遗”阿依特斯)、《静静的嘛尼石》(藏戏、藏传佛教)、《寻找智美更登》(藏戏)等少数民族影片,表现尤为突出。
以上三个阶段的历时性划分,实际上从共时性的角度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类是汉族作者(编导演)主创,一类是少数民族作者(编导演)主创。这实际上也是从“谁在说”的角度,划分为“他者的言说”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这样两类。有研究认为,理想化的“少数民族电影”应该是由少数民族作者主创的,以少数民族为题材,并反映少数民族文化内核的电影。以此为据,王家乙导演的《五朵金花》是汉族导演创作的反映“大跃进”的电影,因为它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也不是“少数民族电影”。⑤在严格的、较为纯粹的意义上,这样的划分是有道理的。
根本上而言,血缘身份和文化身份会决定性地影响到言说方式也就是“怎么说”的。汉族导演总是难免于“他者”立场。有些时候,这一类电影并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常常还是想当然甚至是“越俎代庖”的。借用庄子的那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寓言,有时候,汉族导演恐怕很难体会到少数民族的真正的内心世界。据材料显示,在当年,少数民族观众对《山间铃响马帮来》中汉族演员饰演的苗族姑娘并不满意,对影片中的接吻镜头颇有异议,《刘三姐》上映时,壮族观众认为影片并没有多少自己本民族神话传说的色彩。
在此类电影中,少数民族文化风情有时难免成为“他者”欲望的对象化存在,或是出于商业化视觉奇观需求的考虑,或是借助另类题材构建一个具有多种文化可能性的影像世界。无疑,少数民族题材的文化边缘性特征往往可以为文化的思考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王全安就曾坦言之所以选择以内蒙草原为背景,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拍摄《图雅的婚事》,就因为这片环境更为极端的土地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⑥尽管《图雅的婚事》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但在国内却受到来自少数民族的抗议。影片在民族内与国际上两种截然相反的遭际发人深省。
而少数民族导演从自我族群的视角出发来审视自己的民族以及不可避免的、与他民族(主要是汉民族)的紧张微妙的关系,他们会表现出微妙的矛盾复杂心态:他们大多受过主流文化教育,出于商业与市场的考虑,在电影中还是会不自觉地注目于民族特色的歌舞和独特风俗,也会考虑到政策的允许、电影审查等而偏向主流性的表述。但另一方面,作为民族精英,少数民族导演具有更为强烈的族群意识,往往更为自觉地从自我族群的文化内部出发思考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现实处境与未来命运等问题。他们在理智上接受的现代性立场与感情上对民族文化的热爱之间会发生严峻的冲突(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所以,此类狭义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常有矛盾与痛苦的咀嚼,既具有人类学意义,更不乏民族身份思考和文化认同意义。毫无疑问,少数民族电影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少数民族的心态,有助于其他民族更好地理解少数民族。
著名东方学家萨义德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⑦这可以用作我们看待少数民族电影——其无法替代的文化功能,人类学、文化地理学意义,文化的多元性价值等所应持有的理性准则。
当然,客观上虽然可以分为这样两类,但实际情况会复杂得多。我们也不必仅以主创人员的民族身份为不二的准绳。更为重要的是,拍少数民族电影的人是否真正到少数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感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并加以真实的艺术化的表现。这方面,少数民族导演自然有优势,但不应排除其他民族导演的努力。导演章家瑞就非常自信地认为,“我们太需要来自民族自身对本民族文化的信念与信心,需要真正的民族视角!”他认为,民族电影的成功应当是“从一个民族自身出发触摸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状”。⑧因此更为理想化的标准应该是影片是否真正平等、平和、真实地呈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和精神。按此标准,也许归根到底只有两种电影:真正的少数民族电影和“伪少数民族电影”。
注释:
①邹华芬《十七年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身份认同表述》,《电影文学》2008年第7期。
②[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③张颐武《第四代与现代性》,载王人殷主编《与共和国一起成长》,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80页。
④转引自李飞《静静的嬗变》,《中国民族》2005年第12期。
⑤参见王志敏《少数民族电影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电影家协会编《论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第五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⑥转引自董伟建、余秀才《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刍议》,《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⑦[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6页。
⑧同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