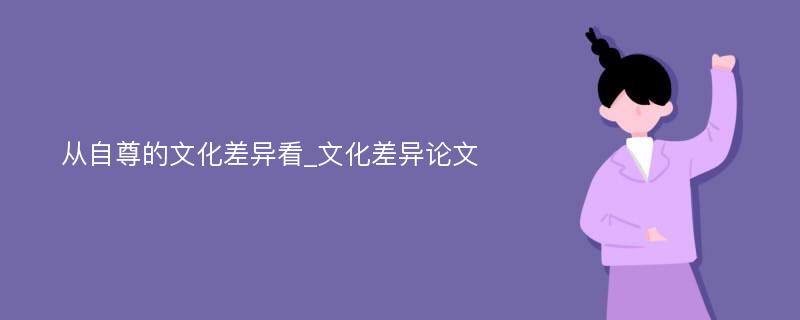
从自尊的文化差异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尊(self-esteem)是个体对自己的总体的积极态度。自1890年詹姆斯在其《心理学原理》中对自尊进行论述后,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研究者也对自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自尊是否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成为研究者争论的焦点。
自尊是具有文化普遍性的。研究证实,自尊作为一种高级的心理需要具有文化普遍性(蔡华俭,丰怡,岳曦彤,2011)。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自尊也具有很多相似的功能,能够促进个体的心理健康,提高幸福感(Baumeister,Campbell,Krueger,& Vohs,2003;Cai,Wu,& Brown,2009),能够缓解失败产生的情绪压力(Brown,Cai,Oakes,& Deng,2009;张向葵,田录梅,2005)和减缓死亡焦虑(Burke,Martens,& Faucher,2010;张向葵,郭娟,田录梅,2005)。
但是,自尊具有文化差异。这一观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有研究者提出(Heine,Lehman,Markus,& Kitayama,1999),他们主张自尊的文化相对论。文化代表了某些特定群体所共享的并异于其他群体所共享的一系列分散的行为规范和认知(Lehman,Chiu,& Schaller,2004)。个人的心理与行为必然受其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制约,因此,不同文化的个体在自尊上虽然有其相似性(即所谓泛文化的),但是仍有其差异性。本文将从自尊的文化差异说起,并进一步讨论应当怎样研究中国人的自尊问题,以就教于大家。
2 自尊文化差异的三个主要方面
根据既往的研究,自尊的文化差异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三个主要方面:自尊的根源性、自尊的包容性和自尊的表达性。
2.1 自尊的根源性
在现有的文献中,自尊被定义为个体对自我持有的一种情感体验或对自我的整体性评价。这种自我的情感体验或认知评价的根源,其实就是遗传与环境交互作用的问题。自尊受遗传因素的制约(Neiss,Sedikides,& Stevenson,2002),但自尊显然不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从环境影响的角度来看,自尊的来源是个体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的有意识判断,而个体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社会文化价值观塑造的。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构成要素,是文化范畴中主观文化的一部分,是最突出的一种文化体现。自尊在相当程度上植根于社会文化价值观。梁漱溟(1990)认为“在中国没有个人观念;一个中国人似不为其自己而存在。然在西洋,则正好相反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在家庭、社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而西方文化中的人们讲求个人的自由、平等、博爱,其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能力的突显。已有研究发现,同样是低自尊者,美国人对其个体品质的评价比中国人更积极,而中国人对其社会品质的评价比美国人更积极(Brown & Cai,2010)。日本也是自尊跨文化研究中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研究也发现,日本被试的自尊对于社会事件比北美(美国和加拿大)被试更敏感,而北美被试的自尊对于个人成就有更高的敏感性(Nezlek et al.,2008)。西方人的自尊更强调个人的能力和成就,与此不同,中国人具有独特的自尊来源。黄希庭等(1998)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的总体自我价值感、一般自我价值感和特殊自我价值感均包含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杨烨(2008)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自我评价的领域包括国家民族和家庭父母的社会自我维度。杨国枢等人通过对台湾和中国内地大学生的自尊范畴研究,提出华人有四种主要的自尊:个人取向自尊、关系取向自尊、家族(团体)取向自尊和他人取向自尊,后三者则均为社会取向自尊(翁嘉英,杨国枢,许燕,2009)。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社会取向在中国人的自尊中占有重要地位。杨国枢等人认为,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的自尊是个人取向或自我取向的,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的自尊个人取向较弱,集体取向的自尊较强(翁嘉英,杨国枢,许燕,2009)。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个体可以通过与受到积极评价的群体的联系和与其他群体的比较维持积极的认同,从而提升自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集体自尊似乎更多是为维持和提升个人自尊服务的。当群体地位高或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较高时会出现对内群体更积极的评价,否则可能会出现内群体贬损(Andreopoulou & Houston,2002;Rudman,Feinberg,& Fairchild,2002)。当内群体表现不佳时,他们也很少会持有内群体偏好(Crocker & Luhtanen,1990)。而在集体主义文化(如日本、中国)中个体的集体自尊并不受群际优越性或内群体表现的影响(Brown,2007;王伟宇,钟毅平,童真,周海波,2009)。对中美被试集体自尊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也发现,中国人对集体自尊需求的关注程度更高,而美国人对个人自尊需求的关注程度更高,东西方集体自尊差异的根源在于两种文化对于集体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同(魏丽,2009)。
可见,自尊在相当程度上是植根于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具体体现在自尊的来源和关注点上。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的自尊更强调个人的成就和品质,尽管群体成员身份构成了他们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但在他们看来群体仍然是第二位的,他们更关注个人自尊。而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自尊在强调自我的成就和品质时,更强调其社会性和集体性。
2.2 自尊的包容性
自我是什么?它包含哪些内容?其最主要的是自我认同以及自我与他人等方面的关系。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更多涉及的是个体自我认同问题,而在东方文化中则更多涉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朱滢,2007)。无论从群体层面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还是从个人层面的独立型-互依型自我来看,西方人都倾向于知觉他们是独立于他人和环境而存在的,而东亚人的自我是由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关系来加以界定的(Chiao et al.,2009)。
自我概念的基本文化差异是自我与他人的分离或联系。通常认为,东亚人自我包容性更强,而西方人自我-他人区别性更强。自我参照效应的研究结果发现,与西方被试不同,中国被试表现出母亲参照效应(朱滢,张力,2001)、朋友参照效应(管延华,迟毓凯,2006)和恋人参照效应(周丽,苏彦捷,2008)。中国被试以内侧前额叶皮质(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表征自我和母亲,而西方被试的自我与母亲以及最好的朋友在脑机制上则是分离的(张力等,2005;Zhu,Zhang,Fan,& Han,2007)。在文化启动效应研究中发现,美国文化启动后,中国大学生的母亲参照效应降低(Sui,Zhu,& Chiu,2007)。在神经机制上也证实,对于受中国和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双文化被试,西方文化启动诱发了自我-他人区别性,增强了母亲和非重要他人与自我的神经差异;而中国文化启动诱发了自我包容性,降低了母亲和非重要他人与自我的神经差异(Ng,Han,Mao,& Lai,2010)。自我参照效应的结果研究证实了自我包容性的文化差异,自我和亲密他人之间的包容性与区别性是受文化调节的。
由此可以推论,自尊作为自我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可能具有包容性的文化差异。费孝通(2005)认为,我国社会的格局是以“己”为中心,通过家人、熟人、陌生人等形成的呈现差序格局的由近及远的社会关系。关系取向是中国人的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具有关系形式化和关系决定论的特点,强调以关系来界定身份,及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依亲疏程度而异(杨国枢,1992)。这就使中国人的自尊不可避免地与亲密他人联系起来。面子被看作是中国人他人取向的自尊。对台湾的被试群体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群体觉得有面子和没面子的社会事件均不同程度地与自己、父母(或子女)、朋友的品德和成就事件有重要关系(刘丁玮,2002;苏珊筠,黄光国,2003);在情绪体验上也同样如此,相对于陌生人、邻居、老师等而言,父母、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成就和品德对个体的愉快和羞耻情绪影响更大(苏珊筠,黄光国,2003)。这些结果显示,不仅自我的属性,与自我有关的亲密他人也会对中国人的自尊产生重要影响,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关系。但是中国人的自我包容性可能也仅限于亲密他人,而不能概括化到非亲密的他人。而在西方则不同,自我评价维护模型(Tesser,1988)认为,在对于个人重要的领域,当亲密他人的表现优于自己时会降低个体的自我评价,个体会以最大化自我评价收益和最小化自我评价损失的方式来改变亲密度。
总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个体自我的包容性是不同的。自尊作为自我的重要部分,其包容性也存在文化差异。西方文化中个体是独特的、与他人相分离的“自我”,个体的自尊以独立性的自我为中心,即使在自我与亲密他人的关系中,个体仍然会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维护和提升自尊;而中国人的自尊不只涉及个人,还包容了与自我有关的亲密他人,这种包容性体现在“荣辱与共”的社会投射过程中。
2.3 自尊的表达性
人的心理与行为没有哪一种是可以脱离社会文化背景而产生的,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个体都必须适应他/她所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表现出与该社会文化标准相适应的心理与行为。有研究者认为,文化中主导的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标准是决定在具体情境中表达积极自我评价的一种可能因素(Kim,Chiu,Peng,Cai,& Tov,2010)。在东方文化中,自我呈现的一个主导标准是谦虚。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均对自谦的重要价值有所论及,“虚怀若谷,谦恭自守”是儒家强调的修身之道。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仍然认为谦虚具有重要的个人和人际意义(胡金生,黄希庭,2009;Sedikides,Gregg,& Hart,2008)。相对于西方人而言,这种文化标准抑制了东方文化中人们直接地表达积极的自我评价(Brown,2006;Cai,Brown,Deng,& Oakes,2007;Cai et al.,2011;Tafarodi,Shaughnessy,Yamaguchi,& Murakoshi,2011)。虽然中国人也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我肯定,但更主要的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表达自尊。如何表达也是自尊文化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
研究发现,一些东方文化(如日本、中国、泰国)中的人比西方文化(如美国)中的人有较低的自尊水平(Cai et al.,2007;Cai et al.,2011;Yamaguchi et al.,2007)。个人主义文化启动比集体主义文化启动使双文化个体表现出更高的自尊水平(Lee,Oyserman,& Bond,2010;Tam,2009)。而东方文化中个体积极的自我评价更多在内隐层面得以显现(蔡华俭,2003;Kitayama & Uchida,2003;Yamaguchi et al.,2007)。但是在情感层面上东方文化中的个体比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有较高的自我悦纳水平(Cai et al.,2007;Tafarodi,Lang,& Smith,1999;Tafarodi & Walters,1999)。对53个国家16998名被试的文化取向和自尊进行研究也发现,在控制了自我悦纳和性别之后,最具个人主义文化国家比最具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个体报告显著较高的自我能力水平;但控制了自我能力和性别后,最具个人主义文化国家比最具集体主义文化国家的人们自我悦纳水平较低(Schmitt & Allik,2005)。这些研究都显示出,文化会直接影响个体自尊的表达方式。与西方文化不同,东方文化中个人自尊的表达是含蓄的,在内隐和外显、认知和情感上是分离的。
自尊的表达方式是多方面的,在公私情境中自尊的表达也是存在文化差异的。西方人更常公开地表达积极的自我评价,更倾向于采用时间和社会相比较(Ross,Heine,Wilson,& Sugimori,2005)、自我服务归因偏差(Kitayama,Markus,Matsumoto,& Norasakkunkit,1997;Mezulis,Abramson,Hyde,& Hankin,2004)等策略维持和提升自尊。但是对于东亚人,当反应是私密的或匿名之时他们更可能作出积极的自我评价(Kim et al.,2010;Kudo & Numazaki,2003)。这说明,东方文化中的个体在公开和私密情境中对自尊的表达是有差异的,这一点也与西方人不同。
显然,文化会影响自尊的表达方式。西方文化中的个体在外显与内隐层面、公开与私密情境都倾向于以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尊,借助一系列的策略来提升自尊;而东方文化中的个体虽然在内隐层面和私密情境中表现出较高的自尊水平,但在外显层面和公开情境中则更含蓄地表达积极的自我评价。
3 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讨论了中国人的自尊不同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的一些表现之后,使我们想起以下三个问题很值得加以讨论。
3.1 自尊的内涵
对自尊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采用西方对“self-esteem”的界定,满足进行跨文化比较需要构念等同这一条件。但是采用这一界定对中国人的自尊进行研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这种西方的学术性概念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尊”概念是不同的。在我国辞源中明白地写道,自尊有自重(韩非子诡使:“重厚自尊,谓之长者。”)和自加尊号(史记楚世家:“楚熊通怒曰:‘吾光鬻熊,文王之师也……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的双层含义(辞源,1988);汉语词典解释道,自尊是形容词,指尊重自己,不向别人卑躬屈膝,也不容许别人歧视、侮辱(汉语大词典,2003)。在这种概念框架下,自尊更多出现在道德伦理领域。中国人的“自尊”有其特殊的内涵,有研究者认为,汉语中的自尊主要用于描述一种防御方式或防御机制。而西方的自尊是指个体对自我的整体性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感觉(赵志裕,康萤仪,2006/2011)。西方“self-esteem”的学术性概念体现的是中国人的哪一种心理现象?把这个术语翻译为“自尊”,把中国人当作美国人进行研究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在中国民众中有应用推广价值吗?这些问题都是研究中国人的“自尊”需要加以澄清的。不研究中国人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的自尊,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人类的自尊。我们研究中国人的自尊,首先要弄清其内涵,切不可盲目搬用西方心理学的概念,需要的倒是用批判的头脑去审视它们的概念是否能适用于我们中国实际。看来,我国心理学家需要对心理学中的“自尊”进行“正名”,这是研究中国人的自尊的基本前提。
3.2 自尊研究的内容
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人自尊的范畴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自尊以个人取向为主导,而中国人存在个人取向、关系取向、家族取向和他人取向四种特殊的自尊范畴(翁嘉英,杨国枢,许燕,2009)。要全面地了解中国人的自尊特点和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社会心理问题就不能套用西方心理学中现成的概念和理论,而应当全面思考在我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等诸种条件下的自尊结构和机制。目前我国心理学中对中国人自尊的研究基本上是采用西方的研究思路,集中研究的是个人取向的自尊,而对与中国人密切相关的关系取向、家族取向和他人取向自尊却鲜有研究,完全失去了自尊研究的中国文化主体特色。其实,在中国,家庭是最重要的内群体,中国人有着浓厚的家族荣辱观,强调“家丑不可外扬”、“荣辱与共”的连带关系。中国人的自我-他人关系错综复杂,呈现一种差序格局,中国人的自尊是否也存在这种关系特异性?与重要他人的关系中,个体维护和提升自尊的方式是什么?与西方人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方式的区别表现在哪里?等等,显然我国心理学家需要改变西方的研究思路,需要深入了解我国的传统和现实,发展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来描述和解释中国人的自尊。
3.3 自尊的研究方法
中国人的自尊是很复杂的,是不同于西方人的,而目前对它的研究主要涉及其外显和内隐两个层面。对中国人整体自尊的研究,最常用的测量工具是Rosenberg自尊量表(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RSES)(Rosenberg,1965),以及Tafarodi等人(1995)的自我能力和自我悦纳分量表。这只能表明中国被试对西方自尊测量工具的反应,而不是真实中国人的整体自尊,至多测得的是中国被试对独立我题项的反应。有研究指出,用RSES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国家进行的跨文化研究有更大的概念化差异(Baranik et al.,2008)。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国学者对中国人的真实自尊是了解得很少的。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脉络中仔细认真地分析自尊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因素的关系,采用多种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例如采用文献分析法、深度访谈法、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等,贴近中国人的生活实际来研究中国人自尊的结构和机制,而不是套用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对于人格研究中国化,包括对中国人自尊的研究,就方法学而论,它绝不只是一项缺乏感情的例行公事——设计一个问卷或实验→展开调查或实验→收集问卷或数据→整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写出论文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感情和生命投入的过程,是有灵魂的,是要全心全意做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既要尊重被研究对象也要尊重自己的良知。这样,中国的心理学才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服务,从而为人类的心理学知识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做学问是要有感情、全身心投入的,就像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人间词话》)。我们相信,会有更多的有志者投入人格研究中国化的工作。
总之,被心理学家所研究的对象——人的心理和行为是受社会、文化、历史和遗传制约的,生活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下的人,其心理和行为必然有其相似性和差异性。同时,研究者也不是生活在社会真空之中,也是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和遗传因素的制约,不同国家的研究者所探讨的问题、所提出的假设、所构建的理论、所采用的方法等等,无不深受其社会文化的影响,因而各不相同,各具特色。用中国人的观点研究中国人的问题。这也就是我们坚持人格研究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理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