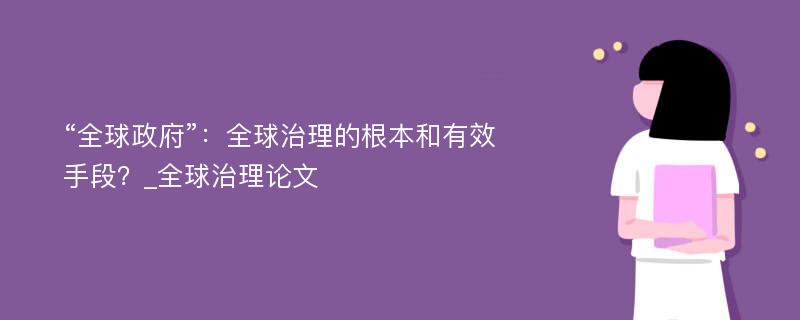
“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球论文,手段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06-0016-23
一、危机四伏的世界缺少根本性解决方案
那些指望世界很快从危机中“复苏”、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所谓“后危机时代”的人们,实际上低估了全球问题的严重性和长期性。
全球问题的“解决者”均是全球问题的“制造者”。要让问题的制造者也成为问题的解决者,这是一个对方案设计者提出的高难度的题目。目前全球问题的国际“集体行动”之所以难以取得有效进展,主要是因为问题的制造者实际上阻碍着问题的解决。主流世界(国际体系)回避采行根本性的解决方案,而一些号称是国际协调和国际合作的解决问题方案,顶多是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如2008年的金融海啸)下的“危机管理”,解一时之忧,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
以下为当前一些最为严重的全球危机:
第一,世界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单极世界”导致了世界的巨大失衡。目前的金融危机,中心在美国和欧洲,席卷全球,但实际上还只是全球经济危机的最初表现。美国、欧盟和日本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三大传统地带,但它们已经全部陷入深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之中。在可预见的未来,美欧日依然难以从债务危机中解脱。美欧日对付债务危机的做法,可用的有效手段很少,无非是两种:一是把快要爆炸的“定时炸弹”的时钟往后拨,推迟危机的大爆发;二是寻求转嫁危机的外部途径,在这方面,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新兴经济体”。
第二,能源危机恶化。目前的焦点问题是,核能向何处去?在这个“工业化时代”,核能一度被当作了解决“能源安全”的主要出路。事实上,若不考虑核能转化为核武器,日本等国家一直把核能当做“能源安全”的支柱。但是,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发生,人们终于认识到核能是不安全的能源。因为不仅是任何安全技术都有其不安全的限度,而且,核电行业如同其它工业化部门一样产生的必然“外部性”(“副作用”)——核废料,无法得到安全、彻底根除隐患的处理。
第三,政治危机。2011年,阿拉伯世界此起彼伏、持续长久、规模巨大的政治“起义”与“革命”,让人联想到1815年前遍及欧洲的革命(当时最典型的革命国家是法国)。阿拉伯动荡的“外部”根源是美欧为中心的全球化使阿拉伯世界的多数公众更加赤贫和被剥夺。他们能做的首先是把勾结全球化外部势力的专制政权推翻。阿拉伯世界的人民终于用行动推动了全球民主。阿拉伯民主震撼了西方,在某种意义上揭穿了西方保守势力的长期伪善: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这些国家真正的民主治理。
第四,国家混乱、解体和无序。一些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如索马里,继续陷入长期的混乱和无序。在国家分裂方面,苏丹一分为二,这也许意味着非洲大陆新一轮国家裂变的开始。非洲目前的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独立运动(“非殖民化”)的产物。为了维持后殖民化时代非洲大陆的国际秩序,非洲国家、西方国家和联合国,一直小心翼翼地希望维持非洲国家边界和领土现状,而不是打破现状。如今,南苏丹的诞生,不仅将鼓励其他希望独立的地区和人民,而且代表着西方的对非政策的历史性变化。
第五,新的大国纷争和地缘战略冲突正在酝酿。东亚地区——“发展”上的“成功”使其成为继欧美之后公认的世界权力中心。目前普遍流行在西方的“全球权力转移”说,加强了东亚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但接下来,不可避免的权力纷争将使这个地区很可能成为危机和冲突的中心。为了对付霸权的衰落,美国的根本策略之一是新的联盟政策,以“崛起了的中国”为对象,① 布局与中国的新战略关系,包括“再冲突”。②
二、“国际治理”及其“改革”
冷战刚结束时,就有人主张改革联合国。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冷战后”时代的第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开始了联合国改革的进程。不过,二十年来(1992-2011)关于联合国改革的讨论居然仅仅聚焦在改革联合国安理会上。1997-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关于改革现有国际经济制度(国际金融组织)的呼声越来越响亮。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改革国际经济制度似乎已经完全提上议程。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运作,国际经济制度的改革集中在让“新兴经济体”增大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话语权”上。
“国际治理”这个词,很难考证出自什么时候,③ 但这个词的历史或许比“全球治理”一词要长一些,也许这两个词都是伴随着“治理”一词的问世而一起出现的。在“治理”前加上“国际”和“全球”代表着两大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世界秩序学说。
“国际治理”强调的是现有民族国家体系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中心性,而“全球治理”则意味着仅仅依靠国际体系,显然不足以解决全球问题。全球治理指的是解决全球问题方案的全球性,即全球问题全球解决。全球体系显然超越了国际体系,是对国际体系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国际治理”的潜台词是,1945年以后形成的国际体制及其国际制度、规则和组织并不应因为全球问题的大量存在和增长而被新的国际体制及其国际制度、规则和组织取代。1945年诞生的这个体制,有些是破旧的,有些是不足的,但经过修补和完善,还可以很好地工作,这也是有人主张“国际治理改革”的原因。
G8等“西方的自由秩序”(WLO)代表的主张基本上是“国际治理”及其“国际治理改革”。而被认为和自我感受是这个秩序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受益者之一”的一些力量,也大体接受和主张“国际治理”及其“改革”的世界观。
而“全球治理”代表的是一种对“国际治理”的挑战。现存国际体制包括国际制度,在解决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中的作用和效果有限。甚至,它们本身是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的一部分,需要对其动大手术(这就不仅是“改革”)。甚至需要重建,甚至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是大大超越了“改革”的,不仅原来处在边缘的、弱小的“国家行为体”要参加进来,而且原来没有参加、被排斥的“非国家行为体”也要参加进来。
应该说,由于涉及不同的价值、利益,到目前为止,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并没有真正的“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主张者实际上是少数派。
许多人、机构和势力是介于“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之间,有时混淆这两个概念,或者不加以区分它们。G20,这个奇怪的非正式“小圈子”,居然使用了严重缺乏定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的术语。因为这个组织不仅包括了主张“国际治理”的保守力量,而且包括了主张颠覆现存国际治理的进步力量。当G20在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上宣布要成为“主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后,一些西方国家,如加拿大和日本,则迅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G20要取代G8。
三、“没有统治的治理”自相矛盾
大体看,“全球治理”一词诞生在“新自由主义”达到其第一个高潮的1989至1991年。当时,西方出现和流行“民族国家终结”的看法,以为国家(政府)正在让位于市场等“非国家”力量。在这个氛围下,有的全球治理学者提出了“没有统治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要“政府”,但又要“治理”,本身代表了一种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自相矛盾的深刻困境。由于此种“全球治理”理论排斥政府,试图降低政府的作用,高扬市场力量,尤其是金融市场(如投资银行)的作用,“治理”似乎得到比“政府”更大的推崇,导致许多人津津乐道“治理”,而简单化地诟病“政府”。
实际上,在非英语世界,语言和情景不同于西方的英语世界。“政府”和“治理”本来就让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两个词对于英语是外语的人来说,其同词源和词根,让人困惑。而在中文中,“治理”总是被理解为是“政府”的事。在中文中,“没有政府的治理”理念中的“政府”应该被正确地理解为“统治”,④ 否则,语言文化在转换过程中,生搬硬套,必然引起理解的错误。
由于西方化和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中的巨大利益,非西方世界也“进口”和实践“治理”。中国在2001年加入代表“新自由主义”最大成果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政府”愈加成为“小政府”,或者,为了扫清市场扩张的障碍,“政府”被迫成为“小政府”。
四、“政府”重新回来?
那些一直观察“没有统治的治理”的学者,如英国的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r),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前夕,其论著表达了对“没有统治的治理”而形成的“赌场资本主义”的极度震惊和犀利批评。⑤ 需要指出的是,斯特兰奇一开始是高度评价那些处在全球“金融结构”控制位置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政治决策者在“新自由主义”教科书中找不到任何解决危机的方案。⑥ 为了对付危机,“政府”而不是“治理”堂而皇之地“回来了”。不仅有持续不断的政府“刺激”(stimulating)、“纾困”(bailout)计划⑦,而且有国际的“宏观经济政策合作”。⑧ 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非常着急地希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出钱出力,“拯救”“全球经济”。所以,金融危机大敌当前,“凯恩斯主义”不仅回到了国内政策,而且作用到了国际合作。于是,在经济学领域,学者们争辩着,到底是“市场”好,还是“政府”好。争论到现在,人们发现,政府的“救市”,又造成了新的问题,酝酿着更大的危机风暴。而更大的金融风暴中,“政府”破产已经是现实。
五、“全球政府”——一种新的替代方案?
2010年10月31日,上海“世界博览会高峰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粒子物理和弦理论的核心人物”、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物理研究所所长格罗斯(David Jonathan Gross)发表了《科学与城市》的“主旨演讲”:
“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虽然它可能会带来创新的科学技术,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但是真实的挑战并不是在于科学家,而是在于我们的政策制定者、经济学家和政府。所以作为一个科学家,在这些方面都是一个外行,我可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们最终必须要建立一个经济和政治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不能建立在无限的不可持续的消费和增长的模式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最后,我们必须实现全球治理,建立‘全球政府’。20世纪科学界的最伟大的英雄——爱因斯坦,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曾经说过,我认为全球现有的主权国家的体制只能带来粗暴、野蛮、战争和非人性,只有全球的法律和规则才能够带领我们向前实现文明、和平和真正的人性。爱因斯坦勇敢地迎接了核武器以及核威胁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今天仍然存在。但是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挑战,那就是环境的灾难。而这个问题甚至比核威胁更加严重,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要所有的国家共同努力。而最终在我看来,必须要建立一个全球的政府。我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一点,而不能再拖延了。”
格罗斯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在世博会的讲话提到爱因斯坦的“全球政府”,相信在中国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甚至会为他如此讲话感到奇怪。中国媒体自然对此也兴趣寥寥,笔者失望地注意到,几乎没有媒体记录他在此次演讲中所谈的关于全球政府的观点。
而格罗斯在世界上并不孤独。在全球多重危机的作用下,在心智、理想、专业、经验、贡献等方面有资格提出这样主张的人物,还有很多。2011年6月,金融危机中诞生的中国“最大智库”之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了其第二次“全球智库峰会”。这次峰会提供的一份材料是介绍为一些人熟悉的法国经济学家、思想家、未来学家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全球政府”主张:“全球化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极端,各种国际法规和准则也在逐步趋同,特别是人类的价值基本有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也有国际社会比较认同正当性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目前应该对成立全球性民主政府进行思考”。阿塔利提出“要对全球治理进行更为有效的改革,需要在十个方面进行有意义的工作”:务实利用现有联盟、认识人类存在的理由、更加警惕威胁、遵守现有国际准则——一系列世界性法规、少边主义——逐个项目推进、政府理事会、持续发展公会、民主联盟、为全球政府筹措资金、世界泛国家主义。⑨
阿塔利的“全球政府”建议,是在许多西方“国家破产”⑩ 后的必要的替代方案。目前的全球危机实际上正在导向全球毁灭。所以,阿塔利指出的全球政府方向实际上是一个避免全球毁灭的新的世界秩序框架。
六、重新定义和思考“全球治理”
目前,有许多对“全球政府”的误解、攻击和偏见。这些误解、攻击和偏见,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狭隘、无知,就是来自帝国主义。原因很简单,无论对民族主义,还是对帝国主义,建立世界的民主政府,都是对它们的挑战。许多人对深重的全球危机缺少意识、判断和根本应对之策,以为还有除了“全球政府”之外更好的解决全球危机之策。
众所周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所谓“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我们完全可以以“全球政府”作为与“无政府状态”相对的另一种假设。以“全球政府”为假设,“全球关系理论”就能成立。对“全球治理”,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全球治理不是排斥政府,不是制造出一种“治理”和“政府”的新的“二分”。也就是说,全球治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是区分“政府”和“治理”,而是如何超越目前的民族国家架构、原则和方法,形成能够管理全球的原则、架构、规则和制度。
原来的“全球政府”构想是产生一个主权之上的主权,即超主权,这个思想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不可行性。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去除其不可行性,保留其合理性。“全球政府”的基本条件也正在逐渐形成:首先、全球化的经济。这一点超出许多漠视者的想象。一个个的在多国经营的公司,其规模和力量超过许多“国家”,而且打破了“国内”和“国际”的界限,是当今的一个个真正的“帝国”。不过,全球化的经济被少数人和集团控制,多数人、多数国家、多数团体在全球化中变成苦力,承担着全球化的成本、外部性,这正是全球治理要正视、解决的根本问题。
其次,民主化,民主国家的数量和民主的质量都在增长。民主是解决问题、突破僵局、化解冲突的几乎唯一的方式。这是建立和形成全球性的全球政府的必要、基础条件之一。世界上多数国家在走向民主,只是这样的民主在多数情况下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内部。这样的民主若是进一步扩大,可变成全球民主,即全球民主政府。在欧洲、新加坡、沙特、美国和日本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必须有权利加入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以某种正当、合法的形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演变,否则,全球化世界最大的政治不公平,即全球的流动人口,被剥夺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三,“国际治理”,即现有的在全球和地区层次上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现有全球性的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并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没有全球政府的功能,恰恰相反,如同上述阿塔利指出的,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全球政府的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一直介于所谓“政府之间的国际组织”和真正的全球中央性的、有着更大自主性、超越民族国家之间的全球治理。欧洲联盟勿需多说,非洲联盟(AU)、南方共同市场(South American Common Market-MERCOSUR)或者南美洲国家联盟(South American Union-UNASUR)、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联盟(ASEAN)(11) 等均是具有程度不同的全球政府功能的地区组织。实际上,在许多人反对“全球政府”的同时,却越来越依赖这些已经具有全球中央政府性质的国际组织。
第四,目前的“全球政府”实践。在全球层次难以实质性地实践的“全球政府”,却在地区层次开花结果。如上所述,欧盟首先意味着一个在地区层次上的“全球政府”。“无政府状态”的发源地欧洲,最早走出“无政府状态”。欧洲联盟(尤其是欧元区)的实践对在全球层次上的“全球政府”是有借鉴、先导意义的。在当前的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形势下(这个危机将持续数年),欧元区的创始国——法国和德国,已经提议设立欧元区“经济政府”。(12) 欧盟债务危机的出路只能是更深入的一体化,而不是从一体化后退(比如让欧元终结)。当然,地区范围内全球政府的实践,难免要继续遭遇和承受巨大的风险。
将来非常有必要实行“全球政府”实践的一个地区是“东北亚”。“东北亚”涉及三大国(中国、俄罗斯、美国)和中等实力大国(日本、韩国、朝鲜),以及资源和领土大国蒙古。历史上,这个地区充满了纷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在这里存在过或者仍然存在着。如何缔造新的东北亚地区秩序?建立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东北亚共同体?在思考方向上,地区层次上的“全球政府”可能是一个指导原则。(13)
而在全球层次上。目前的联合国处在一个最为关键的“十字路口”,联合国可能更加边缘化和失败,也可能被起死回生。关键是要落实、再生联合国创始时的伟大理想,以及按照“全球政府”模式改革联合国(目前关于联合国的改革是按照传统的权力争夺的国际政治进行的,毫无疑问,这样的争权,注定要让联合国改革陷入僵局和死局)。目前,其重获力量的关键是改革目前的全球性中央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七、中国的战略和政策
“世界”不同于“国际”。原来的中国的“世界观”,而非中国的“国际观”更有利于“全球政府”的出现。我们需要更新的“世界观”,而非更强化的“国际观”。民主化国际体制(“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一个正确的战略思路,但是,仅有如此世界诉求还非常不够。许多在“国内治理”上尚未选择民主治理的国家,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国内民主。国内民主是全球民主的必经之路。
国际治理改革,包括中国在现存“国际治理”中更大的“话语权”,只是维持和加强了现存国际秩序——旧的国际秩序,未必有助于真正的全球治理,即对缓解、甚至解决全球危机发挥根本作用。为谋求在IMF中一个副总裁位置,继续帮助维持IMF的欧美主导体制,是在推动IMF走向全球民主上开了倒车。
关于联合国改革。中国似乎在这方面缺少真正的建树,狭隘的、近视的、民族国家的利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阻挡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视线。
关于“另起炉灶”。仅有对“国际治理”的“改革”是不够的。必要的“另起炉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可以造就一个不同于IMF的“亚洲货币基金”(AMF)。AMF若能够在预防下次金融危机上有功劳,则将促进全球治理(包括地区治理)的积极变革。若是“金砖国家集团”(BRICS)能够真正促进“新兴国家”的合作,则将从根本上改变现存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可惜,“清迈协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仍然有限,受制于日本依然以美国为中心外交政策的制约。而BRICS则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成为对“任何第三方”利益的挑战者。
此外,关于“超主权货币”的提议虽然很令人鼓舞,但是,如果这仅仅是为了帮助美国经济和“美元霸权”,为帝国的命运而担心,仅仅是为了从帝国秩序中“分赃”,那么,这样的超主权货币,只是一种假象。
八、全球民主政府的设计
以下是本文关于全球政府的若干主张和设想:
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治理”。目前的国际治理,其组织形式和内容多样、复杂。联合国与国际经济组织是两个系统,存在着在使命和做法不同的国家集团,地区层面的治理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所以,需要实现“全球治理的治理”。(14)
其次,联合国安理会、目前的G20(实际上不只20个)合并组成全球政府的执行机构,取消任何大国特权,民主管理多元、多极、复杂的世界体系。任何国家的单边使用武力必须获得全球政府的批准。全球政府依“全球法”管理“国内”冲突和“国际”冲突。
第三,联合国大会成为世界议会,转化目前的“国际法”为“全球法”。但参加世界议会的不仅有主权国家的政府,而且包括各地区组织,以及通过全球民主过程(世界性而非仅仅民族国家性的政党参与的全球政治过程)产生的个人代表(全球政治家)。可以以欧洲议会模式改造联合国大会。
第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合并,组成独立的全球货币组织(WMO),管理多元世界货币体系,调控一些国家为转嫁负担的不负责的货币政策,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问题。
第五,世界贸易组织(WTO)进一步完善,去除针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不平等条款,避免成为欧美借助规则管理世界贸易的工具,以“自由贸易”和“公正(公平)贸易”相互结合为原则,管理全球贸易。
第六,最终解散北约(NATO),以联合国维和部门为框架,建立全球安全理事会(不同于旧的联合国安理会)和全球维和部队,有力地维持世界民主秩序。
结语
“积极的慎重”、渐进主义的国际制度改革,也许能到达“国际治理”的彼岸,但是,消极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国际治理改革”,仅仅是通过修修补补维持、只是在强化旧秩序而已。国际治理改革即使取得成效,“国际治理”终究无法实现“全球治理”,也就是说,“国际治理”不足以解决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
不过,即便有了“全球治理”,假使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依然很狭窄和缺少雄心,这样的“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和全球危机上也注定效果有限。国际一些代表少数利益者的集团,如G8,以及一些本质上是大国控制的国际组织(如国际金融组织),其所作所为,有“全球治理”之名,却未必有“全球治理”之实。
全球治理的根本前途在于超越“改革”,甚至不妨“另起炉灶”。而“另起炉灶”就要建设、塑造世界民主政府。只有全球民主政府才是应对全球危机的根本方案:把“政府”和“治理”通过全球民主结合起来。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全球政府首先不能被误解为是世界超级中央集权。
收稿日期:2011年9月
(本文的主要观点先后在以下两个研讨会上发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全球经济治理”(2011年6月26日)和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举办的“全球治理与全球学学科的构建”研讨会(2011年8月20至21日)。作者对上述两个研讨会的主办方表示感谢。)
注释:
①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M.Mullen)2011年7月10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强调“中国已经不是崛起中的国家”,而“已经是崛起了的强权”。见庞中英:“煮酒论英雄:美国是中国的一个战略困境”,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7月14日。
② 庞中英:“美国对华政策的合作与冲突策略”,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4期,第7页。
③ 一些英语世界的国际关系教科书,没有对“全球治理”的广泛讨论,但类似的内容在“国际治理”下展开。2001年,加拿大的Jim Balsillie创立了“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英国外交部下设的国际会议机构Wilton Park历年来一直讨论“国际治理”(IG)问题。笔者在2009年3月(即G20伦敦峰会前夕)和2011年6月参加了Wilton Park举行的的国际治理改革研讨会。尽管,诸如这些“国际治理创新”或者“国际治理改革”并不排斥,甚至承认和强调“全球问题”及其“全球治理”,但是,毕竟不同于本文论述的“全球治理”。
④ 庞中英:“关于中国的全球治理研究”,见庞中英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丛书第八卷《全球治理》,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⑤ 参见[英]斯特兰奇:《赌场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⑥ 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和欧洲中央银行行长让-克洛德·特里谢(Jean-Claude Trichet),甚至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及其政府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他们后来的回忆录中均认为,危机如此严重,前所未见,不知如何是好。
⑦ “纾困”一词,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汉语库中,并不存在。这是从港台旧有的汉语系统中转移过来的热门词。
⑧ 以前只谈“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而不提“宏观经济政策合作”。见黄范章(中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中美两国联合声明中看‘宏观经济政策合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性意义”,载中国改革开放论坛《中国战略观察》2011年5月8日。
⑨ [法]雅克·阿塔利:“建立全球政府的十个方向”,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会刊,2011年6月,第21页。
⑩ 参见[法]雅克·阿塔利的《国家破产》一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年版。
(11) 至少自二十世纪快要终结的时候起,从其诞生第一日(1967年)就以反华、遏华为宗旨的东盟及其一些成员国一直声称,“东盟是所有东南亚国家的地区组织”。这一点是对中国的一个巨大威胁,目的是把中国永久排除出东南亚地区。这完全是不符合国际法的,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中国也是天然的“东南亚国家”。中国不是东盟的成员国,不等于中国不是“东南亚国家”。有关评论,见庞中英:“中国也是天然东南亚国家”,载《环球时报》2010年9月7日。
(12) 2011年8月16日,为加强欧元区的经济治理,应对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巴黎表示,法德两国将共同提出成立欧元区“经济政府”,以便让成员国实施财政平衡政策,这一政府的核心经济政策包括征收金融交易税等。
(13) 这是笔者在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建立东北亚共同体”国际会议(2011年7月13日)上的发言。
(14) 有关这一点,作者在“1945年后的全球经济治理”一文已经指出,参见《国际观察》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