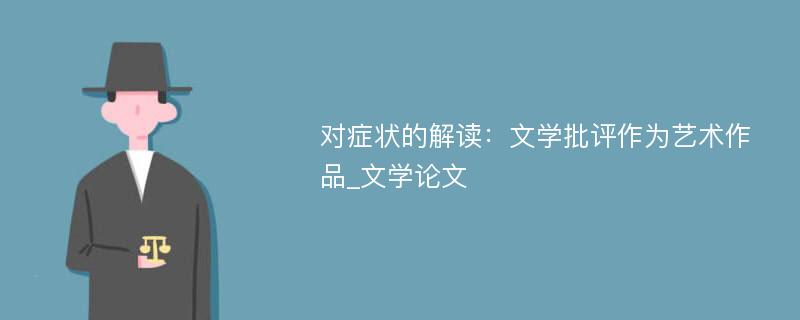
症候解读: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症候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艺术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导言》中首次提出的,这一理论给予后学以极大的启示和推进作用,成为后世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该理论的传人,都将“艺术生产”概念用以界定创作活动,亦即艺术活动整个过程的前端,而将处于这一过程后端的阅读和批评归入“艺术消费”的范畴,对其生产性问题并未置论,而“症候解读”理论恰恰开辟了这一论域。 一、“症候解读”理论的前史:症候是有意义的 “症候解读”理论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认为,人的种种舌误、笔误、遗忘、焦虑都属于“过失”的范畴,而任何过失其实都是有意义的。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它们错误和不当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合理和正当的一面。弗洛伊德对“症候”(Symptoms )问题也有过深入研究,他发现神经病的种种症候,如强迫症、健忘症、忧郁症、癔病、焦虑、自恋等也是有意义的。① 弗洛伊德还揭示了过失与文艺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诗人常常利用舌误、笔误等过失作为文艺表现的工具,如席勒的《华伦斯坦》、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在戏剧情节设计中都有意安排种种过失,作者这样安排大有深意,而且也知道台下的观众能够心领神会。弗洛伊德因此断言,研究过失问题,与其求诸语言学者及精神病学者,不如求诸诗人。 拉康是弗洛伊德的晚辈,他在精神分析学史上是以弗洛伊德的重新阐释者身份出现的,他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出发,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进行了拆解和重建。在哲学方面,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继承了笛卡尔理性主义统驭下的古典心理学传统,他公然宣称与这种“我思故我在”的哲学一刀两断。在心理学方面,拉康提出了“镜像理论”,揭示了人的“主体”意识在个体的早期经验中已然萌发这一事实,进而提出了“主体间性”的概念,认为正是“主体间性”的交互性给人的“主体”意识注入了丰富的社会性、人文性的内涵,由此,拉康将弗洛伊德的学说从生物学、医学的层面提升到文化学和人类学的层面。 对主体间性的重视,推动了拉康理论的语言学转向。拉康认为,主体间性生成于不同主体之间传达意义的信息交流活动,或者说主体间性靠语言来承载和维系,以言谈、对话、应答等形式加以表达。这样,拉康就将语言学引入了精神分析学。拉康进而认为,精神病的种种症候也是像语言符号那样构成的,因而也必须在语言符号分析中得到解决。他提出了“能指连环”的概念,主张在“能指连环”中考量种种症候的意义:“能指只有在与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才有意义。症状的真实存在在这个关联之中。”②总之,症候是有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只有在语言的能指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 二、阿尔都塞:对“症候解读”的大力揭扬 阿尔都塞曾明确说过,拉康“对我有一种不可否认的影响”③。这种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理念层面的,阿尔都塞接纳了拉康的“症候”概念和“症候是有意义的”这一思想;二是方法论层面的,拉康对弗洛伊德学说存在的空白、缺失、疏漏等“症候”进行解读,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了后现代意义上的重建,建立了一种新的阅读模式,此事极大地开悟了阿尔都塞。 阿尔都塞所取得的第一个学术成果是论文《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1947)。该文从“内容”概念出发追问“空无”和“缺失”的本质意义,从而启动了以空缺为本的哲学之思。这一精神历险虽然曾被一度搁置,但决定了阿尔都塞后来的许多事情,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阿尔都塞与拉康的交集较晚也较短暂,大约是在1963年至1965年之间,但是对阿尔都塞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就是这短暂的相交,推助阿尔都塞进入了学术生涯的辉煌时期。期间,阿尔都塞早年所奠定的以空缺为本的哲学之思被拉康学说再次激活,借助精神分析学的概念,铸成了后来使之一举成名的“症候解读”理论。 所谓“症候解读”,意指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的文本中,总是隐含着某些空白和缺失,表现为沉默、脱节和疏漏,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入手,去解读出这些文本背后隐秘的、缺场的东西,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一书中对此作了如下阐发:“所谓症候解读④法就是在同一运动中,把所读的文章本身中被掩盖的东西揭示出来并且使之与另一篇文章发生联系,而这另一篇文章作为必然的不出现存在于前一篇文章中。……在新的阅读方法中,第二篇文章从第一篇文章的‘失误’中表现出来。”⑤下面这段话可与之互文见义: 在某些时候,在某些表现出症候的地方,这种沉默本身在论述中突然出现,并且迫使这种论述不自觉地像闪电一样产生出真正的但是在字面上却是看不见的理论上的缺陷……单纯的字面上的阅读在论证中只能看到论述的连续性。只有采用“症候解读法”才能使这些空白显示出来,才能从文字表述中辨别出沉默的表述……。⑥ 可见,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是指文本中无意识地暴露出来的思想的隐身、理论的缺失、言说的沉默和表达的脱节,而这些空缺和脱漏恰恰将深层次的更大问题呈现在反思面前,对其进行症候解读乃是发现和把握更大问题的入口和起点。 阿尔都塞此论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启发。马克思在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时,发现了它们在剩余价值这一实质性问题上的沉默、空缺和失语,他在查验和诊断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些“症候”的基础上,在《资本论》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阿尔都塞指出:“斯密和李嘉图总是在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形式上分析‘剩余价值’,因而剩余价值总没有以它自己的名称而是以别的名称来称呼。剩余价值没有在与它的‘存在形式’即利润、地租、利息不同的‘一般性’上被理解。”当马克思阅读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时,“他恢复了另一些术语所掩盖的未出现的术语。他把掩盖未出现的术语的另一些术语翻译出来,恢复了它们省略的内容,说出了这些术语没有表示出来的东西。他把李嘉图和斯密对地租和利润的分析读作一般剩余价值的分析,但是李嘉图和斯密从未把一般剩余价值称作地租和利润的内在本质。我们知道,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概念是他的理论的两个关键性概念之一,即说明马克思和斯密以及李嘉图在总问题和对象方面固有的区别的概念之一。”⑦以上两段论述的核心意思是,是否将工资、利润、地租、利息等问题放在剩余价值的范畴中进行考量,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总问题和对象方面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在论述中阿尔都塞提出了“总问题”⑧的概念。根据他在《保卫马克思》中的界定,所谓“总问题”,就是在一定思想内部由诸多相关问题组成的问题体系,它也是决定该思想对具体问题作出答复的体系。“总问题”总是在一定场所形成的,从而具有一定的视野,人们只能在总问题的场所和视野内提出问题。因此,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场所变换了,而人们还停留在原有的视野,便会对眼前出现的新问题视而不见、不屑一顾。正像牛顿以前的物理学家不会在自由落体中看到引力定律,拉瓦锡以前的化学家不会在“燃素”中看到氧气,马克思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不会在价格、交换、工资、利润、地租等可以计量的经济事实中看到剩余价值的存在。此时,对滞留在旧的场所的“总问题”来说,新的问题和对象只是一种空无、缺失、疏漏或沉默,而“症候解读”就是要将这些“症候”所潜隐的深意发掘出来、公之于众。 不仅如此,阿尔都塞还进一步充分肯定了“症候解读”的生产性,认为它涉及了本来意义上的“生产”概念,即一方面将原先隐藏的东西彰显出来,另一方面使原先固有的东西得到改变。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它生产了一个新的、没有相应问题的回答,同时生产了一个新的、隐藏在这个新的回答中的问题”⑨。正是“症候解读”,使得马克思能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中生产出剩余价值理论,正如万有引力定律和氧气的概念是从以往物理学和化学的缺陷中被生产出来的。然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产”——小而言之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大而言之政治经济学的开创,已经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指处于精神生产活动过程前端的创作和书写,而是指处于这一活动过程后端的阅读和解释。 三、马舍雷:将“症候解读”引入文学批评 如果说阿尔都塞是用“症候解读”理论来分析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那么马舍雷则将这一理论引入了文学批评,用以寻绎具体作家作品中存在的空白和缺失,对其进行“症候解读”。有学者指出:“在对文学文本的复杂的物质性叙述中,马舍雷悄悄借鉴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尤其是‘症候解读’这个概念,使我们能够区分出差距和沉默、矛盾和缺席——它们使文本发生变形并揭示了那些转化为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材料的压抑性存在。”⑩此说高度概括了马舍雷“文学生产”理论的渊源、特征、方法和功能。其中要紧之处在于,马舍雷受到马克思影响,提出了“文学生产”的概念,并在这一概念中加入了阅读理论和批评理论的维度,从而刷新了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理论。 马舍雷对“文学生产”的探讨,见诸其《文学生产理论》(1966)一书,该书将“文学生产”提高到文学理论核心范畴来认识,并由此形成许多新的话题。 首先,在文学活动的本质界定上,马舍雷排斥“创造”说而主张“生产”说。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并不是一个创造过程,而是一种生产劳动;文学作品并不是创造的结果,而是生产的产品。以往重视创造的理论忽略了这一点,现在有必要对之加以更正,因此他宣称:“本书贬黝‘创造’,而以‘生产’代替之。”(11) 其次,马舍雷将“生产”与“创造”这两个概念刻意分开并有所褒贬,旨在凸显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在他看来,“生产”不是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进行,而是在文学阅读和批评的过程中发生的:“文学作品尽管来源于创作中一些不可知的冲动和灵感,但它终将沦为读者具有阐释功能的作品。”(12)就是说,作品先是存在于它自身,接着存在于阅读和批评之中,文学生产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文本的接受和阐释的问题,因此不能将在创作中发生的事完全代替在阅读和批评中发生的事。可见,将文学生产问题挪到阅读和批评阶段是完全合理的,其意义绝不亚于以往将文学生产仅限于创作的做法。这就将文学生产的重点从整个文学活动的前端挪到了后端,垦拓了一片开阔的理论空间。 再次,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旨在揭示作品的秘密、披露作品的谬误,这种“症候解读”的功能决定了作品和批评之间的主从关系,确立了批评在文学活动中的核心地位。马舍雷认为,任何作品都隐含一个有待释放的意义,作品的文字往往只是动人却又具有欺骗性的面具,作品的意义就包裹在其中。对作品的认知正是通往这一隐含意义的必经之路,因此,文学批评建立在对作品的某种谬误的披露之上。这就对阅读和批评提出了要求:一是它自身的深度问题;二是它对作品谬误的批判性;三是它必须对作品预设某种含义,并围绕这一含义呈现出多样性、连贯性的表达。“但最重要的是,阐释批评确定了自身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将自身置于作品的中心并揭示作品的秘密”(13)。 第四,马舍雷所倾重的阅读和批评有其特殊性,它往往不是与作品的公然发声之处对话,而是与作品的沉默不语之处交谈。而这种沉默不语之处,就是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概念。人们通过阅读和批评与作品中无意识部分进行的交谈,在促进知识增长和思想提升方面,较之与作品公然发声之处的对话可谓毫不逊色,它激活了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以新的阐释取代了“旧式”的阐释学。马舍雷对这种新的阐释作了如下界定: 阐释是一种重复,但它是一种奇特的重复,它说得越少却得到的越多。它是一种纯粹的重复,在它面前,潜藏的意义将呈现出其赤裸裸的真实性,这就像冶炼矿石以提取其中珍贵的精华一样。阐释者正是这一强力解放的实施者,为了能够按照作品所表达的真实意义进行重建,也为了将作者隐晦、曲折的表达用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他对作品进行拆解、翻译和删减。(14) 这里需要插一句,在马舍雷眼中,阐释学已是“旧式”的学问,它们止步于对作品公开意义的确认,只有“症候解读”致力于对作品隐秘意义的开掘,才堪当深度阐释和扩展阐释,堪当强力解放的阐释。 最后,马舍雷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无意识表现出的空缺、疏漏、失语等“症候”最终都通向意识形态,而这一点必须借助文学批评得到揭示,他在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中,往往将文学生产理论与意识形态问题结合起来。这在他对列宁的托尔斯泰评论的研究中有比较集中的论述。 马舍雷指出,列宁的批评方法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即对一定的文学作品,只有联系作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状况来加以考察,才是有意义的。列夫·托尔斯泰主要属于1861-1904年这个时代,他作为一位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了整个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历史特点。但托尔斯泰对这种关系的反映是闪烁其词、欲言又止的。这并不意味着托尔斯泰误解了他的时代,他只是展现了一幅不完整的画面而已,而这恰恰给读者传达了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状况。 列宁认为,托尔斯泰的这一观点是由他的社会出身决定的,他自发地代表了地主贵族阶级,但托尔斯泰也是一位普通人,他的阅历改变了他固有的看法,对农民的同情使之与那个时代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进而形成人们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哲学,并将这种哲学引入了文学。这种变化看似属于托尔斯泰个人,但实际上也属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处同样历史条件的更多的人。因此,托尔斯泰的作品既暴露了他个人意识形态的矛盾,也暴露了那个时代普遍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而这一切最终都来自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后来伊格尔顿对此作出的评价堪称精当:“在马舍雷看来,一部作品之与意识形态有关,不是看它说出了什么,而是看它没有说出什么。正是在一部作品的意味深长的沉默中,在它的间隙和空白中,最能确凿地感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批评家正是要使这些沉默‘说话’。”(15) 讨论至此,事情似乎变得神秘起来,决定一部作品的根本力量,竟是那些沉默不语、无迹可寻的异质的东西?然而马舍雷的说法是如此的肯定:“作为一切表现形式和思想现象的实际支柱的思想背景,基本上是沉默的,也可以说是无意识的。这像是一个无底的深渊,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个深渊之上。这也像一个行星围绕着一个不存在的太阳旋转,一种意识形态是由它并未提到的东西构成。”(16)这番话虽然说得玄虚、神秘,但只需读一读马舍雷对儒勒·凡尔纳的评论即可了然。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力图表达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劳动和征服”概念,但这一构想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劳动是异化的,完美的征服也不可避免受到殖民风气的陶染,而这背后的异化和殖民性质并未以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只是成为沉默和缺席的东西,凡尔纳的作品恰恰通过特殊的文学方法,揭示了这种“劳动和征服”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评论对小说中无意识地暴露出来的“症候”的诊断,超越了对作品可知、可言部分的把握,不无知识增长、思想建构的意义。这就应了马舍雷的一个重要指点——“批评引导我们阅读这些符号”(17)。由此可见,正是阅读和批评给文学生产提供了开阔的可能性空间。 四、卡勒:“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的生产性 20世纪后期“症候解读”理论在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文论界甚至成为阅读和批评理论的关键词,但对其进行系统研究并推出新见的却不多,乔纳森·卡勒可算一个,他在《文学理论》(1997)中非常简明地对“症候解读”理论作出了新解和重构。 卡勒重提“症候解读”时,已置身于一个全新语境:文化研究勃然兴起,迅速占据了人文学科的王座,文学研究则备受挤占,滑向边缘,这就使得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解读方法发生了逆转。文化研究最早脱胎于文学研究,如今一切颠倒过来了,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内部化蛹为蝶、破茧重生,最终消解了文学研究。与之相应,原先为文化研究所倚重的文学研究方法如今却被冷落和搁置。如果说以往文学研究关注的是每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审美特点和文学形式,那么,如今文化研究已变成了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它“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18)于是有了两种解读方法:一是传统的“鉴赏性解释”(appreciative interpretation ),它运用“细读”的方法对文本内部每种形式和技巧都保持敏锐的关注,并且着力研究意义的复杂性;一是如今的“表征性解释”(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它认为一定时代的所有文本都是外部社会结构的表征,因而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两种解读方法显然存在龃龉之处。值此文化研究风行一时、“表征性解释”当道之际,文学对象的审美特性便有可能被忽略,文学长期使用的解读实践也有可能被弃置。 卡勒使用的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来自阿尔都塞、马舍雷提出的“症候解读”概念,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和拉康,(19)但他对该词的运用又有自己新的理解和阐发。卡勒对“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作出了进一步的比较和厘定,他将这两者分别称为“恢复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recovery)与“怀疑解释学”(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认为前者企图恢复作品产生的原始语境,包括作者的处境和意图、文本对它最初的读者可能具有的意义,后者则旨在揭示文本可能赖以形成的、尚未经过验证的关于政治的、性的、哲学的、语言学的假设。前者致力于帮助当今读者接触文本的原始信息,藉此来评价文本及作者;后者则常常对原始文本的权威性表示怀疑。这两者各有利弊:前者把文本限定在那些远离读者当下关切的、假设的原始意义上,因而可能会大大降低该文本的价值;后者则往往另辟蹊径去评价一个文本,所以它可以引导并帮助读者对当下问题进行再思考,哪怕这样做可能会曲解作者原先的设定。 显而易见,卡勒在上述比较分析中对“表征性解释”或日“怀疑解释学”给予青睐,这与他在“表征”的意义上确认文本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存在着“同一性”有关。他说:“这个概念认为有一种社会同一性存在。各种文化形式都是这个同一性的表现,或者叫现象。所以,要分析这些现象就要把它们与派生出它们的社会同一性联系起来。……在这种关系中,文化产品就是一种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20)而“表征性解释”就热衷于这种直接的“同一性”关系。同时,这种倾重也昭示了卡勒理论旨趣的一个重要转折,即认定文本是外部社会政治结构的表征,他以此取代了阿尔都塞式的“症候解读”对文本内部种种“症候”的反思,从而实现了文本解读的“向外转”。因此可以发现,卡勒更多在正面意义上使用symptom这一概念,即将之更多用作“表征”、“象征”、“表象”、“现象”之意。同理,他使用的symptomatic interpretation一词,更多地应理解为正面的“表征性解释”,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症候性解释”。如果说阿尔都塞和马舍雷是将文本中那些语焉不详和存而不论之处视为“症候”,从对它的解读中发现更大问题,那么卡勒则是将文本本身看成一种“表征”,解读它对一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象征意义。 卡勒清楚地知道,这种“表征性解释”是一种“过度解读”、一种“偏激”的批评,但它恰恰能够揭示作品以前被忽视的含义。而在如今新的语境下,“过度解读”触及的恰恰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在理念、旨趣和方法上的根本性歧异。现在许多文学教授恰恰在做与文学毫不相干的文化研究,这种非常规的、非预设的、引申的批评便成为一种“过度解读”。卡勒指出了它的种种表现。一是它会专注于种种文化现象,譬如电影、连环漫画、哈利波特等,同时它也会关注历史话题、文化话题,以及妇女解放、社会动乱等现实问题。与经典文学相比,学生对这些文化、历史和现实的话题更感兴趣,他们会认为研究种种文化现象比研究某个作家作品更为重要。二是在评论某个文学个案时,它会要求批评者阅读大量其他学科的相关资料,如历史文献、哲学理论、文化话题等,而这些资料却又是非文学的。总之,如果说以往的文本解读惯用的是“细读”(close reading),那么现今采用的则是“粗读”( distant reading ),例如,通过定量分析来统计某一年份的整个文学产出,研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小说类别,考察某一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翻译、阅读、模仿的情形,等等。它关注的是文学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对某个特定文本的深入研究,它把小说中的人物看成一个群体,使之退到背景位置,对其进行定量分析,从新的视角审视人物,不再考虑主题,不再考虑对某个人物的看法,不再考虑人物及其伴侣的出生地和归宿地。以上种种套路和方法往往被人归为“文学社会学”(21)。而这一切都已突破了原先文学研究“鉴赏性解释”的框范,在人们眼前展现了一片开阔的生产性空间。 五、“症候解读”的后现代性质 从以上论述可知,从阿尔都塞到马舍雷再到卡勒,“症候解读”理论像一条红线一以贯之,他们致力于对“症候解读”的机制和功能进行分析和厘定,并以揭扬“症候解读”的生产性为己任。因此,该理论的标举,标志着艺术生产论的研究重点从创作一端向阅读和批评一端进一步拓展。肯定文学阅读和批评的生产性,将其视为一种艺术生产,这无疑是在马克思所开创的“艺术生产论”基础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 原始要终,“症候解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从其前史说起,弗洛伊德是从过失、梦以及神经病的症候之中解读出意义;拉康借助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对精神分析学进行重建;到了阿尔都塞,他关于“症候解读”的创见是从一般阅读开始,从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手中发生的革命性转折中发现的,他将其提升为阅读和批评的一般规律;马舍雷则将“症候解读”引向文学领域,既将其运用于文学作品的批评,又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的批评;卡勒则在后现代语境下将“症候解读”引向文化研究,将其转换为“表征性解释”,实现了文学研究的“向外转”,大大拓宽了文本解读的生产性空间。可见,“症候解读”理论具有较强的自组织性和自我调整、自我修复的能力,从而能够在保持理论主旨基本一致性的前提下,顺应时势变迁而作出调整和变通,表现出较强的适应性,显示了与时俱进的品格。这里需要对几个基本概念作出进一步的界定: 关于“症候解读”。“症候解读”类似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在波普尔看来,知识增长的前提在于证伪,求知的过程就是不断证伪的过程。阿尔都塞也将“症候解读”的知识增长意义看成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他不仅高度赞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古典经济学所作的“症候解读”,而且主张对马克思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可以进行“症候解读”,从而由“第一种解读”进入“第二种解读”。这种层层递进的“症候解读”也就是层层递进的证伪过程,藉此将不断推进知识增长和思想提升,显示强大的生产性功能。不过,“症候解读”也有与“证伪”迥异之处,它不像“证伪”过程是从已有科学结论的可见、可言、可知之处推陈出新,而是从已有文本所暴露的“症候”着眼,从其不可见、不可言、不可知之处看出漏洞、抓住破绽,进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 所谓“症候”,是指已有文本中无意识地却又意识形态地暴露出来的疏漏和缺失。说它是无意识的,是指它未必是作者自觉意识到的;说它是意识形态的,是指它又是不无意识形态倾向的。这里似乎有一悖论:既然是作者并未自觉意识到的,那又何来意识形态倾向呢?实际上,这恰恰是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的现象。例如巴尔扎克,在政治上属于保皇派,但在文学上恰恰接近民主派,在他的小说中经常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断裂:小说保持了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辩护,但对工人运动却往往无意中发挥准确认知的功能,流露出对之倍加赞赏的激进倾向。作品意义的这种无意识却又意识形态的呈现,与通常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诉诸意识形态的呈现截然不同,但它又是符合常规、真实有效的,只不过对其解读的模式不同、途径不同而已,它同样不乏艺术生产的意义。 关于“艺术生产”。除了在马克思意义上的“艺术生产”之外,还有两种,即文学批评之中一般解读的生产与“症候解读”的生产。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后者。“症候解读”的生产性是确凿无疑的,它作为一种生产的意义和作用,较之创造性、建构性的活动毫不逊色,较之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一般解读也不敢多让。它是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生产,一种“相克相生”、“相反相成”的生产,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生产,它通过纠偏、矫正的模式和途径来达到知识增长和理论跃迁。这也就使得“症候解读”的生产性机制更多了一层复杂性和特殊性,而这一点恰恰为之打开了新的问题域。 “症候解读”不是从文本的“明言”之处去寻绎意义增殖的可能性,而是从文本的“无言”之处去寻求其生产性,这一点隐秘而不神秘。“症候解读”所面对的种种空白和缺陷虽然在文本中并不现身,却真实地指向其内里的病疴,它绝不是虚构的,也不是冥想的。难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剩余价值的沉默无语是虚构的吗?难道在笛福的历险小说、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中对资产者的殖民欲望、征服冲动等意识形态的隐匿是冥想的结果吗?如果要说有人对此并未自觉地意识到,那可能是作者本人,而不会是批评家。马舍雷说过,批评家“必须就作品自身来对它进行阐释,必须说出作品没有说和不能说出的内容”(22)。批评家往往是在别人踟蹰不前之处另辟蹊径,在别人沉默不语之处发出声音,“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是其胜场,从而他的批评工作所显示的生产性足够强大、足够显赫。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创建,笛福、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意义,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关于“文学批评”。对“症候解读”的生产性的分析,使人对文学批评不能不重新考量。晚近以来一个带共性的趋向就是在生产性的意义上对文学批评作更加细化的分类,而以往对此总是笼而统之、一概而论。 马舍雷在《文学生产理论》开头第一章就挑出了文学批评的问题。在他看来,“批评”这一概念一直存在着模糊性,批评这门学科似乎就植根于含混和重叠的看法之中,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集于一身,使人很容易从一种感觉转换到另一种感觉,甚至它们的格格不入之处也是相互关联着的。这一复杂情况使得对文学批评作更为具体的区分成为必要。马舍雷将文学批评分为“欣赏的批评”与“认知的批评”,分别指称“审美教育”与“文学生产的科学”。在他看来,如果将文学批评确认为“欣赏的批评”,那就进入了艺术或技术的经验领域,总是由给定的艺术或技术经验构成批评的出发点。但如果将文学批评确认为“认知的批评”,那么对象就从来不是既成的,而是不断生成的,它不是已有知识的重复,而是某种新出现的东西,它一出现就成为对现实的新的添加。其中关键之处在于,在主体与对象、思想与经验之间分清主次、拉开距离,主体将对象限定在认知的范围内。总之,“欣赏的批评”是将所有的理性行为缩减为艺术或技术的一般形式;“认知的批评”则最终归结为单一的点,即真理的出现,这个真理是瞬间的,只是投射到事物秩序上的精准的一瞥。 总之,文学批评往往是二者选一:要么是一种文学鉴赏,它是由预先给定的文学作品决定的,批评的目的在于与作品最终重新结合,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缺乏自主性;要么是一种认知形式,它有一个对象,但这个对象不是预先被给定的,它不是一种模仿,也不是一种复制,而是批评的自主发现。可见,在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是不争的事实,批评家对作品说些什么与作品自己说些什么,这是永远不会混淆的两码事,因此作者写出的作品不一定是批评家阐释的作品,反之亦然。于是马舍雷得出结论:“批评家是用一种全新的语言来阐发作品的异质之处,从而生产出作品在其身又不止于其身的内涵。”(23) 无独有偶,卡勒也将文学批评分为“鉴赏性解释”与“表征性解释”,认为“鉴赏性解释”与文学研究相伴,而“表征性解释”与文化研究相随。这与马舍雷的提法有异但宗旨相通,显示了批评兴趣的时代性转换和新变:二者更赞赏文学批评从依赖给定的文学作品走向崇尚自主创新的文学生产,从文本性的表层解读走向非文本性的深层解读,从单纯的文本解读走向社会政治分析,从拘囿于过往的原始信息走向对当代问题的思考。 关于“症候解读”的后现代转折。说到“症候解读”,就与后现代挂上了钩,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往前追溯,这从拉康就开始了。拉康被普遍认为是后现代理论的先驱之一,他向欧洲哲学史上传统的理性主义挑战,他提出的“镜像”理论和“主体间性”概念,都对后现代理论具有开风气的意义。嗣后,阿尔都塞基于对空无和缺失的本体论认定而提出“症候解读”一说,致力于从已有文本的“症候”中解读出重大问题,从而推进了知识增长和思想跃迁。可见,阿尔都塞采取的理论策略往往是剑走偏锋、另辟蹊径,从理论的边缘性、断裂性地带自出手眼而出奇制胜,这就赋予了“症候解读”鲜明的后现代色彩。 马舍雷继承了阿尔都塞的这一策略,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从文学的边缘之处、断裂地带、碎片部分来激活“症候解读”的生产性。他致力于将文学生产从文学活动的前端腾挪到后端,从文学创作阶段移到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阶段;他不是将文学生产诉诸作品的可知、可见、可言之处,而是诉诸作品的不可知、不可见、不可言之处;他将意识形态的范围扩大到无意识层面,将文学作品的空白、缺失、沉默之处同样认定为意识形态的表现,通过“症候解读”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生产;他对文学生产有无相生、虚实相成的特点进行哲学思辨,在本体论层面将空无置于实有之上、将沉默置于明言之先,并以此破解“症候解读”牵出的种种悖论。凡此种种,都推动了文学批评的后现代风尚。 这一风尚到了卡勒继续发扬光大,尽管卡勒最终还是归于折中主义、中庸之道,但他在论证“症候解读”时往往会发一些过头之论,对那些出现在文学的边缘、断裂地带的偏激、出格的东西表示认同,譬如在作品解读中对“表征”的重视更胜于“鉴赏”,对“粗读”的肯定更多于“细读”,对“过度解释”的兴趣更超过“一般解释”。这里还要指出一点,虽然卡勒的《文学理论》一书如题理应主要讨论文学理论问题,但我们在书中遇上的似乎更多的是文学批评的问题。如果说该书在讨论文学研究时就未曾廓清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两个概念,那么在讨论文化研究时更是将这二者相互通用了。能够说明问题的例证是,该书列论的诸多“理论”流派恰恰是“批评”流派,如女性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话语批评、生态批评等。此外,最近卡勒在中国所作的题为《当今文学理论》的演讲,预测了当今文学理论的诸多新进展,包括叙事学的复兴,德里达研究的复兴,伦理学以及动物伦理研究转向,生态批评的兴起,“后人类”理论的提出,回归美学等,(24)也显示了批评化的倾向。这一现象并不只是概念的泛用或混用那样简单,它昭示的更是当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合流、文学理论走向文学批评的大趋势,而这一趋势恰恰是晚近知识状况发生后现代转折的一个重要征象,它预示着文学批评作为艺术生产将迎来开阔的理论空间。 注释: ①参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第20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②《拉康选集》,褚孝泉译,第24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③路易·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第3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④国内相关著作对阿尔都塞“症候解读”一词有多种译法,本文为保持该词用法的统一性起见,均使用“症候解读”这一译法。 ⑤⑥⑦⑨路易·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第21页,第94页,第99-100页,第16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⑧“总问题”又被学界译为“问题式”“问题框架”“问题结构”“问题体系”等。 ⑩(11)(12)(13)(14)(16)(17)(22)(23)OPierre Macherey,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78,Ⅷ,p.68 ,p.70 ,p.76 ,p.76 ,p.611,p.613,p 77 ,p.7. (15)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第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8)(20)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第53页,第5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9)卡勒曾专门介绍弗洛伊德、拉康和阿尔都塞的相关理论。参见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133-134页。 (21)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的现状与趋势——乔纳森·卡勒教授访谈录》,何成洲译,《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 第2期。 (24)这是卡勒2011年10月20日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的演讲稿,其英文稿Literary Theory Today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标签: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化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资本论论文; 弗洛伊德论文; 证伪论文; 无意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