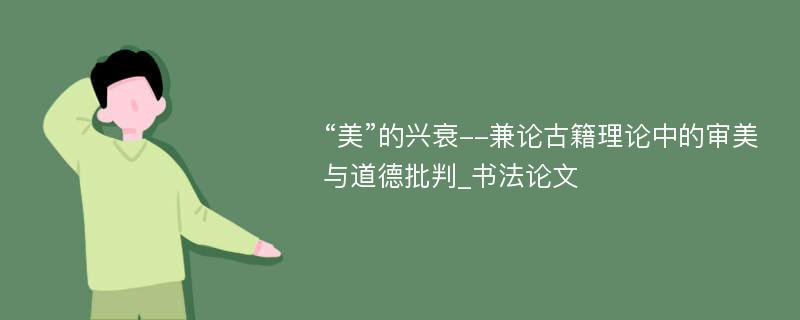
“姿媚”的兴衰——兼论古代书论中的审美判断和道德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论论文,兴衰论文,批评论文,道德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姿媚”内含的道德和审美标准
《说文》云:“媚,说(悦)也。从女,眉声。”“眉”也示意:以目媚人。在先秦典籍中,“媚”的本义为“爱”、“喜爱”,如《诗经·大雅》“思媚周姜”,“维君子使,媚于天子”。亦取“逢迎取悦”之意,如《国语·周语》“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用于两性、君臣、人神的和悦关系。这种微妙的好感若被利用而刻意过度为之,则取“谄媚”之义,如《尚书·冏命》“无以巧言令色,便辟侧媚,其惟吉士”,《孟子·尽心下》“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谄媚”显然为君子所不齿,是道德批判的对象。在《论语》、《孟子》、《史记》等儒家经典中,“媚”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
汉魏以来,“媚”的审美意味逐渐增强,女性仪容的婉美婀娜、自然风光的明丽怡人,常以“媚”来提示,如《尔雅》“媚,美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妩媚姌嫋”,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画论、书论中也广泛地用到了“雅媚”、“润媚”、“媚趣”、“劲媚”等,将其升华为一个独立而固定的审美范畴。
可见“媚”的涵义在形成衍用中,就包含了道德批评和审美判断的双重意味,关乎士人的道德信仰和审美自由。形式美在自觉之初,就已经与其他心性价值发生了纠葛,这不仅是书论中该词一语两用的根基,也是“媚”之风格兴衰起落的渊源。
相对于“媚”而言,“姿”更有内外兼美之意。《说文》云:“姿,态也。”徐锴曰:“心能其事,然后有态度也。”因此,“姿”不仅有“美好、妩媚”之表,更有“资质、才能、禀赋”之实。《世说新语》对名士形貌风度的形容广泛用到了“姿”,而没有用“媚”。如“太尉神姿高彻”,“嵇康……风姿特秀”,“骠骑王武子……俊爽有风姿”。名士们不仅形貌俊美,更具超凡脱俗的才情和智慧。对贤媛的赞美也是“令姿淑德”、“姿慧”,没有用到“媚”。“媚”被认为更多的是以外形的美丽妖娆媚人心旌,而与才德无关。相对于“姿”的形上品格,“媚”的感官性更强。“姿”是由内向外散发出的自足风度,“媚”则是有待的,是在动态的对象性关系中基于“相色”的诱发和取悦。
“姿”和“媚”两字联袂,偏义于“媚”,多用于形容女性美。如阮籍《咏怀》之十二:“流盼发姿媚,言笑吐芬芳。”书法品评用此范畴,始见于唐代韩愈《石鼓歌》:“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宋以后多有书论沿用此义。在此之前,书论中的“姿”和“媚”是分开来用的。“姿”早于“媚”,“姿”往往泛指自然万物和人的姿态形貌,而“媚”则是从其中渐渐分辨提炼出来的。
二、“媚”在书论中的兴起和鼎盛
汉魏两晋,“书肇于自然”的发生论是书法审美的本体依据。书家纷纷强调对自然造化的模拟学习,领会其动态神机,并转化到书法造型之中,由此获得生命的运动感和美感。所以书论突出强调“姿”和“势”,以蔡邕的《篆势》、《九势》,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为代表。与此同时,“骨”、“筋”、“力”等范畴以其对力量、运动和阳刚美的高度概括,早在汉代书论中就已确立了核心审美价值的地位。而斑斓艳丽的美大多还停留在形象譬喻的层面,比如钟繇《用笔法》:“去若鸣凤之游云汉,来若游女之入花林。”卫恒《四体书势》:“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杨泉《草书赋》:“如春华之杨枝……如美女之长眉。”① 南朝王僧虔、袁昂、萧衍的书论还时用美女花鸟比喻。
随着真、行的创制流行,超越于象形之美的纯粹形式美被二王等人极致性地发掘出来。在传为王羲之的《书论》中已用“媚”来形容字间的顾盼呼应与明朗美妙:“作一行,明媚相成。”但此时的“媚”还只是一个形容词,只有到了晋宋之交的羊欣,才在《采古来能书人名》中以“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评价王献之,将“媚”拔升为一个特定的书法审美范畴,并在南朝书评中普遍出现。如虞龢《论书表》评献之书:“笔迹流怿,宛转妍媚。”王僧虔《论书》评郗超书:“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评谢安书:“婉媚翫好。”评谢综书:“书法有力,恨少媚好。”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也用到“劲媚”、“方媚”、“纯骨无媚”等②。“媚”最终被书家拣选出来,以其对婉美妍丽、风流俊逸的阴柔美的高度概括,对形式美令人心旌摇荡之魅力的准确提撕登上了书法舞台,与“骨势”等并列,刚柔相济,阴阳合德,成为书法审美范畴不可或缺的一极,并以“媚”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审美范畴群落,包括“妍”、“丽”、“绮”、“丰”等。
前面曾提到,魏晋人物品藻多用“姿”而不用“媚”,同样,在晋书品鉴中风姿韵度也超越于“骨势”和“媚趣”之上。此“韵”自然沾溉于魏晋时谈玄说佛、精神自由的高逸气息,然而晋书之“韵”与晋人对“媚”的情有独钟难解难分。晋人之“媚”不同于后世的熟媚,有着最初创造形式美、欣赏形式美的纯真和欣悦。陶隐居《与梁武帝论书启》有云:“《大雅吟》、《乐毅论》、《太师箴》等,笔力鲜媚,纸墨精新。”正如宗白华品评晋人山水诗的心得:“陶渊明、谢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也只是新鲜自然而已。”③ 晋人的书法也带着这份春意盎然的清华、自然和欣畅。明媚的书风为晋人超逸的韵度增添了丽泽,而晋人的高韵深情又提升了“媚”的品格,使其媚而脱俗,天姿高迈。“韵”和“媚”一体两面,是晋人不可分割的完美才情。
书法的形式美和精神高度在魏晋南朝时连璧生辉,纯粹的审美批评也初具规模。但此时人们对书法的形上品质、书法与复杂心性的关系还远未触及。随着对形式美初恋般的热情渐渐消退,士人们发现了更为深刻的内在心性和丰富情感,需要超越于形式美的别样表达,于是在“媚”和其他审美价值之间,在旧有典范和新的形式创造之间,产生了持久的矛盾和张力。
三、唐代“风骨”与“姿媚”之争
初唐承续晋人对书法唯美形式的追求,并因为君王的热烈喜好达到鼎盛。各种研讨形式美规则的书论应运而生,如释智永的“八诀”、智果的《心成颂》、欧阳询的三十六法、李世民的《笔法诀》等。“媚”作为代表形式美的成熟范畴,也作为王字的典型特征,被注入了更多“法度”和“典范”的内涵,并时与“刚”、“遒”、“劲”等联袂,被广泛应用在书论中。如:欧阳询《用笔论》:“刚则铁画,媚若银钩。”孙过庭《书谱》:“如其骨力偏多……虽妍媚云阙,而体质存焉。”张怀瓘《书断》评褚遂良学王羲之:“真书甚得其媚趣。”评薛稷:“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窦蒙在《述书赋》中专列出“媚”格:“意居形外曰媚。”并述及相关的“意态”、“妍”、“艳”、“丽”、“秀”、“纤”、“秾”等审美范畴,以“软媚”、“隐媚”、“轻媚”、“丰媚”、“婉媚”等评论各书家。
形式美流行的同时,也凸显其因袭和软媚的流弊,敏感于此,张怀瓘拈出了“风神骨气”,一则挽靡丽之风,将“姿”和“媚”统驭到“风骨”之中,二则为新的书法形式的创造开辟道路。张怀瓘一方面推举王书为神品,另一方面在《书议》中提出:“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据此对王羲之提出批评:“逸少草有女郎才,无丈夫气。”“逸少则格律非高,功夫又少,虽圆丰妍美,乃乏神气。”评高正臣:“习右军之法,脂肉颇多,骨气微少,修容整服,尚有风流。”以此为端,王羲之具有了双重意味:一则开真、行遒媚之先河,是登峰造极的“书圣”;二则后世追慕者得其妍媚而殊乏骨气神采,他又成了首当其冲必须承担此恶果的“罪人”。
初唐以来,文坛有识之士力倡“风骨”,抵御浮艳之风。从陈子昂推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文风,到李、杜、高、岑情思壮丽、风调高华的盛唐诗歌,书坛也感受着风骨英气,开始摆脱王字的笼罩,最终由颜真卿创造出完全不同于王字风范的“颜体”。“颜体”初期“雄”中有“媚”,“颜体”后期则纯以方正雄浑取胜,其抒发恢弘之气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支离重拙却豪壮慷慨。润色开花的秀媚风流终于被元气淋漓的崇高气魄所代替。
然而,创作上的飞跃变化未能在颜真卿本人的书论中得到准确呼应,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自然雄媚”、“明利媚好”、“点画净媚”依然是核心标准。这种认识沿袭了初唐的审美观,说明此时“媚”在书论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即便到了五代,《旧唐书》评柳公权书“体势劲媚”,“媚”的审美地位还是很高。
盛唐后书风的转变是形式美追求渐趋退潮的表现,也是书法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必然结果,其中道德情感及道德批评在书法创新中的推动作用至为显著。在传统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儒家教化所培养起来的道德情感、人格节操和积极有为,始终是士人刚健品格和风骨追求的重要渊源。颜真卿的忠肝义胆和壮烈情怀历来被后世感佩称道,他也因此而成为书论中善美合一的典范、道德批评最坚实的依据。在人格欣赏与书法风骨之间从此建立起极为稳固的同构象征关系。书法教育与人格教育二位一体,软媚流俗不仅是形式问题,更关乎道德情操。
中唐极力排佛兴儒的韩愈,其审美取向的内诣是恢复儒家执著的道德情怀,倡导刚健笃实的儒家人格理想,所以他的书论才会把矛头指向崇佛尚玄的释高闲、王羲之等人。在《送高闲上人书》中,韩愈激赏张旭草书的热烈情感,批评高闲的无动于心;在《石鼓歌》中他对周宣王时古朴劲健的石鼓文大加赞叹,而以戏谑的口吻批评王字:“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从此,“姿媚”便负荷着晋唐两个时代的审美追求和冲突,在赏誉和讥讽之间开始了自己的曲折起伏。
四、“姿媚”的流俗与宋人的意趣
宋人书论虽时有延续晋唐对“媚”的推崇,但大多深受韩愈影响,将“俗”与“姿媚”关联。晋唐备受推崇的形式美不仅演变为低层次的美感,而且带上了道德批评色彩,如朱长文《续书断》品评颜真卿:“公之媚非不能,耻而不为也。退之尝云‘羲之俗书趁姿媚’,盖以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黄庭坚论书云:“数十年来,士大夫作字尚华藻而笔不实,以风樯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殊不知古人用笔也。”又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凡书之害,姿媚是其小疵,轻佻是其大病。”“姿媚”的内涵再不是魏晋时的纯真明媚,也不是唐代的“雄媚”,而是由浮华、工巧、俗媚、病疵等来诠释。这种转换首先与王著等人摹刻《淳化阁帖》而传为范本密切相关,庸媚滑俗、千人一面的卑浊书风激起了有识之士的批判;而更内在的原因则是宋代士人的精神祈尚,道、禅对“色”的超越态度和清淡趣味,儒家对刚健气骨的崇尚,理学对“文以载道”的强调,都在内心深处涤荡着文人的审美观,让他们既欣爱二王的姿媚风流,始终尊其为最高经典,又悄悄绕开他们:另辟蹊径,但大多又无意于颜真卿式的崇高气魄。
这种内敛和收缩是时代气象从壮丽高华转入内省沉静的必然。汪涌豪在《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以“风骨”、“平淡”、“格调”概括盛唐、宋及明清的时代审美精神。这种“平淡”反映到书坛,不再是汉唐的高文大册、碑碣摩崖,也不是魏晋时对“靡丽”、“妍媚”的痴迷,而是以名士的信札、手卷为美,尺牍之间玩赏于个人的意趣和情调,“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或平和温雅,或俊爽桀骜,演绎出“风骨”落幕、“姿媚”流俗后文人趣味的重大转变。
为了脱俗免俗,苏轼取平和萧散一路,而黄庭坚和米芾则取拗峭和奇肆,以狂狷代替醇和的“姿媚”。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故意造作的欹侧和斜耸,既不同于晋人的自然风流,也不同于唐人的正直阔大,而是一种难以遏制的个性化倾向,不合时俗,不甜媚,不践古人,哪怕让人觉得有些夸张、痛苦也要保持一份特立独行的姿态。黄庭坚在《书赠俞清老》中评米芾:“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籍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这种惊世骇俗的狂狷之举在中晚明以后得到了强烈发挥。
五、复兴“姿媚”与“独标气骨”的更迭
当个性创新走到偏激无度的边缘,形式美法则就会悄然复兴力挽乱局。宋代重个性意趣的风尚在元代受到批判,赵孟頫以其清秀逸美、法度严谨的书法示范对当时怪诞百出的书坛起到了清理和规范作用。明代承续赵书风范,尚晋尊法,个性意识退隐,而“姿媚”随之复兴,书论中多有标举“遒媚”、“婉媚”、“妩媚”,一时占据了书论的核心位置。
明初陶宗仪《书史会要》以“媚”评书。评戎昱“筋骨太刚,殊乏婉媚,故雅德者避之”,盛赞蔡襄书“笔甚劲而姿媚有余”,评宋湜“风貌秀整,笔法遒媚”,评康里巎巎“笔画遒媚,转折圆劲”,评王渥“字画遒媚,有晋人风度”。另一位代表是杨慎,他推崇赵孟頫,强调书法“态度”、“风韵”,以婉媚为尚。“唐史称颜真卿笔力遒婉,又称柳公权结体劲媚,有见之言哉!今人竭力仿者但得其遒而失其婉,徒学其劲而忘其媚,米元章所以有笔头如蒸饼之诮也。”(《墨池琐录》卷三)他常以女性丰艳之“媚”譬喻书法:“予尝与陆子渊论字,子渊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妙不清则不妙;予戏答曰:丰艳,丰艳不丰则不艳。”(《墨池琐录》卷二)受此审美趣向引导,明代早期书家大多风流妍媚,不脱赵体风貌。到永乐时台阁体风靡,不可挽回地流向工巧软媚,因袭僵化。明中期的吴中才子在赵体基础上虽有个性发挥,但大都在秀美雅逸中周旋。受禅宗古淡趣味影响的董其昌,在清丽雅淡和追求生新的个性意识中透出的却是局促怯弱的气象。
求异破媚的思路早在祝允明那里就开始,从崇古尊法唯晋人和赵孟頫是瞻,至荡轶古法狂放到无以复加,晚明是一个关捩,其间徐渭、黄道周的书论和创作上的矛盾最具代表性。徐渭在《赵文敏墨迹洛神赋》中肯定赵书的雅媚,认为精致的用笔可以纠正槁涩顽粗,也是行书的表现力之一。他的行书也被袁宏道评为“苍劲中姿媚跃出”。然而,徐渭的狂草或颓放纵逸,或满闷密乱,已经很难用“媚”来解释,更是“丑”,是灵魂的痛苦、挣扎和绝望。黄道周推崇王羲之和赵孟頫,认为:“书法以遒媚为宗,加之浑深,不坠佻靡,便足上流矣。”(《黄漳浦集》卷十九《与倪鸿宝论书法》)但他自己的狂草风貌拗峭奇险,狂狠直下,在压抑痛苦中彰显崇高,已经完全超越了“遒媚”的范围。
晚明书法以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为代表,彻底改变了赵书一统天下的局面。清梁巘《评书帖》云:“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以其实有一段苍老气骨在耳。”“苍老气骨”的不朽风格正是崇高、雄肆和悲怆感的别样表达。书法在“风骨”与“姿媚”的往复摆动中又回到了以“气骨”为尚,这种巨大的转变首先与明代中后期心学大盛、道德热情和道德人格追求殊为强烈密切相关④,而心学后学推动的思想解放和个性张扬更激发了这种崇高感的个性表达。书法雄壮风格的崛起大都伴生于儒学复兴运动,道德批评和道德理想主义的风气往往成为破除柔媚书风、焕发阳刚之气、推动艺术形式变革的契机。书法世界的情感变动和象征表现都深刻地被道德情感所引导和塑造。
六、“姿媚”的衰落与尚碑之“气格”
明清鼎革之际,遗民学者傅山、顾炎武等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对书风的引领产生了深远影响。尚气骨重节操的道德批评是傅山的主要批评角度,他推重以“骨气胜”的颜书,以人品论书品,极力批判奴书:“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题昌谷堂记》)推重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观点:“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主。”(《作字示儿孙》)激烈批判赵书的软美媚俗:“薄其为人,痛恶其书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只缘学问不正,遂流软美一途。”(《作字示儿孙》诗附记)又批判董书的“尚暖暖姝姝”(《书神宗御书后》)。自傅山开始,对传统帖学赵、董一脉的抨击便日趋强烈,大有摧垮这一传统审美取向之势。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新的创作原则:“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足以回临池既倒之狂澜矣!”(《作字示儿孙》诗附记)从此,丑拙、支离、直率这些审美范畴,连同顾炎武所推重的“方劲古拙、斩钉截铁”⑤,代替了传统帖学奉为圭臬的“姿媚”,裹挟着雄健的气魄,开始在尚碑运动中成为支撑性的审美价值。
尚碑运动不仅仅是一场书法运动,它内在的精神命意是捍卫汉族士人传统和儒学传统,与官方理学及皇家艺术趣味抗行,所以士人的书法趣味微妙地关联着气节操守。有清一代成长起来的书家多有好金石的朴学背景,以尚碑为高为雅,为学术之正统,为士人之精神持守故地,所以碑学成为潮流亦是文化捍卫和抗争的必然和典型发露。随着大量碑学资源的发掘流传,书法史的重新清理,碑学地位得以确立。金农在《鲁中杂诗》中写道:“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驰骋。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⑥ 帖学神坛的瓦解和碑学资源的多样,使书学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形态,写碑和碑帖杂糅的书法创新层出不穷。如果说早期郑簋的隶书还有柔媚之风,那么从中期的邓石如、伊秉绶、金农到晚清的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则纯以重、拙、大为尚,金农和沈曾植的书法更以其凌厉和怆烈之象,成为备受争议的“丑书”。
晚清书论的代表包世臣和刘熙载,虽兼取碑帖,但审美取向不脱碑学根底。包世臣强调的用笔“中实”和“气满”,是绝大多数碑派书家奉行的标准;刘熙载在《书概》中对书法阴阳二气的重新解释“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著屈郁,阴也;奇拨豪达,阳也”,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阳刚美和阴柔美,而是超越于此的深沉人生况味和高尚精神境界。所以他在“姿致”和“气格”中以“士气”为尚:“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爱,孔明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姿致何如尚气格耶?”“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清人对“气格”的崇尚,一以贯之于明末清初的遗民气节、朴学运动的文化守成,以至清末国难中的民族觉醒和自强,碑学的隆盛不衰从某种意义上象征着民族生命气象之坚韧与昂扬。
经过两百多年碑学的洗礼和冲击,晋唐法度、姿媚、文雅精致的帖学趣味逐渐式微,落寞中等待着重启的命运之光再次降临。从魏晋人迷恋风流妍媚到清人趋尚古拙质朴,历史似乎在螺旋式地往复,在文与质、姿媚和风骨、法度与个性、美与丑的摆动中,彰显着道德、审美、个性等多重心性价值的魅力、矛盾和张力,也考验着书家的审美识力和价值取向,牵系着一代代士人的道心和文心。
“姿媚”的演变并没有结束,它作为书法审美价值的重要一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几度兴衰起落中,人们既回味着、珍爱着它内含的魏晋风韵和唐人法度,又警惕着它的流俗软媚,济之以遒劲、风骨、意韵、气格甚至狂狷,更有雄浑、平淡、丑拙、古朴等审美风格与之抗衡。“姿媚”不仅仅是“姿媚”本身,它带动的是整个书法史和士人史的丰富内蕴,是牵一发而动万千的缤纷心灵和历史沧桑。
注释:
① 本文引用的书论,未特别注明的,皆引自《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崔尔平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河内利治《汉字书法审美范畴考释》,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宗白华:《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④ 参见拙作《对中晚明书法变革思想原因的重新阐释》,载《东南学术》2005年第2期。
⑤ 转引自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448页。
⑥ 《冬心先生续集》自书墨迹稿本,转引自黄惇等《中国书法史》,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