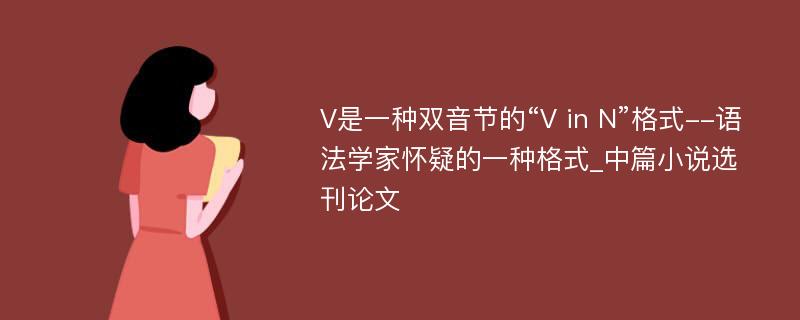
V为双音节的“V在了N”格式———种曾经被语法学家怀疑的格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式论文,语法论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写作背景
最早提到“V在了N”格式的是丁声树等(1961)。该书第七章举出了老舍作品中的两个例子:吃完饭,他躺在了炕上。│她本人可是埋在了城外。
80年代以来,范继淹(1982)、蒋平(1983和1984)、 廖礼平(1984)、朱德熙(1987)、邢福义(1985和1997)、董晓敏(1997)都对这类现象作了论述。其中,董晓敏(1997)的考察最为细致深入。但是,董晓敏讨论的“V在了N”,基本上只涉及了单音节动词。
这一格式中的V,可以不可以是双音节的?范继淹(1982)认为“V(双音)在了N”不规范。该文指出:“扔在了床上│倒在了地上│摔在了地上│掉在了地下——即使合乎规范,适用范围也有限,双音节动词没有这种形式(*围绕在了四周│*寄存在了车站)”。朱德熙(1987)认为这种“V(双音)在了N”不合法。该文指出:“合法的句式的出现频率不一定都很高,不过不合法的句式的出现频率一定极低。下边举一个实例来说。有的文章提出,双音节动词跟单音节动词一样也能造成‘V在了+处所’的句式。……这种句式口语里没有, 书面语里也极为罕见。文章里一共引了十二个例子,其中倒有八个集中在两位作者的两篇作品里,如上文所引。仅仅凭这十来个例子恐怕还不足以证明由双音节动词组成的‘V在了+处所词’的句式已经在书面语里站住脚了。”
本文在上述背景下集中讨论“V在了N”格式中使用双音节动词语的情况。“动词语”的提法,意味着V通常是一个动词, 但有时也可能是一个动词短语。
一 事实跟踪
范继淹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2年,离现在已有15年;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离现在也已有10年。事实表明,近年来“V在了N”格式中使用双音节动词语的现象不是越来越罕见,而是越来越多了。
1.1各种文学刊物,凡是笔者看到的,都发现有这类事实。 请先看13个例子:
(1)自己木已成舟,壮心不死,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孩子身上。 (蒋法武《矿东村0号》,《当代》1983年第2期63页)
(2)这个正在井台上摇辘轳的老头儿, 把刚刚提上来的一筲水泼洒在了地上,……(郑万隆《那寂静的山谷》,《十月》1983年第2 期196页)
(3)她调皮地将头侧了过来,长长的秀发披散在了肩膀的一边。(王金年《韧》,《小说家》1985年第3期94页)
(4)多日来,他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 突然间又降临在了他的面前,……(林希《琴师》,《红岩》1987年第2期76页)
(5)逝去的白鹤被封闭在了湖里, 空中的白鹤却决不会再朝这里飞。(陈吉容《星星索》,《花城》1988年第3期192页)
(6)我只把她的尸体保存在了这里。(王秋海《梦里寻她千百度》,《啄木鸟》1990年第2期65页)
(7)……管理连长又已经树桩般挺立在了丁一知面前, ……(何继青《彼岸》,《中篇小说选刊》1995年第4期142页;原载《时代文学》1995年第3期)
(8)张子慈让老伴拿上东西追出去扔放在了楼门口, ……(孙春平《放飞的希望》,《小说月报》1996年第8期57页; 原载《上海文学》1996年第5期)
(9)……雪峰突然显现在了我的眼前。(余纯顺《走出阿里》,《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18页;原载《小说界》1996年第5期)
(10)那前后两年里的苦难悲怆,都已溶铸在了他的生命中。(赵淇《苍茫组歌》,《小说选刊》1996年第11期21页;原载《解放军文艺》1996年第10期)
(11)不一会儿女乘务员便领着两个肥头大身、扛着大包小包的男人进来,分别驻扎在了两个铺位的上方。(徐坤《如梦如烟》,《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39页;原载《大家》1997年第2期)
(12)……取了自己的衣衫,往那树枝一搭,把那牙苗遮盖在了一片荫凉里。(阎连科《年月日》,《小说月报》1997年第4期8页;原载《收获》1997年第1期)
(13)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偏偏发生在了他身上。(陈铁军《老杂碎》,《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125页;原载《莽原》1997年第2期)
这13个例子分别出自蒋法武、郑万隆、王金年、林希、陈吉容、王秋海、何继青、孙春平、余纯顺、赵淇、徐坤、阎连科、陈铁军等13位作者的笔下,分别见于《当代》《十月》《小说家》《红岩》《花城》《啄木鸟》《时代文学》《上海文学》《小说界》《解放军文艺》《大家》《收获》《莽原》等13个刊物。13个例子按时间顺序排列,全都是范继淹先生文章发表之后出现的;其中10个是朱德熙先生的文章写成之后出现的。下面还有更多的例子,是见于90年代作品的。
1.2这类事实的某些具体说法,有时在不同作者的作品中复现。例如:
(14)他下意识地半欠起身子,目光集中在了家季的身上。(林希《琴师》—78页)(凡是上例已注明的刊物名称期数都用“—”代表,下同)
(15)大家互相看了看,然后把目光刷刷地集中在了老汉身上。(厉夏、方金《古船·女人和网》33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3月)
上例“集中在了”在两位作者的两种作品中复现。又如,下例“出现在了”在四位作者的四种作品中复现:
(16)但第二天那竹签儿却又出现在了小墩子的旧铅笔盒里。(刘心武《小墩子》,《收获》1992年第5期10页)
(17)花妞儿,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边。(厉夏等《古船·女人和网》351页)
(18)此时,……令我一见便怦然心跳的“鬼湖”便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余纯顺《走出阿里》—22页)
(19)那个疯子谁也没有料到又出现在了城里,……(贾平凹《制造声音》,《小说月报》1996年第12期46页)
同样的说法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复现,反映了作者们对这类说法的认同。相同说法在同一作者的笔下复现,自然不足为怪。例如:
(20)此时,静卧在雪山之间、藏族人民心目中的“圣湖”蓦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余纯顺《走出阿里》—20页)
(21)蓦地,喜玛拉雅、岗底斯以及静卧在它们之间的美丽之湖公珠错,就这样不容置疑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同上31页)
1.3这类事实进入了口头广播用语。比如,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李修平广播重要新闻时这么说:
(22)物价涨幅也控制在了百分之×之内。(1997年1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所代表的具体数字当时未听清)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音员说的是标准普通话,这为大家所公认,他们的口头用语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事实上,“控制在了”的说法从李修平的口头上说出来,听起来觉得很自然,并不感到别扭。
1.4这类说法可以进入论说性文章。 林焘先生《北京市郊阴阳平调值的转化》一文曾使用“V 在了”的说法:“总的趋势是连调变读走在了单字调转化的前面。”(《中国语文》1991年第1 期)其中的动词是单音节的。笔者试图做个“小实验”,模仿林先生的写法写了两个句子,分别用了单音节和双音节的动词:
(23)结论既生发于事实又验证于事实,这是《分析录》的又一特色。作者的双脚,牢牢地扎在了现代汉语语法事实的泥土之中。(邢福义《〈汉语层次分析录〉序》,《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2期75页)
(24)用平易质朴的文字来表述学术见解,这是《分析录》的第四个特色。集子中的文章,深入而浅出,把作者的思考与结论透明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读者欢迎这样的文章。(同上)
相信读者阅读起来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语法错误。
1.5 这类说法的使用者在地域上有广泛的覆盖面。
统观本文前边和后边所举的全部例子,可以知道下列人士使用了“V(双音)在了N”格式:周大新(山东)│赵德发(山东)│余纯顺(上海)│方方(南京)│张抗抗(浙江)│季宇(安徽—江苏)│赵淇(广州—江西)│何继青(广州—南京)│邢福义(武汉—海南)│李荣德(湖北)│阎连科(河南)│林旷德(河南)│刘心武(四川)│贾平凹(陕西)│郑万隆(黑龙江)│梁晓声(黑龙江—山东)│徐坤(辽宁)│林希(河北)│王矩(河北)│孙春平(河北)│陈铁军(北京)│李修平(中央电视台)│蒋法武(?)│晓剑(?)│王秋海(?)│晓白(?)│陈吉容(?)│王金年(?)│万方(?)│厉夏(?)│方金(?)│张弛(?)。这里出现了32个名字,粗略地按照东南西北中的地点线索作了排列。有的人长期在甲地方工作,籍贯是乙地方,注明为“甲—乙”,如“安徽—江苏”;有的不知是什么地方人和在什么地方工作,暂且打个问号。如果选择代表地点,以首都北京代表中,以上海、广州、陕西、黑龙江分别代表表南西北,可以显示出这么一个很直观的分布简图:
黑龙江
│
陕西─北京─上海
│
广州
假若包括蒋平(1983和1984)用例中举出的张廷竹、路遥等人,人数就更多。通过这个分布图可以知道,这类说法的使用者不仅人数不少,而且散布在我国幅员广阔的国土上。
二 V的结构和“了”的使用
本部分讨论V的结构情况和“了”的使用条件。
2.1 V的结构
“V在了N”格式中的双音节V,其内部结构并不单纯。
第一,联合式。
“V在了N”格式中使用双音节动词,大多数是联合式。上面所举例子的双音节动词,绝大多数都是联合式的。又如:
(25)……于连夹在手指尖的烟卷也掉落在了地上。(季宇《县长朱四与高田事件》,《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1期59页)
(26)……一圈干叶中,有一滴绿色砰的一下闯撞在了他的目光上。(阎连科《年月日》—19页)
(27)她觉得,她的灵魂依附在了这个永远不会倒下的躯体上。(晓剑等《世界》,《收获》1983年第2期52页)
(28)她全身的力量聚集在了她胸中的一点。(万方《杀人》,《收获》1994年第3期24页)
联合式动词的两个语素,都跟N存在语义联系。其中, 有的两个语素可以分化开来分别进入“V在了N”格式,造成同义或近义的说法:掉落在了地上→掉在了地上│落在了地上。有的不能这么办:控制在了百分之×之内→*控在了百分之×之内│*制在了百分之×之内。这跟所用语素在现代汉语里能否独用有关。
第二,后补式。
后补式V在“V在了N”格式中的使用频率比联合式低得多, 但不是个别现象。如例(4)“降临在了他的面前”,“降临”是后补式。 又如:
(29)你想活着你今夜就离开这儿,随便躲到哪儿,三日五日后回来,我也就饿死在了这儿。(阎连科《年月日》—22页)
(30)张善子闻言大醒,突地双腿一软,跪倒在了秀才面前,……(张弛《天书》,《花城》1989年第6期168页)
(31)不料刚站起迈了一步,一阵带着金星的眩晕就猛扑过来,一下子把他按倒在了地上。(周大新《向上的台阶》,《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第3期36页)
“降临”和这三例的“饿死”“跪倒”“按倒”都由“动+动”构成。下例的结构情况稍有不同:
(32)他的全部身心已经浸透在了一种大言无声的自我陶醉中。(张弛《天书》—53页)
(33)高人云这时刻才开始回想他怎么样就轻易软倒在了街上。(方方《行云流水》,《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第2期66页)
这两例的“浸透”“软倒”也是后补式,但“浸透”更像是“动+形”,“软倒”更像是“形+动”。
从跟N之间的语义联系看,如果把构成后补式的两个语素记为ab,可以分析出三种情况:1.ab和N都有可组合的联系。 如:跪倒在了秀才面前→跪在了秀才面前,倒在了秀才面前│按倒在了地上→按在了地上,倒在了地上。2.只有a跟N有可组合的联系。如:浸透在了自我陶醉中→浸在了自我陶醉中(* 透在了自我陶醉中)│降临在了她的面前→降在了她的面前(*临在了她的面前)。3.只有b跟N有可组合的联系。如 :饿死在了这儿→死在了这儿(* 饿在了这儿)│软倒在了街上→倒在了街上(*软在了街上)。
第三,偏正式。
偏正式V在“V在了N”格式中的使用频率跟后补式大体相同。例如:
(34)他已把讲稿熟记在了心里,……(周大新《向上的台阶》— 31页)
(35)于是一大团怒气就郁积在了做爹妈的心里。(同上47页)
(36)先爷……猛一下顿立在了面前。(阎连科《年月日》—17页)
(37)盲狗……又回来死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同上21页)
(38)无奈,他只好像个病弱的老豹子一样颓然坐倒,半卧在了路边。(赵德发《选个姓金的进村委》,《小说月报》1997年第6期67页)
从语义关系看,如果把构成偏正式的两个语素记为ab,那么可以跟N发生组合关系的是第二个语素b。比方:熟记在了心里→记在了心里│郁积在了做爹做妈的心里→积在了做爹做妈的心里│顿立在了面前→站(=立)在了面前│死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守在了那棵玉蜀黍下(“死在了那棵玉蜀黍下”可以说,但这个“死”同“死守”中的“死”语义不同)│半卧在了路边→卧在了路边。
有的双音节V似乎更像是连动式。不过, 也许仍然可以理解为偏正式。例如:
(39)有一样东西雪花一样飘打在了先爷脸上。(阎连科《年月日》—22页)
(40)焦干的黑色的穗缨,被手一碰,就花谢般断落在了草间。(同上25页)
“飘打在了先爷脸上”是“飘来打在了先爷脸上”,“飘”和“打”之间有连动关系;不过如果把“飘”看成“打”的方式或状况,似乎也可以勉强归入偏正式。同样,“断落在了草间”是“断开落在了草间”,“断”和“落”之间有连动关系;不过如果把“断”看成“落”的情态或状况,似乎也可以勉强归入偏正式。
第四,动宾式和主谓式。
有的双音节V是动宾式,有的双音节V是主谓式。都只发现一例:
(41)学校由牛屎村迁建到这儿,……黄支书老赖拍板在了自己村,……(李荣德、林旷德《天上一朵带雨的云》, 《中篇小说选刊》 1997年第1期205页)
(42)他一下便软瘫地蹲下来,……连身上唯一的白布裤衩都汗粘在了大腿上(阎连科《年月日》—16页)
上例里,“拍板”显然是个动宾式,“汗粘”显然是个主谓式。
2.2 关于“了”的使用
“V在了N”格式中,动词不管是单音节的还是双音节的,“了”的使用情况具有一致性。这里,只结合V为双音节的用例, 粗略地解说为什么有时说成“V在了N”,什么时候不能或不大能说成“V在了N”。
第一,加“了”,是为了强调行为已经定位实现。例如:
(43)全部耙耧人都把存好的玉蜀黍种子拿出来,赶在雨前把秋庄稼点种在了土地里。(阎连科《年月日》—6页)
(44)人怎么就难得燃烧起来呢?那个引发爆炸的药捻儿究竟萎缩在了哪里?(徐坤《如梦如烟》—34页)
前一例,陈述行为定位实现于“土地里”,后一例询问行为定位实现于“哪里”。加个“了”字,对行为的已经实现具有强调作用。
有时,说的是想象的事,但可以想象已经实现,因而也可以加“了”。比如例(29)“你……三日五日后回来,我也就饿死在了这里”。
第二,如果行为尚未实现,而且词面上出现“可以、将要”之类未然性词语,那么不能加“了”。
动结式动词语包含完结意义,但是,从跟客观事实的联系看,它所表示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已经实现的。比方“推倒”包含完结意义,但说“他一用劲,木桩就会被推倒”时,“推倒”的行为尚未实现。“V在(N)”情况一样,“V在”表示一种定位完结的意义,但如果行为尚未实现,并且为“可以、将要”之类词语所标明,是不能加“了”的。例如:
(45)他只消把盲狗领到地里,那田里的鼠窝便可以一个不漏地出现在先爷的锄下边。(阎连科《年月日》—11页)
前面的“可以”表明事情只具有可能性,因而后面不能说成“出现在了”。
第三,即使行为实现,但如果行为游移,跟N的联系缺乏定位性,不大能加“了”。就是说,N所表示的方位处所应该是相对确定的, 而不是泛指性的。即使是用疑问代词“哪里”,也是求代某个确定的方位处所。看下面的例子:
(46)狗便沿着来路往梁上走,先爷跟在它身后,热乎乎的脚步声,像枯焦的几枚树叶打着旋儿飘落在烈日中。(阎连科《年月日》—6页)
这一例,不好说成“飘落在了烈日中”。这是因为,对于泛指性的“烈日中”来说,“飘落”的行为是游移的,不定位的。
范继淹先生所说的“寄存在了车站”,完全可以成立;至于“围绕在了四周”,孤零零地说出来不大能成立,这正是由于“围绕”和“四周”的联系具有较大的泛指性,定位性不强。
第四,“V在了N”总是居于句末,有煞句作用。它或者出现在整个句子的末尾,或者出现在一个分句的末尾,如果出现在句子中间,即使行为已经实现,而且具有定位性,也通常不加“了”。例如:
(47)解放后,他的这种经历深受政府器重,先是安排在民政部门工作,……(陈铁军《老杂碎》—131页)
(48)不管怎么说,都只得和这个打锣的勾搭在一起做了家贼。(同上136页)
上例“安排在”“勾搭在”用于句中,后边分别续上了“工作”“做了家贼”。在这种情况下,不用“了”。
三 数量的多少和格式的合法
本部分讨论如何看待“V(双音)在了N”格式用例数量多少,并讨论如何评估这一格式是否合法。
3.1 关于多少
上述事实表明了“V(双音)在了N”格式的用例数量和使用数量都不能算少。通过长期的跟踪观察,还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这类格式的使用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谁肯花时间再看上若干本《小说月报》或《中篇小说选刊》,一定又可以找到更多新的用例,从而举出更多使用者的名字。
从双音节V内部的结构方式上看,也不能算少。 上面已经列出了联合式、后补式、偏正式(包括连动式)、动宾式和主谓式。有的格式只看到一个例子,但不是不能类推。比方,这样的说法完全可以成立:“敌人终于整天龟缩在了碉堡里。”这里的“龟缩”便是主谓式。
也许可以这么辩驳:不管怎么说,V为双音节的“V在了N”, 还是罕见的。有的文章里可能看不到一个用例,有的文章里可能只看到个把用例,有的文章里顶多也只看到几个用例,绝对不会超过十个!
对于V为双音节的“V在了N”格式来说,这样的评说是不公平的。事物的比较,必须放在同等级、同类项的水平线上来进行。评估“V 在了N”的使用数量,最具有可比性的格式应该是“V到了N”。 根据董晓敏(1997)的统计,V是单音节时,“V在了N”的使用频率接近于“V到了N”,而远高于“V给了N”“V向了N”。V是双音节时,情况如何?请看对两篇小说所作的统计:
作者 作品字数 V在了NV到了N
陈铁军 《老杂碎》约2.5万2例
3例
阎连科 《年月日》约5万 9例
1例
陈铁军《老杂碎》(《中篇小说选刊》1997年第4期)中,“V(双音)到了N”共出现三次:搀送到了(125页)、物化到了(126页)、运用到了(127页),比“V(双音)在了N”多一次; 阎连科《年月日》(《小说月报》1997年第4期)中,“V(双音)到了N ”只出现一次:消失到了(14页),比“V(双音)在了N”少八次。这个小统计也许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至少可以由此知道,“V(双音)到了N”和“V (双音)在了N”在使用频率上互有高低。如果说“V(双音)在了N ”是罕见的,那么“V(双音)到了N”同样也是罕见的。然而,有谁怀疑过“V(双音)到了N”的合法性?
3.2 关于合法
“V结+了”是现代汉语的强势格式。(“结”代表V后结果性补语成分。动宾格式也是强势格式,笔者1997已经论及。)一个结构,只要是动结式的,需要时就十分自然地加上“了”字。比如:看见了,站住了,推翻了,打倒了。
“V在了(N)”格式衍生于“V结了(N)”格式。由于受到“V 结+了”这个强势格式的影响,介词“在”和“到、给、向”只要用到动词后边,便很容易附向动词,成为结果性后补成分,于是“V介N”便很容易转化为“V结(准动)了N”。这就是说,“V在了(N)”格式建构在“V结了(N)”格式的基础之上,有强势格式的背景,得到强势格式的有力支撑。比如:
撒在大海→撒在了大海
撒到大海→撒到了大海
撒向大海→撒向了大海
撒给大海→撒给了大海
如果说不用“了”时“在”和“到、向、给”还可以看作介词,或者说还存在介词和后附准动词两种可能性,那么用“了”之后它们便不再以介词身分介引后边名词给前边动词,而是完全附向动词,以准动词身分跟前边动词组合成了动补结构。
一个语法格式一旦成立,便具有强烈的类化力。正因如此,“V 在了(N)”格式在使用中逐渐得到了发展。其类化轨迹为:
首先,V是单音节的既可成立,类推使用起来,V是双音节的也会跟着出现。比如:
掉到了地上 落到了地上→掉落到了地上
掉在了地上 落在了地上→掉落在了地上
其次,V是双音节的既可成立,类推使用起来,V本身也就允许出现多种结构,包括动结式结构。当V是动结式结构时,“V在”成了更大的多层次动结式结构,即V为动结,“V在”又是动结。比如:
跪在了他的面前→跪倒在了他的面前
吊在了大榕树上→吊死在了大榕树上
再次,V是双音节的既可成立,类推使用起来,V本身也就允许出现多音节的复杂现象。看实际用例:
Ⅰ.“(双音V+双音V)+在+了”。
(49)我真喜欢北大荒的豆油,……好像把一个秋天成熟的谷草玉米和豆子,统统都压缩收藏在了这里,调出了这样深沉明洁丰富的金黄色。(张抗抗《永不忏悔》,《中篇小说选刊》1988年第1期59页)
上例先用两个双音节动词“压缩收藏”,然后再用“在了”。这是“V在了N”中V的扩展。
Ⅱ.“(V在+V在)+了”。
(50)于是女作家们在坐累了的时候就素性躺在或趴在了床上,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大家的聊天和侃。(晓白《学校轶事》, 《小说家》1997年第3期119页)
(51)有一种理论,认为新写实主义作家把自己都隐藏在或者叫做埋没在了自己作品里。……(同上118页)
前一例,先用“躺在”“趴在”,再用“了”。其中的“躺”和“趴”都是单音节的;后一例,先用“隐藏在”和“埋没在”,再用“了”,其中的“隐藏”和“埋没”都是双音节的。这是“V在了N”中“V在”的扩展。
上述的类化轨迹是合乎逻辑的,其合法性是很难怀疑的。应该注意的是,“V在了N”格式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应用的实际需要。具体点说,是因为它具有“V到了N”等其他格式所不能取代的作用。看下面这个例子:
(52)那时候各有自己的管区,……所以这个警察一看田三儿快不行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赶紧扶住他,一边和颜悦色地鼓励他“再坚持一会儿”,一边把他搀送到了别的警察的管区里。恰巧另一管区的警察也发现了这一情况,满脸堆笑地迎上来,又将他搀送了回来。田三儿,一代著名的吃家儿,就这么被两个警察搀来搀去,最后饿死在了双方管区的交接处。(陈铁军《老杂碎》—125页)
上例前面用“搀送到了”,后面用“饿死在了”,修辞上讲究了对称性。由于情况已经实现,都用了“了”字作了强调;由于语义上存在“移位”和“定位”的细微差别,前者需要用“到”,后者则需要用“在”,二者不能互换。可知,“V(双音)在了N”有时是不可取代的。这正是这一格式可以取得合法化地位的语用根据。
四 结束语
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但是书面语并非口语的简单复制,而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句法格式的规律性类推衍生,便是书面语发展的重要轨迹之一。口语里本来没有“V在了N”,老舍写《骆驼祥子》时使用这一格式,应是从“V到了N”之类推衍而来。后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这一格式按其自身规律进一步推衍,于是发展成了一个跟“V到了N”等平行同用的颇有生命力的格式。
据张寿康(1979),“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是在五四运动时期(1917—1921)。考察“V在了N”在书面语中的使用情况,不能只看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作家作品。那些年代的作品,离“五四”运动毕竟只有二三十年;而八十九十年代的作家作品,则离“五四”运动已有七八十年了。改革开放以来,汉语书面语语法格式的发展很值得注意。就“V 在了N”格式而言,是更多地见于新时期中青年作家作品的。
书面语能不能影响口语?“V(单音)在了N”的说法,经常可以在电视里各种球赛的口头解说中听到:“V(双音)在了N”的说法,也在李修平的口头广播中出现了。当然,这类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口语,但无论如何毕竟是从人们口头上说出来的,起码跟口语沾了点边。这是不是表明书面语对口语可以有所“浸润”?口语和书面语之间是只有单向影响的关系呢,还是彼此间可以有双向影响?这个问题很值得进一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