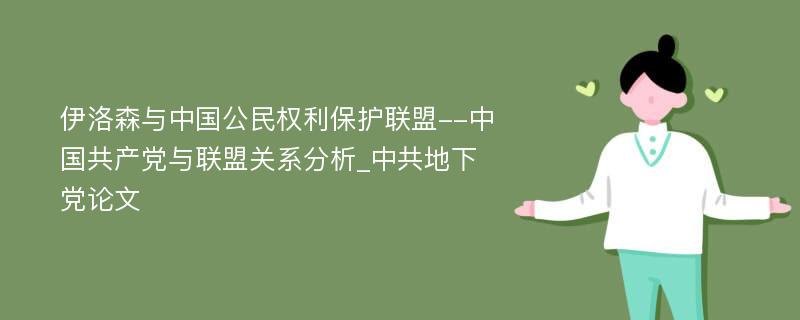
伊罗生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兼析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民权论文,中国论文,生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30年代,由宋庆龄领导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胡适、林语堂等著名人士参加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动,是中共党史和民国史上为人熟知的篇章。其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可歌可泣,杨杏佛甚至因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长期以来史学界早有定论,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倡议发起人。同时,史学界也一直认为同盟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但是,由于材料的匮乏,人们对同盟与中共关系的研究,大体上还是从同盟的活动轨迹和一些当事人的揣测来加以推断。史学界也认识到,同盟得到了当时一些同情中国革命或支持人权的国际友人的支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伊罗生就是同盟成员,后者更是同盟执委会的委员和《中国论坛》的编辑。但是,除了主办《中国论坛》外,伊罗生还起了哪些作用?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和资料的局限,也不得而知。现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罗生档案中所存的一些材料,不但对我们研究伊罗生在同盟中的作用有所帮助,而且对认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缘起提供了新的线索。本文不是对同盟的全面研究,也不是对伊罗生所做工作的完整介绍。笔者希望从伊罗生档案中发现的新材料谈起,并结合其他一些文件,对伊罗生参与发起同盟的作用以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中共地下党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梳理。这一工作应对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共城市工作策略以及国际人士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帮助。
《中国论坛》与民权保障运动的最初设想
新材料显示,虽然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发起人,但是有关成立保卫民权组织的最早建议却是来自美国记者伊罗生。他参与发起同盟与其主办《中国论坛》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单地回顾一下伊罗生与《中国论坛》的创办。伊罗生出身于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曼哈顿的一个地产商。他从小求知欲强,对东方文化有很大的好奇心,喜爱冒险,有着极强的个人主义精神。他又喜欢写作,在大学时期就当了《纽约时报》的实习记者。1930年底他到达上海时,才20出头,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志在闯荡世界的伊罗生有着对生活的朦胧憧憬。虽然他初来中国时尚未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但在美国的学习经历已在他身上留下了一定的思想烙印。特别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深受杜威派学者的熏陶,受自由思想的影响颇大。①1929年纽约市长竞选时,他正好在《纽约时报》实习,随行采访参加竞选的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对这位和平社会主义活动家的思想有不少了解,托马斯朴实的品质令他大为敬佩,二人遂结成了忘年交。②
伊罗生来沪后,先后在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和有国民党背景的《大陆报》任职。这两份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记者身份给了他不少机会去观察1930年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时值南京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政权为维护其统治对一切异见人士进行不遗余力的镇压,上海十里洋场的光怪陆离又让他看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许多特权,中国劳动大众的贫穷苦难更是让他触目惊心。1931年夏,他沿着长江实地考察,深入川北腹地,顺流而下时正碰上百年不遇的洪灾,亲眼目睹了大水吞噬生命、百姓流离失所的惨象。这一切活生生的现实给了这位充满理想的美国青年以极大的震撼。同年春夏,他结交了两位西方左翼记者。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史沫特莱,另一位是名叫弗兰克·格拉斯的英国籍的南非记者(即后来成为中国托派组织领导人之一的李福仁)。前者是当时闻名于上海新闻界的激进分子,与中共和共产国际有联系,并与上海知识界、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交往密切。后者是南非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因支持托洛茨基路线而脱党,刚到上海。史沫特莱和格拉斯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方向有相似看法,对中国革命都抱有同情心,且都来华不久,对中共内部路线、派系斗争尚未了解。因此,两人很快成了朋友,并极力想把伊罗生引入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特别是格拉斯在1931年夏与他一起沿江去了四川等地,一路上对他耐心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史沫特莱和格拉斯的影响下,伊罗生对中国社会的震惊发现很快转化成了对国民党的愤怒。不久,他也成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同情者。③
1931年秋,由史沫特莱引荐,伊罗生认识了宋庆龄和一批文化界的左翼人士,并由此接触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1932年初,在史沫特莱和宋庆龄的鼓励下,伊罗生与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始主办期刊《中国论坛》。30年代初的上海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的腥风血雨,滞留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及其地下党组织面对国民党的严密控制,在千方百计寻求生存机会的同时,急需自己的舆论工具,用以鼓舞人心,团聚力量,重整旗鼓。然而,国民党的无情镇压使得中共出版物和各类左翼报刊难以幸存。而伊罗生是一位享有治外法权的美国记者,他的出现对中共地下组织来说,不啻是雪中送炭。《中国论坛》从1932年1月创刊到1934年1月停刊,一共存在了两年。一开始它以周刊形式发行,由于国民党与上海租界当局的百般阻挠,曾两度被迫中断,出版变得不规律。尽管压力重重,《中国论坛》在其后半期增加了版面,并由单一的英文版扩展成中英文双语版。《中国论坛》总共发行了40期,到后期其发行量达3500份。除了上海之外,它在北京等10多个城市都建立了发行点,在美国、苏联、东南亚诸国亦有读者。
《中国论坛》中的大量篇幅用于揭露与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其笔调尖刻辛辣,对国民党内部纷争和贪污腐化亦多有评论。其中的重磅炸弹是1932年5月大革命失败5周年时所撰写的特刊“国民党反动的五年”,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残酷镇压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压制民主,滥杀无辜进行了多方位的激烈鞭挞。特刊出版后,又以小册子的形式增量发行。《中国论坛》的另一重点是对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评论与谴责。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其报道的焦点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计划和行动,以及中国各界对日抵抗运动。除了对国民党、西方帝国主义、日本军国主义的攻击外,《中国论坛》还承担着宣传中共主张,报道中共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农村武装斗争和反抗日本侵略活动的任务。江西苏区政府与红军的消息通过这个刊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国际进步活动也不时在其版面上有所反映。在杂志创办初期,伊罗生还组织翻译了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一些小说,一批中国左翼文学最早的英文译文通过它得以问世。④
《中国论坛》咄咄逼人的气势一开始就使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感到来者不善。实际上在1931年的夏秋之际,伊罗生与史沫特莱等人的来往及其同情中共的言论就已经让他上了美国驻上海总领馆与上海租界当局的黑名单。⑤《中国论坛》一问世,上海租界的一些英文报刊就纷纷指责它的亲共立场。伊罗生曾供职的《大美晚报》称这是一份“挺妙的粉红色新周刊”。⑥这算是客气的评论,其他措辞严厉的大有人在。就连远在美国的报刊杂志也急着插上一脚,把它斥为“一份反动的、谩骂性的、致力于‘红色宣传’的六页周刊”。⑦在《中国论坛》存在的两年中,伊罗生与其他报刊的舌战从未停止。来自舆论界保守势力和亲国民党势力的攻击虽然频繁,但并没有构成对它的生存威胁。但是出自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就有所不同。《中国论坛》诞生不久,日本侵略者挑起的“一·二八”事变演变成对上海的全面进攻。法租界当局立即以局势不稳为由,下令《中国论坛》暂停,它由此被迫停刊6星期。复刊以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特务对它的骚扰破坏从未停止。法租界刑事侦缉部的不速之客多次不请自来,骚扰《中国论坛》的办公室。在其中工作的中国人员先后受到国民党便衣特务的跟踪威胁。⑧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杂志的编辑部竟难以找到容身之地,其所在的办公楼业主强行毁约,伊罗生的办公室被迫数次搬迁。《中国论坛》一开始有专门的印刷所承接,但时过不久,不少印刷所都知道了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不愿染上“通共”嫌疑,纷纷回绝它的生意。
由于伊罗生是美国公民,享有在华治外法权,国民党当局对他本人奈何不得。但是对《中国论坛》的流通,当局还是有办法设置障碍的。1932年6月,国民党政府在与美国总领事交涉的同时,命令北平和上海等地的邮局扣压《中国论坛》,导致其发行受到严重阻挠。紧接着,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出面,以撤销其领事保护权来要挟伊罗生,逼其就范。到8月,在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当局的压力下,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揽其业务,《中国论坛》一时无法出版,陷入困境。
麻省理工学院伊罗生档案中现有一份《备忘录》,写于1932年6月15日,正是《中国论坛》受到严厉打压之时。此文件虽未署名,但完全是以刊物主办者的立场来书写的。从其内容来看,再参照其他材料,我们应该有把握地认为它出自伊罗生之手。这份文件极有可能是伊罗生在与其他人(特别是史沫特莱)商量,并得到其支持后起草的。⑨《备忘录》一开始就提到了《中国论坛》在国民党当局阻挠下遭遇的邮局发行困难问题。作者急切地表示:“只是为一直以来的形势所不允许,《中国论坛》才没有被作为党的喉舌,其编辑亦未能成为党员。然而,本报与其编辑一直愿意严格遵循一条明确的革命路线,在被要求保持合法性的有限范围内做任何被认定为有价值的工作。”文件简略地回顾了刊物的工作,不无自豪地说:“根据所收到的许多信息,有理由相信这份报纸并非没有影响与价值。”
但是,《备忘录》又指出,尽管《中国论坛》谨慎行事,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镇压还是降临到了它的头上。这就迫使它设法去捍卫出版发行的权利。文件进而强调,归根到底,《中国论坛》所面临的困难就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问题。《中国论坛》一直在不懈地揭露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统治、扼杀言论自由的行为。然而,效果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国民党有一套镇压手段。所以,除了对国民党恐怖统治进行揭发外,中共还应设法寻找新的武器,主动进攻。作者从《中国论坛》的工作谈起,进而论及他对中共地下工作斗争策略的看法,并“建议在中国国内外发起一场尽可能最广泛的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的运动。把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作为我们运动的出发点。这些基本问题将使我们有可能集结起一条广阔的统一战线。这些基本问题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接着,作者详述了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意见,其中最主要的有这么几项:
1.在运动正式发起之前,寻求国内外各类人士和组织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问题的支持。
2.由《中国论坛》打响运动的第一枪,出版一份特刊,登载国内外知名人士的声援书,并同时发表进一步叙述和揭露白色恐怖统治的文章。
3.在接下来一段时期内大造舆论声势,并组成一个专门团体为维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而斗争。
4.改版《中国论坛》,从单一的英文版到中英文双语刊。
5.邀请如孙逸仙夫人这样的人士来带领,她可用来作为整个运动的凝聚点。但是在她周围,应该有一个严密的委员会去完全但不显露地控制运动方向。
6.时机成熟时,邀请国外著名人士来华参加群众性大会。
7.关键是共产党要及时介入,直接领导运动,把这一斗争引导扩展到工人群众中去。
《备忘录》认为,说到底,国民党对各种反对势力的镇压及对不同声音的扼杀是否认人的基本权利。中共地下党的斗争如能从维护和争取基本人权出发,将对自己十分有利,能赢得广泛的支持。它反复强调,中共应利用社会知识精英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以争取基本民权为口号,把各类自由人士吸引进来;特别是在初期,他们的参与将对运动的发动非常有利。它还指出:“形形色色的基本上带有反动性质的人士在运动之初是可以被革命力量所利用的。”文件强调,随着运动愈来愈激进,最初参加运动的自由派人士中的大多数都必然会“叛离”,这一结果不可避免,因此,运动的核心领导必须对这些人物在运动中能起的作用有清醒认识。地下党应该主动掌握时机,建立起运动的群众基础,在适当的时候把这批自由派人士清除出队伍去。作者热切表示,《中国论坛》可以担负起运动主要喉舌的重任。⑩
这一建议的提出是符合伊罗生的个性和先前想法的。早在1931年末《中国论坛》酝酿出版期间,伊罗生就希望把报纸办成堂堂正正的中共舆论工具,公开宣传和报道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当时他提出:“与其因需要而受限制,把它搞得平淡无味,结果不值一读,还不如碰运气尽可能地干多久是多久。”但是这一主张没被接受,中共地下党想作长远打算,不希望办报方向过于激进。(11)最后,对外放风把《中国论坛》说成是一份呼吁抗日救亡的报纸。创刊号出版时,伊罗生遵照了地下党的意见,对一些措辞进行了修改,并声明:《中国论坛》系独立办报,与任何政党无关。(12)当然,上海租界是没有人相信其声明的。结果,伊罗生在刊物上的言论愈来愈激烈,导致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联合围剿《中国论坛》。但年少气盛的他并不畏惧,国民党越是骚扰,他就越想反击。很可能他为此构思了新的计划。从《备忘录》的口气看,建议是直接向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提出的。文件说:“对《中国论坛》作用和性质的整个问题最恰当的认识应从它对革命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价值的角度出发……如果《中国论坛》能从事一项有着明确、具体、直接的目标的建设性任务,其价值增长可能会不可估量。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谨冒昧提出一项行动建议。我们认为,这项行动,即使部分成功,也将帮助党掌握极有利于我们运动的武器。”(13)从这些话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伊罗生求战心切,在与中共地下党的合作中,他很想干一番大事业。
民权保障运动设想的付诸实施
史学界已认识到,虽然同盟的公开亮相是在1932年12月,但其筹备工作在大约半年前就开始了。据杨小佛(杨杏佛之子)回忆,在1932年的夏秋间,同盟的一些文件,如入会志愿书、会费收据等就已付印。(14)但是如果说有关文件在夏秋间就已准备就绪的话,同盟的酝酿工作在时间上应当更早。对照《备忘录》提出的计划与以后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宣言和章程,不难看出,同盟的任务虽然后来写得更具体,但二者一脉相承,在基本点上完全相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谴责国民党“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以及“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的状况,决定组织团体“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必需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15)在同盟宣言和章程所公布的三项任务中,争取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被明确列入。很明显,后者延续了前者的思路,有着清晰的继承性。现有史料没有显示《备忘录》是如何交给地下党的,地下党中又是哪些人阅读了这一文件并作出决定,但从以后事件发展的迹象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有关方面肯定很快收到了这一建议,并对此作出迅速反应,表示了积极的支持。
设身处地地从上海中共地下党的视角来看,《备忘录》提议的这一运动不但有助于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有可能得到各界人士的呼应的。30年代初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一切反对势力的镇压和对一切不同声音的扼杀,不只威胁到了中共的生存,也粉碎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的幻想。知识界的自由派对南京政府成立后日趋专制的倾向深感失望,不少人不惧危险,公开批评国民党对民主的践踏。1931年以来,在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制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政权坚持的“不抵抗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各界对它的不满。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方面,1927年发动反共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在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军警特务系统,企图剿除一切异己,巩固其统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仍藏身于上海租界,继续与国民党周旋。其他各种反对或不满蒋介石政权的势力也聚集于此。宋庆龄于1931年从欧洲回国后定居上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此时对国民党政权也已心灰意懒,离开南京来到了上海,专司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许多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作家和文艺家也把上海租界当作政治避难所,希望上海的特有氛围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一定的空间。总之,上海具备开展这一民权运动的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
迄今为止,史学界的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虽然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依然不时组织工人罢工、街头抗议等激烈活动,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已在考虑城市工作的新方法,寻找新力量。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和“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都是中共寻找新策略的实例。宋庆龄从欧洲回国不久,中共就与她建立了直接联系,从此开始了共同反对蒋介石统治的长期合作。
在宋庆龄与中共的早期合作中,最著名的就是救援共产国际上海远东局秘书牛兰夫妇的活动。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一救援活动与同盟有着直接的关系。牛兰,又名保罗·鲁埃格(Paul Ruegg),其妻又名格特鲁德·鲁埃格(Gertrude Ruegg)。1931年6月,夫妇俩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被迅速移交给国民党当局。中共地下党立即配合共产国际开始营救工作。宋庆龄自1931年下半年起,就承担了公开救援活动的领导工作(16),伊罗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2年7月,救援牛兰夫妇的活动达到了高潮。在伊罗生的建议及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一个以宋庆龄为首、吸引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参加的“保卫保罗与格特鲁德·鲁埃格上海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元培、胡适、杨杏佛、林语堂、鲁迅等人都在其中。(17)这么多国内著名知识分子毅然参与这一运动去拯救一对他们并不熟悉的外国夫妇,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不少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程度已上升到了极点。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当然观察到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状态和人心向背,深知这是有利于中共城市工作的新契机。有迹象表明,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掀起高潮的同时,地下党已经对伊罗生提出的《备忘录》有了明确指示,一个新的活动计划在逐渐形成。
从现有材料看,同盟的具体任务和组织形式在经过大约两个月的讨论后,到8月份已基本成型。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内,组织这场民权运动的设想开始变得更具体化。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口号下,这一酝酿中的组织准备把营救被国民党监禁的政治犯作为主要工作。这一计划的修改和具体化可能是来自中共的直接指示,也可能是包括宋庆龄、伊罗生、史沫特莱、杨杏佛等在内的未来同盟的核心成员讨论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一行动计划必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的首肯的。当时,援救牛兰夫妇的活动正在紧张进行,被国民党政府所逮捕和囚禁的政治犯中的绝大多数人,不是中共党员,便是同情中共的进步人士。把保护和营救政治犯作为运动的集中任务当然对中共有极大帮助。
该组织起初拟定名为“中国保卫政治犯委员会(The China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向国外最早的通报是1932年8月22日伊罗生给罗杰·纳什·鲍德温的一封信。鲍德温是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也是史沫特莱的朋友,时任美国民权自由联盟总监和国际拯救政治犯委员会主席。在此信中,伊罗生告诉鲍德温,一个旨在争取人权、营救政治犯的中国民运组织正在筹建之中。他说:“为此,我向您作出最紧急的呼吁,请求合作与直接的援助。这个想法是组成一个中国保卫政治犯委员会,这一委员会成员将包括中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会组织、作家、教育工作者、艺术家、学生、戏剧界人士——以及所有在保卫基本人权、反对恐怖统治问题上有共识的人士。”他进一步介绍了这一组织所要做的两项具体工作:一是寻求律师在司法方面对政治犯的保护;二是在国内外宣传反对恐怖统治,同时对监狱与法庭本身的状况进行调查。他希望鲍德温同意把这一酝酿中的中国人权组织与美国民权自由联盟和国际拯救政治犯委员会挂钩,建立隶属关系,给予道义和资金的援助。他还告知鲍德温:“虽然这是向国外发出的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一封信,但是调动所有以上提到的中国国内组织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当然,伊罗生在论及建立民权组织时,不会对鲍德温透露这一组织的最终政治目的,并隐瞒了中共与这一计划的关系。他说:“这个建议中的委员会不挂任何政治旗帜。”(18)
同盟的筹备工作在这一时期进展顺利。1932年9月7日,一份中国保卫政治犯委员会章程的草案完稿,准备交付有关人员讨论通过。这份草案的内容与伊罗生在8月22日信函中向鲍德温的介绍一致。草案指出:“中国保卫政治犯委员会组成的目的是援助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他们由于与中国现今统治者政见不同而遭迫害。”章程草案为英文,不像是译文。(19)9月21日,伊罗生再次致函鲍德温,寻求支持。从伊罗生致鲍德温的第二份函件来看,这一组织的名称还有待最后敲定。(20)
在接下来的数周内,一桩突发事件在自由知识分子中掀起轩然大波,也使得同盟的酝酿工作变得复杂起来。1932年10月中旬,国民党特务突袭在上海的中国托派组织,逮捕了陈独秀。尽管陈独秀这时已与中共分道扬镳,是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领导人,但仍被国民党视为中共重要人员,蓄谋剪除已久。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各界顿时哗然。这位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当时虽似落魄,但他在中国知识界、文化界和政界的声望仍是高出云表,仰慕者不少。不少知名人士立即纷纷上书致电国民党政府乃至蒋介石本人,敦促放人。除翁文灏、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傅斯年等人在北平呼吁外(21),上海的各界人士也焦急不安。林语堂在与杨杏佛、柳亚子等人商议后,于10月22日致信蔡元培:“堂与杏佛先生议,学界同人应以文化立场出来说话,况牛兰营救如彼,而对有文化贡献之国人,反漠然若此,似为失体,杏佛先生已经同意。本午亚子来电,亦谈此事,兹已由彼拟就电稿。如蒙同意,请斧正,交夫人转下。杏佛已允签名以外,学界列名,当亦不少。”(22)第二日,以蔡元培领衔的援电发至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23)
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柳亚子等都是“保卫保罗与格特鲁德·鲁埃格上海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对陈独秀事件的热切关注很可能使他们在“委员会”内部也多少谈及陈氏的问题。这又让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中共地下党立即警觉了起来,并迅速对此作出了指示。伊罗生是“鲁埃格上海委员会”的秘书,《中国论坛》又是救援活动的主要舆论工具。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四川路216号302室《中国论坛》办公室内,即“一个地点,两块牌子”,委员会的不少事宜都经伊罗生之手。(24)他保留下来的一份匿名文稿透露了中共地下党当时对运动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的主旨是阻止“鲁埃格上海委员会”出面声援陈独秀。在阐明了中共对陈独秀和托派组织的态度后,这份文稿明确指出:“叛徒们的被捕主要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它接着强调,正是这一原因,“我们不能为要求释放陈独秀而专门展开一场运动。(鲁埃格上海)委员会是特地为保护一位革命者而组建的,我们必须防止用它来保护一个革命运动的叛徒”。针对知识界精英跃跃欲试、力图组织营救陈氏之意,文件进一步指示,如果有人向委员会正式提出这一问题,“我们应讲明发起一场全面反对白色恐怖的斗争的必要性,陈独秀被捕问题在这场运动中会有一个恰当的次要地位。这场全面运动应由现在正在筹备中的新的保卫政治犯委员会来负责。如可能,鲁埃格委员会完全不应涉足陈独秀问题。”(25)
可以说,正是为了抵消由陈独秀被捕而造成的冲击波,抓住契机先发制人,化被动为主动,当时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决定把尚在腹胎中的同盟迅速推向前台,要求同情陈独秀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去参加“一个更广泛的反对白色恐怖的运动”。(26)是否有人最终把营救陈独秀的问题正式放到鲁埃格委员会的桌面上来,委员会内部对此有什么样的争论,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是有中共地下党指示的这一背景,宋庆龄为何在这一时候公开出面就可以理解了。1932年10月底和11月初,宋庆龄先是表示她将向国民党中央“提议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专门处理政治犯事件”。(27)然后声明:“社会仅知营救陈独秀,而不提其同时被捕之十一人,更未追论恐怖时代被牺牲之斗士。予现拟参加组织一团体,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及清共时被牺牲者为职志。予盼中外知识阶级及友朋参加是项运动。”(28)
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就是在这前后积极投入了同盟的筹组工作。他们的参与对运动的发起帮助极大,但是也带来了对运动性质和任务的不同意见。虽然这方面的史料有限,我们仍可看出同盟筹备过程中的内部讨论并不轻松。结果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章程草案(现存伊罗生档案内)一度搁浅,未能及时通过。章程一直到同盟公开发起4个月后才得以定稿发表。同盟正式成立时,发表的是一份宣言。但就是这一简短的宣言敲定也属不易。宋庆龄出面提交的草案被蔡元培认为过激,作了大幅度修改,宋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但是,杨杏佛觉得宋的二稿还是不会得到蔡的赞同,遂决定拉林语堂一起把宋蔡两稿汇成一文。12月17日,杨杏佛致函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的蔡元培,报告道:“因即拟发营救许德珩等电文,同盟须早成立,不及将宣言稿寄京请正,惟全文大体尚妥,且为团体之宣言,与各个会员之立场未必完全相同,已由筹备委员会议决,即送各报发表。原稿一份,寄呈备考。又营救许等电,由铨起草,语气更和平,亦同时送登各报。”(29)杨杏佛之举虽有先斩后奏之嫌,宽厚的蔡元培还是默认了,并在返沪后不久就主持了同盟的首次记者招待会,而且代读了因病缺席的宋庆龄的书面发言。从最初的中国保卫政治犯委员会章程草案到最后公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虽然一些激烈的措辞被温和的用语所代替,不能达成一致的问题被暂时搁置,但就此能把蔡元培等一批知识精英吸引进运动,对中共地下党和宋庆龄等同盟核心成员来说,也是极大的成功。
同盟成立时,总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为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7人。上海分会最初的执行委员亦是上述7人加上陈彬稣与鲁迅。当然,真正的核心成员组成有所不同。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亮相之前,史沫特莱已秘密前往北平活动,帮助促成北平分会。在北平的数星期内,她多次造访了正在清华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年轻学者费正清。史沫特莱向其透露,在上海的同盟内部有一“秘密派别”,这个小团体的成员们往往会在同盟上海会议之前先统一口径,决定“行动计划”。看来这一小小的“秘密派别”就是同盟的真正核心,史沫特莱正是其中的一员。她向费正清透露,她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北平方面也建立这样一个小“秘密派别”。虽然在她的游说下,费正清夫妇在1933年1月北平分会成立时加入了同盟,但费正清对史沫特莱力邀他参加北平“秘密派别”的建议没有兴趣。(30)从后来的情况看,史沫特莱意在北平发展“秘密派别”的计划未能如愿。
同盟的组织发起,总的来说还是相当顺利的。虽然由于“各个会员之立场未必完全相同”,同盟在筹备工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披挂上阵,略显仓促,但对中共地下党和以宋庆龄为首的核心团体来说,应是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的。按《备忘录》所设计的蓝图,各项工作都在逐渐展开。《中国论坛》从1932年8月起被租界当局和国民党政府打压,到1933年2月才解决印刷问题,因此最初一个月的关于同盟的宣传报道,主要由《申报》和其他中文报刊承担。但自2月份《中国论坛》复刊起,它便全力为同盟造势。中共接受了伊罗生的建议,决定改《中国论坛》为中英文双语刊,并特派中共地下党员袁殊为中文版编辑。(31)此外,邀请国外著名人士参加由同盟组织的大会已在计划之中。调查监狱工作、挑选政治犯案例出击等活动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更重要的是,以蔡元培为首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欣然加入,使同盟大为增色。1933年1月胡适在沪上加盟,遂即返北平建立分会,并担任北平分会长。一时间,同盟南北相辅,遥相呼应,形势一片大好。
同盟的分裂、失败与伊罗生的遗憾
同盟的开局虽然不错,但其势头持续时间却不长,北平分会的成立即是其发展的顶峰。这不仅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还由于胡适与同盟核心团体的分歧的出现与迅速激化,这很快就导致了同盟的严重分裂和北平分会的垮台。这一分歧始于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揭露监狱状况的匿名信事件。彼此的分歧起初还只是纠缠于事实真相,如信件所述之监狱状况是否属实、匿名信本身是否捏造等,进而涉及到了组织程序问题——个别领导人是否擅用了同盟总会名义。在宋庆龄公开声明“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后,遂演变成了对同盟性质和对人权保护的不同理解等原则性问题的争论。(32)敏锐的胡适很快察觉到发起同盟的政治目的,不愿继续论战。他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随即拂袖而去。北平分会也随之偃旗息鼓。胡适的离去和随之而来的组织分裂对同盟是一个沉重打击。北平分会的消失使同盟顿成跛足,使同盟想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全国性组织的计划遭遇极大困难。不仅如此,这一风波在同盟的上海成员中也造成了动荡。
自胡适事件始,在同盟内部的争论中,伊罗生与宋庆龄始终保持一致,《中国论坛》还能说出一些宋庆龄不便发表的言论。对伊罗生来讲,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的出走是不足为怪的。伊罗生起草的《备忘录》即反复强调了自由派会最终“叛离”的必然性。按他的设想,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完成其作用后,将会被由中共所领导的革命群众所代替。应该说,同盟的其他核心成员也不会期待胡适等人与他们一直走下去。但问题是,风波来得实在太快。其时同盟的工作刚刚开始,立足未稳,就连史沫特莱也始料不及。匿名信是史沫特莱在北平逗留期间所得。她对这一材料非常重视,刚到手时,就想让费正清将其译成英文。但后者见信件行文潦草,觉得以自己的中文水平尚不够担此重任。(33)史把信带回上海交给临时执委会讨论发表以后,特致信胡适,要求北平分会配合行动。同时,她还把文件迅速发给国外左翼组织,请求声援。(34)胡适怒斥监狱来函为捏造的剧烈反应使史沫特莱措手不及,“甚为焦急……彻夜不眠”。她急忙再次致信胡适解释。(35)蔡元培、林语堂、杨杏佛也纷纷去信安抚胡适,设法平息风波。就在同盟临时执委会忙于处理危机时,《中国论坛》于1933年2月11日复刊,不顾蔡、林、杨等对胡适“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的承诺(36),全文刊登匿名信。综观《中国论坛》的报道,伊罗生与刊物完全无意支持同盟上海成员与胡适达成任何谅解。他不但重申宋庆龄早些时候提出的“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口号,而且要求同盟与“劳苦群众解放运动相呼应”,并对蔡元培没有支持宋庆龄号召的所有报业总罢工一天的建议进行了公开批评。(37)
伊罗生在同盟中的言行自然会引起温和派与保守派的不满。与史沫特莱不同,伊罗生跟同盟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蔡元培、林语堂、胡适等,早先并没有什么交往,史沫特莱却与他们私交不错。伊罗生十分年轻,同盟成立时还不到23岁,但他深受宋庆龄青睐,是同盟总会临时执委会和上海分会执委会的唯一外籍人士。伊罗生担任执委,在组织和情理方面都讲得通,因同盟成员“不拘国籍”,而《中国论坛》实为同盟机关报,伊罗生又是其编辑。但是,有《中国论坛》一贯同情、支持中共的立场在先,又有他极力将同盟向“革命群众运动”推进的主张在后,同盟内部有人对他心存戒备也不足为奇。林语堂所说的“现此临时组织极不妥当,非根本解决不可”,也并非毫无根据。(38)
之后几期的《中国论坛》显示,伊罗生与同盟内部某些人的分歧在日益增长。在同盟开会正式讨论胡适问题之前,《中国论坛》于3月1日发表文章,向同盟中央执委会施加压力。除坚决要求同盟驱逐胡适之外,还谴责“上海的其他人象他(胡适)一样在谈论诉求法律手段,‘公平’审判等等”。文章最后指出:“上海同盟必须带头引路。如果它做不到,其他人会夺过民权斗争的大旗向前挺进。”(39)在宋庆龄的主导下,同盟中央执委会于3月3日开会,通过了“开除”胡适的决议。蔡元培和林语堂尽管没有公开对外发表反对意见,但他们的失落感是不言而喻的。(40)相反,过后出版的《中国论坛》则欢呼“同盟经历了它第一次的内部斗争洗礼”。(41)这与同时以宋庆龄名义发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一文口径完全一致。(42)
胡适与同盟绝交后,同盟总会的对策之一是健全组织结构。在北平方面,同盟欲重建北平分会,但此项努力没有成功。在上海方面,除了将总会执委会和上海执委会分开外,把搁置多时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重新放入议事日程。在讨论过程中,宋庆龄、伊罗生等作了退让,最后公布的章程维持了宣言中“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一切酷刑及蹂躏民权之拘禁杀戮之废除而奋斗”的提法,而“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口号没有列入。章程草案措辞较为激烈,声称运动“目的是援助社会不公正的受害者,他们由于与中国现今统治者政见不同而遭迫害”,这一直接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说法也被删除。章程第三条第五款是有关会员除名问题,“凡会员犯下列各项之一者,全国执行委员会经多数之决议得将其除名”,伊罗生本想加上“为任何个人或团体充当间谍或内奸而加入同盟者”一项,但没有得到多数支持。(43)
自胡适事件以后,史沫特莱对同盟的热情有所消减。胡适带来的冲击波看来对她精神打击不小。虽然她也是支持开除胡适的一员,但在宋庆龄、伊罗生、鲁迅等严厉谴责胡适的时候,她并没有公开向胡适叫阵。(44)史沫特莱来华多年,交友广泛,是同盟中一个非常活跃的核心人物,密切参与了同盟的筹建和早期活动。她热情奔放,是女中豪杰,行事不拘小节,但又有着多疑、情绪化的一面,不易与人相处长久。譬如,从外人看来,她与杨杏佛相交多年,在同盟中配合默契。但她在运动刚开始不久就曾私下对费正清说:“我与他共事,但像我所说的,我会把他当作一只箭猪,与他保持一大段距离。”(45)这种性格使她在与宋庆龄的合作中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上,在这一阶段宋庆龄更器重的是伊罗生。据伊罗生后来说,宋庆龄在那段时期的声明书、报告书都是由他起草的。(46)伊罗生与史沫特莱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发生变化。史沫特莱长伊罗生18岁,在后者转向同情共产党的思想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她对伊罗生在《中国论坛》的工作帮助也很大。而且,伊罗生是通过史沫特莱才先后与宋庆龄和中共联系上的。应该说,当时伊罗生对史沫特莱是很尊重的。但是,从《中国论坛》开办以后,格拉斯对伊罗生的影响日渐增长。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前后,伊罗生已明显流露出对托派的同情。史沫特莱不会不知道伊罗生的变化,虽然他们仍是密切合作的同事和朋友,她却在1933年5月上旬给美国记者斯诺的一封信中说,伊罗生可能和日本间谍有联系。(47)这虽是无端猜疑,但她对伊罗生的暗中不满可见一斑。1933年5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仍在积极营救各类政治犯,史沫特莱却以身体欠佳和写书为由去了苏联。
史沫特莱的退出留给伊罗生更多的工作。他笔头快,办事利索,而且胆大,曾独访囚禁中的牛兰夫妇,大闹监狱。但是,在胡适风波以后,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分歧逐步浮出水面。伊罗生在主办《中国论坛》后不久,就碰到了中共中央与中国托派在某些问题上的争论,刊载的少数文章涉及一些敏感问题,遭到了来自中共读者的批评。这就是为什么伊罗生在《备忘录》中一开始就对中共承认《中国论坛》“的确有过错误,运用语言的准确性不够”等等。(48)年轻的伊罗生对中共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没有太多经验,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是头等大事,中共中央与中国托派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共同点。在同盟筹办过程中,陈独秀被捕,伊罗生也因此清楚地了解到中共对陈独秀和托派的态度,他遵照地下党的指示,没有在《中国论坛》上发表任何声援陈独秀的报道。但在格拉斯的影响下,他已对指责托派的言论极其反感。1933年4月,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有期徒刑13年,地下党指令伊罗生发表文章批判陈独秀,并按照中共中央当时的观点来解释其为何遭国民党监禁。这一次,伊罗生没有从命,《中国论坛》仅发表了一份同盟的简短声明,抗议国民党政府对陈独秀的判决毫无依据。(49)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共地下党深知《中国论坛》的宝贵价值,对伊罗生的违命并没有追究。倒是伊罗生继续对地下党表示了他对同盟发展的不同见解。他认为中共对同盟的领导过于保守。特别是在行动策略上,伊罗生还是沿着《备忘录》的思路,主张同盟迅速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方向扩展,使其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从各种迹象看,地下党在这方面也作了一定的努力。1933年3月8日,由同盟牵头,一个名为“国民御侮自救会”的联合组织在上海青年会召开筹备成立大会。来自劳工、学生、文化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共30多个团体参加了大会。宋庆龄发表了主题演说。杨杏佛在会上指出,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不可分离。自救会不但要求国民党政府积极抗战,保障民权,释放一切政治犯,还准备组织起一支自己的人民武装自卫力量。(50)对于自救会这样的大动作,南京当局没有掉以轻心,迅即采取措施。从4月中旬到5月初,国民党军警与公共租界默契配合,连续袭击了自救会所有的办公地点,逮捕了大批人员。最后,租界当局出面取缔了自救会。在国民党政府的严密注视下,地下党当然会考虑这种做法是否得不偿失。事实上,在国民党与租界全面镇压自救会之前,杨杏佛就放出风声,宋庆龄因工作太忙,从未允诺担任自救会主席一职,蔡元培也不是自救会成员等等。(51)不难看出这是同盟策略的一个调整。从此以后,同盟再也没有尝试其他激进的措施,而是依靠成员们的社会地位与声望来从事营救和宣传工作。中共也没有如伊罗生所期望的那样,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执掌运动的大旗。
在国民党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同盟能够做的事情是有限的。同盟尽力去公开揭露迫害政治犯的案件,谴责国民党的各类恐怖活动,并探访监狱,呼吁放人。但是,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同盟的合法性。只是由于宋庆龄和蔡元培的地位与声望,同盟的代表团有时才能会见南京政府要员。然而,同盟的要求不是被拖延就是遭拒绝。譬如,尽管宋庆龄多次公开呼吁,同盟也没能挽救中共工运领袖罗登贤的生命;同盟全力营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作家丁玲,但直到自身不解而散之时,尚不知其下落。同盟的运动进展艰难,不少问题又事与愿违,以至蔡元培、林语堂等人在1933年春夏就已萌生了退意。(52)
不过,对同盟最沉重的打击当属杨杏佛于1933年6月18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特务刺杀。在无法公开镇压的情况下,蒋介石最终授意戴笠实施暗杀计划。社会各界对杨杏佛的吊唁庄严隆重,同时也成为了同盟本身的告别仪式。虽然宋庆龄郑重声明:“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再接再厉,直到我们达到目的”(53),但大多数成员就此作罢。在轰轰烈烈地活动半年之后,同盟结束了它的使命。伊罗生在随后给国际工人救济会的信中十分遗憾地报告:“很不幸……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经过了6个月揭露监狱状况和竭力保护政治犯的工作后,没有能够抵挡住因其总干事杨铨在6月18日被谋杀所带来的震荡——它还来不及建立起群众基础,其主要成员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杨被惨害之后,他们都惊恐万状,销声匿迹了。”(54)伊罗生认为,如中共地下党能听取他的意见,及时把同盟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组织,结果不会如此。伊罗生与中国共产党最终分裂的原因虽复杂多样,但二者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展过程中的分歧与同盟的失败也是其中之一。
余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存在时间短暂,其公开活动仅持续了6个月,从其酝酿阶段开始算起,也不过1年。但是,它是中国现代史上令人瞩目的第一个有组织的民权运动。在民国史与中国革命史的书写中,一般都称同盟是一个由宋庆龄领导发起的进步民主政治团体。尽管近10余年来,史学界不断出现对同盟多方面、多层次的新探讨,但是关于同盟的发起及其与中共的关系,由于材料有限,仍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伊罗生参与同盟的经历为我们深入认识同盟提供了一个新的窗口,一些新材料展现了一个更为丰富和复杂的故事。根据现有材料,我们至少可以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有关发起中国民权保障运动的最初设想萌生于伊罗生1932年6月草拟的《备忘录》,是当时他与中共地下党、宋庆龄、史沫特莱以及其他人士在反对国民党白色恐怖斗争中紧密合作的产物。伊罗生不仅是同盟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它的发起人之一。不过,伊罗生能提出这一建议并不奇怪,在很大程度上,他有关保障民权的思想来自其早年在美国的经历。他是一个在自由主义思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为一个记者,“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更是他所认为的自然权利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的前提。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政治现实与哺育他成长的社会环境反差巨大,以至于他来到中国以后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没有丝毫自由的独裁统治社会,并使他逐步产生了对蒋介石政权的厌恶和愤怒。在史沫特莱和格拉斯的影响下,他迅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对历史与社会的解释。在与宋庆龄和中共接触后,他欣然参与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活动。在与地下党的并肩战斗中,他仍然受着他所熟悉的民主自由观的影响。因此,向中共提出以争取基本民主权利为出发点的建议,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考察伊罗生在同盟中的作用也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中共与同盟的密切关系。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城市工作方针正在演变。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飞行集会、街头抗议和工人罢工等激进活动开始,中共地下党在30年代逐渐重视对知识界、文化界的影响。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更注意对中间势力的工作。尤其是,30年代初的上海聚集了一批“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知识界人士,愈来愈多的知名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政策表示不满和反感。这些势力的聚集和这种思想土壤的存在为中共地下斗争提供了新的机会。正在考虑新策略、寻找新机会的中共地下党迅速觉察到了伊罗生所提建议的价值,采纳了其主要精神和内容,并对《备忘录》的原始构想作了修整,使运动的任务变得更具体、更集中。
重新认识伊罗生在创建同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丝毫没有削弱宋庆龄在同盟中的地位。没有宋庆龄也就没有同盟的出现。在宋庆龄的公开领导下,“保障民权”的口号迅速吸引了相当多的社会各界名流。同感于国民党政权对基本民权的践踏,一批知识精英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一组织,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运动。在同盟中,除了宋庆龄、伊罗生、史沫特莱与中共地下党有直接的默契外,杨杏佛卷入的深度还有待考察。虽然同盟的各项活动未必都由中共地下党指定,但同盟的行动路线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制定和贯彻的。这一点也能从伊罗生后来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看出来。伊罗生在与中共分裂后抱怨说:“对于这一混杂的同盟和它的工作,我以全力参加,并且我常向你们提出的那些基本的批评,我不曾公布过一次;而结果那年六月国民党暗杀杨铨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证实了我的那些批评是对的。”(55)他的基本批评就是同盟未能向工人群众迅速发展。年轻的伊罗生有才华,但尚显稚嫩,他对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和策略的理解毕竟还浅,对中共组织原则和党内斗争的情况知之不多,更缺少政治经验。他提出的《备忘录》对运动发起和发展的设想颇为理想化,类似于书生用兵。在同盟是否应该及是否能够向群众性组织发展的问题上,中共地下党有其现实的考虑和对形势的判断。同盟的组织成分十分复杂,而国民党的力量如此强大,中共不会像伊罗生那样,期待这一运动会演变成一场不可阻挡的革命群众运动。它主要还是着眼于运动在当时如何能有助于中共领导的城市工作的生存与发展。
伊罗生参与同盟活动的各种事实至少展示了:同盟是一个特殊的中共外围组织。虽然国民党的镇压很快结束了仅有半年生命的同盟,但从共产党与国民党的长远较量来看,这是国民党的失败。最终,中国社会中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间势力对国民党政府的期望丧失殆尽。领导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中共城市地下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不断积累经验的重要一步。团结利用中间势力,掌握争取民主权利斗争的主动权,是中共适应形势而形成的方针策略。伊罗生的参与有其偶然性,但是他和史沫特莱的加入使得这场民权保障运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反叛者或挑战者。他们带着对社会的疑问和思索来到了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度。伊罗生也是其中之一,在中国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了一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也观察到了人类社会的相似之处。此时的中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孱弱国家,又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广阔天地。中国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忘我牺牲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伊罗生。尽管他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其局限性,但是他对中国大众的同情和他所认同的反对独裁、争取民主的思想将其带进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权保障运动。伊罗生等国际人士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中国革命对他们的影响同样有意义,是值得我们继续探索的研究领域。
注释:
①Ira Wilson,"Harold Isaacs:Scratches on His Mind,1930-1934," unpublished undergraduate seminar paper (Harvard College,1976),p.2,in The Harold R.Isaacs Papers,MIT Archive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以下简略为HIP)。伊罗生档案现藏于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对外开放。但是,整套文件尚未整理,基本上保持着伊罗生夫人生前捐赠时的原貌,比较杂乱。档案馆虽有一个粗略的文件索引,但过于简单,并有不少错误。笔者最近一次访问是在2009年9月。据有关人员说,档案馆正在积极申请资金对这批档案进行彻底整理。在这种情况下,请原谅笔者不能对伊罗生私人文件中的材料标明编号,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会误导其他的研究人员。
②Robert I.Rotberg,"Harold R.Isaacs and The Mixing of Peoples," in Robert I.Rotberg (ed.),The Mixing of Peoples: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Ethnicity (Stanford,Conn.:Greylock,1978),p.2.
③有关伊罗生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及其在史沫特莱与格柆斯影响下的思想转变过程,见Harold R.Isaacs,Re-Encounters in China:Notes of a Journey in a Time Capsule (Armonk,NY:M.E.Sharpe,1985),pp.4-13; Peter Band,China Hands: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5),pp.81-95。
④笔者参阅了收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中国论坛》。该刊从1933年2月11日的第2卷第1期起改为中英文双语刊。但是中文版与英文版有时稍有不同,前者略为简约。笔者以下引用的是英文版。
⑤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US Department of State,Decimal File,1930-1939,RG 59,800.00B Isaacs,Harold R./1.Edwin 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16 December 1931.
⑥China Forum,20 January 1932,p.7.
⑦Tyler Dennett,"World War Dangers in Manchuria," Current History Vol.36 (September,1932),pp.758-759.
⑧《同志!》,此信没有日期,没有签名,HIP.
⑨在当时的环境下,伊罗生与中共地下组织的通讯往来是不可能署名的。格拉斯是伊罗生在主办《中国论坛》时期的密友与合作者,有关刊物的各项重要行动他都理应知道,包括发起民权运动、把刊物用作运动喉舌的重大建议。但基于格拉斯的托派立场,他不会参与提出这一建议。史沫特莱与伊罗生的关系在1932年春夏相当不错,合作密切,她是后来同盟的核心成员之一,《备忘录》有几处采用“我们”一词,因此她对建议的参与是有可能的。
⑩"Memo," 15 June 1932,HIP.引文中的下划线为原稿所有。
(11)Isaacs to Viola Robinson,23 December 1931,HIP.
(12)Isaacs to Viola Robinson,3 January 1932,HIP; China Forum,13 January 1932,p.1.
(13)"Memo," 15 June 1932,HIP.
(14)杨小佛:《我所知道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鲁迅研究室陈漱渝、陶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5)《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陈漱渝:《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150-151页。
(16)牛兰真名为雅科夫·马特维耶维奇·然德尼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长。牛兰夫妇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牟8月被释放。有关牛兰夫妇的被捕和营救工作,史学界论述颇丰,此文不再详述。可参阅Frederick S.Litten,"The Noulens Affair," The China Quarterly,No.138 (June,1994),pp.492-512。
(17)China Forum,23 July 1932,p.3.参见《伊罗生为〈中国论坛〉给中国共产党的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宣传部编:《先锋》1934年第16期,第31页。
(18)Isaacs to Baldwin,22 August 1932,HIP.伊罗生在信中告知鲍德温,《中国论坛》将成为这一新组织的主要舆论工具。鲍德温在回复伊罗生的信中表示,美国民权自由联盟是美国国内组织,中国民权组织与其结成隶属关系可能不妥,但支持其与国际拯救政治犯委员会建立关系。见Baldwin to Isaacs,14 September 1932,HIP。
(19)Draft Constitution,7 September 1932,HIP.
(20)Isaacs to Baldwin,21 September 1932,HIP.
(21)《蒋介石致翁文灏、胡适等(电)》(1932年10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9页。
(22)《林语堂手札》(1932年10月22日),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1),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40页。
(23)《申报》,1932年10月24日,《蔡元培年谱长编》下(1),第640-641页。
(24)China Forum,July 23,1932,p.3.虽然“保卫保罗与格特鲁德·鲁埃格上海委员会”是在地下党直接指导下开展工作,但伊罗生在与中国共产党分裂后进露,组织这一委员会是他的功劳。伊罗生在给中共中央的公开信中说:“你们当还记得,创立当地的营救委员会的是我,扩大报纸宣传运动因而唤起了显著的同情也是我。”中共地下党对此没有否认。参见伊罗生《伊罗生为〈中国论坛〉给中国共产党的信》,《先锋》1934年第16期,第31页。伊罗生以后在其他场合也谈到了他在创建“保卫保罗与格特鲁德·鲁埃格上海委员会”中的作用。见"Statement of Harold R.Isaacs,concerning allusions to Harold R.Isaacs and Viola Robinson (Mrs.Harold R.Isaacs) in Shanghai Conspiracy,by Maj.Gen.Charles Willoughby,E.P.Dutton & Co.,N.Y.," 22 January 1952,HIP。
(25)Ch.T.C.Csse,HIP.这份英文文件虽然没有具名,且为草拟稿,但考虑到救援牛兰工作由中共领导,“鲁埃格上海委员会”受地下党直接指挥,除了中共地下党以外,没有其他人可能作出这类原则性决定。
(26)Ch.T.C.Case,HIP.
(27)《申报》,1932年11月1日,陈漱渝、陶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24页。
(28)北平《民国日报》,1932年11月3日,陈漱渝、陶忻编:《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24页。
(29)《杨杏佛手札》,1932年12月17日,《蔡元培年谱长编》下(1),第651页。
(30)有关费正清所知道的史沫特莱在北平的秘密活动,见John King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Harper & Row,1982),pp.66-77。
(31)据袁殊(别名袁学易)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称,他只担任了两期《中国论坛》中文版的编辑。见National Archives II,College Park,MD: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GR 26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Records relating to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Shanghai,1926-48,Box 47,D5760,Surrender of Yuan Shueh Yi,26 June,Translation form Shun Bao and other Local newspapers,18 July 1935。
(32)《胡适致蔡元培、林语堂(稿)》(1933年2月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79页。
(33)John King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p.73.
(34)Agnes Smedley to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ee,3 February 1933,The Philip Jaffe Papers,Emory University Library,Box 14.
(35)《杨杏佛致胡适》(1933年2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88页。
(36)《林语堂致胡适》(1933年2月9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85页。
(37)China Forum,11 January 1933,pp.8-13.宋庆龄的建议是对顾祝同命令杀害《江声日报》主编刘煜生的抗议。
(38)《杨杏佛致胡适》(1933年2月1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88页。
(39)China Forum,1 March 1933,p.14.
(40)同盟成员周建人在1933年3月2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胡博士事……当初蔡公、林语翁等力为辩护,但有些执行委员坚持,终于开除民权会了。盖执行委员中有几位美人比较的略激烈也。”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12,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执委会中的外籍委员只有伊罗生一人,但鉴于史沫特莱在同盟中所起的作用,她经常出席执委会会议是可能的。
(41)China Forum,27 March 1933,p.13.
(42)宋庆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42页。收编者把此文的写作日期误定为1932年12月。实际上此文应该是在胡适事件发生后拟成并在其被同盟正式开除后发表的。
(43)Draft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a League for Civil Rights,HIP.
(44)史沫特莱以后在讲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经历时对胡适的评价还是相当友好的。见Agues Smedley,Battle Hymn of China (Originally published,1944),Beijing,China: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pp.96-97。西方的一些史沫特莱的传记作者指出,由于各方面原因,这一时期的史沫特莱情绪颓丧。有的作者甚至拿1933年2月部分同盟成员与英国作家萧伯纳在宋庆龄住宅的合影为证,照片上的史沫特莱似乎确有不安与消沉之感。参见Janice R.MacKinnon and Stephen R.MacKinnon,Agnes Smedley: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p.157-158。
(45)John King Fairbank,Chinabound:A Fifty-Year Memoir,p.75.
(46)Isaacs,"China Notes," HIP.
(47)Agues Smedley to Edgar Snow,10 May 1933,cited in Ruth Price,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235.
(48)"Memo," 15 June 1932,HIP.
(49)China Forum,4 May 1933,p.9.
(50)China Forum,27 March 1933,p.9.
(51)《申报》,1933年4月15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43页。
(52)参阅《蔡元培致胡适》(1933年3月17日),《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1卷,台湾远流出版有限公司,无页码。在此函中,蔡元培说:“弟与语堂亦已觉悟此团体之不足有为;但骤告脱离,亦成笑柄;当逐渐摆脱耳。”又,在杨杏佛遇害后,蔡告诉记者,他“对民权会之副会长事,早已辞职,故对该会之前途如何,均不得而知云。”《申报》,1933年6月21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第123页。
(53)宋庆龄:《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第73页。收编者把此文的写作日期误定为1934年。此声明应在杨铨被害不久后发表。
(54)Isaacs to Louis Colma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efence,22 September 1933,The Philip Jaffe Papers,Emory University Library,Box 14.
(55)《伊罗生为〈中国论坛〉给中国共产党的信》,《先锋》1934年第16期,第32页。
标签:中共地下党论文; 1932年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论文; 上海活动论文; 美国工作论文; 同盟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宋庆龄论文; 陈独秀论文; 历史论文; 蔡元培论文; 杨杏佛论文; 史沫特莱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共产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