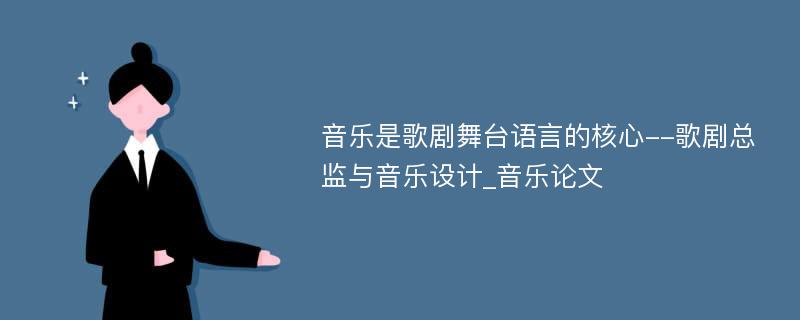
音乐是戏曲舞台语言的核心——戏曲导演与音乐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音乐论文,导演论文,舞台论文,核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曲音乐包括唱腔和配乐。戏曲音乐形象是构成戏曲演出形象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功能,一是抒情性——直接或间接地表述人物的情态和内在的气质、情感;二是节奏性——统领舞台所有艺术因素,包括:表演、灯光、布景等变化的节奏;三是戏剧性——营造舞台气氛,暗示、烘托和推动戏剧矛盾。
戏曲音乐设计与演员的表演,是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关系。首先是从剧情、人物性格、戏剧矛盾出发,选择板式,设计唱腔和配乐;其次当唱腔和配乐基本成形,它就会反作用于表演的结构和节奏,而需要演员适应它。排练的过程也是音乐与演员的表演相互磨合和相互修正的过程。
张庚先生指出,音乐对于戏曲导演工作来说,是十分的重要的:“戏曲的第二度创作,是从全剧的音乐化开始的。戏曲表演是以音乐为核心来组织自己的舞台语言的。矛盾的展开、情感的刻划、高潮的安排、舞台气氛的变化与音乐的设制有关。”〔1〕所以,戏曲导演的构思,要伴随着设计音乐形象来进行,要充分发挥音乐戏剧性功能。导演对一出戏的音乐总体风格要有一个原则性要求,即要有一基调:是悲剧色彩,还是喜剧色彩;是大江东去,还是小桥流水等。对于音乐的布局要有一个系统而谐调的设计,包括每场戏、每个段落的音乐情调的错落、节奏的张驰变化、旋律的情绪反差等,导演心中要有个蓝图。这个蓝图美不美,能否为观众欣赏,影响到自己导演的这出戏的成败得失。
一、唱腔先行
唱是戏曲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塑造人物的音乐形象,是戏曲音乐的重要任务。由于戏曲表演“载歌载舞”。唱与舞在戏曲表演中相辅相成,如果没有唱腔,就无法投入排练。演员在排戏前,都必须对唱腔有个大致的掌握。唱腔先行,还能刺激和帮助导演的情感体验,为导演和演员提供更多的形象联想和提示,启发细节构思,组织舞台行动和调度。因此,戏曲导演在构思全剧的音乐蓝图时,要把设计唱腔放在首要的位置,并且,始终把它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戏曲的唱腔设计和安排,一般采用的步骤如下:
1、角色行当。
戏曲各个行当之间的声乐色彩的区别很大,所以,导演选择演员要注意行当,一出戏里主要角色的行当尽量避免类同,使声乐色彩和表演色彩产生明显的反差,达到听觉形象的丰富多彩。
比如,评剧《闯法场》(石家庄市评剧团演出)中,县官和知府原先都用老生行当扮演,舞台表演一道汤,性格对比不够鲜明。我在导演时,将县官改为老丑行当扮演,从唱腔到表演有了一定的色彩差异,使戏活跃,有了情趣;同时,知府与知县的个性在对比中都得到突出。
2、选择板式。
戏曲的唱腔,不管表现历史题材或现代题材,也不管采用何种舞台思维形式,基本上要在本剧种的唱腔程式的基础上创新。相对来说,唱腔的各种板式对于表达角色情绪有一定的指向性。比如京剧的“二黄”趋于悲壮、凄婉、深沉;“西皮”则趋于激越、欢悦、明朗。板式还分快板、慢板等,它们对于角色的外部动作节奏和心理情感节奏也有对应的效果。“戏曲的板眼往往为一场戏奠定了演出的舞台节奏。”〔2 〕所以,板式选择妥贴与否,关系到角色的感情表述和舞台节奏。选用什么板式和锣鼓点子,决不单单是音乐工作者的事,首先是导演的事,导演要掌握有关剧种的唱腔板式程式的大致规律。
比如,有一出根据古典名剧改编的古代戏,其中母子相会的一场,应该是十分细腻、十分抒情的戏,但由于唱腔选用了节奏局促的板式,与规定情境不符,因此,人物之间由不相识到相认的感情变化无法得到舒展。也由于唱腔板式选择的失误,使这场戏的艺术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
合唱也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艺术手段,但是,戏曲有合唱基础的声腔和剧种比较少,所以,较少应用合唱。赣剧“高腔”的合唱很有基础,还可以分部。但是,不少剧种很少运用合唱,因为戏曲培养演员,重视个人技巧,而缺乏集体性训练,包括集体舞蹈和合唱。虽然如此,该用合唱的地方还是应该用,可以在排戏中提前训练。
3、唱腔与性格。
戏曲传统戏的唱腔是程式化的一曲多用。从唱腔程式的历史发展来看,它是在流变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既具有稳定性,又有可变性。对于某个具体的唱腔来说,虽是“旧曲延用”,却不能把它看作是僵化的模式套用。戏曲作曲需要根据剧本内容、人物性格并遵循传统的音乐程式,在旋律上、节奏上予以变化,必要时可作“破格”处理。
重点唱段是发挥感情的高潮唱段,用来渲染、烘托戏的高潮,通过音乐表述人物外部戏剧矛盾和内心冲突,塑造人物性格。所以重点唱词和唱腔的旋律都要格外突出。高潮的唱段要有相对的完整性,需要一定的篇幅,音域可以宽广些,并充分发挥高音区的腔,使唱段具有一定的气势,有一定的厚度。如果一出戏的重点唱腔不精彩,不但影响这出戏的音乐形象,并且影响这出戏的艺术效果。但是,有的戏的唱段几乎每段都是“重点”,过多的耍高腔、长腔,结果使观众审美疲劳,毫无美感,听得很累。所以,导演与作曲对于重点唱段与一般唱段要选择安排得当。
4、演员的参与。
戏曲音乐从作曲到演唱的过程,并没有严格的分工,不少戏曲演唱家同时也是作曲家。演员对角色会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各个演员的嗓音条件、发音方法、共鸣部位、用气习惯和艺术趣味都有差异。只有充分注意了演员的艺术条件,共同创编出来的唱腔,唱起来才能扬长避短,有可能出情,把人物的情感变化表达得淋漓尽致。演员的参与,即使产生不同看法,可以在创腔过程中尽早谐调,达到共识,在以后的排练中减少返工。
导演必须坚持为戏的内容而安腔布唱,不能为了卖弄演员的技巧而安腔布唱。有的主要演员从个人表现出发,脱离人物来考虑唱腔,为了表现自己的嗓子,认为唱词越多越好,唱腔的“拐弯”越多越好,为了叫好,要唱音调高的腔和七折八弯的长腔。阿甲先生批评这是“鸡毛炒韭菜”,影响人物形象,这些情况导演就要把关。
二、配乐设计
戏曲乐队包括文场和武场。文场指管弦乐、弹拨乐,武场指锣鼓打击乐。传统的锣鼓、曲牌等程式,是戏曲音乐再创造的丰厚的资料库。
戏曲的配乐贯穿整个演出之中,是无时无处不在的艺术力量。西方歌剧的配乐除了作为唱的伴奏之外,只用来表现剧情的情绪氛围,而戏曲音乐却始终伴随着演员的表演:唱腔中的伴奏、前奏和煞尾都须设计配乐;念白、舞蹈(做、打)的节奏都要统一在配乐的规范之中;情感表演甚至一个眼神都离不开配乐;开幕曲,场与场的间奏,人物上、下场,场境气氛等,都需要配乐;配乐还担负模拟风、水、雷、雨、动物、绷线等仿声功能。戏曲舞台上的配乐,应该说是演员表演艺术的一种扩展,它对演出起到美化、强化、深化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导演要看到鼓师也是音乐设计的主要力量之一。有人作过估计,在全剧的演出时间中,音乐演奏的时间比重占80%左右,鼓师是全剧的总节奏感的把握者。如何合理运用和创造锣鼓点子,鼓师最有发言权。所以,导演要充分发挥鼓师的创造性。
导演与作曲、鼓师把事先能确定的一部分锣鼓和曲牌的配乐,在排戏时试用,以备演员按照音乐篇幅和节奏的大致轮廓组织身段。其它的配乐需要在排练过程中根据排练现场情绪气氛、表演的身段进行构思。导演应当与作曲、鼓师在排练场上共同投入创作。有的音乐主创人员不注意看排戏,等戏排得差不多了才构思配乐,这就需要导演事先提醒,否则,演奏的音乐平平淡淡,会把戏演成一道汤。
1、主调的设置。
主调是戏曲借鉴西方歌剧“主调贯穿法”的一种创作方法。也就是音乐主创人员根据剧本的风格、人物性格所创作的一段主旋律,并把它演化变奏为几种情绪曲,渗透在唱段和音乐中,成为主人公的音乐形象,贯穿于全剧的配乐场面之中。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可行的创作方法,成功之例不少。但它的创作必须建立在作曲家对剧本的主题和主人公的性格有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因为音乐作为情感反映的手段,它不是具象,对现实的概括具有不确定性,它必须和人物性格扭在一起,才能发挥其戏剧性;同时作曲者还要熟悉生活,熟悉规定情境的地域音乐和风土人情,并要有丰厚的作曲基本功。如果闭门造车,随意编作,那只能是玩弄旋律游戏,难以达到动人的目的。越剧、沪剧等剧种运用“主调法”比较早,“样板戏”对于“主调法”的运用是比较突出的。近几年来也有不少成功之例,京剧《夏王悲歌》的作曲朱绍玉通过深入西北生活和采风,运用“主调法”,在主人公的唱段、情绪音乐和伴唱中,都反复出现主调的变奏旋律,使戏蕴含着浓郁的西北的地域色彩,气势古朴、粗犷,韵味无穷,加深了这出戏的历史的深沉感和人生的感悟。
2、锣鼓打击乐。
锣鼓打击乐是我国戏曲音乐的一大特色。强烈的音量的传统,与戏曲剧场的演变密切有关。戏曲锣鼓来自民间,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气派,从目前仍活跃在西北地区的民间锣鼓表演(武鼓、盘鼓、战鼓、高鼓、低鼓、腰鼓、花鼓等)中,还可以窥探到戏曲锣鼓形成的踪迹。
戏曲整台戏的节奏安排由鼓师统一掌握,用鼓点把全剧的抑扬顿挫、高下徐疾的舞台节奏强调出来,把演员的唱腔、念白和动作的美感强化出来。戏曲锣鼓还具有描写环境、营造环境气氛功能。正如张庚先生指出:“整个的戏有鲜明的外形节奏,而鲜明的外形节奏必须用锣鼓点强调起来。”〔3〕
锣鼓不但能为人物的外部节奏服务,还能为人物的内心节奏服务。锣鼓的喻情也是来自生活,比如冷锤表现吃惊;乱锤表现慌张;急急风表现紧张。所谓“一打节奏,二打感情”,是要打出人物心理变化和各种情绪转折,用锣鼓帮助传情,在节奏中表现人物性格。有人把单皮鼓比作人的神经中枢,用它来为人物的每一个心灵颤动“点睛”,细腻地表达人物心理活动。比如,我演出的京剧《李慧娘》(苏州市京剧团演出)中,裴生要以死相酬李慧娘时的念白:“待我碰死了吧”,传统的鼓点子“答、答……”是在裴念完整句之后,可是,当我听到裴生说“碰死”时,内心已有强烈的反映,所以,我们就将鼓点子改为在裴生“碰死”一说出口时就打将起来。这样帮助了我的表演,并使观众更鲜明地感受到人物此时心灵深处的情感变化。所以,活用传统的打击乐很重要,但必须从人物出发,从剧情出发。
锣鼓也是一个很有威力的艺术手段,现在有的戏像话剧加唱,其中原因之一是没有充分发挥锣鼓的作用。但是,也要避免“当敲不敲,不当敲而敲,与宜重而轻,宜轻反重”〔4〕的现象, 即锣鼓也要出“情”。有的戏锣鼓太多,太水,所谓“拙戏多锣鼓”。李渔说“锣鼓忌杂”,即要经济,滥用会使观众厌烦。由于锣鼓起源于露天表演,农村也需要过量的热闹气氛,所以不嫌音量大。锣鼓到了剧场,加上扩音器,锣鼓的音量常常超过耳朵的承受度,连续性的敲击更有噪音之感,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这些都需要导演加以注意。
3、场间的间奏。
传统戏里,场与场之间常用“冲头”之类的锣鼓点子来作为间奏,显得比较“水”,比较呆板,有时场间用“急急风”这类锣鼓更是显得过分喧闹。场与场之间的间奏,不应单纯把它作为更换布景填充时间,而要使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并要求间奏音乐作多样化处理。不少新编的古代戏或现代戏已经有很多的创造,比如《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打虎上山”这场戏前的间奏,以圆号为主,节奏明快,旋律昂扬,又如杨子荣唱倒板“穿林海”上场的前奏,形象地抒发了杨子荣不顾个人安危,闯入匪巢的雄心壮志。我演出的京剧《李慧娘》的“杀姬”这场戏结束时,裴生为贾似道以“请在红梅阁待茶”被囚,裴生于疑虑中在简短的“回头”的锣鼓中下场,同时灭灯静场,漆黑的舞台,以三通鼓为间奏,使人们一下感受到下一场阴曹地府空灵而威壮的气氛;“救裴”与“追杀”两场戏的间奏,传统的办法是用“急急风”的锣鼓,虽然紧迫热烈,但缺乏深夜中李慧娘带领裴生潜逃的典型环境的意境。作曲沈利群创编了琵琶与笙的合奏曲,作为这两场戏的间奏,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静谧的夜晚蕴藏着一场生死搏斗的音乐形象。
4、无伴奏处理。
配乐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根据剧情和对比的需要。有时无伴奏表演会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传统戏中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乌龙院》中,宋江着急回到乌龙院,上楼后各处找不到招文袋,随后有一段细细地回忆怎会丢失招文袋的过程。这段戏没有台词,全靠动作表情,时间并不短,没有一点配乐,却使舞台气氛格外紧张,观众格外集中精神观看表演。当宋江想起招文袋是夹在胳膊下时,击一锣,直到想起是自己在拉开门时掉在地上时,突起“乱锤”的锣鼓点,充分强调了宋江紧张、纷乱的心情。武戏也有这样的例子,《三岔口》中摸黑开打时,有时也用静场,为的是制造夜间的谧静气氛。这种无伴奏处理,也是调节欣赏兴趣的手段之一。应当说,无伴奏处理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伴奏。
5、突出“伴”字。
配乐与唱要分清主次,是“伴”和“唱”的关系,配乐要注意音量,不能喧宾夺主。李渔指出:“吹合宜低”、“须以肉为主,而丝、竹副之……有主行客随之妙。”〔5〕伴奏要善于变化音量, 尤其在演员开口唱(包括念白)时,伴奏音乐要随时把音量适当压低,突出演员表演,在京剧传统戏中常常出现胡琴游离于剧情的长长“花过门”,演员尴尬地等着过门奏完才好起唱,这种“独立发挥”在新戏中应当尽量避免。有的气氛音乐,动不动就用西洋乐器,喧闹非常,跳出了规定情境,也失去了美感。
三、发扬剧种特色和地域特色
据余从《戏曲声腔剧种研究》中统计,目前,我国的地方戏,包括京剧和昆曲 在内,总计有370个之多。顾名思义, 这么众多的地方戏曲,是指我国境内,包括汉民族和其它民族所属某一地区的某一种戏曲剧种。它们都具备以歌舞演故事的基本特征,它们之间区别的标志就是声腔音乐。
由于各剧种发生、发展的历史时代、地理环境、文化传统、民情习俗和艺术源渊的不同,各个剧种拥有自己的方言、语音、音乐习尚和唱腔曲调、乐器的独特应用。各剧种的艺术风格就是上述地域文化的历史积淀,都拥有本地域最广大的观众群,所以,剧种的风格不应淡化。戏曲的各种艺术因素,比如剧本、表演、舞台装置等,都可以相互移植、借鉴,唯有唱腔音乐不能,因为它渗透着一个地域、一个时期的审美意识。相反,必须保持、发扬本剧种唱腔音乐鲜明独特的风格。当然,为了艺术创作和满足观众的欣赏的需要,各个剧种应该相互借鉴、吸收兄弟剧种唱腔和板式,但吸收其它剧种腔调,必须在自己剧种的方言基础上消化,如果生吞活剥,便会支离破碎。川剧吸收很多其它曲调,但是用自己的语言和音乐锣鼓消化得很好。移植其它剧种的戏时,同样要注意剧种唱的特色。比如有的剧种适合唱得多,在移植其它剧种的剧目时,就应该扩展其唱词。“样板戏”那个年代,其它剧种移植时,一字不能改,扼杀了创造性,也影响了艺术性,是十分荒谬的。现在有些剧种过分向别的剧种看齐,乍听收音机里的锣鼓音乐,都像是京剧,简直听不出是什么剧种,直到演员开口唱,才分辨出原来是某一个地方戏,可见有的剧种已相互同化得相差无几了。如果各剧种的音乐唱腔都“统一”了,那么,全国也就只剩一个剧种了,这不是我们振兴戏曲的初衷。
四、创新的思考
现在,戏曲音乐要克服的矛盾,还是音乐传统程式的延用与创新的矛盾。旧的曲调程式包括结构原则、节拍、节奏、基本旋律结构,用来表现新的生活时,常常显得手段和技巧比较单薄和凝滞,没有新意。时代需要戏曲音乐创新,但还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梅兰芳先生是京剧革新家,他的“移步不换形”论,其精神至今值得我们参考。“移”者,要创新;“形”者,指的是传统的美学规律,这是非常精辟也是非常实在地说明了创新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现在有些新剧目,音乐的创作个性越来越趋强化,而传统整段曲调的“延用”则愈趋淡化。须知旧的曲调群众比较熟悉和喜爱,创新要立足于群众能否接受,要把握“既熟悉又新鲜”这个尺度,不要为创新而创新。对于音乐程式来说,前辈有一个经验值得考虑:“能不改的就不改,非改不可的才改”。这其实并不是保守,而是慎重。不少流派创始人的经验也值得注意:同一个传统的唱腔程式,演唱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嗓音条件,对传统曲调的节奏、旋律、板式进行调整,在唱的方法和技巧,包括气口、润腔等稍作更改,便达到了唱腔出新的艺术效果。戏曲音乐唱腔这一创作规律,使作曲者、演唱者有尽情发挥的可能。这种发挥,既有助于情感表现的深化,又能使艺术风格色彩多样化。有关戏曲音乐唱腔的创新,不外以下几个问题:
1、时代感。
戏曲音乐唱腔的时代感或时代气息,主要看是否把握了所表现的时代的脉博,是否体现了时代的审美精神。李渔主张艺术要随时代进步:“变古调为新调……传奇妙在入情,即使作者至今未死,亦当与世迁移,自啭其舌,必不为胶柱鼓瑟之谈,以拂听者之耳。”〔6 〕对于戏曲音乐来说,从乐曲到配器,为了有助于人物的塑造,必须要符合戏中所表现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气氛,并渗入时代的审美因素,诸如全剧音乐是否张驰有致、节奏是否流畅、旋律是否为观众熟悉又有新鲜感。不少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的实践中,已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比如,《曹操与杨修》的唱腔音乐,其板式的选择比较妥贴,节奏安排与剧情紧密相关,显得很流畅,没有一道汤的感觉,唱腔旋律注重在抒情中刻划人物性格,西洋乐器的运用和配器的音量也恰如其分,主要角色的唱腔既继承流派又颇具新颖感,赢得了不少新老观众的称道。
2、乐器的出新。
戏曲音乐的乐器以民族乐器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欣赏趣味的变化,戏曲器乐也应当逐步充实,使之更富有表现力,并把唱腔陪衬得更优美。比如京剧现代戏中,曾用了一些西洋乐器,以配合传统的“四大件”,就使其音乐唱腔显得更加丰富多采。关肃霜主演的现代京剧《黛诺》(云南省京剧院演出)的乐器中,并增加了芦笙,增浓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汉剧《弹吉它的姑娘》(湖北省汉剧院演出),整个戏的乐队用的是电子琴及爵士鼓,以这种轻音乐的节奏为演员伴奏,与时代、人物性格,都比较贴切,比较得当。
乐器不要生搬,“拿来”要深思熟虑。有些剧团不管剧目的体裁风格,不管规定情境和人物性格,一律都配备大乐队,用西洋乐器来增强气氛,但与剧目所要表现的内容大相径庭,这是不可取的。其实并非配器越多越好,而是要从内容出发,从表演风格出发。用西洋乐器更要慎重,某出戏要不要用西洋乐器?用哪几种?用在什么地方?都要因戏而宜。特别要注意,要在突出本剧种风格——民间乐器的前提下,发挥西洋乐器的作用。
3、“迪斯科”、电子琴的借鉴。
戏曲音乐的节奏,是在有规律的基础上呈“弹性”状态。最初的戏曲,是由诗歌转化而来,“曲”成为塑造人物的基础。北方从诸宫调,南方从民间小曲;剧本由诗体化(或词体化)的唱词和赋体化的念白组成,搬上舞台时,诗(或词)被配上音乐旋律成为歌唱形式。所以,这种歌唱形式(曲)含有诗的“弹性”的韵律节奏特性。不仅是唱,戏曲舞台上所有的表演节奏,无时不体现这样的“弹性”。所以,把“迪斯科”和电子琴的机械性节奏用在戏中要慎重,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合适的。即使观众感到有兴趣,也不能因此而废“戏”,因为他们喜欢的是“迪斯科”的节奏和电子琴的音乐,如果迁就了他们的“戏外”欣赏要求,那整个戏要表达的思想,人物的性格、感情都将被冲掉。当然,也有处理得巧妙的,比如河北梆子《钟馗》中,有一场众鬼在地府的舞蹈,借鉴了“迪斯科”的节奏和舞姿,渲染了“群魔乱舞”的气氛,这段舞蹈时间又不长,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效果。
注释:
〔1〕 张庚《戏曲美学三题》
〔2〕 转引自高宇《古典戏曲导演学论集》第149页
〔3〕 张庚《戏曲艺术论》第102页
〔4〕 李渔《闲情偶记演习部·锣鼓忌杂》
〔5〕 李渔《闲情偶记演习部·授曲》
〔6〕 李渔《闲情偶记·演习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