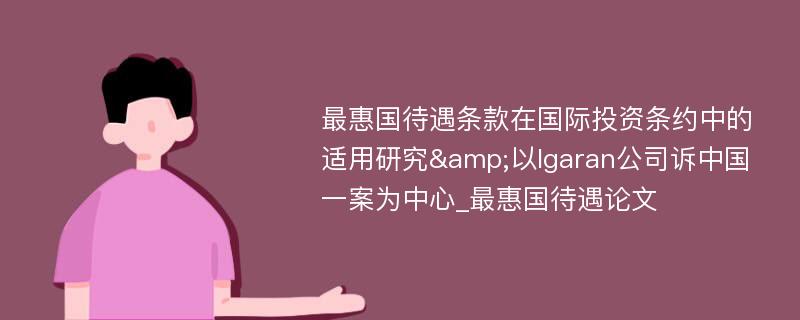
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研究——以“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为中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最惠国待遇论文,条约论文,中国论文,国际投资论文,条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①
2011年5月24日,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秘书处对马来西亚伊佳兰公司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仲裁请求予以登记(即“伊佳兰公司诉中国案”,以下简称“伊佳兰案”)。这是我国政府首次在ICSID成为国际投资争端案件的被告。至于我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包括是否提出管辖权异议,在实体审理阶段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以及万一败诉如何应对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等一系列棘手问题,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面对此案,我国政府在国际投资争端案件中的应诉能力,以及我国投资环境的可信度都将接受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而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是否扩及争议解决事项将成为我国应对“伊佳兰案”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
1990年3月3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国—马来西亚投资协定》)第7条将提交仲裁的争议范围限定于有关征收补偿数额争议和双方同意的其他争议。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成为1965年《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以下简称《华盛顿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在《中国—马来西亚投资协定》中并未订入“中心管辖条款”。不过,中马双方当时已达成谅解,约定一旦中国成为《华盛顿公约》的成员国,双方应及时就扩大提交根据《华盛顿公约》设立的ICSID调解或仲裁的投资争议领域的可能性进行协商。关于协商后双方同意扩大的领域,中国给予马来西亚的待遇,在同样情况下不应低于给予其他国家的待遇且双方同意的新规定应代替《中国—马来西亚投资协定》第7条。②尽管如此,1993年2月6日《华盛顿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后,中马双方却从未就上述谅解展开任何协商。而中国近年来签订的众多双边投资条约(BIT)中大部分订立了“中心管辖条款”,并扩大了允许提交ICSID解决的争议事项范围,不再限于“征收补偿数额争议”。因此,马来西亚投资者极有可能援引《中国—马来西亚投资协定》第3条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中国接受ICSID管辖。而此前,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是否扩及争议解决事项已引起了法律界的广泛讨论。截至2011年7月,中国已是超过140个BIT中的缔约一方,“伊佳兰案”的走向是否预示着拉开了“外国投资者—中国”仲裁的序幕呢?毫无疑问,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扩张将成为开启“潘多拉魔盒”的钥匙。
二、难以捉摸的仲裁庭:最惠国待遇或扩及争议解决事项
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基本要求是指缔约一方投资者在另一方领土内投资的待遇,不应低于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所受到的待遇。最惠国待遇不仅要求缔约国遵守基础条约即缔约国之间签订的包含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下的国际义务,而且把这些缔约国与任何第三国签订的其他国际条约即第三方条约作为最惠国待遇的参照系。这使得缔约东道国承担的外国投资保护义务呈现开放性,甚至是不可预见状态,即无论是目前东道国与任何第三国签订的有效投资条约,还是未来东道国与任何第三国签订的投资条约下所承诺的投资优惠、鼓励及保护措施均自动给予缔约对方投资者的投资。最惠国待遇条款使基础条约具有延展性,缔约东道国被认为事先同意将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无条件地给予来自缔约对方的投资者。国际投资条约中一般都采纳无条件最惠国待遇,③同时规定若干例外。然而,各个国际投资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措辞千差万别,国际投资争端仲裁中有关该条款适用范围所引起的争议逐渐白热化,④最早引起各界对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是否扩及程序事项的热烈讨论,当属2000年“马菲基尼诉西班牙案”⑤(以下简称“马菲基尼案”)。此后,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庭在不同案件中就上述问题继续进行探索,以求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正确适用和解释形成令人信服的观点。目前,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以免除当地救济等候期,二是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以扩大仲裁事项范围。
1.免除当地救济等候期。在“马菲基尼案”中,来自阿根廷的投资者马菲基尼根据《西班牙—阿根廷BIT》第4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要求享有《西班牙—智利BIT》中更优惠的待遇。《西班牙—阿根廷BIT》第10条规定,投资者必须首先寻求东道国当地救济,只有在经过18个月仍然未获得判决才能诉诸ICSID。而《西班牙—智利BIT》第10条则规定,争议发生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只需进行6个月的磋商就可寻求ICSID解决。马菲基尼援引《西班牙—阿根廷BIT》第4条要求西班牙给予其《西班牙—智利BIT》第10条所赋予的待遇。而西班牙认为最惠国待遇仅适用于投资者享有的实体权利,并不包括程序事项或管辖权问题。2000年“马菲基尼案”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驳回了西班牙的这一抗辩,明确认可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可以涵盖程序事项。在“西门子公司诉阿根廷案”⑥(以下简称“西门子案”)中,德国投资者西门子公司同样援引《德国—阿根廷BIT》第3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要求获得《阿根廷—智利BIT》第10条下更优惠的待遇。“西门子案”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认定,最惠国待遇条款允许投资者从其他条约中选择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不过,在2008年“温斯特公司诉阿根廷案”⑦(以下简称“温斯特案”)中,仲裁庭却指出18个月当地救济的期限构成缔约国同意提交国际仲裁的重要前提,并驳回了德国投资者温斯特公司援引《德国—阿根廷BIT》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适用《阿根廷—美国BIT》中的争议解决条款的主张。由此可见,虽然“温斯特案”与“西门子案”涉及同一条约条款,但仲裁庭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
在2010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诉乌拉圭案”⑧(以下简称“菲利普案”)中,原本基础条约《瑞士—乌拉圭BIT》第10条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争议后,应由双方协商解决,如果在6个月内未能解决,争议应提交东道国国内法院解决,为期至少18个月,但瑞士投资者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援引该基础条约下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获得乌拉圭缔结的第三方条约中的相关待遇,即投资者可以直接将争议提交ICSID仲裁。显然,菲利普·莫里斯公司也希望采取马菲基尼所采用的策略,⑨绕开当地救济等候期,以获取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方式。而仲裁员的裁决如何,我们将拭目以待。
2.扩大仲裁事项范围。在2005年“帕拉马公司诉保加利亚案”⑩(以下简称“帕拉马案”)中,仲裁庭拒绝接受来自塞浦路斯的投资者帕拉马公司援用基础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适用第三方条约中的投资争议仲裁条款。仲裁庭认为,仲裁条款必须足够清晰、明确,而最惠国待遇条款一般都是概括式规定,几乎不可能满足仲裁庭所要求的清晰程度,投资者援引基础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以要求适用第三方条约中的投资争议仲裁条款的主张将难以获得支持。在2005年“罗斯投资公司英国有限公司诉俄罗斯案”(11)(以下简称“罗斯案”)中,仲裁庭支持了英国投资者根据基础条约1989年《英国—苏联BIT》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适用《丹麦—俄罗斯BIT》下对其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而《英国—苏联BIT》第8条仅允许投资者将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提交“投资者—国家”仲裁。最终,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扩大至争议解决事项使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仲裁庭确立了对该案的管辖权。“罗斯案”仲裁庭的裁决再次肯定了英国投资者援用最惠国待遇条款获得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方式,同时也考虑了《丹麦—俄罗斯BIT》第11条有关投资仲裁税收例外的规定。仲裁庭指出,责任认定的关键是东道国税收措施以及后续拍卖行为的共同作用对英国投资者的财产构成了征收,而并非单纯考虑税收是否构成征收,因此仲裁庭是否超出第三方条约规定的仲裁事项范围,与上述责任认定无关。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是否扩及争议解决事项这一问题态度暧昧,只是宣称对所有受诉措施综合考量,避免了第三方条约中有关投资仲裁税收例外对其管辖权的影响。(12)这与2009年“伦塔公司诉俄罗斯案”(13)(以下简称“伦塔案”)仲裁庭在管辖权裁决中的观点如出一辙——仅因为有关税收例外的规定而令东道国摆脱投资保护的义务是无比荒谬的。“罗斯案”和“伦塔案”再次引起国际社会对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的争论。在这两个案件中,投资者援引基础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以获得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方式,不但在事实上扩大了可仲裁事项的范围,而且还成功打破了第三方条约中有关投资仲裁税收例外条款的规定,也宣告了东道国对仲裁庭管辖权异议以失败而告终。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功能不再是仅仅限于避免东道国歧视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者,而是使得投资者不但可以从第三方条约中“挑选”对其有利的条款,而且还可以绕开这一条款的例外规定,为投资者提供超乎缔约国意图的条约保护。
在“谢业深诉秘鲁案”(14)(以下简称“谢业深案”)中,仲裁庭也面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国—秘鲁投资协定)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问题。投资者谢业深希望适用第三方条约即《秘鲁—哥伦比亚BIT》第12条中对其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条款——可以向ICSID提交与投资有关的任何争议,而不受制于《中国—秘鲁投资协定》第8条第3款只允许将征收补偿数额争议提交ICSID的限定。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第31条作出解释,认为该条款反映了缔约方在两方面达成了一致:(1)同意将征收数额争议提交ICSID解决;(2)至于可提交ICSID的其他争议,缔约方保留逐案同意的权利。仲裁庭最终认定《中国—秘鲁投资协定》第8条第3款对争议范围明确限定的规定优先于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一般规定,驳回了谢业深的此项请求。“谢业深案”仲裁庭在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问题上的推理明显不同于其他案件仲裁庭,后者较多地考虑了订立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目的在于避免歧视,进而分析其适用范围是否扩及第三方条约争议解决条款,而“谢业深案”仲裁庭则是在对基础条约中的两个条款进行效力比对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迥然相异的推理路径让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虽然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庭对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貌似飘忽不定,但从中也可以发现所谓定律:如果投资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只是为了免除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前置程序安排,如当地救济等候期的规定,那么仲裁庭倾向于支持投资者的主张;如果投资者援用最惠待遇条款的目的触及仲裁争议范围的扩张或改变,如从征收补偿数额争议扩张至与投资有关的一切争议,那么仲裁庭就会更加慎重。
三、针锋相对的理论界:再探最惠国待遇的本质
有些学者或仲裁员反对把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议解决事项的理由在于,这种扩张适用有悖于缔约国提交仲裁的“同意”。例如,在“帕拉马案”中,仲裁庭指出,基础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并不扩及第三方条约中的争议解决条款,除非缔约国在基础条约中明确作出相反表示。2004年加拿大、美国和欧盟在各自的BIT范本中均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限制就表明了这一观点。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和仲裁员认为上述限制是毫无必要的,或至少在以往条约中没有这样的先例。例如,“马菲基尼案”仲裁庭公开驳回了西班牙主张最惠国待遇条款中的“事项”仅指实体事项或投资待遇的实体权利并不包括程序或管辖权事项的观点,强调根据国际先例和最惠国待遇条款中包含有“与条约有关的一切事项”的措辞,BIT争议解决是投资保护的重要方面,与投资待遇的获取有紧密联系。还有学者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涉及争议解决方式才是符合逻辑的解释,投资者通过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获得非歧视的争议解决方式是提高投资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缔约方缔结投资条约的真正宗旨和目的所在。(15)不过,这一观点建立在一个过于简单的假设之上,即通过基础条约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引入各种第三方条约的规定就能提高外资保护水平,而事实并非如此。其理由如下:(1)引入的第三方条约中的相关规定并不必然提高外资保护水平。(2)即便引入的第三方条约中的相关规定能提高外资保护水平,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本质也是为了保证竞争条件的公平,而不是沦为投资者“挑选条约”的工具。这种看似宽泛的选择权实际上制造了更为混乱的局面,增加了投资争议解决的不确定性,东道国将无法预见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争议到底要根据哪一个投资条约进行解决。这绝对不会是缔约国的真实意图。对投资者而言,所谓“更便利”的争议解决方式也多半是一种臆想,在裁决正式作出之前,谁能保证仲裁前置程序一定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呢?或者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庭、ICSID、SCC当中谁更有利于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呢?(16)
如果在条约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那么仲裁庭无疑应当严格按照约文行事。但现实是,几乎在所有的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案件中,仲裁庭面对的均是非常抽象、概括的最惠国待遇条款,于是仲裁庭的解释方法就直接影响该条款的具体适用。虽然个案仲裁庭宣称按照《条约法公约》第31(1)条解释并同时考虑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但事实上这种解释方法要求仲裁庭必须慎重权衡条约文义与目的、宗旨之间的关系,如此才能避免得出荒谬的结论。有学者指出,在一些案件中,仲裁庭仅从字面解读条约,过于简单地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援用了第三方条约中更优惠的条款(事实上是否更优惠还缺乏客观验证),外资保护水平就提高了,最惠国待遇条款也就实现了其功能;而在另一些案件中,仲裁庭则把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这种功能视为一种危险。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程序事项是否属于投资保护的一部分,或如果引入第三方条约中的相关条款是否能提高基础条约对外资保护的水平,而在于缔约方的真实意图以及仲裁庭合理、正确的解释。(17)
最惠国待遇本身有其客观的衡量依据,即两个不同国籍的外国投资者相比,其中一个因受到歧视待遇而产生了经济损失。现实中,可能出现一国投资者被要求用尽当地救济而另一国投资者无需如此,或一国投资者被要求满足某些先决程序、诉诸特别裁判庭而另一国投资者无须如此的情况。笔者认为,这种差别待遇的原因在于不同的缔约谈判产生了不同的条约规定,而并非东道国实施国别歧视所导致。在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引入第三方条约的相关规定时,应当满足“同类原则”、(18)“相同情况”(19)以及与实现公平竞争条件密切相关等要求。
四、“伊佳兰案”:我国面临的考验和未来的缔约选择
(一)“伊佳兰案”:我国面临的考验及其应对
“伊佳兰案”是否有可能解除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扩张的威胁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1988年《中国—马来西亚投资协定》第3条“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仍然是传统的概括式规定,即“缔约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待遇,不应低于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所受到的待遇”。《中国—马来西亚投资协定》第7条“投资争议的解决”规定,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和双方同意的其他争议可以提交专门的国际仲裁庭。对于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除非双方同意,ICSID管辖事项仅限于有关征收补偿数额的争议。正如前文所述,目前关键的问题是,伊佳兰公司是否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享受我国缔结的其他BIT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我国第二代BIT,如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芬兰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等条约均可能成为伊佳兰公司要求适用的第三方条约以获取其认为更有利的争议解决方式。笔者认为,如果我国提起该案的管辖权异议,其中就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可以主张:(1)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着眼点在于衡量具有不同国籍的投资者所享有的待遇,其目的在于“整平游戏场地”,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扭曲;(2)应满足“同类原则”、“相同情况”的要求,不同投资协定中不同的争议解决条款并非对投资者的歧视,而是基于不同的缔约环境和基础而产生的不同结果;(3)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引入第三方条约的相关规定事实上篡改了基础条约的规定,如果缔约方缔结的特定条款很轻易就被其他条约的规定所减损,那么缔约将毫无意义;(4)不能通过对一个抽象、概括条款(基础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解释去规避一个明确、具体条款(基础条约争议解决条款)之规定。仲裁庭的任务在于审查东道国是否违反基础条约的规定,进而决定是否给予赔偿。如果仲裁庭擅自从第三方条约中引入法律标准或程序,那么事实上是在要求东道国履行争议发生前并不存在的条约义务,并且通过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引入的第三方条约之规定与竞争条件没有任何关系,仲裁庭这样做显然有失妥当。更何况投资者最初提出索赔请求的根据并非最惠国待遇条款,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只是为了争取仲裁庭管辖权的成立,这与违反最惠国待遇条款之诉显然不是一回事。
(二)缔约建议:国际缔约趋势及我国的缔约选择
1.国际缔约趋势:从概括性立法到明确限制性立法。放眼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规定都较为概括。例如,《西班牙—阿根廷B1T》第4条第2款规定:“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在其境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投资及与投资有关活动的待遇”。正因为国际投资争端个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有着令人捉摸不定的推理,理论界对此也一直争论不休,一些嗅觉敏锐的国家已经开始在缔约实践中改变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传统面目,对该条款的适用范围作出明确的限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第1103条和2004年《美国BIT范本》第4条均规定:“每一缔约方应给予另一缔约方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任何缔约方或非缔约方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包括投资新设、收购、扩大、管理、控制、经营、以及销售或处置”。需要注意的是,美式BIT已将最惠国待遇延伸至市场准入或新设投资即外国直接投资在投资设业前阶段的权利。传统上美国、加拿大缔结的投资条约多主张市场准入权,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这一权利纳入投资待遇条款。不过这些条约均未明确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是否及于争议解决事项。直到2004年,在《美国—中美洲—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各方才就最惠国待遇条款达成共识并记载于约文草案中:“本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范围明确限于投资设立、收购、扩大、管理、控制、运营和出售或其他处置。缔约方一致同意该条款不适用于争议解决机制,以免出现‘马菲基尼案’的情况”。虽然这一共识最终并未成为该协定的一部分,但它无疑成为条约谈判中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未来投资争议中,这一共识无疑可以佐证缔约国的真实意图,从而避免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扩张解释。(20)2006年5月欧盟委员会在其就未来投资条约谈判的政策指引中指出,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不应当扩张至征收事项和争议解决事项,并且区域经济一体化事项也应当排除在外,以免产生消极后果。(21)“马菲基尼案”等案件也直接导致2007年《哥伦比亚BIT范本》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不适用于投资争议解决事项。可以说,对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作明确的限制性规定将成为一种国际缔约趋势。
2.我国的缔约选择:限制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近年来,随着个案仲裁庭对最惠国待遇条款进行层出不穷的吊诡解释,国际投资条约最惠国待遇条款已经从过去一个“无害”的、很少成为投资争议解决焦点的条款发展成为投资者进行“挑选条约”的工具,以达到绕开ICSID仲裁前置条件或扩展仲裁事项范围的目的。对投资者而言,当条约无明确禁止性规定时,选择对其更有利的条约保护无可厚非;但对东道国而言,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国际投资争端仲裁实践中的深刻变化无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警惕过于宽泛、概括式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可能制造的威胁甚至远超乎东道国缔约当时对该条款功能的估计。我国的第一代、第二代BIT最惠国待遇条款均采用高度概括式规定,其潜在的威胁也不言而喻。在未来缔约中应当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中明确排除对争议解决事项的适用,从根本上降低该条款在实践中的不确定性,对仲裁庭恣意无常的解释予以约束。笔者认为,最惠国待遇条款争议解决事项例外规定可表述为:“本条约所指在相同情况下给予的最惠国待遇不包括其他条约或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争议解决机制,如本条约第×条(缔约方与另一缔约方投资者间争议解决)及第×条(缔约方间争议解决)”。
注释:
①See Ekran Berhand v.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ICSID Case No.ARB/11/15.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双方谅解”部分。
③为了克服潜在的“免费搭车”问题,缔约国可以对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即受惠国若想享受给惠国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优惠,则受惠国必须提供同等的优惠。不过,为了鼓励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国际经济条约中多鼓励给予无条件最惠国待遇。
④从“马菲基尼案”裁决到近来其他有关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的仲裁裁决引起的争论看,其焦点集中于BIT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只适用于实体权利或是否及于程序事项,如争议解决事项、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具有溯及力、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及于“保护伞”条款。
⑤See Maffezini v.Spain,ICSID Case No.ARB/97/7.
⑥See Siemens A.G.v.The Argentine Republic,Decision on Jurisdiction,3 August 2004.
⑦See Wintershall Aktiengesellschaft v.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4/14.
⑧See Request for Arbitration,Philip Morris Brand Sàrl(Switzerland),Philip Morris Products S.A.(Switzerland) and Abal Hermanos S.A.(Uruguay) v.Oriental Republic of Uruguay,ICSID Case No.ARB/10/7.
⑨在“马菲基尼案”之后,仍然有一系列案件采用了该案仲裁庭的观点,这些案件的投资者都试图通过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从而绕开基础条约规定的投资仲裁的前置条件。See Camuzzi International SA v.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3/2; Gas Natural SDG SA v.The Argentine Republic,ICSID Case No.ARB/03/10; 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 and Vivendi Universal SA v.The Argentine Republic ICSID Case No.ARB/03/19.
⑩See Plama Consortium Ltd.v.Bulgaria,ICSID Case No.ARB/03/24.
(11)See RosInvest Co.UK Ltd.v.The Russian Federation,SCC Case No.Arb.V079/2005.
(12)See Lise Johnson,UK Firm Victorious in Dispute with Russia,but Damages Much Less than Claimed,http://WWW.iisd.org/itn/2011/04/07/awards-and-decisions-2/,2011-07-21.
(13)See Renta 4 S.V.S.A.v.Russian Federation,SCC Case No.24/2007.
(14)See Mr.Tza Yap Shum v.Peru,ICSID Case No.ARB/07/6.
(15)See Emmanuel Galliard,Establishing Jurisdiction Through a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N.Y.L.J.,Vol.233,No.105,2005; Dana H.Freyer & David Herlihy,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 and Dispute Settlement in Investment Arbitration,Just How "Favored" is "Most-Favored"?,20 ICSID Rev.58(2005).
(16)(17)See Alejandro Faya Rodriguez,The Most-Favored-Nation Clause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A Tool for Treaty Shopping? 25 J.INT'L ARB.89(2008).
(18)根据基础条约中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获得第三方条约中的某种更有利待遇时,基础条约与第三方条约所规定的应当是“同类事项”。具体到国际投资条约中,投资者根据基础条约最惠国待遇要求获得第三方条约更优惠的待遇时,必须满足上述“同类原则”的限制。不过,这并不能解决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扩展至争议解决事项的问题。
(19)“塔克门德案”仲裁庭就是以此为由拒绝投资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的。仲裁庭认为投资者不能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东道国给予缔约前就存在的投资以更优惠的待遇,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条约与第三方条约缺乏“相同情况”,即两个条约的谈判基础不同。See Tecnicas Medioambientales Tecmed S.A.v.The United Mexican States,ICSID Case No.ARB(AF)/00/2.
(20)See Peterson,Investment Law and Policy Weekly News Bulletin,6 February 2004.
(21)Se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General for Trade),Note for the Attention of the 133 Committee,Issues Paper:Upgrading the EU Investment Policy,Brussels,30 May 2006,http://WWW.iisd.org/pdf/2006/tas_upgrading_eu.pdf,2011-0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