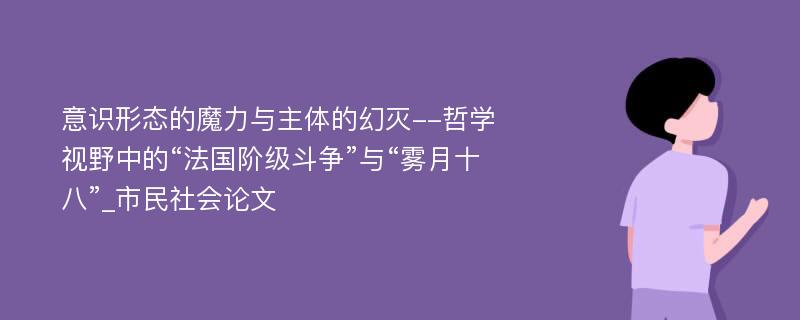
意识形态的魔力与主体的祛魅——哲学视域中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兰西论文,视域论文,阶级斗争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魔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内学术界,马克思在1849-1852年间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下简称为《雾月十八日》)往往被当作政治学著作予以研究,而它们的哲学意义却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了。我以为,这两个文本不仅是马克思非常重要的政治学著作,而且还是非常重要的哲学著作。在此,笔者就以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为突破口,详细剖析这两个文本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全面监控:意识形态理论深化的突破口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析是建立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之上的,正是由于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才使得一部分人从物质生产领域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思想的生产,从而成为意识形态的制造者。但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只是作为体力劳动者出现的,这就注定了意识的生产者不可能是无产阶级,而只能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统治阶级必然会把自身的利益放大为全人类的利益,把自身的意识形态宣布为整个社会的、其他阶级的意识形态,“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① 而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借助于国家,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根本形式。
然而,在一个阶级霸权为主导的社会中,国家的社会权力必然被牢牢地掌控在统治阶级手中,被掏空为一种专政的工具,成为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因此,以这种国家形式被无限放大为普遍利益的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自身的一种理论虚构,是一种虚假的普遍性。也正是立足于此,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称之为“虚假的观念体系”,是对现实的一种幻想和错误的认识。埃蒂安·巴利巴尔认为,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国家和权力建构的政治理论。② 我认为,这一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分析显然是从国家(而非市民社会)介入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专利,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从这种逻辑出发,马克思认为,作为被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必然一开始就能将自己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界划开来,实现与政治国家和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产生出彻底革命的共产主义意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从这里来看,马克思显然高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将其看作为天生的革命者。他还没有从日常生活层面来认识工人,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观念拜物教(日常意识形式)对工人的束缚作用,也没有看到无产阶级自身的拜物教化问题,更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人冲破国家意识形态和观念拜物教束缚的方式。
我以为,马克思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不成熟的观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机制,对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缺乏一种全面的认识。截止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始终都是从市民社会单向度地决定国家入手的,国家究竟对市民社会产生什么作用,似乎并没有引起马克思的注意。然而,1848年前后法国革命的现实却给马克思一个极大的触动,促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为他深化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突破口。
在《雾月十八日》中,通过对法国斗争的分析,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国家不仅可以独立于市民社会,而且还可以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监控、影响着市民社会的一切。他指出,统治阶级的利益始终是与国家机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必然会全面利用国家机器的威慑,“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实现对市民社会的全面操控,把原本属于“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变为“政府活动的对象”,“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③。这促使马克思意识到,资产阶级必然会利用国家机器来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断向工人阶级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如马克思所说:“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④ 而工人在成为自为阶级之前,根本无法识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真实本质,实现与资本产阶级的彻底决裂,反而会无批判地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当作“真理”接受下来,“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⑤,从而对工人的革命斗志产生消极的侵蚀作用,陷入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
马克思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辩证剖析,为他重新审视无产阶级与意识形态的辩证关系开辟了理论空间,实现了对无产阶级认识的去神话过程,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
意识形态与拜物教的魔力:无产阶级的迷茫与失落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根本没有认清资产阶级的狰狞本质,与他们实现彻底的决裂,相反,而是对他们心存幻想,盲目轻信资产阶级共和国意识形态的谎言,放弃自身的阶级立场。
这主要体现在二月革命到六月起义这段时间内。由于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盘剥,再加上经济危机和农业歉收,直接导致二月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最直接后果就是推翻了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在革命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为了消散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也由原来的“革命”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然而,工人阶级并没有识破资产阶级这种意识形态的谎言,竟天真地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在他们的眼中,“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⑥ 在革命中他们并没有抛掉一切陈旧肮脏的东西,并没有在革命中形成彻底的革命意识,而是沉浸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之中,忘却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力图把本阶级革命目标的实现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他们幼稚地以为能够“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⑦。这就意味着,只要资产阶级还没有放弃这种意识形态,无产阶级就不会主动地将革命进行到底,用实际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只会“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这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盲目宠信使无产阶级在日后的斗争中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这为资产阶级窃取二月革命的果实提供了时间。当他们在政治上站稳脚跟之后,就撕碎了那种和谐博爱的面孔,露出了狰狞邪恶的本质,将枪口对准了无产阶级,誓要把工人从临时政府中清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才真正看清资产阶级的本质,然而,他们却丧失了革命的主动性,完全陷入到被动挨打的境地,他们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于是,1848年6月22日,“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这种起义既不是无产阶级自己公开、主动要求“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⑧,而是在资产阶级的逼迫下被动应战,单是这一点就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的。
其次,马克思看到,工人不仅会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蒙蔽,而且还会陷入现代经济社会滋生的金钱拜物教之中,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放弃本阶级的长远目标。马克思指出,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中,无产阶级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阶级意识,除了受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蒙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无产阶级陷入到现代经济社会的金钱拜物教之中。马克思指出:“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制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⑨ 同样,恩格斯在《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中也明确地指出:“最后,还存在工商业非常繁荣这个事实,它本身就足以向拿破仑保证,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会保持中立。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⑩ 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要工人能够获得足够的就业,能够得到一定的报酬,他们就情愿为了一点可怜巴巴的工资而放弃自己的革命利益,工商业越是繁荣,工人阶级越是如此,“商业和工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尝试。”(11) 这样一种心理恰恰成为路易·波拿巴政府侵蚀工人革命意志的手段,他一方面“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12);然而,巴黎的工人们却没有认出这种金条梦的实质,而是一股脑的投入到这种金钱的游戏之中。这种金钱拜物教对工人阶级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它严重侵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志,使工人阶级为了单纯的金钱利益,忘记了自身的革命目标,最终放弃了武装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策略。“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13)
再次,马克思看到,法国农民不仅深受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还深受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拜物教观念的束缚。马克思指出:“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取名为拿破仑。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固定观念一致的。”(14) 由此来看,传统的“拿破仑观念”“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而路易·波拿巴就是利用这种传统意识形态,最终赢得了国家大选。这也表明,农民一开始也像工人一样没有能力鉴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陷入到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圈套和虚假承诺之中。另一方面,农民也会形成现代日常意识,陷入到货币拜物教的漩涡之中,比如,农民为了减少自己的货币支出,就主动地放弃反抗,轻信波拿巴废除葡萄酒税的虚假承诺,甘愿接受波拿巴的愚弄,最终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货币拜物教的旋涡之中,沦为一个不可挽救的可怜虫。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主要指的是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由统治阶级或思想家建构出来的“纯粹的理论”和“虚假的观念体系”。恩格斯准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15) 与此不同,拜物教并不是国家权力建构的结果,而是个体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客观思维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自身滋生的客观产物。第二,虽然这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总体上却是互为一体的,虽然马克思在后期文本中很少使用“意识形态”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放弃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拜物教批判理论决不是对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单纯代替,相反,而是对后者的延伸和深化,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当巴利巴尔认为马克思后期已经用拜物教批判理论“取代”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时(16),显然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忽视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第三,这也证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国家意识形态、日常意识形式相互作用的过程,如果只是直观地面对日常生活,只站在生活世界的外在层面,不仅不能透视生活世界的内在本质,相反,还会陷入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日常拜物教的枷锁之中。第四,工人和农民一开始并不是作为自为阶级中的一员存在的,而是作为普通人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因此,他们也与其他人一样会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金钱拜物教观念的束缚。
经济危机:冲破意识形态与拜物教束缚的可能性机制
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非常明显了:既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拜物教会侵蚀工人的革命意志,因此,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和拜物教观念的束缚,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就成为此时马克思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和《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做了一点积极的尝试。
马克思认识到,在工商业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工人会为了眼前利益,陷入到拜物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牢笼之中,忘记自己的革命目标。于是,马克思自然会认为,只有在爆发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工人才会从眼前的拜物教中苏醒过来,找回已经丧失的本性,爆发出革命的热情。“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17)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完全制定了危机和革命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把革命的成熟时机奠定在经济危机之上。
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呢?首先必须承认,这是马克思利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解释资本主义灭亡的一种积极的尝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是一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经济危机就是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矛盾的外在体现,因此,当马克思把革命建立在危机之上时,实际上是试图证明只有把革命奠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之上才是可行的,换言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全面展开,革命本身是不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对革命时机的一个基本判断,这一点是必须要予以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此时马克思的观点还存在诸多不成熟的地方。首先,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工人摆脱意识形态和拜物教观念束缚的根本机制。我认为,这一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一旦商业危机过去,资产阶级的经济出现复苏,工人又必然会再次陷入到拜物教观念之中,因此,仅仅停留在工商业危机的外在层面,马克思是无法为工人找到一条彻底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拜物教束缚的科学之路的。要想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深入到工人与资本家的内在矛盾之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再生产层面来探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拜物教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在那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剖析,提出了三种相互联系的机制:资本主义的奴役性实践、工人自身经验的累积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发展,必然会迫使工人起来反抗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冲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束缚,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也只是到了这时,马克思才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答。(18)
其次,从危机理论来看,此时马克思显然还是不科学的。他过高估计了危机的破坏力,把危机当作资产阶级社会“病理性”的根本标志,没有认清危机的内在本质;同时,他将革命建立在危机之上,直接确立革命与危机之间的依赖关系,显然对革命形势的判断过于乐观了。直到后面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真正制定了自己的危机理论。在那时,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生理周期性”表现,它本身还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必然性,只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危机才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在不可克服的界限,因此,只有立足于再生产理论才能真正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没有科学的再生产理论,就不会有科学的危机理论。这也就意味着,要想制定科学的危机理论,就必须要把理论的支点推进到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层面,而这恰恰是马克思后面要着手进行的工作。
注释:
①③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0、623-624、611、387、385、400、631-632、473、643、592、678、726、470-471页。
②(16) [法]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1-112、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2页。
(18)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穿透拜物教的魔力:阶级意识与日常意识的辩证法》中详细分析。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工人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