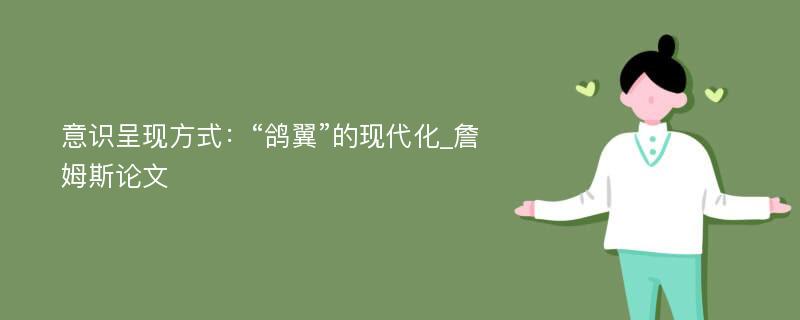
意识呈现的方式:《鸽翼》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意识论文,方式论文,鸽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对现实主义、罗曼司、唯美主义等文艺派别的艺术手法加以吸收和改造后,逐步实现了其创作的历史转变。大致的趋势为:较早的小说罗曼司因素更多,以后现实主义的因素越来越多,再以后更关注心理现实,逐渐与现代主义创作接轨。读书界倾向于认为,《鸽翼》、《奉使记》、《金碗》这几部杰作的写作方法和现代派十分接近。本论文将剖析《鸽翼》的所谓绚丽的语言、文体现象,质疑小说的现代性,肯定小说的传统性。一些研究小说理论的专家也从理论角度,探讨过詹姆斯的小说。所以本论文将联系一些小说理论家的著述,讨论詹姆斯对人物内心意识的摹写,从而解释詹姆斯后期小说与“现代派”的距离。
一
詹姆斯的后期小说中《鸽翼》(1902)也许是最好的一部。弗吉尼亚·伍尔夫素来不喜欢詹姆斯的作品,却也对这部长篇青睐有加。她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因此大病一场。女主人公米丽·袭耳的确非常让人同情。她是美国一个大家族惟一的幸存者,腰缠万贯,却也不久于人世。另一女主角凯特·克罗猗和自己的情人墨顿·登歇穷困潦倒,无法结婚。当墨顿作为记者去美国采访时,和米丽又产生了感情。后来米丽与一位上了年纪的美国妇女苏珊去欧洲旅行,结识了克罗猗,因为苏珊的一个熟人正好是克罗猗的亲戚。穷困而美丽的克罗猗为了达到与墨顿结合的目的,竟然怂恿墨顿去追求同样美丽的米丽,以便在她去世后得到她的财产。米丽得知他们的阴谋后在意大利凄凉去世,但她原谅了克罗猗以及自己爱着的墨顿,并把全部财产给了墨顿。墨顿终于良心发现,在米丽去世后拒绝与克罗猗结婚。这部小说已经拍成电影,但很多观众感到不满,理由之一是扮演墨顿的演员缺少魅力,难以说明他为何能得到两位绝色佳人的爱情。还有一个原因恐怕在于《鸽翼》在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心灵冲突,属于“心理剧”,许多属于心理叙述的内容不便以电影去表现,因为电影更注重展现(而非讲述)。书中的男女人公沉醉于自我的内心世界,以至于小说本身并没有太多戏剧化的情节。虽然小说掺杂了不少叙事者的语言和意识,但人物的心理活动却出现得非常多。读起来,几乎可以在米丽身上看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形象,而且她在意大利孤独地去世的场景也和林黛玉魂归离恨天时的情景相似,很容易引起读者同情,拨动读者的心弦。克罗猗也像是工于心计的薛宝钗。由此联想到了《红楼梦》,不是毫无道理的。最近小说研究专家唐纳德·斯通教授到北大英文系授课,也提到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一些重要小说与我国的《红楼梦》颇具可比之处。斯通教授赞扬中国小说高超的叙事艺术,认为乔治·艾略特、撒克雷(也许还可以包括詹姆斯),这些英国文学史上的大家都比不过曹雪芹。
《鸽翼》创作于詹姆斯的“主要时期”(major phase),对人物内心意识刻画很多。该书的文体至为繁复,同时,评论界都公认它是詹姆斯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在书里表现人物(或者还有作者自己)的心理的真实情境,描绘出“意识的房间”(chamber of consciousness)。小说的内容引出了小说形式上的重要变革,通过人物的视点,从多个角度叙事,挖掘人物的主体意识。内容和形式上的这些重要变革,都启发了詹姆斯之后的现代派作家。
《鸽翼》的文体至为繁复,文字像许多现代派作品一样难读。很多受过文学训练的国外学者,比如韦恩·布斯教授,也认为这本书很不容易阅读,让读者忍不住要把书扔掉。这就给读者一个印象,认为《鸽翼》属于现代派小说。本论文认为,实际上这属于作家风格问题,不应该把这部书与现代派小说绑到一起。
詹姆斯的言说风格,一言以蔽之:欲言又止。记得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在她著名的日记里以揶揄的口气记录过她印象里的说话吞吞吐吐的詹姆斯。亨利·詹姆斯的哥哥,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也对他弟弟说:“看在老天的分上,把你想说的直接说出来!”[1] 詹姆斯小说比较突出的文体特点是句子极为冗长,喜用圆周句,结构繁复,欲说还休,用语典奥。利奇和肖特在他们的名作《小说的文体》一书中,凭借着文体学家的细致和敏锐分析过詹姆斯短篇《学生》的第一、二段。利奇和肖特的分析很精辟。他们所做的分析和概括基本适用于他的其他作品。他们认为,詹姆斯的小说语言基本符合英语的语法规范(常规),没有太大的“变异”。但是,“和劳伦斯所用的简单而朴实的词汇形成对照,詹姆斯似乎更愿意使用非常正式的、从拉丁语派生出来的词汇,如procrastinated,reflected,remuneration,observation,confession,等等”。“詹姆斯的句法是古怪的,同时也是有意义的,需要联系到作者对心理现实主义的关注进行评估。作者试图通过不懈的努力,捕捉到‘丰富、复杂的心理时刻及其伴随条件’……当我们读完这两段时,我们已能感受到(小说所写的)尴尬处境中同时并存的复杂情况和反讽意味。所以故事的进展不是从前往后,而是根据震撼了主人公意识的境况的远近来展开”。“詹姆斯的句法不如康拉德的复杂。在《学生》这两段里,从句和独立句的比率为3∶1……詹姆斯对不定式从句的使用尤其引人注目……由于不定式从句所指的,往往不是事实,所以詹姆斯更多地用来编制心绪之网的,不是已知的事实,而是可能性和假设。”[2] 由于《鸽翼》和《学生》的文体特色基本一致,所以这里仅举出利奇和肖特的话,读者可以触类旁通。
以这种詹姆斯式的风格、语言去描述人物意识,势必影响作家对人物思想意识探讨、展示的深度。在《鸽翼》里,由于典型的繁复的“詹姆斯式”的句子占据了突出的位置,造成詹姆斯作为作者/叙事者的声音过分强大,因而人物的声音和意识必然表现得不够,所以他在实现作家的“引退”方面做得不干脆。笔者细致阅读这部小说,发现书里的“自由间接话语”以典型的形式出现得非常少,大部分话语介于作者的报道和人物“直接话语”之间。由于小说批评界公认,“自由间接话语”作为一个较客观的尺度,可以检验一部小说算不算“现代主义文学”,所以本论文认为,严格地讲,这部小说算不上现代派小说,属于过渡性质的作品。很多读者想当然地认为詹姆斯“主要时期”的创作属于现代派文学,他们的看法不大站得住脚。
《鸽翼》这部作品里有一个主要的标志,深刻反映出詹姆斯的创作从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过渡。这个标志就是,作者的意识渐渐地向着人物意识过渡。俗话说,“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欲以文字表现他人意识(如小说家通过意识流、内心独白等手法努力去做的)也许不大可能,而所谓人物意识,也只是小说家虚构出来的,说不定就是作家本人的意识。但现代派小说家追求的一个主要目标,即是制造出“以小说中人物的眼睛看世界”的效果,詹姆斯就是这些现代派小说家的祖师爷。可是他作为作家的意识,实在过于强烈,影响了他对人物意识的表现。这一点,在《鸽翼》里表现得非常典型、深刻。
詹姆斯为创作《鸽翼》所做的笔记就表明,他的创作受到几个不同人物意识的困扰。[3] 他在采取多角度叙事的时候,对不同的意识该占多大比重不大有把握。笔记还表明,詹姆斯毕竟进行了形式上的实验。比如他通过多角度叙事,得到的效果是,同一个事件,对于不同的观察者/小说人物来说,意义完全不同。詹姆斯还从印象派那里学会了刻画人物的主观印象。此外,詹姆斯的笔记的趣味还在于,它反映出“工作中的詹姆斯”(James at work),似乎在通过笔记说明,可以让事件从不同的方向展开。这和阿根廷后现代小说家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中的看法一致:时间和空间的网络纵横交叉,可以按不同的路线发展、延续,就像故事可以照不同的线索发展。因此詹姆斯的笔记也反映了作家的谋篇布局,揭示出小说创作的规律和秘密。进一步说,如果詹姆斯把笔记上的东西放进小说里,他的小说就会变为博尔赫斯式的元小说或实验小说,具备“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因此,批评家也可以通过诠释活动,挖掘詹姆斯小说的现代(甚至后现代)因素;不过,不应该再进行“过度诠释”。
二
通过多角度的叙事,《鸽翼》对人物内心意识经历的磨难关注得比较多,而作者/叙事者对叙事的干扰也较多。《鸽翼》这部小说与传统小说的相似点很多,虽然它也接近现代主义小说。
詹姆斯的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甚有渊源。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模式里(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等人的作品即是很好的例子),人物心理大多通过全知叙事者的口吻叙出;作家常通过描写人物心理来发表他的一些高见。但是,如罗兰·巴特所说,从叙事文本中清除作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而现代文本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作家的嘴脸不再出现。韦恩·布思也认为,作家的隐退,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4] 詹姆斯在人物视角上做了实验,采取多角度叙事。他把小说人物作为“反映者”(reflectors),以其内心意识记录下对于现实生活的印象,所以作家就无必要处处站出来发言了。这无疑有助于拓宽现实主义的表现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斯被称为心理现实主义作家。从小说的发展来看,也正是通过詹姆斯、福楼拜等作家的艺术实验,作家才渐次从叙事文本中隐退。
值得注意的是,比之于福楼拜,詹姆斯相对比较保守;道德上的保守主义就反映在现实主义的小说形式上。福楼拜对爱玛的心理所做的描写大胆、真率、直接,而詹姆斯对于礼教考虑过多,不敢写到有伤风化的东西。他在《亨利·詹姆斯文学笔记》里谈到自己创作《鸽翼》时,显得顾虑重重:“如果我是在为法国读者而写小说,整个事情就会很简单——年纪更大的,‘另外那个’女人可以做那个年轻人的情妇,他只须应付一下那个快去世的姑娘就可以了——和她建立暂时的关系。但要处理英国人通奸这样的题材,却十分棘手……我们的传统尊重选择的自由,并且普遍接受离婚。”[5] 詹姆斯没有说的是,他太在乎小说的道德训诫价值,太关心小说可能会对“女性读者”产生的影响,这必然会影响到他对小说形式的选择。尽管他认为“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便是它的确试图表现生活”,可是他仍然非常看重小说的社会功能。所以,虽然他在《鸽翼》等小说中对人的内心作了颇有深度的挖掘,但他不敢忘记小说的教育价值。他关心世道人心,老想站出来发言。在作品里,他以“叙述者”的身份发表意见,对人物内心活动妄加评点。许多小说中人物不得不以詹姆斯式的句式来思考;詹姆斯在表现人物细腻的想法时,不时地会展示自己的身影,人物的思想也因此沾染上叙事者的思想。只有当叙事者愿意和人物保持最近的距离,愿意认真、客观地记录人物的意识时,人物的思想才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叙事者思想的影响。仔细阅读《鸽翼》的文本,不难注意到,小说中常常出现作者的意识和小说人物意识争夺发言权的情况。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鸽翼》作为启发了现代派作家的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却很少使用“自由间接话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or FID)这个现代小说的重要叙事手段。因为“自由间接话语”要求叙述者给予人物更多的说话/思考自由,尽量地保留人物个性化的语言特征。正如斯罗米斯·里蒙-凯南所说,“自由间接话语可以复制出人物的言语和思想的个人习惯——有人还会加上,由叙述人的引导语引导出的前语言感受,视觉的、听觉的或触觉的;因为自由间接话语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在描述意识流,特别是‘间接内心独白’的时候,它是一个方便的工具。”[6] 詹姆斯实际上很早就能熟练运用“自由间接话语”,[7] 但是,在詹姆斯的许多小说里,“自由间接话语”出现得不多。即使在《梅西所知道的》(What Maisie Knew)这样主观的作品里,叙述者的声音也过于强烈;詹姆斯生怕梅西年纪小,说不清自己的印象和看法,所以不断站出来插话。只是在詹姆斯为一些小说写的笔记中,因为笔记属于天马行空的构思,直抒胸臆,人物几乎成为作者的代言人,所以“自由间接话语”出现较多。这牵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哈佛大学文艺理论家朵丽·高安的论述显得颇为中肯:
在作家以自己的口气讲述的故事中,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往往成为一个跳板,作家将借此宣讲关于人性的普遍真理。菲尔丁、萨克雷、巴尔扎克尽管在其他方面很不相同,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作家和书中人的思想恰成反比例:叙述者越表现得显眼和个性化,人物心理的深度也就越不可能得以展现,因而要描写的心理也缺少深度。亨利·詹姆斯……认为人物的心理需要作细腻的表现,但他同时又认为,具有高尚情操、幽默风趣、格调高雅的作者,可以给读者许多教益。看起来,作家简直是在充满嫉妒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小说里,他要做唯一的思考的主体,所以他感到,要是和另一个思想意识靠得太近,呆得太久,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小说的历史发展证实了旧派作家的自我防卫本能:由于人们对个体心理问题的兴趣越来越大,清晰可感的叙述者便从小说世界里消失了。但这并不像韦恩·布斯所说的那样,“对人物内心持续聚焦……可以暂时把这个思考着的人物变为叙述者”(参见布斯,《小说修辞学》,芝加哥,1961,p.164)实际的情况是,得到充分发展的人物意识,象虹吸管一样,吸去了过去那个大举扩展的叙述者身上的情感、智力和能量。(但高安不得不承认),甚至在叙述者从中心舞台走过去以后,他还在继续叙事,成为中性的附件,但在以人物为主的叙述中他又必不可少。所以,最早坚持把叙述者从小说中移走的作家——主要是福楼拜和亨利·詹姆斯——他们创作出来的人物意识,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度和复杂性。[8]
高安的观点大致说来是精辟而正确的,但她关于詹姆斯的提法不太妥当。由于詹姆斯的作家意识比较强,所以他的作品表现的人物意识就常常受到作家意识的制约,经常地达不到无与伦比的深度和复杂性。詹姆斯为了表现人物意识,在形式上进行了较大的实验;虽然作者的确在履行其“从作品里引退”的理念,但在表现人物内心活动时,叙述者的干预也还可以感知。试看《鸽翼》中人物凯特的意识(由英文可以更容易地看出詹姆斯的语言特点,所以采取了中英文对照):
It was perfectly present to Kate that she might be devoured,and she likened herself to a trembling kid,kept apart a day or two till her turn should come but sure sooner or later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age of the lioness.The cage was Aunt Maud' s own room,her office,her counting-house,her battlefield,her especial scene,in fine,of action,situated on the ground-floor,opening from the main hall and figuring rather to our young woman on exit and entrance as a guard-house or a toll-gate.The lioness waited-the kid had at least that consciousness; was aware of the neighbourhood of a morsel she had reason to suppose tender.She would have been meanwhile a wonderful lioness for a show,an extraordinary figure in a cage or anywhere; majestic,magnificent,high-colored,all brilliant gloss,perpetual satin,twinkling bugles and fashion gems,with a lustre of agate eyes,a sheen of raven hair,a polish of complexion that was like that of well-kept china and that...Her niece had a quiet name for her-she kept it quiet; thinking of her,with a free fancy,as somehow typically insular,she talked to herself of Britannia of the Market Place-Britannia unmistakable...These impressions,none the less,Kate kept so much to herself that she scare shared them with poor Marian( or Mrs.Contrip,her sister,who marries a parson of a dull suburban parish) .[9]
凯特很清楚,她可能被吞吃掉,她把自己比作发着抖的小孩子,在一旁苟延残喘,但迟早会被带进母狮子的笼子。那个笼子就是毛德姨妈的房间,她的办公室,她的会计室,她的战场,她的特殊场景,风景很好,蓄势待发,它就在底楼上,和堂屋相连,但对于我们的年轻姑娘说来,它的进口和出口简直就是岗亭或收费站。母狮子等待着——小孩子至少有那个感受,她有理由认为,附近有娇嫩的食物。实际上她算得上一头美妙的母狮子,正在展览着,是关在笼子里或别的什么东西里的尤物;威严、美妙、鲜艳、闪闪发光,穿着缎子,佩带珠宝首饰,眼睛放着玛瑙的光芒,头发油光水亮,脸上涂抹得很好,一如保养得甚好的瓷器。她的侄女悄悄给她取了个名儿——悄悄地;展开想象,想到她不与别人交流,正是市场上的不列颠——不犯错误的不列颠。不过,这些印象凯特都秘而不宣,几乎没有告诉过玛丽安(或康追普太太,她的姐姐,嫁的是一个乏味的乡村牧师)。(p.23)
由这段文字可以认识到,叙述者迫不及待地想发言,冲淡了凯特·克罗猗的思想。这样的段落在整本书里还可以找出不少。即使在那些最接近自由间接话语的段落里,也出现作者意识侵占人物意识的情况。如:
There was no such misfortune,or at any rate no such discomfort,she further reasoned,as to be formed at once for being and for seeing.You always say,in this case,something else than what you were,and you got,in consequence,none of the peace of your condition.( pp.25-26的FID)
不会这样倒霉,至少,不会这样让人不舒服,她进一步推想道,倒霉的事不会马上出现,让你看见。你一定会,在这样的情形下,说一些别的东西,而且再也得不到安宁。
这段话是具有自由间接话语特征的。但它既像是叙事者的评论,也像是凯特对自己——“你”说的话。
确如朵丽·高安所说的,作家看起来简直是在充满嫉妒地维护自己的特权。在小说里,他要做惟一的思考主体,因此他感到,要是和另一个思想意识靠得太近,呆得太久,自己的地位就会受到挑战。叙述者越表现得显眼和个性化,人物心理的深度也就越不可能得到展现,因而要描写的心理也缺少深度。小说中人物的意识多多少少被作家的意识扭曲了。
德国学者F.K.斯坦泽尔也对这里讨论的问题做过思考。他提出的关于三大“叙事情境”的说法,有助于说明小说写作方式的转换。斯坦泽尔认为,区分出三大叙事情境——第一人称的叙事情境,作者的叙事情境以及人物的叙事情境,就可以大致描述“叙述媒介”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在作者的叙事情境里,叙事者处于人物的世界以外;在人物的叙事情境里,起斡旋、干涉作用的叙事者被“反映者”代替。“作为小说中人物的反映者思考着、感受着、观察着,但他不会像叙事者那样对着读者说话。读者只是通过这个反映者——人物的眼睛,去看叙述文中的其他人物。在这样的情境下,由于无人在‘叙事’,所以叙事呈现的方式似乎是直接的。因此,人物叙事情境的主要标志,是给人无媒介的幻觉。近几十年来出版的大量小说,都采取人物叙事情境。”[10] 斯坦泽尔的提法似乎与朵丽·高安更接近,而布斯的说法——“对人物内心持续聚焦……可以暂时把这个思考着的人物变为叙述者”,大概只会引起更多的混乱。斯坦泽尔还提到了《詹姆斯文学笔记》中出现的“零度媒介”的情况。如果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来分析,可以发现,叙述者的声音和小说人物的声音出现了冲突,体现出深刻的“对话性”,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尖锐斗争。作家在创作时受到其社会地位、阶级立场、思想境界的限制;作家试图反映社会生活时,受到社会话语的约束,这样的约束主要通过作家必须考虑的读者群体而实现。如上面所论证的,詹姆斯写《鸽翼》时不得不认真考虑英国女性读者的情况,所以在选择“通奸”的题材时就显得犹豫。
不过,也要提到,小说写作的实际可以在一定范围促使詹姆斯放弃作者意识。例如他原来打算从“全知叙事者”的角度适当地关注几个人物的意识,在小范围作多视角的交替叙事;但在实际创作时他觉得应把握住这些视点。《鸽翼》由于聚焦的不稳,迫使作者最大限度地放弃作者意识。詹姆斯在选择聚焦点时的犹豫,也可以在上面提到的文学笔记里找到生动的例证。
詹姆斯试图把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视角编织在一起,试验着在小说中表现人物意识的方法,所以他逐渐把握了“视点”这一重要的技巧。《鸽翼》中未出现前后一致的视点。但这不是个缺陷。因为在这一情形下,詹姆斯让读者看到了他在情节安排方面所做的努力;他对于在小说中如何安排这些人物意识缺少信心,而小说结构上的不均衡反映出人物意识为争夺权力话语所做的斗争。作家/叙事者意识让人物意识呈现的努力,在《鸽翼》里表现得明显。作者/叙事者试图让人物做思想的漫步。这样创作出来的小说就和现代“意识流”小说拉近了距离。作者/叙事者似乎想给予人物完全的思想、行动的自由。事实上,也正是由于作者给了这些不同的意识很大自由,所以作品才会产生美感。人物内心的真实情境、对现代经验的焦虑和回应——这些便可以算作小说要表现的非常现代的内容。“法国诗人查理·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的特点是‘转瞬即灭、流放和偶然’……现代性的感受与‘都市’经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给予现代性意识以形式和象征表现。”[11] 在《鸽翼》里可以看到,随着现代都市的扩展,城市居民享受现代文明——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大都市、多样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带来的利益和自由。伦敦的现代都市生活就给了书中的女主人公很大的自由。凯特·克罗猗在一个社交派对上认识墨顿·登歇以后,又可以在伦敦的地铁里遇到他,从而与他发展了恋爱关系。读者几乎可以在小说里感受现代欧洲都市生活的脉搏。小说开头就对追求经济独立的现代女性凯特·克罗猗进行内聚焦,让读者误认为她的意识是小说的主要意识;也许这也是伦敦的客观现实(当时英国很多与凯特处境相似的年轻的现代女性,由于经济原因,很不容易成家),促使作家首先写她的内心意识,虽然随着故事的展开,凯特作为主导意识的地位逐渐动摇。在凯特之后,又引出她的男朋友墨顿·登歇的意识,让读者以为,小说要讲的是这个男人的内心世界。然后作家又写到了以自己的“鸽翼”呵护这对情人的美国小姐的意识;她在知道被自己喜欢的墨顿利用后,非常难过,病情加重,但却原谅了墨顿。所以墨顿受到道义上的谴责。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觉得越来越不容易把握小说中的主要意识;读者也就随着作者/叙事者,逐渐迷失于意识之网。这些聚焦不稳的叙事话语的出现,为现实主义叙事添加了不谐和音。
可以认为,詹姆斯的确大胆地进行了对现代手法的试验;可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自觉地受到习以为常的方法的吸引和牵制。这一点,从他的《文学笔记》和小说里都可以得到印证。当他在笔记中记录下关于某部小说的初步构想时,他感到那些给了他创作灵感的事件、物象“昭晰而互进”。这时他往往控制不住自己,以人物的口吻去构思人物的语言和意识(他在戏剧上的创作经验也为他描摹人物声吻提供了帮助,因为在写戏剧时更多地要考虑其演出效果,所以不可以太书卷气)。不过到写小说的时候,他要冷静一些,且不自觉地受传统小说的语言和技法的牵制,所以叙事者/作者的声音就显得很清晰了。他努力要融合传统的形式和现代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