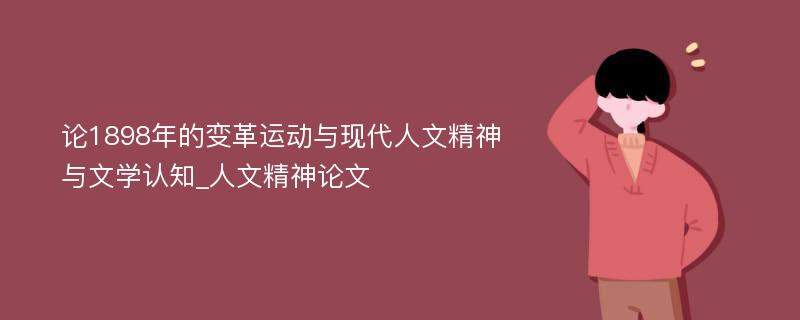
论戊戌维新与近代人文精神及文学感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0)03—0035—07
如何评价戊戌维新运动,有那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这是学术思想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从这场运动的“业果”及其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看,戊戌维新变法不仅仅是一场政治运动,而主要是我国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和年轻的爱国志士在国难当头,民族垂危之际,所迸发的强烈爱国热情的体现,是他们通览世界大势,自觉地接受新社会意识形态所构筑的启蒙文化思潮和人文精神的高扬,是新旧两种意识形态的尖锐和斗争。其时,一批维新爱国志士,先知先觉,忧国忧民,以唤醒民众,开通民智,激发民情为已任,立志革新,致力于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他们所作的一系列文化变革,从文化构成的层面而言,出色地完成了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人的思想解放,强化了人性和人的自主意识,开始实现着我国人文精神的近代化进程,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但从制度和物质层面看,由于维新志士们缺乏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分析,缺乏对科技和经济整体方略的发展要求,加上他们情绪和思维方法的偏颇,遂导致维新变法的失利,又给后人留下了诸多不可避免的“遗憾”!
一、近代启蒙文化思潮与人的价值观重现
在我国近代史上,继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失败,中法战争的失利,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迫使先进的中国人从悲愤和屈辱中惊醒过来,终于在本世纪末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改革思潮,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和以“公车上书”为纲领的戊戌维新运动。这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曾经有过“经世致用”和洋务派“中体西用”学说,但支配各文化领域的思想意识仍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正统的儒道义理的话,那末,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深,斗争现实的残酷,在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文化意识支配下,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已迅速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尽管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有过像容闳的《西学东渐记》、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议》、以及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纪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著述问世,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1]和所谓“实行君民共主”等学说, 但甲午威海一战,宣告了洋务实业救国和“共主”理论的破产。中国向何处去?民族前途何在?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因经济和军事受挫停止对改革社会现状的探求,而是面对严峻的现实和惨淡人生,积极寻求解救祖国积贫积弱的“良方”。一批思想界的先驱者们,从困惑中寻求,从暴风中跃起,进一步从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吸取新的学术思想,译介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权平等、以及唯理分析等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用以武装国人、启蒙群众,从而促进近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汇成了一股新的启蒙思想文化思潮。严复是这一新启蒙文化思潮的开拓者。他原是福州船政学校的首届毕业生,1877年被派往留学英国,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结识了当时驻英大使湘乡派人物郭嵩焘,尝论学习西方良策。回国后适遭甲午丧师,举国震动,“眼见少年气盛之士,疾首扼腕, 言‘变法维新’”,[2]严复怀着强烈的“自强保种”之心,于甲午战争期间,奋笔疾书,撰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论析国事时局的论文,并以至高的热情,译述了《天演论》、《原富》、《法意》、《穆勒名学》、《群已权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意想通过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真切介绍,寻求强国救亡之道,用以启发民众,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严复的这些所为及举措,顺应了时代和人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需求,深刻体现了在新的时局催生下文化观念的变革和新的文化抉择意向,对推进近代启蒙文化思潮的形成,对高扬近代人文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康有为就曾说过: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个人。而鲁迅也谈及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一有空闲,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3]可见,天演进化论影响所及, 决非偶然。
近代维新变法的先驱者们,在寻求真理和作中西文化比较透视的过程中,深深感到:中国思想意识的守旧和落后,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不去掉旧的思想意识就无法汇通中外,无法唤起国民的觉醒。严复在《原强》中指出,那些标榜汉学考据之士,不过都是拾古人唾余,拣末流的破烂罢了,处在“危急存亡之秋”,“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适足于破坏人才”。而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更是大声疾呼:“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梁启超则力主学习西方,藉西学启蒙群众,他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指出:“旧学之蠢中国,犹附骨之疽,疗疽甚易,而完骨为难”,“今日所谓儒者,八股而已,试贴而已,律赋而已,楷法而已。”他们均把长期以来桎梏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把士大夫们终身从事的八股词章,说成是“蠢”人的迂腐陈旧之物,要求改革唾弃。这些看法难免流于偏颇。但是在19世纪末,正当我国处于被列强瓜分,救亡图存迫在眉睫,不反对封建旧学,就无法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历史条件下,维新志士们对封建旧文化的抨击,对于除旧布新,高扬人格及主体精神,对改变“万马齐暗究可哀”[4]的死气沉沉局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的时代,必将产生新的思想和时代文化“精英”。事实是,通过维新志士的宣传和对旧学的批判,已于上世纪之交,在中国大地已开始汇成一股以启蒙文化为先导,以“新民”、开启民智为已任的文化新思潮,从而促进了维新变法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林旭、刘光第、严复、汪康年、徐勒、康广仁、麦孟华、张元济、徐仁铸、杨锐、熊希龄、唐才常等等。他们大多属广东、湘籍和东南沿海各省的有志之士,都具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具有强烈自觉的时代意识和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他们在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年代,一方面发扬历代士大夫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以求实求用精神,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其鲜明的政论和卓越的学术著作,服务于社会人文科学与文教事业,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开始实现着新型知识分子双向角色的认同。他们既是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宣传家,在批判封建旧学说的同时,他们以自己的新思想、新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在许多思想文化阵地广泛开展了改革、启蒙和创造性的新文化尝试。
严复尝言:“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5] “凡为人类, 莫不有一公性情”,“此公性情者,原出于天,流为种智。 ”[6]凡人均具有灵性,均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虽然有过许多君主及开明之士,在提倡尊重和爱惜人才上,发表过好些真知灼见。这在《战国策·燕策》中的“燕昭王求士”、魏武帝曹操的《短歌行》,以及李斯的《谏逐客书》等作品中都不难看到。但中国社会发展到明清之际,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高压政策,也由于文字狱的兴起及八股科举取士,严重窒息和压抑了大批有志之士施展自己的才华。至清末道光年间,龚自珍希求有“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使“大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4]并大声疾呼曰:“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4]。这是封建王朝到了“悲风骤至”的衰世年代, 由一个叛逆思想家所发出的强烈呼喊。迨光绪22年,即1896至1898年间,严译《天演论》的完成和出版,首次把自然科学引进了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带来了西方崭新的文化意识,新人耳目,争相展阅,拓展了国人的文化视野。严复关注时局,善于联系社会现实的译述举措,至今仍有其借鉴意义。他通过对赫胥黎原著的翻译及诸多“按语”,融进了严复自身的开拓精神和文化自主意识,渗透着对人类智慧的高扬,以及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和群体力量的深层意蕴。严复在传递西方文化学说的同时,重申了人的价值及其在自立自强中的意义,他在《天演论》导言中指出:人类“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他高度评价了斯宾塞著作中关于普遍进化的观念,认定人的聪明才智,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类不断进取和自身努力奋斗的结果:“天演”进化,属普遍法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生活在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制天命而用之”,树立起“物竞天择”的思想观念,团结一致,发扬自立自强精神,这就是“国之兴也,必其一群之人,人人皆求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之心。在近代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严复据以我国国情和社会斗争的需要,透过对西方新学说的译介,在哲学文化观上,从情感和心力上,重现了人的价值观,既强化了人群及国民意识,也在新的基点上,注入了人的自强不息精神,从而肯定了人们自身奋斗的价值:“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要救亡图存,要不受他人欺凌,就必须自主自强,不断进取,发挥团结战斗的精神。还在甲午战争后的第一年,严复就以其敏锐的感觉,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倡言以民为本的富国强民之道,在《原强》中他明确指出:“所谓富强之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自由始”,严复以其开放的眼光,吸收和融化西方学说,摒弃长期统治中国的儒道教化与空疏之学,其意在于集为政、利民、自利及自由于一体。他把富国强民与提倡自由、主张民权平等问题视为当务之急,所谓“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7] 乃是顺应了近代启蒙思潮中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变法要求。为此,严复把我国传统文化中“民为贵”的民本思想,适合时宜地发展成“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民力、民智、民德的新民“三要”说,即所谓“人民之大要有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5]的以求“富强”为核心的力、智、 德相统一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和维新变法时期,黄遵宪所信奉的“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生民”(《论学笺》)的观点、与康有为所说的“人人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人有不忍之心”[8], 以及谭嗣同在《仁学》中所言“念人所以灵者,以心”,“通天地万物人我为一身”的主张,以及梁启超所致力提倡的“新民”说、“原动力”说,宣传要“新国”必先“新民”的观点基本相一致,集中体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变法志士们对重视人的价值的关注,对提倡心力、动力和启民智问题的共识,也反映了在新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智者们强调作为人的主体创造性及动力意识,对实现振奋民族精神、祈求富国强民的强烈愿望。
二、近代人文精神促进了人文科学及社会风尚的变革
光绪二十七年(1901),梁启超在《南海先生传》中道: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了,其“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并极其深刻地指出:“戊戌维新之可贵在精神耳。”此“第一章”及“精神”意蕴何在?梁启超未及详评。在我看来,就在于由一批爱国的维新志士,放出眼光,励精图治,以其不折不挠的精神所建构的新的文化思潮和近代人文精神。至此,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逐渐替代了以封建的“德行”为本的伦理精神。正是这种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为上世纪之交中华文化的革新和发展带来了一派生机动人的景象。也为“五四”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1907年,青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论文中,不正是为了顺应冲破一切旧势力、旧罗网的需要,而提倡“尊个性而张精神”,发出了“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强烈呼声,而寻求中国近代新的文化精英和人文精神的吗?
学术界习惯于把人文精神,视为欧洲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同维系封建统治的宗教神权体系作斗争的时代精神,并誉之为人类思想史的一次重大解放,造就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正象1873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9]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及其文化业绩,不光迎来了社会文化变革的曙光,而且对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商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的话,那么与之相较,产生于上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人文精神,则由于我国尚缺乏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根基,人们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意识仍处于封闭禁锢状态,缺乏如恩格斯所说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和乐观的战斗品格。其时,贫穷与落后、愚昧与苦痛,忧患与寻求萦绕于每一个爱国维新志士的心头,其文化品位,未能推进物质和商品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然而尽管如此,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反华工禁约运动,以及洋务运动的破产、中日甲午战争惨败“洗礼”的先进的中国人,已深深地意识到:中国人要站立起来,中华民族要求得独立和富强,首先要思想的醒觉和求得精神的解放。其时,以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麦孟华、汪康年、刘光第、康才常等为代表的年青的维新有志之士,毅然崛起、他们在接受了外来文化思潮的同时,对比现实和时局的变化,勇敢地担当起时代赋予的重担。他们既是学识渊博、感觉敏锐的智者,又是胸怀抱负、为国事担忧的思想家。在思想战线上,他们面对的不是欧洲中世纪教会、神权的统治,而是在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化行程中的中国的积贫积弱,人民群众仍处在麻木和愚昧状态之中;面对的是封建的专制主义以及维系这一制度的伦理纲常。他们从近代历史变迁大势中,深深体验到:光是提倡“经世致用”尚不足称,光凭实业救国也行不通,如果不从思想上,从文化精神上启蒙和教育群众,不挣脱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不打破沉重的精神枷锁,那新学就不能施行,新民只是句空话,维新也毫无希望。于是,他们吸取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创造等新的思想观念,对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规范和社会意识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康有为提倡“公羊三世说”,宣扬人权、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大同社会;陈宝箴在湖南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培育维新人才;谭嗣同高扬“心力”发出冲击封建君主伦常罗网的呼喊;严复对经验论、进化论哲学的鼓吹和对自由意志的赞颂;唐才常的宣传“民权”力倡维新;梁启超倡导“新民说”,以及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介绍和宣传,如此等等。宣传西学、变法维新,除旧布新、冲击罗网、鼓吹平等,高唱自由,开通民智,激发民情,极大地振憾了维系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维新派的先知先觉者们,把批判旧学与理论建设和宣传启蒙群众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把时代的进步文化思潮与民众的心理需求汇通为一体,构成了近代人文精神的有机网络,引起了中国社会思潮的急剧变化,充分体现了维新志士的先知先觉以及传播人文精神而战的可贵品格。这种人文精神,既促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文社会科学,诸如哲学、历史、政治、伦理学、人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的观念变革,也大大推动了教育事业、近代宣传媒介、出版事业和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维新变法的志士们,在新的社会思潮和人文精神的驱动下,重新审视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作了一系列开拓、探索和创造性的尝试。他们把开民智、新民德、启民情,把学习西方文化,唤醒民众,提高国民素质当作首要任务。还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就撰文强调:“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10]他们在发展文化教育、创立学校、废科举、变官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898年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创办,就是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发生的戊戌变法的产物。二、维新派在创办新学堂的同时,还大力提倡办各类学会和各种报刊。康有为说:“自强学会开后,海内移风,纷纷开会,各国瞩目”,“学堂学会,遍地并起”,“南学会”、“戒缠足会”、“延年会”等名目繁多,即使在港澳和日本华人中,其时也成立有戒鸦片烟会。
中国人自己办报虽从19世纪50年代已经出现,但到了19世纪中叶,在维新变法思潮的推动下,以宣传维新自强为宗旨的报刊才逐渐增多。仅戊戌变法前后,除了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外,比较知名者还有《国闻报》、《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报》、《采风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以及在香港创刊的《中国日报》、《中国旬报》等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创刊的报刊达30多家。它们对宣传维新变法,对启发民智,传播启蒙思想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随着维新变法思潮的高涨,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封建旧观念,旧陋俗的批判和斗争。严复环视中国的社会现状,深感讲文明少,旧恶习多,在痛斥封建专制的同时,极为痛心地指出:“中国礼俗,其贻害民力而坐令其种日偷者,由法制学问之大,以至于饮食居处之微,几于指不胜指”,而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5] 他强调必须从国家生民利益出发,清除种种恶习陋俗。他们反对吸食鸦片,指出烟毒“失业废时,耗财损身”,赌博“大则倾家荡产,小则争相斗欧,”其时,上海、广东、湖南、浙江、福建、天津等地均创办有不缠足会。而湖南的不缠足会则由维新先锋志士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成立,并订有简明章程,印有《戒缠足歌》等广为宣传,影响至大。他们还提出易服剪辫,革除古礼之跪拜,女子守贞节等的陈规旧矩。如熊希龄在长沙创立“延年会”,反对侈奢浪费,大吃大喝,提倡清洁卫生,健全体魄。谭嗣同为此十分高兴,遂作《延年会叙》道:“地球公理,其文明愈进者,其所事必愈简捷。”他赞赏西方人的办事讲效率、求实效精神,反对中国士大夫及官场的误时误事,浪费时间和生命的行为,指斥“宾客之不时,起居之无节,酒食之征逐,博奕之纷呶,声伎戏剧之流连忘返”,乃至“玩人丧德”、“倡优杂进”等种种弊端与陋习,而提倡精神文明和新的生活方式。随后,梁启超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上,公开撰文反对歧视压迫妇女的不文明行为,主张维护女权,提倡男女平等。总之,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维新变法志士,在近代人文精神的搡动下,以移风易俗相号召,把改革封建陋习与树立社会新风、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结合起来,通过报刊等宣传媒介,宣传新的生活方式,启发民众向旧陋习作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先举起了摒除陋俗、促进文明建设的旗帜,直接影响辛亥革命期间革命派所展开的移风易俗的斗争,其意义是巨大的。
三、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和艺术感悟的偏颇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为促进近代社会变革和启蒙教育群众,为宣传人文科学,振奋国民精神,所有维新志士都十分重视文学的革新创造,决计以文学为阵地,寻求普及文化的方式及发展流向,用以启迪民智,激发民情,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精神。他们,或致力于文体改革,提倡报刊体和白话文;或倾心于译介泰西文学,传递西方文明信息;或躬身从事诗文创作,倡言文学革命;或适时开展理论批评,提高通俗文学小说戏剧的地位和价值。为此,于上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它面向社会,普及民众,勇于探索、立意创新、有口号,有队伍和文化阵地,开始实现着我国古代文学向近代化转化的过程,也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必要的准备,成绩卓著,影响至大。
早在19世纪60年代,黄遵宪在《杂感》诗中,就提出过诗歌创作口语化要求,主张“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要求摆脱传统诗歌束缚,运用口语写诗,首先开创了“言语与文字合”的革新创作意向。至70年代,谭复生为宣传维新变法,于《时务报》上发表“报章文体”之说,提出“文体改革”,用以抨击古文、八股文弊端,为新体散文的出现开辟了道路。随后,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以上海强学分会和《时务报》为阵地,大力倡导新文体,而《无锡白话报》的创办人裘廷梁,则倡言“白话为维新之本”,于戊戌变法前后有效地配合了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宣传工作。直至1898年冬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旬刊)和1902年春《新民丛报》(半月刊)的相继出版,新文体已蔚然成风,使文体革新成为近代文学革新的一项主要内容。这一文体革新,有别于中国文学发展长河中的唐宋古文运动,或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其巨大的价值在于,它是在拯救民族危亡和求得民族独立富强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启蒙群众、传播新的社会文化思潮、寻求革命的内容与大众化形式为一体的情况下开展的。同样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体现了近代维新志士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全方位的创新意识和民族精神。
如果说维新变法期间,作为外交家的黄遵宪,从窥测世界文化变革的局势中,觉察到“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竞有左右世界之力。”他在《与丘菽园书》中说的这些意见,大力肯定诗歌创作的巨大教育作用和感化力的话,那么,还在戊戌变法前夕,作为维新派领袖的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蒙学报演义报合序》等著作中,已以启蒙教育、普及文化为圭臬,高度肯定着民间歌谣、特别是小说的作用和价值,指出:“西国教科书最盛,而书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他国且然,况我支那之民不识字者,十人而六,其仅识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学、教愚民,实为当今救中国第一义。”[10]此间充分体现了早年梁启超对教育事业和启发民智的关注和热情。值得提及的是,1897年10至11月间,严复、夏曾佑于天津创办《国闻报》,发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的“雄文”,殆万余言,大力介绍西方文化学说,宣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事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又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他们也从“使民开化”的角度,赞扬小说(说部)的感染力及其社会功能,堪称为我国小说理论史上的第一篇雄文。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其维新之志未歇,在东渡日本途中,偶然读到日本柴四郎(东海散士)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爱不释手,将其译成中文,作《译印政治小说序》,刊于1898年11月创办的《清议报》,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说”的概念,并认定“小说为国民之魂”,如云: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士,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农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11]又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2]这种把社会变革与小说感化力和造就国民灵魂联成一体的评论思维方式,迥异于以往评点式或赏析性的文学批评,其着眼点在于思想启蒙和社会文化的普及,从中我们可深深感到,作为爱国维新志士的梁启超, 虽身在他邦, 但依然心系祖国,以及继续以唤起民众为已任的高尚情怀。继出版《清议报》后,1902年2月,梁启超又以“动则其机势不可遇”的满腔热情, 于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发表“新民说”,“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13]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政治学说,并发表诗歌论著《饮冰室诗话》。是年冬,又创办《新小说》杂志,刊登新的小说和小说理论文章。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名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躬身创作的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及近代著名小说家吴趼人的小说等均刊登于此。《新小说》杂志成了我国近代初具规模的新型小说刊物,其价值和意义,正如阿英先生在《小说闲谈·清末小说杂志略》中所说:“《新小说》可称之为‘开山祖’,小说地位之提高有赖乎此。《小说丛话》之开辟,亦以此为基点,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洪水祸》、《痛史》、《九命奇冤》、《黄绣球》、《新中国未来记》等,固自有其不可磨灭之时代价值;惜乎兼刊侦探,不免是白璧微瑕。”总之,近代维新变法的思想家们,为了使文学成为改革社会宣传唤起民众的有力武器,竭力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强化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政治倾向,成为近代文学革新运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经过维新志士们的共同努力、提倡和实践,既提高了“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的地位,也首次冲破儒道教化和“以劝善惩恶”为主旨的传统文艺观及随感式的评论思想模式,加上有识之士在开展维新活动和译介西方近代文化学术著作的同时,高举批判旧思想、批判“桐城派”空疏之学的旗帜,并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口号相号召,遂形成了上个世纪之交强大的文学革新思潮。这一革新思潮,不仅强化了作家创作的民族意识和国民意识,有效地促进了文学观念和评论思维方式的转变,而且带着明显的中国文化的开放格局,密切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社会和人生的联系,为实现现代文学的普及、通俗化与大众化迈出了新的可喜的一步。但另一方面,近代维新志士,在从事文学革新、提倡政治小说和阐述小说的社会地位时,又存在以表自异和简单化的倾向,存在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等缺点。又如,早期新诗创作中“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14];在倡导文体改革时,对桐城派及其“义法”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强调小说的功能时,却把小说视为新国新民之本,甚而把“造就新社会的希望,寄之于小说创作”;在宣传维新变法鼓吹革命时,却又忽视了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的差别,等等,充分暴露出他们的举措和思维方法的片面性,即注意了批判一种错误倾向却又走向了另一种倾向,给当时及尔后的文学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诚然,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艺术,离不开政治,与时代和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文学决不是政治和思想观念的说教,决非哲学和道德伦理的“宣言”,而是一种感悟和审美的意识形态,是透过语言艺术在形象化的描绘中去展示社会心理和人生情感之真谛,让读者从审美活动中接受新思想,培养新的精神境界的意识形态。在维新变法活动中,梁启超曾扬言:“过渡时期必有革命,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14]又说“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我民。”近代维新志士们以开通民智、启发民情为已任,视培养民力、民智、民德、民情作为振兴国家的头等大事,充分表达了他们的爱国为民的赤诚之心,体现了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革新及时代精神。但文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种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变革规律。这一点维新志士们缺乏应有的认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由于时代的推搡,维新志士较多地注意了“革命”和反传统的一面,而缺乏对我国国情和传统文化作细致分析的另一面。我国是一个处在长期封建统治下的国家。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升和发展时期,也曾创造过许多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继承和借鉴这些优秀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发展民族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可惜维新志士们没有深刻注意和认识到这点。例如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杂志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猛烈抨击我国古代小说,把“陷溺人心,败坏国民道德”,甚至把宣扬升官发财的状元宰相思想、迷信落后的妖巫狐鬼、淫靡无聊的佳人才子思想等的“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统统归咎于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这种绝端化的思想方法,虽然遭到同时代小说评论家获葆贤,黄摩西,天僇生等人的反对,提出“文学之倾向于美,属于审美之情操”,必须“以文学之眼观察”小说[15],以及提出我国古代小说乃扎根于自身的生活土壤,有其独特的内容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形式的特点等,意想纠正梁启超论述的偏颇。但这些观点,已为文学的“左右世界之力”、“新民”、“新政治”和“新国家”的理论所掩没,影响不大,纠正不力。二、与情绪之激进和“一哄而起”的思想方法相关。无可讳言,维新志士饱含的对旧文化的愤激之情及高涨的革命情绪,容易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并产生心灵的共鸣,但另一方面又易于出现举动的浮躁和言论的空谈。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本已愤慨之极,甚至在太平洋舟中读《桃花扇》亦颇有故国之感,而酸泪盈盈。[16]至日本后,梁启超结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曾“与孙君游数月,乃大为所动,几尽弃所学,由是乃高谈破坏”,表现为鼓吹革命,破坏现存文化的高昂激进情绪,所谓“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17]壬寅秋,即1902年秋天,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梁启超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1902年11月14日在日本横槟创刊的《新小说》上,正是当时政治激进和情感高昂的反映,这怎能不产生思想方法的偏颇和片面的呢?三、未能营造一个学术争鸣的时代氛围。维新变法期间,有如:怎样吸收西学创造我国的新文化,如何学习西方文化发展新诗;又如在进行文体革命中怎样对待文言文和美文,在提倡政治小说和提高小说的社会作用时必须注意小说的审美性、艺术性,以及如何正确评价我国古代小说的地位和价值等等,观其时,均有不同的意见和争论,只是未能创造学术争鸣的风气,使之向完善的方面发展,这亦是时代的局限使然,当然不能苛求,但今天回顾总结教训还是必要的,十分有益的。
[收稿日期] 1999—8—3
标签:人文精神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严复论文; 天演论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时务报论文; 清议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