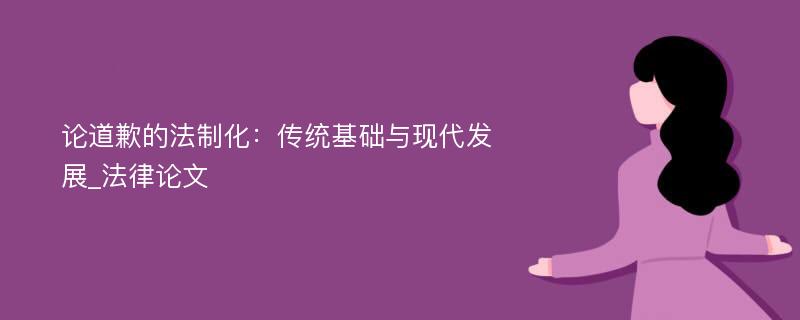
论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传统基础与现代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赔礼道歉论文,传统论文,基础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已于2014-09-23 11∶15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40923.1115.004.html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4.05.02 中图分类号:D911.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823(2014)05-0392-10 我国《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先后将赔礼道歉规定为一种独立的民事责任方式,在救济名誉权、肖像权等民事权益损害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责任方式产生于中国道德传统,并被东亚甚至西方诸国借鉴,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却屡屡遭遇争议。如何认识赔礼道歉责任的传统基础以及现代发展中的种种争论,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完善其法律适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赔礼道歉的传统基础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它维护着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文化基础和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1]1。作为社会纠纷处理方式的赔礼道歉,之所以在我国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明确纳入立法范畴,不仅决定于我国两千多年的礼教文化传统,更是名誉法益社会性的重要体现。 1.赔礼道歉的文化基础:儒家礼制传统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所谓“赔礼”是指向人施礼认错,而“道歉”则是指因做错事而表示歉意①。在现实生活中,赔礼道歉是化解社会矛盾、缓和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这与我国儒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传统社会中,礼是社会规范的重要依据,其核心在于长幼有序、上下有差,违反这些规则即为“失礼”,予以纠正(服礼)的主要途径即是道歉[2]。特别是在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儒家行为规范成为法律的重要渊源,儒家经典成为解释法律的重要依据,礼制成为重要的社会规范。在之后数千年的发展中,虽王朝更迭、法典重修,但礼的精神在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却从未消失过,它铭刻在中华万千子民的内心里,代代相传[3]。 赔礼道歉的规范方式即产生并发展于儒家礼制文化的传统土壤之上,并深植中华民族子民的观念之中。因此,赔礼道歉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讲礼仪、爱面子传统道德观念的国家里,往往容易取得纠纷顺利解决、当事人和好如初的双赢效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②。 儒家文化向来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意图通过教化改变人心的方法收潜移默化之功,因此强调观念的内生性与自发性。道歉源于道德责任,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而产生内疚感,从而向受害人承认错误、表示歉意。“承认错误、表示歉意”主要是通过言语完成的,这是赔礼道歉的内核。同时,随着“以礼入法”的不断深入,礼制亦借法律及社会制裁的力量来维持。一个人有非礼的行为,所得反应不外乎舆论的轻视、嘲笑、谴责或不齿,《礼记》所谓:“在执者去,众以为殃。”[1]348在此基础上,道德责任在化为法律责任的过程中,不是内核的改变,而仅仅是增加了法律外衣而已[4]。这样,传统意义上的赔礼道歉即兼备内生性和强制性的双重特征,其内生性通过道德教化而加强,强制性则依靠礼制规范来保障。对受害人来说,赔礼道歉具有心理补偿功能;对侵害人来说,赔礼道歉具有自我补偿和道德恢复功能;对于社会来说,赔礼道歉有助于道德整合、法律权威再建,发挥着惩罚和教育功能[5]12。赔礼道歉的法律化并非因混淆道德与法律责任而产生的异化,而是我国传统社会“礼”与“法”相克相生的对立统一。 2.赔礼道歉的功能基础:名誉的社会性 赔礼道歉不仅具有矫正遭受侵害的社会秩序的功能,还发挥着救济他人名誉损害的重要作用。我国自古就有重视名誉的优良传统,欧阳修在其名篇《朋党论》中曾谓,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体现了对保持良好名誉的内心需求。墨子在《修身》篇中曾言:“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根据通说观点,名誉是对人的道德品质、能力和其他品质的一般评价。名誉有无损害应以社会上对个人评价是否贬损作为判断之依据,而这种看法的判断是以言论的受众为中心的(recipient-oriented)。名誉由权利人所处社会所形成,并在社会中找到其实现基础与意义。 名誉的定义受到社会价值和观念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可能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王泽鉴教授指出,名誉系一种客观社会的概念,因社会的价值观念及认知的变迁,得有不同的评价,具有时代性[6]177。因此,名誉损害的救济当然不能脱离某一社会一般公众的传统观念,名誉损害救济手段的选择只能从本国社会中寻找出路。换言之,名誉损害救济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主体所在社会对名誉的观念根基与普遍认知,并受社会主流文化的深刻影响。 基于我国传统的“熟人社会”基本结构与家庭聚居生活模式,名誉对于自我实现与社会交往的意义更加不容小觑。社会共同体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基础,成为确定名誉是否受到侵害以及恢复名誉方式的重要标准。由于传统文化观念根深蒂固,法院的判决常常被看作单纯的外在强制,难以纠正公众对被害者已经扭曲的名誉认知。相较而言,侵权人赔礼道歉能够使被害人迅速占领道德评价的至高点,进而从根本上挽救被不当侵害的个人名誉。对被侵害者而言,侵权人的赔礼道歉更有助于抚平其受到的精神伤害。 在目前我国法院注重调解结案的背景下,赔礼道歉的有效运用可以有效提高调解的成功率。事实上,法院鼓励诉讼中的赔礼道歉不但有利于重建道德,也有助于纠纷的迅速和彻底解决,做到案结事了。200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不仅契合我国数千年的社会文化传统,也为未来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中国发展与比较研究 在现代民法中,恢复原状是救济民事权益损害最为适宜的责任方式,而赔礼道歉被认为是恢复名誉的重要途径。名誉损害的非财产性决定了金钱赔偿在救济权利损害方面的局限性。在我国,不少被侵权人最为迫切的诉求是“讨一个说法”,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美国一项实证研究表明,促使原告提起诽谤诉讼的主要动因在于洗清名誉受损的冤屈[7]791。由于道歉是一种受文化因素制约及影响(culture-bound)的救济方式,各个国家对于赔礼道歉作为责任方式态度上的差异体现的并非制度选择的对错或优劣,而是根植于国民性格的传统社会文化[6]527-528。不过,随着社会调整方式多元化以及法律诉求价值的多样化,赔礼道歉也在素来强调“自主意识”的西方世界逐步获得了认同。 1.我国关于赔礼道歉责任的立法与实践 在我国现行立法中,首次确立赔礼道歉法律化的当属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在总结民事活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该法设立专章统一规定“民事责任”(第六章),并于该章第四节单独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根据第134条规定,赔礼道歉为十种民事责任承担方式之一。该法既独创民事责任方式独立规范之先河,又首开赔礼道歉法律明文化之先例。该法第120条明确规定,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等受到侵害的,权利人有权要求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按照参与起草《民法通则》的专家学者解释,之所以将赔礼道歉规定为民事责任承担的一种方式,主要是总结了革命老区的经验,认为“民事纠纷有些就是一口气,赔礼道歉也就解决了,作为民事责任提高到法律高度,有利于解决实际中存在的这种问题”[8]245。民法学者对于《民法通则》的这一做法也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其有利于缓和矛盾、切实保护受害人的权利,符合我国的民族传统,是民间调处纠纷经验的法律化、制度化[9]445-446。此后,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先后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著作权法》、《国家赔偿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得以确立。 由于赔礼道歉所具有的深刻的道德烙印,在《侵权责任法》的立法过程之中曾引起广泛争论。王利明教授认为,赔礼道歉表明侵权人认识到其行为的不当,同时也表达了对受害人人格尊严的尊重,本身可以发挥一种抚慰的功能,可以澄清是非曲直,表明了加害人为自省而付出的努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抑和减缓诽谤和侮辱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促进当事人之间的和睦相处[10]499。但有学者指出,强令加害人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道歉,侵害了加害人的消极言论自由,即违反宪法上良心、思想、信仰自由的精神,不合比例原则[11]。还有学者认为,判决加害人向受害人赔礼道歉无法强制执行,应废弃此种法律责任形式③。同时,也有学者从功能的视角以及民法的道德性等角度出发坚决捍卫赔礼道歉的合法地位④。2009年底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完全继承了《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于第15条明确将赔礼道歉规定为独立的侵权责任方式。 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数次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赔礼道歉的适用范围与执行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1993]15号)第10、11条规定了赔礼道歉的承担与执行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号)第8条规定,侵权致人精神损害的情形可以适用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自1985年以来刊登的有关人格权的18件判决中,有16件判处或责令加害人消除影响,为受害人恢复名誉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12]。另外,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关于媒体侵权案件的实证调查,法院认定构成侵权的案件中,合并适用责任方式的判决达到100%,适用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判决达到100%⑤。由此可见,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在实践中得到了非常广泛的适用,特别是在调解结案时,赔礼道歉对妥善解决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东方国家(地区)肯定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传统 众所周知,东方国家素有重视“面子”、珍视名誉的传统,多数国家和地区均设有名誉权救济的特殊责任方式——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实务上通常表现为赔礼道歉,或称道歉广告、道歉启事、谢罪广告等。长期以来,名誉之恢复一直都是名誉权损害中最为常见的诉讼请求,许多受害者甚至选择名义上或象征性赔偿而体现其对经济利益的漠视,但赔礼道歉的诉求常常是无法妥协的底线。 日本民法第723条规定,名誉权受到侵害的,除可要求损害赔偿外,还可以同时“命为恢复原状的适当处分”。由于仅通过金钱赔偿通常无法弥补受害者所受到的名誉损害,因此根据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民法上肯定了恢复原状的救济方式,并与抚慰金赔偿共同构成名誉权救济的责任方式。根据日本民法起草者之一的梅谦次郞教授的观点,所谓的“适当处分”可以包括道歉广告、当庭道歉、交付道歉信、侵害名誉的撤回等,但实践中最为盛行的主要是道歉广告。根据实践经验,道歉广告通常都是指定刊载的报刊版面,并规定刊载的周期、文字的大小、使用的语言等具体方式,由加害人向受害人承认名誉损害的事实,并刊登以道歉为主要内容的文章[13]195。通常情形下,道歉广告的主要内容由确立名誉侵权责任成立的判决书加以指定,且得依替代执行方法加以强制执行。 同处东亚的韩国民法借鉴日本上述立法例,于民法典第764条规定,侵害他人名誉的,法院除要求损害赔偿外,“尚得依被害人之请求,命其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实践中,强制赔礼道歉被认为属于“恢复名誉之适用处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213条规定了损害赔偿基本原则,无论何种财产或人格权益受到侵害,被害人均得请求恢复原状。该法第195条第1项后段明确规定了适用于名誉损害的特别救济方式,即“得请求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该条立法理由明确指出,名誉被侵害“非仅金钱之赔偿足以保护者,得命为恢复名誉之必要处分,例如登报谢罪等”。因“适当处分”为不确定概念,实务中原则上由法院就个案认定,既可由加害人登报道歉,亦可命败诉人负担费用,刊登澄清事实的证明或刊登判决的重要内容。 3.西方国家对赔礼道歉责任认定方式的借鉴 在西方国家,通常不得以赔礼道歉作为恢复名誉的救济方式,以强调个人意志、内心信念自主,而东方国家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以及道德教化。相较于东方国家在恢复名誉中掺杂了诸多道德因素,西方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公布判决、撤回报道等方式以求受到损害的名誉恢复原状。在德国,依据民法第249条规定的恢复原状请求权,原告可主张不实报道的撤回(Widerruf),不过该种责任方式仅适用于事实陈述,而无法适用于意见表达的情形。在美国,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均普遍认同,单纯的损害赔偿根本无法完全救济受害者的名誉损害,涉及回应权、撤回报道、更正报道、宣示性判决等名誉救济的改革方案更是层出不穷,而且许多建议已在不少州纳入了制定法规范的层面。但这并不代表西方完全排斥赔礼道歉的价值,发生争议的只是法院是否有权力强制要求被告进行赔礼道歉。 在英国,1996年的诽谤法案第2条明确规定了赔罪提议制度(offer to make amends)。根据该规定,因发表具有诽谤性陈述而被起诉的被告,可以申请对诉争陈述进行适当的更正或者向受害方表达真诚的歉意,也可以申请以合理可行的方式公开更正或道歉的内容,或者支付合理的补偿金。如果原告接受了被告的赔罪提议,其可以放弃起诉或继续诽谤诉讼程序,但有权依法要求强制执行赔罪提议的内容。如果双方就提议付诸实施的具体方式达成一致,原告可以向法院申请执行命令;如果双方就道歉、更正的方式无法达成一致,被告可以依照相关规定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在公开法庭或者与发表相类似的方式作出赔礼道歉或者更正的声明。不过,即使法庭签发了赔罪提议的执行命令,仍不得强制被告进行赔礼道歉或者发布更正,而仅能强制公开判决摘要。如果双方无法就支付的补偿金数额达成一致,法庭可以根据提议执行的内容、更正的适当性、赔礼道歉的真诚程度以及在该情形下公开的方式是否合理等因素相应增加或减少应予赔偿的数额。如果被告提出的赔罪提议未被原告接受,该事实可以作为诽谤诉讼中被告的一项抗辩,但被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诽谤性指称是针对原告且内容不实的情形除外⑥。从这些规定中不难看出,英国诽谤法上的赔礼道歉更加强调被告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只有被告的提议能够启动该项程序,而且倾向于通过双方当事人以某种协商的方式来实现,目前还并非一项原告可得请求的救济方式。为了避免妨碍新闻自由的争议,英国法院在强制执行方面表现得非常保守,其结果就是大大限制了赔礼道歉和更正报道在实践中应当发挥的实际效用[14]270。但不容置疑的是,英国诽谤法在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以及规范化过程中所作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近年来,加拿大两省专门就道歉的效力立法,并鼓励政府、官员、公众大行道歉之风,以促进民事纠纷尽快完结。先是2006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以下简称B.C.省)议会以成文法专门通过的《道歉法案》(Apology Act of 2006 British Columbia,S.B.C.2006,C19)。继而2007年萨斯喀温省也在其证据法中就道歉的效力作专条立法( Evidence Amendment Act,Saskatchewan,S.S.2007,C24)。此外,立法者们还酝酿通过一部《统一道歉法案》,以期适用于全加的民事法领域[2]。赔礼道歉对于民事纠纷的解决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赔礼道歉这一发源于中华传统礼制文化的制度,不仅在东方国家和地区立法中获得了普遍认同,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而且在部分西方国家也开始蕴育、萌芽并茁壮成长。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不仅体现了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救济人格权益损害方面的共同需求,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和”文化因素在平衡民事权利冲突以及建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中的积极作用。由于赔礼道歉的具体适用涉及当事人的内在良心与人格自由,这种极富道德意味的责任方式要想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立足扎根,还需要面对来自宪法的拷问。 三、赔礼道歉的违宪争议: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的冲突 名誉侵权诉讼深受双方当事人掌握证据的多寡与证明力的影响,即使被告媒体内心确信报道内容真实,依然有可能因举证不足或其他要件的缺失而承担败诉后果。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要求被告作出悔罪的意思表示,而这种意思表示可能与被告内心的真实意愿有所差异。为了保障人格尊严并促进人格自由发展,现代各国宪法均将言论自由或良心自由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基于传统道德原则产生的赔礼道歉责任与现代保障个人良心自由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受到关注,并成为违宪审查的重要内容。 1.日本的合宪解释 道歉广告面临违宪的争议,首先在日本实务中变为现实。1952年,被告在政治竞选活动中通过媒体指称原告存在贪污行为,法院判决名誉侵权成立,且要求刊登道歉广告。判决一直上诉至最高裁判所,主要争议问题即在于法院命被告刊登道歉广告是否违反日本宪法第19条所保障的“思想及意志的自由,不受侵犯”的基本权利。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要旨主要包括三点:①命败诉被告于报刊等刊登谢罪广告系民法第723条规定的“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之一种,不仅已为学说判例广泛接受,亦为日本国民生活所司空见惯。②一般情形下,谢罪广告应依诽谤诉讼判决由道歉人意思决定,强制执行的场合应当符合民事诉讼法“适于强制执行”的情形,如仅止于说明事实的真相、表明道歉之程度,尚属可替代行为而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间接强制加以实现。③本案中,判决要求被告于大众媒体发表其所公布事实为虚伪、不当的谢罪广告,并未对其课加耻辱性或痛苦性的劳苦,未伤害伦理上的意思或良心自由,与宪法意旨并无违背。在该案判决中,藤田、垂水两位法官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从未认真考虑过良心自由的日本国民应当对此进行深刻反省⑦。学说上亦不乏认为其违宪的观点⑧,尽管最高法院对道歉广告采取了合宪解释,但实务上对该责任方式的适用则更为谨慎。 日本判决指出:“如果受到损害的名誉已经恢复或名誉损害得到足够经济赔偿的时候,或名誉损害行为的反社会程度轻微、伤害较小时,可以认为不责令刊登道歉广告。”⑨另外,在一些原告也有错误或原告社会评价降低程度有限的案件中,道歉广告的请求未获得法院允许。司法实务中对于道歉广告的谨慎态度已使得其适用范围大大缩减,主要局限于“性质比较恶劣”的名誉诽谤案件,而且多流于形式。 2.韩国的违宪解释 韩国民法第764条同样受到了来自宪法的质疑。在一个涉及名誉权的案件中,被害人以《女性东亚》所刊载的文章侵害其名誉权为由向首尔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包括谢罪广告在内的责任方式,但因系争规定系属违宪被驳回,原告遂向韩国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宪法法院于1991年以全体一致的见解作出判决,认定谢罪广告因违背人民良心自由而违宪。因为作为对国民基本权利限制的谢罪广告“手段的选择非但不适合目的的达成,且其程度亦将过重而逾越韩国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的比例原则的界限”。如果民法第764条规定的“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包含谢罪广告在内,则违反宪法意旨;如果解释上未作此超出表征意义的扩大解释,则属符合宪法[6]510-511。 韩国宪法法院主要以国际人权公约等作为论证依据,相较于日本而言显然超越了东方国家固有的文化传统,而向更为宣扬个人自由的西方宪政理念看齐。由于名誉损害后果的表现以及救济方式的妥当性深受各个国家文化传统、社会观念的影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虽然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使得西方法治观念深得人心,但数千年的东方传统仍具有不可忽略的统制力。贸然以舶来之理念认定谢罪广告违反宪法良心自由,是否对受害人名誉损害的救济给予足够重视等问题仍值得商榷,其妥当性本身在韩国亦难免存在争议⑩。 3.我国台湾地区的合宪解释 在我国台湾地区吕秀莲诉《新新闻周刊》一案中,被告媒体及其他6人被判将法院审定的“道歉声明”、判决主文及理由刊登于《中国时报》、《联合报》、《自由时报》、《工商时报》各一天。被告不服,向大法官会议提起释宪申请。大法官会议于2009年4月3日作成释字第656号解释,肯定了道歉声明作为一种“恢复名誉适当处分”的合宪性,并附加了合宪性解释的限制条件,即不得涉及人格尊严之侮辱(11)。该解释的核心在于,为了恢复受害者名誉而强制要求加害人作出道歉声明,是否逾越了必要比例而侵害加害人不表意的自由。 该解释指出,名誉权与不表意自由均涉及人性尊严与个人自主,宪法上应予平等保护。为实现维护个人主体性及人格之完整,为实现人性尊严所必要,“民法”第195条规定,名誉受损害者,除金钱赔偿外,尚得请求法院于裁判中权衡个案具体情形,藉适当处分以恢复其名誉,而道歉声明即为实践中通行的方法之一。同时,不表意之理由多端,涉及道德、伦理、正义、良心、信仰等内心之信念与价值,攸关人民内在精神活动及自主决定权,乃个人主体性维护及人格自由完整发展所不可或缺,亦与维护人性尊严关系密切,国家的强制限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的检验。该解释从目的正当性及限制合比例性两个方面详细论证了赔礼道歉并不违反宪法不表意自由的理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12)。 尽管大法官会议通过合宪性解释将道歉声明作为“恢复名誉适当处分”方式之一种,整体上与宪法并无违背,但对于其适用却作了审慎的限制,反映了“道歉”这种已深植人民内心数千年的恢复名誉方式在面临民主人权新思想洗礼后的前途命运。大法官们以人性尊严之维护为立论,反思了强制公开道歉与现代文明思想之间的微妙冲突。首先,仅允许其以最后手段之姿使用,也就是只有在命加害人负担费用、刊登澄清事实声明或判决内容等手段仍不足以恢复被害人名誉时,始准诉诸此一最后手段。另外,即使道歉广告系为必要,仍不得以“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损及人性尊严”的方式为之。 4.赔礼道歉合乎我国宪法精神的理由 赔礼道歉责任方式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并不存在唯一、确切的答案,关键是该种责任方式是否符合本国传统社会文化与现代法制观念的根本基础与发展趋势。由于我国欠缺有效的宪法实施机制,主张赔礼道歉违宪的观点主要来自学者的论述,主要理由无非包括三个:一是此种责任方式侵犯了加害人所谓的“良心自由”或者“不表意自由”;二是这种责任方式不当地将道德上的义务提升到法律义务的层面;三是强制赔礼道歉无异于要求加害人公开自我侮辱,严重侵犯人格尊严。而在笔者看来,这些理由均力度不足、论证欠周。 首先,侵害“良心自由”并非当然地欠缺正当性。正如我国台湾地区“司法院”陈新民大法官在释字第656号解释中独自发表的意见中所言,持此论者(侵害不表意自由)似乎忽视了任何法律后果都不免带有强制的色彩,甚至没有强制力就没有法律的效力。法治国家的真谛乃在于以法律之力与法官判决之力取代原告与被告的意志以及其所实施的“力”。所有法律后果的特色即在于“无庸获得内心同意”的强制主义原则。 在多数文明法治国家,针对公民人身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施加违背本人强制力的情形比比皆是,民法中人身专属性极强的债务亦有其存在理由。所谓良心自由的价值虽难说劣后于上述人格法益,但说其较之更为重要也显然没有理由。若经法官确认侵犯他人名誉且必须登报道歉方可恢复名誉时,侵权人竟可以援引个人良知抗拒,显然是对法律强制力的一种选择性失明。如果在这种价值取舍上不能把握其分寸,岂不是赞同所谓“东条英机式的坚持”(13)?在我国法的语境下,这种理由的说服力就显得更加微弱了。“良心自由”并无明确的宪法依据,虽可暂在“人格尊严”的庇护下存身,但其道德意味却一点都不比赔礼道歉弱,即使在台湾地区,也是将言论自由条款扩张解释包括“不表意自由”在内来证成。如果论证基础本身在法规范上的正当性或有效性尚需继续商榷的话,以此为大前提的演绎结论无疑有“空中楼阁”之嫌。 其次,道德义务论者则显得更加牵强。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为习法者所熟知,并经数千年的争论仍难分伯仲。但最基本的共识是,二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的,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认为赔礼道歉仅能在道德场域发挥作用的观点(14)显然过于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区分。诚然,赔礼道歉确实来源于道德准则,准确地说是来源于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道德文化传统,但将之纳入法律责任方式并非天然就欠缺正当性,而是看这种责任的“转化”是否符合法治的一般原则与公众的普遍观念。从立法目的观之,这种责任方式的设立与其说是源自于道德义务的强化,不如说是出于受害人名誉权救济的考虑。强制的赔礼道歉并非简单的报复行为,而是法律责任和社会诉求的共生物,是一种具有人道性质、深富道德建设意蕴的对越轨行为的矫正方法。严格地讲,赔礼道歉的责任化确实与加害人的基本权利存在冲突,但此种冲突本身是宪法和法律所准许存在的,甚至是无法消除的,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将这种限制控制在“合比例”的限度内。从这个角度讲,赔礼道歉责任方式是否违宪并非如学者所声称的那般“显而易见”。另外,名誉损害的社会面向决定了救济手段的选择只能从本国社会中寻找出路,因此以西方的法治观或者道德观来检验中国的名誉权救济方式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虽然侵权人道歉(最好是“衷心认错式的道歉”)是否能作为弥补名誉损害后果的良方尚有待实践检验,但至少也是一个极少数的“道德迈入法律”的适当门径(15)。某项制度在一个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无法容忍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却可能喜闻乐见。有关赔礼道歉的讨论亦是如此,利益衡量必须深植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土壤才能公正地评判其利弊得失。至少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这种道德义务的法律化确实强化了名誉损害的救济实效,而且为社会公众所广泛接受。这种违宪性的主张虽不能说注定徒劳无功,至少是任重道远的。 另外,主张强制赔礼道歉侵犯人格尊严的观点表面上也显得颇为有力。我国台湾地区许宗力大法官认为,强迫一个不愿认错、不服败诉判决的被告登报道歉,对其所造成的人格尊严的屈辱,与强迫他(她)披挂“我错了,我道歉”的牌子站在街口,或手拿扩音器对着大庭广众宣读“我错了,我道歉”的声明,委实说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充其量只是百步与五十步的程度差别(16)。笔者认为,此种声称赔礼道歉“侮辱人格尊严”的观点显然是过于夸大其辞了。既然我们承认“道歉是人类建构文明、和谐社会的重要元素之一”,那么勇于承认错误、真诚地向因其行为受到损害之人表达歉意,就应该是这个社会最为广泛的共识,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实施损害他人不法行为时多数人会选择接受道歉的责任方式,尽管不一定必须真诚。许大法官将赔礼道歉“偷梁换柱”为“不自愿的赔礼道歉”,其论证逻辑存在着重大的误差。因为现实实践中,究竟多大比例的诽谤诉讼败诉方属于“宁折不屈”的类型,显然是应当首先判定的事实问题。判断某种法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乃反映出绝大多数国民所产生的“法感情”(Das Rechtsgefuhl),并以普遍性的社会价值及目的性来予以决定,绝对无法兼顾到少数特异价值观之国民的好恶,因此只能是一种“普遍的法感情”。 既然赔礼道歉在实践中得到了如此广泛的适用,说明它符合绝大多数人的社会观念。由于无辜的加害行为伤害的不仅是受害人的权益,还包括加害人的良心自身,通过强制赔礼道歉尽可能地唤醒侵权人的良心,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侵权人尊严的恢复而非侵犯[15]。而根据一般人的立场观之,承认犯错并向他人道歉非但不是对人格尊严的侮辱,反而可能是对其社会评价的提升。 四、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现代价值与适用完善 相较于韩、日等国只是在实践中将赔礼道歉作为“恢复名誉的适当处分”的方式,我国才是坚持此种责任方式最为彻底的国家。我国《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不仅先后明文确立了赔礼道歉作为责任方式的地位,而且仅具有单纯学术价值的违宪论调在实践部门的坚持甚至热捧面前显得有些单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赔礼道歉责任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并妥善解决其适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1.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独特价值 本文对于赔礼道歉的辩护立场并非对实践做法的简单盲从,而是以其独特的现代价值为基础的。首先,赔礼道歉是救济受害者名誉的最适当、有效的责任方式。诚如学者所言,赔礼道歉责任作为一项与现代精神损害制度不同的、真正的非财产之责任方式,对于科学健全且逻辑自洽的民事责任体系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12]。由于要求加害人向受害者承认错误的法律责任唯独存在于名誉损害的领域,可见赔礼道歉的正当性及必要性是从救济受害人的角度而言的。不过,本文并不认同“对于精神性损害用金钱损害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既不道德也不充分”(17)的极端观点,也不盲从于“金钱赔偿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理性的求偿意识”(18)的绝对意见。尽管名誉损害常常导致精神的痛苦,但其本质却在于社会评价的不当降低,这是设定名誉权救济方式的最基本的前提。因此,赔礼道歉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抚慰受害人愤怒的情绪或者受伤的心灵,而是向社会宣示被告指称的失当,以挽回社会公众错误的评价前提。从这个角度讲,赔礼道歉虽难说更为有效,但却足够“对症下药”。实际上,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是立法者经过慎重权衡之后确立的,并非想象中那般是对道德与法律的草率混淆。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为激励被告主动进行赔礼道歉,以有利于纠纷解决和社会和谐,可以考虑在被告进行赔礼道歉时适当减轻其责任[15]。因为损害赔偿本来就是名誉权救济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侵权人赔礼道歉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减轻了受害者的精神损害。 从表达自由与名誉权保护协调的整体制度架构观之,赔礼道歉显然也更好地兼顾了原、被告双方的利益考量。名誉权救济的责任方式并非孤立的话题,而是平衡冲突基本权利的重要一环。违宪论者从极富道德伦理色彩的“个人内心良心”入手,却忽略了侵害名誉权的最重要主体——新闻媒体。当以法人形态存在的媒体作为赔礼道歉主体的原型时,以良心自由为论证理由的观点顿时失色不少。对于新闻媒体而言,对记者的刑事追诉与高额的经济赔偿才是引发报道“寒蝉效应”的罪魁祸首。相较而言,赔礼道歉不仅更好地救济了受害方的名誉权损害,而且对于媒体所造成的伤害实际上微乎其微。在缺乏赔礼道歉传统的英美国家,为了挽回受害人损失的名誉并吓阻媒体的一再犯错,陪审团不得不判决屡创纪录的高额赔偿金,并由此引发过度限制言论新闻自由的现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许多国家均在新闻法或相关法规中引入了所谓的“回应权”或“更正报道”制度,以分散金钱赔偿在名誉权救济中过于繁重的使命负担。 事实上,我国台湾地区陈新民大法官在释字第656号解释的意见书中敏锐地指出了解释主文并未考虑到自然人与媒体被告的区分,而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明显为新闻媒体提供了绝佳的“减压”机制。另外,加害人赔礼道歉主动认错有助于纠纷的解决以及调解的成功,并成为减轻加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理由。根据《名誉权解答》第10条规定,赔礼道歉的范围应当限制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之内,在名誉权的救济中保留了宝贵的弹性空间(19)。例如在一则案件中,侵权文章发表于某报刊第三版,道歉位置在第三版即可,而无须要求须在头条位置(20)。从整个诽谤法制度来看,赔礼道歉在平衡双方利益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仅仅从赔礼道歉这个制度入手分析,就会因“身于此山”而无从领略该制度的真正面目。事实上,赔礼道歉的救济方式与作为名誉权本身基础的人格尊严完全契合,因为真诚的歉意可以助益于原告受到伤害的人格尊严的修复,进而获得原、被告双方人格利益的双赢[14]270。 2.赔礼道歉责任方式的适用完善 由于赔礼道歉责任的实现需要责任人内心的自省,其实际的执行成为法官面对的难题。我国司法实践充分考虑了赔礼道歉强制执行的不现实性,并明确规定了替代的履行方式。《名誉权解答》第11条规定:“侵权人拒不执行生效判决,不为对方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公告、登报等方式,将判决的主要内容及有关情况公布于众,费用由被执行人负担,并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第六项的规定处理。”换言之,非自愿的赔礼道歉将转化为财产上的责任,即由责任人承担刊载判决主文的费用。当然,赔礼道歉强制执行现实性的缺失并不能成为否定其正当性的理由。在民事或者行政执行程序中,几乎所有国家均明确区分强制履行与替代强制履行的执行方式,这就表明法律义务或责任并非全部具有可强制执行性。在民事合同法中,诸如具有人身性质的债务并不因无法强制履行而降格为道德上的义务或者自然之债。通过公布判决主文的方式来替代赔礼道歉的强制执行,不仅避免了对侵权人不表意自由的过分干涉,又达到了公之于众以正视听的效果,司法实践中应当予以坚持。 不过,我们也不能过分夸张司法实践所面临的困境。其一,现实中多数侵权人是主动进行赔礼道歉的,拒不履行赔礼道歉判决的应属于极少数情形,因为极个别案例去质疑适用于绝大多数案件的规则,显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其二,刊载判决书无法替代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法院判决公开的正当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将赔礼道歉完全由刊载判决取代,实践中必然导致所有的名誉侵权案件原告均要求公布判决,不仅对加害人造成更为繁重的经济代价(21),而且新闻报刊将不堪重负而成为“名誉侵权判决汇编”,削弱其本来功能。而且,长篇累牍且晦涩难懂的判决书很难引起社会公众的阅读兴趣,相较于简明扼要且精悍短小的道歉广告,其救济名誉的现实效果实难相提并论。 另外,司法实践中可以妥善避免因赔礼道歉而造成人格侮辱的现象。因救济名誉受害者的权益而对责任人施加相应义务固然合理,但却不得以伤害加害人的人格尊严为代价,以免赔礼道歉沦为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的合法手段。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均通过对该责任方式的适用施加“未涉及加害人之自我羞辱、污蔑等损及人性尊严”的条件限制,进而对该种责任方式作出合宪解释。实际上,这种过度的方式很容易在实践中避免。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并非任由受害人肆意主张,而是在人民法院主导之下进行(22)。相较于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要求采取公开的形式,赔礼道歉则不以公开为要件[16]29。法庭主导下的口头道歉并不会发生人格侮辱的问题,书面或者公开发布的“道歉声明”仍需由人民法院进行审核,实难想象还存在因赔礼道歉而受到人格侮辱的可能性,这种担忧多半属于杞人忧天。 五、结语 综上所述,赔礼道歉是一种极富东方特色特别是中国特色的名誉救济方式,成功地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纳入了法律纠纷的解决之中,不仅使得名誉权的救济更为充分、有效,还很好地控制了在此过程中对于表达自由的过度限制。赔礼道歉责任的争议,集中反映了法律与道德规范域场的交叉与纠葛,也体现了中华传统道德礼制观念所面临的现代民主自由价值的冲击。作为立法明确确立的救济人格权损害的责任方式之一,理论研究应当正视赔礼道歉在解决实践纠纷中发挥的独特功能,并为司法操作中面临的难题提出更多具有建设性的完善建议。一味指责赔礼道歉所具有或不具有的微瑕并上升到“违宪”层次的论调,则颇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诚如学者所言,法治不只是冰冷无情的规则、裁判与惩罚,其实现还需要唤醒良知、重建道德和确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们需要秉承深刻认识人本身,以法治凝聚道德,通过法治建设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原则,使人“知耻服礼”,让凝聚道德的法律成为信仰[12]。因此,应当坚持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探索道德与法律相辅相成的有效机制,使得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在现代法治的土壤中开花结果。 注释: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69页。 ②参见郭明瑞《民事责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转引自吴小兵《赔礼道歉的合理性研究》,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6期。 ③参见冀宗儒《论赔礼道歉作为民事救济的局限性》,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 ④参见黄忠《认真对待“赔礼道歉”》,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黄忠《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实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⑤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课题组《新闻侵权诉讼研究报告——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20年来受理的新闻侵权诉讼为研究样本》,载《判解研究》2011年第1辑。 ⑥Defamation Act 1996,Section 2. ⑦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昭和31年7月4日大法庭判决[昭和28年(才)1241号],载《日本国最高法院裁判选译(一)》,台湾地区司法院2002年印行,第123页。 ⑧主张违宪的观点,请参见[日]松井茂计《媒体法》,萧淑芬译,元照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⑨参见日本大阪地判56·9·18《判夕》464号第145页。转引自[日]五十岚清《人格权法》,铃木贤、葛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⑩韩国学者对此不乏批评之声,指责法院忽略了韩国文化对道歉的需求,而正是韩国的社会文化使赔礼道歉变得极为必要和有价值,并且还是纠纷解决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转引自黄忠《赔礼道歉的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实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2期。 (11)释字第656号解释:“所谓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属以判决命加害人公开道歉,而未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损及人性尊严之情事者,即未违背宪法第二十三条比例原则,而不抵触宪法对不表意自由之保障。” (12)大法官会议多数意见分两点阐明:其一,系争规定目的正当。鉴于名誉权遭侵害之个案情状不一,金钱赔偿未必能填补或恢复,因而授权法院决定适当处分,目的洵属正当。其二,限制符合比例原则。法院在原告声明之范围内,权衡侵害名誉情节之轻重、当事人身份及加害人之经济状况等情形,认为诸如在合理范围内由加害人负担费用刊载澄清事实之声明、登载被害人判决胜诉之启事或将判决书全部或一部登报等手段,仍不足以恢复被害人之名誉者,法院以判决命加害人公开道歉,作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尚未逾越必要之程度。惟如要求加害人公开道歉,涉及加害人自我羞辱等损及人性尊严之情事者,即属逾越恢复名誉之必要程度,而过度限制人民之不表意自由。 (13)参见释字第656号解释,陈新民大法官发表的“部分协同、部分反对意见书”。 (14)此种观点请参见姚辉、段睿《“赔礼道歉”的异化与回归》,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15)参见释字第656号解释,陈新民大法官发表的“部分协同、部分反对意见书”。 (16)参见释字第656号解释,许宗力大法官发表的“部分协同、部分反对意见书”。 (17)参见黄忠《认真对待“赔礼道歉”》,载《法律科学》2008年第5期。 (18)参见姚辉《人格权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5页。 (19)例如,口头诽谤一般适用于口头的赔礼道歉;在地方性报刊上发表的诽谤报道,通常不能要求在全国性报刊上刊登道歉广告。 (20)黄仕冠、黄德信诉广西法制报社、范宝忠侵犯名誉权案,参见http://www.qinquan.info/123v.html,2014年5月1日访问。 (21)由于判决主文等公告相较于道歉广告更加冗长,其刊载于公共报刊的经济成本对比是一目了然的。以引发释字第656号解释的“新新闻案”来讲,据相关统计,刊登“道歉声明”部分就需花费被告37125600元,而刊登“判决全文”部分则需花费386640000元,相差有10倍之多。另外,考虑到实践中广泛认可的口头道歉的责任方式,二者之间可谓天壤之别。 (22)《名誉权解答》第10条规定:“赔礼道歉可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进行,内容须事先经人民法院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