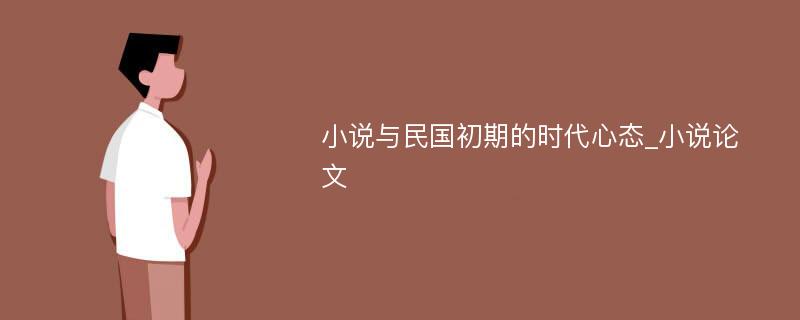
民初小说与时代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说与论文,心态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小说起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徐枕亚《玉梨魂》(1912)引起轰动,在《民权报》刊完后印成单行本,两年之内再版10次,成为民初小说审美趣味变化的表征。但小说的变化与建筑和服饰形成鲜明对照。建筑由于紫禁城失去了作为全国建筑的制度规范尺度,使西方建筑在中国凭趣味和财力而自由展开;服饰上一方面剪辫和放脚,另方面西装由官、军、商、学带头穿着成为时尚。建筑和服饰显出了历史不可逆转的向前跨进,小说则很像一种向后的“回逆”。民初小说的变化,从三个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一,从题材上说,政治小说、谴责小说从主流演为支流,而日益弱小,言情小说从边缘入主中心,而日益扩张。林纾写小说,自道云:“非为言情而设。”但也认为小说要动人,必须有男妇之情,为投合时代的趣味,他的小说是“经以国事,纬以爱情”。“当时曾有人估计,言情小说要占到民初所有小说的十之八九,这个估计很可能是夸大的,不过即使把它降到十之六七,也是一个惊人的比例,远远高出于其他时代。”[①]不难理解,“鸳鸯蝴蝶”竟成了文学史家称谓这一时期小说的代名词。二,从小说的语言载体上看,清末小说革命是白话呈现大声势,民初小说则以文言为主力军。在民初大写小说,有长篇5部,短篇200余篇的林纾,作为有名的遗老,用的是文言,自不必说,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两派,在《小说时报》《小说大观》《礼拜六》上叱咤风云的包笑天、周瘦鹃用的是古文,被称为鸳鸯蝴蝶的史汉派;以《民权报》《小说丛报》《小说新报》为舞台唱小说时代之歌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用的是骈文,被目为鸳鸯蝴蝶的骈文派。三,小说情味上的回归传统。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才子佳人小说的卷土重来,确实体会到了古代诗词中的哀艳心态。
怎样寻出这三点变化后面的动因,首先可以说的,是小说为维护、保持自己刚刚从小说革命中获得的文艺高位而作的无意识调整和应战。小说成为“文学的最上乘”,是革命家为了唤起民众进行体制外动员的政治功利而进行的一场文艺等级革命。革命成功了(清朝成了民国)又失败了(在社会的现实景况上),对于本作为革命阵营的一翼的小说来说,直接接受到的是,革命的失向。革命成功,社会依旧,小说家都感到小说的作用曾经被夸大了。然而又正因为这一夸大,才有了小说的高位。小说失去了革命的助力,但并不想失去自己的高位。向高贵的东西靠拢以保持高位成为民初小说的无意识走向。就当时来说,高贵传统有两方面。一是中国传统,即与白话小说相对立的诗文形式和诗文情调。二是西方小说传统,但西方小说的翻译,以林纾为代表,就是译成古文的,因此西方传统在这里又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了。我们看到,民初小说一方面以古文骈文写作,显得相当“高雅”,用古文的,在故事结构上卖弄着伏线、接笋、变调、过脉等古文家的文章义法,用骈文的,在故事肌肤上炫耀着炼词炼句的诗词乐调,所谓“有词皆艳,无字不香”。另方面又以有着朝向西方小说的“形式创新”,如徐枕亚长篇小说《雪鸿泪史》,用的是日记体,吴双热《孽冤镜》,用旁观者似的第一人称叙述。包笑天《牛棚絮语》、周瘦鹤《花开花落》在短篇小说结构剪裁上的新意……在新旧并存、东西交错的民国语境中建造一种维持小说高位的新型坐标,并在此坐标上努力奋进,构成了民初小说似旧而新又似新而旧的独特形貌。
小说成为文艺的新星耀然升起,在实际上,是为两股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所推动的:革命进程和都市化进程。前者作为一种明显的势力,在上面呼风唤雨,左右了小说的外貌,后者作为一种隐性的力量,在下面推涛作浪,支持着小说的高扬。清朝坍塌,革命失向,面对大变而未变,未变而大变的现实,全国上下,在短暂的欢腾之后,很是茫然。革命家纷纷脱离小说领域,而去干自己认为更重要的事情。小说失去了革命潮流的支持,而仅在都市化的溪流中载沉载浮。都市文化人成为领导小说的主体,与革命相脱节的都市法则、都市消费、都市趣味成为小说的主流:
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在这百不快活之中,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快活〉祝词》)
礼拜六下午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礼拜六〉出版赘言》)
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眉语〉宣言》)
语言中充满了商业气息,广告语气,追逐、迎合,而又制造、浓化着都市趣味。一方面,民初小说要坚持小说在文艺中的优势地位,从而走向了语言、形式、情调中的“雅”,另方面,它保持这种优势地位的实实在在的基础又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是)都市化进程。(自从康、梁掀起体制外革命以来,就产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革命与都市的分裂)。这又使民初小说走向了语言、形式、情调中的“俗”。民初小说就是这种“雅”与“俗”的奇妙拼贴。就前一方面来说,它保证了中国小说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入主文艺中心的连续性,成为从小说革命到五四小说的必要的历史承转。从后一方面来说,它又远离了革命中心,这里已经预含了,当革命一旦回到文学上来的时候,它或早或迟要遭到来自革命的批判。然而由于革命自己离开了小说,以都市化为依托的小说潮流:鸳鸯蝴蝶成了民初心态的时代特征。
二
鸳鸯和蝴蝶为民初小说家经常咏叹,典出咸丰年间小说《花月痕》中31回“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鸳鸯蝴蝶,同命可怜,这确实非常传神地点出了民初小说的主要特点。下面我们选四部影响极大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来看其趣旨。
徐枕亚《玉梨魂》(1912年发表于《民权报》,1913年9月出单行本)。出身书香门第的才子何梦霞任教乡村小学,寄居崔家,与崔家的孙子、自己学生的母亲、年轻的寡妇才女白梨影由书信而生恋爱,书信从来是中国才子才女最美而又得心应手的达情露才工具,高雅香艳由此而生。在当时,寡妇恋爱被视为骇俗之举,恋爱寡妇被目为不道德之人。二人不由自主地发生恋情,又用最大的毅力固守礼教。既为了遵守不得不守的礼,又为了摆脱这摆不脱的爱,梨影把自己的小姑推荐给梦霞,得到崔翁的同意确定。但才子爱的是梨影,不愿代替人。小姑已受自主婚姻新潮的影响,怨恨家人的包办。演出了心的误解,人的矛盾,情的缠绵。梨影进退两难,悒郁致病,死了。小姑自怨自艾,也死了。才子深受刺激,出走革命,阵亡于武昌城下。
吴双热《孽冤镜》(1912年发表于《民权报》,1914年2月出单行本)。姑苏世家公子王可青,游玩常熟,浮舟湖上,偶见楼中美女薛环娘,一打听,不但得知美人芳名,更喜美人家兄是他刚认识的一位朋友。薛家较贫,父亡母存。于是上门认识,两情相悦,订下婚约。谁知可青归家,父亲已为他订了一大官千金,王反抗无效,被锁在府中。想尽办法,也不过是托人带信给环娘,诉其无奈和不幸而已。此时,薛之兄早怀病体,已亡。母女二人移家南京,盼望可青已久,闻此变异,双双呕血,两命呜呼。而王可青娶进门的名门之女,却是一位悍妇。受了这双重刺激,王可青疯了,死了。
李定夷《筼玉怨》(1913年?发表于《民权报》,1914年7月出单行本)。没落官家子弟刘绮斋就读上海,春日郊游,遇一美女。一打听,是朋友的表妹,名门闺秀史霞卿。于是写信,约会于公园。两情投合,私订婚约。在刘家,母亲开出条件:只要儿子学有成,业有成,就承认这门亲事。这些刘绮斋都办到了,毕业考试第一名,到云南一父执手下做事,颇受重用。史家呢?霞卿生母已亡,庶母不善,父亲畏内。庶母想方设法陷害霞卿,买通盗匪将史掳去,幸一强盗听史哭诉,唤起天良,助其逃归。庶母又串掇其父,要将霞卿嫁给一个纨绔子弟。霞卿坚决拒斥,并试图自尽,才使父亲暂搁其事。史自认为良缘难就,恶网难逃,写一绝命书与刘。刘接书后急忙奔回。赶到时,正值前不久史庶母与仆人通奸,被人杀死。史父已察觉到庶母对霞卿的阴谋,深为自疚。于是正式当面承认了刘史的婚约,而且进一步亲上加亲,为刘在日本的弟弟绚斋订下了霞卿的妹妹碧箫。故事如果在这里结束,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然而没有。绮斋接到了弟弟患病的电报,急忙乘海船去日本,不料海途中遇风浪,轮船沉海。消息传来,霞卿身体受了庶母的迫害,本就虚弱,又受此噩耗打击,一命归天了。在日本的绚斋病笃而亡,碧箫对此,自叹薄命,竞剪发出家了。其实绮斋并未淹死,被人从海中救了起来,然而变故种种,已成事实,于是留下一缕青丝,不知所终,大概也遁入了空门。
苏曼珠《断鸿雁零记》(1912年)。日本世家公子三郎,幼年丧父。义父是中国人,带他回中国,与朋友之女雪梅订婚。后来义父家境衰微。女方家悔约。三郎为了不使雪梅为难,剃发为僧。雪梅却表示非他不嫁。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和生母尚在日本,雪梅赠送百金,让他去日本见生母并商量未来。三郎找到了亲人,母子皆欢,儿子怕惹母亲伤心,未提自己出家和雪梅之事。三郎的表姐静子爱上了他,母亲也决定选静子为儿媳。三郎也深感静子的可人,几乎不能自持。然一想到自己已是和尚,二念及中国的雪梅,仍表示终身不娶。母亲的再三劝说,静子的愈显动人。三郎不得已,留信静子说明和尚身份,并毅然悲怆地回到中国,修行于杭州灵隐寺。一天,偶遇以前邻居,方知雪梅因不堪继母逼嫁富家,已绝食自尽。三郎大惊,失声痛哭。回到家乡去吊雪梅之墓。但雪梅的丫环不肯为他带路。只有流着不尽的眼泪在一片荒坟中寻来觅去,直到日暮天黑,也不知她的墓之所在。
这些小说的共同点是明显的:一,写男女的至情,始终不渝,生死不改,志同鸳鸯。由这里必然产生一种感人之情。从都市化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能够抓住人的卖点。从民初小说维护小说高位来说,它的独特之处是情调高雅,用情深厚,氛围香艳。二,都是遇到了阻碍。而阻碍的核心是使青年男女不能自主婚姻的封建礼教。四篇小说的三篇,其祸根都是家长的不同意。两篇是主人公的身份(《玉梨魂》中的寡妇和《断鸿雁零记》中的和尚)在礼教习俗中被规定为不许恋爱。从这里必然产生一种吸引人的故事。四篇小说都写得情节波折,往回缠绵。从都市化方面来说,这是能够抓住人的另一人卖点。就民初小说的独特性来说,一方面它好像退回到了传统题材中:一种《西厢记》式的礼教与年轻恋人的冲突。然而它虽回到传统题材之中,却深化了传统题材。比如,《玉梨魂》呈出的寡妇恋爱问题,《断鸿雁零记》呈出的和尚恋爱问题。[②]另一方面,题材虽是传统,问题却是现实。《玉》《断》两部小说基本上取自作者的亲身经历。民国以后,政体已变,现实依旧,礼教依旧。鸳鸯蝴蝶小说的作者们不是革命家,而是都市文化人,他们的立场本就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包笑天)他们深感礼教对人的压抑,但不是要否定礼教,而只是想改良礼教。从这里可以理解一些鸳鸯蝴蝶小说“杰作”的趣旨。如李定夷《廿年苦节记》对封建节孝的颂扬,周瘦鹤《恨不相逢未嫁时》中对主人公在所爱之人和所嫁之人的内心矛盾中以礼自持而生的坚定和哀伤的欣赏,包笑天《一缕麻》能够把反礼教的思想和宣扬礼教的思想熔铸成一个至情至性的双重悲剧故事,李定夷的《自由毒》对不能“发乎情、止乎礼”的自由女的否斥……因此,鸳鸯蝴蝶小说中的主人公对恋爱阻碍——礼教,基本上采取的是从《诗经·蒹葭》就开始不断重复出现的中国传统中的经典态度:刚强而又柔弱的合一。说刚强,是因为对恋爱目标的执着,不惜以身殉爱;说柔弱,是因为对礼教的无奈与承受。因此产生了:三,悲剧结局。从都市化方面来说,这又是一个大卖点。从民初小说的艺术特色来说,对悲剧结局的追求尤为突出。这意味着什么呢?小说史的比较可以深化这一思考。
三
鸳鸯蝴蝶小说与从明末到清末的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具有最大的可比性。这类以《玉娇梨》《好逑传》《铁花仙史》《平山冷燕》等为代表的小说,据郭昌鹤先生研究,共50部,这是一种类型小说。郭先生对其模式有很好的归纳。[③]小说模式的第一项:模范才子,文弱美貌,极超等的天资,长于诗文及武艺,好色而风流,生于江苏或浙江,是达官贵人的独养子。这一项在基本点上(文弱美貌,长于诗文,世家子弟)与鸳鸯蝴蝶小说的才子是一样的。第二项:模范佳人,有貌,有才,有德。这与鸳鸯蝴蝶小说的佳人也是相同的。第三项:才子佳人相逢。或于后花园,或于庙宇,总之,从现象说,讲一个“巧”字,从理论说,讲一个“缘”字。这又与鸳鸯蝴蝶小说基本相同。第四项:是谁穿针引线?不像《西厢》,红娘是穿针引线的重要配角,才子佳人小说,对红娘角色不甚重视,在郭先生选出的12部代表作里只有六个红娘。这又与鸳鸯蝴蝶小说同,或无红娘,或有“红娘”也不重要,仅起一个介绍的作用。第五项才子佳人好事多磨,受尽阻挠。又是一个共同项。第六项:结局,大团圆。12部代表作中,无一不是大团圆。9部才子中了状元,3部做到兵部大元帅;12部中7部是“奉旨面婚”。才子佳人小说最后是实现中国传统的最高理想:金榜提名时,洞房花烛夜。这与鸳鸯蝴蝶小说的悲剧结局完全相反。才子佳人小说无论怎样磨难,最后一定要走向大团圆,鸳鸯蝴蝶小说无论怎样似乎要大团圆了,千方百计都要使团圆继续走向悲剧。这种人为的痕迹在李定夷的《筼玉怨》中尤其明显。才子佳人小说的第三、四项是反对礼的,而第六项又是返回礼的。既表明了礼的宽容性,可改良性,又表明了作者对礼的态度和幻想。鸳鸯蝴蝶小说的作者也是反对礼和同时对改良礼教充满幻想的,然而他们不但在第三、四项中突破礼,进而在悲剧结局中用命运的无奈实际上强化了对礼的“控诉”。然而,鸳鸯蝴蝶的主色正是要突出这种命运的无奈。
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正是一种最典型的“无奈的时代”。
正因为要突出这命运的无奈,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前几项因素移入鸳鸯蝴蝶小说中都因其与这悲剧结局的拼粘而被扭转为一种新的意蕴。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也是处于一种无奈的困境中的,但处于困境中他们却对社会文化怀着一种根本上的信仰。因此“金榜提名,洞房花烛,妻妾成群”成了他们匮乏中的白日梦。《玉娇梨》天花藏合刻《序言》讲得清楚:“寒士落泊不遇,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泄其黄粱事业。凡上之可惊可喜,皆胸中之欲歌欲哭。”鸳鸯蝴蝶小说的作者却处在一种没法按传统方式幻想的无奈现实中。如说他们有传统依托的话,那么他们依托的是从《诗经·蒹葭》、《离骚》、《九歌》和《孔雀东南飞》以来的深情、无奈、哀怨传统。只是把这个传统(按民初文学的最高等级门类形式)小说化了。这样,鸳鸯蝴蝶小说,从艺术上说,就与传统文学有了两方面的关联,才子佳人的小说传统和诗歌的悲怨传统,从这里可以把它定义为一种“旧”,从思想上说,无奈心态,对于正在急剧地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中国社会,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当它与一种深厚的传统联系起来时,不是传统使它获得了肯定的理由,而是它与传统一道获得了不被肯定的理由。这已经预含了它在五四受到的猛烈抨击。
鸳鸯蝴蝶小说准确地抓住了民初的无奈心态,而这“抓住”又是靠了都市大众文化的推动。大众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要揣摸、迎合、追逐大众消费心理(《民权报》总务主任就是在发财念头的驱动下,把《玉梨魂》印成单行本的,而且果遂财愿。)从这方面来看,鸳鸯蝴蝶小说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形成了都市大众文化的模式。
鸳鸯蝴蝶小说在旧的革命远离文学而去,关心、介入和“利用”文学的新革命尚未到来的间歇岁月中,担负了维持小说高位的重任,形成了它的趋“雅”一面;在与革命分离的现代都市化的推动下,它造就了中国现代大众文化的第一次小说模式,呈出了媚“俗”的一面;作为文学史的时间延续,它显出了多方面的向传统“靠拢”;作为文学与社会的必然关联,它准确地反映了民初大众的无奈心态。
[本文作者受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资助]
注释:
①袁进《鸳鸯蝴蝶派》,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5页。②此观点由袁进先生提出,参①第55页。
③参郭昌鹤《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上、下),载《文学季刊》创刊号、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