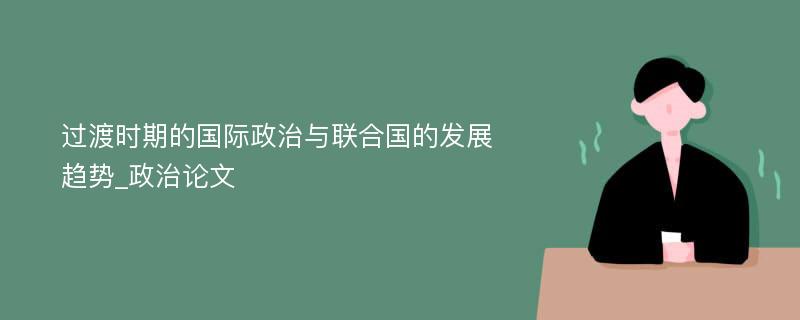
过渡时期的国际政治与联合国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走向论文,过渡时期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国际政治的新变化与联合国未来的关系。文章提出,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到多极的转变,全球化趋势,政治的经济化,东西力量对比的西方化和国际政治主体的多元化,是过渡时期国际政治的新特征。联合国结构的调整和对全球问题的关注,经济与政治的并重,地区集团的影响,决议的西方化,是国际政治新变化所决定的联合国的变化趋势。
关键词 国际政治 联合国 妥协
当我们注视本世纪末的国际舞台时,我们发现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气候正处在转换时期。这种转换不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毁灭以前的世界政治图景,而是在原有的图画中涂上浓重的新色彩。这是国际政治变化的一个过渡时期。这种变化对国际政治主体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对联合国的影响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本文就过渡时期的国际政治与联合国的变化作一简论。
一
当今过渡时期国际政治的表征基本上可描述为如下几个方面:
1.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到多极的转变,世界多极化趋势
战后世界形成的以美苏为首两大阵营的对峙鼎立了40多年后,由于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而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多极的世界。这种多极的格局既有以前的两极,又有新崛起的力量。尽管各极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但整个国际政治格局从两极到多极已不可逆转。
2.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的转变,全球化趋势
过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世界政治的基本模式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台球模式,国际政治以权力利益为核心,彼此之间为了“增加权力、显示权力、保持权力”而斗争,国际政治的画面是对立、冲突、流血、战争。当人类社会发展到本世纪末的今天,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通联系的便利,世界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科学技术工艺的国际化,整个世界已成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各国利益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的各种活动已越来越多地具有全球维度。全球化浪潮冲击着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范式,国际政治模式由台球模式向蜘蛛网模式转变,全人类将相互依赖、合作与互利。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民族主义的复兴对全球化趋势仍有极大的钳制力,不过,国际政治的全球化趋势之风更加强劲。
3.全球重心从政治转向经济,政治的经济化趋势
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因素的下降,和平与安全不再只是一个政治概念,更多地包容了经济内容,经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间接作用正转化为直接作用。经济从国际政治的后台走到前台。谁能在经济领域占据优势,谁就能在政治舞台上唱主角。因而目前各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发展经济,占据经济领域的制高点。这只需从美、日、欧政策调整就可略见一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西雅图会议的召开是美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步骤,欧共体的马约则是欧洲政治与经济合作的深化,日本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的转变是日本以亚太为依托,执掌亚太经济之牛耳的选择。世界经济危机决不亚于一场战争对人类产生的冲击。经济领域的摩擦与冲突直接危及着世界的安全大厦。当今时代,经济与政治已经合流。国际政治争端的内容和解决的方式更多地带有沉甸甸的经济份量。
4.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向多元政治体系过渡,国际政治角色多元化
冷战的结束,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加强,给国际政治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政治的角色发生了新变化,原来推动国际政治变更的力量基本上由国家一元力量决定,国家是政治行为的主体,然而在世纪之交,决定国际政治蓝图的是多种力量,多种角色,有国家、个人、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它们加入到国际政治体系中来,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开始雕塑国际政治的新模式。
5.国际政治东西方力量的天秤向西方倾斜,政治力量西方化
八、九十年代是国际力量分化改组的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峙的力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社会主义力量遭受严重挫折,生存危机摆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在东西方40年的和平较量中,东方力量现在处在下风。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力量在世界的辐射力、影响力、渗透力较东方强得多。政治力量已由东西相持向西方倾斜。
二
国际政治舞台背景的变化必然刺激活跃在舞台上的角色之一联合国,导致其变化。
1.国际政治由两极到多极的转变,对联合国的行为和结构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美苏两家战后40多年,把联合国作为限制对手的工具,曾多次使用否决权而使联合国无所作为,实际处于瘫痪状态。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对峙的结束,俄罗斯向西方靠拢,联合国在国际舞台开始活跃起来,逐渐从一个政治讲坛、辩论场所向具有一定强制力的实体过渡,通过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执行,原来以美苏两家争夺为背景的热点地区在联合国的干预下渐渐冷却下来,从柬埔寨的维和行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阿富汗的和平谈判中,都可看到联合国的生动面孔。特别是在海湾战争中,由于美苏两家的联手,采取了共同的行动,使联合国通过了一系列谴责伊拉克行为的决议,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湾危机。这种行动在东西两极对峙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进行的。从联合国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看到联合国由世界政治论坛向一定程度的强制实施和平的实体转变,活动能量比以前大大增长。二是多极力量的出现,更准确地说,新的力量崛起也对联合国的结构大厦构成了冲击。我们知道联合国的核心是安理会,其中五大国具有否决权,是核心中的核心。然而这一结构在新旧力量变化的情况下发生动摇,改革安理会的呼声高涨起来,呼声主要来自两种力量。一种是曾经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两国正加快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1991年中曾根说:“日本和德国都有资格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日本政府“希望得到与日本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相称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德国外长金克尔对《明镜》周刊记者说:德国在重新统一和获得全部主权后,必须从观众席上退下来,它需要安理会中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另外一种是中小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目前五大国磋商运作机制越来越不满,希望通过增加中小国家的发言权来改变现状。马哈蒂尔说:“联合国最不民主之处就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两种改变现状的力量对联合国的原有结构提出了挑战。联合国是由主体国家组成的,国家之间政治力量发展不平衡必然要打破联合国内部的权力配置结构。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出现的种种关于联合国框架的方案就是政治力量深刻变化的反映。联合国的权力结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2.全球化扩展推动联合国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全球化有如一枚铜板的两面,一面给人类带来了繁荣与进步,人类在吮吸着它酿出的甜汁;另一面也给人类带来了挑战和困惑,且比以往更加严峻和强烈。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人口爆炸的压力,恐怖主义的全球威胁,能源的消耗与匮乏,臭氧层的破坏、海洋的污染,还有足以毁灭人类几次的大规模的核武器的积聚与扩散。这些问题有如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人类的头顶。解决这些问题决非一国能力所及,需要地球上各个国家共同努力,协调行动,从全球角度处理这些问题。这就需要国际组织出面承担起这一重大责任。只有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才能担当这一重任。这是国际政治向全球政治转变的客观需要,也是联合国行为的一个变化趋势。我们已经看到了联合国解决全球问题的一缕曙光。在联合国的倡议下,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首脑人物带着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寻求解决这一全球问题的途径。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它反映和标志着人类已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国家的命运同整个全球的前途休戚相关。正如克林顿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指出的那样,“国外同国内今天已经没有明晰的界线,世界经济、世界环境、世界爱滋病危机,世界军备竞赛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环发首脑会议的召开充分显示了联合国在当今人类事务面前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在世界所处的地位不同,特别是南北国家的巨大差距,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如在《森林未来公约》方面,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施加压力,让其承担保护森林的义务。他们认为森林是生物种的宝库,是新药和食品的丰富来源,是二氧化碳及其温室气体的强大吸收剂,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而拥有大面积森林的南方国家则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森林是贫穷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各国在使用自己森林资源以寻找发展和克服贫困方面拥有主权,反对把森林问题国际化,因此,在环发首脑会议上,会议只通过了没有约束力的声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并不表明发达国家就是从全球角度看待资源,发展中国家就是从本国利益看问题,其实发达国家也有自己的私利。这次会议表明,联合国已在全球问题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联合国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3.国际政治中经济份量的增加,使联合国关注的焦点逐渐从维持和平向促进发展的方向转变。联合国成立时的宗旨是维持和平与发展经济。但在以往,联合国一直把重心放在政治方面,即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而把发展经济放在次要地位。据一份调查报告,联合国就东西方冲突的表决在1947年约占大会的45%,1961年达65%。60年代末期达70%,南北问题从1947年占大会表决的20%下降到1961年的12%左右,到60年代末降到10%以下。尽管在70-80年代情况有所变化,但还不足以改变联合国政治与经济的对比度。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战后至80年代,国际政治一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战争的幽灵威胁着人类,东西意识形态对抗主宰着世界政治。冷战结束后,大战的可能性降低,经济与政治日趋融合,南北问题不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指出“不发达国家的前途是我们时代最紧要的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之一,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会深刻地影响世界的前途”。发展中国家在失去了10年的发展后,南北鸿沟正在迅速扩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更加严峻。在国际生产和流通领域,至今仍维持着传统的国际分工模式;在国际金融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依附地位。1950年世界银行统计中低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总值的比值为1:24.3,而1990年扩大到1:54.6,发展中国家外债达1.5万亿美元。南北现状决不亚于一场规模巨大的武装冲突,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既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又时刻威胁着发达国家的安全。为适应冷战后的形势要求,联合国应当承担起全球经济重任。加利说:“虽然发展活动可能不如维持和平行动那样吸引人,但是前者同样重要,而且它们的确为全球的安全与稳定奠定了基础。联合国正竭力把工作重心放在发展方面。”
4.国际政治主体多元化特别是区域组织地位的上升对联合国的行为产生了影响。现今的国际政治如果从组织系统考察基本上可由四类组织联结起来,即世界性组织,区域性组织,专门性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世界性组织,主要从全球角度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可以说是金字塔的顶点。其次是区域性组织,例如欧安会、欧共体、非统组织、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联盟等。这些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联系,调节相互关系和利害冲突,保障地区和平与安全。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凡属于与联合国的宗旨及原则相符的区域性组织,无论是既有的,亦或期待的,《宪章》一概予以认可,并鼓励会员国予以充分利用,尽量发挥区域性组织的作用。不但各区域性组织的活动要符合《宪章》的宗旨及原则,而且“如无安理会之授权,不得依区域办法由区域机关采取任何执行行动。各区域组织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采取的行动必须随时通报给安理会。”联合国应成为一切国际组织的中心,对各区域组织行使指挥之权。当今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区域组织对联合国有两种影响。一是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在地区层次上解决问题,如伊斯兰国际组织曾积极帮助调解两伊冲突,美洲国家组织和孔塔多集团积极推动中美洲冲突的解决。另一方面,区域组织则绕过联合国自行其事,从而对联合国的威信和权力构成了挑战和侵蚀。这一点在波黑问题上清楚地反映出来。起初欧共体力图排斥联合国出面调解,只是在自己调停失败时才请联合国出面干预,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十分恼火。这种矛盾说明了区域组织的权力日益增长,要求分享和主宰地区事务。更加需要指出的是,区域组织力量的上升给联合国的运行机制和基石带来冲击。众所周知,联合国是在主权国家的基石上建立的,但是由于地区组织的大规模的兴起,特别是地区组织从一般功能性组织开始向政治性组织过渡,向政治实体过渡。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显示了区域性组织朝这方面发展的征兆。欧共体将来的发展将动摇联合国创立者的国家至上的观念。我们将会看到联合国内的行为主体不再仅仅是民族国家,还有发达的区域性组织。这样联合国的运转不再只是来自主权国家的驱动,而且还有来自区域组织的影响。在东西方对抗降低,意识形态争斗中的因素下降时,人们将会更多地看到联合国的决议打上区域组织的烙印,在国家斗争的背后站着区域性组织,联合国内部的力量的分布将以地区的形式体现出来。
5.国际政治力量天秤的西倾将使联合国更多地受到西方国家的操纵。战后40多年,联合国内部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一直进行斗争,两者力量旗鼓相当,难分伯仲,因此很多决议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冷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变化直接影响了联合国内部力量的配置。联合国核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对比为4:1,也就是说,美、英、法、俄结成一块,而中国单枪匹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明显占据上风,美国在安理会中非常活跃,无疑起了带头作用,很多事情往往由美国发起,提出建议,先同英、法两家商量,然后再与俄中协商,最后拿到安理会讨论,实际上不过是履行程序。我们从柬埔寨大选的安排,到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援助,从海湾战争出兵到波黑内战的干预,从对利比亚的制裁到对伊拉克的禁飞,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操纵,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联合国的很多决议涂上了浓重的西方色彩。而且日本德国谋求常任理事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这会加重西方在联合国图案上的颜色。西强东弱的态势在世纪之交将难以改变,这会大大加强西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正如卫报所说:“联合国已成为一个保守机构,几乎完全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利益效劳的机构”。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这次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以前权力新结构的建立都是在战争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次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改变则是在和平的背景下进行的,新旧两者不是以武力决胜负,而是以综合国力决胜负,各种力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没有一个占垄断地位,实际上是新旧力量并存的过渡时期。这一转换的特点将使我们看到:一方面有的大国尽管有所削弱,但在世界舞台上仍有相当的实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而他们的利益不能受到大的损害,更不能被取代,原有的权力框架基本上要维持。另一方面,一些二战的战败国和一些地区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力量壮大起来,要求发挥更大的作用,它们要求对联合国原有的机构进行一定程度的改组,反映它们的心声。这两种力量的嬗变决定了联合国的权力变化具有妥协的特点。原有的大国既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注意新兴大国的要求。新兴大国既要在联合国内拥有更多的权力,与旧有的大国平起平坐,但又不能过份损害原有大国的重大利益。未来联合国的走向不是对过去的全部否定,不是对既有权力结构推倒重筑,而是对以往的继承,对原有权力结构的改造。因而,我们将会看到《联合国宪章》的变化是既有保留,又有修改,这实际上是国际政治力量斗争的缩影,也是国际政治过渡时期特点的一个侧面反映。
冷战后的世界正处于新旧交替规范失衡的时期。各极力量力图使联合国成为自己谋利的工具,全球化浪潮的拍打又要求联合国承担起更大的全球责任。联合国的两难处境恰是国际政治中以国家为本位和以全球为本位对立的深刻写照。联合国的尴尬正是国际政治变动中双重性格射在它之上的投影。在国际政治波涛汹涌的大潮中,世人期待联合国能够平稳地行驶在维持和平与促进发展的航道上。主要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1994年6月15日
标签:政治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联合国秘书长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联合国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东局势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