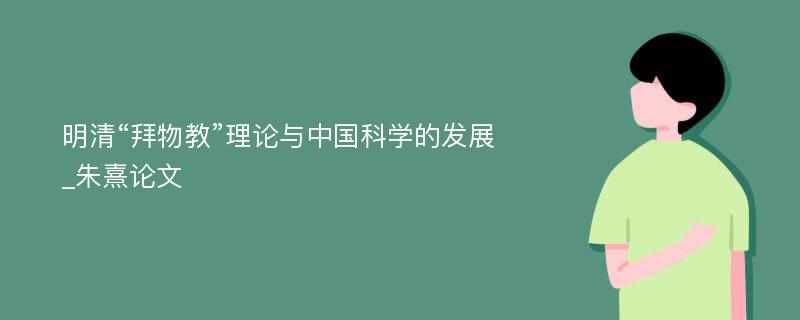
明清“格物”说和中国科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清论文,中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942(2003)04-0075-07
程朱的“格物说”具有道德论和认识论、人文道德精神和科学理性精神的双重意义。正因为它蕴含有科学理性精神,所以不仅从人生价值上把明清大批士人从单纯的自身道德修养转向对外在世界及其“物理”的探讨,而且从方法论上也为明清古典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随着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和实学思潮的高涨,程未的“格物说”在内容上吸收了“西学”成分,在格物方法上也吸取了西方近代科学“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和注重实验的实测精神,使之成为中国古典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衔接点。中国科学的发展,不只是借助于西方科学,同时也可从中国“格物说”中寻找到它的内在根据。
一、程朱“格物”说的双重涵义
“格物”说在北宋以前只含有道德修养论意义,从北宋二程开始,程朱理学才第一次赋予“格物”说以道德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涵义。
程颐一反郑玄、孔颖达的传注传统,依据自己的理学思想,撰写《改正大学》,对“格物”说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那里,“格物”这一概念具有认识论和道德论的双重涵义。
(一)在认识论上,他的“格物”说有四个基本内容:1.何谓格物?程氏所谓“物”,不仅包括人们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凡遇事皆物也”,而且包括人之外的一切客观物体。格物即是穷致事物之理。他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曰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1]格物就是穷求事物之理。有时,他也把“格”字训为“至”字,他说:“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来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2]“格”虽有“穷”、“至”二义,但二者是相通的,皆是穷致事物之理。2.程颐所谓穷理,并不完全是研求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而只是借助于“格物”这一媒介,去认识人心所固有的“天理”。他说:“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则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3]在程颐看来,心中固然有众理,然不格物虽有之亦不可得。只有通过格物,才能获得,“格物”是“致知”的方法。就他把知的来源说成“吾之所固有”而言,是一种先验论;就他主张致知必在于格物而言,又具有经验论倾向。3.由格物到致知,是一个由渐知到顿悟的过程。他说:“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济事,须是集众理,然后脱然自有悟处。”[4]“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2]“格物穷理,非是要穷尽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它可以类推。”[5]程氏在这里既反对“格一物而万理皆知”,亦反对“格物须物物格之。”只有在“集众理”、“积习既多”的基础上,通过“类推”即综合归纳和类比推理的方法,才能达到“贯通处”。这里虽有佛教顿悟、直觉之义,但程氏把认识看成是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有其合理的思想成分。4.何以能通过格物达到“致知”呢?这是建立在他的理一元论基础之上的。他说:“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语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学者皆当理会。”[5]正因为“物我一理”,所以通过格物,即可印证吾心固有之天理,内外相证,就可以达到合内外认识的最高境界。
(二)在伦理学上,程颐把“格物”看成是排除物欲引诱、恢复人心天理的过程。他说:“‘格物在致知’,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迁,迷而不知,则天理灭矣,故圣人欲格之。”[6]这是说,人生而固有天理,只是由于被外物所蔽,“迷而不知”,所以天理灭矣。只要通过格物以恢复失去的天理,“自格物而充之,然后可以至圣人。”把格物致知看成修身养性,达到圣人境界的必要手段,这自然是伦理学问题。正是从这一基本前提出发,程颐在格物穷理对象上,既要探索“外物”,更要格“性分中物”。有人问:“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程颐回答说:“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间皆是理。”[7]在穷理途径上,他说:“凡一物上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穷理亦多端,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皆穷理也。”[2]又说:“诵诗书,考古今,察物情,揆人事,反复研究而思索之,求止于至善,盖非一端而已也。”[8]从格物穷理的目的、对象和途径诸方面,说明在程颐那里“格物致知”是一个伦理学命题,这是不容置疑的。
朱熹在程颐《改正大学》思想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格物”说。朱熹一生对《大学》用力最深,他“移其文”、”补其传”而成的《大学章句》,是理学家对“格物”说的集中表述。朱熹在《大学》的“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致也”处,自注云:“此句之上,别有阙文,此特其结语耳。”[9]于是,他按照自己的理学观点作了一篇《补传》,全文如下:
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就是朱熹有名的格物致知论。他既明确规定了“格物”、“致知”的含义,又论述了二者的关系。这里既涉及到认识能力、认识对象和认识过程,又谈到道德修养的目的和方法。它的基本内容有四点:
(一)何谓格物?这是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核心观念。何谓“物”?朱熹所谓“物”是指一切客观对象,“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10]“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貌象而盈天地之间地,皆物也。”[11]既包括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也包括人这一主体自身,外延十分广泛。格物至少包含三个意思:1.“即物”;2.“穷理”;3.至极。其中“穷理”是最基本的含义,而欲穷理就必须“即物”(即接触具体事物),穷理又必须穷“至乎其极。”简言之,格物就是“即物而穷极物理”,即在具体事物中穷尽事物的本然之理。他多次说道:“格物,格犹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于文祖之处。”[12]“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3]“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格物,须是穷尽到十分,方是格物。”[14]他把格物比喻为吃果子,“先去其皮壳,然后食其肉,又更剥那中间核子都咬破时得。若不咬破,又恐里头别有多滋味在。若是不去其皮壳,固不可。若只去其皮壳,不管里面核子,亦不可。……格物,谓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若是里面核子未破,便是未极其至也。”[12]正是从这一完整的“格物”定义出发,他极力反对把格物仅训为“接物”。他在“训格物以接物,则于究极之功有所未明”句下,自注云:“人莫不与物接,但或徒接而不求其理,或粗求而究其极。是以虽与物接,而不能知其理之所以然与其所当然也。今日一与物接,而理无不穷,则亦太轻易矣。”[15]这表明朱熹反对把格物仅仅归结为“接物”,并不表示朱熹反对“接物”。实际上,朱熹是十分强调接物的。他说:“人多把道理作一个悬空的物,《大学》不说穷理,只说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若不接物,何缘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极其知者,却只泛泛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穷究。如此,则终无所止。”[14]
(二)何谓致知?朱熹曾说:“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12]“知者,吾自有此知,此心虚明广大,无所不知,要当极其至耳。”[14]致知就是推极吾心固有的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从“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极其至也。”[16]“人心之灵,莫不有知”,但这种固有的知识,只是通过“格物”在主体上得到的知识的扩充的结果。格物是主体作用于客体而言,致知是就认识过程在主体方面引起的结果而言。“致知是自我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缘得知?”[14]格物与致知“只是一本,无两样工夫也。”[17]
(三)格物和致知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其区别而言:1.“格物是物物上穷至其理,致知是吾心无所不知。格物是另细说,致知是全体说:”[14]2.“推极吾所知,须要就那事物上理会。”“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15]在这里,朱熹提出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所谓主体是指“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所谓客体是指“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就其联系而言,格物是致知的手段,致知是格物的目的。他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他又说:“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盖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别有致处也。”[12]他还形象地论证说:“夫格物可以致知,犹食所以为饱也。”[15]
(四)由格物到致知,是一个由“积累”到“贯通”的过程。他说:“一物格而万理通,虽颜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耳。”[18]意谓只有不断地接物,使之“积习既多”、“用力之久”、才能达到“格物”、“知至”的最高境界。这里,朱熹的本意虽是论述如何通过格物印证吾心之天理的过程,但是他毕竟认识到人的认识过程的辩证运动,这是十分可贵的。
以上四点,是就朱熹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命题所作出的分析。但是,在朱熹那里这一命题还具有伦理道德意义。“格物致知”作为伦理学命题,至少也有三层意义:1.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明德”。他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12]所谓“明明德,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12]何缘有不明?“为是气禀之偏,又为物欲所乱。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之于味,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所以不明。”[19]“明明德”就是通过格物达到“明天理、去人欲”的目的。他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围攻把守,人欲自消铄去。”[20]这些都不是讲的探讨客观事物之规律,而是追求道德之至善。2.“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是体认和践履先验的天理。所谓“格物”之“物”,朱熹训为“事”,“物犹事也。”[12]他把天下之事分成“内事”和“外事”两大类。他说:程子“见人之敏者,太去理会外事,则教之使去父慈、子孝处理会。曰:‘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若是人专只去里面理会,则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全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时,已有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12]又说:“伊川意虽谓目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争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之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21]朱熹的意思是说,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是“内事”而不是“外事”。所谓“内事”,是指“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皆人所不能无者,但学者须要穷格得尽。事父母则当尽其孝,处兄弟则当尽其友,如此之类。”[14]这至少要占“格物”的六七分内容。如果不这样,就必然像“炊沙成饭”、“游骑无归”那样得不到结果。所谓“外事”,是指格“一草一木一器用”之理,即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但这不是“格物”的主要内容,至多只能占“格物”的“三四分”。3.“格物致知”的方法和途径。朱熹指出:“物理无穷,故它说得来亦是多端,如读书以明道义,则是理存于书;如论古今人物以别其是非邪正,则是理存于古今人物;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则是理存乎应接事物。”[22]这三条穷理的途径和方法,都与探索客观世界的科学真理无关,都是研究如何体验和践履道德的。从上述三方面看,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是一个伦理学命题,这也是明白无误的。但是,朱熹不同意司马光的“扞物”之说。认为如果说只有通过捍御外物才能得到至道的话,那就等于断绝父子而后知孝慈之理,“是安有此理域!”[23]在朱熹看来,“至道”就在人伦日用之中,“至道”只能在人伦日用之中求之。
从上述分析中,说明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存矛盾。他们从理在物中又在物上的宇宙观出发,当从形而下看,把格物规定为“即物穷理”时,它多少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当从形而上看,把格物归根到底说成是穷形而上学之理,或把致知说成明吾心之天理时,它在本质上是先验论。当他们把格物致知当作认识论命题时,它多少含有一些合理因素;当他们把格物致知说成“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学命题时,则纯是先验论。朱熹的豁然贯通说,虽不等于我们说的由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但他已经观察到人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现象,而要深入到事物内部,即是一个由表及里、由粗到精、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具有合理的辩证法因素。
二、明清实学家“格物”说与中国古典科学的发展
正因为程朱的格物说含有外向性的科学理性精神,所以明清实学家的格物说除了含有内向性的道德修养外,还着重发挥了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大力提倡“实测之学”。他们以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为指导,主张广泛地考察与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使之成为推动明清时期古典科学发展的思想动力。
王廷相从训诂学角度,对程朱的格物说提出了批评。他说:“格物之解,程朱皆训至字。程子则曰‘格物而至于物,此重叠不成文义;朱子则曰‘穷至事物之理’,是至字上又添出一穷字,圣人之言直截,决不如此。”[24]指出程朱把“格”字训为“至”或“穷”字,“重叠不成文义”,是一种“屋上架屋之烦”、“言外补添之扰”,是违背圣人之言的。王廷相依据他的“物理不闻见,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的道理,对格物说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格物,《大学》之首事,非通于性命之故,达于天人之化者,不可以易而窥测也。诸士积学待叩久矣,试以物理疑而未释者议之,可乎?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浮,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欹测?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吹律何以回暖?悬炭何以测候?夫遂何以得火?方诸何以得水?龟何以知来?猩何以知往?晰蜴何以为雹?虹霓何以饮涧?何鼠化为鴽,而鴽复为鼠?何蜣蜋蝉,而蝉不复为蜣蜋?何木焚之而不灰?何草无风而自摇?何金之有辟寒?何水之有温泉?何蜉蝣朝生而暮死?何休留夜明而昼昏?蠲忿忘忧,其感应也何故?引针拾芥,其情性也何居?是皆耳目所及,非骋思于六合之外者,不可习矣而不察也。”[25]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王廷相所谓“格物”,是指接触、观察和探索外界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言。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地质到物候,都存在着“物理”。只有通过人们的感官去接触客观事物(“耳目所及”),才能“通于性命之故,达于天人之化”,获得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认识。这里的“物理”绝不是程朱所说的绝对之天理在事物上的体现,而是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规律性。而要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物理”),首先就要以耳目等感官去接触事物,考察事物。“必从格物致知始,则无凭虚说亡之私;必从洒扫应对始,则无过高躐等之病。上达则存乎熟矣。”[26]这样,王廷相就从认识路线上同程朱的格物说划清了界限。在致知问题上,他也不同于程朱、陆王,指出:“明道莫善于致知,……不徒讲究以为知也,而人事酬应得其妙焉,斯致知之实地也。”[26]“君子之学,博闻强记,以为资藉也;审问明辨,以求会同也;精思研究,以致自得也,三者尽而致知之道得矣。”在这里,王廷相明确指出两点:1.“致知”的目的和内容,既不是通过“格物”“推极吾之知识”,也不是“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而是“明道”即探究客观事物的固有规律性。2.“致知”的方法和途径,既不是通过一件一件地“格物”去体认“天理”,也不是通过“去人欲,复天理”去获得“良知”,而是通过后天的“博闻强记”、“审问明辨”、“精细研究等方法”获得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特别是他强调把“人事酬应得其妙”的实践活动作为“致知”的重要途径,更是一种真知灼见。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理性认识,他通过“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地理之象”、“昆虫草木之化”,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使他成为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他依据浑天说理论,认为昼夜现象是“日远而晦,日近所明”所致;太阳并无出入,只是“以人远不见,如人地耳”。依据浑天说理论,他认为天所以运而不息是“天乘夫气机”所致;地所以不坠是“地浮于窍”所致;海所以不溢是“四海会通,地浮于上”所致:陨石雨是“星之光气”所致;“日之食,彼月掩之”,“月食日,形体掩之也”。在云、雨、露、霜、电、雹、霾和四时的成因上,他以气学观点作出了近乎科学的说明。在地理地质学上,他认为地球是“水火凝结,物化糟粕而然”,“山是古地结聚”而成,平原是“水土之漫演”而成,岩石是“土之结”,原生矿物是“金气郁热,化石成矿”。他还对各种动植物作了大量的观察与研究,修正了中国古代物候学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一些新的科学成果,从而丰富与发展了我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为中国古典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继承与发挥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把“医者贵在格物”[27]作为自己一生从事本草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李时珍所谓“格物之学”,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上立论的。他说:“虽曰医家品药,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28]。这一诠释,显然是承袭了二程的“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5]的思想。正是在程朱格物说的这一科学理性思想指导下,他通过“搜罗百氏,采访四方”,足迹启遍于数省,广泛地采集各种草木矿石标本,亲自解剖动物,检验民间医方。在广泛实践与大量感性知识基础上,“察其良毒”,“考释性理”,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这一不朽的医学巨著。他按照“即物穷理”的归纳方法,建立了三界递进的本草演释体系,从而为中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
明清实测之学除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外,还有从欧洲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从明中期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实学思潮的高涨,不但拓宽了程朱格物说的科学内容,而且进一步把中国古典科学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它成为中西方科学思想的契合点,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明清实测之学的发展。
明代著名实学家徐光启面对“西学东渐”的现实挑战,在“补儒”、“合儒”思想指导下,大力提倡“格物穷理之说”,并在它那里寻找到了中西方科学的衔接点。在徐光启那里,“格物穷理之说”既含有中国古典科学的内容,如天文、地理、律历、数学、动植物学、机械力学、生理医学、农田水利学等,同时也大量吸收与容纳了当时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主要是以“象数之学”为基础的“格物穷理之学”,包括有天文气象学、测量学、水利学、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学、医学等。徐光启在“格物穷理之学”中,善于吸取西学中的有用部分,用以补充、修正与发展中国古典科学。如他在主持修订明代《大统》历法中,按照他提出的“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指导思想,大量地编译西方的历法书籍,以西方历法之优点来补充《大统历》的不足,以西方科学思想来修正《大统历》的错误。《崇祯历法》就是一部中西方历法思想会通的科学结晶。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也是在实测的基础上,将中国古典农书与西方“农田水利之学”(如《泰西水法》)巧妙结合的成果。徐光启极力称赞的《同文算指》一书,也是李之藻“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29]而成的。
方以智作为明清之际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深受“西学”的影响。他把人世间学问分成“宰理”。(社会伦理道德学)、“至理”(通几之学者即哲学)和“物理”(自然科学)三种。他所谓“格物”,也就是探讨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物理”)的“质测之学”。什么是“质测之学”呢?他解释说:“物有其故,实考察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30]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是“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的外在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物有其故”),“舍物则理亦无所得矣,又何格哉!”[31]就其研究任务而言,是认识与把握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律(“推其常变”),鉴定其物质(“类其性情”),评品其优劣(“征其好恶”)。依据他对格物说的理解,对“宋儒惟守宰理”,“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他的“质测之学”集中地反映于《通雅》和《物理小识》中。在他的这两部著作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内容,如天文、地理、动植、矿物和医学等,同时也大量地吸取了“西学”内容。据美国彼得逊教授统计,仅《物理小识》一书援引的传教士的书籍资料就占5%,其中包括西方传入的历算、物理、化学、水利、火器、采矿、造船、仪表等。这也说明,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即“格物穷理之学”)是中西方科学思想会通的结晶。
清初理学家陆世仪在实学思潮影响下,对程朱的格物说重新作了说明,指出“格即精察也,物即随事也,”“格物”就是“随事精察”。由此出发,他着重继承了程朱的格“草木之理”的“向外工夫”,认为人对草木“察其色,尝其味,究其落生死之所由,则草木之理皆可得”[32l。他把天下的知识的分成“可以不虑而知”的“心性性道德”和“必待而知”的“名物度数”两类。在他的格物说中,虽然含有心性道德之学,但更强调向外的“名物度数之学”。在他所列的“当读之书”中,除了阅读《四书》、《五经》和宋儒的性理学著作外,还要求士人阅读中国古代的科学书籍和“泰西之学”。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学、数学比中国“精密”,指出“西学有几何用法,《崇桢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在天文图中,中国的“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可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33]在他所列的“水利农田书”中,除了中国古典水利农田书籍外,还包含有西学内容的《农政全书》等。这说明,陆世仪所谓格物之学,也含有西学的内容,是中西之学合璧的产物。
清代康熙皇帝既是一位文韬武略的政治家,又是一位“留心格物”的科学家。《康熙几暇格物篇》就是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从事格物学研究的成果。该书除了讨论中国古典科学之外,还对“西学”有所介绍和评论。他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研究,既广泛又精细,如“冰厚数尺”条,详细记载了北极长年结冰现象;“达发哈鱼”条,讲述了大马哈鱼的洄游现象;“食气”条,描述了熊的冬眠现象;“定南针”条,阐述了地磁偏角现象;“石鱼”条,讲述了中生代狼鳍鱼化石;“鼢鼠”条,记载了早已绝迹的猛犸象遗骸等。他也十分注重广泛调查与社会实践,并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了理论说明。如在“潮汐”条中,康熙不但记述了他亲自对沿海各地发生潮汐的时刻不同的社会调查,而且还“问及西洋人与海中行船者,皆不同”;在“地球”条中,康熙指出中国“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在“瀚海螺蚌甲”条中,他以洪水之说解释了瀚海型地貌的成因。他还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亲自试验与选育优良稻种等。
从上述徐光启、方以智、陆世仪和康熙皇帝格物说的分析中,说明明清之际实学家的格物说,在内容上已超出了中国古典科学范畴,不同程度地吸收与容纳了“西学”成分,皆为中西方科学思想的结晶。同时,他们在格物方法上也吸取了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与逻辑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二是注重实验的“实测精神”。
明清实学家在中西学(特别是数学)的对比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科学所以落后,西方科学所以进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西方的“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即由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来发现自然客观规律的思维方法)。中国学者长期在经学思维方式束缚下,只注意儒经注疏、名物训诂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刻板僵化,往往忽视抽象演绎方法,只知其“法”(即对经验数值的运算方法),不知其“义”(即对数学原理的逻辑论证),从而阻碍了中国古典科学的发展。在明清之际,不管是李之藻的“缘数寻理”,“步步推明”的科学演释方法,朱载堉的“理由数显,数由理出”的逻辑思维方法,还是康熙皇帝的“数以理神,理以数显”的“数理合一”观点,王锡阐的“因数可以悟理”的方法,尽管还未能最后取代中国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并从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格物方法上毕竟注入了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为中国古典科学转向近代科学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极为重要的。
明清实学家深受西方“实测之法”思想的影响,在格物中,提倡实测精神,运用实测手段。这与中国古典科学的某些神秘性、直观性和主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徐光启极重“制器测天”,在农田水利上总是“手植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清代医学家赵学敏设置药圃,亲自栽培与实验,撰成《本草纲目拾遗》;王清任多次到刑场、义冢等地解剖尸体,撰成《医林改错》等。这虽说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实验之法,但它毕竟含有近代实验科学的启蒙成分。中国古典科学如能沿着西方实测之法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走向近代科学。
总之,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明清实学家在程朱的格物论中注入了西方近代科学内容,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撰写了一批中西合璧的科学论著。在格物方法上,指出了中国古典科学“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的狭隘经验论的弊病,提倡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由数达理”、注重实验的科学之路,使程朱格物说具有近代科学启蒙因子,初步实现了中西方科学思想的结合,使之成为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中介和桥梁,为中国古典科学向近代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西学”的输入和近代的“格致之学”
从明代万历年间,特别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输入中国之后,除了道学家继续宣传宋明理学家的格物致知说之外,许多学者在“西学”思潮的影响下,开始突破中国古代“格物致知”的传统观念,赋予它以近代科学的内容。这不仅表现在彻底抛弃了这一古老命题的伦理学意义,将它变成真正的纯粹的认识论命题,而且也把近代实验科学,特别是研究声、光、电、热的物理学和机械制造等看成是格物致知的基本内容,从而把格物致知说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之上。在中国近代,不少学者常把自然科学译成“格致学”,把自然科学学家称为“格致家”。例如,改良主义者马建忠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以格致之学为本。他说:“讲富强以算学格致为本。中国不患不富,而患藏富之不用,将来采矿、酿酒、制机器、创铁路、通电报诸大端,在在皆需算、化、格致诸学。”[34]这里所谓格致之学,即是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严复在阐述“开民智”时,也说:“夫朱子以即物空畀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风斯在下矣。”[35]严复把格物致知释为“即物穷理”,努力寻求西方自然科学与程朱格物说的结合点。同时,他也指出朱熹也读书为穷理是不对的,因为固守“宋学”、“考据学”和辞章之学,于国计民生无用,于救亡“无补”。所以他强调“西洋以格物致知为学问本始”,提倡学习和宣传西方的自然科学。在格物致知方法上,认为西方“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36]。从而把西方的实验方法援入格物致知论。同时,他还认为“格物穷理之用,其途术不过二端:一曰内籀(Induction),一曰外籀(Deduction)。”[37]他把西方的归纳法(内籀)和演绎法(外籀)导入格物致知说,认为这是“即物穷理”的科学方法,这比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格物穷理”的方法要高明得多。
近代洋务派认为“一切西法无不格致中出”,他们在上海、宁波、广州等地相继设立格致书院,编译《格致启蒙》、《格致测算》、《格致举隅》等书,以“兴行格致之学”为宗旨。李善兰在墨海书馆翻译西方格致之学,华衡芳在上海格致书院、湖北自强学堂、两湖书院“宣讲格致之学”,“专究乎致知格物之学”。徐寿、华衡芳、王韬等人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编译西方格致之学。王韬将上海格致书院历次课艺题目、优秀试卷以及评阅人的评语、眉批等汇编成《格致书院课艺》。他们认识到中西方虽然都讲“格致之学”,但二者是有原则区别的。陈寿指出:“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常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测皆真也。”[38]上海格致书院学生钟天纬认为:“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学生王佐才亦指出:程朱“所释者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者。”[39]在中西格致之学对比的基础上,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不能与各大国抗衡者何哉?格致之学不行也。欲求富强必先格致,士工商兵与农须各精学,各专其艺而严绝夫不富不强之本,然后富强可言,强为真强。”[40]洋务派者试图通过抛弃程朱的“义理之格致”,阐扬程朱的“物理之格致”,以求达到“真富”、“真强”之目的。
近代著名政治家唐才常对中国格物致知论作了一次总结。首先,他对王阳明以“致良知”解释“格物致知”提出了批评,指出王阳明“狃于良知顿悟者,自粃糠事功而外,即格物致知之理,亦以顽空应之。浸淫至于前明,而承学之士,益以其荒渺不可知之论,求其所谓明心见性者矣。”在抛弃了王阳明等人的格致之学后,他又寻找到了朱熹的格致之学与西学的结合点,指出:“格致之学,汉、宋诸儒以来,亡虑百十家。惟朱子‘即物穷理’一言,孕义宏深,天人靡阂,故其探索气化之功,冠绝群伦,荒浇之儒,望尘弗及”[41]他采用“因类比附”的方法,从《朱子语类》中摘引若干条科学资料,以证明在朱学的科学思想中,已包含有西方的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自然科学的内容,并以其为“格致之先资也”。由此证明朱子“其理甚实,其用甚宏,而即物穷理之洵不诬也。”唐才常肯定朱熹的“即物穷理”的科学理性精神,并将它赋予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内容,有其可取之处。但他认为《朱子语类》中已包含有西方近代科学内容,将朱子格致之学近代化,则是不可取的。
孙中山先生在《上李鸿章书》中,也把“各物致知”这一古老命题赋予近代科学的内容。他说:“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本之务,舍此则无以兴物利民,由是孜孜然以穷理致用为事。……格致之学明,则电见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机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此犹其小焉者也。至于火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电气传邮,顷刻万里,此其用为何如哉!”[42]
上述说明,程朱这派的格物说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不但是宋明古典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明清古典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衔接点,是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突破口。
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不只是借助于西方科学,同时也可以从中国格物说中寻找到它的内在根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推行“科教兴国”方针,努力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才能使中国早日跨进世界科技强之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收稿日期:2003-0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