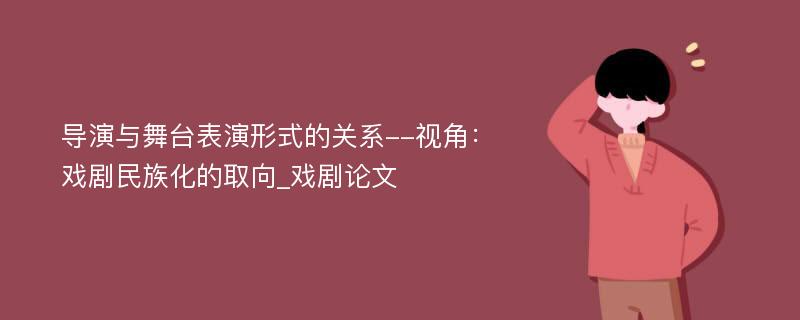
导演与舞台演出形式的关系——视觉化:话剧民族化的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剧论文,取向论文,导演论文,舞台论文,演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戏剧的国王死了,国王的戏剧仍活着。”
一切艺术都是形式发展的结果。
『概念源起』
⊙什么是戏剧导演?
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导演”条目显示:实现戏剧演出任务的艺术创作者;另根据该卷“戏剧导演艺术”条目显示:导演艺术就是创造演出的艺术。
⊙什么是舞台演出形式?
简而言之,舞台演出的形式,就是指导演赋予戏剧文学作品在演剧空间中所作的维度性的视觉化体呈和处理的方式。
⊙导演寻找、发现和确定舞台演出形式的过程,就是整合形式与内容,获得艺术的真实的审美取向的过程。
⊙那么我们又如何在充满能动的想象力和诗情的演剧空间中,寻找和发现以及确定一种完全属于中国人的、适合于中国人视觉思维和审美经验的思维原点和站立点呢?
『回顾和启示』
在斯坦尼之前,德国人理查·瓦格纳所提出的“总体戏剧”观念,以及他的系列歌剧作品,同样深深地影响了世界剧场史的发展。
自R·瓦格纳(1813~1883)倡导总体戏剧综合论以来, 逐渐形成了以剧本和演出作为研究对象的导演学。导演学明确了导演艺术的任务,确定了剧本、演员和观众“三位一体”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戏剧是以演出为目的的并融汇多种艺术种类、相互有机结合成整体性的演剧空间多维形象的特殊形态的综合性艺术。该特性的确立,界定了导演的职责和现代导演艺术的特质。
战后的冷战时期,全球戏剧进入多元呈现态势,综合因素的增加,各综合成分适应不同风格、流派的演出,部分职能大有改变,戏剧属性有了全新的发展, 原有的综合艺术观念处于不断的变异之中。 战前以Antonin·阿尔托、Adolf·阿庇亚、戈登·克雷、Max·莱因哈特、 梅耶荷德等戏剧大师倡导的以导演为主,导演绝对控制整体演出的“导演中心学派”(亦称“导演戏剧”)在战后戏剧表现美学理论的彰显和剧目导演实践中得到空前的光大和发扬,迄今起着全球性的广泛影响。
“导演中心学派”(或称“导演戏剧”)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那种认定“导演是为演员的新的创作助产的接生婆,导演的创造要死在演员创造中而复生”,导演是“演员老师、镜子”的观念截然不同;强调导演是“演出的作者”,要求“导演活在舞台上,导演主宰一切,独立创作,演员不过是这位主要创作者手中的材料而已”;认为要“结束戏剧从属于剧本的状态,恢复一种介于姿势和思想之间的独特语言的观念,而不再继续依靠神圣而权威的剧本,是必需的。”; 认为剧中所有要素均由一个人来控制掌握即导演,力求对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中的虚浮性进行革命,代之以象征性的形式,用光将所有演剧空间的视觉要素统一成一个整体构筑“有韵律的空间”;认为自肯布尔家族到埃德蒙·基恩或麦克里迪和亨利·欧文抑或安托万乃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矫揉造作,应该用立体的体量、光和影来取代自然主义的琐碎细节,剧场应该是视觉的,是直接诉诸感官满足视觉享受的场所;认为剧本只是剧作家提供的一个骨架或大纲,如何表现则由导演来完成,戏剧的演出风格与剧场建筑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认为一切戏剧艺术的最重要本质是它的假定性本质。
在当代,欧美戏剧已进入后现代主义创作阶段,风格特征已呈现出零散多元化、多中心、多边缘状态。后现代主义戏剧的创作原则可概括为:矛盾、更替、中断、任意、极度、短路原则。这些原则直接规定着并体现为作品中的特征、效果,即不作选择地把各种可能性矛盾地展示在作品里,出现叙述的更替;用这种更替来破坏作品的连贯性,并进一步追求作品中的任意性,大量的隐喻、转喻在作品中出现,力求在作品与现实,艺术与生活间造成短路,去采用虚构与事实的结合来缩短与生活的距离,甚至将作者与谁是作者的问题同时放入作品,包括对作品在使用传统手法的过程中,在作品中当即揭露其运用的意图等等。
后现代戏剧的表征:
1848~ 1890~1950~
资本主义的 国家/古典 垄断/帝国 跨国/晚期
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
能源/动力 煤炭/蒸汽机 电力/马达核能/反应炉
文化风格
写实主义
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主要艺术媒体小说 电影 电视
主体 有中心的取消中心的已失去中心的
语言符号 具有指涉性的 约定俗成的成了符征之流
客体
真实的世界相对的世界虚构的文本
代表性剧作家 易卡生、契诃夫
皮蓝德娄、贝克特海诺·穆勒
代表性戏剧家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阿尔托、布莱希特 威尔逊、福曼
以上这种演剧观在中国新时期话剧导演艺术创作中同样得到光大和发扬,在众多脍炙人口的剧目实践中,从初期导演主体意识和探索意识的觉醒,迄今为止有系统有理论自觉地从“再现美学”向“表现美学”拓宽的阶段性学术概括总结。足可以坦率地说,这是对斯坦尼、丹钦科演剧体系做了民族化式的考量与修正,尽管是改良的抑或是调和主义式的,无疑这是49年建国以来戏剧导演学理论在创造舞台形式范畴上的所获得重大突破和成就。
『体认与发现』
一个导演是一种生产思想和趣味的机器。作为舞台演出的始作俑者,其方法论的终极意义在于通过运用假定性手段筑构演剧空间表现性的视觉化形象,若从手段上的意义去定位导演,导演就是演剧空间表现性的视觉形象的创造者,这个手段运用过程就是一个导演赋予完全的属于自己的那个演剧观念的同时,去构筑和创立属于绝对个性特质那个演出形式的过程。一个剧目的舞台演出缺乏形式的养成,就是一个导演赋予戏剧文学作品在演剧空间中所作的维度性的视觉化体呈和处理方式的缺失。
需要进行强化辨伪的是,导演潜心创造某种让人心仪的有意味的舞台形式的过程,绝对不以导演作为演出的作者排斥戏剧文学作品内容为代价去获得艺术的真实的审美取向。
所谓的形式与内容的长久之争,事实上是可以被看作是形式研发把握过程中视觉要素与听觉要素争夺主次位置的之争。
那种由来已久贬斥形式创造的老掉牙的诽谤,动则就将导演打入“搞花架子玩花活”的形式主义行列,某些话语权的把持者任何时候都将形式和内容来作极其滑稽和弱智的条状分割,极其主观地认定导演的终极任务就是以牺牲文本践踏文本为代价去创造演出的形式。而且这种常识性的谬误迄今还被奉为评价戏剧演出优劣的圭臬。事实上这种以文本作为安身立命之地,以文本的内容作为唯一衡量戏剧演出优劣以否的标准,长久以来几乎是固执而病态地成为话语权把持者的职责。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著名艺术家闻一多先生就在《戏剧歧途》一文中,指出戏剧之所以不能达到“纯形”的涅槃世界,永远注定了是一付俗骨凡胎,永远不能飞升,原因“那都是害在文学的手里”。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最精致的结晶,我们没有理由把语言从戏剧中驱逐出去,我们只反对仅把戏剧当作语言的艺术,反对戏剧成为语言文本的奴隶,但并不反对在戏剧中运用语言。
一般而言,阅读戏剧文学作品的读者多为专业人群,一般读者群对戏剧文学的文本并不感兴趣,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剧本月刊》、《新剧本》《剧作家》在邮局的报刊栏抑或街头的报摊书市成为热卖的货品甚至被陈列,文本若不被剧院团列为排演剧目,终究只能是一堆铅字,一位剧作家之所以成为剧作家是因为他的文本被导演屡屡排演并获成功,这一成功的结果就是导演寻找、发现和确定舞台演出形式的过程,就是整合形式与内容、获得艺术的真实的审美取向的过程。因此剧作家称谓的合法性存在与否,是导演赋予文本在演剧空间中所作的维度性的视觉化体呈和处理方式所给予的。
实践告诉我们,戏剧文学从来只是文学的一个分支,虽有其相对独立的存在价值,但剧本(纯文本)只是为整体戏剧演出提供了一定的文学基础,只是整体演出的一个部分,并不代表演出的全部。所谓“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应源出此别无他意,若有他意,那导演势必落人“剧本不好导演白忙乎”的汗流浃背之境,这种内容与形式被人为割裂化的症候体现在导演与剧作家合作间,竟成为二者交恶之后互相攻讦的借口。所谓导演和剧作家之间的合作关系已成为戏剧演出的一种独特的风景,亦成为内容与形式常被话语把持者以强化和争辩的出师之名。
岂知,内容与形式本身就是一体两面,若是剧作家以全方位地观照审视自身的创作,通晓舞台演出规律,对导表演创作有所涉猎,自觉地向演出靠拢并溶为一体,所呈现的剧本就不至于使导演掉入重新再创作剧本的泥潭,因为在体制内主流戏剧创作中,编剧是文本的始作俑者,导演毕竟不能替代剧作家的一度创作身份,从通俗的意义上说,导演与剧作家的关系仿佛是永远的夫妻关系、兄弟关系,不是来自不同阵营的阶级敌人的相互利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一个成功而优秀的导演背后都有为之合作长久的剧作家,如斯坦尼与契诃夫、焦菊隐与老舍的之间的相得益彰的合作友谊。如此,导演才能轻装上阵精力百倍地去研发创造新的舞台形式。
因此,我们也决不否认一部好的戏剧文学作品完全可以一字不动地作为视觉形象体呈于演剧空间,但这意味着该剧作在平面文字阶段就必需具备高度形式审美愉悦特质。可它终究不能脱离导演将其立于舞台的这样一个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舞台形式不自觉产生或自觉养成的过程,即便是所谓的剧本朗读会,也具备特定空间扮演特质,只不过是把扮演性降低,但依然存在。即便是剧作家兼导演职能于一身,也不能逃脱这一过程,何况乎我们这些解牛的庖丁呢?!
在考量与讨论舞台形式的此间,我们仍然无法丢开被人为复杂化的甚至是令人厌倦的“再现”和“表现”说的阐述。
所谓艺术表现,就是从某种情感状态(或体验)向着审美理解转化。所谓内在情感外化,不是情感的释放或涌出,而是改变它的性质,使它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变成一种艺术的理解。艺术家的目的并非像因果论所说的那样,将某种内在情感展示出来,而是真正理解这种情感,而这就意味着从一种“情感状态”转变为一种“审美概念”(或美的意象)。表现就是对一种感情的审美理解。
我个人倾心于舞台形式的“表现”说。因为这符合本民族的审美原则和经验。“表现”相对“再现”在视觉语汇体呈上更具备想象力和冲击力,尽管我们相信“再现”在某些时刻也具备赤裸的写真轰炸性,可舞台在本质上终究是个扮演性、假定性的空间。
与此对立相反的斯坦尼认为:一切“剧场性”(即假定性)的东西都显得不自然和虚假,与心灵及真实格格不入。苛求在舞台上纤毫毕现地再现剧中人物生活的时间和空间形态,即在时间上按生活写真复制的推进方式,以“现在进行时”的一维性时态向前演进,在空间构筑上则几近逼真地展现真实生活的物理环境。将空间限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时间的限制相应辅之。导演的任务前提就是在“第四堵墙”内炮制生活的幻觉。观演之间只能有“间接交流”杜绝“直接交流”,斯坦尼甚至认为:我们的艺术只认可…那种跟对手交流的形式,即用亲身体验到的情感去跟对手交流。其余的交流方式,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是要予以摒弃的。演员必需“过着独立的生活”,而观众“不过是偶然的目击者”。
“再现”的高度封闭性空间结构样式固有其鲜明特点,这种“墙”外挖个小孔观剧的方式,使那种潜意识中的窥视癖的大众趣味得到满足。但对于导演施展他充满诗情哲理的想象力而言却是一场噩梦。导演主体能动创造的表现,决无法越过对剧作所描述的客观环境和人物关系的逼真复制之雷池,所展现的人和事物的联系,是借镜生活写真面貌、生活表面逻辑而直接不易觉察地展现的。导演的艺术创造价值只能消失于剧作者言语创作的主体性之中而万劫不复。
世界存在着,仅仅复制世界是毫无意义的。
视觉的再现往往是艺术家低能的标志。一位低能的艺术家创造不出哪怕是一丁点能够唤起审美感情的形式,于是便求助于日常生活感情;要唤起日常生活感情,就必定去使用再现手段……如果一位艺术家千方百计地表现日常生活感情,这往往是他缺乏灵感的标志;如果观赏者总爱在形式中寻求日常感情,这是他缺乏艺术敏感力的症状。优秀的视觉艺术品能把有能力欣赏它的人带到生活之外的迷狂中去,以艺术手段唤起生活感情则无异于用望远镜看新闻。事实上,追求酷似远非是艺术创造中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反,它却可能是最不能达到美的坏因素。欲使作品逼真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我们又如何在充满能动的想象力和诗情的演剧空间中,寻找和发现以及确定一种完全属于中国人的,适合于中国人视觉思维和审美经验的思维原点和站立点呢?
传统欧洲戏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歌舞成分逐渐减少,戏剧的因素却逐步增强并成为主导因素,最终发展成为以外部形体动作和对话为基本手段的戏剧形式。而中国戏曲则是在戏剧性成分逐步增强的过程中,保留了大量的歌舞成分,形成了歌舞抒情性与戏剧性相融合的戏剧形式。
我个人以为就是要站在中国戏曲这个国粹巨人的肩膀上,垂首研探全人类内在共通的禀性,在不断的洞察并汲取国粹菁华和养成中去构建一种视觉体现为主、听觉传递为次的,表现性的极具民族审美品位和诗格的话剧。
应该说近50年来,焦菊隐先生也许比其他任何中国戏剧导演都提供了更加强烈地影响了我们去进一步认知话剧民族化本质的方式。关于创造话剧的“新形式”的问题,焦先生认为:“创造新形式,就一定要根据话剧本身的条件和特点,特别要根据它所反映的生活现实内容,借鉴戏曲的美学处理方法,创造性地丰富话剧的表现手段”,当然这种“话剧的新形式,决不能是戏曲的形式。”
倘若我们对理清导演与舞台形式的关系,是站立在当代性的立场上,对中国戏曲的本体三大特性之综合性、虚拟性、程式性做进一步深化体认,对构建一种视觉体现为主、听觉传递为次的,表现性的极具民族审美品位和诗格的话剧,也许能获得一些柳暗花明的启示。
1.研发它的综合性,是在于进一步挖掘演剧空间中听觉因素的潜在放大可能度,即将听觉作为一种视觉形象来进行造型处理。约翰·凯奇在他著名的《4’33”》中,舞台上演奏者一动不动地在钢琴前静坐了4分33秒,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开和关上钢琴的琴盖来表示三个乐段的划分,目的在于使听众在沉寂无声的时候注意到周围发生的各种偶然的声响,以及对这种声响的想象,这种极端的才情为我们开启了思路。
纯粹从技术角度理解,戏剧当中使用的语言是要通过表演为介质,在本质上是非陈述性的,非抒情的,包含着动作,是一种能够唤起空间视觉感的声音,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语言,这种声音在空间中应成为一种直观,是形体动作和心理活动的直接投射,而不是文学修辞。作为空间的一种声音,并不限于对话、独自和旁白的方式,声音与声音,声音和经动作构成的调度场面可以有多向度的组合。演员口中发出的音节、音乐、音响的一切形态原则上的声音都可以成为被视觉化的语言形态。它既可以是完整的也可以是破碎的、非逻辑的、抑或突如其来的,以此使声音成为一种身心的需要,而不只是文学修辞表达和传达某种意义,要让声音成为一种视觉的流程,使不同时态的声音都可获得直观可感的空间表现性的视觉语汇构建,使声音产生具有原始咒语般的暗示力量,将观众带入任何假定的情境。这样,就能激活扩大导演的想象力疆界,使导演在创造舞台形式过程中不仅仅将注意力放在肢体动作语言和一般性的舞台视觉形象上,还要注意研发声音在戏剧演出形式中的存在的巨大潜力。在本年度初冬来华的日本民间剧团少年王子馆演出的实验性剧目《剧终》里,角色描述杯中物,对声音(一句语词)近五十遍的重复拉长的实验性处理,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亦如美国导演罗伯特·威尔逊早期作品《一封给维多利亚女皇的信》中,捧着信笺的少年们反复宣读其间内容,声音在连续长时间的不断的反复中被相互生硬的打断,从而形成一种声音的被切割感,信的文本内容被有意忽略了,消失在这种声音的空间表现性的视觉语汇的体呈之中。又如他震动国际剧坛的著名剧目《沙滩上的爱因斯坦》中,极简主义音乐旗手菲利普·格拉斯作曲配乐,演员在音乐旋律不断的重复中反复地做着同样的动作,此间声音(音乐)以一种几乎独立存在的角色身份演绎着空间表现性的视觉流程,构建着空间表现性的视觉语汇。
2.研发它的虚拟性,在于进一步挖掘舞台时、空间处理的高度假定性和扮演性,使整体演剧空间成为视觉化造型处理的诉求对象,并不单指对演剧空间物理性的外部处理,应该是导演驾驭整体演出所有要素来挖掘视觉的潜在表现可能。
极其建设性地在不断发现创造视觉潜在表现的种种可能,在罗伯特·威尔逊创建的意象剧场中,如他创造视觉上的“停格”、“倒带”、“暂停”诸多意象,形成了他独具个性的时间感。时间是威尔逊式戏剧的外部形式,而空间则是他的内核。威尔逊认为“我发现慢慢的动、慢慢的说话,其实可以变成很戏剧化的。”他通常统兼舞台设计和灯光设计于一身,经常以“公寓”来形容他的舞台空间,认为“所有的艺术家都会在当中找到他最适合的房间”,使其构建的演剧空间里永远有着令人惊艳的视象。
因此,视觉化将不可置疑地作为导演构建舞台演出形式的第一存在。由此出发去构建连续流动性的空间来展现空间的无限性。
中国戏曲那种演员以身带景,空间随着人物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一般它是通过主要四种虚拟方式来实现的:1).通过上下场的形式自由转换空间;2).以曲词叙述空间的转换,3).用程式化的动作表现空间的流动;4).用圆场等程式并辅以人物叙述说明地点变动转换空间。这种变化的简约精巧,通过个体演技的渐次演绎而不断地使空间产生变换,如水一般流动不居,在没有实际景物的存在下来展现瑰丽神奇的天上宫阙抑或玲珑清丽的水中龙宫,令人叹为观止。而这些,都是在演员视觉化的表演、叙述、和观众的视觉想象中共同来完成的。
构筑未来表现性的极具民族视觉审美品位和诗格的话剧就要汲取以上这种虚拟件的内在精髓,从初期简单的模仿逐渐走向中期的探索进入成熟的创造,从而建立自身视觉化的语法乃至体系。
3.研发它的程式性,在于进一步挖掘话剧表演的肢体动作的直接表现性和场面的仪式性,即强化话剧表演在空间中摆脱对文学修辞的一贯的依赖附着,使其肢体动作具备独立的视觉审美价值。这并不意味着照搬戏曲程式,在传统中国戏曲中的程式是固定的,可话剧舞台形式却渴望创新,显然这是一个迷人的矛盾,我们不能在重复西方传统戏剧格式的同时,又掉入到东方戏剧传统的程式的束缚中去,只能借鉴固定的程式,在程式中纳入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意识和趣味,创造新的“程式”这一瓶颈。在本年度上演的现代京剧剧目《骆驼祥子》中获得个案性的重大突破,其突出贡献在于主要人物样子的“车舞”程式表演上,该演员在原地张弛有度奔跑的肢体动作与戏用大道具黄包车达到几近完美的融合,供观众想象的无限的时间、空间的流动感在程式动作渐次展开中产生,使我们极其强烈地感受到这一高度提炼于现代生活的新程式所给予的充满诗意的动态视觉美感。这表明程式是完全可以在现代生活中被发现被提炼被创造出来的。演员作为舞台形式体呈的主要介质,话剧表演就应该向戏曲程式学习,在一戏一格中借鉴这种高度视觉化的极简主义式的表演方法,使话剧表演技巧逐渐具备独立的视觉审美价值。
苏联著名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曾经预言:“也许,中国戏曲将帮助欧洲戏剧从自己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从照相式的现实主义和记录式的表演中解脱出来。……我毫不怀疑,未来的戏剧将体现出现在看来似乎格格不入的两大戏剧因素的特殊结合。”
『手段与眺望』
导演创造舞台形式的双刃剑:
1.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演剧艺术假定性美学原则和具体手段,是区分和辨别一个戏剧导演专业能力的试金石。
著名表现派导演梅耶荷德在1936年一次谈话中回想起观看梅兰芳的演出,曾高瞻远瞩地预言:“任何戏剧艺术都是假定性的,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假定性……我想,梅兰芳的假定性最接近我们的时代。”
近20年来,假定性一词和背后隐藏的反动力成为中国戏剧回归本体探索的涉渡之舟;20年后中国戏剧创作群落中只被褪尽铅华的残存的少数演出形式探索者们试图还以此为底牌全力抵抗的,是无所不在的又一轮戏剧伪现实主义化的狂浪,舞台上鲜见有鲜活的形式研发,空间中全面充斥着形式想象的赤贫,这印证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历史总会二度出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
近20年来我们所争论不休舞台假定性究竟是什么?我想,就是激活在有限演出时间和单一的演剧空间内,视觉化地表现广阔生活的无限可能性。
德国科学家巴道夫斯基革命性地界定了空间三向维度的概念,作为演剧空间的物理属性已然存在,而戏剧行动的加入,使其在与时间相结合而不断演进整合的状态中获得了四维的向度特性。焦先生说:“戏曲……它可以说是典型的‘正式舞台’学派。这派中心理论认为,在剧场里消灭舞台感觉(即假定性)是不可能的。……取消舞台的感觉既然不可能,那么,索性向观众坦白地宣布,这就是舞台,这是正正经经的舞台,这就是在演戏,而把一切人引入艺术的真实意境的工作,尽量集中在表演上边,岂不更好些?因此,在这种‘正式’舞台上,一般不用写实而用风格化的布景,或者在最小的限度上利用一些写实的道具。”
因此,必须承认假定性是演剧空间本体特质,导演研发创造舞台演出形式才具备广阔的可能性。一个空荡荡的舞台,由于导演给予演员的富于想象力的表演和观众运用想象力的欣赏,无形变成了有形,导演让观众自由地从行动世界走向内部感受的世界,空荡荡的舞台上下仅能容纳整个世界,也能表现人的一切方面,使之成为视觉审美的演剧空间和哲理诗情的演剧空间。
2.正确寻找和确定和把握一个具体剧目的演出总体形象(即演出形象种子)是衡量一个戏剧导演总体驾驭剧目演出能力强弱,美学品位高低的分水岭。
一个合格优秀的导演作为一个剧目完整的演出的作者,就需努力在哲理内涵上给予总体的把握,这个哲理内涵的总体把握在导演学上被称之为“演出的形象种子”。“演出的形象种子”就是导演对一个演出整体的哲理把握。形象种子是一个蕴涵诗意的形象的哲理,能够诱发创作群的创作热情,它在理念上和形象上都应该是深刻的鲜明的抑或是有激发力的,甚至可能是多义性的,因而这颗“形象种子”应该凝练成一个象征,一个蕴涵哲理的象征形象。一个可以通过视觉、听觉形象被诗化地呈现在演剧空间内的象征。如佐临先生所言,意象的功夫是导演的法宝,有了它,他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没有它,他休想有什么成就。
需要进行强化辨伪的是,导演潜心创造某种让人心仪的有意味的舞台形式绝对不是导演作为演出的作者的最高任务所在。它的全部目的就是表现人,康德说:“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决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使用,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戏剧作品,应该以人自身为目的,而不应该把它当作传达某种观念的手段。”
以此为最高目的,正确运用手中的双刃剑,来正确揭示、强化凸显一个具体剧目演出的内在人文涵义、诗情哲理(同时这也是考量一个戏剧导演人文修养深浅的水平仪)。从而才能做到一剑在手,天下我有。
导演赋予演剧空间形式实验的先锋性不仅仅是一些反常规的舞台装置的集锦,它还应该表现为导演超常规的视觉化思考,表现为导演超前的视觉洞察力和视觉想象力。一个导演为剧目排演确定某种形式时,就是将形式与内容作为整体去考量的,在这个意义上形式就是内容。倘若一个剧目仅在形式上标新立异,而在内容上去迎合某种时尚,形式与内容也就身首异处了,又倘若只是在形式上做文章,在内容上又流于空洞,它可能会抽空实验性的实在内容,而把自己附着于一个苍白的技巧外壳中。当代中国戏剧的廉价乐观主义化和日益的商业化的对自由的先锋精神的双重阉割,无疑是演剧空间形式不断发现的终结。
瓦西里·康定斯基认为,艺术家总是站在一个与众不同的立场上,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观看这个世界。随着这种新的视点和视象被愈来愈多的人接受,它自身又沦为传统的陈词滥调和毫无生气的老生常谈,而这些陈词滥调反过来又激发出一种对更新的艺术视角的需要,如此下去以至无穷。那么,在戏剧创作中的导演对演剧空间形式的研发应当是由进行突击的导演和作家的一个创作群所组成的。这群人应该是僵化体系的反对者,应当是一种前风格,是一种变化的方向,相信这种变化终将被接受,并且真正地改变一切。因而,被人们称之为新戏剧的东西,通过它的表达、探索,有着一种高级的要求。可以想象,一切革新的尝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因循守旧和精神上惰性的反对,也是必然的。正是这种必然成为一种参照系,为每一次的突袭提供了反作用力。
展望下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实在需要一种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气质;需要侠气、热血、极致。而站立在上下世纪之交的我们,综观20世纪中外戏剧创作血路心城,名留戏剧青史的大师和他们所实践的脸炙人口的剧目,阿庇亚、戈登·克雷、莱因哈特、梅耶荷德、阿尔托、格洛托夫斯基、彼得·布鲁克、罗伯特·威尔逊、焦菊隐、徐晓钟……
试问,在每一道历史刻度上哪一个那一位不是靠着形式的革命性创造而安身立命的?!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迟疑地认定,寻找、创造、确定具有鲜明视觉化属性的舞台形式是一个导演存活于演跨空间的生命起点。如同俄国当代大师级导演托夫斯托诺戈夫认为的导演的主要才能之一是视觉感。缺少这种视觉感,便无法从事导演这门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