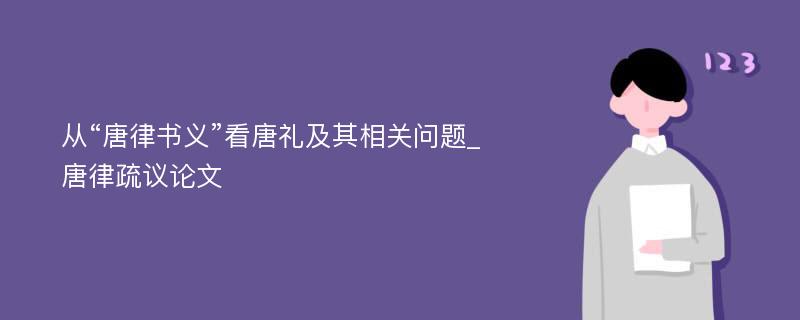
从《唐律疏仪》看唐礼及相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律论文,看唐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K20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 —1763(1999)01—0050—06
我国古代的成文法源远流长。保存至今最古老而又粗具刑法体系的法律文献是《尚书·吕刑》,流传后世而其系统大体完整的成文法数《唐律疏议》较早。
长孙无忌等人撰于永徽年间的《唐律疏议》,“其所疏释的律条基本上定于贞观,而律疏的部分内容和文字又是永徽以后直至开元间多次修改的产物”,所以有专家做出结论说:“这种整体的连续和局部的变化告诉我们:《唐律疏议》并非永徽或开元一朝之典,而是有唐一代之典。”(看刘俊文先生为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律疏议》写的《点校说明》)我们认为这个结论在原则上基本正确,但在细节上实不尽然。
李唐一代法律由律令格式组成。“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唐六典》卷六)律令格式的依据又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礼。
撰写以及改定《唐律疏议》的那些达官贵人当然是站在当时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制定律条并加以疏释的。疏文和律文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都起到体现和维护李唐一代礼制的重大作用。可以说:《唐律疏议》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将法和礼的关系体现得最为完整而又较早的典型之作。
一 《唐律疏议》的指导思想
长孙无忌等人永徽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进律疏表》云:
伏惟皇帝陛下体元纂业,则天临人,……仍虑三辟攸汷,八刑尚密,……刑靡定法,律无正条,徽纆妄施,手足安措?乃制太尉、扬州都督、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无忌……等摭金匮之故事,采石室之逸书,……撰《律疏》三十卷,笔削已了。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
据上引表文,唐高宗及其所宠信的大臣长孙无忌等人承认当时国家因为法律未定而造成的麻烦(“徽纆妄施,手足安措”云云),《律疏》(即《唐律疏议》)之撰定与施行,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麻烦。《周官·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长孙无忌等人谓《律疏》为“三典之隐括”,实以为该法律可施行于新国、平国与乱国,任何世道皆可以此法治之,故其下文自诩该法“信百代之准绳”。又,上引表文“临人”之人,乃避太宗世民之讳而用以代“民”字者。临人即治民之意。可见制定《唐律疏议》的李唐君臣认为刑法用以治民治国,自无庸置疑。
早在先秦典籍里就有不少思想家政治家论述过礼的功用,譬如:
夫礼,所以整民也。(《左传》庄公二十三年)
夫礼,国之纪也。(《国语·晋语四》)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是礼亦用以治民治国者。礼与法律是治民治国的两种工具,礼法相通,礼法相依。长孙无忌等人《进律疏表)又云:“律增甲乙之科以正浇俗,礼崇升降之制以拯颓风。”礼与法律有同等作用,都可以拯风正俗,唐代政治家是明白其中道理的。
现在我们要说明的是:唐代不少法律是据礼义制定的。对某些法令而言,礼为法之依据。《唐律疏议》可以为我们这个论断提供多处证据,譬如卷一《名例律》“十恶”条“七曰不孝”:
注: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及诈称祖父母、父母死。
疏议曰: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而问故。……
今按,小戴辑《礼记·奔丧》:“始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可见疏文所谓“依礼”并非妄言,实在是有古礼做为依据的。“十恶”条“八曰不睦”:
注:殴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尊属。
疏议曰:依礼,夫者,妇之天。又云:妻者,齐也。……依礼:男子无大功尊,唯妇人于夫之祖父母及夫之伯叔父母是“大功尊”;“大功长”者,谓从父兄姊是也;“以上”者,伯叔父母、姑、兄、姊之类;“小功尊属”者,谓从祖父母姑、从祖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舅、姨之类。
今按,《仪礼·丧服传》云:“夫者,妻之天也。”《礼记·郊特牲》:“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为妇之天,妻与夫齐(注:又见于《白虎通义·嫁娶》及小戴辑《礼记·曲礼》注。),是古礼之信条。“男子无大功尊”云云,亦可由《仪礼·丧服》经传推知其有据。然则《唐律疏议》此文所谓“依礼”实亦可信。又如此书卷九《职制律》云:
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
疏议曰:……“及进御不时”者,依礼“饭齐视春宜温,羹齐视夏宜热”之类,或朝、夕、日中进奉失度及冷热不时者,减罪二等谓从徒二年减二等。
今按,《礼记·内则》:“凡食齐视春时,羹齐视夏时”。《文王世子》、《内则》有关于朝、夕、日中进奉诸事的记载。可见《唐律疏议》此处所谓“依礼”亦非妄言,亦有古礼做依据。卷九又云:
诸乘舆服御物持护修整不如法者,杖八十。若进御乖失者杖一百。……
疏议曰:乘舆所服用之物皆有所司,执持修整自有常法,不如法者杖八十。“若进御乖失者”,依礼:“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之类,各依礼法;如有乖失违法者,合杖一百。……今按:“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语出《礼记·曲礼上》。是《律疏》此处所谓“依礼”,非以古之同类曲礼为依据而何?
唐人制律修法,其条目细节有直接以礼为依据者,已如上文例证。论其大纲核心,其原则要旨,固依乎礼,请看《唐律疏议》卷一《名例律》: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代政治家视礼为政教之一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本者根本,用者行用(用途),正与我们上文据《律疏》原文而作的“唐代不少法律是根据礼义制定的“这一判断相合。《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唐人定法,显然师法孔子,也注意到德礼政刑之于治国教民,各有其应有的位置,皆不可或缺。
唐人以法入礼,依礼制法,以法代礼,以法护礼,《唐律疏议》一书可以提供这些方面的许多证明。四库馆臣尝言及“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注: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二史部政书类二《唐律疏议提要》。),我们认为此说不尽然。由于阶级立场与认识能力的限制,长孙无忌们不可能尽得“古今之平”,而“谓唐律一准乎礼”却是客观史实,基本可信。清代大学者孙星衍撰《重刻〈故唐律疏议〉序》(注:见岱南阁丛书本。收入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律疏议·附录》。),亦谓“律出于礼”。早在此前一千多年,班固在刘歆《七略》基础上撰《汉书·艺文志》,其中写道:“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法以辅礼制,律出于礼,古代学者早已把当时礼与法的关系说得清清楚楚。陈寅恪先生以为“礼律古代本为混通之学”(注:见《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四《刑律》。),他的说法未免有含混之嫌。
为治民治国而依礼制法,法表礼实(注:元·王元亮《唐律释文序》(收入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律疏议·附录》)谓“刑者礼之表”,此说颇精,非深明乎礼法者不能道。),以法行礼,以法护礼,以法律表现礼治,而法与礼皆表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这就是《唐律疏议》的指导思想。刘俊文先生的《唐律疏议笺解·序论》说:“唐律的真髓蕴含在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之中。”“质言之,唐律的全部律条都渗透了礼的精神。”他说得很对。
《唐律疏议》主旨既明,下文请从此书看李唐礼制以及礼仪。
二 《唐律疏议》反映的宗法制度
先秦礼书与七十子之徒所作传记,都曾着力阐述宗法制度。以法律形式明文肯定、大力维护宗法制度,迄今所见保存最完整者,殆非《唐律疏议》莫属。
《律疏》卷二十五《诈伪律》云:
诸非正嫡不应袭爵,而诈承袭者徒二年。非子孙而诈承袭者,从诈假官法。若无官荫,诈承他荫而得官者徒三年。……
疏议曰:依《封爵令》,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以次承袭具在令文。其有不合袭爵而诈承袭者,合徒二年。……
按:据此律疏,可知有资格承袭先人官爵者是正嫡,起码也该是子孙。这在私有财产制度为主的社会里是不言而喻的。由是立嫡的事就受重视了。
《律疏》卷十二《户婚律》云:
诸立嫡违法者,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得立庶以长,不以长者亦如之。
疏议曰:立嫡者本拟承袭。嫡妻之长子为嫡子,不依此立,是名违法,合徒一年。“即嫡妻年五十以上无子者”,谓妇人年五十以上不复乳育,故许立庶子为嫡。皆先立长,不立长者亦徒一年,故云“亦如之”。依令:无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孙;无嫡孙,以次立嫡子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子;无庶子,立嫡孙同母弟,无母弟立庶孙。曾玄以下准此。无后者为户绝。
按:这一段疏议已将宗法制度精髓大体道出。首先考虑的是立嫡子,无嫡子则立嫡孙,无嫡则立嫡之母弟,无嫡之母弟则立庶。立嫡为重,立长为重,程瑶田《宗法小记》(注:《清经解》卷五百二十四。)谓“宗道”即兄道,那是说得很对的。李唐律令的贡献,一是明白地规定用法律保障立嫡,对违法者要处以刑罚;二是明白地限制立庶的前提是“嫡妻年五十以上”而无子。妇人年五十而无子,则终其一生难以有子矣。嫡妻年五十而无子,则立嫡殆无可立矣。“立嫡者本拟承袭”,立嫡既不可能,为传承大计,不得不立庶矣,因为庶毕竟还是自家子孙,同宗同一血统中人。倘若并庶亦无,则无后为户绝矣。
又按:《律疏》卷四(属《名例律》)最后一条律文之下有一段疏议说:“依令,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无嫡子,立嫡孙。”此下文字与上引卷十二疏议“无嫡孙”句下全同,又云:“若不依令文,即是以嫡为庶,以庶为嫡。又准令:自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若违令养子,是名违法。即工乐杂户当色相养者,律令虽无正文,无子者理准良人之例。”这里提出了养子继承本宗的原则,即“听养同宗于昭穆合者”,不得违令养子。此原则,对于工乐杂户等人家也是适用的。当然,“违令养子”与“以嫡为庶,以庶为嫡”,都是违法的(违令违法性质相类)。
《律疏》卷十二记下了唐代养子的法令条文:
(1)诸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养女杖一百。官户, 各加一等。……若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
疏议曰: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若有百姓养杂户男为子孙者,徒一年半。……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良人养部曲及奴为子孙者,杖一百。“各还正之”,谓养杂户以下,虽会赦,皆正之,各从本色。……
(2)诸养子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徒二年。 若自生予及本生无子欲还者,听之。即养异姓男者,徒一年,与者笞五十。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听收养,即从其姓。
疏议曰:依《户令》,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既蒙收养而辄舍去,徒二年。若所养父母自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本生者,并听。即两家并皆无子,去住亦任其情。……异姓之男本非族类,违法收养,故徒一年;违法与者,得笞五十。养女者不坐。其小儿年三岁以下,本生父母遗弃,若不听收养,即性命将绝,故虽异姓,仍听收养,即从其姓。如是父母遗失,于后来识认,合还本生;失儿之家量酬乳哺之直。
今按,由上引《律疏》可知唐代社会养子之法,普遍奉行“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这一原则之外,还有贵贱“各从本色”、既蒙收养则不得随意割舍这两项原则,还有收养异姓男的规定。如此,养子之法一是限于同宗中昭穆相当者,二是限于同一阶级阶层,三是收养之后非收养者不愿留养或被收养者本生父母无子,不得终止收养者与被收养者的关系,四是收养三岁以下异姓男不算违法,异姓男可以改从收养者之姓。概括而言之,一是同宗性,二是阶级性,三是稳定性,四是权宜之计有限性。前两者为主为重,第三者为辅,第四者为次为轻。同宗而昭穆相当,是血统伦常不变的基本保证。各从本色,则是保持贵贱身分不变的措施。养子要求同宗而昭穆身分相当,自是门阀制度的继续。养子而要求法律保障其稳定性,也是维持门阀制度的需要。但如同宗无子、无昭穆相当者,则收养三岁以下异姓男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性办法。无论是维持门阀制度的措施,还是作为权宜之计的补救性办法,都是宗法社会宗法制度的必然产物。门阀与宗法,其观念与制度显然都是相类相通甚至相同的。异姓男被收养而改从养父之姓,或者还本生之家,难道不都是宗法的要求吗?
《律疏》卷十二又云:“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此处所谓“继入后”,即后世所谓“过继”;从被继者的角度言之,即上文说的所谓“养子”。惩处“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可见唐人对宗法制度重视的程度,决不在历朝之下。
宗法与丧服关系最为密切,唐代丧服制度是唐代宗法的突出的表现形式之一。请于后文论之。
三 《唐律疏议》中的祭祀
《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律》云:
诸大祀不预申期及不颁所司者杖六十,以故废事者徒二年。
疏议曰:依令,大祀谓天地宗庙神州等为大祀,或车驾自行,或三公行事。斋官皆散斋之日平明集省受誓诫。二十日以前所司预申祠部,祠部颁告诸司。其不预申期及不颁下所司者,杖六十,即虽申及颁下事不周悉,所坐亦同。以故废祠祀者,所由官司徒二年。应连坐者各依公坐法节级得罪。
蒙按:疏议谓祭祀天地宗庙神州等为大祀,与开元礼与王泾《大唐郊祀录》相合(注:看《新唐书·礼乐志一》、《旧唐书·礼仪志一》与《大唐郊祀录》卷一。)。既是行大祀,一般应由皇帝亲自主持;但若有特殊原因,皇帝不能亲行,则由三公代理。三公位高权重,代行大祀,仍然算是表示对大祀的重视。祭视而必预申期以及“散斋”云云,亦与其他典籍所说礼仪不悖。但若有司失职,未能做到预申祀期,未能按规定提前颁告诸司,以致耽误了祭祀大事,应该受到何种惩处,有关礼书没有说明,多亏长孙无忌等人的《律疏》告诉了后世的读者。《律疏》下文云:
牲牢玉帛之属不如法,杖七十,阙数者杖一百,全阙者徒一年。(注:“全阙”谓一坐。)
疏议曰:牲谓牛羊豕。牢者牲之体。玉谓苍璧祀天,璜琮祭地,五方上帝各依方色。帛谓币帛。称“之属”者,谓黍稷以下不依礼令之法。一事有违,合杖七十。一事阙少,合杖一百。一坐全阙,合徒一年。其本是中小祀,虽从大祀受祭,若有少阙,各依中小祀递减之法,阙坐更多,罪不过此。馀祀阙坐皆准此。
今按:祭祀而用牲牢玉帛,李唐亦然,《律疏》可为铁证。《周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李唐祭祀用玉正用《周官》之制(注:《新唐书·礼乐志二》),《律疏》亦可为证。倘若所司差池,应当受何惩处,这就是法律的责任了。《律疏》下文云:
即入散斋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致斋不宿本司者,一宿杖九十。一宿各加一等。中小祀递减二等。(注:凡言祀者,祭享同。馀条中小祀准此。)
疏议曰:依令,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礼散斋二日,致斋一日。散斋之日,斋官昼理事如故,夜宿于家正寝;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一宿加一等。其无正寝者,于当家之内馀斋房内宿者,亦无罪。皆不得习秽恶之事。故《礼》云:“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致斋者两宿宿本司,一宿宿祀所;无本司及本司在皇城外者,皆于郊社太庙宿。斋若不宿者,一宿杖九十,一宿加一等。通上“散斋”,故云“各加一等”。“中小祀”者,谓社稷、日月、星辰、岳镇、海渎等为中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从大祀以下,犯者中祀减大祀二等,小祀减中祀二等,故云“各递减二等”。
蒙按:“三日斋,一日用之,犹恐不敬”,语出小戴辑《礼记·郊特牲》。据说是孔子的话,后头还有一句是:“二日伐鼓,何居?”郑注:“伐犹击也。齐者止乐,而二日击鼓,则是成一日斋也。”孔疏:“祭前宜齐而专一,不得伐鼓也。……于时祭者在致齐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违礼,故讥而问之。”长孙无忌等人此处所作疏议,引《礼》文嫌突兀,颇费解,我们不得已而加以说明如上。要之,诚如《礼记》孔疏所说:“祭前宜齐而专一”。斋而不专一,习秽恶之事,则于天地祖宗神明为不敬,莫如不祭。致斋,散斋,祭祀前为集中思想、专一心志而独居一室的仪式中最重要的两种。《礼记·祭统》:“及时将祭,君子乃齐。齐之为言齐也,齐不齐以致齐者也。是以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则不齐。不齐则于物无防也,嗜欲无止也。及其将齐也,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耳不听乐。故《记》曰:‘齐者不乐。’言不敢散其志也。”又云:“定之之谓齐,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君致齐于外,夫人致齐于内,然后会于大庙。”孔疏云:“‘及时将祭,君子乃齐’者,谓四时应祭之前未旬时也,方将接神,先宜齐整身心,故齐也。”又云:“‘君致齐于外,夫人致齐于内’者,外谓君之路寝,内谓夫人正寝,是致齐并皆于正寝,其实散齐亦然。”看来唐人所作《礼记》之疏与《律疏》说法一致。李唐君臣忠实地继承了古代祭祀礼制与观念,重视祭前斋戒之仪,所以唐律明令规定祭前散斋致斋必须居宿何处,违律犯令者必酌情处罚之。
又按:上文已指出唐人《礼记》之疏与《律疏》关于祭前斋戒之义与行斋处所所持说法的一致。我们还注意到,《律疏》对中小祀所作解释与《旧唐书》《新唐书》所记开元礼的规定也是一致的。
让我们接着看《律疏》卷九《职制律》疏议的下文:
疏议曰:依祠令,在天称祀,在地为祭,宗庙名享。今直举祀为例,故曰“凡言祀者祭享同”。按:此文是对上引注文的解释。将祀与祭享区别言之,亦与《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郊祀录》相同,而实昉于《周官·大宗伯》。《职制律》下文又云:
诸庙享,知有缌麻以上丧遣充执事者,笞五十;陪从者,笞三十。主司不知,勿论。有丧不自言者,罪亦如之。其祭天地社稷则不禁。
疏议曰:……“其祭天地社稷不禁”者,《礼》云:“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不避有惨,故云“则不禁”。
蒙按:《律疏》此处用互文见义法。下句说“主司不知,勿论”,则上句亦斥“主司”言之,主司知而遣有缌麻以上丧充执事者,当笞五十也。疏引《礼》“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句,见小戴辑《礼记·王制》。“其祭天地社稷则不禁”,既可证唐礼与古礼之渊源关系,又可证唐法自唐礼出,其谁曰不然!
又按:唐代为祭礼立法,主要见于《律疏·职制律》。《律疏》卷十九《贼盗律》也有若干材料,如下:
诸盗大祀神御之物者,流二千五百里。(注:谓供神御者,帷帐几杖亦同。)其拟供神御(注:谓营造未成者)及供而废阕若飨荐之具已馔呈者,徒二年。(注:“飨荐”谓玉币牲牢之属,“馔呈”谓已入祀所经祀官省视者。)未馔呈者,徒一年半。已阕者,杖一百。(注:“已阕”谓接神礼毕。)若盗釜甑刀匕之属,并从常盗之法。
疏议曰:“供而废阕”,谓神御之物供祭已讫退还所司者,故云“废阕”。“若飨荐之具已馔至”,馔者谓牲牢枣栗脯修之属,已入神所呈阅祀官讫而盗者各徒二年,故注云“飨荐谓玉币牲牢之属”。……“已阕”者,谓神前饮食荐飨已了,退而盗者得杖一百。……
按:上引《律疏·贼盗律》说的是对那些盗窃大祀神御之物与拟供神御者及相关用具者的处置。唐以前祭祀历来有省牲之仪,上引《律疏》可证唐亦有之。据上引《律疏》可知:不但“牲牢”,而且“枣栗脯修之属”,而且所有“飨荐之具”,都必须先呈阅祀官查验。《贼盗律》下文还有“诸盗不计赃而立罪名”条,疏议说到对“盗中小祀等物”之人的论处,本文不赘述。
《律疏》卷二十七《杂律》:
诸弃毁大祀神御之物若御宝、乘舆服御物及非服而御者,各以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准盗论减二等。
诸大祀丘坛,将行事有守卫而毁者,流二千里;非行事日,徒一年。壝门各减二等。
按:这两条把唐人对那些弃毁、亡失大祀神御之物,毁坏大祀丘坛、壝门的人如何处置的法令告诉了后人。疏议除了解释原文,还将唐人对那些弃毁、亡失中小祀神御之物,毁坏中小祀设施的人如何处置的办法作了补充。律与疏文当然还有别的意思,不烦缕述。毫无疑问,上引《杂律》与上文并未徵引的疏议原文都是对唐人礼书的补充。譬如疏议云:“神御谓供神所御之物。”又云:“非行事日谓非祭祀之日。”“壝门谓丘坛之外拥土为门。”皆是也。
《律疏》卷十五《厩库律》:
诸供大祀牺牲,养饲不如法致有瘦损者,一杖六十,一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加一等。
疏议曰:供大祀牺牲用犊,人帝配之,即加羊豕。其养牲:大祀在涤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养饲令肥,不得捶捕,违者是不如法。“致有瘦损者,一杖六十,一加一等”,五不如法,罪止杖一百。以故致死者,加罪一等,一死杖七十,五死徒一年。其羊豕虽供人帝,为配大祀,故得罪与牛皆同。《职制律》:“中小祀递减二等,馀条中小祀准此。”即中祀养牲不如法,各减大祀二等;小祀不如法,又减中祀二等。
对于供给大中小祀的牛羊豕的饲养有这么多的规定,唐人及其前礼书不曾详述如此。饲养稍不如法,竟会遭到杖捕甚至徒刑的处罚,真个是人不如兽了。换一个角度,人们难道看不出李唐君臣对祭祀的重视吗?
又,《律疏》卷二十三《斗讼律》第一条疏议提到夫死妻携子适人,“而所适者以其资财为之筑家庙于家门之外,岁时使之祀焉”,据此文而为李唐家庙之制添一佐证,应亦不诬。
(未完待续)
[收稿日期]1998—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