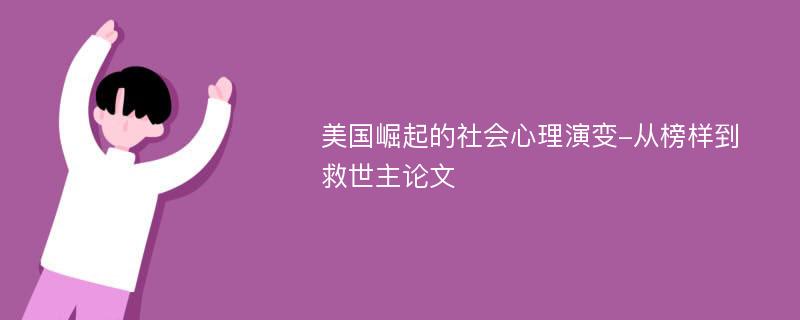
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演变*——从榜样到救世主
潘亚玲
【内容摘要】从19世纪末的物质性崛起到二战后的全面崛起,美国至少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战略缓冲期。美国有效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进行了三轮未必是自觉的战略试错,逐步推动社会心理从榜样论向救世主论转变,为崛起后的对外战略动员奠定了基础。第一轮战略试错的实质是利用新获得的巨大物质力量,主要通过美西战争确保榜样得到尊重,但其传统权势政治逻辑基础令美国社会无法接受。第二轮战略试错则转向另一极端,在一战及其后以高度理想主义手段确保榜样的纯洁性,但同样不受美国社会欢迎。第三轮战略试错实现了权势政治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这一新平衡模式迎合了榜样可以普及的美国社会心理,塑造了更为长期的救世主心态。美国经验表明,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崛起大国必须有效利用未必充分的战略机遇期,在不动摇物质性崛起可持续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开展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为长期可持续崛起奠定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关键词】 美国崛起 战略试错 社会心理塑造 美国例外论
尽管美国的物质性崛起被认为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但是直到1950年4月,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才被告知美国“已独步天下”①。换言之,美国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经历了大致半个世纪,充分证明大国崛起存在从能力到权力的转换过程。②从大国崛起的战略、心理准备角度来看,美国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战略缓冲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尽管这未必是有意识的前瞻性设计的后果。③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尽管战略试错貌似寻找崛起的更佳战略抉择,但它同样是在寻找国内长期性战略动员或社会心理的坚实基础。因此,充分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时间,事实上也是大国崛起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美国充分利用了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有意或无意地开展了至少三轮战略试错,推动美国社会心理从榜样论向救世主论转变,从而为崛起后的社会心理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一轮战略试错是在19世纪90年代,更多是利用物质性崛起的全新力量确保榜样得到尊重,但以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老罗斯福)总统为主倡导的欧洲传统权势政治逻辑令美国社会无法接受。吸取了第一轮战略试错的教训,第二轮战略试错转向理想主义一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试图确保榜样的纯洁性,但也并未真正把握美国社会的真实心理需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提供了第三轮战略试错的机会,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小罗斯福)总统实现了权势政治与理想主义的有机结合,这一新的平衡方式很好地迎合了榜样需要输出的美国社会心理,从而真正塑造起美国社会延续至今的救世主心理。美国经验表明,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如何抓住演变中的可能正遭受严重挤压的战略机遇期,逐渐提高崛起的可持续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崛起大国的当务之急。
一、榜样需要尊重:现实主义权势政治的成与败
尽管自建国之后便不断发展,但美国崛起仍很大程度上是在内战结束之后才真正成为可能;只有在内战结束后,美国才真正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进而为其物质性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美国持续崛起并在19世纪末期成为世界性的物质强国,美国人自移民之初便不断自我强化的榜样心理进一步固化,对榜样应得到的国际尊重也日益渴望。但事与愿违的是,国际社会直到此时仍严重忽视美国的物质性崛起。美国对尊重的强烈渴望,使以武力确保榜样得以尊重的偏执心理渐占上风,并在美西战争中得以释放。而正是由于美西战争很大程度上释放了以武力保障尊重的偏执心理,美国社会对以老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权势政治信奉者大加挞伐;美国向帝国主义的转型在实践中是成功的,但在社会心理层面却是失败的,遭到了美国社会的全面排斥。
南北内战后的国家重建,使美国迅速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一方面,在内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才真正达到令人眩晕的速度。据计算,1873年至1913年期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5%。这个超常的增长速度几乎体现在所有经济部门。④例如,美国的工业排名从1840年的世界第五位迅速上升到1860年的第四位,1870年的第二位,1895年的第一位;到1913年,美国的制造业产量超过英国与德国的总和,占世界总产量的1/3。如果以GDP衡量,美国早在1870年就超过了英国,到1913年不仅总量是英国的两倍以上,人均GDP也超过了英国,而德国和法国则仅占美国的2/3左右。⑤另一方面,内战结束也加速了美国的内部扩张,美国所塑造的新权势格局很大程度上为其对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相继购买或侵占更多领地,使美国人欢呼雀跃,“它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首先是法国,接着是西班牙,然后又是法国,现在则是俄国。”⑥
首先,在央行投放资金基本传导至实体经济方面,报告指出央行投放的资金基本上全部传导到了实体经济。超额准备金率(超储率)是衡量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关键指标。从货币运行机制看,商业银行在资产扩张过程中,如发放贷款、购买外汇、购买债券等,都会在其负债方派生出等额存款。随着存款增长,银行须按要求把相应的超额准备金划转为法定准备金,由此起到支持银行资产扩张的作用。超储率的高低,既可以衡量银行流动性水平,也是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传导的重要标志之一。
美国的物质性崛起,极大地强化了其对自身充当世界榜样的自信。在欧洲移民们跨越辽阔海洋来到新大陆之际,事实上抱有一种理念:他们自认为代表未来,自觉或不自觉地幻想在新世界建立一种与旧世界不同的社会秩序。⑦移民们自称是上帝的选民,负有弥合荒野和文明之间裂隙的使命,要把上帝赋予的这块土地变成“希望之乡”。正如马萨诸塞移民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预言:“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⑧可以认为,榜样意识既是美国立国之基,也贯穿整个美国外交战略史。随着美国日渐崛起,美国人对自身的世界榜样认知日渐强化,对自身“实现荒野文明化”⑨的使命感也日渐强烈,逐渐演变为后人所熟知的“天定命运论”(Manifest Destiny)并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基础。
尽管日渐自信,但美国的榜样作用或地位并未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从美国人的视角看,自身作为世界榜样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例如,直到1892年,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仍没有一位是大使级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认为美国足够重要;⑩又如,尽管其物质性崛起已经相当明显,但美国仍被视作二流国家;⑪再如,美国曾尝试调解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但法国根本不予理睬。由此可以认为,在物质性崛起与全面崛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且需要充分的战略机遇期以实现从能力到权力的转换。例如,曾在内战期间任国务卿的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早在1853年就指出,从地球上获得最多、生产最多、向外国出售商品最多的国家也必将是全球强国。⑫但他怎么也没有料到,美国经济上崛起为大国和国家国际影响的相应扩展之间存在着如此长的时间滞后。
对物质性崛起与全面崛起之间的时间滞后缺乏理解,加上国际社会对美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和心理变化不够重视,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社会的自尊,推动先前只是相对中性的“榜样需要尊重”的心理需求,向颇为偏执的以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的方向发展。首先,美国人更加强调自身的榜样作用。内战结束后,不少美国人深信,废除了奴隶制度进而获得新生的美国具有道德上的天然优势,因此必然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例如,有参议员认为,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块阵痛和抽搐的土地……一座人类激情的火山和一条人类鲜血的河流”,这是美国边境以南地区的普遍景象。⑬其次,随着自身崛起,美国对自身利益的想象逐渐从相对保守向强势肯定的方向发展。美国对中美洲地区运河的态度演变便是典型:一开始,美国接受中美洲运河的中立地位,但随后便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对运河的控制权,到最后甚至声称美国将不会“让任何使我们在美洲大陆上正当的和传统的优先地位的主张遭到质疑的条约永久化”⑭。再次,美国社会日益欢迎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或确保自身得到尊重。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指出,国家往往寻求尊重尤其是自我尊重,而对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这可以被视为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美国人尽管信心满满,但对于感觉到的不被尊重的迹象很敏感,部分是因为与他们对自己的怀疑有关。1892年与智利的小规模冲突显示出,当自信和不安全感混合在一起时,可能将导致好斗性的令人吃惊的显示。⑮而一位佛罗里达州参议员也曾在1884年问道,“在你放弃了你所拥有的海岸后,这个世界上的国家谁还在意你的道德力量?……当出现突发事件时,他们所尊重的是得到足够显示的公众力量。”⑯
[30][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许先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271页。
对汉江中下游而言,中线调水带来的直接不利影响是河道水量减少,水位下降,枯水期延长,中水期缩短。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多年平均年调水量为95亿m3,加上陕西引汉济渭工程规划近期从汉江调水10亿m3,远期调水15亿m3,汉江中下游水量将分别减少至 246亿 m3和 241亿 m3,分别减少29.9%和31.3%。水文情势的变化又将影响到生态环境、城乡供水、农业灌溉、堤防安全以及汉江生物物种和渔业产量等诸多方面。
到1897年再次爆发古巴危机时,美国的实力相比前两次危机时已大为增强,公众对榜样未得到相应尊重的认知更加极端,刺激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于通过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更加狂热。由此而来,在1898年4月作出的对古巴进行干涉的决定和随后向西班牙的宣战所产生的分歧要小得多。首先,绝大多数坚持榜样论的人都认为应当在古巴采取行动。一些后来以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者闻名的人,也都加入了被指为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战争的阵营。⑱例如,信奉海军战争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老洛奇(Henry Cabot Lodge)认为,如果美国“代表着人性和文明,那么我们就应该发挥我们伟大国家的所有的影响力,来结束在古巴的这场无法无天的战争,并再一次给这个岛屿带去和平、自由和独立。”⑲又如,北卡罗来纳州一家报纸宣称,“反西班牙战争的根据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事情的真实体验——对荣誉的珍视、人类的理想、人权的改进和维护。”⑳其次,以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也有利于强化榜样自身。因为不少人担心,伴随国家快速崛起而来的是,美国人似乎逐渐沉迷于对财富和个人利益的追逐,几乎不再拥有马汉所称的“男子汉气概的战斗精神”[21]。再次,通过战争强化爱国主义,既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内战前的南北裂痕,也有助于促进种族团结,尽管这一效应很快被证明并不持久。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的,1898年战争完成了南北和解,使原邦联战士尚武精神的传统投入到一场爱国战争;[22]从战争开始之日起,“我们有了新的联合,不再分北方人南方人,我们都是美国人”[23]。
一场以维护榜样尊严为名且仅持续3个月的战争,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在亚洲得到了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阵地,并正式赢得在西半球的统治者地位。尽管如此,以老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权势政治信奉者们却抱怨“能让我们大显身手的战争机会还不够多”[24]。老罗斯福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偏执的社会心理的代表。与其他人一样,老罗斯福对美国榜样地位和美国能造福世界的观念深信不疑;但他们所坚持的是,美国不应信奉孤立主义,而应以欧洲传统均势逻辑为基础,将美国的“神授使命”真正推进。[25]也正因如此,老罗斯福不仅在亚洲推出“门户开放”政策,也在西半球提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认为所有“积习成癖的不正当行为”都可能“要求某种文明力量的干预”,并认为这种文明力量当然就是美国。[26]
只有优质的材料才能造就优质的工程,明确认识到施工现场材料验收的重要性,不断规范材料的进场验收,才能为施工项目的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科学合理地对施工现场的材料验收将不仅能够给建筑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能推动整个建筑行业的持续发展。
尽管美西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现的“社会心理危机”得到有效释放,美国似乎摆脱了“中年危机”重返“青年时代”,[27]但通过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的偏执狂并不符合美国的建国传统。因此,尽管战争获胜被大加宣扬,但反对呼声也同步上涨,其代表是1898年6月成立的“反帝国主义联盟”。该组织认为,美西战争是一场伪装成解放战争的帝国主义战争,美国吞并菲律宾意味着对美国自治和孤立主义理念的放弃。[28]尽管各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根本上是由于权势政治与美国建国传统在基本哲学取向上的不同,美国社会对榜样需要尊重的偏执狂热在经历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等对外扩张行动的有效释放后,逐渐趋于冷静,美国紧随物质性崛起后的第一次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并未如愿。
区县级电视台在采编环节上处于相对薄弱的位置,对于专题节目的策划有待进一步提高。采编环节薄弱,一方面是素材的缺失问题,另一方面是电视台自身的基础问题。目前,国内各大优秀电视台不断推出各类节目,除了获得资本的青睐,吸引各类优秀创作人才外,其在采编环节上更是独具匠心,所制作的专题节目能够引发观众与节目本身产生共鸣。无论是从人的情感,还是世间百态,都是采编环节中的素材之一。策划,就是创意,也是区县级电视台能够突出重围的一大突破口,然而,很多区县级电视台恰恰没有把握好这一利器,更多的是墨守成规,没有善于发现采编环节中的突破口。
二、榜样必须纯洁:全面胜利与重返孤立
自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遭到国内强烈反对后,美国从战略上退回到孤立主义。随着二战阴影渐趋浓厚,源于确保榜样的纯洁和被尊重的中立论再次浮现。1937年10月,罗斯福总统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Quarantine Speech)。罗斯福强调,“很不幸的是,无法无天(lawlessness)这种瘟疫确实正在世界上四处蔓延。当传染病开始流行时,社会将会同意把病人隔离开,以保障整体人群的健康,避免疾病的蔓延。”[53]尽管强调美国人民要对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心理准备,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承担某些责任,并提出“隔离病人以保障社区健康”以试探民意,但罗斯福的战略立足点仍是保守和防御性的“不卷入”或中立。这一源于榜样纯洁性的中立战略认为,传递“美国价值观”肯定是积极的,但只能通过在国内设定美德榜样的手段予以实现。美国应以两大洋为安全屏障,扮演其恰当角色。[54]正如罗斯福总统后来的评价所说,“可惜这个建议未被采纳,甚至还遭到恶意诋毁。它被指责成唯恐天下不乱,企图干预外国事务,甚至被讽刺为根本没有战争危险却自己吓唬自己。”[55]这一保守战略有相当强的社会心理基础。盖洛普(Gallup)公司于1938年9月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34%的美国人赞成一旦英法与轴心国交战就卖给它们武器。[56]
一战的爆发为美国实现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转换提供了另一重要战略机遇。它一方面使美国得以尝试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战略,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物质性崛起。的确,尽管第一次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以失败告终,但仍对美国社会心理产生了长远影响。正如入江昭(Akira Iriye)所指出的,殖民扩张没有造成国内的分裂,相反的是,经过内战完成的经济统一为采取积极外交政策并无须担心失去国内凝聚力大开绿灯。[31]一位当代美国观察家也指出,这个国家正进入其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它必然会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大国建立更密切、更复杂的关系,而这将导致既定的外交政策过时。作为后果,负责对外事务的美国国务院也因此迅速扩大,其雇员从1898年的仅82人快速增加到1910年的234人。[32]但由于前一轮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遭遇,一战爆发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本身并未被及时发现和捕捉。对威尔逊总统而言,一战的根源是什么并不重要:“对于战争的惊人的洪水喷薄而出的那个隐晦不明的基础,我们没有兴趣研究或是探索”;美国人倾向于认为,无论是在欧洲还是远东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妒忌和竞争行为”,太过愚蠢、太过复杂以至于不值得关心。[33]
对美国社会而言,美西战争后至一战后期,其核心关切是美国作为榜样的纯洁性。鉴于美西战争后的美国社会心理,威尔逊总统尝试延续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的孤立主义,以孤立维护榜样的纯洁。威尔逊强调,“和平可以使世界和解、改善,而冲突则不能”,美国必须成为和平的榜样。“一个民族因自尊心太强而不屑一战,这种情况是有的。”[34]尽管美国公众和传媒都积极报道各国相继宣战及战争的各种细节,但仍重在劝说“每一个真正热爱美国的人,都要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公正。”[35]
尽管如此,威尔逊总统内心却有着更为宏大的目标。在他看来,美国物质性崛起的天然后果是向外扩张。他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强调,美国工业已经膨胀到如此程度,国际市场必须成为美国制度的新边疆,否则意味着灾难。[36]因此,尽管坚持中立,但威尔逊本人及其主要顾问们都更同情协约国。他认为,如果德国人战胜的话,“美国人将不得不在本土防御,这对美国政府和美国的理想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37]尽管威尔逊总统凭借“使我们远离战争”的口号赢得连任,但他却对此感到吃惊,私下抱怨道,“我不能做到使国家免于战争”“他们把我说得像神仙一样,但任何一个小小的德军中尉随时都可搞一些预谋的违法行动而把我们投入到战争中去。”[38]
随着战争的发展,美国社会心理逐渐变化,从一开始的绝对中立逐渐转向武装中立。在1917年3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威尔逊总统强调,虽然美国并非参战国,但战争的确对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仍应设法置身事外,追求超越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利益。尽管有的伤害已无法容忍,但美国仍不应对公平交易、正义、生活自由及共同对抗有组织的错误等抱有奢望。美国要以武装中立来确保自身最低限度的权利和行动自由,既不是征服也不是想获得优势;美国不追求以他国为代价的利益,而应发挥巩固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39]
需要指出的是,榜样纯洁性的维护至少可以有两种手段:一是保守性的孤立或隔绝战略,通过孤立自身而避免被玷污;二是进取性的全面胜利战略,全面改造整个体系或将榜样的模式推广至全世界,从而实现榜样的纯洁。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对协约国的同情心逐渐上涨,美国社会经历了从绝对中立到武装中立,从维护和平到赢得完全胜利的心理转变。例如,就在对德宣战3个月前的1917年1月,威尔逊在国会参议院的演讲中还强调,战争必须结束,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后和平;新的战后和平必须是一个没有胜利者的和平。胜利意味着强加给战败方的和平,战胜方的条件强加给战败方。战胜方的条件被接受,但却是基于不可接受的特征和耻辱而被迫接受,这将留下痛苦的记忆和愤恨;和平建立在沙滩之上。[40]随着战争延续,特别是德国在1917年2月宣布无限制潜艇战,尤其是该国潜艇拦截并炸沉伊利诺斯号战列舰后,美国人义愤填膺,毫无疑问,美国必须开战,因为穷凶极恶的德国人已事实上对美国宣战,使美国无法再继续保持武装中立,进而无法继续以保守方法维护美国作为榜样的纯洁性。因此,采取进取性的战略以维护榜样纯洁性便成为必然。
要把教育水平引向更高阶段,就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因此,提升教师课堂教学技能,引导教师专业成长,打造一支真正意义上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提高学校办学效益是各地区、各学校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对德国宣战,其理由是美国作为榜样的纯洁性正在被德国玷污。他说,德国政府是一个恶魔,危及“人类生活之根本”,由德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一场针对所有国家的战争”,美国的目的“不是去报复,更不是欣然张扬武力,而仅只是为了维护正义,维护人权,维护我们至高无上的尊严……世界必须让民主享有安全。”[41]威尔逊的核心逻辑在于,为持续维护榜样的纯洁性,美国参战必须拥有在道德上更加高尚的目标。一方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进而是热爱和平的,它不喜欢打仗、不会轻易挑衅;但一旦被挑衅而必须要动武,它不会轻易宽恕它的对手造成了这样的局面。美国开战是为了惩罚那些非常轻率、非常敌意地挑起战争的国家,给它们留下永远无法忘却的教训,防止事情再次发生。[42]但另一方面,就美国参战是确保未来和平而言,战争结束的方式和条件有着重大区别。它将导致一个值得保卫的和平,得到整个人类同意的和平,而非一个仅服务于参战国利益的和平。换句话说,战争是为了一个正义和有效的和平,而不是一个新的均势安排。战后和平不是新的势力均衡,而是一个权力共同体(community of power);不是有组织的敌对,而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43]
以维护榜样的纯洁性为出发点,美国参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场战争的性质,使其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成为一场十字军的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44]。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状态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昔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变革。[45]这正是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深层逻辑。威尔逊总统在此次演说中进一步明确了美国的参战目的,即“在世界生活中确认正义与和平的原则,反对自私和专制的强权,是在世界真正自由和自治的民族中间确立目的和行动的一种协调,它将从此确保这些原则得到遵守。”[46]“十四点”原则的确也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如公开外交(反对秘密条约与同盟)、海上航行自由、贸易平等、军备控制、民族自决以及确保未来和平的全新国家联盟,等等。
档案管理是一项动态性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档案的生成具有动态性的特点,油田档案的组成包括技术资料、日常文件等,经过简单筛选后,大多数都会作为档案进行留存。其二是档案的管理具有动态性的要求,管理人员需要根据油田企业工作需要,定期对这些档案进行销毁、更新或解密等处理。例如,一些档案具有保存时效,这些档案超过保存时效后,就需要按照相关要求销毁。还有一些加密档案,例如专利档案等,也有加密时效,一段时间后需要解密,对外公开。确保档案管理的动态性,对更好地发挥档案价值也有很大帮助。
威尔逊在回避权势政治、追求榜样纯洁性的道路上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目标如此崇高,因此也与老罗斯福总统一样不在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47]在请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讲中,他对国会说,“把这个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引入战争,引入一场最残酷且最具灾难性的战争,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人类文明本身似乎也存亡未卜。但是,正义比和平更加珍贵,我们应该为自己所珍视的目标而战——为民主而战,为了使那些屈服于当权者的人获得在政府中的发言权而战,为了小国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了人们能普遍行使权利,使自由人民和谐一致,使所有国家得到和平与安全并使整个世界充满自由而战。”[48]仅关注目的正当性,威尔逊总统及其政府对所有反对战争的舆论予以严厉限制;当官方行动不能迅速使公众就范时,治安维持会就会自动过问。压制的对象是那些反对这次战争的激进分子、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以及德裔美国人和被怀疑不够忠诚的其他移民团体。[49]
威尔逊总统对榜样纯洁性的极端追求与不择手段,不仅引发了来自民间的强烈反对——美国“还未进行过如此不受欢迎的战争”[50],其追求全面胜利的“十四点”计划特别是建立国联等更是遭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强烈抵制。尽管与老罗斯福总统相比,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话语更能动员美国公众,但其倡导的理想方案在现实政治中难以推行,是美国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第二次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32]“A Short History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history.state.gov/departmenthistory/short-history/prestige.
三、榜样可以普及:救世主与霸权确立
威尔逊总统推进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高度理想化的方案与政治的现实可行性之间的差距过大。美国社会拥抱因建国理想而来的天然理想主义,并不代表其对政治现实的全然无视。尽管自19世纪后期物质性崛起后所进行的两轮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均告失败,但仍对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塑造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战略试错很大程度上让美国社会认识到权势政治的现实可行性,而第二次战略试错则唤起了美国社会心灵深处对理想主义的天然偏好,正是由于这两大基因的并存,导致仅追求某一极端的任何尝试都将以失败告终,而这正是老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的命运。与其前辈们相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很好地利用了二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在推动美国逐渐卷入战争的过程中,有效地结合了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既延续了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中基本确立的美国作为“救世主”的地位[51],更变相复活了老罗斯福总统的权势政治,从而确保了第三次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成功,为全面崛起后的美国外交战略奠定了持续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美国实现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战略试错有一个独特特征,即尽管战略试错很大程度上以失败告终,但并未对其物质性崛起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是持续推动美国向全面崛起方向迈进,对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塑造也渐趋成熟。从物质性崛起的角度看,尽管有两轮失败的战略试错,但美国的绝对和相对实力都不断增长。例如,根据一项权威的世界经济史数据分析,美国的GDP在1900年时相当于英国的1.7倍,德国的1.9倍,法国的2.7倍;到1913年时增至英国的2.3倍,德国的2.1倍,法国的3.6倍;到1929年大萧条爆发前进一步增长为3.3倍、3.2倍和4.3倍;大萧条和二战爆发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美国的GDP在1940年时为英国的2.8倍、德国的2.4倍和法国的5.6倍;到1945年时更是增长为英国的4.7倍、德国的5.4倍和法国的16.1倍。[52]正是持续的物质性崛起,为美国反复进行战略试错提供了经济和军事基础;而二战的爆发则提供了第三次战略试错的战略机遇。
美国在物质性崛起后的第一次战略试错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塑造的失败,与其说是目标的错误,不如说是手段与目标的结合存在问题,并诱发了严重的公众反感。因为强烈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真正目的并非反对帝国主义本身,而是另外两个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外殖民未征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另一方面则是害怕美国人被外来移民“污染”的种族主义关切。例如,战争的残酷引发了美国社会对自身榜样地位的反思。一位随军牧师说道:“谈论战斗和解放可怜的古巴与西班牙的暴行,谈论成千上万被害的古巴人与饥饿的集中营,难道美国就比西班牙好些吗?”[29]又如,一位女权主义者指出,“我们曾对残暴的西班牙人抱有多么强烈的愤怒之情啊!……可是,当硝烟散去、死者入土,当战争的代价以物价与房屋上涨的形式转嫁到人民头上的时候,……我们才突然明白……美国人民的生命、鲜血与财富不过是用来保护美国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而已。”[30]对自认为是世界榜样的美国人民来说,第一次战略试错及社会心理塑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美西战争为代表的战略手段事实上玷污了榜样本身。这一心理推动美国在一战中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转向另外一个极端,无论是保持中立还是追求全面胜利的目的都是维护榜样的纯洁性,但由此导致的“非黑即白”的战略方法,同样不是美国社会所渴望的。
(2)沉箱码头段沉箱顶标高+1米,当地设计最高水位+3.24米,沉箱处水深较浅,施工船舶难以进入沉箱路侧区域施工;且沉箱陆侧水域面积较小,抓斗船无法布置船位;
可以认为,1937年的美国仍然遵循标准的榜样纯洁性和榜样需要得到尊重的逻辑。但随着战争的迫近和爆发,美国社会心理基础遭到严峻挑战。因为大萧条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转向,敌对的经济集团使得回归正常经济状态变得更加复杂,日本和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已演变成为自由主义的危机”[57]。这样,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出笼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罗斯福从一开始不指名地公开谴责蓄意以侵略战争或战争威胁作为政策工具的国家,转变为公开点明这样的国家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那些反法西斯国家。《慕尼黑协定》出笼后,美国民众中赞成向英法出售武器的人数升至68%,但认为保持和平比打倒纳粹更重要的人却有64%。[58]
更大范围的社会心理转变主要体现在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与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一场持续约3年(1939—1941年)的大规模辩论中。比尔德视美国为全世界效仿的美德榜样。他认为,围绕美国的海洋不仅保护美国免遭外部入侵,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其免遭军国主义和特别是欧洲的道德上存在争议的权势政治的侵蚀。美国于1917年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构成对美国自身地理位置的违背,几近以美国作为世界自身榜样的伟大使命为代价。[59]尼布尔是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先驱,信奉人性恶的观点,认为美国忽视欧亚大陆情势的代价是自身成长。如果华盛顿允许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掌握整个欧亚大陆,很快会发现自身将面临直接威胁,因为世界政治已为权威主义议程和增长的经济权势所主导,事实上将美国冻结在两个大陆性帝国之间,因此,必须阻止这一前景的发生。[60]但作为神学家,尼布尔也强调应对权势不公需要强调社会正义,任何对权势的垄断都是“最大的不公”,因此需要民主制度。[61]
当电机采用电压型变频器供电时,会产生一个新的轴电流来源,即变频器的共模电压。当采用PWM切换的三相电压供电时,每相都含有很多次的谐波分量[3]。输出的三相电压即使基频分量是对称的,但无法使所有谐波分量都对称以满足瞬时三相电压矢量和为零。因此变频器瞬时中性点电压不为零,该电压就是共模电压的来源,故共模电压可看作变频器三相电压的零序分量。共模电压对电机轴电流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尼布尔所建构的基督教现实主义较好地结合了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得以在学术界之外广泛流传。例如,罗斯福总统强调,为维护美国本土安全,“欧洲大量国家持续的独立存在”非常有必要,因此,通过将美国安全与欧洲均势相联系,支持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进而保卫美国的价值观,是美国的正当选择。[62]又如,在国会,代表出口导向产业和农业的南方州议员们意识到纳粹德国及日本的威胁,推动罗斯福发展激进的国际主义政策,在国内建设军事化的“堡垒国家”(garrison state);他们与北方的共和党一道,将干涉主义输出到欧亚大陆,以保存美国的国内认同,完全扭转了比尔德的逻辑。[63]在学术界,以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为代表,声称美国的权势地位一贯依赖欧洲均势,进而重写了历史。[64]斯皮克曼认为,如果美国不只是想成为“强大的德国和日本帝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的话”,干预欧亚大陆就是必要的。[65]历史学家约翰·汤姆森(John Thompson)也强调,“处于危险的更多是美国塑造世界事务的能力,而非北美安全。”[66]
随着美国思想界逐渐转向更加进取性的立场,加上二战全面爆发并持续,罗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后来成为美国宣战官方理由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予匮乏的自由和免予恐惧的自由。罗斯福强调,世界形成了自由世界与奴役世界对立的状态,四大自由应为世界人民所享有。[67]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人日益接受罗斯福的观点,认为和平比阻止纳粹获胜更为重要的民意支持率已降至32%。[68]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在对国会的宣战演讲中说:“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国不仅将全力保卫我们自己,而且将确保永远不再受到这种背信弃义行为的危害。”[69]这不仅标志着美国正式参战,更标志着美国全面从对榜样的保守战略,转向进取性的救世主战略。因为美国参战不是仅为了美国自身,而是在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中保卫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
这一进取性战略或救世主战略中有着同样明确的榜样纯洁性追求,甚至远超过一战时的威尔逊总统,因为正是基于这一纯洁性要求,推动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发明即“无条件投降”。罗斯福总统在1943年宣布,德国和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要求战败方必须“无条件投降”。在1945年5月8日的广播演说中,杜鲁门总统宣布德国已投降,但同时也强调“在西线获得的胜利现在必须在东线获得,已经有半个世界自由了的全世界必须将邪恶全部清除掉。”[70]正是“四大自由”和“无条件投降”,使罗斯福得以在与“魔鬼”(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从而真正将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相结合,使美国得以从“山巅之城”(city on the hill)发展成为“城中山巅”(the hill in the city);[71]一种典型的救世主心理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作为一个榜样国家,从此往后的任务不再是确保榜样得到尊重,而是如何得以普及,或者说如何使美国“从海洋到照亮海洋”(from sea to shining sea)。[72]
罗斯福成功地结合了老罗斯福和威尔逊的优势,同时又成功地避免了后两者的悲剧,其所奠定的美国社会救世主心理,成为此后美国霸权的一个基本特征。事实上,就在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罗斯福和杜鲁门总统便尝试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即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所称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战时建构。[73]在苏联表现出与美国价值观的重大差异时,美国便事实上启动了“冷战”,到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美国迅速将二战所培育起来的救世主心理转而应用到与苏联的权势斗争中。由于苏联的存在,美国的新使命就是承担起支持热爱自由民主的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把信奉一个道德世界、反对布尔什维克唯物主义的人民动员起来”,去“把世界从极权主义中解救出来”。[74]美国全面崛起的社会心理基础终于得以完全建立。
余 论
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美国用了约50年时间。从个体角度看,利用半个世纪进行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几乎让一整代人没法看到美国的全面崛起;但从整体角度看,这50年大大提升了美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就此而言,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塑造及其演变至少可提供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尽管历史上更早于美国的大国崛起到底有多长战略机遇期难以准确评估,但半个世纪的缓冲对美国全面崛起而言的确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不是两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战略机遇期或许会更长。美国显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全面崛起之后对其他崛起大国的战略机遇期高度敏感,往往通过挤压其他大国崛起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所需的时间,实现对其他大国崛起的预防性管理。日本崛起事实上中断,被证明是一个成功案例;而当前对中国崛起的“提前管理”[75],则是一个新的尝试,它可能因中国持续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而进一步强化。因此,中国要实现可持续的崛起,就必须: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以便进行更为全面和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另一方面尽可能提高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效率,又好又快地利用可能被持续挤压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底线是不破坏物质性崛起的可持续性。如前所述,尽管前两次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以失败告终,但从长期看仍有助于美国的长期性全面崛起,且未对物质性崛起产生消极影响。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经验是,美国在处理与当时的体系霸主即英国的关系时高度敏感,总体是小心避免与英国的直接对抗;哪怕是在即将全面崛起之际,也相当照顾英国的感受,直到英国于1947年正式交出霸主权杖。当然,美国在全面崛起后也对此类战略相当敏感,以避免对崛起国的过度宽容导致自身最终不得不“禅让”出霸主地位。因此,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战略环境既有自身崛起的因素,也有美国对自身成长史上的经验总结而来的预防性考虑。在开展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的时间和空间环境均更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需坚持经济崛起的首要地位,尽可能降低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规模、压缩其地理范围,避免给予美国“咄咄逼人”的印象。
第三,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渐进性对于维持甚至延长战略机遇期相当重要。尽管坚持全新理念,美国崛起仍是渐进式的。如同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从来不试图创建一种全新的制度,我们只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一点点地改良、修缮和改造既有的古老制度,从而让它更适合这个时代”“这辆车经过无数次修理,身上装潢了不同的零件,到最后,谁也说不清我们开的车是一辆别克,还是卡迪拉克,或者是一辆福特。”[76]从战术上看,美国崛起更多是渐进式的,尽管其战略后果却是革命性的,大大提高了崛起的可持续性。当前中国崛起的困境在于,一方面物质性崛起尚未完全实现,另一方面物质性能力转化为政治性权力的难度大为增加。因此,渐进式而非革命性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或更有助于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培育。
第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合理平衡是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得以成功的关键。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塑造经历了左右摇摆,最终形成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的离奇组合,尽管这恰好是当今为人所诟病的美国外交的虚伪性。[77]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曾入木三分地指出,美国具有“一种惊人的能力,一夜之间就可以改变思想观点,……前天,为了我们和另一国之间的那些利害攸关的争端,即使牺牲一个美国人的生命也是不值得的,而今天,其他一切都可以不顾;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任何牺牲在所不惜;除非对方无条件投降,否则必须无限制地使用暴力。”[78]相比美国,中国文化传统一向强调中庸平和,强调在极端之间的平衡,因此在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的过程中,提前设计各种平衡模式并试验其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的可行性,或许更有助于中国在遭受严重挤压的战略时空环境中实现可持续性崛起。
①[美]韩德:《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马荣久等译,牛军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张春:《可持续与开放的崛起: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10页。
③尽管物质性崛起绝不意味着全面崛起,但学术界普遍更加重视物质性崛起的标志性意义;尽管如此,仍多认为美国在这一过渡期的外交战略是一种“探索”,与本文强调的战略试错、社会心理塑造等有大致相似的判断。例如可参见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洪华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⑭Edward P. Crapol, James G. Blaine: Architect of Empire,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2000, pp. 76, 77.
[42][美]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第93页。
⑦时殷弘:《理想和现实:论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中美文化研究》1989年第1期,第67页。
⑧Daniel J.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Vintage, 1958, pp. 5-10.
⑨Cynthia M. Koch, “Teaching Patriotism: Private Virtue for the Public Good in the Early Republic,” in John Bodnar, ed., Bonds of Affections: Americans Define Their Patriot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4-40.
⑩Ernest May, Imperial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1, pp. 3-6.
⑪熊志勇等:《美国的崛起和问鼎之路:美国应对挑战的分析》,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⑫转引自[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83页。
⑬James William Park,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A History of Perspect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65,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
沙盘实训课程是仿真企业经营环境,在了解经营规则的前提下,在竞争的环境中开展经营活动。因为模拟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各团队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经营的好坏,甚至有些团队因经营不善而导致企业破产。对于经常破产的团队而言,可能在心理上有挫败感,容易对沙盘实训课程失去信心和兴趣。因此,为了提升同学们的抗压能力,使其从经营得失中体验收获,需要对学生进行激励。
⑤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Vol. 11, 1982, pp. 275, 284;另可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伍晓鹰、施发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章。
⑮[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袁胜育、郭学堂、葛腾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8页。
华中科技大学档案馆在学生毕业季即时推出了“毕业了,请办好这档子事!”,通过推文,提醒毕业生们一旦没有档案,会给个人生活及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毕业后在转正、职称申报、办理养老保险、公务员或者考研政审,以及开具一些证明,如亲属关系、出国、考研等,都要用到档案。
⑯H. Wayne Morgan, From Hayes to McKinley: National Party Politics, 1877-1896, Syracus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357.
⑰转引自[美]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第109页。
⑱[美]罗伯特·卡根:《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第539页。
⑲Henry Cabot Lodge, “For Intervention in Cuba,”Congressional Record, 54th Congress, 1st session, 1896, pp. 1971-1972.
⑳George H. Gibson, “Attitudes in North Carolina Regarding the Independence of Cuba, 1868-1898,”North Carolina Historical Review, Vol. 43, January 1966, p. 63.
[21]David Healy, U.S. Expansionism: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 p. 103.
[22]John Higham, Strangers in the Land: Patterns of American Nativism, 1860-1925,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70-171.
[23]Cecilia Elizabeth O’Leary, “‘Blood Brotherhood’: The Racialization of Patriotism, 1865-1918,” in John Bodnar, ed., Bonds of Affections: Americans Define Their Patriot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75-76.
[24][美]沃尔特·拉菲伯等:《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
[25][美]夏尔—菲利普·戴维等:《美国对外政策:基础、主体与形成》,钟震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页;[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3页。“神授使命”特指美国的所谓“天定命运”。
下面举一个词相同但释义不同的例子。中国成语中有关龙的成语很多,龙也被列入十二生肖的范围。在中国龙是吉祥的象征,通常伴随凤凰、老虎等动物出现,预示着中国的发展向龙一样腾飞。同时也象征欣欣向荣的发展势途,中国人被喻为龙的传人,可见龙在中国是一种精神象征。而在西方国家相关典籍中,对龙的记载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龙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dragon”是龙的英文释义,在英文语法中该词是可以用来形容人的,通常具有贬低的意味。这与中国的龙的理解恰恰相反[3]。
[26][美]沃尔特·拉菲伯等:《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第69页。
[27]徐弃郁:《帝国定型:美国的1890—1900》,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页。
[28]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1775—2005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7—192页。
[29][美]威廉·G·帕特森、J·加里·克利福德、肯尼斯·J·哈根:《美国外交政策》,李庆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页。
以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美国迈向帝国主义的首次重大尝试、即美西战争中。美西战争的直接诱因是古巴危机,但在美西战争前事实上已有过多次古巴危机,尤其是1869—1870年和1873年的危机。比较这两次危机,美国政府对1873年的危机更倾向于考虑采取战争手段,而公众在1869—1870年危机中要求战争的呼声更高。公众对1873年危机的战争呼声之所以不那么高,很大程度上在于当时美国所经历的经济危机。1873年,美国有5 000家企业破产,损失总额达到2.29亿美元。⑰因此,榜样自身的危机对于公众期待通过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的意愿有着明显的影响。
[31][美]沃沦·I·科恩:《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2页。
多年来,很少有贪官是通过《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暂行规定》被发现的。因此,在落实相关条例规定时,要增加审核、公示、考核、惩治等环节内容。《国家公职人员行为道德典》以近年来出台的一批党规为制定根据,提升至道德层面约束官员。《国家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惩治条例》则应该以近年来“两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为基础制定。[8]
[33][美]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0页。
[34][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崔永禄、王忠和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58页。
[35]《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全集》,李剑鸣、章彤编,陈亚丽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0—302页。
[36][美]沃尔特·拉菲伯等:《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第77页。
[37][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259页。
[38]同上,第265—266页。
[39]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s Inauguration Address,” Firstworldwar.com, March 4, 1917, https://www.firstworldwar.com/source/wilson1917inauguration.htm.
[40]Woodrow Wilson, “We Need a Peace without Victory,” speech by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to the American Senate, January 22, 19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nov/14/woodrow-wilson-senate-address-1917.
[41]Jack Lane and Maurice O’Sullivan, eds., A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Reader,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99, Vol.1, pp. 125-128.
实验技术人员对机能“三理”知识并不熟悉,自身实验水平并没有适应综合性机能实验,对机能实验的开发和探索作用有限。此外,新式实验设备的运用和实验设备对计算机系统的依赖,要求技术人员的实验管理能力更加全面、综合。但目前,实验技术人员受学历、年龄等限制,综合素质并不高,工作能力有待加强。
⑥Charles S. Campbe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865-190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6, p. 20.
[43]Woodrow Wilson, “We Need a Peace without Victo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8/nov/14/woodrow-wilson-senate-address-1917.
[44]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Delivered at a Joint Session of the Two Houses of Congress,” April 2, 1917,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law/help /digitized-books/world-war-i-declarations/ww1-gazettes/US-address-of-president-to-congress-April-1917-1-OCR-SPLIT.pdf.
[45][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第40—41页。
[46]John A.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earson, 1986, p. 15.
[47][美]沃尔特·拉菲伯等:《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第76页。
[48]Jack Lane and Maurice O’Sullivan, eds., A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Reader, pp. 125-128.
[49][美]沃尔特·拉菲伯等:《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第99页。
[50][美]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第305—308页。
[51]Hans Hoyng, “‘We Saved the World’: WWI and America's Rise as a Superpower,” Spiegel, January 24, 2014,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how-world-war-i-helped-america-rise-to-superpower-status-a-944703.html.
[52]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 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53]Jack Lane and Maurice O’Sullivan, eds., A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Reader, Vol. 1,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1999, pp. 410-412.
[54]David F. Schmitz,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 World in Crisis, 1933-1941,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2007, chap. 2; George C. Herring, From Colony to Superpower: U.S.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77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69-372.
[55][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334—335页。
[56][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342页。
[57]John Darwin, The Empire Projec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World-System 1830-19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18.
[58][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美国的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第342页;[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347页。
[59]Campbell Craig and Fredrik Logevall, America’ s Cold War: The Politics of Insecurit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3-27; and Campbell Craig,Glimmer of a New Leviathan: Total War in the Realism of Niebuhr, Morgenthau, and Walt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60]Robin W. Lovin, Reinhold Niebuhr and Christian Re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1]Reinhold Niebuhr,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Vol. 342, July 1962, p. 156; and Eric Patterson, “Niebuh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Realism,” in Eric Patterson, ed., Reinhold Niebuhr and His Critics: Reassess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Niebuh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3, pp. 8-10.
[62]John A. Thompson, “The Geopolitical Vision: The Myth of an Outmatched USA,” in Joel Isaac and Duncan Bell, eds., Uncertain Empire: 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Idea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1.
[63]Peter Trubowitz, Emily O. Goldman, and Peter Rhodes, eds., The Politics of Strategic Adjustment: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64]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1943, p. 6.
[65] 有关斯拜克曼的地缘政治思想,可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174页。
[66]John A. Thompson, “The Geopolitical Vision: The Myth of an Outmatched USA,” pp. 103-107.
[67]Daniel T. Rodgers, Contested Truth: Keywords in American Politics Since Independ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 pp. 210-234.
[68][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347页。
[69][美]戴安娜·拉维奇选编:《美国读本》(下),陈凯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466—467页。
[70]Harry S. Truman, “Broadcast to the American People Announcing the Surrender of Germany,” May 8, 1945, http://www.trumanlibrary.org/calendar/viewpapers.php?pid=34.
[71]Jeffrey W. Legro, Rethinking the World: Great Powe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83.
[72]Jay Sexton, The Monroe Doctrine: Empire and 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London: Macmillan, 2011, pp. 100-123.
[73]G. John Ikenberry, Liberal Leviathan: The Origins,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xi.
[74] Robert H. Ferrell, ed., Off the Record: 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 pp. 98-102.
[75] 对美国这一战略的较早讨论,可参见张春:《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74—90页。
[76][美]弗雷德里·L.艾伦:《美国的崛起:沸腾50年》,高国伟译,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59页。
[77]Stephen Mennell, “Explaining American Hypocrisy,” Scientific Journal Virtus, Vol. 2, May 2015, pp. 161-172.
[78][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葵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From Exemplar to Savior: Domestic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for America’s Ascendance
PAN Yaling
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enjoyed a strategic buffering period of about half a century from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marked by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wealth and influence to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it began to dominate the global system. Taking advantage of this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 successive administrations conducted three rounds of strategic trial and error—although not deliberately—to gradually transform the nation’s social psychology from one of an exemplar to that of a world savior. The first round of strategic trial and error failed because political leaders utilized its newly acquired material gains to earn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the American example by way of power politics (as in the Spanish-American War). The second round of trial and error—the opposite of the first one—failed to win social acceptance because policymakers attempted to uphold the purity of the American example through idealistic means. The third round trial and error was finally supported because it was a combination of both power politics and lofty ideal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has shown that sufficient strategic trials and errors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shaping is a prerequisite for an emerging great power’s sustainable ascendance; and while ensuring that its continued rise in material terms is not compromised, an potential great power ha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its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y—not necessarily long enough—to carry out trials and errors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shaping.
Keywords: American ascendance, strategic trial and error, social psychology shaping,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作者简介】 潘亚玲,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副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昆明 邮编:650091)
【中图分类号】D7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9)02-0001-20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902001
*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回潮研究”(17BMZ09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孙震海]
标签:美国崛起论文; 战略试错论文; 社会心理塑造论文; 美国例外论论文; 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