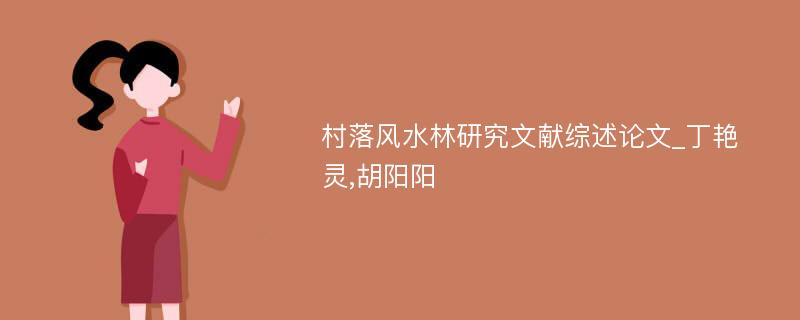
摘要:风水理论源远流长,其在村庄聚落选址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村落风水林的存在,也是进一步对风水理论的延续与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17年间,研究探讨关于风水林的论文共有140多篇。有关村落风水林的研究成果总体数量虽然不多,但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中国大陆的学者对乡村风水林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风水林定义、分类、区域特征、价值、社会文化、郡落特征以及研究意义等方面。
关键词:风水理论;村落;风水林;定义;类型;郡落特征
1引言
风水学是古代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时,考察山川地理环境,包括对气候、地质、水文、地形地貌、生态因素、林木景观等各环境因素的综合评判,并通过占星、卜莁等手段来对城郭屋宅、陵园、寺庙等建筑的营造方位和营造时辰以及某些技术和禁忌的总概括。史箴认为它源于徽商的甲骨占卜,形成于秦汉,成熟于唐宋,明清时已达到非常完善的风水理论体系了。风水理论大致分为两个流派,其一为形势派,着眼于山川形胜和建筑外部自然环境的选择,另一派为理气派,注重于建筑方位朝向和布局(王其亨,1992)。风水理论自古与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人们在乡镇聚落选址时必不可少的参考因素之一。如微地形对小气候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就极为风水所重,概括成有利的选址模式,比喻为“穴”,如针灸中人体的穴,一般是三面或四周山峦环护,呈北高南低、背阴向阳的内敛型盆地或台地,这种“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是“藏风聚气”,具有良好生态和景观效益的风水格局,实际是阐明了微地形、小气候、生态和自然景观的依从关系。(李远国,2005)风水意识是古人在漫长的适应、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总结出的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理论。古代风水论中“藏风亦聚气、得水乘生气”是生存环境的理想形式;理想的风水环境是由“土高水深,草郁林茂”的生态环境组成的[1]。传统风水理论中对绿色山脉、清澈水系、郡落林脉的保护就是对“龙脉”的保护。古人云:“青山常青,绿水长流”,即是指人们植树造林形成风水林木,保持着山常青,防止了山上水土的流失,溪水倒影着山上绿色的风水林地,长久的流淌,这就是古人要保护的风水和美好自然环境[2]。
2风水林文献综述
2.1风水林起源
传统的风水学在剔除那些玄幻迷信的糟粕后,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人民根据自身长期对自然细致观察以及实际生活的体验,所产生的一种有关住宅、村镇及城市等居住环境的基址选择和规划设计的学说[3]。这一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之一就是产生了一种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林业形式——风水林[4]。风水林之说实际上是风水学中的部分组成内容,在古代风水理论中就有“草木郁茂、吉气相随”的说法,林木茂密是古代人们用来衡量风水环境好坏的标准之一[5]。
2.2风水林定义
邱尔发、王成等人认为:风水林是指在村庄一定范围内,由当地村民为了保持良好风水而特意保留或自发种植的树林,它体现南方村庄文化、民风习俗意识,是乡村人居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村落风水林是古代人们深受风水思想的支配,认为对平安、长寿、多子、人丁兴旺、升官发财具有吉凶影响而人工培植或天然生长的林木。杨国荣认为,所谓风水林也就是人们受风水理论的影响,在路口、村后、庭院、坟墓周围等与有关的地方所植的林木,树种一般是松柏和杉树[7]。广东省中山市人民政府规定所称风水林是指自然村周边天然或人工种植的林木,包括成片或散生的林木[8]。陈传国等则认为风水林在中国有上千年传承,传统意义上的风水林就是村民在村庄周围种植或自然生长的竹木,面积不定,多为世代相传下来的,一般树龄为数十年乃至上百年,风水林某种程度上应归类为次生林,但它们往往会受或轻或重人为活动的干扰[9]。郑希龙等认为风水林是宗教意识和风水思想共同支配下的产物,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居环境[10]。刘颂颂等人认为村边风水林(自然次生林)是指我国南方地区村前屋后保留的天然林,常由原生植被受有限度破坏而成或由此生裸地,人工林等自然演替恢复而成,一般呈岛屿状分布[11]。
2.3风水林类型
巫柳兰认为:风水林根据地域不同分为村落风水林、坟墓风水林、寺院风水林[12]。程俊认为,村落风水林是其中的重要类型,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水口林、龙座林、垫脚林、宅基林4种类型[13]。王婷婷则从不同角度对风水林进行了划分,按照起源不同分为人工林和天然林,按照养护对象分为村落风水林、寺院风水林、坆园风水林,按照游憩功能分为人居风水林和郊野风水林。且认为村落风水林可划分为水口林、风口林、宅基林、龙座林。并将祠堂风水林作为宅基林的一种,认为其属于村落风水林[14]。美国西萌石大学地理与东亚学教授柯利思•考金斯认为,江西有4种类型的村庄风水林。第一种是后龙山风水林,就在村庄的山坡,可保护村庄免受地表径流的侵蚀,确保地下水和地表水常年供给。另一种是山坳风水林,可阻挡从风口或山坳窜入山谷的狂风。第三种是水头风水林和村头风水林,由通常处于村庄上方的柳杉或沿溪植造的阔叶林组成,发挥着类似山坳风水林的功用。第四种是村口林(村尾林)和水口林(水尾林),根据风水理论,它们有助于“保住”村庄的财富,防止财富随着风、水从村庄低处流走[15]。
3村落风水林文献综述
3.1村落风水林渊源
风水林的不同分类类型各有渊源,关传友认为村落风水林起源于古老的社神崇拜,村民将树木作为神灵的依附对象和标志,在村落中广泛地种植林木,希望受到树木的恩惠和庇护,保佑他们健康长寿、子孙升官发财、家族兴旺发达等,久而久之,风水林便成为古代村落居宅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之一[16]。刘沛林认为,这种社神崇拜理念只不过是古人们的一种环境吉凶模式心理,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朴素、原始的社神崇拜心理被引入一整套哲学和技术的解释体系——风水学,于是便产生了有关古老的林木与乡村聚落命运发展有重大联系的理论[17]。村落风水林被赋予藏风聚气的意义,人们认为林木茂密就是好的风水环境的表现,通过寻找好的有林木的环境来寻找理想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广植林木和保护林木来获得好的风水[18]。
3.2村落风水林区域特征研究
程俊对岭南地区的村落风水林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从景观、生态、文化和旅游价值四个方面论述了岭南村落风水林作为典型的地域景观资源,在岭南乡村环境景观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19]。杨期和,杨和生等人对梅州客家风水林的郡落特征进行了初步研究,调查了其物种组成及层次结构,研究发现这些风水林具有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典型郡落结构,垂直结构分层现象明显、层次清晰、植物多样性和均匀度较高。通过对客家风水林的营造模式、传统保护方法及其价值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岭南地区的新时代乡村环境景观营造提供新的思路[20]。邢福武将岭南村落风水林根据其生境条件、郡落组分、景观外貌等特征划分为低地常绿季雨林、山地常绿阔叶林等类型[21]。李萃玲,宋希强研究采用典型取样法,对海南保存较好的风水林进行了野外调查,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其空间形态和分布格局进行了分析,认为海南风水林的郡落类型主要为常绿季雨林、热带低地雨林和红树林,其空间分布形态可划分为聚集性和游离型两大类型[22]。
3.3村落风水林群落特征研究
许飞、邱尔发等人分层随机取样法对福建省乡村风水林进行调研研究,认为福建省乡村风水林科、属、种组成较为丰富,共包括35个科、55个属、69个种,以樟科、桑科、壳斗科、金缕梅科、禾本科、蔷薇科、无患子科、山茶科、杉科、漆树科为主,主要应用树种以榕树、香樟、枫香、龙眼、木荷、细柄阿丁枫、石楠、蚁母、朴树、锥栗为主。从不同类型乡村风水林应用树种组成来看,山区型主要风水树种有锥栗、榕树、香樟、细柄阿丁枫、蚊母、楠木、木荷、柳杉、苦槠、火力楠、枫香、红枫和铁杉。半山型主要风水树种有香樟、枫香、石楠、木荷、蚊母和细柄阿丁枫。平地型主要风水树种有榕树、香樟、木荷、龙眼和枫香。沿海型主要风水树种有榕树、香樟和龙眼。此外,山区型和半山型风水林中还常伴生有大量丛生、散生竹林[23]。杨期和、杨和生等人在粤东梅州市桥溪村风水林设立样方,对其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植物进行调查,分析该风水林的群落特征及植物多样性。结果表明:该风水林3 000 m2的样方内,共有维管植物67种,隶属于37个科54个属,其中蕨类植物4科4属4种,裸子植物3科3属3种,被子植物30科47属60种。群落分布型以热带性分布占优势,热带属所占比例为74.08%。群落主要优势科为樟科、壳斗科、金缕梅科,优势种为细柄阿丁枫、刺毛杜鹃、鼠刺、阿丁枫。群落为常绿阔叶林,生活型以高位芽为主,占73.13%,其中又以中高位芽类型最多,约占43%。乔木层可分为三层,但以株高6~9.9 m的个体数为最多;藤本的比例高达17.91%。该风水林群落比周边其他群落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植物多样性,且物种分布较为均匀,种间相遇率较大。桥溪村风水林与粤东和华南地区的其他常绿阔叶林有很大的相似性[24]。岭南村落风水林中的很多树种是当地野生自然郡落的建群种,反映了植物的地域分布特色,其植物种类丰富的优势科主要都集中在大戟科、樟科、茜草科、桑科、壳斗科、桃金娘科、蝶形花科7科中[5]。
3.4风水林社会文化研究
许飞、邱尔发等人认为,乡村风水林应用树种主要与当地气候和地域文化有关。一方面乡村风水林受当地气候条件的影响,全省以九龙江为界,呈现出明显的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两种季风气候,其中,沿海型乡村多数位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较为温暖,树种以榕树、龙眼、芒果等为主,而山区型、半山型和平地型乡村多数属于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较为寒冷,树种以香樟、细柄阿丁枫、蚊母、楠木、木荷等为主。另一方面乡村风水林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妈祖文化在沿海乡村较为盛行,因此以妈祖文化为代表的榕树、龙眼等风水树数量相对较多[23]。张桂红、李赛赛通过分析桂东客家人传统民间信仰以儒、道、释为主,普遍接受风水观念,村落风水林广泛分布于乡野村落,风水林与村落的年代一样久远。该地区村落风水林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色彩,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科学思想和文化内涵。主要从神灵的庇护与和谐的人际关系两方面进行阐述[25]。
3.5村落风水林价值分析
巫柳兰认为风水林在乡村环境中存在着景观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旅游价值[12]。俞孔坚[26]认为风水林在树种的选择上主要考虑其适应性而不在乎物种的稀有程度,对风水林的保护、水资源的合理利用等是我国农业生态节制行为的典型,而“风水林”的价值体现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而不在森林资源本身。崔勇[27]认为风水林是极少数区域内为数不多的原生植被的一部分,是当地生物呈现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在研究物种保存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纵等[28]、邬红芳[29]则针对其文化景观方面的价值进行了研究,认为水口林反应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我们创造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提供良好典范,并为我国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的启示作用。欧应田[30]认为风水林是传统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景观作用、生态意义、文化思想方面着重体现着中国式的特色,并通过阐述莞竹花园后山改造的可行性,探索一条能够保护和利用风水林的有效途径。祝功武[31]通过对广州农村村落风水林的环境、分布特点及其景观作用的研究后,指出广州要想在农村绿化美化和环境建设中取得好成果,必须发挥“风水林”的作用。
3.6村落风水林研究意义
村落风水林是在乡风民约的制约下保存下来,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它是乡村人居林的宝贵财富[32]。一方面,其经过长期的气候考验而留存,是乡村人居林建设树种选择与配置模式最重要的依据;另一方面,由于风水林主要分布在乡村居住区周围,在山区乡村水源涵养和水土保持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对维护乡村生态安全,美化和改善乡村居住环境起着重要的作用[33]。乡村风水林也是乡村生态文化的重要载体[34]。有学者认为,通过对岭南村落风水林展开深入和完善的研究,充分挖掘其潜在的价值,探讨其可行的应用形式,认为可以充分挖掘地域景观文化资源的优势,避免因景观开发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从而为环境景观的营造提供新的思路[35]。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美国西萌石大学地理与东亚学教授柯利思•考金斯对江西风水林的调查与研究最后得出结论:科学保护江西风水林,对农村和城市的社区来说都将产生多重效益。森林、树木提供多重的生态服务,从长远看每年还奉献有关全球气候变化的数据。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风水林可以成为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自然实验室[15]。风水林也具有巨大的社会文化价值,不仅对长期保护它们的人们来说是这样,对理解中国南方农村社区和自然之间长远的持续关系也是如此[36]。汉族社区最值得注意也最具有生态意义上的土地利用传统就是普遍存在的风水林保护。在风水林这一古老的体系里,村庄或村庄群把他们的森林保护起来,从而保护好水资源、农业生产和生活空间。这一风俗也保住了一些呈块状分布的成熟原始常绿阔叶林——这种森林普遍构成中国南部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自然植被[37]。由于风水林历时久远,林中多有古树名木,它们见证了森林演替和自然地理的变化,蕴含着丰富的森林文化内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繁荣生态文化、弘扬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风水林因其在科研、观赏及文化方面有优越的潜在价值,使其成为地带性乡土树种调查的重要基地、发展森林旅游业的物质基础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宝贵财富[38]。这些在风水林中保存下来的物种,更为附近的生境提供自然演替及更生的物种来源,维持整体生态环境的物种多样性。[39]
4 小 结
1990年以来,有关乡村风水林的研究成果总体数量虽然不多,但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中国大陆的学者对乡村风水林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风水林定义、分类、区域特征、价值、社会文化、郡落特征以及研究意义等方面。从地域上来看,对广东、海南等地风水林的研究较多,主要将风水林作为一种林业资源进行探讨,包括群落特征、风水林植物应用等方面,并将风水林作为生态模式应用于生态公益林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广西、福建地区风水林研究主要针对其郡落特征、文化民俗方面;江西地区风水林的研究主要针对风水文化、乡村园林景观以及风水林郡落中动物等方面的研究。通过研究风水林有利于挖掘地域景观文化资源的优势,避免因景观开发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从而为环境景观的营造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关传友.中国古代风水林探析[J].农业考古,2002(3):239-243.
[2]朱仔伟,许军,张杨凯,等.村庄风水林在新农村建设规划中的价值研究—以南昌市新建县厚田乡为例[J].南方林业科学,2012(2):61-64.
[3]尚廊.中国风水格局的形成、生态环境与景观[J].风水典故考略,2004(5):20-25.
[4]杨国荣.关于中国传统林业遗存:风水林的历史文化初探[J].林业经济问题,1999(6):60-63.
[5]程俊,何昉,刘燕.岭南村落风水林研究进展[J].中国园林,2009,25(11):93-96.
[6]邱尔发,王成,贾宝全,等.我国新农村人居林建设研究[J].中国城市林业,2008,6(5):10-15.
[7]杨国荣.关于中国传统林业遗存—风水林的历史文化初探[J].林业经济问题,1999,(6):60-63.
[8]中山市人民政府.印发中山市风水林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N].中山市人民政府报,2008-6-5(1).
[9]陈传国,闫雪燕,廖宇红,等.从佛山市风水林中筛选公益林造林树种[J].林业实用技术,2008,(9):15-18.
[10]郑希龙,邢福龙,刘东明,等.东莞风水林药用植物资源调查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9,37(2):635-637.
[11]刘颂颂,叶永昌,朱剑云,等。东莞大岭山村边自然次生林郡落种群时空格局及其动态特征[J].广东林业科技,2005,(12):18-12.
[12]巫柳兰.村落风水林在乡村景观建设中的价值及优化[J].安徽农学通报,2014(21).
[13]程俊.乡村环境景观建设研究——以岭南村落风水林景观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2009(6):61-61.
[14]王婷婷.德化县风水林郡落生态学特征研究[D].福州:福建农林大学,2009.
[15]柯利思•考金斯,韦荣华.江西村庄风水林中国南方社区管理森林巧用自然的千年指挥[J].森林与人类,2014(12):40-49.
[16]关传友.中国传统园林与风水林理论[J].皖西学院学报,2001(1):42-45.
[17]刘沛林.风水模式的环境学解释[J].陕西师大学报,1995,3(1):83-88.
[18]倪金根.风水与古代中国绿化[J].古今农业,1994(3):45-53.
[19]程俊.乡村环境景观建设研究——以岭南村落风水林景观为例[J].现代农业科技.2009(6):61-61.
[20]杨期和,杨和生,赖万年,等.梅州客家村落风水林的群落特征初探和价值浅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2,39(1):000056-59.
[21]邢福武.深圳七娘山郊野公园植物资源与保护[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78-82.
[22]李萃玲,宋希强.海南风水林的空间形态与分布[J].中国园林,2014(2):87-91.
[23]许飞,邱尔发等.福建省乡村风水林树种结构特征[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12,34(1):99-106.
[24]杨期和,潘素芳、赖万年,等.粤东桥溪村风水林郡落特征初探[J].广西植物,2015(6):833-841.
[25]张桂红,李赛赛.信仰、自然与生活—桂东客家村落风水林的文化解读[J].文化学刊,2015,No.57(7):60-61.
[26]俞孔坚.盆地经验与中国农业文化的生态节制景观[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2,14(4):37-44.
[27]崔勇,张国革,陈德文,等.广西那坡县风水林植物物种多样性及其保育对策[J].广西农业生物科学,2008,27(增刊):53-56.
[28]张纵,高圣博,李若南.徽州古村落与水口园林的文化景观成因探颐[J].中国园林,2007,(6):23-27.
[29]邬红芳.水口园林的文化内涵与美学价值[J].文艺研究,2009,(4):151-152.
[30]欧应田,钟孟坚,黎华寿.广东东莞市千年古秋枫保护的生态环境分析与环境改造方案.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7,26(B10):756-759.
[31]祝功武.整理村落与“风水林”建设绿色新农村[J].中国城市林业,2007,5(6):53-55.
[32]廖宇红,陈传国,陈红跃.等广州市莲塘村风水林群落特征及植物多样性[J].生态环境,2008,17(2):812-817.
[33]刘晓俊,庄雪影.深圳小梅沙村风水林群落及其保护[J].广东园林,2007(3):52-54.
[34]张勇夏,陈红锋,秦新生,等.深圳大鹏半岛“风水林”香蒲桃群落特征及物种多样性研究[J].广西植物,2007,27(4):596-603.
[35]程俊.珠三角村落风水林调查及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09.
[36]贾艳艳,唐晓岚,张卓然,等.太湖东西山古村落风水林探析[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48(4):504-510.
[37]刘代汉,何新凤,蒋家安.桂林后龙山风水林文化现状及承传研究[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1):23-27.
[38]罗旋.浙江风水林调查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12.
[39]邓剑.风水林的生态特征及保育价值探[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3,26(5):9-10.
[40]许东先,宋磊,赵庆,唐洪辉,魏丹.广东省东源县古树特征研究[J].林业与环境科学,2018,34(04):88-94.
[41]余雪贵,吴育璇.东莞市风水林功能多样性研究[J].绿色科技,2018(13):27-29.
[42]李冬琳,邓双文,邢福武,刘东明,易绮斐,潘伟韶.海南文昌维管植物区系特征分析[J].植物科学学报,2018,36(03):309-319.
[43]田奔.乡土元素在乡村景观营造中的应用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18.
[44]王伊可.浙中南传统村落水口景观浅析[D].浙江农林大学,2016.
[45]李林.风水理论在现代园林中的应用[D].安徽农业大学,2016.
[46]任栩辉,叶彬彬,刘青林.植物文化及其在文化建园中的应用[J].农业科技与信息(现代园林),2015,12(01):22-28.
[47]刘世强,矫鑫,李霄鹤,兰思仁.客家园林探究[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35(01):30-34.
[48]吴欲波.风水林探源与当代启示[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29):17984-17986.
[49]许飞,邱尔发,王成.我国乡村人居林建设研究进展[J].世界林业研究,2010,23(01):56-61.
[50]关传友.论中国古代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与实践[J].中国水土保持科学,2004(01):105-110.
论文作者:丁艳灵,胡阳阳
论文发表刊物:《基层建设》2019年第14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7/29
标签:风水论文; 村落论文; 乡村论文; 树种论文; 文化论文; 景观论文; 特征论文; 《基层建设》2019年第14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