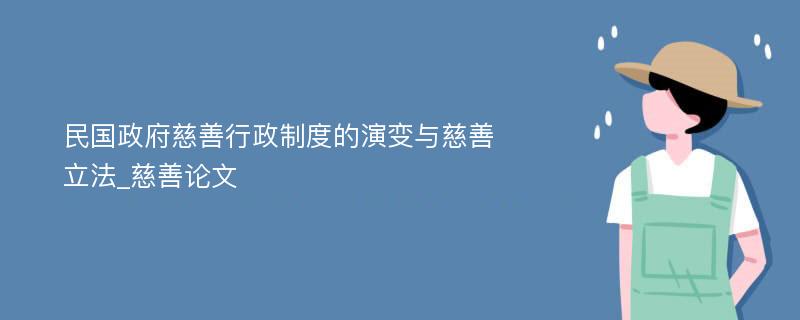
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与慈善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慈善论文,民国论文,体制论文,行政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3)01-0064-07
民国年间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民国政府逐渐建立起一整套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管理体制,包括慈善行政体制。慈善行政机关的建立及其相应职权的划定,使得民国政府的慈善立法有了推动力量,进而为规范慈善事业发展、加强慈善组织管理提供了一个基本路径。民国中后期,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行政体制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同时慈善立法日渐完善,法律位阶也越来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演变对其慈善立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彼此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在参阅前贤、钩沉史料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对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确立、演变过程以及由此促发的慈善立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舛误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民国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形成及其演变
(一)北京政府时期慈善行政体制的初创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设立内务、军政等六部。随后,参议院议决通过《内务部官制》,规定内务部置民治、警政、礼教、卫生等六司,其中,民治司负责灾荒抚恤、慈善团体管理等事项,卫生司掌理疫病防治与救恤①。袁世凯上台后,各行政机构虽有变更,但基本延续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制。如,1912年8月8日公布的《修正内务部官制》,“内容与原官制大致相同,惟列举各司职掌较详”②。内务部掌理的行政事务计14项,其中赈恤、救济、慈善、感化、卫生五项均与慈善事业相关联,属于广义的慈善行政范畴。具体言之,民治司主管贫民赈恤、罹灾救济、贫民习艺所、盲哑收容所、疯癫收容所的设置与管理、育婴、恤嫠及其他慈善事项;卫生司负责种痘、传染病与地方病的预防等事项③。这样,民国政府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晰了内政部及所属司有关慈善事务的职权范围,初步确立慈善行政体制。后来,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内务部官制又两度修订,但对慈善行政体制并无多大影响。
同时,北京政府还进一步明确内务部各司、科的具体职责,这使得民初慈善行政的运行机制渐臻完善。1914年7月公布的《内务部厅司分科章程》,即规定由民治司第四科专门掌管慈善救济事项;警政司第二科、第五科分管消防、卫生事项(民初,救火防疫事宜多由水龙会及其他善会善堂负责,因而也属于公益慈善事业)。尽管后来组织机构屡有变更,但慈善公益事项仍属民治司管辖。1917年3月,内务部民治司再度变更分科职掌范围,第四科继续主管慈善行政,然具体事务有所扩大,涵盖了地方罹灾救济、地方筹办赈捐之核准、地方捐赈人员奖励、红十字会之设置救济及奖励、京师平粜、收养贫民、散放棉衣及开辟临时粥厂、育婴恤嫠及其他慈善事业,以及经管游民习艺所、济良所、教养局和贫民工厂、地方善堂等十余项④。1922年9月,内务部各厅司之间的慈善行政事务又有所调整,疫病防治从警政司划出,重归卫生司管理,诸项慈善公益事务仍归民治司第四科。可见,民治司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主管慈善事业至为重要的行政机构。
随着中央行政管理体制的变更,地方慈善行政机构也相应地进行过调整。1913年1月,北京政府颁布法令,规定省行政公署政务厅主管各项慈善救济事务。后来,省级行政公署改为巡按公署、省长公署,但政务厅职责未变,仍主管公益慈善及救济事项。在县级,地方慈善事务则长期划归内务科管理。由此,北京政府基本上确立、完善了中央和地方各级的慈善行政体制,即实行中央—省—县的三级管理体制,分别负责同级的各项慈善事务。
(二)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慈善行政体制的发展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慈善行政体制也在数年间自上至下建立和运作起来。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设立内政部,置秘书处及民政、土地、警政、卫生四司,赈灾救贫及其他慈善事项属民政司职掌范围,而水灾之防御及救济事项归土地司负责⑤。其中,民政司第四科负责社会救济及其他社会福利事项,具体为贫民救济、残废老弱救济、勘报灾歉、地方罹灾调查赈济、防灾备荒、慈善团体考核、慈善事业奖励、地方筹募赈捐与游民教养事项⑥。上述事项大都属于慈善事业的范畴,或与之息息相关。10月,国民政府改组,内政部改隶行政院,仍“管理全国内务行政事务”,惟部内改设总务、统计、民政、土地、警政、礼俗等六司。增设的统计司,其执掌事项中乃有“关于宗教、慈善团体及其他社会团体之统计事项”;民政司仍负责赈灾救贫及其他慈善事项⑦。1930年底,卫生部并入内政部,改为“卫生署”,其他六司依旧,而民政司、统计司继续掌有赈灾、救贫、监督其他慈善事项,以及统计慈善团体之职权;土地司掌有水灾防御及救济事项,而礼俗司则增列褒扬事项,负责褒奖慈善捐赠及其他有功于慈善事业等德行可嘉者⑧。1936年7月,国民政府又一次调整内政部设置,撤销卫生署,统计司改为统计处,其余各司名称因循不变,其职权也大致未改,仅将水利防御及救济划出,归全国经济委员会。有关赈灾、救贫、其他慈善事项及褒扬事项继续为民政司、礼俗司执掌⑨。在历次调整中,民政司都设有一科,专门管理慈善事业,负责慈善团体的监督考核、奖励等。
地方慈善行政体制也渐次推展开来。1927年7月以后,各省由民政厅负责管理全省的慈善事务⑩。此后,一直相沿不变。而与省级行政建制并设的特别市,“一切农、工、商、公益等事项”均归社会局管理(11)。1930年,特别市撤销,改为行政院直辖市,但其慈善行政体制并未改变,社会局仍负责各项慈善事务。一般的县、市,则由民政科主管公益慈善事业。这种慈善行政体制甚至向乡镇及区公所等地方基层延伸。1930年,《修正区自治施行法》就规定,“育幼、养老、济贫、救灾等设备事项”是区公所、区长负责的各项事务之一(12)。在一些特别行政区域,国民政府也试图建立起相关的慈善行政机构,并从法律上赋予其监管慈善事业的权限。1931年威海卫管理公署设立后,即由总务科负责育幼、养老、济贫、救灾等设备事项(13),以发展地方慈善公益事业。
从广义上讲,灾荒救济也属于慈善行政体制的一个方面。1928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赈务处,掌理灾区赈济及善后事宜;处内又置赈款委员会,凡赈款的募集、保管、分配和使用,均应经该会议决(14)。1929年2月,国民政府撤销赈务处,设立赈灾委员会,以统一全国赈灾事宜。该会置执行、监察、设计三委员会及秘书处,其人员由国民政府特派,并从中指定常务委员会9-11人,1人为主席。一年后,国民政府明令该赈灾委员会改为振务委员会,办理各灾区赈务事宜。振务委员会由国民政府特派委员11人组成,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农矿、工商、铁道、卫生各部部长为当然委员;会内设总务、筹赈、审核三组;总务科负责筹划会务、购置物品;筹赈科负责筹募赈品赈款、赈品运输、免税及免费各项护照的办理;审核科负责审核赈款、赈品的出纳等(15)。随后,国民政府在省、市、县各级也设立振务委员会、分会。
(三)南京国民政府后期慈善行政体制的变革
卢沟桥事变既是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后期的分界线,也是其慈善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战事爆发,难民骤增,救济日趋繁重,原有慈善行政已无法有序进行,于抗战十分不利。这迫使国民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现有的慈善救济机构,理顺慈善行政体制,以便事权归一,提高行政效率。
1937年9月7日,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决定成立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设总会于南京,由行政院、内政部、军政部、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署、赈务委员会等部门各派一人为委员,加强协调统筹;各省市县也普遍设立分、支会,办理难民救济事项(16)。至此,一套上下有序、分级负责的难民救助体制初步确立起来。但因战事继续蔓延,难民人数不断激增,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逐渐暴露出事权不大、与赈务委员会职权重叠等弊端。鉴于此,1938年2月24日,国民政府公布了《赈济委员会组织法》,进一步统一难民救济体制。依照该法,赈济委员会掌理全国赈济行政事务,下设三处。第二处负责救灾机关的指导监督、灾民的救护与管理,以及赈款的募集、保管、分配等事项;第三处为各项慈善事务的主管机构,具体包括慈善机关的指导监督,残废老弱的救济,贫民的扶助,游民的教养以及其他有关社会救济事项(17)。4月27日,国民政府将原设的赈务委员会、行政院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合并改组,并接管内政部民政司执掌的救济行政业务,正式成立了赈济委员会。赈济委员会权力颇重,下辖各省市县赈济会、各救济区等机构,同时兼管多项慈善行政事务,这对于战争期间慈善事业开展有一定的规范、促进作用。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曾三次调整赈济委员会的组织机构,主管慈善事务的第二、三处职权略有变化。上述两个机构的设置和调整表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慈善行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平常的慈善救济转向战时难民救济。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慈善行政体制另一重大变化是社会部的设立。社会部原系国民党党部机构,根据蒋介石的训示,1939年11月开始进行改组改隶事宜。1940年11月16日,社会部正式改隶于行政院,管理全国社会行政事务。其中,社会福利司第五科负责掌理各项慈善救济事务,具体为残疾老弱救济、贫民救济、救济经费的规划及审核稽查、慈善团体的指导监督、国际救济的联络等项,第六科也掌管多项儿童福利救济事务(18)。同时,各省在省政府之下设置社会处,或于民政厅内设社会科,院直辖市则由社会局主管,县政府也设置社会科。由此,变更和建立起一套上下衔接的慈善行政体制。由于施政理念的变化,国民政府开始由消极救济转为积极救济,并将社会救济扩充至社会福利。南京国民政府在慈善行政方面的变革,客观上有助于慈善事业的有序发展。
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内政部进行了机构调整,以适应战时需要。1938年2月,内政部所属机构调整设置为总务、民政、警政、土地、礼俗五司及统计处、卫生署、禁烟委员会。在各司、处中,民政司仍旧掌理赈灾、救贫及其他慈善事项,不过,部分社会救济行政已划归新设立的赈济委员会;统计处还负责慈善团体及其他社会团体的统计事项;礼俗司仍执掌慈善事业的褒扬事项(19)。虽然这次机构调整划出了民政司部分救济行政职能,但在整体上对慈善行政影响并不大,仍负责日常慈善业务。
为接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赠的慈善物资,办理收复区善后救济事宜,1945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下设有储运、分配、财务、赈恤四厅及调查、编译、总务三处。赈恤厅、调查处负责有关慈善救济业务,具体包括难民的资遣返送、收容救助、灾区灾情调查与救济等(20)。8月,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收复区的善后工作随即展开。国民政府很快在全国成立了15个善后救济分署,各分署设赈务、储运、卫生、总务四组,由赈务组负责具体的工赈、急赈等慈善救济业务;卫生组负责防疫医疗救济业务(21)。实际上,各分署在收复区的善后救济工作大都同当地慈善团体有密切关联,或补助、接济慈善团体款物,或直接依托慈善组织开展善后救济;或慈善团体负责人参与到分署的工作中。行署及地方分署成为战后国民政府慈善行政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1947年底,行总因善后救济工作已基本完成而撤销,相关慈善救济业务划归社会部。随即,社会部下属机构也进行了大调整,设社会福利司,有两科负责慈善事务。但社会福利司的业务范围更宽广,慈善行政在整个社会行政体制中的地位有所下降。
民国慈善行政体制的沿革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近代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嬗变进程,它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慈善行政理念的变化,即由消极救济而趋向积极救济,并摒弃传统慈善的施舍观念,进而为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慈善事业逐渐融为社会福利事业的一部分。
二、民国时期的慈善立法
在建立慈善行政体制的过程中,民国政府也着手推进慈善立法工作,渐次颁行了一系列慈善事业的法律法规。总的来说,民国慈善立法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其内容基本涵括了慈善组织的监管、慈善捐赠褒奖、税收减免等三大方面。
(一)监管慈善团体立法
中国红十字会成立于清末,及至民初,其地方分会已达上百处,广泛分布于南北各省,成为全国颇具影响的一个慈善团体。中国红十字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北京政府的关注,觉得有必要制定法律进行监管。在袁世凯的推动下,1914年9月24日,北京政府公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这是民国时期第一部关于红十字会的法规,也是第一部监督慈善组织的单行法、专门法。该法明确了政府对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管理权;规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与任务为“辅助陆海军战时后方卫生勤务”,并“分任赈灾、施疗及其他救护事宜”;确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组织结构与人事任免(22)。为便于实施,1915年10月,又公布了《中国红十字会条例施行细则》,详细规定了红十字会的各项事业、会员、议会、职员、资产、奖励及惩罚(23)。1920年,红十字会条例及施行规则进行了修正,将基金增列为总会资产之一,存储于银行,并明定非经内务、陆军、海军三部核准不得动用。尽管北京政府制订的《中国红十字会条例》及其细则还不够完善,但它的颁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中国红十字会及其各地分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红十字会立法乃至慈善组织立法的先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很重视中国红十字会的立法工作。从1927年至1949年,先后制定颁行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及两次修正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战时组织条例》,并草拟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立法趋于成熟和完善。南京国民政府在30年代的红十字会立法活动,基本上继承和移植了北京政府法规的主要内容;同时,又不断加强政府的监管力度,以致红十字会在抗战期间实行军管,一度演变为国家机构,战后才逐渐回归民间慈善团体。
为加强对慈善组织的管理,1915年12月,北京政府还颁布了《游民习艺所章程》,对习艺所这类慈善机构的设施、收养对象及教养科目进行规范(24)。此时,一些省区也开始关注慈善团体的立案备案问题,相继出台一些地方性法规,将当地慈善组织置于法规的监督管理之下。这些做法,也为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监督管理慈善团体奠定了基础。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要求各级政府依法设立救济院,并斟酌各地经济情形,分别缓急,次第筹办或合并办理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等所,以教养无自救力之老幼残废及救济贫民生计(25)。随后,全国各县对原有善堂善会进行接收、改组,逐渐纳入到救济院系统中。10月,又制定了《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规则》,规定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应将机关名称、所定地址、所办事业、财产状况、现任职员姓名、履历详细造册呈报主管机关查核,转报内政部备案(26)。两规则颁布实施后,因有人呈请解释私立慈善机关管理范围,加之其法律位阶低,调整范围及法律关系有限,1928年底,国民政府饬令立法院赶速制定慈善团体立案注册条例。1929年6月12日,经多次审议,《监督慈善团体法》最终获得通过颁行。该法由于调整范围广,内容较全面,成为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慈善事业的基本法。它首先界定了慈善团体,即“以济贫、救灾、养老、恤孤及其他救助事业为目的之团体”,并对发起人的人数及其资格、主管官署检查事项与褒奖办法等作了规定(27)。7月,行政院出台《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细则》,补充规定了慈善团体设立备案程序、募捐许可及财务信息呈报制度等,并进一步明确了各级主管官署,以便查核。及至1932年9月,内政部公布《各地方慈善团体立案办法》,细化立案条件与程序。此外,1929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寺庙管理条例》及随后修正的《监督寺庙条例》,也规定了“寺庙应按财产情形,兴办公益或慈善事业”(28)。为推动其实施,1932年内政部又制定了《寺庙兴办公益事业实施办法》,后因中国佛教会呈请而暂缓施行。至1935年1月,该办法经修订改称《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由内政部公布实施。该规则规定“寺庙应斟酌地方之需要,兴办慈善公益事业”,并“应受主管官署之监督并当地佛教会之指导”(29)。这些法规的颁布施行,推动了传统善堂善会向近代慈善团体的组织变革,并进一步规范引导慈善救济事业的转型与发展。
40年代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公布施行《社会救济法》、《救济院规程》、《管理私立救济设施规则》、《私人办理济渡事业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以规范各类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而1943年《社会救济法》的出台似乎表明,由于西方国家现代社会保障思想的播迁,南京国民政府欲将传统消极的慈善观念转变为国家积极的行政责任,逐步纳入到社会福利制度中,这对民国后期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慈善税收优惠立法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普遍从税制上扶持慈善事业发展。民国政府也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在税法中规定了慈善组织和捐赠人可享受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
1、慈善组织享受的税收优惠
民国年间颁行的各种税法中,对慈善组织予以税收优惠的税种主要有收益税、所得税和行为税三类。
在收益税方面,相关税法主要是《土地法》、《土地赋税减免规程》、《房捐征收通则》和《营业税法》。1915年10月,北京政府颁行《土地收用法》,规定地方自治团体或人民为谋公益事业之需要,经国家允许,可收用宅地、山林、荒地等公有或民有土地,而“关于教育、学术、慈善所应设之事业”即合于其需要之一项(30)。1930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法》对慈善组织在土地赋税方面也给予多项优惠政策。如第四编第九章规定:学校、公共医院及慈善机关用地“得由中央地政机关呈准国民政府免税或减税”(31)。1936年,《土地赋税减免规程》颁行实施,对减免赋税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二三十年代,上海、南昌、北平、四川等省市先后制定了房捐征收地方性法规,对于慈善团体的房产,亦规定可酌情减免。1941年5月,财政部统一颁行《房捐征收通则》,其免捐规定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房屋,“业经立案之私立学校或慈善团体”即属之(32)。《营业税法》自1931年6月公布施行,其中也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作社、贫民工厂等,得免征营业税。”(33)
在所得税方面,相关税法主要有《所得税法》、《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1914年1月,北京政府公布了《所得税条例》,后因政局紊乱,未能在全国推行(3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续筹办所得税。1936年7-8月,《所得税暂行条例》暨施行细则经立法院会议通过并明令公布。关于免税条款,该条例以列举方式对三类不同所得分别作了规定。具体言之,“第一类营利事业所得之减免,仅限于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法人所得。此项所谓法人,以合于《民法总则》中规定的公益社团及财团之组织,经向主管官署登记成立者为限。惟非营利事业之法人或团体而兼营营利事业者,视为营利事业,仍应课税。”(35)第二类薪给报酬所得之减免,卯款“残废者、劳工及无力生活者之抚恤金、养老金及赡养费”亦属之。第三类证券存款所得之免税规定有寅款“教育慈善机关或团体之基金存款”,施行细则解释其“系指具有长期固定性质、用利不动本之定期存款或有特定用途经主管机关核准得动用本金及作为活期存款存储者”(36)。抗战爆发后,财政部拟具修正草案转立法院审议,立法院以条例系临时性质,所得税已成定制,宜改称税法。1943年2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所得税法》,同时废止《所得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于同年7月9日公布。新颁《所得税法》的修正内容主要是调整税率、提高罚则,而对第一、第二、第三类所得的免税条款仍保持不变,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法人所得,以及教育慈善机关或团体之基金存款等,依然可免纳所得税(37)。为增辟税源,抑制非法暴利,财政部决定开办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1943年1月28日,《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法》公布实施,其课税范围为土地、房屋、堆栈、码头、森林、矿场、舟车机械之租赁所得或出卖所得,但对“教育文化、公益事业之租赁所得或出卖所得全部用于各该事业者”可免税(38)。
在行为税方面,《印花税法》、《筵席及娱乐税》等税法对慈善组织也有一些免税规定。如,1934年的《印花税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凡不营业、不营利性质的票据(如慈善机构的账簿)属于免征之列(39)。1942年4月,《筵席及娱乐税法》公布实施。根据该法规定,筵席税率为10%,娱乐税率为30%,由馆商、场商代征;学校、公共团体举行游艺募捐,收入作公益之用,或为赈灾筹款者,经核准可以免税;征收细则及相关免征事宜,由各省市政府依法分别订之,送财政部核准后施行(40)。1943年、1946年和1947年,该税法三次修改筵席税征收税额及娱乐税征收范围,对于公益慈善机构所举办的各种娱乐,如其全部收入用于慈善救济事业,仍属免征娱乐税之列(41)。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还制定《铁路运输赈济物品条例》及《减价凭单持用办法》、《铁路运输灾区商运粗粮减价条例》等法规,准许赈务机关、民间慈善团体运输赈品时减免一定税费。
2、捐赠人享受的税收优惠
1915年夏,北京政府曾拟订《遗产税条例草案》11条,其中规定,“凡捐赠其财产于公益慈善或合族义庄在1000元以下者”,准免纳遗产税,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42)。然而,因军阀割据,该草案悬置未果。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屡议遗产税。1938年10月、12月,公布《遗产税暂行条例》及其施行条例。这两个条例首先明确了遗产税的立法原则和立法精神,并对课税财产、减免税范围、税率、征收程序等作了规定。其中,第7条列举有关免纳遗产税的五种情形,第五款即为“捐赠教育文化或慈善公益事业之财产未超过五十万元者”(43)。1945年和1946年。立法院两次审议《遗产税法》修正案,对调整免税额、扩大免税和扣除范围、提高税率等内容进行了修订。关于捐赠教育文化或慈善公益事业之财产的免税额,也由原来的未超过50万元调整为未超过200万元(44)。1946年7月12日,行政院又公布《遗产税法施行细则》,对遗产税法中存在的若干细节予以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该细则第五条规定:“依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四款、第五款免税者,应将捐赠之财产额,报明遗产税稽征机关。依本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五款捐赠之财产额,超过二百万元时,应按其超过部分之价额,与其他应纳遗产税部分之价额,合并计算征收。”(45)
除上述税法之外,国民政府颁行的其他法律也含有对慈善组织的优待条款。像1935年7月24日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规定了各级政府对于慈善救济事业在必要时予以补助金或协助金(46)。1937年7月颁行《军事征用法》,也规定在战事发生或将发生时,陆海空军为军事上紧急之需要,得依法征用军需物及劳力。但在征用标的上,第9条规定了免征条款:“养老院、盲哑院、慈幼院、贫儿院、孤儿院、栖流所、战时救护组织及其他慈善机关使用之必要场所建筑物及设备,不得征用之。”(47)
(三)褒奖慈善捐赠立法
北京政府时期的慈善捐赠褒扬立法,主要有《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和《义赈奖劝章程》两项。民国肇建后,各省以捐资兴学屡向中央政府呈请援例褒扬。然而,国体更新,旧章已不尽适用,北京政府遂令教育部、内务部着手草拟相关法案。1913年7月17日,国务会议公布了由教育部草拟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该条例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准由地方长官开列事实,呈请褒奖。”其以私财创办或捐助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有关教育事业者,照准前项办理,并对捐资者按捐赠数额分别给予不同等级的金质、银质褒章或匾额。这是民国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对捐资者的褒奖,刺激了人们捐资兴学的积极性。1914年、1918年和1925年,教育部先后三次对《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进行修正,补充了团体捐资、华侨捐资、遗命捐资等褒奖情形以及两万元以上巨资兴学的特奖办法,并经国会议准或大总统核准公布实施(48)。1925年通过的《修正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形成了北京政府时期慈善公益捐赠褒奖的基本格局,对后来南京国民政府同类法律法规的制定、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民国前期另一部关于慈善捐赠的重要法规《义赈奖劝章程》公布于1914年8月,它主要鼓励人们对灾害进行捐资救助。此外,北京政府还于1914年颁行了《褒扬条例》,对尽心公益者予以褒奖。1921年,内务部制定的《慈惠章给予令》及其施行细则,也规定凡合于捐募赈款、办理公益与慈善事业的妇女,分别等次,授予慈惠章。这些褒扬条例的制定,有利于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慈善公益活动,通过多渠道聚集社会财力、人力、物力,弥补政府救济的不足,推动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1929年1月底2月初,相继颁布《兴办水利防御水灾奖励条例》、《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捐资举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对以私财捐助办理水利、教育、公共卫生及救济等慈善事业的民众和社会团体,按捐数之多寡订立褒奖之等差。这些条例后来都进行过一些修订,如《兴办水利防御水灾奖励条例》经修订为《兴办水利奖励条例》,于1933年10月14日公布;1935年4月4日又公布了《修正兴办水利奖励条例》。鉴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教育现状,1934年7月又颁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补充办法》4条,对于在蒙古、西藏、新疆、西康、宁夏、青海及甘肃等地方捐资兴学之褒奖,予以适度倾斜,并由教育部、蒙藏委员会共同负责审核备案、查酌授与;捐资额达3000元以上,依等级还可颁令嘉奖、或题给匾额(49)。30年代初,由于各省灾荒频仍,为鼓励慈善救济团体募集赈款,协力赈灾,国民政府还公布实施了《办赈团体及办事人员奖励条例》、《褒奖条例》、《颁给勋章条例》及其施行细则。这三项条例都规定了对热心慈善公益者予以褒奖,授予匾额、褒章或勋章。如,1935年2月22日公布的《颁给勋章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创办慈善事业规模宏大、福利社会昭垂久远者”可颁给采玉勋章;若友邦人民“创办教育或慈善事业,有功于我国家社会者”,亦授予采玉勋章(50)。
抗战爆发后,大量工厂被迫内迁,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工商凋敝,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原有法规的若干条款,如关于褒扬捐资的数额标准已失去激励作用,显得不切实际,有必要进行调整。1942年8月29日,国民政府首先公布《修正捐资兴办社会福利事业褒奖条例》。随后于1943年7月29日修正公布《兴办水利事业奖励条例》。1944年2月10日、4月1日,又接连公布了修正后的《捐资兴学褒奖条例》、《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1945年5月10日,再度修正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第2条、第6条及第7条条文。以上修订,主要是根据物价情形对褒奖等级相应地提高了捐资额度的要求,同时对褒奖程序进行一些变更。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慈善法规已颇具规模,渐臻完备,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兴盛。具体言之,其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界定和规范慈善活动的主体组织及其行为;二是鼓励和褒奖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捐赠活动,建立起激励机制,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尽管民国政府的慈善法规还存在条文互歧等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但这一系列具有近代色彩慈善法规的制定与颁行,不仅对民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而且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注释:
①②⑩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9、360、464页。
③《中国大事记》,《东方杂志》第9卷第3期,1912年,第13页。
④商务印书馆编译处编:《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245—246页。
⑤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8册,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149页。
⑥徐百齐编:《中华民国法令大全》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06页。
⑦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7册,第33—34页。
⑧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20册,第110页。
⑨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51册,第80—81页。
(11)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5册,第3页。
(12)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16册,第119页。
(13)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20册,第179页。
(14)(15)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414—415、415页。
(16)秦孝仪主编:《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第1册,《革命文献》丛书第96辑,台北裕台公司1983年版,第56页。
(17)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61册,第149页。
(18)秦孝仪主编:《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第2册,《革命文献》丛书第97辑,第25—27页。
(19)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61册,第133—134页。
(20)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92册,第24页。
(21)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94册,第110页。
(22)《中国红十字会条例》,《申报》1914年9月29日。
(23)《中国红十字会施行细则》,《政府公报》1915年10月8日。
(24)商务印书馆编译处编:《最新编订民国法令大全》,第480—481页。
(25)(26)(27)上海市社会局编:《公益慈善法规汇编》,上海市社会局1932年刊本,第20—21、20—21、16—17页。
(28)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523页。
(29)《佛教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规则》,《江苏省政府公报》总第1880号,1935年,第8—9页。
(30)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1153页。
(31)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16册,第114页。
(32)(33)国家税务总局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29页。
(34)国家税务总局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35)(36)(42)(44)国家税务总局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第24、24、213—216、232—233页。
(37)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84册,第25页。
(38)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83册,第140页。
(39)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574—575页。
(40)(41)国家税务总局主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第316—318、323页。
(43)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64册,第18—19页。
(45)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97册,第103页。
(46)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44册,第7页。
(47)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59册,第104页。
(48)《教育部制定捐资兴学褒奖条例及拟定特奖巨资兴学办法案(1913—19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北京政府教育部档案,档号:1057—96。
(49)《捐资兴学褒奖条例补充办法》,《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3期,1934年,第95页。
(50)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编:《国民政府公报》第41册,第64—65页。
标签:慈善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行政主管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行政立法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