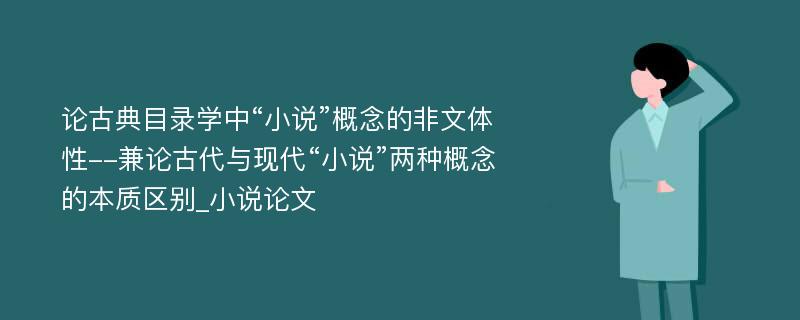
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非文体性质——兼论古今两种“小说”概念的本质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录学论文,概念论文,两种论文,小说论文,古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典目录学向来被誉为治学的门径,对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研究,我们也常常借助古典目录学来界定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却往往发现古人所谓的“小说”与今人所谓的“小说”①大相径庭,难以侔合,因而对“小说”概念的界定不免有些进退失据,无所适从。这种困境,无论是在一些有关“文言小说”的研究论著中,还是在一些有关“文言小说”的书目类著作中,都几乎不可避免。怎样摆脱这种困境,成为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
如果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仔细考察一下我们常常引以为据的古典目录学著作,就会发现,其实从《汉书·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家”始终是作为一个收容其他部类的“不入流之作”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的“垃圾桶”而存在的;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始终没有被赋予任何正面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定义,它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实在是两个难以混同的概念。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必须仔细区分这两个名同实异、所指非一的“小说”概念,才能避免因概念的混乱而陷入研究的困境。
而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研究者虽已有所讨论,但尚未能彻底辩明②。本文希望能对这个问题加以更加细致、系统的讨论,以期推动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研究的进展。
(一)
现在一般研究者提起“小说”,总会首先指出“小说”一词初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同时,有的(并不是全部)研究者也明白,这里的“小说”指的是琐屑的言谈、细小的道理,与“正说”、“大道”相对而言,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全无关系。此外,《论语·子张》中的“小道”,《荀子·正名》中的“小家珍说”,都是与《庄子》的“小说”意义相近的词,可以作为理解《庄子》的“小说”概念的参考。总之,诸子在论争中,皆以己说为“正说”、“大道”,而贬斥异己学说为“小说”、“小道”,这就是“小说”一词的来历。
“小说”一词虽然是在诸子论争中随意而偶然地产生的,但由于后来荣登了古典目录学的大雅之堂,遂与其他“小道”、“小家珍说”之类的词判然殊途,最终成为一个固定术语,而“小说家”也成为古典目录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类;但“小说”一词最初出现时就具有的上述这种消极含义,对于后来古典目录学所谓“小说家”的概念,具有极为重要的负面规定作用。
在古典目录学中,“小说”一词首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汉志》系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成,其所列“小说十五家”及“小叙”,基本可以认定是来自于刘歆《七略》的。而与刘歆同时的桓谭,在其《新论》里也提到了“小说家”一词:“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③两处基本同时出现的“小说家”一词,对于我们认知当时所谓的“小说”概念有相互参证的意义。
《汉志》“小叙”可谓我们判断其“小说”概念最直接的资料,可惜这段话却语焉不详。它只点明了“小说家”的远源——“盖出于稗官”,揭示了“小说”的来源——“街谈巷语”,也肯定了其薄弱的存在价值——“有可观者”,却“致远恐泥”,但始终没有赋予“小说”以一个正面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定义。可以说,这段“小叙”对于“小说”及“小说家”的界定,尚不及桓谭所论精确明了。《汉志》认为的“小说家”是什么,只能从其所列书目来考察。
《汉志》所列诸书,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该书至隋亦佚。这些书的亡佚,对后人正确判定《汉志》“小说家”的准确含义造成了很大困难。十五家中,自《封禅方说》以下六家为汉人著作,据排列次第,《黄帝说》以上应为(或伪托为)汉前著作。这些汉前著作,据班固自注,可信者唯《周考》、《青史子》、《宋子》三种,其余皆被判定为“依托”、“后世所加”、“非古语”。在班固认为比较可信的三种中,《周考》已佚,不可考。《宋子》已佚,无可靠佚文流传④。《青史子》今存佚文三条,即“胎教”条、“巾车教”条、“鸡祀”条⑤,皆言礼,后人多质疑其何以入“小说家”⑥,但观其文,却正符合桓谭所论“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有助“治身理家”的“小说”概念。
此外,被怀疑为“依托”之作的《伊尹说》也有佚文留存,《吕氏春秋·本味篇》所载伊尹“以至味说汤”之事,一般认为即出自《伊尹说》⑦。其余几种依托之书,研究者虽也有论,但各种典籍中记载的黄帝、汤、务成子、鬻熊、师旷等人的言行事迹,是否即出自《汉志》“小说家”中的相关书籍,尚不易判定⑧,因而其书的性质和特征便也难以推论。
《汉志》所录汉前“小说”,据现存佚文来看,基本符合“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的“小说”概念,而所录汉人“小说”则极为驳杂。其中《百家》今存佚文两条,刘向《说苑·叙录》云:“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⑨由此可知,《百家》应是刘向校书时汇集各家书中“浅薄不中义理”的片断而成。其余著作,据研究者推测,《封禅方说》、《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可能是有关封禅、养生的书⑩;《虞初周说》可能是“医巫厌祝”方面的书(11);《待诏臣饶心术》可能是有关见闻果报劝诫之类的书(12);《臣寿周纪》可能记周代琐事(13)。
这些“驳杂之作”之所以入“小说家”,余嘉锡认为,这些书“虽出于方士,而巫祝杂陈,不名一格,几于无类可归,以其为机祥小术,闾里所传,等于道听途说,故入之小说家”,“小说家”一类,“盖至是其途始杂,与古之小说家,如《青史子》、《宋子》者异矣”(14)。余氏所论有一定道理。班固在“诸子略”叙中,指明“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对“小说家”则黜而不论。其视“小说家”为“琐说”、“小道”,把它与其余九家之“正说”、“大道”判然分别的态度,不言而喻,因而把这些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归入“小说家”也是顺理成章的。
概括言之,《汉志》的“小说家”中,虽然有符合桓谭所论的“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有助“治身理家”的“小说”,但占多数的却是一些其他部类的“不入流之作”(如《百家》)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如《封禅方说》、《虞初周说》等),具有一种“杂烩”的性质,因而我们无法从中归纳出“小说”任何正面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定义;而《汉志》“小说家”收容其他部类的“不入流之作”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的做法,正是整个古典目录学以“小说家”为“垃圾桶”这一传统的滥觞。
(二)
从《汉志》发轫的以“小说家”为收容“不入流之作”和“驳杂之作”的“垃圾桶”的传统,为后来的一系列史志目录所踵袭。《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是《汉志》以后另一部重要的史志目录。《汉志》“小说家”所录诸书,至《隋志》成书时俱已亡佚,《隋志》另著录《燕丹子》等“小说”二十五部。
《隋志》“小说家”小叙延续了《汉志》的说法,认为“小说”是“街说巷语之说”,但它舍弃了《汉志》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而增加了《周官》中有关“诵训”和“训方氏”职责的记载。这传达出《隋志》对《汉志》的理解,即认为“诵训”和“训方氏”大抵相当于《汉志》所谓的“稗官”。对这一理解,余嘉锡已驳其非:“诵训所掌,乃四方之古迹方言风俗,训方氏所掌,则其政治历史民情也,当为后世地理志郡国书之所自出,与小说家奚与焉?”(15)而从《隋志》“小说家”著录作品本身来看,与其小叙的解释也并无对应关系。因此可以认为,《隋志》小叙只是对《汉志》小叙作了一些不深考的沿袭,可存而不论。《隋志》究竟怎样看待“小说家”,需要从其著录作品本身来考察。
《隋志》所录“小说家”作品,今存的有《燕丹子》、《世说》(刘义庆撰)、《世说》(刘孝标注);有佚文可见的有《杂语》(16)、《郭子》、《笑林》、《小说》(殷芸撰)、《水饰》(17);虽无佚文,但有前人论述可据,可大致判断其性质的有《琐语》(18)、《古今艺术》(19)、《器准图》(20)。
这些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为谐谑类,如《笑林》。《笑苑》、《解颐》虽无佚文可见,但从书名来看大致也是这类作品。谐谑类入“小说家”,正是自《隋志》始。二为轶事类,如《杂语》、《郭子》、《琐语》、刘义庆《世说》、刘孝标注《世说》、殷芸《小说》。这些书皆简略记载秦汉魏晋六朝名人轶事,而《郭子》、《世说》尤重人物清言妙语。三为图说类,如《古今艺术》、《器准图》、《水饰》(21)。
谐谑类和轶事类,志人记言皆以简略相尚,而图说类更是片言只语,这些作品大概皆因琐屑驳杂而入“小说家”。《燕丹子》一书,叙事连贯,情节曲折,迥异于《隋志》所著录的其他“小说”书,而颇合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但详审其入“小说家”的原因,则很可能是该书托名先秦人物,不见于《汉志》,而反见于此时,史志撰写者对其真伪存疑,因而退入“小说家”者。《隋志》“小说家”所著录其余各书,既无佚文可见,又无相关资料可据以准确判定其性质,但可以肯定,这些书也绝不会符合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
直接以“小说”二字命名的殷芸《小说》,或许对我们认知当时人的“小说”概念有些许参考价值。据《隋志》自注,此书乃殷芸受梁武帝敕命所撰。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杂说》也有类似说法,且更言明,此书所记载的乃是一些如“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之类的“不经”之说。清人姚振宗据此推论曰:“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事凡此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此《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也。”(22)据现今辑佚本来看,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尽管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书中有些片段很像故事,比较符合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但从其命名的本意来说,仍然不出自先秦沿袭而来的“琐说”、“小道”的范畴,其所收集的只是《通史》所不取的“不经之说”。
《隋志》“小说家”所著录的作品,没有一部可以认为符合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而另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符合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的《搜神记》、《吴越春秋》一类作品,却更多著录于史部的杂传类、杂史类。一反一正,或许已足以说明,《隋志》所谓的“小说”,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毫不相干。
总而言之,《隋志》的“小说家”虽增益了一些志人记言之作,这些书或许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甚至具有某些文学性因素,但从其“小说家”所包含的全部作品来看,仍如《汉志》一样具有“杂烩”的性质,我们难以从中归纳出这些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可见,《隋志》也仍如《汉志》一样,并没有赋予“小说”以任何正面的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定义,其“小说家”仍然是收容其他部类的“不入流之作”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的“垃圾桶”。
(三)
《旧唐书·经籍志》(以下简称《旧唐志》)系据唐毋煚《古今书录》修成,而删其原有小叙,“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23)。所著录“小说家十三部”,删除《隋志》所载而已经亡佚之书,新增《鬻子》(鬻熊撰)、《博物志》(张华撰)、《续世说》(刘孝标撰)、《小说》(刘义庆撰)、《释俗语》(刘霁撰)、《酒孝经》(刘炫定撰)、《启颜录》(侯白撰)等七部书。
《鬻子》系自道家类误入,可存而不论。《博物志》今存,其书山川地理、飞禽走兽,无所不记,但皆片言只语,不成体系,该书大概也是因琐屑而从《隋志》的“杂家”退入《旧唐志》的“小说家”的。《启颜录》有佚文,属于谐谑类。《续世说》、《小说》两书虽佚,但名字近似《隋志》“小说家”所载刘义庆《世说》、殷芸《小说》,性质应与之相类。《释俗语》、《酒孝经》两书已佚,性质无从判断。总体看来,《旧唐志》与《隋志》相比,其“小说家”无很大变更。
至《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小说家”体格顿时庞大,作品数从《旧唐志》的十三部增至一百多部。新增的作品主要有以下几类:一为志怪类,有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等;二为杂史类,有韦绚《刘公嘉话录》、高彦休《阙史》等;三为箴规类,有李恕《诫子拾遗》、狄仁杰《家范》等;四为考订类,有李涪《刊误》、李匡文《资暇》等;五为叙述典故类,有刘孝孙《事始》、刘睿《续事始》等;六为谱录类,有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等(24)。
新增的六类作品中,以志怪类和杂史类作品居多,这些作品在《隋志》、《旧唐志》中归属于史部杂传类、杂史类,到《新唐志》则被退入“小说家”。志怪类颇合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而杂史类某些作品也具有文学性因素,因而有人认为,在“小说”(这里他们自觉不自觉地用的是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观念的发展上,《新唐志》“小说家”是一个质的飞跃,此时的“小说”观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
但这种观点却似乎有点一叶障目。除志怪类和杂史类作品外(其实杂史类中也仅仅是某些作品或许含有一点文学性因素,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距离尚远),《新唐志》“小说家”所增益的其他四类作品,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相去甚远,难以混同,而这一点足以说明《新唐志》并不是从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出发,对作品进行分门别派的(当然《新唐志》也根本不会具备文学性的“小说”概念)(25)。进一步考察则更会发现,在《新唐志》“小说家”中蔚为大观的志怪类和杂史类作品之所以入“小说家”,并不是由于宋人的“小说”观念有了发展,而是由于宋人的史学观念有了发展(26),他们再也容不得这些“子虚乌有”的“不入流之作”和不成体系的“驳杂之作”混迹于史部,因而把它们统统退入了“小说家”。
杂史类作品从《新唐志》起成为“小说家”中比重最大的一个类别,这开始造成人们以“小说”为“野史”的观念。《新唐志》以前的《汉志》、《隋志》和《旧唐志》,其中的“小说家”无所不收,而又没有任何一类作品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具有一种“杂烩”的性质,因而人们很难说清楚它们所谓的“小说”究竟是什么;而从《新唐志》始,杂史类开始在“小说家”中占据主要地位,因而人们产生了所谓的“小说”大概就是指“野史”这样一种印象。而“野史”其实也如同“小说”一样,是一个含有鄙夷色彩的、没有任何正面的质的规定性的概念,仅仅被用来指称那些史部所不要的作品。因而,即便是根据“野史”这个概念,我们也同样难以准确说明《新唐志》所谓的“小说”是什么,因为其实这也并不是古典目录学从正面给“小说”下的定义。
“小说”由“杂烩”向“野史”的倾斜,有一定的必然性。作为一个“崇史”的国度,中国史学的发展快于别的学科。随着史学观念的不断发展,古典目录学中的史部越来越“规整”,为此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剔除那些不合“规范”的作品;而具有“垃圾桶”性质的“小说家”,就不得不越来越多地收容那些从史部退下来的作品。但这无助于推进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向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的发展,同样也没有把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家”从“垃圾桶”的尴尬境遇中解脱出来。
《新唐志》之后的古典目录学著作,“小说家”中继续被塞进一些“驳杂之作”。宋代两部重要的私家目录都是如此。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把《后山诗话》、《东坡诗话》等诗话类作品归入“小说家”,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又把《梦溪笔谈》、《铁围山丛谈》等丛谈类作品归入“小说家”。这些填塞都被后来的古典目录学著作沿袭,成为在“小说家”中占一席之地的新的门类。《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在历代正史艺文志中最为驳杂,前代史志和私家目录中“小说家”作品的所有类型,在《宋志》“小说家”中几乎都可以见到,而且更把经部、子部的注释、评论类作品,如《五经评判》、《鬻子注》等,甚至把佛教类、诗文总集类的一些驳杂作品,如《物类相感志》、《诗海遗珠》等,也统统退入“小说家”。
经历代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的不断填塞,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家”越来越驳杂,于是就有学者出来作总结整理。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依据古典目录学的载录,把“小说家”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等六种。所列六种,“志怪”、“传奇”最近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杂录”稍远,而后三类——“丛谈”、“辨订”、“箴规”,则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全无关系。对于“小说家”的驳杂程度,胡应麟也头疼道:“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至于子类杂家,尤相出入。郑氏谓古今书家所不能分者有九(27),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说也。”(28)可见早在胡应麟的时代,古典目录学“小说家”五花八门、无所不收的“垃圾桶”性质,已经使得学者们困惑不已。
(四)
到《四库全书总目》,分“小说家”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等三派,“校以胡应麟之所分,实止两类,前一即杂录,后二即志怪,第析叙事有条贯者为异闻,钞录细碎者为琐语而已”。(29)《四库全书总目》把从前目录学著作列入“小说家”的“丛谈”、“辨订”、“箴规”三种剔除出“小说家”,而改隶于杂家,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四库全书总目》与今人“英雄所见略同”,其“小说”概念已开始接近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但它同时也剔除了今人认为最具文学性的“传奇”——不仅把它剔除出了“小说家”,而且不再予以著录。这就足以说明四库馆臣的“小说”概念与我们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仍是完全不同的。
而究其原委,《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的“小说”,主要指的是“史余”(这个概念大体相当于上文所提到的“野史”,可谓是“野史”的另一种文雅的称呼)。其“小说家”的小叙里,就时时流露出“以史格文”的倾向:“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推崇“资考证”,贬斥“诬谩失真”,用的完全是史学的标准。其“小说家”诸书的“提要”中,也流露出同样的倾向:“足与史传相参”,是对这类书的最高评价;而“颇涉语怪”、“不免稗官之习”,则常谓书中之瑕疵。
正是出于视“小说”为“史余”的观念,《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所收容的大都是史部的“不入流之作”:
《大唐新语》:……故《唐志》列之杂史类中。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30)。
《四朝闻见录》:……惟王士祯《居易录》谓其颇涉烦碎,不及李心传书。今核其体裁,所评良允。故心传书入史部,而此书则列小说家焉(31)。
《穆天子传》案语:《穆天子传》旧皆入起居注类……实则恍惚无征……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今退置于小说家,义求其当,无庸以变古为嫌也(32)。
这些书因“有乖史家之体例”,“以为信史而录之,则史体杂,史例破矣”,所以被“退置于小说家”。其他如经部,子部之释道家,以及农家、集部之“不入流之作”,也有被退入“小说家”的:
《孝经集灵》:……其言既不诂经,未可附于经解,退居小说家,庶肖其真(33)。
《仙佛奇踪》:……考释、道自古分门,其著录之书亦各分部,此编兼采二氏,不可偏属。以多荒怪之谈,姑附之小说家焉(34)。
《牡丹荣辱志》:……以姚黄为王,魏红为妃,而以诸花各分等级役属之……非论花品,亦非种植,入之农家为不伦,今附之小说家焉(35)。
《谐史集》:……凡明以前游戏之文,悉见采录,而所录明人诸作,尤为猥杂。据其体例,当入总集,然非文章正轨,今退之小说类中,俾无溷大雅(36)。
这些书因“未可附于经解”、“不可偏属”于释、道二家、“入之农家为不伦”、“非文章正轨”等理由,而被“退居小说家”。此外尚有无可归属之专题词典类(如《古今谚》、《六语》等)、别集之“妄荡”者(如《居学余情》),也统统被退入了“小说家”。“小说家”诸书“提要”说明该书因何退入“小说家”时,大抵不从正面解释该书有何“小说”之特质,而多言其因不得入某部某家而被退入“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的“垃圾桶”性质,便因这种叙述文法而表现得尤为鲜明(37)。
与此同时,《四库全书总目》以“小说”为“史余”,推崇“实录”、“雅驯”、“允正”等史学原则,强调“可资考证”的史学用途,因而对“虚妄”特征明显、多言男女情事的唐传奇摒弃不载,而且在其他书的“提要”中也时时流露出对唐传奇的鄙夷:“连篇累牍,殆如传奇”自是贬斥,“又唐人小说之末流”(存目《昨梦录》“提要”),则谓之末流中的末流也。同时,《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中,今人认为最具文学性的“记录异闻”派(即今人所谓的“志怪”),同样不符合其收录标准,这类书之所以得以保留,多数是因为它们是“前朝旧书”,“诸家多所援引”之故。可见,《四库全书总目》保留这类书,仅仅因为它们是一批“老古董”,食之虽无味,弃之却可惜,而绝非是从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出发,来认可它们的价值的(当然四库馆臣也根本不会具备文学性的“小说”概念)。
总而言之,自《汉志》伊始的视其他部类为“正说”、“大道”,而视“小说”为“琐说”、“小道”的观念,到了《四库全书总目》也并无什么改变,“小说家”仍然是收容其他部类(以史部居多)的“不入流之作”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的“垃圾桶”。
讨论到这里,古典目录学“小说”概念的非文体性质已经基本可以明了。我们虽然未能对所有的古典目录学著作加以讨论,但基本上囊括了有代表性的、影响比较大的著作。其他未能提及的古典目录学著作,在“小说家”的载录上大体也无出其外。
(五)
从《汉志》、《隋志》的“杂烩”性质,到《新唐志》的偏重于“野史”性质,再到《四库全书总目》中“史余”性质的更加突出,这是我们可以大体看出的古典目录学“小说”概念的发展轨迹。但自始至终,“小说”这个概念都没有摆脱其诞生之初即带有的鄙夷色彩——琐屑、浅薄,也没有摆脱与“正说”、“正道”判然殊途的卑微地位。正是这种先天的负面规定性,阻碍了它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正面的质的规定性的文体概念,而只能被动地指称一切“非正说”、“非正道”的东西。正是从这种“小说”概念出发,古典目录学中的“小说家”,只能命定地成为一个收容其他部类的“不入流之作”和无类可归的“驳杂之作”的“垃圾桶”。这个“垃圾桶”内的东西或许会与时为变,但其作为“垃圾桶”的性质却不可能改变。这也正是我们永远无法说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到底指什么,“小说家”究竟是怎样一个派别的原因。以这种面貌存在的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无法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其间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且,以这种面貌存在的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不仅无法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实际上也难以发展成为任何一个具有“是什么”的正面的质的规定性的概念。
当然,我们说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未曾发展成为文学性的“小说”概念,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小说家”中的某些作品确实含有文学性因素。只是这同样无助于证明古典目录学的“小说”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是同一个概念,犹如我们也在史传著作中发现了“小说”因素,但不能把史传著作等同于“小说”一样。
同样,我们指明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未曾发展成为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也不是说我们认为从《汉志》到《四库全书总目》的漫长时期里,“小说”这个概念始终与文学无涉。其实,接近今天文学性“小说”概念的“小说”一词,在古典目录学以外的论述中,比如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却时可一见。如宋人洪迈认为:“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38)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酉缀遗》曰:“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39)明人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云:“唐人于小说,擒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40)这些论述中所说的唐人“小说”,都指唐传奇,其评论所称道的,正是为古典目录学所不齿的唐传奇“离于史而近于文”、志人叙事曲达人情的特点。
此外,在俗文学方面,“小说”这个词也有渐趋文学性的倾向。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小说讲经史》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41)元人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曰:“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42)这些论述中的“小说”,都指“说话”之一种,其所着眼的这种艺术形式所具有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题材为人喜闻乐道等特点,正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相近。
以上这些论述中的“小说”概念,已接近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当然,在其自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琐说”、“小道”,从而刻意与诗文等主流文体保持距离方面,其实也仍然没有彻底摆脱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羁绊,而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仍有一定距离。
虽然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在俗文学方面,“小说”一词较为接近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但这并没有对古典目录学产生什么影响。正如那些具有一定文学性的“小说”作品,无法获得古典目录学的青睐一样。这两个在不同领域里出现的“小说”概念,实际上其内涵已经相当不同,从而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性质(43)。而传统的文学批评和俗文学中所出现的这个“小说”,才是我们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的远源。
今人论古代的“小说”,其实都是想从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出发,赋予其所讨论的材料以文学意义,但却往往以古典目录学“小说家”的载录为指归,这就难免扞格难通了。现有的几部“文言小说”书目类著作,有的虽然未能明辨自己文学性“小说”概念的出发点和以古典目录学“小说家”的载录为指归确定研究范围之间有什么牵强和不妥,但在收录标准上尚能坚守一格,专收古典目录学“小说家”所载作品(44);而有的则强为弥合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和今天文学性的“小说”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曲为之说,则不仅存在前一类“文言小说”书目类著作所具有的牵强和不妥,而且在收录标准上也显得首鼠两端,不名一格(45)。这种突出地存在于“文言小说”书目类著作中的问题,在“文言小说”的研究论著中也或多或少存在,而这都是由于混同和杂糅古典目录学的“小说”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两个概念所导致的。
认清古典目录学“小说家”的“垃圾桶”性质,将之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明确区分,有助于我们摆脱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的掣肘,从而更好地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出发,来判断我们所面对的材料究竟是不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小说”。名正方可言顺,我们认为,对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和今天文学性的“小说”概念的区分和正名,对于古代小说、尤其是“文言小说”的研究来说,可谓是一项正本清源的工作,对推动其顺利开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今天所谓文学性的“小说”一词,可以说是近代从日本输入的“新名词”。日人以中国传统的“小说”一词,来译从西方传入的“虚构的叙事文学”(story,novel,fiction……),于是就有了今天文学性的“小说”一词,与中国传统的“小说”一词名同而实异。中国传统的“小说”一词,其实本身就包含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内容,既指古典目录学的“小说家”,也指唐传奇、话本小说等文学作品。今天所谓文学性的“小说”一词,其内涵与后者比较接近,而与前者完全不同。不了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或不明白两者间的重要区别,自然就会造成概念的混乱。在本文中,我们称传统的“小说”概念为“古典目录学的小说”,称今天的“小说”概念为“文学性的小说”。
②其实,觉察到古典目录学的“小说”与今天文学性的“小说”之间差异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但由于这两个概念外延上的交叉,往往引导着讨论这个问题的论著从起始的别异倒向结论的求同,从而最终未能得出它们其实是两个不同概念的结论。如石昌渝《“小说”界说》(《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提出:“自明代小说崛起与诗文抗衡以来,对于‘小说’就有双重的定义——传统目录学的定义和小说家的定义……要弄清‘小说’概念,最重要的是与传统目录学的观念划清界限。”这个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可惜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由于作者未能从对古典目录学著作的详细考察来立论,对古典目录学“小说”概念的实质未能认清,因而未能达到作者所预期的彻底界说古典目录学“小说”和小说家的“小说”(按:石文所说的“小说家的‘小说’”是从文学意义上着眼的,大约相当于本文所说的“文学性的‘小说’”)差异的目的。又如张哲俊《东亚比较文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认为中国古代的“小说”概念并非一个文类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概念(见该书第七章第二节);高小康《中国古代叙事观念与意识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把从班固到《四库全书总目》所谓的“小说”称为“古义小说”,认为其“唯一靠得住的共同含义就是一个‘小’字,即不正统、不系统、不可靠、没有重大价值和功用”(见该书第一编第一节)。但张著在行文中其实仍然混杂使用两个“小说”概念,并没有彻底摆脱概念不清的嫌疑;高著虽然认识到了“古义小说”的实质,但尚未从古典目录学的发展过程着眼,来对这个问题加以更为细致的考察。基于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③《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拟李都尉从军》诗“袖中有短书”句唐李善注引。关于刘歆、桓谭、班固使用“小说家”一词的关系,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有一段颇为近理的论述:“谭与刘歆同时,其书盛称子政父子,谓为通人,是必曾见《七略》,而班固尝受诏续其《琴道》一篇,固熟读《新论》者,故桓子之言,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1页。
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宋子》一卷,共六条,俱从《庄子·天下篇》辑出。但《庄子·天下篇》仅叙述宋子言行事迹,难以证明其必然出于《宋子》。此外,《荀子》、《孟子》中也谈及宋子言行,但也难以推断其是否出于《宋子》。
⑤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胎教”条(辑自《大戴礼记·保傅篇》、贾谊《新书·胎教杂事》,两书文字互有异同,马氏用以互校)和“巾车教”条(辑自《大戴礼记·保傅篇》,以贾谊《新书·胎教杂事》校之),丁晏《佚礼扶微》卷二也辑有两条,其中“胎教”条与马氏重复,另有“鸡祀”条(辑自《风俗通义·祀典》)。
⑥章学诚《校雠通义·汉志诸子》谓其书“不当侪于小说”,见《文史通义校注》下册,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49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亦曰:“亦不知当时何以入小说。”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8页。
⑦最早猜测《吕氏春秋·本味篇》与《伊尹说》有关的是宋人王应麟,其《汉艺文志考证》在“《伊尹说》二十七篇”下提到了“《吕氏春秋》伊尹说汤以至味”。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19页。翟灏《四书考异》考《孟子·万章上》的“伊尹以割烹要汤”条,根据《史记》应劭注(实为《史记索隐》引应劭《汉书音义》之言,应劭未尝注史记,翟氏说误,余嘉锡已辨其非,说见《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许慎《说文》中相关引文不云出自《吕览》而曰出自《伊尹书》,更推论汉人犹得见其书,“故犹标著其原目”。余嘉锡、袁行霈都赞同此说,分别见于《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文史》第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伊尹“以至味说汤”之事,尚见于多种典籍,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推论其次第曰:“伊尹为庖以干汤之事,《墨子·尚贤上篇》、《孟子·万章篇》、《庄子·庚桑楚篇》、《文子·自然篇》、《楚辞·惜往日》,以及《鲁连子》(《文选》卷四十七《圣主得贤臣颂》注引)皆载之,不知与《伊尹说》孰先孰后。惟《吕览》之为采自《伊尹说》,固灼然无疑。他若《韩非子·难言篇》、《史记·殷本纪》之出《吕览》后者,又不待论也。”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2页。
⑧黄帝、汤、务成子、鬻熊、师旷等人,或作为传说人物或作为历史人物,其事迹言行散见于多种先秦秦汉典籍,袁行霈《<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对此网罗颇力,可参看。但该文在推论这些记载是否都出于《汉志》“小说家”所著录之书方面似有疏误,恐难以为据。如他认为“《荀子·大略》、《新书·修政语上》、《史记·殷本纪》都载有成汤的话,其中有些不见于《尚书》,似应出自小说书《天乙》”,从不见于《尚书》并不能直接推断出它们必定出自《天乙》。并且,《汉志》自注已指明,《天乙》“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那么《天乙》与上述诸书,尤其是与《荀子》成书的先后,尚值得商榷,更不宜遽然判定诸书皆引自《天乙》。其实,首倡该说的王应麟已遭余嘉锡批驳,说见余氏《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再如《师旷》六篇下班固自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指出,《师旷》“在小说家者不可考,唯据本志注,知其多本《春秋》而已”。袁氏似乎对班固自注和鲁迅推论俱未加详审,更拈出《左传》襄公十四年、十八年和昭公八年所载师旷事“是出自小说家《师旷》还是出自阴阳家《师旷》”为一问题而加以辩解。(按:师旷事不见于《春秋》经文,则班固、鲁迅所言《春秋》自应指《左传》,其所载师旷事,除袁行霈所言襄公十四年、十八年和昭公八年外,尚见于襄公二十六年、三十年。)如此种种,实为百密之疏也。
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钞本《说苑》。《百家》佚文两条,分别见于《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和《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所引《风俗通义》佚文中。
⑩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6-277页。
(11)《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曰:“非惟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持此秘术,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
(12)(13)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639页。
(14)(15)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78页,第270页。
(16)《杂语》,《隋志》不题撰人,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推为侯白撰,不确。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535页。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云:“《世说》各篇注引孙盛《杂语》,疑即盛撰。”近是。见《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3939页。孙盛《杂语》佚文除见于《世说》注,尚见于《三国志》裴注、《太平御览》、《艺文类聚》诸书,各书所引,去其重复,共存六条,皆记魏晋间名人逸事。见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40页。
(17)《郭子》、《笑林》、殷芸《小说》、《水饰》等四种,鲁迅《古小说钩沉》并有辑本。殷芸《小说》辑本,尚有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及周楞伽《殷芸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周书据鲁、余所辑又有增补,共得一百六十三条,最为完善。《水饰》尚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18)刘知几《史通·杂述》将《琐语》归为小说中之记逸事者,云:“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顾协《琐语》、谢绰《拾遗》,此之谓逸事者也。”由此可知,《琐语》与《西京杂记》等书性质相近,因而下文将之归入轶事类。
(1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古之秘书珍图,有《古今艺术图》五十卷,既画其形,又说其事,隋炀帝造。”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因之推论此处小说书《古今艺术》盖系《古今艺术图》之“但说其事,而无其图者”。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538页。
(20)《器准图》可能是有关“浑天地动欹器漏刻”的图画及说明文字。见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37页。
(21)《水饰》可能是杜宝所作《水饰图经》七十二幅图的说明文字。见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页。
(22)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537页。
(23)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
(24)以上所列六类作品之入“小说家”,实不始自《新唐志》,而始自成书于其前十余年的《崇文总目》。《崇文总目》“小说家”收书一百四十九部,已经基本囊括了以上所列各类“小说”书。欧阳修《文忠公集》有《崇文总目叙释》一卷,可知《崇文总目》部类之分别,欧阳修实主其事;而《新唐书》的纪、志、书、表,也都是在欧阳修的主持下完成的(见《宋史·欧阳修传》)。所以,《崇文总目》和《新唐志》实皆出于欧阳修之手,两者应具有一贯性。不过,《崇文总目》虽在《新唐志》之前,但考虑到今存之《崇文总目》已非全帙,且今人在论“小说”观念的发展时,多据《新唐志》以证成其说,故我们也姑舍《崇文总目》而据《新唐志》立论。
(25)《新唐志》无“小叙”,而《崇文总目》各类前皆有“小叙”,其“小说家类”的“小叙”云:“《书》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又曰:‘询于刍荛。’是小说之不可废也。古者惧下情之壅于上闻,故每岁孟春以木铎徇于路,采其风谣而观之,至于俚言巷语亦足取也,今特列而存之。”《新唐志》“小说家”罗列各书基本蹈袭《崇文总目》,其“小说”观也难免一仍《崇文总目》之旧,故而《崇文总目》“小说家类”的“小叙”,或可用以说明《新唐志》之“小说”观;而从中可以看出,其“小说”观其实依然袭蹈《汉志》、《隋志》之旧轨,而并没有赋予这个概念以任何新意。
(26)陈寅恪先生《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尝有言:“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页。
(27)按“九”当作“五”。郑樵《通志·校雠略》曰:“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又如文史与诗话亦能相滥。”
(28)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282-283页。
(2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页。
(30)(31)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183页,第1201页。
(32)(33)(34)(35)(36)纪昀:《四库全书总目》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05、1230、1230、1233、1235页。
(37)《四库全书总目》把“小说家”当作“垃圾桶”的倾向,已经有研究者指出。如季野《开明的迂腐与困惑的固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的现代观照》(《小说评论》1997年第4期)提到:“小说仿佛成了收容所,不合史书体例的诸作贬到这里,只能使小说的概念更含混,使其内容更庞杂。”苗怀明《文臣之法,学者之眼,才子之心——纪昀小说观新探》(《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重申其意:“小说一类仿佛成了一座内容庞杂的收容所,凡不合史书体例的著述纷纷被‘退置’到这里。”但他们都未能从整个古典目录学的宏观背景来解释这种现象,因而未能认识到把“小说家”当作“收容所”实际上是整个古典目录学一以贯之的传统,而初不始于《四库全书总目》。
(38)今本《容斋随笔》不见此言,此言见于清人陈世熙《唐人说荟》“例言”所引“洪容斋”语,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1922年,第1页。
(39)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2001年,第371页。
(40)桃源居士:《唐人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页。
(41)吴自牧:《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6页。
(42)罗烨:《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3页。
(43)对于这种分化,前人已经有所觉察。比如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历朝小说》云:“小说至今日,滥觞极矣,几与《六经》史函相埒,但鄙秽不堪寓目者居多。盖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2-83页)刘廷玑把“小说”的发展分为“历朝小说”、“四大奇书”、“近日之小说”(如《平山冷燕》等)。“历朝小说”指“自汉魏晋唐宋元明以来”,“可以索幽隐,考正误”的“小说”,这类小说略近于本文所说的古典目录学的“小说”概念;而“四大奇书”与“近日之小说”则近于本文所说的文学性的“小说”概念。刘廷玑虽然没有认识到“古”与“今”两种“小说”其实各有渊源,而并非前后相因的关系,但他敏感地意识到两种“小说”的名同实异,实是过人之见。
(44)如袁行霈、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45)如程毅中:《古小说简目》,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宁稼雨:《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