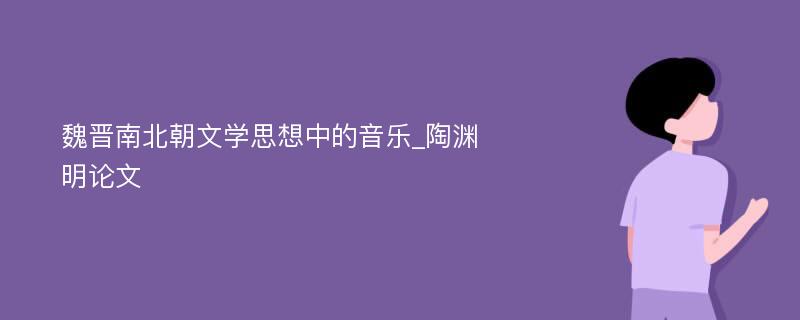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中的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悲”、“乐”互斥互补观点出发,探讨了有着明显悲剧气氛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中的“乐”特征及形成过程。文章认为,惶惑与苦难灵魂的艰辛跋涉,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悲凉苍穹的罅隙中,也露出“乐”的曙光——去苦求乐,而这表现在“纵欲为欢”的外向性乐与回归田园山水的内向性乐两个方面。
说起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或诗学精神,谁都知道它们充溢着一股浓厚的悲剧气氛,这里怎么谈起它们的“乐”来了呢?诚然,悲剧色彩、忧患意识与“乐”在语义上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在关切生命底蕴的文学中,这种对立情形非常复杂。中国传统诗学精神,一方面讲厚人伦、美教化、个体需要与社会伦理的同一,这当然会让人产生忧患意识和悲剧意识;另一方面,它又十分重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愉悦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超逾一切世俗烦恼的快乐满足。事实上,无论诗人们强调哪一面,自逸其乐、自娱其欲与悲剧意识、忧患意识的主体心态在中国诗学精神中都是存在的。虽然它们确实存在着明显的逆反,但出人意料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一矛盾刚好构成了它们相辅相成的要素。“乐”既是释放忧心能量、淡化悲剧气氛的手段,又是主体心态的终极性意向。一旦忧国忧民受到挫折、悲剧心情过于沉重,“乐”就是一帖绝好的精神安慰剂、最后的护身符。下面,我们将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中“乐”的特征和形成过程作一剖析。
一 惶惑与苦难灵魂的艰辛跋涉 汉末战乱,军阀群起。就在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的现实中,人的精神产生了危机,它突出地表现为对儒家传统信念的怀疑、对人生困境的晓悟以及生与死的意识的觉醒。哲学上生死、有无命题的提出,表明了人们对孔圣“不知生、焉知死”和“实有”思想的困惑。
时代的沉重、苦难的煎熬,注定要让敏感的诗人最早也最深刻地感受到,荒谬、残酷的生存空间和异彩纷呈的哲学思想,给汉魏之际的诗学精神涂上了浓厚的悲剧底色。汉末古诗中“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的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建安年间,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1〕的悲壮;曹植“引领情内伤”、 “感物伤我怀”〔2〕的多愁善感。 这些形成了一种“悲”的时代交响曲。后来的文论家如刘勰、钟嵘都看到了这种文学现象。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中说,魏之三祖“辞不离于哀思”。在这篇文论巨制中他还精辟论述了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形成原因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3〕,突出强调了诗人在苦闷时代中产生的悲剧意识。 钟嵘在《诗品序》中列举“感荡心灵”的事例,悲悲切切,绝大多数都是“托诗以怨”的情感,“骨横朔野”、“魂逐飞蓬”、“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反映出他对前辈诗人及诗歌作品中悲剧色彩的强烈感受和认同。
进入晋代,浓厚的悲剧尘埃仍然没有散去,诗人的精神世界又出现了空前的虚无和惶惑。思想家和诗人们怀疑、抨击自己曾奉为圭臬的儒家传统教义,“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4〕, 渴望在诗中重新确立一种新的价值信念,填补因弃置儒家圣典而带来的思想空虚。阮籍不无悲怆地吟唱道:“容色改平常,精神自漂沦”〔5〕。 “弧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6〕。 自认前途渺茫,又急于找寻、苦苦求索的孤独感弥漫于诗中。嵇康也惶惶于“良朋”的选择途中:“驾言出游,日夕忘归,思我良朋,如渴如饥,愿言不获,怆矣其悲”〔7〕。弱肉强食的人间混乱, “一身不自保”的文人个体生命的无常,令人惊恐的价值荒谬以及骇人可怕的信念虚妄,使诗人们堕入了黑暗的精神深渊。无名的苦痛、悲哀、焦灼及不安向诗人们不断袭来。它们逼着诗人们注意生命的终极价值:“时路乌足争,太极可翱翔”〔8〕。似乎诗人要离开这个混浊的人世, 去别处实现自己的理想。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并没有去“翱翔太极”,甚至也没有虔诚于老庄的虚无和纯自然状态,而是企盼着明辨自己的灵性,找回生命的本质,寻觅情感的归宿。苦难的灵魂经过一番痛苦的追求后,终于找到了“乐”的终极保障。阮籍“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认为“谁言万事难,逍遥可终生”〔9〕;嵇康也“盘于游畋,其乐只且”〔10〕; 谢灵运说得更明白:“幸赊道念戚,且取长歌欢”〔11〕。诗人们超越那垂涎于物欲的贪婪目光而转向热爱自然、皈依自然;超越那悲戚的情感意向而转向纵情求乐。在那“乐”的十字路口,一边是适己任情的丽人美酒、长生药术,一边是真意盎然的松菊田园、嶙峋山石。何去何从?就看诗人们如何抉择了。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这种“乐”的终极价值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诗人要求从纷乱的尘世返回到个体生命的本然基础是一个由悲到乐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怎样产生的?这个过程产生的根基乃是由于自先圣儒学就深入阐明过的一种生命本源自盈无缺的心理意向,即人自身的“生生大德”。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在于“学生”——“生生之谓道”,天道本身就是生命之道。身处陋巷、隐逸林泉、醉酒纵欲,虽然其表面上都是背弃社会固有的秩序,但作为理性智识它们又分明是人生去苦求乐的逻辑推阐。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2〕。谢灵运也说:“居德斯颐,积善嬉谑。……鄙哉愚人,戚戚怀瘼;善哉达士,滔滔处乐”〔13〕。在他们“反身而诚”及“居德积善”的静修中,个体心态感到完满无缺,与天地万物相通。它不但内在地规定了自足自备、无待于外的主体心态,而且内在地规定了生命体自盈自足的“处乐”意向。因此,即使在满纸衰辞的建安诗人那里也透过感叹的云雨,在悲凉苍穹的罅隙中,露出一些“乐”的“曙光”。曹操的诗歌在悲怆中隐含着昂扬乐观的基调;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云:“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他的《箜篌引》,孙月峰评曰:“言欢宴之乐,出于久安之义,当及时建立,无徒以忧生为也。”〔14〕都表明曹植有一种超然的潇洒和含泪的乐感。这种乐是盎然充盛的生命流行之乐。这种乐到了阮籍、嵇康、陶渊明这里就更明显、更丰富深刻了。下面我们将分别加以论析。
二 “纵欲为欢”的外向性乐 前面已述,魏晋南北朝诗人身不由己地被黑暗和动乱的时代抛入虚无的深渊,在苦涩艰难的灵魂漂泊中,他们找到了“乐”的价值信念。那么,他们的“乐”有什么特征呢?
“乐”在心理学上讲是一种主体愉悦的情感,在哲学上说则是一种人生体验、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在获得快乐感受的途径上,分外向和内向两种。外向性乐是指主体快乐感受的获得绝对地依赖于外部事物的存在,在心理上主要通过摄取外在于人心的种种要素来求得自身的悦欣满足。这种快乐感受是一种补偿性的乐,也就是《列子·杨朱》中所说的“善乐生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的“逸乐”,乐而不贫,乐而不苦,它与安贫乐道、乐箪瓢的“乐”是不一样的。六朝文人主要通过任情纵欲、服药饮酒来实现这种乐。
《列子·杨朱》说:“恣耳之所欲听,恣目之所欲视,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体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在这段文字中,它鲜明地提出了一种纵欲观,洋溢着追逐声色快感的激情,它还认为“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这就是“乐”。这种乐并不追求生命长度的延续,而是指生命密度的加强,那就是“猗靡相携持,悦怿犹今辰”〔15〕的一时之乐。它在本体论上否定了“养怡之福,可得永年”的价值观。嵇康虽然不同意这种观念,却也认为“人性以从欲为欢”〔16〕,为六朝文人放恣情欲的生活态度寻求到了哲学的合理性。于是,这种乐一方面表现为原始自然层次上的情欲冲动,另一方面是绝对超脱的意志自足。阮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中!”〔17〕他们把原始的、与动物不相区分的自我放恣和主体意志上与天地合一的自我超脱合为一体了。放恣情欲的乐还特别醒目地集中在对女色的依恋上,而且这种迷恋毫不掩饰地流露为性感的刺激性欢乐。阮籍曾有“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18〕的“好色之举”,并且,他还不无自乐地在诗中吟唱道:“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19〕,津津回味起自己的冶游之乐;在诗论上主张“诗缘情而绮靡”的陆机似乎要为他的绮靡之情做一注脚,他在《为顾彦先赠妇》诗中说:“愿保金石躯,慰妾长饥渴。”正说明他所云“情”的内涵之一便是性爱的愉悦。这种乐是放恣式的超脱之乐,或叫超脱式的放恣。他们试图用非理性行为来实现理性的超脱,以此补偿价值的虚无;在意识麻醉中重新寻求救治诗人精神痼疾的希望,找到弥补传统信念弃置之后的信念空缺。这种乐能帮助诗人达到超越世事纷争的目的吗?
服药饮酒是六朝诗人寻求“乐”的另一种手段。在传统道德价值系统解体、善恶无凭的价值虚无和人生苦难、性命无常的生存虚无的双重夹击中,他们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20〕的人生之乐。这“自然”一方面指“绝圣弃知”而返归原始状态;一方面则指“生生”的自然之道,也就是要任性所为。唯其如此,他们饮酒“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21〕。在这看似荒唐怪诞的回归原始生活的“嬉娱”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人世正常生活的逆反心理。服药以求养生怡乐,延年益寿,是不少六朝诗人的时尚,也是他们的一种乐。嵇康在《重作四言诗》中希望神仙:“授我神药,自生羽翼,呼吸太和,练形易色。”这种乐是他“生生”的保障,在徜徉于云石之间、沉醉于炼药之中、任性而随意里显现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如果仅仅把六朝诗人的任情恣欲之乐看作是追求肉体感官的快乐,那就太小看他们了。肉体感官的快乐不能导致永恒的福乐。从情感形式上看,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外向性乐;但从意志趋向上来看,他们竭力找寻的是外向性乐与超脱傲世精神的统一。他们企图用情感的外显和恣狂来实现精神超脱,从而把自己的灵魂从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然而,想放纵情欲与意志超脱双得,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正因为不可能,所以他们的这种乐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在他们的“恣情”之乐中,首先显露出的是双重的二律背反即悲与乐的统一。阮籍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22〕和嵇康诗“旨酒盈尊,莫与交欢,琴瑟在御,谁与鼓弹”〔23〕都透露了这种消息。游览本是乐事、有酒也可交欢,但前途渺茫、知音难觅,灵魂何处皈依呢?在乐中含悲。虽然如此,悲与乐还是统一的、循环的,并且,乐永远是他们的终极价值保障物。这样,才能使中国诗人狂而不疯、痛苦而不寻短见。
“乐”作为“六艺”之一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它最初是和“乐教”相联系的:“乐者,通伦理者也”〔24〕,“乐取于人以为善。”〔25〕其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中人与人的和谐一致,也就是《礼记》中所说的“乐者为同”、“乐者,天地之和也”,它既指音乐,又是人和自然界合一的情感体验。然而,在我们前面对阮、嵇等人的“乐”的分析中,我们看出,他们的乐已超出了一般的音乐和伦理意义范围,而是作为一种“生生”的观念形态和审美意识。它主要是指主体在同客体的审美关系中所达到的人生体验,以及由这种体验所产生出来的自盈自足感。这种乐,不脱离客体存在而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在六朝诗人那里,“诗”正是表现这种情感体验、达到“乐”的审美境界的重要媒体。因此,钟嵘认为诗人有“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作用,他称赞阮籍的《咏怀》能够“陶性灵,发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26〕。这就是说诗能使创作主体达到一种美学式的精神境界,能去忧存乐,乐而忘忧,到达超越的由悲而乐的“远大”处,从而实现那出于情感而又超情感、达于理性而又超理性的本体情怀。但阮、嵇这种乐仍是直观的、依赖外部条件的外向性乐,直至到了陶渊明、谢灵运那里才真正具有了一种超客体的、与自然界融化的内向性乐。
三 回归田园山水的内向性乐 西晋以后,所谓的“任达”、纵欲之乐普遍盛行,乃至到了“相与散发倮身之饮,对弄婢妾”〔27〕的荒唐地步。在这种风气下,比较清醒的嵇康早就提出:“乐之为礼,以心为主”〔28〕,虽然他主要说的是音乐上的“乐”,但与我们下面所说的“心乐”并不是没有关系;乐广更具体地提出了“纠偏良方”〔29〕:“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乃尔?”〔30〕
那么,所谓的名教中的“乐”是什么?这种乐就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仲尼之乐;就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31〕的颜子之乐。这种乐既是主体所达到的一种美学式的道德精神境界,同时又有超功利的一面。在这种乐中,快乐的感受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依赖于外部事物的存在,它不注重肉体的官能享受,在绝对意义上依赖的是主体自身的道德情感和意志本能,是自足性的“心乐”。这种乐在主要表现出外向性乐的诗人及文论家那儿也不是没有。陆机在《招隐诗》中就说:“至乐非有假,安事浇淳朴。”《庄子》中有《至乐》篇,说欲求至乐,惟无为近,陆机诗是说乐的获得靠清静安贫,而不必靠富贵的外物;阮籍的《咏怀诗》说:“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也指的是精神的满足感;嵇康曾“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32〕,“意”的会心,就是乐的到来,故而使人流连忘返。但这种内向性乐以晋宋时代的陶渊明、谢灵运最为典型。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先有做政治家的愿望,然后才有做诗人的余情。陶渊明青少年时代虽然曾经想到要“击壤以自欢”〔33〕,做一名布衣书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34〕但他萦萦在怀的仍然是“大济于苍生”的理想。因此,他青少年时曾仗剑出游:“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35〕谢灵运更是有“独登要路津”的志向:“兼抱济物性,而不缨氛垢”、“万邦咸震慑,横流赖君子”〔36〕,大有拯救生民于水火的救世主气概。但他们的这些理想在那营营纷乱的时代和艰难污浊的仕途上被击得粉碎,使他们对自己的价值信念和为实现这一信念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深感失望。陶渊明事后醒悟道:“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37〕;谢灵运也大彻大悟:“久露干禄清,始果远游诺。宿心渐申写,万事俱零落。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38〕。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陶诗中所说“乐”、谢诗中所说“远游”是一种拒斥了价值关怀后,把自己融化在自然界,超然于人世外所达到的超功利的美学境界。他们认为这是深层的乐,而“欣豫”、“万事”则是一种直觉的、感觉上的情感体验和年轻气盛时的价值意向,陶、谢认为这种心怀“猛志”和“干禄”的“欣豫”是“无乐”,只有归耕田园,任情山水中才是真正的“乐”。故陶渊明说:“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39〕谢灵运也同样认为:“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披拂趋南径,愉悦偃东扉。”〔40〕诗人在绿林清荫、风月花草里,在大自然的生生和谐中,主体审美体验达到了“乐”的境界。因而这种乐具有超功利的特点。它融理性与情感为一体,以主观体验为主要特征,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合而为一,进入了物我一体、内外无别的精神状态。这种乐超出了追求感官享受之乐的局限,深入到了美的本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感到有一种最大的精神愉快。很显然,这是一种内向性乐,与上述那种依凭于“欲”的发泄和“情”的放纵的“乐”是有很大区别的。
现在我们要探究的是,他们那种济苍生的热衷肠怎么变成了怀抱山水田园的“凉”心之乐?是什么促成了这种价值意向的转换?
在陶、谢这里,要达到这种乐的境界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回归到自然形态本身去:“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41〕,“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42〕;谢灵运也说:“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羁雌恋旧侣,迷鸟怀故林。”这里的山林是自然形态的代表物。二是要确立人的本性:“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43〕、“守道顺性,乐兹丘园”〔44〕。只有这两个意向对象合在一起,才可称为“返自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乐。正因为这样,当陶渊明“乃瞻衡宇”,看到了自己“性本”的归宿时,竟“载欣载奔”,象小孩回到母亲怀抱似地“乐”起来,逍遥出世,与道俱成,当其得“意”,其乐融融。这种意又是什么?它怎么能使诗人真正完成了由热心肠到“凉”心肠的转变过程?陶渊明的《饮酒》(其五)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的《登江中孤屿》诗也说:“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他们所说的“真”或“真意”是感性个体通达“道”的路径,是个体的有限性进入超个体的无限性的桥梁。陶、谢要超逾尘世,就得超逾一切假的信念形态包括一般的俗世的“意”,而只有超逾了这种俗“意”,才能在拈菊花微笑、看空水澄鲜中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而逍遥悠悠了,这时的田园山水都成了诗人们“心乐”的化身了,“热”心也就在幽静的山水中变成了“凉”心。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他们对这种由“热”到“凉”的情怀转变能心安理得吗?其实陶、谢的“性本爱丘山”、“乐兹丘园”、皈依山水并不是完全真实的,也非其初衷。由于现实的邪恶、残酷、不公平,使得每一个禀有“济苍生”的价值关怀意向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这样的困惑和窘迫之中:“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值欢无复娱,每每多忧虑。”〔45〕“延州协心许,楚老惜兰芳。解剑意何及,抚故徒自伤。”〔46〕“此心”(指“猛志逸四海”之心)渐渐消逝,佩剑也已解除,热情的忧患,忧心的徒劳,价值关怀面临着世界邪恶的种种揶揄和否定,使价值关怀化为毫无价值。然而,他们不但否定了虚妄和错误的价值关怀意向,而且也进一步否定了价值关怀本身,即拒斥一切价值关怀包括济苍生的爱心。在倒脏水的同时,把婴儿也倒出去。这或许是中国文人能进退从容的长处,但它们经得起自己良心的拷问吗?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体都去担当人类的苦难,抗拒世界的黑暗,面对世事的混乱和丑恶,一个人如能不同流合污、逐波随流而独善其身,也算是一种超越,但它作为一种整体文化现象和社会意识,就值得我们追问和深思了。
注释:
〔1〕《短歌行》。
〔2〕《赠白马王彪》。
〔3〕《时序》。
〔4〕〔16〕嵇康《难自然好学论》。
〔5〕〔6〕《咏怀诗》三十四、一。
〔7〕〔10〕〔23〕《见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8〕〔9〕阮籍《咏怀诗》三十五、七、三十六。
〔11〕《长歌行》。
〔12〕《孟子·尽心上》。
〔13〕《善哉行》。
〔14〕《孙月峰先生评文选》。
〔15〕〔19〕《咏怀诗》五十五、二、五。
〔17〕〔21〕《世说新语》。
〔18〕〔22〕《晋书·本传》。
〔20〕嵇康《释私论》。
〔24〕《礼记·乐论》。
〔25〕《孟子·公孙丑上》。
〔26〕《诗品》序、上。
〔27〕《晋书·五行志》。
〔28〕《声无哀乐论》。
〔29〕〔30〕转引自《中国哲学史》第370页,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31〕《论语·雍也》。
〔32〕《晋书·嵇康传》。
〔33〕《感士不遇赋》。
〔34〕〔41〕《饮酒》十六、五。
〔35〕《拟古九首》八。
〔36〕《述祖德》。
〔37〕《杂诗》五。
〔38〕《富春渚》。
〔39〕《和郭主簿》一。
〔40〕《石壁精舍还湖中作》。
〔42〕陶渊明《时运》序。
〔43〕《归园田居》一。
〔44〕谢灵运《答中书》。
〔45〕陶渊明《杂诗》。
〔46〕谢灵运《庐陵王墓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