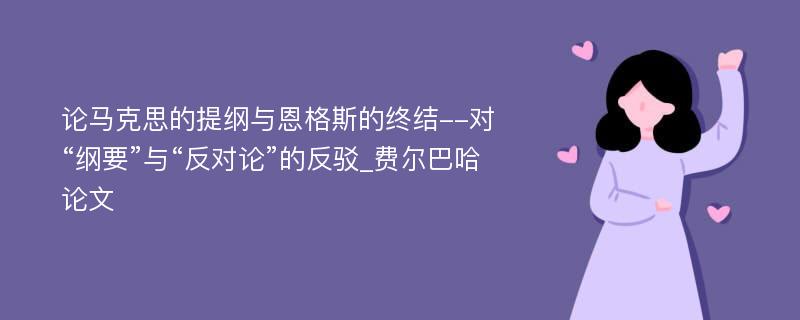
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驳《提纲》与《终结》“对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提纲论文,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07)06-0739-06
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出版单行本写的“序言”中,曾讲明了将马克思1845年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作为《终结》一书的附录公之于世的目的和意义,并称赞《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深刻表明《终结》与《提纲》的思想实质、特别是关于对费尔巴哈的基本观点的分析和批判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现代西方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者却断言,从马克思的《提纲》到恩格斯的《终结》,有一个从能动主义到机械的简单唯物主义的转换。他们说《提纲》是以人为中心的,论述了能动的实践因素在认识中的意义;《终结》是以物质为中心的,论述了哲学基本问题,没有突出实践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意义。国内理论界多数论者是反对西方“对立论”的观点的,对《终结》的历史贡献和理论意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等问题,都作了充分肯定和深刻阐述。但是,近几年,早已被批判了的“对立论”的这种主观论断的错误观点,在国内却又有研究者予以重新宣扬。他们从主观设定的观念出发,对《提纲》和《终结》中的某些论断,进行肆意阐释,并美其名是作“学术性”研究。他们认为,马克思在《提纲》中是“从实践出发”,恩格斯在《终结》中对马克思论断的理解是“从自然界出发”的。他们说:“在《终结》的序言中,虽然恩格斯把《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但我们发现,恩格斯叙述哲学基本问题的出发点仍然与马克思的出发点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他们“认为,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实践出发,还是从自然界出发”;“从本体论维度理解实践,还是从认识论维度理解实践”;“从人的问题着眼,还是从纯粹思想的问题着眼。”[1](第242-256页)这种“学术性”的研究实为罕见,它把二者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话语对象而作的论断,硬是扯在一起作主观的类比,这是对原典的曲解。尽管在他的“阐释”中引证了原典中的原话,但他们不顾马克思和恩格斯创作原典的时代背景、创作原典的直接原因和针对的具体问题,又不从原典原话的逻辑和具体内涵出发作阐释,而是从他们设置的观念逻辑出发,作了错误的阐释。其实,这种所谓“学术性”研究的重新阐释,并不新鲜,也不是什么“新见”。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就有人鲜明地提出来了,认为《终结》有其历史局限性和理论上的缺陷,“它的主要局限性表现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对哲学体系的表述上,它没有突出实践的内容,对主体的作用也有所忽视”[2](第5页)。我们认为,这些见解是偏颇的,是不符合恩格斯撰写《终结》原意的,是对《终结》的“好读”而未甚解的表现。不过,这也确实向我们提出了如何研读原著文本的问题,特别是如何深刻而正确地理解恩格斯将《提纲》作为《终结》的附录公之于世的目的和意义。为此,我们认为,首先,必须认真地研读恩格斯于1888年为《终结》写的“序言”。其次,在正确地理解“序言”的基础上,对《终结》和《提纲》从精神实质上进行历史的和逻辑的比较研究;然后才可能全面地正确理解和把握恩格斯在出版《终结》时,将马克思的《提纲》作《终结》的附录公之于世的重要意义。
首先,我们应该研读恩格斯于1888年为《终结》写的“序言”,其中有三点是值得着重理解的。第一,恩格斯引证马克思的话说,1845年马克思和他“在布鲁塞尔着手‘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3](第211页)。这里是说,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真正的历史原因之一,用恩格斯后来回顾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话说,他和马克思“两人已经深入到政治运动中;我们已经在知识分子中间,特别在德国西部的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一些人的拥护,并且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了广泛联系。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我们明确了这一点以后,就立即着手工作了。”[3](第197页)这里充分表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观点上是一致的,在理论见解上是相同的,而且《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章的主要内容,不仅是依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理论原则和基本观点进行了阐述,而且是对《提纲》的某些论点作了引申和补充。第二,恩格斯在“序言”中说:“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而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一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无论哪个地方都不全面系统的。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好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3](第211-212页)这里表明,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和评判,尽管不全面系统,但还是进行过分析和评判,而对费尔巴哈却从来没有做过像对黑格尔哲学那样的分析和评判;加之《新时代》杂志要求恩格斯针对施达克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错误观点,写一篇全面系统评析费尔巴哈哲学的论述,恩格斯认为是很有必要性的。为此,恩格斯不仅写了全面评析费尔巴哈哲学的系统文章,并于1888年辑为《终结》一书,而且还把马克思40年前拟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终结》的附录公之于世,以表明他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和评判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把《终结》和《提纲》对立起来,不仅违背和扭曲了恩格斯的初衷,而且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的,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错误倾向。第三,恩格斯说:“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之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指《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者注)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所以,旧稿对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3](第211-212页)这说明《终结》和《提纲》对批判施达克的错误观点和全面系统评析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目的,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把二者对立起来是没有依据的主观臆断,是不会得到认同的。
因此,我们认为,《终结》与《提纲》不仅在理论原则、基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上也是完全一致的。这里也说明:真正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文本,不是从中摘取片言只语或借口某些范畴是否突显,就主观武断地大做文章,最后得出违背文本的错误结论,误导了读者。自觉不自觉地淡化或贬低了马克思著作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地位。为此,要树立起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态度,要像列宁要求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4](第785页)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破除洋教条主义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式为“中介”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不良倾向;才能真正做到挖掘和高扬原著本身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以引导干部和群众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著,运用其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指导新的实践。
我们说,恩格斯的《终结》和马克思的《提纲》的理论原则、基本观点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虽然是一致的和相同的,但是在形式上和某些具体内容的阐述上或对某些论点的强调上,还是有相异之点的。事实上,恩格斯公开发表马克思的《提纲》,在其评论中已做了说明。恩格斯说:“这是匆匆写成的供以后研究用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3](第212-213页)这里,就深刻地启示着我们如何科学地理解《提纲》和《终结》的差别:
首先,《提纲》和《终结》是不同时代的作品。前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创时期,为建立哲学理论体系而制定的要领,是供进一步研究用的,没有打算公开发表;后者,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创立之后,经过40余年的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检验,以及经过了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战,“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3](第212页)它已经成功地把欧洲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使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团结起来。为全面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而写的专著,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他们是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又怎样同它脱离的以及他们的哲学观同黑格尔哲学观的本质区别等问题所作的一个简要而系统的阐述。简言之,《终结》是恩格斯在总结、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40年历程的结晶,它是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之大成。
其次,就具体的论述内容看,《提纲》和《终结》所针对分析批判的对象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针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性、抽象性及其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性质,概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历史观、人学观等。后者是通过批评施达克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曲解,针对混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全面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和联系,不仅全面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黑格尔哲学,而且还对作为旧作物主义最后代表的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历史的全面系统的分析批判,指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同18世纪的唯物主义一样,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是唯心主义历史观,但与庸俗唯物主义是根本不相同的,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仅就批判费尔巴哈哲学来说,《提纲》和《终结》在批判的详略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提纲》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人学观、社会历史观、宗教观及其在哲学发展史上革命变革的意义等方面,作了概括的纲领性的论说;《终结》则对上述诸方面的根本观点,不仅作了历史的阐述,而且阐述得更为系统和细致。不仅论述了自然界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异同,还阐述了宗教变迁和社会历史变化的关系;不仅论证经济发展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变化的重要作用,还阐明历史中心人物的思想动机的关键作用。此外,《终结》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为偿还“一笔信誉债”,通过历史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怎样从黑格尔“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的过程”,深刻地批评了施达克的《论费尔巴哈》中关于一般唯物主义和庸俗唯物主义的错误观点。
再次,就《提纲》和《终结》的形式及其历史作用来说,二者是不相同的。前者只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没有打算付印的笔记;它是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拟的一个要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雏形,即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终结》既是为批评施达克《论费尔巴哈》的错误观点,更是为驳斥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挑战。恩格斯之所以提出哲学基本问题,阐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清楚地说明了《终结》的独特作用,即批评了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也批判了不可知论及其新变种——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研究者”批评恩格斯是“从认识论维度理解实践”,是无的放矢,是完全错误的。同时,《终结》也是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各个方面的基本原理的专著;它既简明而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区别、联系,又科学地评价了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影响,及其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此外,对《提纲》和《终结》还可以从其它层面提出一些差别和不同。但是,其本质性的方面,二者是相同的。恩格斯在出版《终结》单行本时,把马克思的《提纲》找出来作为《终结》一书的附录公开发表,就表明二者在一些理论原则、基本观点、根本目的和作用上都是相同的,它们的相同性是其主导方面,它们的差异性是服务于主导方面的次要方面。
我们说,《终结》和《提纲》的相同方面是主导的,主要表现在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上。现将二者相同的主要问题作概括的分析:
第一,关于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分析和批判是一致的。《提纲》开始就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5](第58页)费尔巴哈以其感性直观的唯物主义反对思辨唯心主义是机智的,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认为人的认识不是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形成的,而是在受外界事物的刺激下受动地形成的,并说自我的受动的状态是客体的能动的表现或方面。这种割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的消极反映论,是不能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抗衡到底的。由于这种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不仅导致对实践的错误理解,而且也导致了对人和人的本质理解的抽象性,因而就不能科学地阐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最后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所以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同它的不彻底性是密切关联着的。
恩格斯在《终结》中,通过首次提出和论证哲学基本问题,深刻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他指出:“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3](第227-228页)这种形而上学的非历史的观点,表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唯心主义的。所以说,在恩格斯看来,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是旧唯物主义的三大主要缺点,也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这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科学规定性,不仅使他不能把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到底,而且还把唯物主义同庸俗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他说:“50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并到处兜售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越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3](第229-230页)因此,“而且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作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3](第241-242页)这里充分表明,恩格斯在《终结》中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不仅和马克思在《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批判还有所推进和发展,从而也深刻地揭示了,恩格斯在《终结》中之所以提出和阐明哲学基本问题,是针对特有的具体对象的,是为了历史地、全面地深刻批判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既不存在和马克思“在哲学观的出发点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也未“蕴涵着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拒斥”。持这种论者断言:“恩格斯并没有深入地反思过马克思在《提纲》中叙述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之间存在的本质的差异。”[1](第244-245页)这是不顾不同话语对象和不同问题所指的主观臆断,是对原著思想实质的肆意阐释。
第二,《提纲》和《终结》对人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二者对费尔巴哈关于人和人的本质的纯自然性和抽象性的观点作了深刻批判,并论述了人的社会历史性、实践能动性和自觉自主的意识性,以及这些特性同自然的关系、同社会的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性。所不同的是论述形式和批判角度上有些差别:《提纲》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的过程中,强调了人的能动性、实践性,以及社会关系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性,论述了人的功能本质和社会本质,并着重强调了人的社会本质方面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第60页)而《终结》是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人的功能本质和社会本质。首先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和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阐述,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认识论的角度,深刻论述了人的能动性和实践性,强调了人的思维能动性和生产活动(工业和实验)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意义。有人说:“当恩格斯说,‘实践,即实验和工业’的时候,他并没有把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革命的实践’考虑进去”[1](第250页)。并举出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对哲学家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以说明恩格斯对“实践”理解的不足。这种“学术性”研究的学风,实在令人好笑。恩格斯在《终结》的第一章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和特点的剖析和阐明,不是以德国政治变革的特点为理论前提的吗?这不是“革命实践”对哲学家思想重要影响之思想观点的表现吗?其次,通过阐述如何科学地揭示和研究人们的思想动机的动力问题,从人的自觉自主的意识性深刻论述了人的社会本质,强调了作为历史人物的人和作为人民群众的人,他们的社会本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表现是不同的,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性,而他们的能动作用就表现为阶级斗争。恩格斯的这些论及,应该可以看作是从思想实质上对《提纲》中关于人和人的本质问题的推进和发展。可以说,从《终结》的第一章至第四章的论述,都贯串着关于人的能动性、实践性、社会历史性和自觉自主的意识性,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思想观点。断言《终结》未涉及人的问题的观点,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有的论者企图以人的问题把《提纲》和《终结》对立起来,则是更为错误的。
第三,关于实践问题,在国内外诘难《终结》的论者中,都不能否认《终结》论述了实践问题,即使像悉尼·胡克把从《提纲》到《终结》看作是“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的能动主义,到算作为辩证的、在实际上则是机械的简单化的唯物主义的相应变化”的错误观点,他也不能否认《终结》论述了实践问题。但是,他们为了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贬低《终结》对《提纲》的发展和意义,仍在实践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终结》未强调能动的实践。悉尼·胡克说:“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恩格斯为了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并没有充分地强调这个能动的实践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和重要性。”[6](第30-31页)指责恩格斯“不把感觉当作获得认识的重要线索”,而“求助于实验和实践”。他所说的“能动的实践”,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性”,悉尼·胡克的这些议论是以实证主义的唯心主义为基础的,是从理性主义实践观谈认识的能动性的。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认识的能动性是建立在物质活动的实践之上的。能动性的实践是物质性的,不是理性或精神的。其次,他歪曲了恩格斯在《终结》中强调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原则,混淆了唯物主义的感觉论和休谟的感觉论的原则区别。他认为,恩格斯把实验的结果“当作直接认识的实例的感觉”,是属于休谟的感觉论;“不把感觉当作获得认识的主要线索”,是休谟的现代信徒们企图“接近非感觉主义关于真理和存在的轨道”[6](第31页)。悉尼·胡克的这些观点,和被列宁早已批判过的马赫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列宁指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或感觉的观点,都不会排除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之间的差别。无论主观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源泉。所以,列宁说:“从感觉出发,可以沿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自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沿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4](第225-226页)恩格斯在《终结》中把休谟和康德称之不可知论者,主要是指他们的共同点,而不是他们的分歧点。恩格斯把康德主义者和休谟主义者叫作不可知论者,是因为他们否定作为我们感觉源泉的客观实在。因此,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所增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3](第225-226页)对此,能说没有充分强调“实践因素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吗?显然是不能像悉尼·胡克所断言的。事实上,《终结》在这里不仅从认识论上强调了实践的意义,而且也从本体维度阐明了实践的意义,特别是在第四章中,还从历史观上深刻论证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恩格斯通过关于历史人物、人民群众、民族的和阶级的背后动机的动力的分析和论述,实际上是深刻揭示和系统阐述了社会实践的不同层面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不同作用,并具体地提出和论证了阶级斗争实践(即革命实践)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思想观念以及宗教变迁的巨大意义。所以说,不应在实践问题上制造《提纲》和《终结》的对立,更不是悉尼·胡克所歪曲的:《提纲》到《终结》是“从马克思的自然主义的能动主义”,“到机械的简单化的唯物主义的相应变化。”而应当看作:《终结》对实践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在其深度和广度上,都丰富和发展了《提纲》中关于实践的观点,使之更加具体化了,这是符合实际的正确认识。
标签:费尔巴哈论文; 恩格斯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终结论文; 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德意志意识形态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唯心主义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