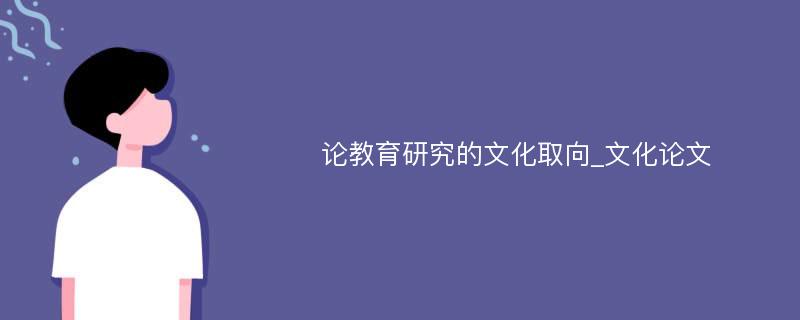
论教育研究的文化学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说的在教育研究中引入文化学的研究理路或“文化研究”的方法,不能直觉地理解为扩大教育研究的对象范围。这里的文化学路向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旨趣,它是在参照国外近几十年来的“文化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代中国文化与教育研究的特殊关系,探讨如何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与教育问题。
一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研究领域形成了两种风格各异的传统。一种是狄尔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一系的人文主义传统,另一种是由泰勒开出的实证主义传统。前者走的是近似形而上学的理路,旨在捍卫人类的普遍价值,因而很容易引起人们情感性的认同。后者则以自然科学为榜样,将地方性的文化“象征符号”视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其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当然两种倾向并不是绝对地分化,有一些学者如韦伯和贝尔则是二者兼顾。(注: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实证主义的文化研究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已开始向社会学与政治学靠拢,(参见马林诺斯基:《科学的文化理论》译序,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 页)这似乎可以看成是西方五六十年代文化研究的先声。)文化研究崛起之后,迅速改变了欧洲文化研究领域的传统格局,清扫了其中不切实际的哲学气质以及缺乏现实社会关怀的价值中立之类的科学原则,将文化研究引向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目的和文化批判上。这些切中时弊的改造无疑可以引起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应。文化研究在西方世界迅速普及,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成绩斐然,但直到现在,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就近年来这一领域推出的经典著作而言,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对象之广,以至于有人认为,文化研究不仅是跨学科的,而且其本身还有意打破学院式的固定学科分类。其实早在文化研究诞生之际就有学者强调:文化研究没有固定的学科基础。正是如此,文化研究习惯于在各种学科之间游荡,而且似乎还故意拒绝学科化。(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 年版, 第328页。)
总之,和传统的学科相比,文化研究没有也不愿意成为一门学科。它习惯于在与不同的学科话语(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的持续碰撞过程中所争取到的边缘区域和交叉地带发表自己的声音。文化研究在总体形态上的复杂性,使人们仍旧很难在什么是文化研究上给出一个基本界定,因为它想要保持的正是“对于出乎意料与想象、不请自来的可能性的开放性”。(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28 ~329页。)
二
没有固定的、属于自己的方法,这恰好表明文化研究对于方法的选择是实践性、策略性的,建立在自我反思和现实“语境”要求之上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与方法选择所依靠的是它自己提出的问题,问题的来源也不是旧有理论的内在缺陷,而是蕴藏问题的现实背景。可以说,问题取向与背景意识就是文化研究在方法论层面所表现出来的首要特征,由此才催生了它的实践性与开放性。
就注重问题而言,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研究在形成时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柯林武德的影响,后者正是以强调问题意识著称。但与柯氏具有浓重的形而上学气质不同,文化研究反对封闭地理解任何文本以及固执于某一特定的方法,它只能依据自己在特定社会的需要将某种方法引进自己的研究,而且这一实践也不能提前确定,因为它不能预先保证在一定的背景下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在它那里,不会拘泥于某一特定的方法,与此同时,它也不排除任何方法:文本分析、语言学、解构主义、实地调查、对话访谈、精神分析、历史研究、综合研究等,总之,只要合适都可能帮助它形成理论观点与知识发现。
由于文化研究总是在特定的现实社会中展开研究,所以它总是按自己的理解把“文化”看成是某一“群体(社会)所遵循的生活方式”,(注:R.E安德森等:《社会环境中的人类行为》,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60页。必须指出的是,安德森只是在理解文化上把握了当代欧洲文化研究的理论起点,至于在理论的“后设层面”上,则没有坚持文化研究的风格,而更多具有人类学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文化”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互动关系,而不是以传统的视角把文化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早在文化研究诞生之际,霍加特就曾以这样的思路完成了他的经典著作《识字能力的用途》,并指出: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无法摆脱由许多别的生活实践所建构的更大的社会网络系统。(注: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31页。)文化研究的这些理念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说, 西方现代理论界自胡塞尔起就一直在寻找认识“生活世界”的途径,却又因为受自身的形而上学的局限,而只能停留在空喊口号、无法着陆的尴尬处境,那么,“文化研究”路向的开出,则为西方理论界摆脱尴尬局面、走入现实的“生活世界”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如果说,胡塞尔等人似乎只是提醒人们“生活世界”出了问题,而文化研究则可以告诉人们:哪些人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以及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甚至该怎么办。也正是这样,西方理论界在文化研究的启示下,逐渐深化了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认识。
6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进入了有意识的建构时期,当时西方社会发生的巨变,使得文化研究更加强调文化与其他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的关联性。在此情况下,文化研究的旨趣集中指向:文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性生产与再生产)与经济发展、社会政治的互动关系中揭示或解释文化。当代的文化研究显然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文化批评的视野,通过关照社会关系的总体背景,来解释文化的实践走向和形态差异。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文化研究是一种非常关注社会现实(重视语境)的实践活动,所以,它的话语与实践本身必须被不断地历史化和本土化。历史化要求文化研究密切关注社会政治与权力关系在新时期的变化,对于自己的价值取向与方法选择应保持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从而维持文化研究向历史的开放性。本土化则意在强调:当一种文化研究理论被移置于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时,它的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价值取向,必须根据新的语境作出调整。这一点对于非西方世界来说尤其重要。
三
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从80年代开始被陆续介绍到中国,并被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成为90年代文化研究的主要话语资源。但是,由于对西方的语境缺乏应有的反思或反思不够全面、深刻,这些理论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变形与错位,有的甚至丢失了原来的精髓和要旨。教育领域对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反应虽然迟缓一些,但多少也会受到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走向的影响,从而也萌发了一些文化关怀倾向。正是这样,先检讨一下文化研究领域的反应,或许可以有助于对自己的反思。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伴随着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大众文化研究以及道德状况研究也成了文化研究中最为关注的焦点。不可否认,这类研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其中的问题也同样明显,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知识界仍然习惯于将文化看成是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和普遍永恒的价值形式,而没有把中国当代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分析。如针对大众文化而发起的“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许多人都把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混为一谈了”,没有从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去反思“商业化浪潮的冲击”,(注:董乐山:《文化的误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更不要提在揭示大众文化与这个历史变化过程的关系以及潜在的运作方式、未来走向的基础上向人们“提供思维方式、生存策略”,而是急着以一种“理想的归宿”来终结它。
这种大众文化态度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教育传统和个人经验的影响很容易把文化看作超越性的结构,从而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逻辑起点定格于一个抽象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现实社会——蕴涵了大众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互动关系的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难以整体性地解析中国社会文化结构这个大众文化得以形成的具体语境,而不得不走更为熟悉的理路。这一结局甚至连那些曾强烈要求“走出书斋”的理论研究者也无法避免。
似乎是作为一种对大众文化研究的真诚回应,教育研究领域不仅提出了要提升精神、追求“超越”的号召,而且还依据西方的文化思想对教育实践展开了研究。一些文化知识界使用的概念,如“现代性”、“生活世界”和“人文精神”等经常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职是之故,以这些概念进行研究的教育理论或多或少也沾染了文化知识界的视野局限。如前所述,中国的文化研究往往从价值观的角度与这些概念进行对话,而不是将这些概念所涉及的各种事实看成是历史性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运作结果,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类教育理论常常是按照从“价值预设”到“价值定位”的理路来构建,结果理论只像是断了线的“空中彩球”,永远无法回到地面上来,这其中的部分原因自然与抽象地理解文化或没有将文化视为是一种有着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有关。
四
以上只是从侧面说明理论界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研究意向。尽管对“文化研究”本身尚缺乏理性的认识,但作为一种倾向,文化研究正日益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同样,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文化学的研究路向,而且除了之前我们提过的各种文章中所流露出来的文化关怀以外,在教育历史研究领域,还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些专著型的以文化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不仅对历史性的文化教育本身的内在结构、精神特征和发展演变进行了梳理(如《文化的传递与嬗变》),而且还在历史性的社会背景下探讨了文化教育的功能(如《近世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可谓为教育研究提供了许多充满趣味和意义的话题,但是,由于欠缺经验和理论支持,还很难将历史事实与现实情况连贯起来,从而可以丰富我们的整体性知识和深化对社会文化教育的了解。
在更大程度上,我们选择文化研究路向乃是出于这样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客观原因。我们知道,进入90年代后,教育研究领域存在着诸多的迷茫与困惑,以探索整体性知识为使命的教育研究对这一点感触或许会更深一些,以至有人觉得“教育学”已经走到了“终点”,(注:吴钢:《论教育学的终结》,《教育研究》1995年第7期。 )陷入了彻底的“贫困”。我们要么只能忍受“失语”的痛苦,(注:李江源:《中国教育学的失语与话语重建》,《现代教育论丛》1999年第3期; 郜元宝:《“文化失语症”的语言学诠释》,《大家》1999年第3期。 )要么就向它“告别”,走入所谓分化的教育领域。毫无疑问,这已经向我们提出了挑战。但是,同样无庸置疑的是,我们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这样的挑战。倘若我们认为无论教育怎样“分化”,只要这些分化领域不想迷失“大方向”并承认其母体在这个层面上的职责与功能,那么,仅仅凭这一点,“教育学”就不会“终结”。这种整体性的和方向性的思考活动至多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与认为“教育学”要被“终结”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代中国教育与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我们呈现发展变迁的图景,并日益复杂化。尤其重要的是全球化的趋势还会使这幅本身就已够复杂的图景变得更加模糊难认。因为与以往西方与中国的融合是局部的、片面性的不同,当代中西融合的运作方式则是整体性的,即文化上的融合。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另类的“整体的社会生活方式”正在进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及其运作机制。这就意味着,要想认识中国,还必须了解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作为探索实践“发展规律”的学科之一的“教育学”所面临的压力与困难也是史无前例的。由此我们也更加相信,教育学是没有理由被终结的,因为它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一个使命,即让我们对实践发展有个总体把握,不至于在局部领域出现不协调的莽撞行为,加剧社会的紊乱,降低或抵消社会发展的成就。
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教育学倘若真的陷入了“贫困”或丧失了“尊严”,那也只是表明了“教育研究者”的贫困。在此认识下,教育研究者摆脱贫困的出路即在于“走出书斋”,投身于现实的教育与社会实践中,在反思、扩充已有知识储备的基础上,继续理论建构的使命,从而能够以提供有效知识的方式换取当代社会的尊重。这里的“走出书斋”无疑首先意味着一种视角转换,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现实,引入现实(历史)性、批判性、实践性、开放性的思考方式。而这些思想品格正是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核心精神。
面对现实,我们可以说,当代中国教育实践的发展变迁不是教育本身,更不是教育学本身所能单独解释清楚的,它是整个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而且我们还清楚,连现代意义的教育学本身也是“文化移植”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包括理论语言在内的广泛且深刻的文化变迁即是我们探究中国社会与学术发展时必须面对的基本事实。当然这里的“移植”不是“照搬”,而应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外来的与固有的、历史的与现实的、理性的与情感的、思想的与制度的、观念的与实践的,各种因素互相纠缠、相互作用,共同造成了现在这个及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处于这种语境中的教育问题一开始就明显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也是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这启示我们,如果不能整体性地认识中国社会文化的结构转型,乃至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迁,就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教育实践与理论的新走势。与之相联系,对于中国教育与社会结构变化的理论意义上的整体了解,就需要有超出原有教育研究领域的知识积累和思想方式,因为这个变化过程涉及传统、政治、经济、科技等各个方面,从而要求跨越并综合各学科的理论积累与研究方法,而文化学路向的开出无疑可以促使我们在这些要求下进行一种非常有挑战性的探索。
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所理解的一样,乃是指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由此,文化意义上的教育就应该首先被理解为现实(历史)的教育状况,并且这种状况是现实社会各层面互相作用的结果,而不是某种纯粹的教育理想在历史中的展开。正是出于这点考虑,我们在借鉴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时,更意在吸收其中可以活用的灵魂,即策略工具和思维方法,以求解答现实的教育状况及其文化性和社会性的形成因素,并期望在此基础上可以使人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如何改进所发生的事情,以及提供有效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策略。或许人们会觉得这样的理路无法达到整体性的认识,但在文化学意义的教育研究看来,倘若整体性的认识是指向那种类似于神话的黑格尔式的整体知识,则恰好会成为教育文化研究的扬弃对象,因为旨在形成定论的整体性认识在我们所指的“文化研究”中是不存在的,在这里,历史性的蕴涵着教育运行状况的现实语境才是惟一的永恒存在,所以它只承认历史性的关于现实语境的整体性知识,只有这样,它才能避免在新的现实语境中,由于知识过时或方法陈旧而陷人“贫困”,从而保持其内在的开放性和实践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就教育的文化学研究所作的方法论上的阐述无疑是极其粗略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宁愿把这种尝试视为一种探索的开端,即从自身出发重新深入反省方法论、语言以及视野等问题,自觉推动中国教育学的建设,而且我们相信,这样做的意义还将波及教育学以外的社会学科,正如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曾经引起哲学、文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广泛认同。总之,在教育研究领域引入文化学的路向不仅是必须的,而且还是可行的。尽管与其他的研究理路相比,由此途径去把握中国当代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总体面貌与内在规律同样需要持续地投入巨大的个人热情与思想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