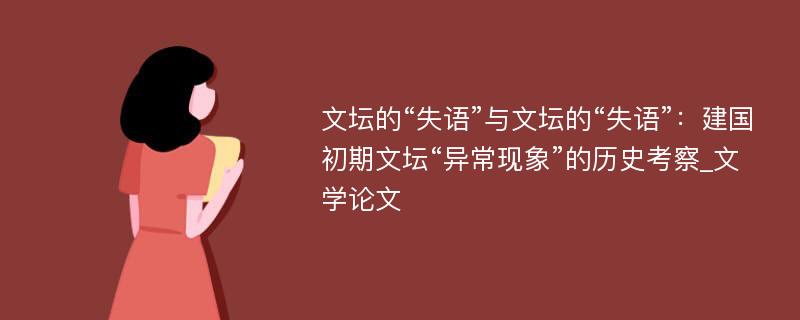
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新中国建国之初文坛“畸相”的历史追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之初论文,新中国论文,历史论文,畸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54(2004)03-0072-04
因年高病残退出文坛,或因创作源泉枯竭而中断文学创作,虽然是当事作家的遗憾和不幸,但对于一代文坛,却仍不失为一种平常现象。但如果一大批作家,而且是一大批名流作家同时集体停止文学创作,那就不仅仅是不正常,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和遗憾了。
而众多作家同时集体“失语”的文坛畸相,就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并且这些作家中的大多数将“失语”状况延续到了生命的终点。
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彪炳现代文学史、但在50年代初相继停止文学创作的那些作家1949年的年龄吧:
茅盾1896年生 53岁 巴金1904年生 45岁
叶圣陶 1894年生 55岁 艾青1910年生 39岁
沈从文 1902年生 47岁 钱钟书 1910年生 39岁
冰心1900年生 49岁 田汉1898年生 51岁
丁玲1904年生 45岁 卞之琳 1910年生 39岁
许杰1901年生 48岁 许钦文 1897年生 52岁
冯至1905年生 44岁 吴祖缃 1908年生 41岁
张恨水 1895年生 54岁
此外还有几位虽未停止创作,但创作状况(数量、才气、灵气、艺术水准)大不如前的作家:
郭沫若 1892年生 57岁 老舍 1899年生 50岁
曹禺1910年生 39岁
以上这些作家,新中国成立时年龄最大的57岁(郭沫若),最小的才39岁(曹禺、艾青、钱钟书),18位作家平均年龄47岁,正当人生也应该是创作生命的盛年。然而,这群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风流,30~40年代的文坛之星,却几乎同时“陨落”在建国之初。即使有少数几个仍在勉力创作,但艺术水准与此前相比已是大幅度滑坡。其余则差不多同时“歇笔”,再无有影响的新作问世,最甚者如沈从文,被彻底逐出文坛,在故宫红墙内研究古代服饰、“客串”导游讲解员,从此与文学形同路人。
可以肯定这决不是年龄、身体状况的原因。因为在二十多年之后,上面提到过的巴金、艾青,在耄耋之年,却又以抱病之身重新出现在文坛,并且奋笔疾书,梅开二度,再造辉煌,以“杜鹃啼血”、“老牛奋蹄”般的悲壮,让自己的艺术生命来了一次奇迹般的“回光返照”。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残缺了二十多年的艺术人生虽然得到些许弥补,但逝去的永远逝去,再也无法追回。
而其余几位作家,却因为种种原因,连这次“回光返照”的机会都没有出现。他们的艺术生命,几乎就那样永远“封冻”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中。其中只有老舍是个例外,建国头17年中因政治的激情还曾活跃过几年。但“文革”初起,他却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使是他十分活跃的那几年里,艺术上他也未能重返自己三四十年代的高度。
“集体失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实,又岂止上面提到的区区18位名作家!何其芳、陈学昭、林徽因、施蜇存、洪深、丽尼、阿英、胡风、穆旦……这些作家诗人不也同前面提到的18位名作家一样,“集体失语”了吗!
是什么原因造成建国初期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
事情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现在或许是可以追问历史的时候了。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共产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如此辉煌又如此具有传奇色彩,不仅令国民党反动营垒闻风丧胆,也让共产党的盟友、朋友及大多站在“第三条道路”上的知识分子(包括绝大多数的文学家、艺术家)目瞪口呆。惊愕、狂喜、愧疚、遗憾……各种复杂的心理,都因这巨大的胜利而出现在当时作家的心中,甚至还有恐惧,像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等作家,远离大陆避居海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恐惧心理的作用和结果。虽然他们只是极少数,但也代表着文化人当中的一部分。
面对着旭日初升的人民共和国,每一个作家都在反思自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对于那些思想进步、始终关注劳苦大众疾苦的作家,心情恐怕是更为复杂,因为他们曾经选择了与共产党近乎相同的道路,当初要是参加武装斗争,今天也可以昂首走进战斗者、胜利者的行列。然而现在他们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坐享革命之成果,成为“分一杯羹”的宾客。因此,惊愕、狂喜的心情中掺进愧疚、悔恨、自责、遗憾的心理也就不足为怪了。
思索的结果,是对“革命”无条件的认同,是人生道路、创作道路的重新选择,是人生观、世界观的重新确立。而这一点,对于已有过几十年人生经历阅历、甚至形成了个人文学风格的文学艺术家,决非一朝一夕之事。思考、认识、反复,再思考、再认识、再反复,文学艺术家在此期间正在自觉或半自觉地“洗脑”——进行个人历史上巨大的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在这极为痛苦的过程中,作家艺术家纷纷选择宣言口号式的“急就章”匆匆表态,以获得新社会及执政党的政治认同,寻求自己的“政治归宿”。“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寻家、认家、归家,成了当时作家人生道路和创作题材的共同趋向。既然“归家”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旅途,那么旅途上也就只能写出观感、游记类的作品了。共和国之初,标语口号式的诗歌、小说、戏剧,观感游记杂感类的散文之所以大量出现,与作家艺术家人生道路的重新选择、政治立场与价值观念的重新定位,有着很大的关系。郭沫若、巴金、茅盾、叶圣陶、曹禺、冰心们纷纷这样作,远在海外的老舍万里归来,也匆匆忙忙这样作,而一代名流沈从文则多次发文表态后仍不被认同,伤心绝望竟至自戕(未遂)。
“毛主席/告诉咱/咱们工人当了家/要使中国工业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当家的主人/都来学文化。”这是时代诗人郭沫若50年代初的作品。这是诗,还是政治表态,读者的答案是不难作出的。
频繁的政治运动(包括思想改造运动)是造成文坛“集体失语”文学现象的另一重要原因。回顾共和国之初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发生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八次运动。这些运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方面,声势之巨、涉及面之广、震慑力之大、卷入者之多,都可以说是空前的。而这几次运动,除了与经济、军事有关的“三反五反”、抗美援朝不直接涉及文学艺术家,其余都与他们相关或密切相关,而有些则是直接指向他们的(如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反革命集团”)。认识、检讨、表态、批判、划清界线成了他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事实上,中国的政治运动如同一只巨大的网筛,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只能被动地接受颠簸而别无选择。
在无可逃循的似乎永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所幸这些运动终于在新时期终止了),文学艺术家赔上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能够顺利地通过“考验”已是幸事,政治上的“生存”已成了第一位的生活内容,至于文学创作,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共和国建国之初,尽管不少文艺名流、社会贤达已身居高位——郭沫若、黄炎培已是政务院副总理,茅盾、章伯钧、罗隆基、巴金、老舍、曹禺、艾青、田汉已是国家部长、副部长或类似级别的协会主席、副主席,但却无法在运动中“逍遥”,只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讲话、作报告,表现出自己正在“积极投身运动”以获得一张政治立场方面的“合格证书”。正如巴金老人在《随想录》中所说的,自新中国建国以后,这类认识、表态、站队式的文章不知写过多少。尽管如此,还是在十多年后被打入“另册”。以至于“文革”中的当权者张春桥曾恶狠狠地说:“对于巴金,不枪毙已经就是落实政策了。”
文艺名流、社会贤达尚且如此,其余小有名气或没有名气的文学艺术家又当如何?随波逐流,是运动态势下十分自然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当文学与政治(具体表现为各项政策和各种政治运动)发生矛盾时,相互间的作用力也就有了天渊之别。文学对于政治,其影响力如隔靴搔痒;而政治对于文学,其作用力却如刀砍斧削。文只能载道,只能表情达意,只能被欣赏、被玩味、被抚摸,若说它可以立国兴国、治国安邦,只是一种文人式的自我陶醉或虚拟幻想。小说如此,诗歌、戏剧、散文或其它五花八门的“文”也莫不如此。当时也许没有任何人强迫文学艺术家参与运动,或让他们放弃文艺去选择政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却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这样,文学的损伤乃至某种程度的牺牲也就在所难免了。
建国之初的文艺政策、舆论导向,受前苏联的影响极大。一个初次执掌政权的政党,在文艺领导方面的经验几乎是一片空白,文艺理论、文艺政策方面的幼稚也就在所难免。能借鉴的只有“苏联模式”,此外就是解放区文艺工作的作法或经验,在方向上也只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向可选择。因此,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制定一切文艺政策的基础、成为文艺的舆论导向也就势在必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就是“左”的表现,但其幼稚性、简单化与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否则30年后的邓小平文艺思想中也就不会对其进行修正了。
然而当时的文坛,却只能别无选择地执行这种文艺政策,接受这种舆论导向。为“工农兵”去写作,去演出,“写工农兵、演工农兵、唱工农兵”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潮,甚至成了惟一的潮流,任何试图偏离这种主潮的尝试(例如肖也牧及其短篇《我们夫妇之间》,朱定、白朗、碧野等的作品),马上就被斥之为“资产阶级创作倾向”,被无情批判乃至全盘否定。当时甚至把“写不写工农兵”和“是否以工农兵为主角”当作了立场问题,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变成了为具体的政策服务(见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一文,《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身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的邵荃麟,以及此前后中宣部负责人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的讲话,既是一种政策的宣讲阐释,也是一种舆论导向。写、唱、演工农兵成为当时不容怀疑的文艺主潮,后期竟至走向极端到只能写“工农兵中的”“没有缺点的英雄人物”,文艺创作因此钻进了“牛角尖”。此后又来了个“揠苗助长”,变成“工农兵写”,煞费苦心地从文化程度低下的工农兵群众个体中去发现、培养工农兵作家,刚刚脱掉文盲帽子(甚至还不算真正脱掉文盲帽子)的个别尖子人物如王老九、崔八娃、高玉宝等,一跃而成为“文坛新星”、“著名作家”,而专写农民生活的赵树理则成了所有作家的榜样。优秀作家的名篇佳作甚至从学校教材中被剔去,而王、崔、高的诗歌、小说如《毛主席和我握了手》、《狗又咬起来了》、《半夜鸡叫》、《我要读书》却成了教材中的必读篇目。
在这样的文艺政策、舆论导向中,作家们惶惑、迷惘。要么,顺应政策,写一些宣传、解释政策式的作品,要么,就此“挂笔”,或改行从政、从教。此外似乎没有其它的道路可走。看看这一时间段的文坛名流,写“传声筒”、“宣传品”式作品的作家有,如郭沫若、何其芳;写“讲话稿”的作家有,如巴金、沈从文;改行当“官”的有——挂着作家之名在各级政协、文联、作协当不是官的“官”,更是大有人在。惟独没有几个还能坚持文学创作。位尊者食有鱼,出有车,稍次者也衣食丰足,工薪照发。至于多次表态仍不被认同的(如沈从文)也可打发到故宫去当当讲解员,好歹有碗饭吃,如同老人家说的“养起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全无事,更何况不写作品就不可能犯下新的“错误”,何必青灯白发爬格写稿自寻烦恼。
文坛名流们也曾试图修正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去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如沈从文就曾写“革命大学”的一个炊事员,进而又准备写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茅盾也曾应公安部长罗瑞卿之约写“肃反”题材,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正好映证了一句俗话:“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藤结什么瓜。”勉强自己写并不熟悉、并无体验的生活,或勉强让自己去适应并不完全理解的文艺框架,碰壁也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唐·李峤《咏风》),“风”的力量是如此巨大,它使文学艺术家的传统文艺观念严重动摇,甚至导致他们对自己产生错误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暂停创作、修正文艺思想、改变文学观念一时就成了他们的共同行动。然而,随着“左”倾文艺思潮的渐烈和政治运动的升级,“暂停”变成了“退场”。到“文革”狂飙突起,文艺界被“犁庭扫院”“打倒一切”时,三四十年代的文坛名流几乎被悉数扫进“牛棚”,文学创作变成了“高危职业”,再也无人敢问津。浩劫过后,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过花甲之年,即便想重出江湖、梅开二度,也已经力不从心,更不用说没有熬过浩劫的那些作家(如老舍、闻捷、肖也牧、杨朔、傅雷等)了。
“失语”现象就这样延续到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终点。
作为精神产品,文学艺术作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宣传、教育、感化、愉悦、审美等等。作为其功能中的一种,宣传教育功能是直接但却是浅层次的,片面强调它们,则会带来文学价值标准的失衡,并由此带来作品艺术水准的滑坡,甚至使作品倒退到“宣传品”、“政治教材”的地步。而当时过分强调的“为政治服务”、“为政策服务”、“写工农兵”、“工农兵写”等,则是不断强化着文学艺术的宣传教育作用,弱化其应有的感化、愉悦、审美功能,这样一来,文艺作品艺术水准的滑坡也就不可避免。
在艺术形式上,针对当时群众文化水平低下,适当强调通俗化、大众化也无可非议。然而,“真理多前进一步就会成谬误”,若将它们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通俗化、大众化就会变成粗俗化、浅陋化。崔八娃一篇400来字的小说习作(第一稿中竟有几十个错别字)成为当时的名篇,《高玉宝》成为当时的长篇“名著”,都是这种过分强调的结果。此时的文坛,虽然“假、大、空”还未能形成风气,但“粗、浅、薄”(粗俗、浅陋、单薄)却已成了一种文艺时尚。文坛宿将老舍甚至放弃了最为稔熟的小说形式,专写“劳苦大众都能看得懂的”、充斥着大白话、大实话的话剧;郭沫若的诗写成了人人都听得懂的“儿歌”,或充满政治概念的“新作”;艾青的诗成了押韵的大白话;数年后的“文坛新秀”“著名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姚文元,其“处女诗”只能令人掩鼻。这里略举一二: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奋斗/勇敢前进前进/跟着毛泽东
——郭沫若《少年先锋队之歌》
……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
——郭沫若《满江红》
郭老甚至将这种“诗风”保持到寿终正寝,他老人家最后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中写道:
……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水调歌头》
著名诗人艾青,23岁时写下《大堰河——我的保姆》那样的传世之作,50年代40多岁时却写下这样的诗句:
杨庄有个杨大妈/她的年龄五十八/大手大脚大嘴巴/大大的眼睛黑头发……
——艾青《藏枪记》
最令人“喷饭”的,要数当时“文坛新秀”姚文元的“四言诗”《和平出在斗争里》:
美帝美帝/是纸老虎/外强中干,见风转舵/你若怕,就欺你/坚决斗争,一定胜利/全体同胞,斗争到底/哪里逞凶,哪里粉碎/同志们……从来光明胜黑暗,和平出在斗争里!
(《文汇报》1958年7月20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髦。姚文元恐怕也不是那个年月的惟一的“特产”。文学水准如此低劣的他后来竟成了“文坛新秀”、“著名文艺理论家”、“全国舆论总管”,由此可见当时文风粗鄙恶劣到了何等地步。
文艺美学的底线被彻底击破,价值标准严重失衡,一些还想坚持艺术原则的文学家面对此情此景,只剩下惊恐、惶惑、迷惘、叹息的份了。随波逐流心有不甘,坚持艺术又不合时宜。“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诗句),还是用“沉默”来表示对这种“时髦”的个人态度吧!
“风,起于青萍之末”。事过几十年后回首,我们方才醒悟:集体式的“文坛失语”,只是“左”倾文艺路线的先兆,以后逐步发展成文化清理、文化整顿、文化围攻(“革命大批判”),直到演变成文化剿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不容怀疑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之下,无论是屈从的还是躲避的,或者是曾经积极参与的(如周扬、胡乔木、吴晗、老舍、郭沫若等),都未能躲过那场灾难,文学艺术也遭到了一场空前的、长达十余年的“浩劫”。幸运的是,历史在1976年10月给了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文坛一次难得的机遇,否则中国的文学艺术说不定仍在极“左”的文化专制的樊笼中。
昨天已幽幽远去,明天正姗姗而来。站在世纪之交,回顾50年前的文坛往事,并非只是“发思古之幽情”。当年文坛的“失语”和“失语”的文坛,给当代文学、给当事作家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也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慨叹。反思历史的目的不是重现当年文坛的“畸相”,而是警醒后人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收稿日期:2004-02-24
标签:文学论文; 郭沫若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艺论文; 沈从文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