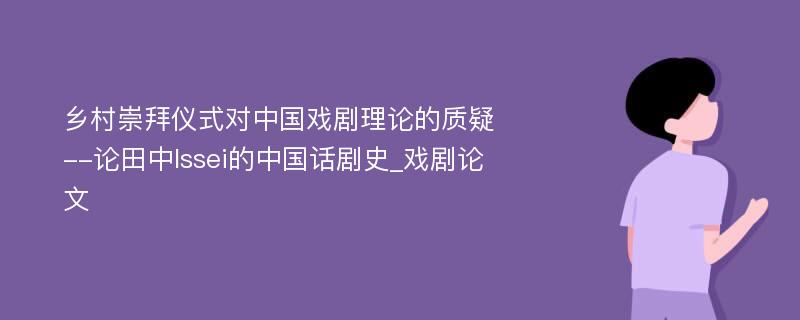
中国戏剧发源于乡村祭祀仪礼说质疑——评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戏剧论文,祭祀论文,乡村论文,仲一成论文,仪礼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底,我参加中山大学主办的一个有关节令民俗的学术会议,发言涉及到中国戏剧史的起源与民间祭祀仪式的关系。在此之前,我一直对日本著名学者田仲一成先生在《中国戏剧史》以及其他相关著作里提出的有关“中国戏剧起源于乡村祭祀礼仪”的观点有异议,既然田仲先生恰好与会,就在会上直言了我的看法,以就教于田仲先生。会间休息时,田仲先生就此和我做了简短的交流,并且给我看了他刚刚在中山大学为学生们做的讲演的文稿。这次讲演的内容是针对南京大学解玉峰副教授公开批评他的《中国戏剧史》的应答。我想田仲先生大约是想用这篇讲演稿同时回答我的批评,只不过,当我读他的讲演稿时,因其言辞之激烈而颇感意外。
田仲先生多年来对中国民间祭祀戏剧的深入研究具有广泛影响力,但他的《中国戏剧史》可能是个例外,在已有的众多中国戏剧史著述里,他的这部观点独特的新著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当然,田仲先生自己对这部新著的学术价值一定是充满自信的,这几乎是他数十年潜心研究中国戏剧的理论归宿。对于他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这部新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戏剧史》是一部提出了学术新见的著作,而不同于他此前更为人们熟知、更擅长撰写的那些材料湮没了见解的田野考察报告。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与评价田仲先生的《中国戏剧史》,即使是着眼于研究田仲先生这样一位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戏剧专家的学术思想的角度,也有其特殊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对这部《中国戏剧史》的评价,尤其是对他有关中国戏剧起源的核心观点的评价,可以加深我们对艺术史的学术建构方法的认识。
讨论田仲先生的《中国戏剧史》,我们需要注意到,他提出中国戏剧起源于乡村的祭祀仪礼这一独特观点时,是基于某种独特的学术背景的,其中有丰富的感性材料作为支撑。因而,我虽然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与他的分歧,并不是对他所提供的田野考察材料的质疑,也不止于普通的异见,它涉及到相当广泛的学术层面,不仅涉及到中国戏剧史的起源,更涉及探究中国戏剧起源的研究方法。而田仲先生对解玉峰的批评的激烈回应,又将问题的涉及面扩大到更广泛也更深刻的领域,这让我更觉得,就他的《中国戏剧史》展开深入讨论很有必要。
田仲先生治中国戏剧多年,出版发表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学术著作,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学术贡献。
田仲一成先生在中国戏剧领域的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他对以香港新界为代表的中国民间社会的祭祀戏剧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尤其是对地方宗族组织在这些与祭祀密切相关的戏剧演出中的重要作用的揭示。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已经得到充分肯定。但是当他以此为基础论证中国戏剧的起源,尤其是主张中国戏剧的发生应该从乡村的祭祀仪礼中去寻找时,就已经跨入了另一个领域,而在这个领域要想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需要更多的知识、材料与理论支撑。
有关中国戏剧的发生或曰起源,事实上包含了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又很容易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一是从泛戏剧的角度看中国戏剧的起源或发生;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国戏剧——或者通常被称为“戏曲”的这种演艺形式——的起源或发生。当我们泛泛地从事中国戏剧的发生学研究,讨论中国戏剧何时起源、经过怎样的路径发展、以至何时成熟时,当然可以通过阅读先秦以来的史籍找到许多文献,而所有与妆扮、表演、歌舞以至于杂耍相关的材料,都可以为其所用,无论是先秦时代的优孟衣冠和《九歌》,还是汉代百戏与隋唐戏弄,宫廷与民间的巫傩等等,都明显与普泛意义上的戏剧有关。如果是在这个意义上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戏剧史,这些内容当然可以且应该包含在内。从这个角度讨论中国戏剧的起源,固然有其特殊的意义,然而,如果我们要讨论的是从宋元以来一直流传到今天的戏曲,讨论它的起源与发展,就必须特别慎重。
中国戏剧——戏曲——的起源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界难题,是由于我们目前所知的宋元年间出现的戏文和杂剧,具有独特且成熟的形制,而无论是它的剧目体系、音乐体制还是表演体制,要想从此前已知的戏剧现象中找到清晰的源头都不容易。按钱南扬先生的研究,除了完全佚失的以外,已知南戏至少有87本,其中包括《永乐大典》“戏”字韵下列载戏文32本,徐渭《南词叙录》中著录的有65本等等①,如此说来,说宋代流传的戏文有百本之多,并不过分。今人对戏文的形制所知甚少,但是通过《永乐大典》残卷里基本可确信为宋代遗存的《张协状元》,以及这些戏文大致可知的故事情节,设想它们都有相当的长度,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的需要一个完整的单位时间(整个下午或晚上)演出的本戏,因此与宋金时代的更接近于零星的折子片断的杂剧差别很大,这大概是个不会太离谱的判断。而在宋代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徐渭所说的“南渡”之前即北宋和更早的时代,我们完全找不到与之相类似的表演一个完整的故事的大型戏剧的记载。元杂剧也是这样,它的结构与形制,虽与南戏不同,但也具有足够的长度。更值得注意的是,戏文与杂剧都有非常之完整的音乐结构,它们使用的大型套曲,都足以使之区别于此前所有雏形的戏剧;至于戏曲通过唱念相间的方式以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样的表演模式,在先秦到唐宋的各种雏形戏剧活动中,也看不到前兆。而如果我们无法解释宋元戏文与杂剧是以怎样的艺术样式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戏曲的起源。
假如我们相信一种艺术样式不会凭空出现,尤其是像戏曲这样格局宏大的舞台艺术样式,大约不会因温州(永嘉)几位才子一时兴起的创造突然出现,那么我们就需要在历史进程中细细追寻,去探索戏曲这种文体、它所拥有的复杂而完备的音乐构成以及在表演中特殊的脚色扮演制度等等是从何而来。可惜田仲先生对中国戏剧起源的新论述,与此三者全无关系。从他的《中国戏剧史》里,我们看到宋元年代的戏曲作品以及演出中,存在诸多与农村的祭祀仪礼相关与相似的成分,却缺少一个关键的环节——他不能说明或者是没有想到需要说明,农村的祭祀仪礼有什么可能发展成为宋元戏文和杂剧这样成熟的戏剧,这样两类如此不同的艺术样式之间的关联如何建立,或者更清楚地说,从祭祀仪礼发展到与之截然不同的戏文或杂剧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这两类文化活动之间如此之大的鸿沟是如何被跨越的。然而,这才是解决中国戏剧——至少是中国戏曲——起源的关键。诚然,正如田仲先生的《中国戏剧史》里所引用的大量资料所述,从元杂剧到明清传奇,直到晚近的地方戏,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出,都夹杂有大量和民间祭祀仪礼相关的或相似的内容,但是仅因戏曲里有这些内容,就想要证明戏曲“源于”祭祀仪礼,无疑还是很不够的。
其实,在此之前多位对中国历史文献掌握得更丰富的学者,也做过同样的努力。任二北先生著《唐戏弄》,就试图通过大量与歌舞戏弄相关的文献,证明唐代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戏剧表演;杨公骥先生解读《公莫舞》,想以此强调西汉时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整故事情节的演出剧本。他们所引征的材料本身都很有价值,可靠性也无可置疑,可惜仍然离结论差了一步——无论是从《公莫舞》,还是从唐戏弄,都还不能建立起一条艺术形态演变的完整因果链,从这些戏剧现象,我们还无法解释戏曲的诞生。因为就我们今天可见的南宋戏文和元杂剧而言,它们都已经拥有非常之完整且独特的大型格局,而从宋戏文和元杂剧到此后的明代传奇,以及从戏文、杂剧、传奇到其后兴起的地方戏之间的关系,都是如此清晰,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把握从戏文开端的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然而,在南宋之前,要想从前述的各种雏形的戏剧演出中找到戏文之所以形成的原因,却十分困难。
晚近以来,研究戏曲的学者们在戏曲起源方面并不是没有成果。自王国维考订诸宫调后,郑振铎和日本的青木正儿等学者都对诸宫调的缘起、内容与形态做了大量研究。李家瑞从中国各地流传的戏剧经典中发现了许多由说书演变成戏剧的痕迹,找出大量的“前身是说书,后来变成戏剧的例子”②。吴则虞更判定诸宫调是“直接继承了变文俗讲的形式,通过创造过程,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丰富提高”的“话本”里最具丰富性的一种,“无异是唐宋讲唱文学的总汇”,他指出,“讲唱文学发展到了诸宫调是无以上升,必然引起更高级的艺术形式——戏剧的发生发展,而诸宫调就成为他的奠基人”③。几十年间有关中国戏剧起源的这些点点滴滴的进展,越来越清晰地让我们看到,从佛教传入以来,出现了以讲唱方式传播佛教经义的变文俗讲,唐宋年间盛行的讲唱文学就是变文俗讲世俗化的产物,而集唐宋讲唱文学表现手法之大全的诸宫调,它与宋元戏曲之间的形态是如此相似,只需由叙述体转化为代言体并且由演员搬演,就可以直接演变成戏曲。而我们从古往今来的戏曲作品中不仅看到了大量原本是说书讲史、后来成为戏剧的作品,甚至还可以在戏曲的内容与表现手法里,发现许多本该讲唱文学才有的非代言体的成分,它们都可视之为由讲唱转化成戏剧时转型不彻底留下的遗痕。征以近代戏剧史,直到20世纪初,在江南一带,我们还可以发现原为讲唱的滩簧很轻易地转为戏曲的例子,包括越剧、锡剧、甬剧、沪剧等等。
曾经有那么多著名学者在努力寻找证据,探索戏曲由讲唱文学——包括说书、诸宫调等等——转化而来的可能性,他们的论断虽然还没有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但至少这些考订体现出对艺术发展逻辑过程的尊重。他们的研究虽然并未形成定论,却是在切实地从戏曲的体制、格局、表现手法以及具体题材内容等等方面,为戏曲的形成寻找具有实证性的渊源。正因为,要解答戏曲起源这个难题,就需要找到它的剧目体系、音乐体制以及表演体制的来源,所以它才成其为难题,而它们都很难从汉唐以来的各种雏形的戏剧活动中找到——不用说,想要从农村的祭祀仪礼中找到戏曲的源头,更是天方夜谭。
虽然以田仲先生的学术背景言,很难要求他全面掌握有关戏曲起源的上述文献,但如果设想要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最好是对相关领域的以往研究有较全面的了解,我想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而我与田仲先生一样,在中国戏曲的起源问题上恐怕都只能算是外行,因此我的质疑与批评,并不是要围绕上述文献展开有关戏剧起源的争议,而是着眼于田仲先生的理论方法与学术逻辑。
从这个角度,我想指出的是,田仲先生在提出他大胆的新见时可能没有注意到,从学术逻辑的角度看,只看到两个对象之间的相关与相似,并不能简单地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考察中国民间戏剧,不难注意到乡村戏剧演出与以神庙和祠堂为中心的祭祀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但是如果再细加观察与辨析,还可以看到另外一层,在我看来,乡村里每年固定时节举办有一定规模的祭祀活动——无论是祭拜神灵还是祖先——同时组织戏剧演出的现象确实是非常之多见的,但是在这里,祭祀与戏剧两者之间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共生关系,把祭祀活动时邀请戏班从事的戏剧演出看成祭祀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妥当。在很大程度上,民众只是利用祭祀这样的组织形式,为他们请戏寻找一个理由,换言之,祭祀活动的存在,更像是乡村民众耗费不菲资赀获得欣赏戏剧的文化娱乐机会的一个合法借口。在这里,虽然我们很难说民众从戏剧中得到享乐的冲动冲淡了祭祀仪礼的神圣性,至少戏剧的剧目选择与祭祀活动之间的关系,其疏远程度要超乎人们的想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对于生活在中国的这个早就已经高度成熟的民族而言,信仰与娱乐都是重要的精神活动,人们应该惊讶的不是民众居然能将世俗的戏剧演出和神圣的祭祀信仰置于同一个精神空间,值得惊讶的是这样两大类活动居然可以如此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甚至分不清主从。
更不用说,中国乡村的祭祀仪礼活动以及各种雏形的祭祀性戏剧活动之早于欣赏性戏剧,也不足以说明欣赏性戏剧就一定是从祭祀性戏剧演变而来的。巫傩的出现当然远远早于戏曲,中国各地乡村目前仍然存在的傩戏表演中,确实包含了许多我们在戏曲舞台上也可以看到的,内容包容了许多原始信仰成分的巫傩祭祀活动和戏剧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但是我们无法就此推论,说是巫傩格局渐渐扩大而发展成了戏曲。更大的可能性是,当戏曲出现并且在人们的精神娱乐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之后,戏曲中的某些民众喜爱的剧目以及片断,就渐渐被充实到傩戏里,而不是相反。目连戏的发展演变轨迹就更为明显,如刘祯所言,“目连故事渊源于佛经,而直接影响后世多种目连故事作品的是变文,变文是后世目连戏及其他形式作品之祖祢”④。而在后世目连戏的演出里,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作为主干的目连救母故事以外,还经常被加入各种各样,往往与目连关系不大的故事内容,而目连戏能够在一地连演十多天,除了作为主干的目连故事本身的宏大,还由于在整个大的故事框架之中,表演者可以加进更多的内容。有关目连的讲唱文学作品先于戏曲,而我们又能从后世的目连戏里找到许多戏曲折子,但我们却不能就此断定戏曲受到目连戏的影响甚至取材于目连戏,因为更大的可能是,当戏曲出现之后,乡间大型的祭祀活动中演出目连戏时,会出于娱乐等等考量,将一些人们熟知的戏曲内容加入到目连戏演出的整体当中。如果不能厘清这一现象,对中国戏剧乃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诉求的认识,就会出现偏差。
更重要的是,田仲先生在戏剧理论层面上的思考是有缺陷的。他曾经在该书的“序论”中特别指出,他是通过田野观察发现了中国农村民间戏剧与信仰以及祭祀礼仪之间相互依存、共生为一体的诸多现象,同时接受了简·艾伦·哈里逊对希腊戏剧的起源的解释,以及日本学者折口信夫、西氏信纲对这一学说的继承发展,才提出中国戏剧起源于农村的祭祀礼仪这一观点的,他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普遍适用的视点”⑤。就如他后来对解玉峰的回应文章里所提及的那样,他觉得戏剧发源于祭祀仪礼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中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个例外⑥;田仲先生对有关戏剧起源的各种理论,恐怕了解得颇为有限;即使是古希腊和日本的戏剧均与乡村的传神仪礼相关(其实古希腊的戏剧是城邦的大型表演活动,很难说源于乡村),也不足以证明全世界的戏剧都一定要遵循同样的规律,艺术的问题是如此之复杂,要想通过一两个地区的现象推导出全球通用的规律,需要格外小心翼翼。抽象地说所有戏剧甚至人类表演活动归根到底都起源于巫术,或许是对的,但是具体到个别的戏剧现象与戏剧类型,比如具体到戏曲,或者论及歌剧、芭蕾舞等等,就需要更为细致的分析。全世界那么多文化圈那么多戏剧现象,并不一定都会遵循着从祭祀性戏剧转变为欣赏性戏剧的普遍规律,如前所述,中国的戏曲就很可能是从已经发育得相当完好的讲唱文学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把讲唱文学看成是戏曲的源头,如同李家瑞所说,“我觉得比前人所说的中国戏剧原于‘八蜡’(《东坡志林》),近人所说中国戏剧原于‘傩’的说法,比较着实一点”⑦。戏剧的诞生,尤其是欣赏性戏剧的诞生,当然需要很多文化上的铺垫,这是世界上只有很少民族才能创造出成熟的欣赏性戏剧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看,从先秦时代开始的中国乡村祭祀仪礼,无疑是在戏曲诞生之前为它做了重要的精神准备的文化活动之一,但是要用这点关系就说中国戏剧起源于它,还是略嫌牵强。田仲先生或许没有想到,这些理论与他所接触到的感性材料之间的关系,还远远不足以解释中国戏剧的起源。至于在具体阐述中,他进而从中国传统戏曲剧本的文体结构分析着眼所作的论证,认为“戏剧独特的起伏结构就是源自春天的祭祀以及随之而生的成人式”⑧,可是“由苦恼到欢喜”这样的结构形式实在是太具有普遍性了,几乎可以从所有讲述故事的文学形式中看到,也非祭祀和成人礼所独有,根本不足以说明独特的戏曲何从产生。
其实,田仲先生也认识到,“戏剧产生的条件,首先就是商业的发达……还有一个条件是宗教与艺术的分开,艺术从祭祀活动中分离出来”⑨。商业的发达源于城市的出现,中国戏曲恰恰就源于城市而非乡村。戏曲发源于城市,是与它最初的商业化属性相关联的。恰由于戏曲从一开始就是以提供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性演剧,因此它需要人口相对集中的“市”,它不会产生于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的农村地区,只会因为在城市里发育得比较成熟后倒流到农村。因此,田仲先生坚持说中国戏剧起源于乡村祭祀,就很难以服人。以我们现在所知的文献看,有关戏文最早的记载是它初出于永嘉(今温州),被称为“永嘉杂剧”,它盛行于杭州,广泛流传于以南宋朝廷为中心的两浙地区,由此形成气候;同样,有关元杂剧的记载,也都指它在北方的大都和南方的杭州等大城市里的创作与活动,它的创作者以及名伶们都生活在都市,从未见他们以及这些剧作有与乡村祭祀仪礼相关的记载。中国戏曲发源于城市,在城市发展起来而后再流到乡村,不仅戏文如此,杂剧如此,甚至连20世纪新出现的一些剧种,如评剧、越剧等等也是如此。
这些都是田仲先生的《中国戏剧史》未能充分考虑到的,也是他有关中国戏剧的起源的新见得不到中国同行认可的原因。
其实,有关中国戏剧的起源,具体地说,有关戏曲的起源,既可以说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已经基本解决的问题。说它尚未解决,是由于戏曲形成过程中还有许多环节,比如说妆扮、脚色以及元杂剧分析的由来等等,我们还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说明它们的来源,比如有关脸谱,周华斌先生敏感地指出它应该源于唐代就已经有的涂面而非形同面具的“代面”,但是多种多样的脸谱造型的来源以及它的发展轨迹还有待于探寻⑩。其他相关的问题,难以索解之处还有很多。说它已经解决,是因为它最早形成于两宋之交或南宋初年,大致是由各种讲唱文学发展而来,它从一开始就是都市勾栏瓦舍内市民化的商业性演剧等等,这都是学界早就已经认可的,而那些我们尚不了解的部分,今人甚至后人,恐怕都很难找到新的材料以得出更新、更有说服力的结论。历史总是会留下很多疑难,但是我们有时必须谦恭地承认,研究者不是无所不能的,有些缺憾恐怕永远也无从弥补。
有关中国戏剧史的整体架构,确实可以有两种,一是以泛戏剧为对象的架构,一是以戏曲为主体对象的架构。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如果一部中国戏剧史要考虑到历史发展的逻辑完整性,那么,我以为还是以戏曲为对象更适宜。许多零星的前戏剧现象,包括戏曲诞生之后仍然广泛存在于城乡各地的泛戏剧现象,确实可以而且也应该得到戏剧史的观照,但这些观照只能说是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戏剧整体的认识,而并不足以改变我们对中国戏曲的起源的认识。这就是田仲先生研究中国戏剧起源的成果给予我们的启发,同时也包含了我对田仲一成先生《中国戏剧史》的学术得失的总体评价。
最后还想提及这篇书评的缘起。2006年底我在中山大学的会议上曾经建议田仲先生将他那篇讲演稿再做斟酌,加工修改调整润色后整理成文寄给《文艺研究》杂志。田仲先生当时似乎是欣然接受的,但半年以后,我在《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读到田仲先生的文章《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公开发表的文章已经与讲演稿不同,尤其是在文辞上做了许多修饰,所幸基本观点仍然基本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他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愈显密切。几个月后,解玉峰撰文在《学术研究》做了回应(11)。读了两位的文章,我觉得其中最为关键的话题并没有充分展开,甚至还衍生出了更多话题。如同解玉峰此前的批评文章所说的,《中国戏剧史》最值得讨论之处,在于他主张中国戏剧起源于农村的祭祀仪礼,除了这个观点本身是否正确以及周延,田仲先生何以会提出这样的观点,如何评价这一观点,进而如何评价田仲先生《中国戏剧史》的学术价值等问题,事实上变得越来越纠缠为一体;在解玉峰对田仲先生答辩文章的回应里,不仅没有将这个问题推进一步,甚至再明显不过地用“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得与失”转移和回避重点。因为田仲先生的学术失误并不在于他用民俗学方法研究中国戏剧,而在于他并不拥有解决中国戏剧起源这一复杂问题所需的学术积累和理论把握能力。这就使我觉得仍有必要正面展开看法。
还有一点不能不说,田仲先生在他发表在《学术研究》上的答辩文章里,认为解玉峰对他的批评,典型地表现出中国大陆诸多大学里的学者“以民俗学为禁忌”的学风,他以为解玉峰是因为排斥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方法,才拒绝接受他对中国戏剧起源的新见,这恐怕有极大的误解。恰好我也做过多年农村戏剧的田野考察,同样也非常关注民间祭祀仪礼与戏剧之间的关系,我得出的结论却与田仲先生截然相反。而我以对浙江台州民间戏剧演出的田野作业为基础撰写的《草根的力量——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与研究》出版后,意外地得到许多好评,多家高校与科研机构邀请我去就此做学术讲座,我在和这些重要的学术单位——包括田仲先生曾在讲演稿里激烈批评的解玉峰所在的南京大学——的学者们接触过程中,丝毫感受不到田仲先生所说的“以民俗学为禁忌”的学风。同样,田仲先生之所以在中国的各学术单位备受崇敬,不是由于他在戏曲史或戏曲理论方面的贡献,而恰恰就是因为他从民俗学角度考察当代乡村戏剧活动,为同时代的学人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经验材料。三十年前,田仲先生学术精力旺盛的年代,他的研究方法以及课题在中国大陆可能会遇到一些障碍,三十年后的今天还抱怨大陆的高校以及研究单位“以民俗学为禁忌”,就让人觉得有些恍惚,似乎他还沉溺于三十年前。事实上三十年来,中国学者在民俗学方面早已有不菲成果,即使以田仲先生研究的民间祭祀礼仪与戏剧的关系论,其涉及面之广,研究之深入,也早就远远超过了只局限于三两个村庄的小范围考察的田仲先生,更不用说中国戏剧起源的研究。我充分尊重日本学者在中国戏剧研究领域的成就,青木正儿、波多野乾一等前贤在戏曲及京剧发展史的研究方面有开先河之功,堪称相关学科的开创者。但大量中国学者对中国戏剧历史,毕竟已有近百年的研究,看不到这些成果的存在,要想在中国戏剧起源上做惊人之论,就容易信口开河,丧失一位知名学者起码的严谨。
诚然,解玉峰对田仲先生的批评文章里,或许确实流露出对民间文化以及对于诸多后发达地区文化的轻蔑之情,他对巫傩祭祀等等文化活动多少显得有些轻佻的评价,也值得商榷。解玉峰的文章里多断语而少论证,这当然是极不合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批评就不正确,轻率并不意味着错误,而且他的行文风格,也只是他个人学养所致。田仲先生对后学严加教诲,或许并无不当;然而,田仲先生因为受到一位青年学者的批评,就断言“中国的‘中国学’学者不喜欢人类学”,认为中国本身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大学教授”们“研究方法基本上集中于文献,而忽视或回避民俗学、人类学及基层社会的研究”,要借此教导所有“中国的‘中国学’学者”如何做“中国学”的研究以及如何参与“世界‘中国学’的对话交流”(12),那就有些不知所云了。我不幸恰好就是中国的一位研究“中国学”的大学教授,我不知道我的同行们如何面对,至少我个人对田仲先生的训斥,切切不敢领教。而这也是我撰写这篇书评的动机之一,我觉得中国的学者们在中国戏剧起源方面的研究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历史自有公论;哪些成果与观点能留传后世,时间会说明一切。
注释:
①钱南扬:《宋元南戏考》,载《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6月)。
②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史语所集刊》第7本第2分册(1937年)。
③吴则虞:《试谈诸宫调的几个问题》,载《文学遗产》增刊第5辑(1957年12月)。
④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第34页。
⑤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云贵彬、于允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页。
⑥田仲一成:《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3期。
⑦李家瑞:《由说书变成戏剧的痕迹》,《史语所集刊》第7本第2分册,1937年。
⑧⑨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第7页,第468页。
⑩周华斌:《神头鬼面——中国最早的脸谱造型》,载《文艺研究》2003年第5期。
(11)解玉峰:《民俗学对中国戏剧研究的意义与局限——兼答田仲一成先生》,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
(12)田仲一成:《献疑于以民俗学为禁忌的作风——就中国戏剧的发生等问题答解玉峰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