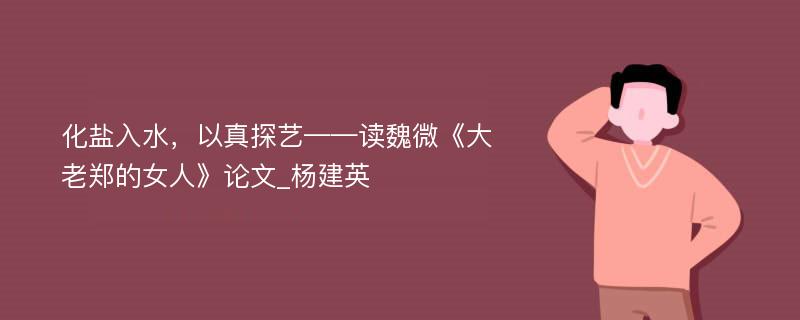
摘要:自1985年《日日新》在四川创办以来,“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在写作与评论中被认可,“技巧”与“真诚”成为衡量作品价值的纬度之一。洪子诚在提出“手艺”概念时说到:“开花是灿烂的,可我们要成熟”,其中的成熟便是对生活的深入体察,对文字书写的苦练沉淀,将自己当作“工匠”认真打磨写作“技艺”。以真诚对待生活,用技艺体现书写与心灵的紧密联系,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又一角度。本文试图从“技艺与真诚”出发,探讨魏微作品《大老郑的女人》中细密体贴的写作技艺,展现作者对生活与时间的真诚体味。
关键词:魏微;形式;内容
《青年作家》2019年第一期刊载了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对话录,王蒙在文章里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到这样一段话:“我的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也是我一贯主张的是:我对任何写作手法或方法都不承担义务。什么意思呢?用一个粗俗的比喻,就像打乒乓球,既可以打上旋球下旋球,又可以打削球。也就是说,一切方法、一切流派、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是为我所用的。我并不是为了创造一种风格而写作,而是用什么风格或手法能更好地表达,追求一种与众不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1]文学创作中形式与内容关系的议题,屡屡被人提及,各种观点都成为了老生常谈,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对作家的经验之谈加以重视。王蒙这段话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大诗人庞德一个诗学观点,即“技巧考验真诚”。面对青年诗人的追问“这30年来,你的兴趣却从形式转到了内容,这种转变有没有什么原则?”庞德回答说:“技巧考验真诚。如果一件事不需要花上技巧去叙述,它的价值就比较差。”庞德说:“我想人是以得天独厚的生活为题材的。我并不懂方法,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得多”,和巴金老人所说的“把心交给读者”,秉持着同样的文学信念,重视内心蕴含的容量大于作品外在的形式。
一、浅淡地叙述与细致的刻画
“修辞以立诚”,首先须丰富心灵的版图,其次是对内心进行打磨,以一定的形式将对外界的感悟耐心精心细心地诉诸笔端。古今中外文学有所成者,大都以其诚挚打动读者;玩弄技巧的风尚在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昙花一现。也有例外:运用技巧的能手王蒙,他的创作开国内意识流先河,但这些技巧的使用并不妨碍内容的表达,反而使他开拓出了创作的新境界。真诚行于书写,技巧考验真诚。一部耐人咀嚼的作品中,技巧之于内容,应如盐入水,饮水知盐品出咸淡,以达化境;而不是水中掺沙,硌人咽喉。
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便是这样一部“化盐入水”、咸淡适宜的作品。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技巧与内容相得益彰,是技巧化入了真诚的绝佳例子。读者很难不被作品叙述的调子打动。故事叙述清浅,使小说具有一种迷人的气质,将往事娓娓道来。跟随作者第一人称的叙述,读者仿佛置身到过去那个时代里的小镇。在那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小镇,每一位读者甚至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故乡小城的印记。小说描画了一个小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风习演变,细致地刻画了这一过程中的人情世故、人心冷暖。说故事的主角可以说是大老郑和他的女人,也可以说是小说的第一人称“我们”,更可以说是这个小城。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作者在写作上对风俗与人心的微妙变易、社会风尚和道德秩序的把握都极为敏锐,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活动、连续、渐变的风俗画片。小说要表达的是大的时代变迁下,生活的复杂和生存的艰难,人性的微妙,人和人之间的善意和误会、理解和不解。这里面涵盖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涉及婚姻、家庭与爱情,卷入社会风俗、世道人心、时代命运。一篇小说撬动了真实现实的许多关节,打开了隐藏在所谓的现实下暗涌的征象和心象。我们会发现,好的作品都有一种特质:不离开以爱情为基础的家庭的书写,擅长以婚姻破裂和爱情的分合为潘多拉宝盒来撬开社会和时代风云的变动,用微妙人心印证宏大时代,像《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就是此类作品。
二、小人物的日常与大时代的变迁
这里面当然也有技巧的。正如臧棣所言:“写作就是技巧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从而在新的语言肢体上使之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3]“大老郑和他的女人”,这带有晦涩暧昧的感情故事绝不死作者的唯一想要表现的。作者将他们置于时代的现场,是要通过这一对露水夫妻,切入时代的脉搏,给时代的世风人心进行把脉。借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写出时代的变迁,这是一种高明的手法。社会总归是由无数的普通人构成,在辉煌的幕后是无数小人物的生存和挣扎。避开隆隆崛起的时代的亮光灯,转而把视线投注在小人物、小夫妻身上,这是作家的人文情怀,是作家的悲悯情怀。整部作品里作者的情感隐藏在行文中,对大老郑和他的女人、对整个流变的社会给予了耐心的理解和真挚的同情。所谓心诚则灵,这正是作家的心灵的微光照亮在被遮蔽、被删除的人物身上。我们也可以说,这样的取景,这样的布局,是作者有意为之的。但是读完小说,淹卷深思,仿佛能听到作者的声音说“我只能这样写,因为我的心就是这样”。读这样的小说,我们感觉文字仿佛从作家血管里流出来的,叙述的音色蕴藉着作家的心声。作者不设立道德裁判所,只是真诚地讲述。其中仅有的道德的评判,来自“我”的母亲,但作者并没有下定论。这个时代太复杂,有太多问题值得去深思,小说正是这种思索的产物。比之于道德的简单归类,个人的生命、生存更加丰富而复杂。去正视去关注他们的悲哀与幸福,这是一种诚与真的心灵向度。这不禁让人觉出文字美妙、神奇所在。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一篇文章,具有洗净人心灵的魔力,何以故,源于作家心灵的洁净。
有研究者指出《大老郑的女人》并存着两种时间观念:“一种是停滞的,一种是上升的。前者来自日常生活的舒缓节奏,后者源于现代化的高速进程。魏微以高度自觉的时间意识,揭示了八十年代新旧交错的时代特征。在这一过渡时期,农村停滞的日常生活受到巨大冲击;而生活方式的变更、传统家庭的松动、婚姻与爱情的错位,则表明农民向非日常生活主体转换的复杂艰辛。小说采用双重视角,既有利于展示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又造成了杂语共生的复调效果。”[2]这样的设置当然是出自作者精心的构思。作者出生于江苏小城,江南沿海省份的地缘优势让其中的人们更易于接触到时代变迁的足迹,她经历过这样的变迁,对日常生活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奏有深切的体知,因此才能敏锐地把握两种时间观念的交错,创造出一种复调的效果。其实小说不仅只有两种时间观念,还有两个家庭的对照,两个女人的对比,“我的”态度、父与母态度的差异,小村生活与小城故事的映照,半新半旧的生活比对,以及对大老郑女人前后反应的写照等等,这些都是写作技巧的运用。这些手法的运用,让我们更清晰、更全面地了解了作为小说主角的“小城”的生活实景,增加了我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实感体会。小说采取了倒叙的视角,将我们的视野与当时的情景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营造出疏离感受。时代毕竟在发展,大老郑和他女人的露水情缘也许成为历史的遗响,但更是一种联系。它似乎预示着未来时代发展的迹象,将我们与过去的人事接连起来——“十几年前的事”与作者、读者在场的此时此刻沟通起来了。小说的根扎进了时间的泥土里,它的枝叶或许伸向了我们生活的天空。
三、埋头拾取生计与抬头寻找幸福
小说探讨了王安忆特别重注的生计的问题。她曾提出小说中“生计”的概念。“小说中的‘生计’问题,就是人何以为衣食?我靠什么生活?听起来是个挺没意思的事,艺术是谈精神价值的,生计算什么?事实上,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内容。”[4]一个人如何生存,又该如何幸福地活着?当幸福生活实现的方式与道德良俗发生正面、激烈地冲突,该如何面对与处理?正如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思索的,个人的幸福被整个社会所击败,最后破灭了。《大老郑的女人》所追问的是很深刻的,而它以“大老郑的女人”为题也体现了作者的关怀视角。大老郑为家人生存计,远离家乡外出务工,生活孤单清冷。与大老郑生活在一起的女人为着同样的原因,与其展开一段秘密、暧昧的同居生活。远离家乡相互扶持与照顾的两人,让两个家庭演变成“三个”家庭。故事随着“女人”丈夫的寻找落下帷幕,隐入夜色。让人深思的是,两个家庭的困顿、“三个”家庭的饱足与正常道德良俗激烈碰撞下,究竟那一方会赢得更多的谅解?这正是作品迷人的另一个地方,生计与生活如一棵树上的藤蔓,各自生长却纠缠在一起。正如王安忆所说,“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内容”。
小说的开篇尤其吸引读者的注意:“原来,我们这里是很安静的,街上不大看见外地人”,“时代的讯息像风一样地刮过来,以它自己的速度生长,减弱,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移风易俗的,改变众人命运的究竟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似乎隐隐感到一点生机的存在。生命具有的伟力是任何外在的东西不能抹杀的。这就让我想到作品的生命不因外在的形式而衰弱,它能经受技巧的考验。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时常反问自己的心灵是否足够真诚,这真诚是否能够经受考验,而他的心灵是否丰富广袤到能够与时代的命运相沟通?有了这样的前提,技巧才能入盐化水,实现作品的百般滋味。
技巧是对真诚的考验。排在第一位的是真诚,是一个作家内心想要表达的内容。文学是心灵的产物,一个人内心的宽广决定了文学作品在探索中走得能有多远。“一切方法、一切流派、一切对风格的追求都是为我所用的。”[5]技巧都是为内容所用,没有真诚的内心,技巧便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只是虚有其表的炫技。心灵的言说需要文字的载体,用文字写下内心深处对生活的领会,却也有必要采用一定的艺术技巧,不同的表达内容最适宜的表达方式,正如每一颗种子有适宜它的土壤。艺术家对技巧的追求,是为了使得表达效果更加贴合真诚的心灵,但如果过分重视技巧,就会成为一种僭越,结果只能是形式大于心灵。技巧考验真诚,这句话包含了意思的另一面,就是把技巧当做对真诚的必要锤炼。“如果一件事不需要花上技巧去叙述,它的价值就比较差。”庞德这句话揭示的,是一定内容的表达需要一定形式作为承载。正如魏微在《大老郑的女人》中所呈现的复调叙述与情理冲突。而所谓技巧,对于文学作品而言,大到文章的结构布局和内在氛围,小到下笔的用词和叙述的语气,都属于技巧范畴,这些元素的有机组合会给作品带来质的变化,正如古人说的“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如果内容不能经受一定形式的考验,说明内容还不够真诚,而技巧的运用,恰恰可以使作者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发掘出真正有意义的心灵内涵。因此,我们也不必畏惧技巧,只需把技巧当做对真诚必要的考验。让技巧融入真诚,如盐化水。
参考文献
[1]王蒙,张英:人生再艰难,文学仍在场.《青年作家》[J].2019(1)
[2]洪子诚:诗人的手艺概念.《文艺争鸣》[J].2018(3)
[3]瞿天铖:借日常生活写时代变迁——《大老郑的女人》的文化哲学解读.《名作欣赏》[J].2006(14)
[4]王安忆:小说中的生计问题.《小说选刊》[J].2016(5)
[5]王蒙,张英:人生再艰难,文学仍在场.《青年作家》[J].2019(1).
作者简介:杨建英(1989.08-),女,江西赣州人,江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论文作者:杨建英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0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11/12
标签:技巧论文; 大老论文; 真诚论文; 小说论文; 王蒙论文; 时代论文; 作者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1月50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