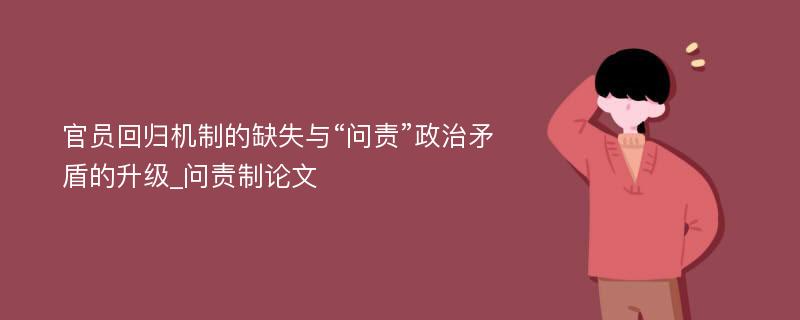
官员复出机制缺失,“问责”政治矛盾升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官员论文,矛盾论文,机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责的显性政治矛盾升级
2009年3月因三鹿奶粉事件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早在2008年就调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行政级别也从副厅级升到正厅级。同月被给予行政记过处分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也早在2008年11月从河北农业厅调任邢台市市委副书记,并在2009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而在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邢台市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正职领导未有变动的痕迹。
三鹿奶粉事件中的问题官员赶在问责之锤落下前异地高升,击破了先问责后复出、在复出时降级或平级换岗的最低社会共识底线。
围绕问责官员的“复出”,民间质疑之声铺天盖地,尖锐度骤然升级。而与此同时,山西省太原市一位官员则表示,官员内部对“问责”的意见也越来越大。于是,意在使吏治进入能上能下的官员问责制进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不严厉实施问责制度,往往受到舆论的反对,并助长不负责任的风气;严厉实施问责制度,又容易出现问责过分的问题。如果受责官员不能复出,问责制会受到极大的内部阻力;如果受问责官员复出,则问责制又会被疑为形同虚设。
身陷问责风暴的官员已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2003年以来,仅被媒体报道的问责官员累计就近5000人次。另据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办的数据,2005年各级监察机关对滥用权力、谋取非法利益的47306名行政官员给予政纪处分;2006年,全国共追究执法责任9万多人次;2007年近6万人次被追究责任;2008年全国主要行政执法部门被追究责任的更是多达约8万人次。如何处置逐渐庞大的问责官员群体,成为一大显性的政治问题。
官员复出机制亟待建立
问责制度本身并无意将受责官员打入冷宫。早在2002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成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而按照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规定,公务员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6个月、记过12个月、记大过18个月、降级撤职处分有效期两年。
“干部是党和国家多年培养出来的,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如果轻易废弃是损失也是浪费。因此从组织工作来说,通常的想法是干部应以教育保护为主。”一位地方组织系统人士介绍说。
但在实际操作中,问责官员的复出与其被免的时间间隔多数并未超过一年。或许意识到了舆论可能的压力,官员的复出总是显得极为低调。披露他们复出的消息多是媒体的报道,而非组织人事部门的任用公示。
“这是一个非正常现象,问责官员的每一次复出之所以容易引起争议,引发民意反弹,主要是因为民众对官员复出的原因、条件和程序不清楚,觉得有暗箱操作的嫌疑。”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
而复出的非公开化进行本身也无章可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目前尚无关于官员复出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的规定,也显得过于模糊。这使本是问责制度化、常态化不可或缺的官员复出机制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随着社会舆论对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高度关切,汪玉凯猜测可能出于“保护”不错干部的目的,复出方式不得不走形。于是出现了鲍俊凯和刘大群在遭问责前就异地高升的新模式。
“现在是到了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的时候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通过建立规范透明的复出制度,让民众清楚知道什么情况的人可以复出,其复出的依据在哪里,这才是平息当前社会争议的必由之路,也是对复出官员的一种更好的保护。
问责基础之失
官员复出的隐蔽化源于前一环节——官员问责的隐蔽化。建立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是廓清官员的职责、构建相应问责程序。汪玉凯直言:“没有当初事件中官员职责不清和问责机制的简单粗糙,就不会出现如何复出的麻烦。有些官员被问责是替别人或集体扛的,但你能这么跟社会说吗?”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汉宇2008年带领民建中央行政问责制课题研究组调研事故频发地山西后发现,事故发生的职责划分很不清楚,官员被问责具有模糊性和牺牲性。李汉宇说,没有明确责任划分的问责制度不仅是一种摆设,而且容易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长期以来,中国治国基本靠出台红头文件,这在具体落实时很难把一个责任通过法规规范或法制落实到每一个具体层面。结果就是一般由各级的最高行政领导确定是否要问责、力度如何、什么样的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而各级最高行政领导的判断更多是出于一种对形势的政治性判断。这使得问责不是依据失职情况和错误大小,而是取决于媒体与社会的关注程度。
在一些地方,党政官员虽然非常重视安全生产责任,但却无职无权,因此在提高安全生产方面难有作为;部分官员虽然具体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但却缺乏必要的人事权和财权,很难改变生产现状。探究更深的原因,安徽省巢湖市政协秘书长叶铭葆将之归结为整个官制设计中存在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称问题。这种不对称使问责失去了科学的评判标准,造成问责的随意性和选择性。
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党委掌握人事任免权,行政首长对不称职的部下难以采取组织措施,这导致政府的责任与权力不对称。此外,在政府班子内部,也是集体决策,分头办理。这种领导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即使是行政一把手,在讨论问题时也要注意听取班子成员的意见。同时,作为分管某方面工作的班子成员,虽然可以就所分管的工作提出处理意见,但这些意见能否被采纳,则要取决于集体讨论的结果。在此种情况下,难以准确认定问责的对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称,问责被滥用不是最危险的,最怕的是责权利不均衡,使问责制失去实施的合理性基础。
将问责纳入程序化
“责”只是“问”的基础,如何“问”也需要一套标准和程序来加以保障。但目前对于政策决策失误和失职、渎职、滥权达到多大程度,造成多大损失即应承担多大责任,相应事件、事故导致多大损失等事项尚缺乏可供一致遵循的标准。大多数地方或部门只有当事件引发强烈的舆论关注并引起领导重视时,问责才进入实施。对此,李汉宇直批现在的问责制正在走向情绪化和不确定性的错误方向。
由于问责规则的后置性导致被问责人承担政治责任或者其他责任的,被问责人通常不易接受。这也是公共事件中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最初原因。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一部专门的行政问责法律。不过1997年以来,各地政府已经自行展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制及推行工作,着力将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责任追究机制引入行政管理之中。但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程序以及责任形式等方面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打个比方,同样是开会打瞌睡,在四川会被记大过,到云南就会被免职,到上海就只谈谈话。如此,被问责的官员肯定会觉得不公平。
目前,民建中央已将提案和意见提交中央有关部门,建议尽快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制定“行政机关公务员问责办法”,由国务院公布施行。
对于全国性的问责制,姜明安提醒说,对官员启动问责,一定要满足时间性条件。“干部对工作和下属的熟悉需要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设置因管辖范围大小而不同。比如说省级领导应该入职半年至一年,市级领导应半年,县级领导应三至六个月”。同时,要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影响大小来决定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级别,比如特大事故追责到省一级或者地市一级,重大事故追责到地市一级或县一级等等。
汪玉凯认为,一旦启动问责,就需遵循质询、责任认定、检讨、道歉、请辞、免职等操作程序,以保证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进行。由于问责对行政官员的仕途影响极大,需要给予被问责官员申辩的机会,而且申辩的内容应当记录并作为处理的重要依据。同时还应当完善相应的救济程序,例如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等。
官员被问责后,其具体的“复出”可分类设计。华北电力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谭琪提出两分法:对因违反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失职,对重大事件有直接责任的官员,不予“复出”;因工作不力、失误或人民群众不满意引咎辞职的官员,应建立跟踪、考评机制,以一年为“复出”的基本年限,按照群众意见、复出条件和法定程序(标准)等步骤,公正公开地“复出”。学者们还建议建立官员复出回应机制,实行决策承诺制、决策公示制,通过社会调查、听证制度等完善复出制度的法制化,建立公众-回应载体-政府-公众的回应流程系统。问题官员在群众认可的基础上,依据回应流程系统向群众做复出程序说明。
问责主体缺位
针对目前行政问责基本上采取行政系统内部问责的方式,日前民建中央提出了完善党委系统问责制的建议。李汉宇说,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之间的责任承担目前没有透明合理的判断依据。而只有执政党及其官员在责任体系之内,才有可能实施严格意义上的问责制。
相关统计显示,官员问责事件中99%的启动者为上级党政部门,而由人大启动的法律问责基本没有。这种依赖行政等级权力的问责制使行政运行高负荷运转,也使其他资源处于闲置状态。
一个社会的良性治理依赖于政治-行政二分,政治对应民意,行政对应问责。不过汪玉凯认为,这种“问责”只能局限于恶劣后果出现以后的官员处理,而不可能到达所有的权力行使过程。过于依赖结果性“问责”,一方面难以改变不出现恶劣后果下的权力无责任状态,另一方面也会积累官方和民间更大的矛盾。
(摘编自《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