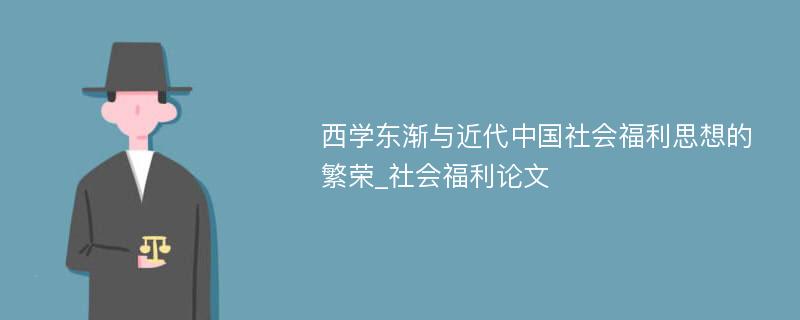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学东渐论文,社会福利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4-0120-07
19世纪中叶,西洋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闭锁已久的国门,从此,中西方间的接触和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充满着“血与火”的冲突和震荡中,自18世纪中叶清政府实施“禁教闭关”政策后中断的“西学东渐”进程,又重新开始启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近代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对鸦片战争惨败的痛切反思,很快就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不仅仅靠先进的武器装备,在“利炮坚船”的背后,还有制度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初,很多进步思想家逐步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制度有着密切关联。以此为契机,他们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并未给予足够的研究和关注。故本文试结合19世纪下半叶西学东渐的具体过程,对中国近代社会福利思想勃兴的轨迹做一初步的研究探讨。
一
所谓“社会福利”,主要是指政府、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了帮助社会成员解决困难,满足其物质及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相应的服务,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主要包括公共福利设施、少儿福利、老年福利、妇女福利、残疾人福利、慈善事业、社会救济等内容。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福利制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一经产生,便对稳定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研究和关注。具体观之,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中西文化的初步接触和交流为前提条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冯桂芬和太平天国的著名政治家洪仁玕,率先介绍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情况,并主张在中国实施。
从历史上看,在中西接触之初,国人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视西人为野蛮落后的夷狄,耻于师法学习。到了五六十年代,随着中西方国家间进一步的接触和交流,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封建士大夫率先突破了“坚船利炮”的认识范围,由“制洋器”转向“采西学”,敏锐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决不仅仅表现在“器物技术”领域,遂开始把目光投向“社会”层面,以探寻西方强盛之本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冯桂芬和洪仁玕。冯桂芬曾撰文专门评述介绍荷兰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写道:“荷兰有养贫、教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入养局,廪之而已。[1](P54)在他看来,向来被传统士大夫视为落后野蛮的“夷狄之邦”之所以能够打败堂堂的“天朝上国”,决非仅仅靠手中的“利炮坚船”。在先进武器的背后还有“制度”因素在起作用,前述的收养贫民的社会福利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由此,冯氏开辟了从“社会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强盛本源的新路径。
与冯桂芬同时代的洪仁玕,由于其游历香港的特殊经历,使他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有了更为详尽的了解和认识。他在《资政新篇》中提出太平天国应该学习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举办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同时,还应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他设计规划兴建医院,引进西医,以解救百姓的疾病之苦。从《资政新篇》的整个体系和内容看,它所涉及的社会福利的文字虽然并不多,但它却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介绍了西方社会福利事业的基本情况。
第二阶段:19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自强运动的进展,中西接触更为频繁,在出洋驻外公使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笔下,对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了更为详尽的介绍。
在这些出洋者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关于西方社会“贫孩院”、“养老院”、“贫民医院”等福利保障制度规定及实施情形的记载。如清朝驻英国公使馆副使刘锡鸿在其出洋日记中即把英国政府的一些福利政策称之为“养民之政”,大加褒扬,说:“(英)人无业而贫者,不令沿街乞丐,设养济院居之,日给飨餐,驱以除道造桥诸役。故人知畏劳就逸,转致自劳而自贱,莫不奋发以事工商。国之致富,亦由于此。”[2](P95)同时期随郭嵩焘、刘锡鸿赴英的翻译官张德彝则对英国社会福利慈善事业的筹款办法比较关注,写道:英国的慈善医院的“各项经费,率为绅富集款。间有不足,或辟地种花养鱼,或借地演剧歌曲,纵人往观,收取其费,以资善举。”同时,他还注意到志愿者在慈善医院中的作用,即“各院医生固皆善人,即扶持病人者,亦皆善男信女愿为供奉者。”[3](P427)郑观应也说“夫泰西各国乞丐、盗贼之所以少者,岂举国皆富民而无贫民哉?好善者多,而立法綦密,所以养之者无不尽,所以恤之者无不周耳。”[4](P527)与前一阶段相比,此阶段对西洋社会福利制度的介绍多系直接的见闻,其描述更加细致,影响也更为广泛。
第三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戊戌变法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和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也结合其海外经历,将西方社会福利观与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相结合,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
康有为在其变法富国论和理想社会论中,都提出了系统的社会福利主张。他认为救国必须从“扶贫救弱”开始,只有国民走出“穷弱”,国家才能变得强大起来。在《大同书》当中,他更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认为只有建立“公养”、“公教”、“公恤”的福利保障制度,人类才能真正地走向大同。而孙中山则在三民主义中,集中阐释了“民生”的含义,构想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福利保障社会的蓝图,在这一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5](P89)代表了中国人民对理想大同社会的强烈渴望和向往。
二
作为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制度的回应,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近代中国思想界提出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思想主张,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其具体观点主要有:
首先,从中西社会比较入手,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
就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的总体特征而言,大部分思想家的社会福利思想主张都带有典型的“宗族福利保障”色彩。从孟子的井地模式,到龚自珍的“农宗论”,莫不是以宗法家族为社会成员间相互救助的基本单位。这种“宗族保障模式”虽然有其温情的一面,但它与近代社会制度化的保障制度相比,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近代中国思想家正是从中西比较研究入手,对中国传统“宗族保障”的狭隘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
率先对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模式的狭隘性提出了激烈批判的是郑观应,他认为,西洋慈善机构的建立,有其现实的思想基础和社会条件。一方面,西方民众信奉基督教,主张“兼爱”,这为民间慈善机构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素有慈善捐赠的社会风气,有些富翁往往独自捐资数十万,以行善事。他说:“西人遗嘱捐资数万至百数十万者颇多。闻英人密尔登云:英国有富家妇,夫亡遗资甚多,其创立大小学堂、工艺书院及置穷人贩卖零星物件之地,共费银一千五百万镑。”而相比之下,“中国富翁不少,虽身受国恩,而竟未闻遗嘱有损资数万至数十万创一善事者,宁愿留为子孙花费,殊可慨也。”[4](P526)
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则是在系统比较探讨中西社会福利思想不同特点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宗族福利保障”模式进行了总体性评判。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宗族保障模式”具有偏狭性的弊端,即:“就收族之道,则西不如中,就博遍之广,则中不如西。是二道者果孰愈乎?夫行仁者,小不如大,狭不如广;以是决之,则中国长于自殖其种,自亲其亲,然于行仁狭矣,不如欧美之广大矣。仁道即因族制而狭,至于家制则亦然。”[6](P173)而其偏狭弊端的具体弊害主要表现在:(1)“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得公费以多养医生,以求人之健康,而疾病者多,人种不善。”(2)“人各私其家,则无从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3)“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抽公费而办公益,以举行育婴、慈幼、养老、恤贫诸事。”(4)“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得公费而治道路、桥梁、山川、宫室,以求人生居处之乐。”[6](P189)在这里,康有为把封建宗族保障模式与宗法家族制结合起来进行批判,主张打破家族的藩篱,追求公众的“大福利”,表现出他激进的反封建思想和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决心。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宗族保障模式”行“仁爱”不够广博,只是局限于“自亲其亲”的范围内,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
康有为还分析了中西方社会福利保障模式差异的原因,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西社会的凝聚模式不同,即“欧美人以所游为家,而中国人久游异国,莫不思归于其乡,诚以其祠墓宗族之法有足系人思者,不如各国人之所至无亲,故随地卜居,无合群之道,无相收之理也。”[6](P171)正因为欧美人重国家,轻宗族,所以才会捐千百万金钱,建立学校、医院、恤贫院、养老院等社会福利机构,使整个国家中的贫穷者受益。而由于中国人重宗族而轻国家,其社会福利善举只局限于捐祖堂、义田、义庄以恤贫兴学,只是荫其宗族而他族难受其惠,抚恤对象是宗族而不是国人。这种宗族保障模式的直接流弊,便是中国人手足不能相救,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贫弱。
其次,综合中西社会福利思想,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
在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系统的社会福利保障方案的是洪仁玕。他所设计的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等社会福利事业和机构,其经费不是靠国家出钱,而是靠私人捐献施舍来兴办。他说:“兴医院以济疾苦,系富贵好善”,“兴跛盲聋哑院,有财者自携斧资;无财者善人乐助。”[7](P525)很显然,他所设计的社会福利机构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慈善事业为蓝本提出来的。他还建议设立“士民公会”,以监督社会福利事业的正常有序地运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康有为、孙中山也试图将中西社会福利思想结合起来,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在中国这样土地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进行“扶贫济弱”,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移民垦荒;2.劝工警惰,即令各州县设立警惰院,收留无业游民和有劳动能力的乞丐,进行职业教育,使这些人能够自食其力。穷者得食,社会自然会走向安定。3.恤鳏寡孤独。各州县筹集款项,设立善堂,对社会上的鳏寡孤独、盲聋残疾等的生活困难和生理有缺陷者,实施救助。
而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社会福利主张:1.救济工农。他说:“德国当俾斯麦执政的时代,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做工时间是由国家规定了8点钟;青年和妇女做工的年龄与时间,国家定了种种规定,要全国的资本家担任去执行。”[8](P372)2.安老怀少。孙中山认为:“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9]((P36)他还把“安老怀少”作为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来看待,说:“实现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10](P523)在1924年制定的《建国大纲》的第11条中,规定将土地、山林川泽、矿产等收入,都归地方政府所有,“而用以经营地方人民之事业,及育幼、养老、济贫、救灾、医病、与夫种种公共之需。”[11](P570)在上述种种社会福利项目中,将养老放在前列。体现了孙中山对“安老怀少”问题的重视。
再次,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中西合璧式的乌托邦方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在康有为设计的“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组织中,所有的社会福利事业都由社会公共机构来承担,主要包括“公养”、“公教”、“公恤”[6](P280)三个方面:1.公养机构。康有为认为,大同世界的成年男女,自由婚姻,定期同居,届时需易人。妇女怀孕后入公立政府组建的“人本院”赡养,实施胎教。婴儿出世后一律由公立的“育婴院”、“慈幼院”抚养。2.公教机构。在大同世界,儿童6岁入“小学院”,11岁入“中学院”,16岁入“大学院”,20岁毕业。经过长达14年的义务教育培养,使每一个年轻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专门的技术训练,可以凭借其专长去为社会服务。3.公恤机构。人如果患病或因工作受伤致残,可以进入社会举办的“医疾院”,得到精心高超的治疗。人到了晚年,则可进入社会举办的“养老院”、“恤贫院”,受到“公恤”,在这里老人可以欢快地度过晚年。通过上述的“公养”、“公教”、“公恤”等社会福利机构,人类社会便可以达到幸福快乐的大同之世。
孙中山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福利保障社会。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同盟会宣言》中,对平均地权的方法作了以下的解释和规定:“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2](P297)按着上述原则进行操作,经过“核定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涨价归公”等步骤,实现了土地国有化,消灭了贫富分化。此外,由于革命成功和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地价不断上涨,涨价部分全部归国家所有,为国民所共享,这样就可以废除一切捐税,只保留地租一项,百姓就已经是用之不竭了。即实行单一税后“现今苛捐尽数蠲除,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12](P329)可见,孙中山构想了一个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福利保障社会,这反映了中国人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和大同世界的强烈渴望,也代表了先进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尖锐批判,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到地位。
三
19世纪中叶以来,国人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接受之所以如此迅速,其原因极为复杂,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同思想和民本思想的某些“暗合”式的联系。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其最高的社会理想境界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因此,在近代,当中国士大夫初见西方社会福利制度时,都情不自禁地以“西学中源”的思维模式,将其视为是中国古代圣人的社会理想在西洋的翻版。晚清驻英公使薛福成在英国曾赴一贫孩院参观,他发现“院中男女孩凡三百余人。……俾能自给衣食,无饥寒之虑焉。吾不意古圣先王慈幼之道,保赤之经,乃于海外遇之也。”[13](P611-612)据此,薛福成称西洋社会“绰有三代以前遗风”,“不甚背乎圣人之道。”[13](P272)郑观应也认为西方的福利慈善事业“意美法良,实有中国古人之遗意。”[4](P526)孙中山更认为:真正的民主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是蕴藏于中国传统中,寄“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14](P25)很显然,在他们看来,既然西洋社会福利制度与“三代圣贤之道”是相通的,那么学习之,赞叹之,都是很自然的事情。
二是西方文明的示范作用。在中西方接触之初,国人仍视西洋为夷狄,不屑一顾。但无论是驻外公使亲临西洋,还是开明士大夫从书本上管窥西方,都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中西文明强烈的对比之下,虽然仍有部分士大夫顽固坚持“华夷之辨”,拒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性,但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却逐渐开始面对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并主张向西方学习。晚清首任驻英副使刘锡鸿本是一位力持“用夏变夷”的保守派代表人物,来到英国后,曾数次参观伦敦的养老院、孤儿院、养疾院等社会福利机构。惊叹之余,感到所见实在难以置信,认为在伦敦官方的安排导引下“公往”参观,官方部门很可能预先告知这些部门洒扫庭院,难免失真。一次,他特意未经官方安排,“私往”伦敦城内的野士凌墩养老院游览,结果所见依然如故。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今西洋之俗,以济贫拯难为美举,是即仁之一端;以仗义守信为要图,是即义之一端。”[2](P129)在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性初步认识的基础上,此时期的思想界主张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作为一种先进的制度引进,以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在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将社会福利问题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认为中西社会强弱盛衰的原由虽然有很多,但民之富强的程度应是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薛福成在《出使日记续刻》中,曾将西方富强的原因归因于“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等五端,其中,“保民生”主要是指“凡人身家田产器用财贿,绝无意外之虞。告退官员,赡以半俸;老病弁兵,养之终身;老幼废疾,阵亡子息,皆设局教育之。”[13](P803)力倡给民以充足的社会福利保障。在他看来,要想强国,必先富民,很难想象,一个哀鸿遍野、乞丐遍地的国家能成为富国强国,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其次,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它第一次对传统的宗族福利保障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反思。如前所述,中国传统社会福利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族福利保障”特点,很多封建士大夫在封建统治陷入危机时,往往都以此作为救世妙方。鸦片战争前夜,被称为近代第一位思想家的龚自珍所提出的救世方案即为“农宗论”。19世纪50年代,冯桂芬虽然对荷兰的“养民之政”大加推崇,但当他直面中国社会时,提出的济世药方仍是“复宗法”。而真正对传统的宗族福利保障模式提出深刻反思批判的,还应首推郑观应、康有为和孙中山,他们试图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新的社会福利保障模式,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
收稿日期:2001-03-10
标签:社会福利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孙中山论文; 冯桂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