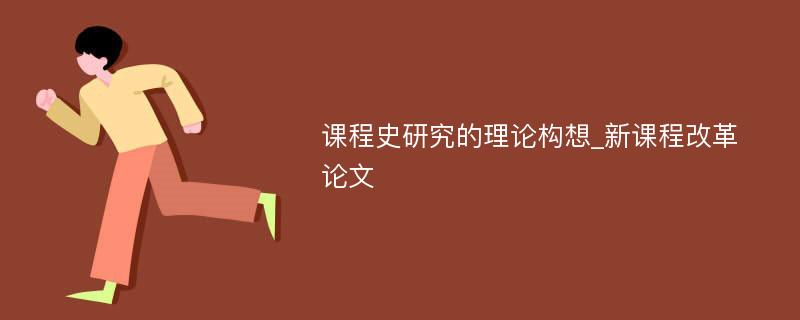
课程史研究的理论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国家就不断地有课程史研究的成果出现,60年代以后,课程史的研究更是成为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我国,关于课程史的研究则长期处于学科边缘或者是自发状态。下面就为什么要研究课程史及如何研究课程史提出本文的思考,以就教各方同仁。
一、课程史:课程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世界课程史研究进程与我国研究的迟滞
20世纪早期,英美国家关于课程史的研究实际上就已经开始起步。关于19世纪和更早期的美国学校课本的资料可以在1904年Johnson和Littlefield的著作中找到,在英国的Foster Watson的评论中也可以找到英国现代学校学科出现的踪迹。而关于美国19世纪课程历史的概览性描述则包括由国家教育研究协会(The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NSSE)1926年出版的《第26年书》(The 26th Yearbook),之后还有类似的1933年出版的《第32年书》(The 32nd Yearbook)和1945年的《第44年书》(The 44th Yearbook)。二战期间,课程史的研究有一个短暂的停顿期。到20世纪60年代,英、美等国的课程史研究取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
这个时期关于课程史研究的重要事件是协会的创立、期刊的兴办和一批著作的出版。例如“大英教育史协会”成立于1967年,来年即出版通讯,1972年即出版期刊,从此以后课程史研究找到了发声途径。此外,该协会更举办了三个课程史的年度研讨会,其中出版了两本专书,分别是1971年的《变革中的课程》(The Changing Curriculum)和1979年的《战后课程的发展:一个历史的视角》(Post-war Curriculum Development:A Historical Appraisal)。在这期间,其他研讨会的部分个人文章也于1975年结集出版,名为《学校课程》(The School Curriculum),该协会亦于1974年组成课程史经典研读小组。同时,课程研究期刊《Journal of Curriculum Studies》创立,收录学者对于英国的课程发展、中等教育阶层的课程系统,以及课程领域的各种层面研究的论文。
而在美国,Gremin(1961)的《学校的转型》(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和Krug(1964)的《美国高中的形成》(The Shaping of the American High School)以及全国教育研究协会第26期的年刊《课程结构的基础和技巧》(The Foundation and Techniqute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这些作品被视为课程史领域研究的开始。[1]随后,哥伦比亚师范大学巴拉克(Bellack)教授于1969年发表美国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论文《课程思想与实践的历史》(History of Curriculum Thought and Practice),指出现行的课程研究缺乏历史视野,要求课程学者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课程,被认为是课程史作为学术领域的最早明确认定。[2]巴拉克的论文变成讨论课程史研究的起点,因为他为课程史研究划定了界线。1971年美国全国教育研究协会出版了课程研究的《第70年书》(The 70th Yearbook),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战后的课程发展。同时,北美的安大略教育研究所(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出版了两份期刊:《课程理论网络》(Curriculum Theory Network)和《课程探究》(Curriculum Inquiry),对美国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课程改革也有探讨。坦纳(Tanner)、卡斯维尔(Caswell)等课程学者都开始课程史领域的研究工作,巴拉克的学生克里巴德(H.M.Kliebard)更是这个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1986年,克里巴德出版经典名著《1893-1958年的美国课程斗争》(The Struggle for the American Curriculum:1893-1958),1990年,坦纳也出版《学校课程史》(History of the Curriculum),使得美国课程史的研究真正进入成熟阶段。
1977年,经过坦纳、卡斯维尔和巴拉克等人的积极奔走和筹备,美国的“课程史研究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urriculum History)成立。1975年在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增加了两个部门:“课程与目标”和“历史与史学”,以用来资助关于课程历史的研究。
在我国台湾地区,钟鸿铭教授、白亦方教授、欧用生教授等也都在关注并研究课程史问题,白亦方教授出版了《课程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很多学校的教育(课程)系所的博、硕班都开了课程史研究的课程。相比较而言,大陆地区的课程史研究尚处于比较自发的状态中。说是自发状态,也就是有一些课程学者开始在关注并提出要研究课程史,比如较早期的吕达先生出版了课程史研究的专著;《中国教育学刊》2007年第5期刊出的任平博士的《不能忽视和懈怠的主题:课程史研究》,提出要研究课程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1期刊出的何珊云博士的《课程史研究的经典范式与学术意义》;《全球教育展望》分别于2011年第8期、2012年第3期和2012年第4期刊出了吴刚平教授和余闻婧博士的《我国古代书院的“道——化”课程思想》、吴刚平教授和夏永庚博士的《学业考试为主课程评价制度的古典遗产与现代形态》和陈华博士《西方课程史的研究路径及内涵探析》等,以及一些其他散见的课程思想史研究文章,都开始在关注课程史及其研究问题。但从课程理论的整体研究层面来看,课程史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水平还是在成果方面都还非常的薄弱与不够。
(二)课程史研究的学术意义
正如杜威所言:“没有协调和连贯,事件就不是事件,而仅仅只是偶发。假如过去有任何意义,则必须和现在做协调。颠倒过来也是真的:(那就是)现在必须和过去相联接。”[3]杜威已明确地指出,任何事件的发生和发展,都肯定是受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孕育和限制,不管成功或失败,都必将对后续的历史发展产生影响。教育及课程领域的事件及改革也无不如此。但为何要研究课程史?其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
台湾课程学者杨智颖教授2003年在总结概括很多专家的主张基础上,概括出课程史研究如下七点意义:提供课程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复杂关系;探讨社会脉络之间的关系,以检视某一特殊时期的课程是如何被教,为何要教,为何只在某些地区被教,以及为谁的利益而教;提供学科或功课表之正式结构背后的人类活动过程与动机;提供我们对于目前所评价的课程发展模式有所了解;提供现在及未来课程研究与实践的借鉴;协助我们了解已界定之专业与个人生活的传统;理解过去的课程是如何限制目前的课程发展。[4]
在此,本文主要总结出课程史研究价值的两个核心关键词,即“理解”和“借鉴”,并分别作出说明。
1.课程史提供理解课程现象与问题的完整图像
“课程史是一种实践的(Practical)过去。”[5]我们今天在课程领域当中碰到的很多的现象与问题在过去说不定也存在过、发生过,那么透过课程史这样一个“第三空间”,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的课程现象与问题。“所有的历史不可避免地都是当代史,历史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处理目前情境的目的而撰写。”[6]
课程史毫无疑问属于历史,而历史的撰写是今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所从事的叙述、分析与批判。一方面,需要尽可能地去呈现事实,但也会渗透作者自己的主观意识形态。同时,更多的意图应该是“以史观今”和“学史明智”。通过这样历史的跨时空的叙述,可以将人的视野拉入到一个历史的时空镜头中,去看待、认识、分析、批判、解决某一些现象与问题,可以获得比常规思维更多的思路与方向。历史可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成就和有益的影响,什么是错误的转向和消极的影响。这些知识对我们判断当前的课程问题与走向是有用的。“如果没有课程史的知识,我们恐怕遗留的是现在不完整的知识,毕竟,这是过去经验的结果。假如我们想要比过去更好,在这之前就必须先去理解及建构。”[7]“课程史是收集课程领域的记忆,没有它我们就无法获得当代课程问题的完整图像。”[8]
2.课程史为当下的课程实践提供智慧资源
前已提及,历史的作用主要在学史明智,透过对过去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为我们今天理解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同时也可以为我们今天解决一些实践问题提供一些智慧资源。“课程史是关于课程的一种知识形式,阐述在学校发生的事物如何与社会相关联。在决定做什么时,课程史的知识是不可或缺的。”[9]“课程史是个人记忆的延伸,一种教育者们能共同分享的延伸,使成为专业领域的记忆。就课程史发生的作用而言,它能规范和指导改革者的活动。”[10]就历史的范畴而言,包括横向的本国历史和别国历史,也包括纵向的当今历史和过去的历史。本国的历史可供借鉴,他国的历史也可以提供借鉴。国与国之间在特定的发展时期、发展阶段碰到的问题会有某些相似之处,所从事的改革运动也会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目的。从这些改革中我们可以吸取到宝贵的经验和教训。综观各国历史的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教育问题或者说课程问题,不仅仅只是单一的某一个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问题,是一个社会整体层面的问题,不太可能从某一局部、某一点去尝试很大的突破,这样的“以一搏三”甚至是“以一搏九”的改革思路难免会造成改革的步履维艰。美国为了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进行的教育改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著名的八年研究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参与这项改革的不仅仅只是某些中学和小学,而且包括了一部分大学,并且在大学的录取过程中,参与改革的中学的学生享有某种优先权,这就使得教育系统内部上升与下行的渠道打通了。而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失败了,因为其思路也只是试图从课程本身的改变来实现某些外在的宏远理想,而且课程本身在设计上就存在很多的问题。从这样一些课程史的角度来认识与分析,可以为我们今天从事课程改革和课程实践提供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思路上的警示。正如课程史专家巴拉克所言:“课程史将帮助我们觉察课程改变的可能性和复杂性,并意识到将过去的学说和实践扭转到现在的情境中是困难的。”[11]坦纳因此也曾说:“历史的结果是教师、校长、教育委员会与教育部门在考虑课程决定时应当利用的研究成果和概念。”[12]无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课程实践,其结果可能往往都不令人乐观。
二、课程史研究:主题与方法
(一)课程史研究的主题
课程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如何开展研究,需要找到合适的切入点。台湾课程学者白亦方教授曾总结出课程史研究的八个主题,分别是:第一,某一学科在我国的源起与发展,也就是强调某一学科的历史变化;第二,以量化、质化方式来探讨课程实务的对照与呼应,比如课程发展委员会之功能与现状的普查等;第三,某一课程学者的思想与影响;第四,探讨某一时期的课程政策演进与影响,分析和揭示政策制定过程中各种人员、利益集团等之间的博弈;第五,某一组织对于课程内涵及实施策略的主张及影响;第六,新科目出现的时代背景与教育界的回应;第七,某一课程运动的兴起与当地的解读或批判;第八,某一课程理念的概念分析。[13]白教授的主题分类给我们研究课程史提出了大致的方向。
本文根据白教授的分类,结合大陆地区的特点,提出如下课程史研究的主题:
(1)学科史。学科史一般按单一学科进行,研究学科的目标、内容、地位等的发展与演变,并探究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动因等。这里面可以包括新学科的出现与发展专题问题研究。
(2)课程大纲或标准的演变史。一般也可以按学科分类来进行,分析一定历史时期内某学科的课程大纲或标准的发展与演变,及其背后的历史原因。
(3)课程改革史。研究一定历史时期内所经历的课程改革,每次改革的原因、推动机制、改革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改革过程中各利益集团的博弈、改革的实际成效、改革成败的经验和教训等,可以进行多个层面的横向比较分析。
(4)课程思想史。主要研究某人或某些著作当中所体现的课程思想,比如孔子、朱熹以及近代的陶行知等他们的课程思想观点及在历史上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5)中小学课程计划(结构)的演变史。主要研究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小学学校课程计划的演变历程,各学术团体之间的博弈以及背后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追求与导向。
(6)课程发展史上重要的事件分析。这些重要的事件包括某一本重要的课程著作的出版、某一次重要的课程改革、课程结构当中某一次重要的调整、某一新的课程形态的出现等等,分析这些重要的事件对课程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以及课程实践产生的重要影响。
(7)特定的人物研究。这些特定的人物可以是在课程理论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可以是某一次课程改革的主要旗手,可以是在学校实践过程中对课程改革与发展进行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效的一线教师、校长等等。
(8)学校或个人层面的课程史。主要是以某一所学校、某一个教师、某一个学生为聚焦点,从一个微观的角度来透视国家整体层面的课程政策、课程计划等在学校及个人层面的实施情况,以及随着历次国家课程政策、计划的改变,在学校及个人层面所产生的或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还可以反映基层学校教师和学生所期望的课程需求,发现一些“沉默的声音”。
(9)课程管理演变史。主要可以从宏观或微观层面来分析国家、地区和学校层面的课程管理制度的制定、管理内容和方式的发展与演变,以及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导向。
(10)课程核心概念的演变史。主要是围绕课程领域的某些核心概念,探索其地位的演变、内涵的演变等,以及从这些演变背后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导向的变迁,并由此可以透视出整个课程理论发展的内部逻辑与走向。
(11)重要的机构和协会在课程理论的建构及课程改革实践过程中所起到的特定的历史作用分析。比如中央和各地方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机构、各师范大学的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委员会以及现在定期举办的课程研讨会等,在全国和地区范围内对课程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对课程实践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贡献,以及存在哪些局限与问题等,都可以是研究的主题。
(二)课程史研究的思想方法
历史事实本身是复杂的,历史的研究本身就具有不可避免的困难度和复杂性,又加上研究者自身的主观意识形态的渗透,使得历史的研究又越加的复杂。同一件事情,在不同人的观念里、在不同的报道中往往有着区别甚至是完全冲突的说法,这在历史与政治事件中是屡见不鲜的。课程史的研究往往也是如此。于是美国历史学家Charles Beard 1933年提出了三种历史观:第一种,认为历史是混沌的,而且每一种尝试去解释它的方法都是一种错觉;第二种,认为历史以一种循环方式运动;第三种,认为历史的运动是线性、直线或螺旋,和在一些方向上运动。[14]这三种史观未免都比较消极,第一种完全否认了历史的可知性;第二种认为历史只是在做循环运动,没有进步和发展;第三种与第二种类似,只是以线性或直线或螺旋地在运动,至于往哪个方向运动,则无法确认。而Charles Beard本人的历史观则是积极的。他认为:“世界是朝一个更好的未来逐步前进,历史学家的功能是在加速此种改进:在改进现在的兴趣上改善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学术目的,那就是去帮助改革者避开陷阱与过去的失败,藉由帮助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透过知道和解释伟大的观念运动,建立一个更美好的未来。”[15]这种积极史观应该是我们课程学者从事课程史研究的必要的思想前提,否则就将陷入悲观与消极情绪之中,也就失去了研究课程史的积极性与学术目的之追求。
从事课程史的研究,搜集各种史料,进行辨别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但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应该尽可能多角度、多渠道,不可随意采用一家之言,因为任何类型的报道或研究论文背后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渗透。从学术的角度看,历史事实和事件不能单独构成一部历史。各种政策文件、报道、研究论文、教材等都是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的文本。所以不可随意采用一家之言。否则就很容易陷入史学家W.E.Mardson所指出的两种错误的史观:[16]
第一种是“无历史”(Ahistorical):主要是不管历史观点,书写者认为那是无关或无趣的。造成许多结论都是自我意识的历史介绍,或者只是卖弄学问。很多这样的著作都是天真浪漫的,产生和存在于一个世俗的空间里。
第二种是“反历史”(Unhistorical):措辞与其他普遍接受的历史学者定义不一致,提供不精确、过度简化或扭曲的过去的印象。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武断的、两极的、刻板的。这样很容易导致课程领域缺乏学术信度。
简而言之,“无历史”也可以说成是无视历史事实和其他人的观点,只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世界里;“反历史”则是对历史做过于简单的处理,不精确、简化甚至是扭曲历史,所得出的结论也是武断的、刻板的,分析和解释也是缺乏力度的。
(三)课程史研究的研究方法
1.批判论述分析
批判论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是兴起于1990年代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批判论述分析是在延续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批判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CL)的基础上,并结合不同类型的论述活动而产生的。CDA这个标签第一次被实际使用是在Fairclough(1995)出版的《批判论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书中。“CDA方法主要是研究社会及政治脉络中的文本与谈话如何呈现、再制和抵抗社会权力的滥用、支配与不平等的现象,并采取一种很明确的态度,即了解、揭露,最后反抗社会的不平等。”[17]在社会学领域,涉及社会问题,尤其是论述在权力生产与再制或支配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问题时,常常使用批判论述分析方法。
批判论述分析包含了文本、论述实践和社会实践等三层面,分析重点在于:(1)文本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主要分析文本中的“词汇”(Vocabulary)、“语法”(Grammar)、“连结性”(Cohesion)和“文本结构”(Text Structure)。这些范畴的分析是递升的:词汇主要是在分析个别的词语,语法是在分析结合分句和句子的单字,连贯性是在分析分句和句子如何连结在一起,文本结构则是在分析文本大范围的组织特性。(2)论述与风格的分析,以此探讨文本生产、分配与消费的关系。(3)将论述置于社会实践的脉络中,着眼于意识形态与权力斗争的概念,其目的在解释为什么论述的社会实践会是这样,并试图针对这结果加以解释。
这种方法后来逐渐被引用到教科书的分析上来,以分析教科书当中的意识形态、性别差异、文化差异等。批判论述分析在课程史研究的应用中,主要是用来分析文本及文本背后所渗透的价值取向。因为“对于课程运动的描述,我们似乎停留于学校有形易见的时数变化、学科名称增修或挪移、课程标准(纲要)字面意义解读、学生评鉴标准设定、教学活动设计项目、组织名称功能之更易比较等行政管理层级,以及学术理论之引介(或移植),反而对潜藏于这些作为、名称、组织机构、理论背后的预设、价值体系、学术精英的主张之辨别却着墨不足”,[18]通过批判论述分析,可以将支配这些面上工作的背后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各利益集团的博弈等有效地揭示出来,以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课程这一“复杂事物”的理解。
2.国家、地区以及学者之间的比较研究
此种研究主要是选择两个或多个国家、地区、学者进行课程发展史的横向和纵向比较研究。前已提及,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发展的阶段与历史上,会有某些类似,在教育上也会有一些类似的探索与改革。学者与学者之间课程观点、思想之间的渊源、异同、论辩、对实践的影响等。通过彼此之间的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可以分清彼此之间在理论建构的内部逻辑及结构和走向,及理论本身的价值追求或意识形态性;可以发现彼此在实践领域碰到的相同或不同的课程问题、课程改革的价值追求、实际过程的运作、改革成效、成败的经验等。
3.俗民志研究
俗民志又称民族志、人种志研究,英文为Ethnography。“原为社会人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记录、评价,并以社会或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19]“民族志研究的主要工作是发现知识而非验证理论,因此,它依靠的主要是发现的逻辑,其目的是发现行为者所建构的社会真实,掌握、理解并发掘行为者的意义,并加以描述解释。”[20]
俗民志研究主要可以用来研究课程史当中有代表性的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及学校,通过对相关学校及人员的持续的深入的观察、交流与沟通,获得一手的资料并进行深入的分析。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现在这些课程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其历史脉络、地位和影响如何等等。
4.传记与口述史研究
传记主要是用来研究课程史当中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的人物,考察他们的课程思想观点、这些观点之所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与实践基础、重要的课程行为、对当时课程领域产生的重要影响、与其他课程专家之间的讨论与辩论、其本人对自己课程观点与实践工作的评价等。还可以从某些特定的学者、教师身上来透视某些学科在学校整体课程结构当中的地位的发展与变化。这也是研究学科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有的课程学者由于长期从事课程领域的教学或研究工作,也曾经参与了某些重要的课程事件,也可以以一种自传的方式来从事基于本人的课程史研究。
口述是相对于文字而言,历史除了已经现有的文字之外,更真实和鲜活的历史存在于人们的头脑当中。它“主要是通过一个人或一群人叙述其生命、生活经验或故事以累积文本的方式。历史则牵涉到事件何时何地发生,何人牵涉,如何发生等等事实,以及对这些事实所作的诠释与观点。”[21]“口述历史”突破了研究历史的资料来源必须取自于文字的限制,将历史的取材与资料来源扩展至相关人员的叙述,并将历史的诠释权回归广大的民众。每一个人在口述的过程中,他/她都是事件的参与者与解释者。因此,这种方法对于研究那些弱势群体及基层人士的“沉默的声音”最有效。也是从事传记研究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上述第三和第四种方法可以有利于打破历史研究受文献控制的局限,为课程史研究提供更多的思路。
总之,课程史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亟待研究的一个领域,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不成熟的民族,那么一个没有历史的学科同样也是不成熟的学科。正如白亦方教授所言:“课程史研究,此其时矣!”[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