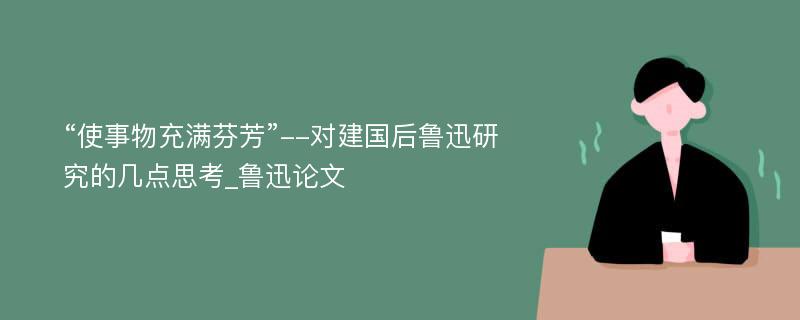
“只留清气满乾坤”——建国后鲁迅研究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断想论文,乾坤论文,只留论文,清气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各位代表,各位与会的领导和朋友们:
今天,我们汇集在花团锦簇、佳宾如潮的春城昆明,召开本世纪末中国鲁迅研究界的最后一次盛会。为配合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我们把这次会议的议题定为“中国鲁迅研究五十年”。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术话题:既可以检阅半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园圃的累累硕果,又可以总结半个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正负两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希望各位远道而来的学者和作为东道主的云南省的学者都能在会上尽情表达自己的心声,充分进行开放性的对话和坦诚的交流,为下个世纪鲁迅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我学力甚浅,准备这篇发言的时间又极为仓促,确实无力勾画出五十年来中国鲁迅研究的学术轮廓,只能大题小作,发表一些零碎的、近乎即兴式的感想,以期引起诸位前辈和友人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
如果从鲁迅的文学活动初见报端算起,鲁迅研究至今已有整整90年历史。对这段历史加以划分,前40年是一个大阶段,后50年又是一个大阶段。一般称前一阶段为建国前的鲁迅研究,后一阶段为建国后的鲁迅研究。建国后的鲁迅研究,又可以大体切割为建国前期的鲁迅研究,文革中的鲁迅研究和新时期(包括后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三个时期。有些专家把建国后的鲁迅研究分为毛泽东时代的鲁迅研究和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两个时期,这种提法似乎不太准确,因为新时期并不是完全摆脱毛泽东思想的时期,邓小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期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中,有一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建国前期的鲁迅研究时间跨度有十七年,即从1949年10月至1966年6月。 这一时期的鲁迅研究虽然无法摆脱当时“左”的政治路线的影响,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但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其主要表现是:一,由李何林、王瑶等第一代鲁迅研究家建议、规划,鲁迅研究作为一门新型学科正式进入了高等学校的课堂。这个举措的意义无论如何评估都不能算高。因为鲁迅作品是一种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的“经典”,而鲁迅作品的经典性又必须通过教与学来承传。所以西方关于文学经典定义是:“人们相信重要得足以作为阅读、学习、书写、教学的作品。”二,在冯雪峰的主持下,在王士菁、林辰、孙用、杨霁云诸位前辈学者的参与下,编注了第一部有注释的《鲁迅全集》十卷本,于1958年前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还出版了《鲁迅译文集》十卷本。虽然58年版《鲁迅全集》收罗并不齐备,个别注释与历史事实不符,但却为深入系统地研究鲁迅奠定了比较坚实的文本基础。58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也为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提供了基础。三,作为鲁迅的亲友,许广平撰写了《鲁迅回忆录》,冯雪峰撰写了《回忆鲁迅》,周作人撰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鲁迅的青少年时代》。这些著作虽有明显的历史局限,但毕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此外,作为老一辈鲁迅研究家,唐弢撰写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陈涌撰写了《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些学术成果,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水平。在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以林非、朱正、林志浩等为代表的第二代鲁迅研究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在新时期发挥了更大的学术潜能,作出了更加引人瞩目的贡献。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研究时间跨度有十年, 即从1966 年6 月至1976年10月。在这一时期,林彪委托江青主持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公开发表的纪要中,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被全面否定,因而所谓“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也就在实际上被完全架空。在“四人帮”肆虐的那些灾难性的岁月中,鲁迅被歪曲、篡改、拔高、神化,成为了一个简陋而枯燥的政治符号。这就造成了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对鲁迅的隔膜,使他们产生了“厌恶和尚,恨及袈裟”的逆反心理。这种后患,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然而,也有一批热爱鲁迅的正直的知识份子并没有屈服于残酷的现实。在学术被亵渎、人才遭蹂躏的暗夜里,他们仍执着地从鲁迅的作品中寻求着真理的光和热,以枣树直刺夜空的精神力图冲破“四人帮”的精神罗网。1975年11月1 日,毛泽东就鲁迅著作的出版和研究问题发表了重要批示——这是毛泽东临终前对文艺问题的最后一个批示。在这个批示的鼓舞和保护下,一批挚爱鲁迅、痴迷于鲁迅作品的人们集结起来,为重新编注《鲁迅全集》而不计名利地工作,这就使文革后期的鲁迅研究出现了亮点,并为日后的鲁迅研究作了比较充分的资料准备和人才准备。在这批人当中,有些已离我们而去,如单演义、薛绥之、包子衍、马蹄疾,但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各自为鲁迅研究所作的独特贡献。
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时间跨度有二十三年,即从1976年10月至今。其中,人们又习惯于把开始确立市场经济模式的1992年作为后新时期的开端。在这二十三年中,鲁迅研究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和变化的条件下,在中外文化和文学思潮空前冲撞交汇的形势下进行的。作为对鲁迅研究发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首先应该提及发生于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正是这场讨论,彻底砸碎了现代迷信、教条主义和新蒙昧主义的精神枷锁,使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从属地位中解脱出来,一个凝固的、板结的、一体化的文学秩序由逐渐松动而终于解体。这场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的尊重实践、尊重科学、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原则使鲁迅研究领域恢复了活力与生机。广大研究者打破了单一的政治视野、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格局和“时代背景——主题思想——写作特点”的写作模式,引进了比较研究、哲学分析、结构主义、接受美学、原型批评、系统论、符号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宏观把握,视角多元,方法更新,注重突破,构成了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基本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80年至1986年的七、八年间,鲁迅研究的各类论文就发表了六千余篇,各类专著出版了二百余部。一部收罗比较齐备、注释比较详尽、校勘比较精确的新版《鲁迅全集》也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之际在国内外发行。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以研究《野草》蜚声中外的孙玉石和以钱理群、王富仁为代表的第三代鲁迅研究者的群体。他们知识结构完善,思想敏锐,敢于创新,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时期中国鲁迅研究的中坚。
在回顾新时期鲁迅研究足迹的时候,我想起了发生于八十年代文坛的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有的引起了争议,有的没有引起争议,但都对新时期的鲁迅研究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第一件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每篇作品之前是否要保留“题解”,以介绍写作背景和主题思想。当是有专家认为,今天的读者在阅读鲁迅作品时存在“知人论世”的困难,不一定能准确把握鲁迅作品的精神实质,为更好地普及鲁迅作品起见,应该在《鲁迅全集》中增加题解作为阅读的指南。当时主持《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负责同志却认为,在鲁迅作品的权威性版本中加上题解,容易给读者以“钦定”“御批”的错误印象,从而使得鲁迅作品的主题模式化——当然,这并不妨碍有些专家将自己的见解写成题解,并作为个人专著出版。
今天看来,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已趋明朗,其意义已超乎《鲁迅全集》是否应该保存题解的范围。凡参加过1981年版《鲁迅全集》编注工作的人都知道,当时由鲁迅研究者和工农兵理论骨干共同撰写的“题解”,基本上是对鲁迅作品进行单一的政治性解读,而政治性解读的特点则是将具有非特指性、非确定性和具有多义性、含蓄性的艺术符号与有着特指性、固定性、明确性的一般文化符号高度对应和绝对统一,如《秋夜》中的“粉红花”代表旧民主主义者,“朔方的雪”代表北方革命力量,“夜游的恶鸟”代表反动文人之类,其结果则是对鲁迅作品文学性、艺术性的疏离和对工具性、实用性与非文学性的亲和。所以,对于鲁迅研究来说,在近于法定本的《鲁迅全集》中取消题解,是对鲁迅研究的一种松绑,也使得鲁迅作品从他律向自律回归,从程式和框框向艺术回归。
应该提及的影响鲁迅研究的第二件事,是王瑶在1984年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王瑶认为,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得失,不能采取文革前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标准,也不能采取改革开放初期的“反帝反封建”标准,而应该采取文学现代化的标准。也就是说,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观念,作品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手段,作家思维和感受方式以及语言艺术等方面,只要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就应该给予肯定,给予恰当的评价。这样一种进一步走向宽容的批评观、价值观同样给鲁迅研究以深刻启示。此后,不少鲁迅研究者拓展了思路和视野,从广泛的世界联系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来评估鲁迅的文学道路和文学业绩。他们对鲁迅现代意识形成的内部线索,对鲁迅有关“传统”与“现代”的理论阐述和创作中的现代批判意识,特别是对鲁迅为确立中国人的现代品格而作的努力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使鲁迅研究领域不断向纵横方向开拓。不过,王瑶提出的“文学现代化”这一措词似乎尚可推敲,用“文学现代性”的提法取代“文学现代化”的提法可能更加准确,更加切合文学艺术的特点。现代性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理性精神,启蒙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它在各个发展阶段又具有不同的历史具体性。不断挖掘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意识精神,不仅能够深化鲁迅研究,而且有利于对鲁迅同时代的作家、流派、社团作出科学的评价和准确的定位。
我想提及的第三件事是围绕“重写文学史”这一口号引起的论争。1988年4月, 两位上海的中青年批评家正式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对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进行了冲击,以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这场冲击波自然不能不波及鲁迅研究领域,得到了呼应和赞扬,也受到了诘难和抵制。其实,“重写文学史”本是一个无须质疑的提法,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用当代意识对文学史进行重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需要重写,而在于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如何进行重写,如何通过重写更加逼近历史的真实。如果说,我们重写文学史的目的是为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使学术研究挣脱实用主义和狭隘功利主义的枷锁,那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和支持的。但如果把“重写”简单地理解为历史的颠倒,那就会在纠正一种片面性的过程中蹈入另一种片面性。比如有一位“重写文学史”的倡导者把以鲁迅的《野草》为代表的审美的传统视为文学的正途,把“文学为人生”“为无产阶级大众的文学”一律视为文学的歧途,在我看来至少是一种对鲁迅的误读。因为在鲁迅的文学里,审美的功能跟“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功利性是相一致的。鲁迅不是从政治层面上表现人生,而是从人生层面上表现政治。他从来不佩服那种否定文学功利性的批评家,从来不追求那种超出于人间世的“纯文学”,从来就认为好的作品既是从作家心中流露的东西,又具有积极的社会效应。在鲁迅这类自觉肩负历史重任和承受时代重压的中国现代作家看来,在民族的尊严与生存受到威胁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以“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回避社会矛盾,回避民族危机,为自己营造精神上的象牙之塔,这实际上是背叛民族的行为,同时也是背叛艺术的行为。同样,在鲁迅这类具有崇高使命感的中国现代作家看来,关心政治、干预政治并不是文学的耻辱和污点,而是文学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他们作品中具有的鲜明政治性和强烈的爱憎感并未影响艺术的独创,反倒使这类“属于别一世界”的作品在世界文学的阵营中异军突起,鲁迅也才能成为一位具有纯粹精神意义的伟人。因此,把鲁迅作品中的审美传统和革命传统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也不符合鲁迅作品的实际。
跟八十年代比较起来,九十年代面临着经济、文化、科学、知识的多方面转型。随着整个文化复杂多变的转型,鲁迅研究也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对这一时期鲁迅研究发生深刻影响的政治事件,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邓小平这次南巡引发了新时期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并最终完成了指导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思想。从那时到今天的七年中,鲁迅研究领域进一步开放和活跃。审美的社会价值论和丰富的人学内涵不断更新着鲁迅研究的内容和精神取向,从思维方式到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系统都发生了科学化现代化的根本变革。用叙事学的研究方式解读鲁迅小说,用存在主义、生命哲学解读鲁迅的散文诗,成为了近年来鲁迅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对鲁迅杂文的研究摆脱了西方文学概论中关于纯文学的狭隘定义,不仅仅从杂文的议论因素之外来挖掘其文学性,而是从鲁迅杂文的总体着眼,深入挖掘其艺术本质属性,将以概念范畴为思维材料的纯理性思辨与鲁迅杂文中那种夹叙夹议的符号化、象征化、直觉化、意象化的议论加以细致区分。对于鲁迅人学的研究,形成了近年来鲁迅研究的一个热点。有些年青的学者(如李新宇),对鲁迅人学思想形成的中外文化渊源,鲁迅关于“立人”的正面主张和对中国国民性负面因素的深刻解剖,鲁迅人学思想的内部结构及其历史命运,都发表了新的很好的看法。总之,众语喧哗,新论迭出,构成了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新景观。这一时期在鲁迅研究领域十分活跃或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有张梦阳、王乾坤、张福贵、孙毅、高远东、皇甫积庆、李春林、刘玉凯、朱晓进、郑家健、房向东、高旭东、李继凯等,由于我的孤陋寡闻,一定还遗漏了一些应该提及的名字。这批学者朝气蓬勃,前程似锦,代表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希望和未来。还有一些长期在鲁迅纪念机构从事领导工作以及长期主持鲁迅著作出版和鲁迅研究学术刊物的学者,如王仰晨、李文兵、陈早春、王世家、裘士雄、王锡荣、张竞等,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众所周知并无法取代的。
在回顾建国五十年来中国鲁迅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时候,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国际范围,世界社会主义正处于低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正倚仗其经济军事实力,打着“全球一体化”的旗号飞扬跋扈。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各条战线的成果虽然举世瞩目,但也有许多十分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为前人所未遇的新问题。由于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一些人发生所谓信仰危机,以致成为各种唯心主义错误思想的俘虏。鲁迅研究领域同样面临着尖锐的挑战,其中既有新儒家的挑战,后现代派的挑战,新生代作家的挑战,也包括商品大潮的挑战。由于市场的诱惑力超过了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鲁迅“匡正时弊,重铸民魂”的传统不同程度地被一些人淡忘和漠视,知识分子在城市文化热中日趋世俗化。对此,有的研究者表现出一种不变不惊、我行我素的超凡心态,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感到困惑和不安。
为了迎接世纪末的挑战和新世纪的召唤,我感到中国的鲁迅研究者需要继续发扬两种精神:一种是科学的追求精神,一种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追求精神是人类心灵、情感和理智中最活跃、最具进取性的因素。这种精神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主要表现为追求真知,追求创新,追求开拓,不断探求认识对象的本质,并不断发现未知世界的存在。最近,我愈来愈感到学术上的空虚和危机,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鲁迅的知识结构是那样庞大而完善,内心世界是那样丰富而细腻,而我个人的知识水平却是那样肤浅,生活阅历是那样不足,因此很难走近他,跟他进行平等的精神对话。过去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些鲁迅著作,比如《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今天看来其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都需要重新估定;而以前为我所忽视的一些文章,如《破恶声论》,最近重读,却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历久弥新的经典魅力,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的教益与启示。这篇文章中对兽性爱国者的批判,对托尔斯泰不抵抗主义的批判,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关于张扬个性、发扬心灵光辉的有关论述,都使我不能不感到青年鲁迅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天才。我们如果不愿意成为这篇文章中斥责的那种只凭道听途说和一知半解的一点东西来招摇撞骗的“伪士”(即假知识分子),而成为不随声附和、不怕孤立诋毁、能坚持自己信仰的“独具我见之士”(有独特见解的知识分子),那就需要重新认识研究对象,回归文本,走进经典。只有发扬科学的追求精神,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和开拓。
我们需要继续发扬的第二种精神是科学的理性精神。要发扬这种精神,首先就必须坚持实证原则,把任何结论都建立在颠扑不破的事实的基础之上。这是划分科学、非科学、反科学的原则,也是我们每一个鲁迅研究者(包括理论大师)都必须遵循的原则。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强调的“字字征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应该成为我们撰写论文、论著时共同追求的目标。五十年来,我们在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收获,以致达到了鲁迅研究资料基本齐备,任何新的史料发现都不足以改变对鲁迅基本评价的地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写的《鲁迅年谱》(四卷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研室编选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薛绥之教授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成为了鲁迅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但是,新史料的发现仍然存在着潜力。比如,陈子善去年到日本访学期间,就买到了1936年3月20日鲁迅致内山完造的原信。最近, 又有日本学者在台湾发现了鲁迅致蔡元培的两封书信。在日本庆应大学担任特别招聘教授期间,我也跟我的研究生发现了一封鲁迅1927年1月15 日致原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的辞职信。原文是:“文庆先生足下:前蒙惠书,并嘱刘楚青先生辱临挽留,闻命惭荷,如何可言。而屡叨盛饯,尤感雅意,然自知薄劣,无君子风,本分不安,速去为是。幸今者征轮在望,顷即成行。肃此告辞,临颖悚息。聘书两通并还。周树人启。 一月十五日”。 这封信为1981年版《鲁迅全集》未收,是研究鲁迅厦门时期生活的新资料。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自有鲁迅研究以来,就不断有人伪造鲁迅的手迹、诗歌、文稿以及有关史料。最近,又有人在鲁迅史料考证中采用了一种“破字谜”的研究方法。我认为这是一种与实证精神相违背的研究方法,不能相信,也不宜提倡。尽管鲁迅笔名之一“宴之敖”中隐含他跟周作人失和的真相,但不能将这种破译的方法推而广之,以致把“鲁迅”的“迅”字都当作“羽太信子”这一日本人名中“信”字的谐音,并进而把鲁迅这个神圣的名字破解为“孝道”与“恋爱”的矛盾。在鲁迅史料研究范畴也有两种学风的对立,这是客观存在,不必讳言。
记得1996年在鲁迅逝世六十周年纪念会上,我曾经讲过,鲁迅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而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也需要继承鲁迅的这种殉道者的精神,燃烧自己的心,照亮坎坷曲折的学术征途。歌德说,“我所以得天独厚,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世界大事纷至沓来的时代。”跟歌德相比,我们更其幸运,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比歌德的时代更加波澜壮阔。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曾经把汗水、泪水、血水洒在鲁迅研究的稿纸上,在鲁迅研究史上留下了永恒的记录。今天,只要我们继续高扬鲁迅的精神旗帜,就能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不致心灵失重,就能在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攻击中坚持学术阵地,就能在艰苦的探索中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们这次会议是在国际花卉博览会的举办地召开的,这使我又想起了元代王冕《墨梅》诗中的两句:“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在群芳斗艳的学术园圃中,愿我们的鲁迅研究之花像不惧严寒、不媚时俗的墨梅,既吐出浓郁的学术芬芳,又洋溢着磅礴的人间正气。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