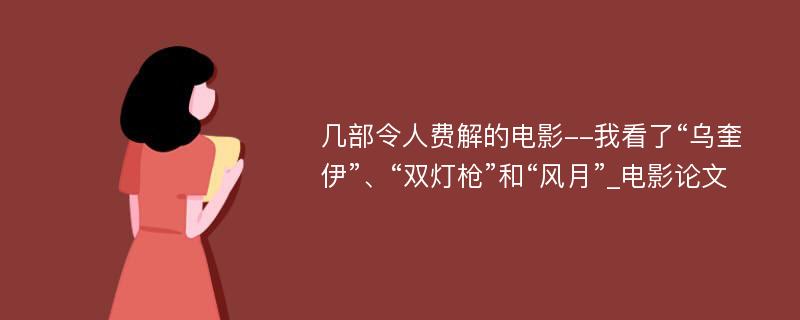
让人困惑的几部电影——我看《五魁》、《炮打双灯》和《风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让人论文,我看论文,风月论文,几部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认为,对某些影片来说,它的故事结构及其表意特点,不仅可能被批评者和观赏者所忽略,甚至可能被它的创作者所忽略,或许我们应当说,对此,就连它的导演可能也没有特别清醒的意识。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而且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正因为如此,电影批评才是有意义的。
我记得,几年前,使我把《五魁》和《炮打双灯》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这两部影片让我感到困惑。记得当初,看过了《五魁》之后,只是觉得整部影片都有些做作,没有什么好感,心里想,黄建新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导演,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影片呢?看过了《炮打双灯》之后,觉得很好看,拍得也很精致,但对其含义,觉得它与《五魁》一样,让人感到困惑。我想了好长的时间都想不出,导演拍这样一些影片,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什么意义。由于这个原因,我比较注意阅读对这两部影片的评论。但是,并没有消除我的困惑。直到我看过了《风月》的录相以后,我才想到,把这三部影片联系起来考虑,可能有助于我们对它们的理解。
一旦我在心中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寻找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理由就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现在,我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把《五魁》、《炮打双灯》和《风月》这三部90年代的中国电影联系在一起。首先,这些影片都是由海外投资,可能都会被当成商业艺术片来对待。其次,这些影片的题材均表现一个假定性很强的旧社会的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历史性的故事。但它们都拒绝你去把它同历史相联系。再次,我还发现,在对这些影片的理解上,评论者的评论与创作者关于影片立意的说明差距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没有注意从创作者的立意的角度来加以评论。
但是,真正促使我把这三部影片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却只有一点,即这三部影片在故事结构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对一个“空转的故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看到,在《五魁》中,影片一开始就表现一个年轻的女子出嫁到一个有钱人家,人还未到,她的男主人就死去了。这个故事还怎么进行呢?后来她被下人五魁救了回来,影片故事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故事是“照样”进行的。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就好象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生命力就在于,当它的真正的主人已经不在了的时候,它还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具有运转能力,当然,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中确切地了解到,它是在空转。它的作用就是保证一个女人与一块木头的“生活”。在这里,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主人的位置上发挥作用的,是她的婆婆,她的婆婆曾经是这个机构的受害者。现在她又成了一个加害者。
由何平导演的影片《炮打双灯》同样对“家庭机构”(要准确地说,应该是“家族机构”)的空转现象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影片中的“少爷”是一个19岁的美貌女子。她在蔡家爆竹业家中的全部力量,只体现在她作为这个家族唯一继承人即主人的位置所规定的力量上,在“正常的”运转中,她是这个家族机构的代表,但是这个机构的运转,却并不取决于她的主观意图。为了防止财产的外流,这个家族规定她不能同外人结婚。她的悲剧就在于,她竟然天真地相信,她同一个画年画的青年人相爱的个人愿望竟然能够为这个家族机构所允许。
由陈凯歌导演的影片《风月》对这种空转现象的探讨似乎更为深入。在影片中,庞氏家庭的老爷去世了,少爷也成了“植物人”,这个家族面临着与《炮打双灯》中的蔡家几乎同样的没有主人的危机。解决的办法是由庞家的小姐来充任主人的角色,但是,当小姐也成了植物人以后,就只有选择一个属于庞家远支的实际上是一个下人的端午来充任这个位置。他倒不是一个植物人,而是一个生物学上活生生的人,但观众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活人在这个完全有能力自行运转的家庭机构中的作用,只能是形同植物人。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影片的导演们究竟是如何说明他们的影片的立意的。
当采访者问到黄建新拍《五魁》最感兴趣的是哪一点的时候,黄建新这样说:“我当时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善良的脚夫最后变成一个土匪的故事。由好人变成咱们观念中的所认为的不好的人,这样一个过程,有二律背反的关系在里头。当然原小说与影片差距很大,我对小说感兴趣的就只是这点——就是一个人物他定位的过程,而这中间的东西都可以替换。”[1]
当采访者问何平拍《炮打双灯》的初衷和着眼点是什么的时候,何平提到两点,一是“正正相加得负”的人文思考,二是燕赵文化的苍凉感。“小说提供了中国文化的哲学可能性,这个可能性就是一个画年画的和一个做爆竹的,从事的都是中国老百姓生活中喜庆行当,而两者的相加却产生了悲剧。也就是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人们的普通生活中,画门神、造爆竹,避邪驱患,辞旧迎新,都是百姓寄托美好愿望的事情,为什么两个延续千年的风俗碰撞在一起会产生悲剧?……一个创作者、一个导演最初偏爱上某种事物,决心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一定是有其它的乐趣在里面,不光只是电影的本身。”“北方文化分两大系,从文化的悲壮上讲,一是齐鲁文化,一是燕赵文化,齐鲁文化更接近豪迈,《水浒传》的英雄都是齐鲁文化的英雄,而燕赵文化则更接近苍凉,为什么冯骥才本人把自己文学的重点放在燕赵文化上,是因为燕赵文化比较接近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就是说,它悲壮里面加着浓重的苍凉命运感,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一种人文精神,我们之所以要花费一笔资金去制作或者说去复制一段历史,一定是会与当今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周围的人,目前的这个社会在人格方面所缺少一种力量、一种典范或是说缺少一种精神、活人的精神,那是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希望去表现的。”[2]
陈凯歌在谈到《风月》时这样说:“《风月》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但又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我们讲不谈政治,只谈风月,但在‘风月’两个字后面有更重要的人性内容。讨论在某一种社会形态下男女两性的关系。整部影片基本是在分析和判断,男女两性在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社会门坎时各自所占据的位置。尤其是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这部作品保持着我过去一贯有的思考和判断,是一个处在由我们单独的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社会变动期中间,人们的感情发生变化的故事。我是用我自己的观点比较细致地去说明男女两性现存的关系是什么,揭示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总之他强调了,“从个人的命运反映出时代的变化”,强调了、个人所不能控制的社会变动”。他还提到,程蝶一“是一个随时准备为艺术牺牲的人,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牺牲品,而且是个甘心情愿的。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生命状态,这个生命状态不管周围的事物怎么转动变化,他是不变的。”他认为,他的《风月》,就“是在继续做这件事”。[3]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关于创作立意的想法与我前面提到的观察确实具有某种关联。比如,五魁为什么要成为土匪呢?年画的喜和爆竹的喜为什么最后成了悲呢?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结构的力量。这些中国最具思考性的导演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结构的力量。结构主义承认结构是有力量的,但这种力量不一定就是进步的力量。就是说,一个人追求理想,光有良好的愿望是绝对不行的。这些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影片的确能够表明,它们的导演已经关注到了中国历史及现实中的机构性“空转”现象。这些问题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必然要遇到的同时也是必然要提出的体制改革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些导演们对它只是有了某种不够清晰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来源于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稳定结构的观点,甚至可能来源于结构主义思想在中国电影理论研究中的传播和影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一再指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形式总是很快就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如此,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因此革命的任务、改革的任务必须不断地被提出。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影片基本上没有被从导演本人所表述的创作初衷(尽管这些表述看起来还不够明朗)的角度来加以评论。
戴锦华在提到《五魁》时说,《五魁》似乎是黄建新的一次“闪失”,一处“歧路”,一次对文化时尚的屈服;也许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与拓展。[4]李奕明很明确地说,“第五代电影如今已风骨尽失,徒存皮毛。其证明就是一向与第五代若即若离的导演黄建新却在1993年拍了一部貌似经典第五代形态,实际上只徒有其皮毛的影片《五魁》。”[5]
张颐武在评论影片《炮打双灯》时指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国风俗的奇观化;二是缺乏现实涉指。他认为,这部影片具备了中国第五代电影的几乎一切经典的特征,“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有关‘中国’的寓言。它依然有一个闭锁的、巨大的院落,有奇异的民谷,有一条滚滚滔滔的大河,有生死的缠绵与人性的透视。它给我们看到了灿烂的烟火,美丽的男装的东方妇人,古老的手艺与严苛的家规。这一切再一次把‘中国’化做了一个‘民族寓言’。这里没有对中国当下语境的具体‘状态’的探究,而是以运动的长镜头不断地窥探一个静止的空间。”[6]
李奕明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之上批评这部影片,“于今天大陆的现实及女性的生存境遇毫无涉指关系”。“这一寓言化的致命困境在于它与当下中国的信仰与道德重建毫无关联,支撑着这种寓言内部运作的男性/女性、压抑/释放、逃脱/落网等二元对立结构,并不能构成今天中国文化中信仰与道德的主要冲突,因而在大陆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并不具有历时性的意义,而只是一些共时的抽象主题,也就不能为今天国人的文化匮乏和道德困境提供任何启迪性意义和解决的路径,更无从为他们提供任何心灵上的精神抚慰。因此这种寓言性的主题就不能成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人生哲学。坦率地说,国人不需要这种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体验无关的寓言化的影片。”[7]
据说,《风月》在戛纳电影节再次受到冷遇,得分不高,评论也相当不客气。这部影片被认为是,“玩弄技巧”,“制造空洞而无生命的故事”。“展示的只不过是用电影手段表现出来的虚伪假象。”“导演选择这样一个悲情故事,是为了制造一个空洞的谎言。”“虽然能从影片中感受到昔日中国的地道原味,但这种故事已经老掉牙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导演的立意,并非没有关涉到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下中国的某些现实问题。但这些立意未能得到批评认同的事实却表明,这些影片在表意方面的确存在着某些不足。就是说,好的立意、娓娓动人的故事、流光溢彩的影象和音响表现单独一项既不足以保证影片的最后成功,也不足以保证它的哪怕是相当深刻的内含被充分地理解。这三者的完美结合才是确保影片成功的有效条件。
但我还是愿意表示,这些影片,尽管其创作意识尚不够清醒,尽管还存在着某些不尽人意之处,但其勇于探索用电影手段表达对于现实的某种思考的艺术精神及获得的成功,却是弥足珍贵的。我甚至认为,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提出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课题已经进入了这些导演的艺术思维和艺术视野是公正的。“空转”难道不是我们生活中思空见惯、见惯不惊、乃至熟视无睹的一种现象吗?如果说这些影片还不足以恢复我们对于生活的已经麻痹了的敏感性的话,那么,我们是否没有理由期望,这些导演一旦具备了清醒的意识,就会创作出真正不同凡响的电影作品呢?
注释:
[1]《当代电影》1994年2期,柴效锋:《黄建新访谈录》
[2]《当代电影》1993年3期,沈芸:《<炮打双灯>:何平如是说》
[3]《电影艺术》1996年1期,冯湄:《气犹在,血未凉》
[4]《当代电影》1994年2期,戴锦华:《思索与见证:黄建新新作品》
[5]《电影艺术》1996年2期,李奕明:《世纪之末:社会的道德危机与第五代电影的寿终正寝》(下)
[6]《当代电影》1993年3期,张颐武:《<炮打双灯>:寓言的困境》
[7]《电影艺术》1996年1期,李奕明:《世纪之末:社会的道德危机与第五代电影的寿终下寝》(上)
标签:电影论文; 风月论文; 炮打双灯论文; 五魁论文; 当代电影论文; 黄建新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