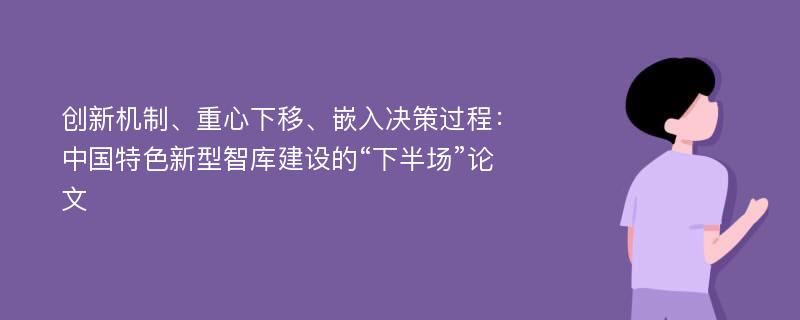
创新机制、重心下移、嵌入决策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下半场”*
李 刚
摘要 根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的时间表——到2020年实现总体目标,2013年以来的五年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上半场”,未来三年属于“下半场”。“上半场”成果丰硕,截至2017年底有九大类604家智库,分布于50多个战略和政策领域;智库的制度建设和运营管理探索出不少经验,涌现出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目前各界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深远意义认识得更加清晰,包括:新型智库建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路径;新型智库建设继承了儒家“学为政本”传统,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科学理性和专业理性;新型智库建设本质是开放言路,建立制度化的“政-知”“政-产”“政-媒”“政-社”意见交通渠道,调动各行业知识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新型智库建设促进了有利于开展政策辩论的理性“第二公共政策空间”。“下半场”面临五大挑战:智库产业集中度和产业集群性很低,“散”“弱”“小”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新型智库建设未能突破“三明治陷阱”;研究咨询业务过于集中政策过程的前端,业务模式头重脚轻;智库和政府内部研究机构是“两张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以消除;智库成果认定与激励的指挥棒设计不合理。新型智库体系建设要解决智库产业的集中度和集群性问题,实体化和法人化是解决体制机制创新、克服“三明治陷阱”的重要途径,业务重心下移和后置是解决智库浮于表面注重形式传播问题的重要思路,而推行“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模式”是解决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衔接、发挥“内脑”和“外脑”协同研究效应的重要选择,智库成果认定与激励措施的调整则始终是最重要的保障。
关键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学为政本 智库产业集群性 第二公共政策空间 三明治陷阱 智库成果认定引用本文格式 李刚.创新机制、重心下移、嵌入决策过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下半场”[J].图书馆论坛,2019(3):29-34,41.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倡议。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的时间表——到2020年实现总体目标,那么2013年以来的这五年应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上半场”,未来三年应该属于新型智库建设的“下半场”。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习近平总书记的总结仍然是对五年新型智库建设切中肯綮的评估。
离散小波变换相对连续小波变换,运算量小了很多,具有快速算法等优点,因此我们在小波变换的过程中选择了离散小波变换,而不是连续小波变换。
经过这五年的实践,我们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深远意义认识得更加清晰。
第一,新型智库建设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重要路径。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才是现代化的?什么样的治理能力才是现代化的?现代化不光是工具层面的,也应当是价值层面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体现在国家治理的价值、理论、方法、工具所具备的现代性。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化、规范化、科学化、协同化、效用化的治理体系才是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综合运用并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最大效用,达成全民福祉的最大化,形成“良好治理”,就是现代化的治理能力。新型智库无疑是观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加强新型智库建设实质上就是在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性成长。
信息化投资效益贡献率模型采用国际通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方法,以量化的方式认识电力企业信息化在管理效率提升、经济效益改善方面带来的实际作用的大小,评价信息化投资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
第二,新型智库建设继承了儒家“学为政本”传统,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科学理性和专业理性。儒家强调“学为政本”,这和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思想家说,中国文明是“早熟”的文明,这是与西方传统对比后得出的结论。秦汉以后,中国就建立了高度理性的非世袭的郡县制和官员任期制。到隋唐科举制已经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制度,比近代欧洲文官制度早了数百年。可以这么说,中古以后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就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贤人政治。但是,近代以来,西方逐渐走向了“学为政本”的国家治理法治化和专业化的路向,中国反而陷入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国家治理不再依赖学术和知识共同体,而是粗鄙的武夫和民粹,学为政本的传统被迫中断。现代智库虽然起源于西方,但却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嫁接到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现代西方国家治理架构。现代智库体现的“学为政本”的贤人政治精神契合中国文化的精神,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知识界为何对建设新智库充满热情。
第三,新型智库建设本质是开放言路,建立制度化的“政-知”“政-产”“政-媒”“政-社”意见交通渠道,调动各行业知识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积极性。根据我国宪法,人民在国家治理中处于中心地位,但是在国家治理的体系和实践中,决策体系相对封闭,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和机会均有限。实际上,不要说普通群众,就是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咨询的选项也不多。新型智库建设不仅给政府的内脑——各级各类研究室带来了专业化的决策咨询工作理念,而且通过外脑——高校研究机构、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主流媒体的智库化转型,使得理论界、社科界、高等教育界的专家获得了制度化的建言献策管道。如果说“内脑”是新型智库建设中的存量部分,那么“外脑”就是智库建设中的增量部分。如果说“内脑”是以往决策咨询的主体,那么现在“外脑”和“内脑”则获得了对等的主体地位,虽然它们的话语权并不相等。这种不相等并不是由于到决策中枢的距离远近,而是来自“内脑”和“外脑”的分工和专业素养。在短期和应急决策咨询上,“内脑”发言权较大,而在长期和基础的决策咨询中,也许“外脑”话语权更大。决策咨询体系增量主体的扩大促进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协商性、民主性、包容性。
如果从新型智库实体建设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据中国智库索引(CTTI)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已有九大类604家智库,分布于50多个战略和政策领域。根据规模和研究能力,这些智库分为国家高端智库、省级重点智库和普通专业智库三个层次,其中还包括一些按照“民非”、社团或者企业形式运行的社会智库。另外,在智库的制度建设和运营管理上也探索出不少有益的经验,涌现出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
冯一余到单位上班,跟同事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得焦虑症了。同事都笑,说,现在谁不得焦虑症才是怪物呢。后来就聊到了停车,有个老张说,哎,现在新花样真是层出不穷哎,有人因为抢不到车位,竟出钱雇人看守。冯一余说,是你们家小区吗?那老张说,不是我们家,我是从网上看来的。冯一余也到网上看了一下,果然有这样的事。
正是因为认识到新型智库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难得机遇,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才怀着满腔热情和历史使命感积极响应中央的号召,努力推动新型智库建设。
(4)地质灾害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下引发的,包括地质背景、自然地理条件、水系等,而本文中只考虑到了害点密度、坡度、坡高、坡型、岩土类型、冻土、植被、降雨、断层和人类工程活动10项因素。在今后的其他地区评价工作中可选取更多与地质灾害发育相关的因素作为分析指标,在此基础上再做易发性分区和危险性评价,其结果会更准确和全面。
第四,新型智库建设促进了有利于开展政策辩论的理性“第二公共政策空间”。互联网的兴起虽然极大地提升了政策辩论的参与度,但是有时候这种参与也是无序的和非理性的,这往往使得正常的政策辩论在网络空间中无法开展。一方面是由于长期以来民众接受的政策素养教育严重不足,的确不知道如何开展一项严肃的政策辩论;另一方面是因为一部分自媒体人和公号的写手为吸引眼球,无所不用其极,搅乱了正常的政策辩论。而在新型智库建设过程中,政策共同体的要素和边界逐渐明晰,形成了包含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策研究机构、新型智库、主流媒体等部门的专家组成的“第二公共政策讨论空间”。在这个共同空间中,智库起到了连接器和催化器的作用,推动了理性的公共政策辩论和协商。
相较而言,美国智库产业的集中度和集群性很高。华盛顿智库街上的近400家美国智库,三分之一以上的全职研究员和职员都在百人左右。美国西海岸的兰德公司有员工1850人,芝加哥大学的全美舆情研究中心(NORC)有全职研究员和职员600余人。可以说,美国智库不仅多,而且单个规模大、研究咨询力量强、影响力大。反观我们的智库,虽然中国社科院全院总人数4200多人,有科研业务人员3200多人,但这些研究人员分属31个研究所、45个研究中心和120个学科,每个研究所(中心)拥有的研究人员平均起来不过42人。更关键的在于,这些研究所和研究中心都是独立行政单元,跨所(中心)的协同合作非常困难。这种现象不仅中国社科院存在,不少省级社科院也是如此。至于高校智库,“小”“弱”“散”的现象则更严重。“C9联盟”中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动辄数百个,但是其中绝大多数都属非实体非法人的教授课题组,往往会因为教授“转会”或者退休而“人亡政息”,形成大量“僵尸机构”。可以说,我国智库体系中杂牌军多、正规军少,业余选手多、专业选手少,新智库多、老牌智库少。因此,中央抓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省市抓重点智库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能把有限的经费和专家资源集中到一起,还是分散发展,那就不可能迅速改变新型智库体系“小”“弱”“散”的特点。
1)落实国家政策、完成节能指标的要求。国家节能减排多项政策措施陆续出台,节能减排力度逐步加大。如何紧跟国家政策导向,结合企业实际,及时制定应对策略,完成节能指标要求,是节能管理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一,我国智库产业集中度和产业集群性很低。实体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新型智库就形成了“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的局面,以及“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总体上说,我国智库机构“散”“弱”“小”的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其实由于数量增加了,智库类机构“散”“弱”“小”的总体情况可能反而更严重,这导致我国智库产业集中度和产业集群性很低。
2017年,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和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征集评选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新型智库建设案例,例如“复旦发展研究院:始终坚持国际化路径促进传统论坛转型为智库论坛”“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智库研究要抓重大现实问题要突出前瞻性——《重新认识和准确定义新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北京市信访矛盾分析中心:智库实证研究的佳作——《社会矛盾指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三十年专注农村社会调查——从走村串户到构建大数据智库调查服务平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近年来立足中非合作实践需要,成功探索出了一条学科、智库、媒体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江南大学食品安全风险治理研究院旨在打造小而专、小而精、小而强,国际化视野的高校专业智库”“长江教育研究院:充分利用人大政协渠道,搭建一流专业论坛,十年如一日专注中国教育现代化”等等。
对照《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的到2020年要实现的总体目标,新型智库建设上半场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我国的主要专家资源集中在高校系统,但是高校过于重视学科建设,把主要资源都投入到了学科建设。决定学科建设能否进入一流的主要指标主要包括纵向的项目、学位点、重点实验室、戴帽子的各类人才数量、高水平论文和各类奖项等,遗憾的是新型智库的质量和数量并不在其中,这就导致大部分高校对新型智库建设都不够重视,不愿意投入真金白银。国家在一流高校里认定了14家高端智库(含培育智库),有些智库的确发挥了智库的功能,比如北大国发院、人大国发院和复旦中国研究院;但也有一些智库还是以教学研究为主,转型脚步慢了半拍;还有的高校虽然拿到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入场券,但是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于母体单位(平台单位)来说,下属智库只是众多业务单元之一,是否值得为中央/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的政策落实制定配套的细则和流程,还有许多其他考量。以高校为例,学科建设是主要任务,不可或缺,而智库建设属于锦上添花,可有可无。如果要中央/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的政策落实制定细则、配套资源,就会存在是否会激怒主体院系的问题。如果同意智库增加经费中专家劳务费用支出比例,那么非智库单位要比照执行怎么办?不同意的话,非智库单位会援例争吵;如果同意的话,科研经费中学校分成势必减少,伤及自身利益。因此,大部分高校都会对中央出台的增加经费中专家劳务费用支出比例的文件采取置之不理的做法。三明治中间层对智库宏观治理影响巨大,可以说对非独立智库而言,母体单位(平台单位)的智库治理才是最直接最关键的,中央/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的智库治理属于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如何破解智库宏观治理中的三明治陷阱呢?根本解决方法是把非独立智库变成独立法人实体机构。比如,南京大学为化解智库治理的“三明治陷阱”,就让下属的两家省级重点智库——长江产经研究院和紫金传媒智库在省民政厅注册为“民非”法人实体智库,这样一来三明治陷阱的中间层就不存在了。独立的法人实体智库可以直接执行中央/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的有关智库治理的政策文件,学校内部其他院系和研究中心也无法援引这两家智库享受的政策红利。为了让这两家智库同时利用学校资源,南京大学还发文成立了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和南京大学紫金传媒智库。南京大学通过一个法人实体两个牌子的方式成功化解了智库治理的“三明治陷阱”。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大部分智库都是附属型智库。根据中国智库索引的数据,我国智库体系中95%的智库都是母体机构下属的非法人的实体智库和非法人挂靠性质智库。这些智库外部治理结构类似三明治,三明治的上层是国家/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中间是母体单位(比如高校、社科院),下层才是智库。之所以称之为智库治理的“三明治陷阱”,是因为国家/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根本无法直接管理到这些母体单位下属的非独立智库,而是要通过母体单位(也可以叫平台单位)才能作用到智库。母体单位(平台单位)就像三明治的中间层,隔绝了国家/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和非独立智库之间的直接治理联系,国家/省市部委智库管理部门任何政策落地都需要母体单位(平台单位)制定实施细则,或者经过母体单位(平台单位)的认可同意配套相应的落地政策。比如,中央出台的增加经费中专家劳务费用支出比例的意见,如果未经母体单位(平台单位)认可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财务审批的流程,那么中央含金量很高的意见就不可能作用到非独立智库(三明治下层),非独立智库望眼欲穿的好政策由于三明治中间层的梗阻就无法落地,政策红利也就无法释放出来。
第二,新型智库建设未能有效突破体制上的“三明治陷阱”。实体数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智库研究质量的同步提升和新型体制机制的落地生根,我国智库的治理体制当前难以突破“三明治陷阱”。2018年3月,黄坤明同志在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试点工作以来,中央和有关部门在经费管理、人员出国、奖励激励、会议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政策,赋予试点单位很大的自主权和政策空间,但不少单位承接、落实还不到位,很多政策仍然悬置,人员管理、薪酬待遇、职称评定、财务管理等方面的掣肘比较突出。
2.3.4 心动过速发生率 纳入 8 个研究[6,9‐12,15‐17],各研究间为同质性(P=0.72,I2=0%),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图4)。结果显示,卡贝缩宫素组的心动过速发生率显著小于缩宫素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20,95%CI=0.12~0.31,P<0.00001)。
第三,智库的研究咨询业务过于集中政策过程的前端,业务模式头重脚轻。政策过程包含议程设置、政策辩论、决策与路演、政策教育、政策评估、政策反馈修正等,这是一个完整的“政策环”,每个环节都需要智库参加,但是每个环节需要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智库参加。如果从国家政策层面来说,在议程设置阶段和政策辩论阶段主要需要高层次高端智库参与,其他层次的智库由于缺乏全局性的视野和经验往往就不适合此项工作。可是在政策评估环节,即使是地方智库也可以从本地区出发对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开展评估和反馈。但由于我们智库考核指标设置的问题——往往给与高层次批示极高的权重,导致几乎所有智库都在思考全国性政策议程设置问题,并就此写内参、写研究报告。这种定位错误,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劳动和无效劳动,如雪片一样飞向北京的内参其实大多数是没有必要的。因此,绝大多数省级智库不应该把业务重心放到全国性政策议程设置的决策咨询工作上。
相反,大量的专业智库应把业务模式重心下移和后置,把主要精力放到政策教育、政策评估和政策反馈上来。专业智库不应该去当“国师”——为党委政府出思想、出概念和出思路,而是应该承担技术性支援工作。专业智库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是采集数据、是数据分析、是建模计算,是协助政府脚踏实地的落实政策,是用自己的数据、计算能力评估政策和项目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反馈给政府。对于专业智库来说,可能核心能力并非思想力,而是调查、数据、计算、规划、评估等能力。没有这些核心能力,智库只能开展定性研究,靠拍脑袋为政府出主意,那样业务重心就浮于表面。
第四,智库和政府内部研究机构是“两张皮”,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难以消除。智库是政府的“外脑”,政府内研究机构是“内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强调的其实是“内脑”和“外脑”的协同。“内脑”要指导、引导和推动“外脑”的对策研究,要解决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两张皮”的问题,要消除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之所以未得到有效解决,原因很多。首先,我国智库体系中高校智库比重过大。根据CTTI数据,全部CTTI来源604家智库中58%属于高校智库。这种情况得到中国社科院评价研究院的《中国智库综合评价AMI研究报告》核心智库目录的印证。该报告确定了166家核心智库,其中高校智库有79家,比重为47%。高校智库往往由传统学术研究“翻牌”而来,更擅长的是学术研究而非对策研究。高校智库因为固有的“师道尊严”文化,往往缺乏“客户第一”的服务精神。智库是一种高端的决策咨询服务工作,不管是高端还是低端,只要是服务业,没有“客户第一”的服务精神,服务工作就不可能做好。因此,让高校智库主动对接政府研究机构,心甘情愿地为政策研究部门做好技术支援性工作——调查研究、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撰写研究报告初稿,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政府政策研究部门恐怕也未必看得上智库,更不愿意和智库共享数据和信息。坦率地说,二者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政策研究部门也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忧虑。
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途径还是智库主动采用“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模式”。“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模式”是我们首次归纳的一个学术概念,指的是智库的对策研究通过嵌入政府政策研究过程解决“外脑”和“内脑”协同问题。嵌入首先说明了智库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之间存在着一定距离,存在一定的区别,嵌入也意味着智库的对策研究有独立的价值,有自己独特的属性——和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相比,智库研究可能更关心中长期问题,更关心基础问题,更关心前瞻性问题。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包括政策过程的嵌入、决策咨询流程嵌入、决策咨询场景的嵌入和政策共同体的圈层嵌入。政策过程嵌入是指智库应该嵌入一个政策的完整过程,和“内脑”开展紧密合作,从议程设置、政策辩论、决策与推广、政策执行、政策教育、政策评估和政策反馈全过程的参与和发挥作用,不仅要关心政策文本的产生,还要促进政策文本的落地以及落地后的效果。决策咨询流程的嵌入是指要在调查研究、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分析研判和撰写报告等过程中都和内脑紧密合作,充分发挥智库技术支援的优势,服务内脑的政策研究。决策咨询场景的嵌入是指积极参加领导的调研活动、决策咨询会议和政策路演活动,获得决策咨询活动的现场感与语境,如此才能了解政策产生的前因后果。政策共同体的圈层嵌入是指智库要和政府决策者、政策研究部门形成密切的联系,产生强烈的互信关系,这是其他三种嵌入的前提,也是结果。当然,政策共同体中并非只有决策者和政策研究者(内脑),还包含其他的要素,智库要和这些要素之间都形成密切的圈层嵌入。如果智库能实现四种形式的嵌入,那么就有可能解决对策研究脱离实际、不接地气、没有市场的困境,成为党委政府想得起、用得上、离不开的智库。
第五,智库成果认定与激励的指挥棒设计不合理。成果认定和激励制度是引导智库发展的指挥棒,但目前这个指挥棒设计不够合理,是制约智库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智库成果认定标准非常单一,从我们收集到的各种认定奖励文本来看,各类智库都看重批示的行政级别,无论是折算成文章还是直接奖励金钱,都是行政级别越高的批示得奖越重。这种做法简单粗暴,必然导致智库只愿意为决策者服务而不是为决策过程服务,必然导致智库只原意为高端决策者服务而不是为基层治理服务,必然导致着力揣摩领导意图的政策研究而不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的政策研究。其实,智库所承担的大量政策评估、政策宣传等工作都不会产生批示,但是这些技术支援性工作恰恰是政府更需要的。因此,这些工作都应该纳入智库成果的认定范围。政策评估等工作政府会以横向项目的形式交给智库,而在我们的智库考核体系中,横向项目恰恰是最不受重视的。我们认为,对于国家高端智库和省级重点智库而言,的确批示的权重应该大一些,因为这些智库的主要功能是咨政建言。可是对于大多数专业智库而言,用专业能力为党委政府提供技术性支援工作往往不会产生批示,对它们而言,批示就不应该是主要考核指标。
五大问题能否解决好,决定了新型智库建设下半场的成效。新型智库体系建设要解决智库产业的集中度和集群性问题,实体化和法人化是解决体制机制创新、克服“三明治陷阱”的重要途径,业务重心下移和后置是解决智库浮于表面注重形式传播问题的重要思路,而推行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模式是解决政策研究与对策研究衔接、发挥内脑和外脑协同研究效应的重要选择,智库成果认定与激励措施的调整则是最重要的保障。
Innovation Mecha nism,Focus Shift and Embedded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peration&Business Model:The Second Half of the New Think-Tank Initiativ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 G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he general preface to “Think Tank Series of Nanjing University”,written by Professor Li Gang.According to the timetable put forward in the Opin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five years since 2013 is the first half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the next three years after 2018 will be the second half.The first half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By the end of 2017,there had been nine categories of totally 604 think tanks,distributed in more than 50 strategic and policy areas;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of think tanks have explored a lot of experience and many cases that deserves being cited have emerged.At present,people from all fields of society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has inherite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 of“learning for politics”,and promoted the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rationality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 ess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is to open the way of expression,to establish institutionalized channels of exchanging opinions of“government-knowledge”,“government-property”,“government-media”and“government-society”,and to encourage the enthusiasm of the intellectual elit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governance;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promotes the rational“second public policy space”which is conducive to policy debate.The second half of the new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is facing five challenges:the low concentrat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 of the think tank industry is still“scattered”,“weak”and “small”;the new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has not effectively broken through the“sandwich trap”of the system;the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business of think tanks is too centralized in the front end of the policy process,which makes the business model become top-heavy;think tank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within the government are“two skins”,an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cannot be eliminated;the design of the baton for identifying and motivating the results of think tanks is unreasonable.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ncentration and clustering of the think tank industry,the new think tank system has to be built.Substanti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are the two important ways to improv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overcome the“sandwich trap”.The downward shift and postposition of business focu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ink tanks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form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surface.The implementation of“embedded decision consulting service mode”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cohesion between policy research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as well as the collaborative effect between internal brain and outside brainpower.Adjust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nk tanks and incentive measures is most importa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
Keywords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think tank industry cluster;second public policy space;sandwich trap;embedded decision consultation service mode;identification of think tanks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项目编号:17JZD009)中期研究成果之一。本文系李刚教授为“南大智库文丛”所作新序,本刊发表时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 李刚,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lamligang@163.com。
收稿日期 2018-09-24
(责任编辑:刘洪;英文编辑:郑锦怀)
标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论文; 学为政本论文; 智库产业集群性论文; 第二公共政策空间论文; 三明治陷阱论文; 智库成果认定论文;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论文;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