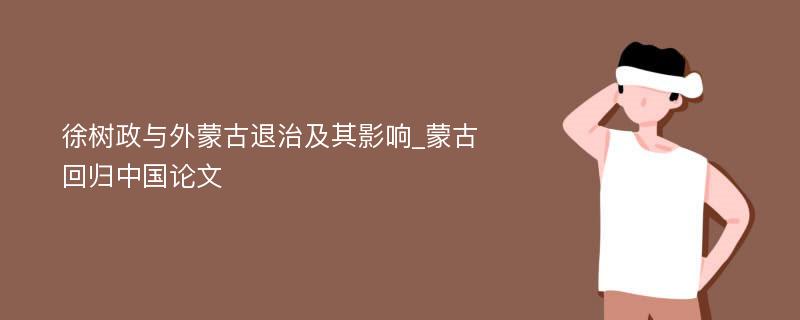
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蒙论文,徐树铮论文,古撤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9年6月13日,皖系的徐树铮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总揽了热河、察哈尔、绥远、甘肃、新疆、内外蒙古诸省及地区的行政、军事、财政等大权。任内,成就了轰动全国的外蒙古回归祖国之事业。1919年11月,外蒙古“情愿撤消自治”,统一于中央。这一事件对国家和对徐树铮本人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外蒙古回归,对徐树铮个人所具有的重要性是不能低估的,这是他自认为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作为北洋军阀的重要一员,他被公认为是段祺瑞的心腹灵魂。皖系当权时期,他对内执行“武力统一”政策,操纵安福国会,纵横捭阖,玩弄政治。对外,卖国媚外,与日本签订了出卖利权的军事协定。但就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徐树铮,在主持撤治交涉的短短几天时间内,就和平地圆满完成了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历史使命,为国家立下了其他军阀望尘莫及之功绩。
在此,本文试图客观地再现这段历史,藉以说明徐树铮在撤治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展示其政治形象中积极有为的一面,尽可能客观立体地认识徐树铮。同时,本文还将就外蒙古撤治对其自身和对民国外交、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加以探讨。
一、圆满促成外蒙古撤治
1919年的外蒙古,地域范围包括喀尔喀四部: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三音诺颜汗及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二区。其政治体制是根据袁世凯政府所签订的《中俄声明》和《中俄蒙协约》确定的名“自治”实独立的政权统治,即中国不得在外蒙古派驻军队、建立与内地相同的行政组织和进行移民,设于库伦的外蒙古自治官府实质上完全独立于中央政权之外。撤消自治则是在1919年(民国八年)8月4日的库伦大会上由王公首次提出的。他们向中央驻库伦都护使陈毅陈明愿取消自治,归向中央。撤治问题先是由陈毅负责交涉,但是,直至徐树铮强揽交涉权之前,历时逾三个月,陈毅却始终未与自治官府进行过公开正式磋商,只是私下与王公公推的代表、自治官府外交总长车林多尔济议定了《外蒙古撤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古及善后条例》六十三条草案。依据草案条文规定,不仅中央在外蒙古行使完全主权将是徒托空言,而且撤治后由王公总揽政权结束喇嘛柄政局面,因此引起了以活佛为首的全体喇嘛的强烈反对。尽管王公于10月底单独递呈撤消自治请愿,但喇嘛的态度却更加强硬,根本无意让出政权,双方达到了势不相容的地步,活佛更派人入京诬蔑陈毅并要求将其撤回。至此,陈毅根本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一筹莫展,撤治交涉陷入僵局。陈毅交涉的失败,造成了民国外交、政治上的棘手局面。嘉亨尊活佛入京,“意欲请美使援助”,(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59年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72页。)俄、法等国也分别就喇嘛入京事提出问讯。陈毅交涉过程中出现的先与王公议定条件而非先请撤治的程序问题导致中央政府在外交上陷入被动。外蒙古孤悬西北,强敌环伺,同时面临着急于取俄自代的日本与虎视眈眈的俄国旧军官谢米诺夫等侵略势力的巨大威胁,处境日益危殆,长此延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此时,有两种选择:要么,外交上畏首畏尾,坐视自治官府内讧,侵略势力趁火打劫,外蒙古难免割裂厄运。要么,在尊重蒙人意愿的前提下,和平地排除阻力,实现外蒙古真正回归。其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当机立断选择了后者,赴外蒙古于危急之时。他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29日抵达库伦,针对内阁给陈毅的不准徐树铮过问撤治交涉的阴令,于11月10日向中央政府坚决表示,西北筹边使“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自己“一日不离职……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注:《收西北边署抄送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85页。)随之将交涉权从陈毅手中强夺过来。在11月11日会同都护使陈毅、副都护使恩华、李垣及褚其祥旅长与杨志澄参议就撤治事宜进行磋商的会议上,徐树铮明确提出两条新的交涉原则:其一,主权原则。撤治后政权应收归政府,不能政府收其名,王公收其实。其二,策略原则。关于交涉对象,当时情况下,以喇嘛为主。这两条俱是针砭陈毅交涉失败症结而提出的,对打开交涉局面非常迫切和必要。综观此后徐树铮主持的撤治交涉,正因为全面贯彻了这两条原则,并与灵活的策略手段相倚为用,方较成功地勾勒出民国以来中蒙关系史上之绝笔。
在交涉过程中,坚持以喇嘛为主要交涉对象的策略原则。徐树铮一改陈毅以王公为唯一交涉对象的做法,采取以喇嘛为主要交涉对象的新原则。这个变化基于两方面的现实考虑。一方面是鉴于在撤治问题上喇嘛所持的强硬态度,说明促成撤治的关键在于争取其政治态度的内向转变。外蒙古官僚政治体制,在前清为政教分离,黑派王公治政,黄派喇嘛管教,各有所司。民国后,伴随着外蒙古分裂与自治官府的建立,形成了喇嘛把持政权的局面。王公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力,也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爱国心,自请取消自治制度,以便摧毁喇嘛柄政的政治法律依据,撤治是其一致的意愿。这同时注定了喇嘛为维护既得权位,对王公所提出的撤治倡议持有敌意。透析时局表明,欲取消自治制度,必须促成控制自治官府的喇嘛势力自愿放弃自治,这是扭转局势的关键。因此,徐树铮明确表示:“活佛强制之力尚在,纵全数王公迫请,而活佛不应,终无如何。故喇嘛一流人物,未可过于抛荒。(注:《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四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75页。)另一方面是基于宗教在外蒙古政治与民众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以活佛为首的喇嘛宗教势力既把持着政权,成为政治权威之源出,又是蒙古人民精神支柱的体现。这种特殊的政教合一的尊崇地位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种事实,即喇嘛的政治倾向直接影响着广大蒙古人民所持有的政治态度。对此,徐树铮有清醒的认识,认为,外蒙古能“自团结者,厥惟宗教是赖。即王公之于蒙众,亦非藉宗教之力,不能行其权”。(注:《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四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75页。)所以,交涉僵局出现后,漠视喇嘛为交涉大忌,应全力以喇嘛为交涉对象。
围绕这一策略原则,徐树铮从几方面入手,努力去缓和喇嘛对交涉官员的敌对情绪,以图打破僵局,力促其早日主动撤治。据他观察,要打开缺口,取决于喇嘛高层人物的态度,主要有四人:巴特玛多尔济、大沙毕商卓特巴、绷楚克、棍布。其中,巴特玛多尔济任自治官府总理兼内务总长,是最关键的也是徐极力争取的人物。徐树铮对其“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注:《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93页。)表示对他在自治官府中重要地位的认可,加以感化,希望能有助于他尽快转变态度。同时,又对症下药,“崇以荣观”,与怀感联络交互为用。交涉过程中巴特玛多尔济提及希望中央册封他为亲王。王爵册封权于外蒙古自治后即归活佛掌有,结果,造成了封王过多、册封不公之弊。上述四人中,巴特玛多尔济年龄最长、权位最重,可其他人封亲王,他却只有王衔,对此,他心蓄不满。徐树铮当即向其许诺一旦撤治完成,即由中央加封他为亲王,“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双俸”,(注:《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93页。)作为对其发挥重要作用的褒崇。并保证也不变动活佛所享有的宗教礼仪与待遇,“不令佛有失体面”,打消活佛的担忧。对活佛、喇嘛的这些许诺,完全符合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并非徐树铮个人的虚妄之言。早在10月底,中央政府就明令“此次凡有助取消助力之喇嘛等,如愿意封爵者,皆可听”。(注:《吴局长说帖》,《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54页。)上述“一意向喇嘛示好”的争取手段,近则有利于消除喇嘛对中央的隔阂与疑虑,加强双方的了解与沟通;远则初步昭示着中央政府对外蒙古比较宽松的政治态度,从而为交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良好基础。与联络争取喇嘛相辅相成的是,徐树铮又极力向其展示中央在外蒙古所具有的保护能力。防卫力量严重不足,一直是外蒙古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据统计,外蒙古武装力量包括自治官府驻库伦军队约千余人,外加各王公旗下现役兵,总共不过五千余人。军队武器落后,平时毫无训练,战斗力极为薄弱。早在陈毅主持交涉时,王公就曾提出希望中央出兵帮助卫护蒙疆。为了解除自治官府的后顾之忧,随徐树铮驻库伦的西北边防军褚其祥旅便被赋予了这一重任。西北边防军是当时国内装备最为精良的一支武装力量,徐树铮通过不断地向喇嘛展露褚旅的先进武器装备、整肃的军容军纪与团结一致的军心,以此说明中央在外蒙古确实具备了保护蒙疆的国防能力。西北边防军进驻库伦,安定了人心,为外蒙古官民抵抗外来侵略势力的侵扰提供了切实依托,从而无形中化解了撤治交涉过程中的一大障碍,对喇嘛态度的转变应具有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交涉过程中,徐树铮还坚定地恪守撤治务求其实的政治原则。关于撤治条例,他特别强调条文大意,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各种意见愈易丛杂,将来梗阻,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注:《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四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76页。)徐树铮初到库伦时即指出六十三条例有七不可,于主持交涉之始,即完全抛开了对中央主权及撤治完成均不利的六十三条。关于新条例的议定,坚持务求简略的指导思想。追求条例内容的“简”是实现中央在外蒙古主权“实”的前提,因为只有避开黑黄二派关于未来权力的争执,才可能实现王公、喇嘛对撤治的一致赞同,方可早日恢复我国在外蒙古的主权;同样,只有简略,中央对外蒙古行使治理权才不会因受各种因素的掣肘而流于空言,双方关系才能真正走上正轨,建立起合乎主权原则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因此,在同巴特玛多尔济谈及撤治条例时,徐树铮坚持以简略为准,甚至认为无需条件,一切留待撤治后再酌商议定。总之,通过以上种种交涉活动,针对撤治交涉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障碍,徐树铮有的放矢,一一化解了喇嘛藉以反对撤治的顾虑与口实,并在切实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使外蒙古自治官府初步了解到中央对撤治后的外蒙古所持有的较宽松的政治态度。至14日,除了活佛态度尚不明确,撤治的其他阻力基本解除。
最后,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与外蒙古政情,徐树铮审时度势,恩威并施。进入撤治交涉的最后时刻,为了顺乎蒙情促使活佛尽快明确态度,徐树铮不惜采取他自谓为下策之举,对活佛与巴特玛多尔济施加压力,先以蒙情极度危急,长此以往,活佛与巴特玛多尔济难以承担祸蒙之罪相警示,进而以不得已之时拿解二人相恫吓,希望借此帮助活佛做出顺乎民心与潮流的明智抉择,迅速和平地完成撤治,使外蒙古导向稳定、光明的政治前途。很快,11月17日,王公、喇嘛联名具呈的请愿撤治呈文由都护使陈毅与筹边使徐树铮分别电达北京。11月22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令正式布告外蒙古撤治“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注:《大总统令》,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602页。)棘手的撤治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徐树铮自11月11日主持交涉,至17日外蒙古自请撤治呈文即正式电达中央,他是如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此建树的呢?实则,徐树铮很早就为此间的交涉做了大量准备。在到达库伦之前,作为其职权范围,对撤治事就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对喇嘛、王公之争有基本的了解,明悉外蒙古面临的外来威胁,并对六十三条做了研究。及至库伦后,尽管有内阁禁令,但他仍就一些具体问题积极发表见解,并亲自面见活佛,了解情况。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他很快就明了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相应的解决办法也已成竹在胸,这才促成了随后亲自主持交涉时能够坚定地有条不紊地推进交涉,取得比较快速顺利的进展。此外,徐树铮之所以能迅速完成撤治这一重大历史使命,是他及时地把握住了有利时机,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撤治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它简单是指,到1919年,主张撤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归向中央,王公心仪已久,即使对于喇嘛,这也是一种现实的考虑。因为此时的自治官府内外交困,政治经济面临严重危机。政治上,同时面临着日本的侵略野心与谢米诺夫等的分裂煽惑,而无论哪一方势力,都是自治官府所不愿与之合污的。库伦大会上,王公、喇嘛共同拒绝谢米诺夫的分裂盅惑以及对日本侵略企图的恐惧,即是明证。经济上,自治官府债台高筑,陷入全面危机。此时,它唯一的正确出路就是回归祖国,借助中央政府的力量,抵御外来侵略势力,恢复和发展外蒙古社会经济。因此,重新统一于中央政权,是外蒙古社会发展的必然,是任何政治力量所无法违背的。这决定了撤治具备着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但复杂的是,人们往往易被喇嘛的表面态度所迷惑。分析表明,多方面现实因素的作用决定了喇嘛对中央的态度注定具有回归倾向。交涉过程中,他们之所以反对撤治,主要是由于害怕撤治后完全丧失对外蒙古政权的控制,以及对防卫力量与撤治后中央对蒙政策等问题存在后顾之忧。如果认识不到喇嘛对撤治态度的两面性,交涉就会陷入曲折。陈毅就是因没有明析这一点,始终把喇嘛看成是撤治的真正敌对力量,故而长时间交涉却毫无进展。反之,如果能切中问题的要害,撤治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是徐树铮成功之所在。他洞悉喇嘛的处境与顾虑,抓住有利时机,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于交涉出现危机之时,力挽狂澜,很快促成外蒙古自愿撤治。所以,有利的契机,充分的准备,正确的方针策略,很强的控制和推进时局发展的能力,是徐树铮短时间内促成撤治成功的要素。
对于外蒙古撤治之功绩归属,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陈毅运动蒙人,取消自治已将成熟”,徐树铮却坐收渔利“据为己有”。(注:《徐树铮正传》,中央国史编辑社1920年版,第22-23页。)《安福部》也认为,“数年他人力征经营之苦功尽为树铮所攘夺”。(注:《安福部之筹边》,《安福部》中编,宏声报社1920年印,第20页。)根据前面的分析说明,陈毅的交涉不仅未能实现中央政治上恢复对外蒙古治权的根本目标,而且,由于六十三条例的议定,使交涉全面陷入窘境。故无所谓“陈毅之功垂成”,却为徐树铮据为己有之说。徐树铮主持交涉仅几天时间,就打开了陈毅交涉造成的僵局,和平地完成了外蒙古回归祖国之重任。这一客观事实不容漠视,其功绩也是任何人无法取代的。
二、外蒙古撤治的社会影响
外蒙古回归对民国外交、政治及外蒙古社会自身均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
外蒙古撤治,对外粉碎了一切侵略、分裂外蒙古的阴谋活动,维护了祖国北部边陲的稳定。20世纪以来,我国北方边陲有两大威胁,一来自俄国,一来自日本。1911年10月,帝俄策动外蒙古独立,不仅控制着外蒙古的内政外交,还通过《俄蒙协约》、《俄蒙商务专约》等条约,操纵了其经济,疯狂掠夺外蒙古资源。俄国十月革命后,日本企图趁俄在外蒙古的侵略势力瓦解之际,谋求取俄自代,建立日本在外蒙古的特权和控制地位,造成其势力范围由内蒙古扩张到外蒙古、独控外蒙古的远东政治新格局。对日本的这一侵略阴谋,中央政府早已察觉。在整个撤治交涉过程中,中央始终认为外交上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其狡恶思逞者,惟一日本”。(注:《交通部说贴》,民国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34页。)这个时期,日本对外蒙古采取的是相对隐密的侵略方式。1918年上台的原敬内阁在西方列强压力下,表面上标榜对华不干涉,但实际上其侵略活动仍然昭彰若揭;侵略手法上采用暗助谢米诺夫与蒙古分裂势力煽惑胁迫外蒙古脱离中国的侵略、分裂活动,藉以实现其侵略野心。对此,我们可列举多项事例加以说明。例如,我国驻西北官员多次电陈:谢米诺夫之属员称日本“允供给枪械”,(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六月二十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415页。)在煽惑外蒙古独立过程中,“其中且有日本某军官主使一切”。(注:《收驻鄂木斯克总领事[范其光]电》,民国八年七月八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429页。)外交部也得到了有关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与侵略势力布里亚特人会议及宴会的照片。如此不一而足,这些都是日本侵略活动不争的事实。1919年(民国八年)11月17日外蒙古就内向发表声明:“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概无效力”。(注:《收库伦都护使陈毅电》,《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92页。)这不仅正式宣告将俄国残余势力从外蒙古完全清除出去,而且,外蒙古回归,有力地摧毁了日本取俄自代的侵略计划,沉重打击了日本在华侵略势力,一时遏制住了其在我蒙疆的侵略势头,从而解除了外蒙古人民“深恐日人借此攘夺蒙人利权”(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八月十六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462页。)之担忧。除此之外,企图将外蒙古从中国领土割裂出去的另一种势力是以谢米诺夫为首的侵略势力。1919年春天,在日本的支持下,俄旧军官谢米诺夫与内蒙古分裂分子共同组成反动政权——大蒙古国,并一厢情愿地将地域范围包括布里亚特、呼伦贝尔及内外蒙古。声称:“在蒙国边界所有同种部落,议定一律保护其土地”。(注:《收库伦都护使署公函》,民国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562页。)由于他们的骚扰威胁,中国的北、西、东三边不同程度地面临危机,其中尤以外蒙古最为严重。为了策动外蒙古分裂,他们三次前往库伦,鼓吹种族分裂,煽惑胁迫自治官府,武力侵犯唐努乌梁海等地区,对外蒙古回归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与后顾之忧。不仅如此,其侵略目标还指向满洲里与西藏。总的看来,在动荡的北部边陲局势中,外蒙古的地位至关重要,“外蒙古设有动摇,西北领土将全体瓦解”。(注:《收驻库大员[陈毅]电》,民国八年六月十一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409页。)而今,外蒙古自请内向,拒绝分裂,使这股势力将外蒙古从我国分裂出去,建立由他们控制的傀儡政权的阴谋活动彻底失败,从而稳定了我国西北部边疆局势,对我国对外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外蒙古回归,有效地维护和实现了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与统一,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至此,蒙疆两地方政权实现了由实际的独立向统一于中央主权的地方政权的转变。至11月下旬,《中俄蒙协约》确定的名“自治”实独立的外蒙古政权体制被新确立的中央对外蒙古名符其实的主权关系取代,中央政府得以再度在外蒙古设官、驻扎军队,行使对这一地区的管辖与治理权。这是徐树铮促成外蒙古撤治的突出贡献,对此,孙中山先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外蒙古……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感慨“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注:《复徐树铮电》,《孙中山全集》(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9页。)
外蒙古回归,政治上对呼伦贝尔产生了积极影响。黄教是蒙古民族共同的宗教信仰,作为宗教领袖所在地和宗教势力中心的库伦对呼伦贝尔有着独特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外蒙古撤治对呼伦贝尔的影响更因撤治前两地具有的相同政治背景与政治态度而加重。辛亥革命后,库伦与呼伦贝尔政权俱是俄国借辛亥革命之机策动指使分裂势力武装颠覆我国在两地的治权而建立的完全由其控制的名“自治”实独立的政权,这种特殊的政治联系,无形之中加深了外蒙古新的政治归属对呼伦贝尔的影响作用,带动了呼伦贝尔迅速做出了顺应潮流的正确抉择。1919年12月下旬,呼伦贝尔正式致电中央,谓“因外蒙古……将治权归还中央”,“呼伦贝尔所有区域……商请仿办”(注:《民国日报》1919年12月27日,第663页。)撤消自治,听候中央政府治理,并宣布民国四年我国被迫签订的中俄《呼伦贝尔条约》无效。总之,外蒙古与呼伦贝尔的失而复归,使辛亥年以来被割裂的领土与主权再度回归与统一,从而实现了民元肇造者们追求的五族共和的统一民国,历史的遗憾得以弥补。
外蒙古自请撤消自治,为本地区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历史的沉淀,中央在外蒙古的主权并非仅如条文规定的那样简单明了,尚需经历一个敏感的巩固期。外蒙古能否长期内向统一,其中政治治理外蒙古的社会效果是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对此,徐树铮有清醒的认识。当人们尚沉浸于外蒙古回归的喜悦之中时,他就精辟地指出:“蒙事重在将来启导其文明,不在今日名义之间也”。(注:《收西北筹边使[徐树铮]库伦来电》,民国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1919),第601页。)充分估计到治理蒙疆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在外蒙古实施了以启导文化、发展经济为核心的全面开发治理活动。就如何治理外蒙古,徐树铮有一套系统的治蒙设想作指导,这一设想早在1919年4月17日就以条陈的形式提了出来,内容涉及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及至外蒙古归诚,由于具备了有利的社会政治环境,而且,徐树铮也可以自如地行使权力,将治理外蒙古的设想付诸实践,使对外蒙古的治理发展活动一度出现了比较活跃的局面。其中,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主。外蒙古的经济窘况历来比较严重,以致于这往往成为决定其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经济上的依附导致政治上受俄国控制即是明证。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外蒙古经济的落后局面,推动经济的发展,徐树铮采取了恢复和活跃商品经济、稳定货币金融、振兴实业等多种举措。早在撤治前,外蒙古金融即陷入紊乱,严重危害了商民利益,为了恢复经济、整理金融,徐树铮在库伦开办边业银行,发行以骆驼队为图案的钞票,稳定货币。此举不仅有利于经济秩序的较快恢复,而且也可为外蒙古的开发筹措部分资金。外蒙古地下资源丰富,矿产种类繁多,地方财政经济却极端窘迫困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徐聘请德籍化学教授巴尔台来蒙实地考察,以便拟定系统的开发计划。藉开辟地利,推动外蒙古近代实业的起步,为外蒙古地方财政找到强有力的支撑点。此外,经济治理还包括促进内地与边地的经济交流,鼓励内地商人来蒙贸易、保护蒙人切身经济利益及发展汽车运输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一系列的开发活动,徐树铮为外蒙古设计了一个崭新的发展前景。与此同时,徐树铮始终很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一再倡行教化。虽然由于资金的限制,及徐树铮很快离库返京,许多发展规划或付诸流水,或半途而废,但是,徐树铮在治理外蒙古期间所采取的推动外蒙古经济、文化发展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包括实施的各项具体措施与设计的长远规划,都是围绕建立自立的地方经济与提高整体文化素质这一根本目标而展开的,它适应了外蒙古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利于外蒙古的政治稳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
外蒙古撤治成功给皖系军阀带来了巨大利益,对派系斗争产生了深刻影响,兹不加赘述。然综观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作为北洋时期的军阀人物,这一历史举措无疑是值得肯定和赞许的。这也是徐树铮乃至北洋政府的政治活动中少有的亮点之一。可悲的是,外蒙古不久后的得而复失,又使之黯然失色。所以,军阀政治、军阀政治家纵使一时把握千载良机,也会因其反动本质而最终葬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