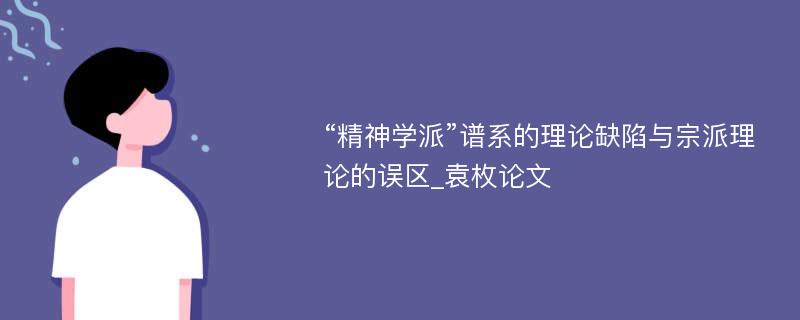
“性灵派”谱系的理论缺陷及就宗派立论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谱系论文,性灵论文,宗派论文,误区论文,缺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1)11-0030-03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存在一个标举“性情”或“性灵”的庞大诗歌创作群体。他们提倡自由抒写反对各种形式主义诗风,在文学史上被称为“性灵派”。“性灵派”谱系是以“性灵派三大家”为中心提出的。“性灵派三大家”指乾隆时期诗坛重镇袁枚、赵翼以及在乾嘉之际备受瞩目的翰林诗人张问陶。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年进士,著名诗人,世称“随园先生”。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探花,著名史学家、诗人。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遂宁(今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被誉为“蜀中诗人之冠”。“性灵派三大家”是近年流行的新提法,它由此前流传甚广的“乾隆三大家”演变而来。“乾隆三大家”指袁枚、蒋士铨和赵翼。清人尚镕《三家诗话》载:“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而才情学力,俱可以挫笼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帜而起,震耀天下。”[1]
“三大家”并称本是基于其才情、学力及声望并驾齐驱,与诗学观点和创作风格无涉。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首次从诗论主张的角度提出:“袁、蒋、赵三家并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同……宜以张船山代之。”[2]这一看法是“性灵派三大家”说的源头。上世纪90年代,钱仲联、严明发表《袁枚新论》,“从诗坛盟主影响一代诗风的角度”,提出了在乾嘉之际“以袁枚为主帅,赵翼、张问陶、孙原湘等人为羽翼的性灵诗派风起云涌,称雄诗界”的观点。[3]沿着这一思路王英志从“性灵说”内在传承关系的角度提出:“如果说性灵派于乾隆时期以主将袁枚、副将赵翼为代表人物,那么于嘉庆年间则推张问陶为重镇。”[4]这一提法在稍后发表的《袁枚于乾嘉诗坛的影响》[5]、《性灵派三大家简论》[6]中得到重申。至此一个以袁枚为“主将”,赵翼、张问陶、孙原湘等人为“主力”,袁氏家族诗人及随园女弟子为“偏师”,蒋士铨、黄景仁、李调元、陈文述、宋湘等名家为“同盟军”,网罗乾嘉时期众多著名诗人的“性灵派”谱系逐步形成。
一、“性灵派”谱系的理论缺陷
“性灵派”谱系的提出填补了清代性灵诗歌研究的一项空白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此说高估了袁枚诗派的影响力,存在不容忽视的理论缺陷。
首先,谱系内的诗人在创作旨趣、风格及具体诗法上存在很大差异。标举“性情”或“性灵”是众多诗人被归入“性灵派”的直接理由,然而他们对“性情”或“性灵”的理解却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导致了创作主旨、艺术风格及具体诗法等诸多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袁枚《钱玙沙先生诗序》云:“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焉。”[7]可见“性情”和“灵机”是袁氏“性灵说”的核心内容。古人使用术语前往往缺乏对术语本身的精确定义,“性灵派”谱系内的诗人对“性情”和“灵机”的具体理解就很不相同。以“性灵派三大家”为例,袁、赵、张三人对“性”与“情”关系的认识就存在根本分歧。袁枚在《书复性书后》中专论“情”的关键作用云:“性不可见,于情而见之……孔子之能近取譬,孟子之扩充四端,皆即情以求性也。”[7]可见“情”在其诗论中占有核心地位。他甚至说“天性多情句自工”,认为“多情”是写出好诗的充要条件。然而“情”有很多种,诗人应重视表现哪种“情”呢?传统诗教强调作诗须体现“性情之正”,以艳体为下品。袁枚却认为:“一往情深,言由衷发……夫亦何伤于人品乎?”[8]其《答蕺园论诗书》明确提出:“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7]赵翼思想中正,故不认同袁枚偏好艳体的立场。他曾戏控袁枚于巴拙堂太守云“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9]要求太守秉公办理,予以惩戒。虽以戏言出之,他还是借此明确表达了自己和袁枚思想观念上的分歧。和袁枚强调人品与诗品无涉的立场相左,赵氏始终坚持以一代史家的眼光,知人论诗。时人论宋诗往往认为苏轼胜于陆游。赵翼却指出苏轼在“乌台诗案”后“不复敢论天下事”,而陆游“以诗外之事尽入诗中”,“命意既有关系,出语自觉沉雄”,并由此得出“陆实胜苏也”的结论。[10]张问陶亦强调“人品”与“诗品”的统一。梅成栋《六匹心声诗序》载:“昔先师遂宁张船山先生与栋论诗曰:‘未观诗品先观人品,未有人品不立而诗品可传者。’又云:‘人有奇气方能言诗。夫所谓奇气者,非激烈昂藏剑拔弩张之谓,性天之内必有。不容已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至而后流露于飞潜动植风云月露间,皆足以发其悱恻芬芳之旨,而达其温柔敦厚之思,三百源流昭揭于此。’”[11]正由于强调“悱恻芬芳之旨”和“温柔敦厚之思”,故张氏重视性情之“真”的同时,亦提倡性情之“正”,创作旨趣和袁枚大相径庭。朱文治《书船山纪年诗后》比较二人诗风云:“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迹绕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风骚又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川东老史臣。”[12]
袁、赵、张三人对“灵机”的强调程度也很不相同。“灵机”指诗人所具备的灵性,也称灵感。袁枚最重“灵机”,认为村童牧竖之辞非学士大夫可及。他强调:“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甚至追求作诗“不用一典”[8],故袁诗给人以不重规矩,轻视学力的印象。赵翼论诗也谈灵感,但更强调学力的作用。他曾指出:“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诗人不得不用书卷也。”[1]钱大昕《瓯北集序》论赵诗“有兼人之学”亦指出了其学人之诗的本色。张问陶认为灵感在创作中仅起辅助作用,其《论诗十二绝句》云:“凭空何处造情文,还仗灵光助几分。”[13]对用典的问题,他在《使事》中提出“莫须矜獭祭,集腋要成裘”[13]的主张,既反对搜奇逞博,又强调合理征引,与袁、赵的主张鼎足而三。
其次,“性灵派”谱系内的诗人并不都认可袁枚的诗歌创作。
盟主是一个诗派理论和创作的旗帜,诗派成员在这面大旗下集结,自当对其大力推崇,然而“性灵派”谱系内的一些诗人却质疑袁枚的诗歌主张甚至明确反对将自己归入“袁派”:且不论对“三家说”不置一词的蒋士铨,“肌理派”盟主翁方纲的诗弟子宋湘,即使被称为“性灵派”主力的赵翼、张问陶也对袁诗颇有微词。
赵翼为袁枚作诗时有微词,并不限于向巴拙堂太守作控词而已。他曾称赞蒋士铨“名高久压野狐禅”[14],“野狐禅”即袁枚。《偶阅小仓山房诗再题》亦有“惹销魂亦野狐精”之句。他早年虽默认“三家说”以为标榜之资,内心深处却未必视袁诗为正法眼藏。
相比赵翼,张问陶的立场更加鲜明。张、袁相识缘于洪亮吉的推荐。乾隆五十八年(1793)洪亮吉对袁枚屡屡称道张问陶,袁枚作书答曰:“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张问陶听说后“自检己酉以来近作,手书一册,千里就正”。袁枚收到诗册后称张氏“肯如此撝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15]有论者据此认为张问陶对袁枚极为推崇,而袁氏引之为“生平第一知己”亦可谓“厚爱之至”[4],此说恐未得本意。从上下文分析,张氏录近作“就正”是出于对一位八旬前辈说“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一席话的感动;而袁枚引一个小自己五十岁的后辈为“生平第一知己”则更多是对其“撝谦”态度的赞赏,不宜视为他们诗学主张一致的旁证。乾隆五十九年(1794),张问陶听到有人议论他诗学袁枚,立即作诗云:“汉魏晋唐犹不学,谁能有意学随园”[13],褒贬之意甚明。他还在与袁氏诗弟子的交往中不止一次表示:“催来好雨留宾易,谈到随园下笔迟。”“文心要自争千古,何止随园一瓣香?”[13]因此不能仅凭一些空泛的恭维话判断他认同袁枚的诗歌创作。
第三,判断某个诗人是否归属“性灵派”的尺度不统一。
乾嘉时期另一些标举“性情”的诗人无论论诗主张还是作品风貌都与“性灵派”成员非常接近,却被排除在该谱系之外,其中以洪亮吉最为典型。
洪亮吉(1746-1809),字稚存,号北江,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榜眼,时人以“经术词术,并登峰而造其极”誉之。[16]就论诗主张而言,洪氏最重“性”、“情”,强调诗歌创作须出自肺腑。他在《读雪山房唐诗选序》中尖锐批评“格调说”:“文悫(沈德潜)则专主体裁,而性情反置不言,其病在于以己律人,又强人以就我。”[17]他对考据诗风也甚为不满,作《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讥之云:“只觉时流好尚偏,并将考证入诗篇。美人香草都删却,长短皆摩击壤编。”这些主张与袁枚“性灵说”的立场完全一致。就创作风格而言,洪亮吉与张问陶相当接近。洪氏曾感叹己诗和张诗神似云:“我诗与君诗,识者不能别”。张问陶《华阴客夜读卷施阁诗文怀稚存》诗回忆与洪氏论诗受教云:“敢为险语真无敌,能洗名心更不群。死有替人应属我,诗多奇气为逢君。”他甚至感叹:“大笔一枝山万仞,题诗何日与君同?”明确地表达了在诗歌创作上欲踵武洪氏的意愿。金天羽《答樊山老人论诗书》亦从清代诗风嬗变的角度将二人相提并论云:“有清一代,诗体数变:渔洋(王世祯)神韵,仓山(袁枚)性灵,张(问陶)、洪(亮吉)竞气于辇毂,舒(位)王(昙)骋艳于江左。”[17]就交游情况而言,除与张问陶堪称莫逆外,洪亮吉与赵翼、袁枚都有很深的渊源。洪、赵同为阳湖人。嘉庆五年(1800)赵翼作《题稚存万里荷戈集》有“人间第一最奇境,必待第一奇才领”之叹,并以李白、苏轼喻洪氏。此后两人唱酬频频直到嘉庆十四年(1809)洪亮吉逝世,赵翼痛悼云:“老我独伤同调尽,共谁茗碗作清谈。”[18]洪亮吉与袁枚早在乾隆三十五年(1770)就已相识。袁氏谓洪诗“有奇气”,“逢人辄颂之”。其《仿元遗山论诗三十八首》第二十七首有“常州星相聚文昌,洪顾孙杨名擅场”句,以亮吉为常州诗人之首。他晚年写给张问陶的信中亦盛赞洪氏,称之为“旷代逸才”。和张问陶一样,洪亮吉对袁诗也持批评的态度,但他同时承认自己直接受到过袁枚诗论的影响。读洪氏《三与袁简斋书》知其早年作诗好用古字,袁枚曾作书规劝云:“前礼吉喜作古字,先生自数百里移书规之,礼吉至今服膺。”洪氏在《答随园前辈书》中亦提到袁枚“教以自成一家之言,实于亮吉有师友渊源之益。寻山识路,饮水知源。虽取径不同,洵瓣香之有在也。”[19]
划分一个文学流派应该采用统一的尺度。如果亲口否认诗学袁枚的张问陶可被视为袁派后劲的话,那么与之诗风高度相似且主动承认与袁枚有“师友渊源之益”的洪亮吉是否该归入“性灵派”谱系呢?情况与洪亮吉类似的还有孙星衍、黄景仁、法式善等一大批著名诗人,他们的流派归属又该如何看待?
二、两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性灵派”与“随园派”
“性灵派”一词最早见于二十世纪中期的文学史,与“格调派”、“肌理派”对立存在。然而“性灵派”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其边缘非常模糊。乾嘉时期反对形式主义诗风,重视创作个性的诗人都可以被视为该派成员。“随园派”这一称谓则出自袁枚本人。韩廷秀作《题刘霞裳〈两粤游草〉》云:“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袁枚读后云:“余道此诗,亦‘随园派’。”[8]照韩氏的标准凡主张表现“性情”的诗人都是“随园弟子”,此说意在为袁派造势。袁枚素有开宗立派的强烈意愿,故顺水推舟地予以肯定。事实上,与之同时代的郑燮、蒋士铨以及年辈稍后的洪亮吉、法式善等虽标榜性情,却都不信奉袁枚的“性灵说”。“性情”与“性灵”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法式善曾指出:“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门人鲍鸿起文逵辨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于礼义,而泽之以风骚……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将不可胜言矣。’”[20]法式善、鲍文逵力辨“性情”和“性灵”,正是要在袁枚“性灵说”的追随者和其他重视“性情”的诗人之间划清界线。
即便就标举“性灵”而言,袁枚也没有首倡之功。他的“性灵说”远绍南朝钟嵘与南宋杨万里,近承晚明公安派余绪。风行于乾嘉时期的“性灵思潮”其实是一种具时代意味的思想倾向,“性灵诗人”的称谓并不专属于袁枚及其拥趸。“性灵派”谱系说的支持者都相信“随园派”即“性灵派”,这种看法夸大了袁枚诗派的范围,事实上他们仅是性灵诗人中的一支。
三、当前性灵诗歌研究就宗派立论的误区
关于如何处理个人和宗派关系的问题,朱东润先生曾指出:“(对于某些风格相似的作家)也许有人指出他们之间大同小异,所以不妨承认宗派的存在。倘使他们的中间只是大同小异,原不妨这样说,但是谁能保证他们的中间不会是小同而大异呢?因此,在这些情况下,就时代或宗派立论,有时固然增加了不少的便利,有时也不免平添了若干的困难。”[21]这是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朱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保留“无数的个人”而“决然放弃时代和宗派的标题”的做法,避免了在个案研究尚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就时代或宗派立论”而造成误判。这种审慎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在讨论性灵诗人流派归属时予以借鉴。
长期以来讨论某历史时期诗歌创作风格时,我们习惯先挑选最著名的诗家作为“盟主”,再大致参考诗学主张与交游情况将与之时代相近的一干诗人划入其麾下,然后从“宗派”角度立论。这样做固然方便,但由于“盟主”身份的认定及对其影响力的评价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容易拔高“盟主”的文学史地位。当我们简单地认为“性情”即“性灵”并在“随园派”和“性灵派”之间画上等号后,就会倾向于把标举“性情”并与袁枚有交往的诗人都列入以其为盟主的“性灵派”谱系。这样做不仅抹杀了包括赵翼、张问陶在内众多杰出诗人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也使袁枚诗派本身因被骤然放大而变得模糊不清,以至有论者承认:“迄今为止,学界的研究者尚没有对该派成员作出确切的统计或划分,而且以后也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工作”。[22]
袁枚的确是有清一代声名最著的诗人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开创的“随园派”有容量收编赵翼、张问陶这样卓然独立的诗坛大家。目前乾嘉时期诗人的个案研究尚不充分,贸然就宗派立论容易陷入认识上的误区。鉴于此,我们不妨将这一时期标举“性灵”,重视个性表达,反对形式主义诗风的诗家统称为“性灵诗人”。至于他们各自的流派归属则宜抱以审慎的态度,存而不论以待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