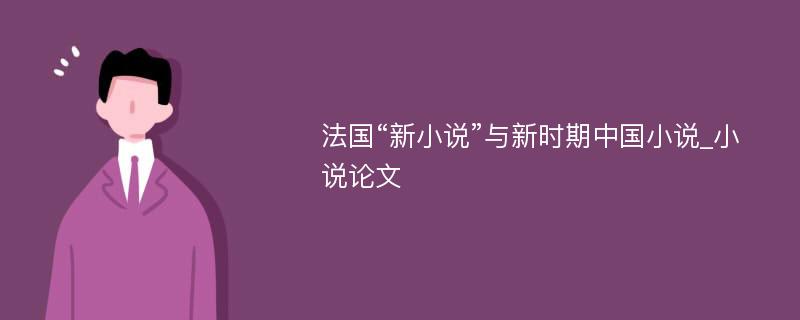
法国“新小说”与中国新时期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法国论文,新时期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于国门的再度打开,在激发传承本土传统活力质素与借鉴吸收西方优秀创作的大背景上,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旋律是碰撞的、交错的,并在迷惘的选择中和选择的迷惘中走向下一世纪。因为在短短不到十几年的时间里,西方在一个世纪里所酝酿产生的各种文艺思潮就在中国文坛上作了一次匆匆的巡礼,加之中国在新时期历史处于转型期中的动荡、活跃、多变,使得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观念之驳杂、流派之众多,恐是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与之比拟的。有些思潮流派自诞生之日起,实际已预示着走向衰落和消亡;有些作家不用说“各领风骚三五年”,恐怕能做到“各领风骚三五月”就该聊以自慰;批评家由于文学现象变幻莫测、且批评思潮本身更迭之迅疾,也更多表现出左右难以逢源又颇富诱惑地被文坛所吸引的面容;读者的阅读也一改过去被动和轻松的愉悦变为对本文的积极主动的再创造……。何以如此?传统的危机导致作家的创新;“当下”的境遇激发着作家的奇异想象;文学观念的变革促使作家进行实验冒验;外来思潮的输入与本土的碰撞迫使作家进行新的选择等等,原因不一而足。但是,有一个方面是能够达成共识的,这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学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并进而产生现代性乃至现代主义文本,近年来许多学者专家的论述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本文拟就在这一大前提下,对法国产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新小说”派对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的影响轨迹作一较为粗略的梳理。
一、先锋实验小说:布托的时代
小说是叙述的一种特殊形式。
小说是绝妙的现象学的领地,是研究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或者可能以什么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妙场所;所以说,小说是叙述的实验室。[①]
——米歇尔·布托
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学流派对另一国家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可以是单方面的,也可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进一步,同一流派的几位作家在对另一国家的文学发生影响时,时常有这种现象发生,即在某一流派里,是这位作家受到重视,在另一流派里,又是那位作家与之更为接近。基于这点,本文将在文学的真实观和叙事方式上展开论述,并将先锋实验小说定位为米歇尔·布托的时代。
在法国“新小说”派的作家队伍中,主要代表作家一般被公认的有三位:娜塔丽·萨洛特、阿兰·罗布—格里耶、米歇尔·布托。这三位作家之所以有此殊誉,主要因为不仅他们的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更具有“新”意(新的文学真实观、新的叙事方式),而且因为他们虽然同属于一个文学流派却有着自己富有个性的真实观和叙事方式。就布托而言,他的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则更多地将目光倾注于文学的形式探索方面。布托认为,研究小说的形式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真人真事的叙述,包括今天的“传统”小说,在逐渐成为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的同时,按照一定的原则固定了下来,经过了整理和简化。这样,对现实的原始的了解被另一种干巴巴的了解代替了,有些情况被故意删掉了。这种了解渐渐掩盖了真实的经验,被当作实际的经验,最后被普遍地信以为真。但是,“对小说形式进行的探索,使我们看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形式里有偶然的东西,使我们看清这种形式,摆脱这种形式,在这种呆板的叙述之外、重新找到被这种叙述所掩盖或隐藏的一切,重新找到那包围着我们全部生活的一切叙述”。[②]由此,布托认为,小说乃是对小说本身的探索,小说本身就是小说的目的。进一步,布托认为,小说是模仿实情的虚构。基于这种文学观念,布托在文学创作园地里从多个视域,多种角度进行了形式的多方面探险,因此,在“新小说”派作家中,布托有“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技巧”的作家之称。他认为,只有新的形式才能揭示出现实里的新事物。从布托那五花八门的小说形式的实验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叙事观念及方式对中国新时期的先锋实验小说发生了影响。一是迷宫式的时间游戏,一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融合。
“时间”,是20世纪的人类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当传统的线性因果链被纷繁复杂的碎片般的现实所打碎、敲断时,对时间的认识的传统观念便开始动摇了。如果说,过去的人们更多注意到时间的历时态,那么,今天的人却偏重于对时间共时态的认识和关注,尤其是对“当下”和“此在”的时间投以更多的关注。这样一种时间观念的变化,投射到文学创作上,便引起文本形式方面的变化。因为一种感情的萌动及爆发,一件事情的动机及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不仅仅是能从因果线性联系中找出,而且还需从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以多维多变的动态视界去把握和观照了。布托“迷宫式的时间游戏”即缘于此。在文本的动作过程中,他采用切割的方式将时间分解成一个个碎片,然后再将这些碎片变成一个个间隔封闭的空间,即“时间的空间化”,进而再以不同的方式将这些被空间化的时间碎片排列组合在一起,共时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一当读者进入到这样的本文世界中,便犹如进入了一个迷宫一般,一个个的碎片五光十色,散发着作者的奇思异想,但彼此间却没有因果,更没有通篇中心意象的指涉,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无序的、零散化的、不确定的、模糊化的文本世界。在你阅读时,便会被召唤着、强迫着,不由自主地去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并加以梳理。一旦你达到了目的,走出了这一时间碎片的迷宫,你同时就完成了对本文的再创造,进而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在迷宫中探险猎奇的完满实现,一种在紧张的张力关系中的实现。自然,倘若这种形式探险走入极端,难免不影响和破坏文本的整体美感,因为小说的天职仍然是叙述。但布托却以另一种叙事方式度过了这个难关,即客观与主观的密切交融:“写一部小说,不仅是写一整套的人物活动,而且要写一整套的物件,这些物件必须或远或近地与人物相联系”。[③]在这里,有物,有人,且又以人为主,可见布托注重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他还十分重视想象的作用:“每当我们把目光移到一个明确无误的想象空间时,我们便能名符其实地跟随时间的步伐,研究时间的不规则形式”。[④]因此,在布托的创作活动过程中,既有对“物”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有人的主观意识活动,如联想、幻觉,等等,于是,过去、现在、未来便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小说也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如果说,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文坛因“新小说”派的产生而打破了它的平静,以致于人们可以不读“新小说”派的作品,但不能不谈“新小说”。那么,同样,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是极不平静的,因为出现了“先锋派——实验小说”,人们也可以不读“先锋派”的作品,但却不能不关注、不谈论。这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或许两者都是。因为这两个文学流派的产生都以对传统的质疑为前提,又都以对新的小说道路、新的形式技巧的摸索为创作宗旨,从两个流派的文本实践看,其相似乃至于共同性也是多方面的。或许,“先锋派”的出现就是得之于“新小说”派的启迪?也无不可。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就是在本土与西方现代主义相互碰撞的环境中进入创作的,当时,不仅已有了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概述性的介绍及文本选择本(包括“新小说”),而且对于“新小说”派有关资料的专集也已问世,如柳鸣九主编的《新小说派研究》,其中不但有“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经典文本选,而且还有经典文论、访问记以及全面详细的述评。被称为“先锋派”的具有前卫性质及挑战性的作家们自然不可能不知道“新小说”派,也就不可能不受到它的影响了。如著名“先锋派”作家余华就曾说受到过“新小说”的影响。
当我们将观照眼光放在影响发送者的“新小说”派和接受者的“先锋派”——实验小说这一特定的比较空间时,会发现是“新小说”派在形式方面大胆创新和刻意探索更多地在“先锋派”小说里响着回声。只因为,“先锋派”作家们主要将文本当作了技巧,以大胆的形式实验和涉水冒险而有别于这一时期其他流派的文学创作。而在“新小说”作家里,布托又是以形式技巧的实验探险为最突出。
在“先锋派——实验小说”的作家当中,马原首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这主要是因为他以自己的文本作实验最先亮出了“形式创新”这块赫然醒目的牌子,而且摸索并创造了最具有马原特色的创作形式模式——“叙述圈套”。这一“叙述圈套”的核心内涵有“有意识地混淆真和假的界限(布托:小说是模仿实情的虚构);对叙述本身的专注和崇拜(布托:小说是叙述的一种特殊形式);夸大外在世界的自动性和无意识涌现(布托的时间碎片游戏)等。甚至,马原还以“虚构”为题写了一篇关于虚构的《虚构》(布托: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中国文学由此从“写什么”转换成“怎么写”,由“创作”向“写作”发展,进而进入形式的创新。
洪峰一直被当作是马原的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追随着,他的作品中“洪峰”与叙述者、隐含读者之间以往传统中那种默契关系的打破也不能不渗透有布托“文学即虚构”的真实观的烙印和痕迹,因为作者跟读者知道的一样多或者还不如读者知道的多,小说形式中原本就有“偶然性”(布托语)。
苏童的小说通常都用第一人称,给人一种直接切入感。布托说:“作者在作品中引进一个他本人的代表,即用‘我’向我们讲其故事本身的叙述者。显然这对作者十分有利”。因为“‘他’把我们弃在外面,‘我’却把我们带进内部。”[⑤]在这里,作者当然大于叙述者,但是叙述者在通常情况下会摆脱作者的控制,进入一种与作者对立的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一种主体身份,并把作者置于客体来进行观察。
作为“先锋派”作家,格非的《褐色鸟群》和《迷舟》无疑是形式探索的经典文本。其模糊性(由“空缺”和“悬搁”造成)也不是没有“迷宫游戏”的感觉。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信使之函》中那种一个个既有现实又有梦幻、既有真实又有杜撰的精美碎片式细节的排列组合,简直可以和布托同享“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技巧”的殊荣。
当然,要论及成功地吸取和借鉴“新小说”派尤其是布托的形式探险技巧的“先锋派——实验小说”家,自然是非余华莫属了。且不论他的《鲜血梅花》与布托的《时间的运用》作为对“复仇”的反讽性摹仿有异曲同工之妙,最突出的是他的《往事与刑罚》中那种对时间的切割分解与布托“迷宫式时间游戏”在《时间的运用》中的运用可谓同出一辙。《时间的运用》主要“事实内容”是谋杀案件,而且案中有案,由三个不同层次的事件组成:一是侦探小说作家伯顿化名汉密尔顿写了一本名为《布勒斯东的谋杀》的小说,叙述一个运动员被亲兄谋杀的故事;二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个房间与现实中一个市民的房间很相像,而他的兄弟前几年死于车祸;三是伯顿写小说的秘密泄露、险被一辆汽车撞死。但是,在本文中,这些事件只是一种框架和一件外衣。布托显然更感兴趣的是形式而不是故事,是文本的技巧游戏而不是去叙述环环紧扣的谋杀事件。文本最大的成功在于把时间分解切割并转换成一个个封闭的空间,然后碎片般展示于读者的阅读视野。文本由一个旅美的法国青年的日记构成,但布托采用了追述的形式,并且让追述者当年5月追述去年10月,当年7月追述去年5月,当年6月追述去年11月,当年8月追述去年6月,当年9月追述去年8月、7月、2月、3月。本是一年完整的时间,由于这种切割和分解,一个自然流程便被截成一个一个的小空间,并把它们零乱地混杂在一起,交给读者去发挥、梳理,而不同的梳理则会产生不同的游戏模型。余华的《往事与刑罚》也更多表现出对时间的关注。余华在文本中好象要向叙述一个著名的专家学者在60年代因不堪忍受欺辱而自杀的故事,时间是1965年3月5日,但却又出现了1958年1月9日、1967年12月1日、1960年8月7日、1971年9月20日。文本中的如下两段描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你在最后的时刻,将会看到1958年1月9日清晨的第一颗露珠,露珠在一片不显眼的绿叶上向你眺望。将会看到1967年12月1日的中午的一大片云彩,因为阳光的照射,那云彩显得五彩缤纷。将会看到1960年8月7日傍晚来临时的一条山中小路,那时候晚霞就躺在山路上,温暖地期待着你。将会看到1971年9月20日深夜月光里的两颗荧火虫,那是两颗遥远的眼泪在翩翩起舞。
他是怎样对1958年1月9日进行车裂的,他将1958年1月9日撕得象冬天的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对1967年12月1日,他施予宫刑,他割下了1967年12月1日沉甸甸的睾丸,因此1967年12月1日没有点滴阳光,但是那天夜晚的月光像杂草丛生一般。而1960年8月7日同样在劫难逃,他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钢锯,锯断了1960年8月7日的腰。最为难忘的是1971年9月20日,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将1971年9月20日埋放土中,只露出脑袋,由于泥土的压迫,血液在体内蜂涌而上。然后刑罚专家敲破脑袋,一根血柱顷刻出现,1971年9月20日的喷泉辉煌无比。
显然,余华是将一个个封闭的空间化的时间碎片以极简洁的语言呈放在读者眼前,因为这几个日子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作为死亡故事,也是彼此封闭的、任凭读者想象和排列。但在前一段描述里,却又出现了早晨、中午、傍晚、深夜,又是一个完整的时间!进入这样的文本世界,难道还不会产生“迷宫般”的感觉?时间被切割分解的游戏也充分得以体现。
米歇尔·莱蒙说:“实在,对存在的强烈感受使人无法写出一部小说。我们不能既说出存在的事物同时又叙述一个故事”;“新小说不一定来源于纯粹形式或其意义的表面危机,而来源于人们叙述故事的不可能性”。[⑤]
二、新写实:萨洛特的时代
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某种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事物。人物的每一个手势可以描绘出这种深藏的事故的某一面,一个无足轻重的小摆设可以反映它的一个面目。小说的任务是要写出这种事物,寻根究底,探索它最深层的秘密。[⑥]
——娜塔丽·萨洛特
在“新小说”派作家中,萨洛特是一位向内开掘最富有贡献的作家。布阿德福尔在《新小说派概述》中这样评价萨洛特:“她着手进行的是揭示小说的真相的工作。她致力于去显露我们的真我,剥去差不多已经把真我完全包起的教育、社会生活、偏见和陈词滥词等等人为的涂料”。[⑦]萨洛特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将更多的笔触伸向了人的心理意识活动领域,而且不怕“影响的焦虑”,在乔伊斯、普鲁斯特、沃尔夫三大巨人的背景上,走出了自己的创作道路。从文学观念看,她认为小说尽力完成的应该是描述出人物内心深层中的“原生物式”的心理活动内容。由此、她发现了人的“内心独白的前奏”这一以前常被忽视的领域。所谓“内心独白的前奏”是指人物内心独白产生之前所发生的那些细微的、隐蔽的、复杂的心理反应。“隐藏在内心独白后面的东西,是一堆数不清的感觉、形象、感情、回忆、冲动与任何内心语言也表述不出来的隐秘的小动作,它们蜂涌到意识门口,聚集成一个密密的群体,突然冒起,随后又分开,换一个样子重新聚集,以新的形式再一次冒现。”[⑧]
为了体现极为本真、客观的还原,萨洛特在叙事方式上采取了“潜对话”。所谓“潜对话”,从她的介绍看,既不是那种发为声、形为文的对话,也不是表现为与语言相反的动作、沉默、暗示、语词、身姿、表情等等。它不外化、不表现、不具有外在的具体的某种形式,完全发生于内心之中,潜伏于内心世界里。具体而言,一是心理活动中的对话,它可以是想象的,或已经发生的或正在发生但还未发为声形于色的;二是不止一个人物内心世界里所进行的那种与他们各自在实际交往中正在进行的对话并不一致的对话,即“辞不达意”;三是指人与人之间那种难以言状的互相感应关系,而它们往往是模糊的、朦胧的、难以言状的,没有任何具体的表现形式。就这三个层面看,萨洛特在创作中更多运用和描述的是第二个层面上的“潜对话”。这种“潜对话”构成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相异或相反的心理活动内容。萨洛特为达到客观还原的目的,往往注意抓住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庸的、琐屑的、细碎的且重复的对话作为还原的媒介,与此同时又不忘展示内心相异或相反的“潜对话”。在这里,矛盾、张力深藏于事物的平庸外表的背后。“内心活动试图在对话本身中展开,而对话不过是其结局、或者说是其终点,通常总是被套上皮头以便浮出表面。为了抵抗内心活动的不断压力,为了控制内心活动,对话就变得僵硬、夸张、显得谨慎小心,慢慢腾腾,正是在内心活动的压力下,对话拉长,变成弯弯曲曲的长句子”。[⑨]
本文之所以将“新写实”与萨洛特定位,不是因为她是女作家而“新写实”中也有两位女作者取得了很高成就如池莉和方方,而是因为她的对日常生活琐屑的还原以及相异相反的“潜对话”的叙述方式与“新写实”有极大的近似性。因为,“新写实”也反对传统文学中人为的主观因素对人自体的包裹和掩饰,它要剥离掉观念的预没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对事和人的侵蚀和施暴,要描述还原出人真实实在的生存处境和生活境遇。无论是琐屑的、平庸的、细碎的,都不加掩饰地描述出来,且将理性的观念悬搁起来,中止判断,反对观念的渗透和张扬。它使创作视野下移,变有序为无序,变戏剧性为生活流,让文本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同时,靠细节组成一种氛围、状态、意境,将评论权交给读者。这都与萨洛特的文学观念不谋而合。
《天像馆》是萨洛特的代表作,内心独白是其主要内容。在萨洛特看来,日常交往的语言只是人们聚会碰头的一个公共场所,这个公共场所并不代表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往往还掩盖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当人们以常规的、俗套的、程式化的语言对话时,他们的内心里往往进行着相异的甚至是相反的心理活动,而这正是“潜对话”所面对的世界。在《天像馆》里,每当出现人际关系,出现不止一个人物的空间,我们都可以听到两种同时进行的对话,即人物之间口头上的对话与人物内心里潜在的对话。只不过,有不少时候,没有表层的口头的对话,而是有共处时某种表层的态度或程式化的对峙。如第一章中,老姑妈与装修工人们关于门把的那一场交涉与对话,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老姑妈这一边,表面上是客客气气的态度,低三下四的调门,苦苦哀求的话语,内心里却是一大堆埋怨的、愤怒的、诅咒的、轻蔑的语言;在装修工人那一方面,表面上是不冷不热的解释与推诿,内心里却是一种厌烦、蔑视、轻狂、侮辱的念头。这来自两个方面的四股语言感情之流,交错迸击,极为有力地还原出“当下”那种更为深层更为隐秘的对话内涵。“内心独白前奏”在《天像馆》中更有突出的体现,这种展示其实就是把短暂时间里(一分钟甚至几秒钟)的心理活动过程细致地表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一种感情、一种心态如何从其发韧到形成,如何从复杂的混沌状态之中脱颖而出。如第五章的第一、二节,这两节所写的是阿兰如何给他所追的一个女人打电话。从他开始拨电话号码到打通电话,与对方约定见面,整个过程为时不到一分钟,最后以他春风得意的自我感觉为结束:“他笔挺地站着,他强而有力,自如地掌握着自己,所有的官能都处于活跃状态。他头脑清晰,充满勇气,满怀成功感与幸福感,行径狡黠而又具有尊严,对答如流,嗓音热烈而动听,是那么招人喜爱以致他自己也被迷住了”。但在这最后的自我感觉之前,有着复杂的“前奏”,在这“前奏”中又混杂着各种成份,有他对自己家人的逆反心理和猜疑,有由这种猜疑所引起的“气愤”和“狂怒”,有报复情绪,有豁出去的冲动,有拨通电话号码时的期待与激动,有可能被拒绝的顾虑与惶恐,还有得到对方肯定答复时如释重负的轻松。所有这些在以分秒计的短时间里一涌而来,导致了最后的自得感。这样一分钟的一个细节,被她用近两千字的篇幅加以描述,使读者把握到人物内心的每一个“颤动”,从而极为客观又有深度地凸现出人物内心不同层次的心理活动内涵。
池莉的《烦恼人生》历来被认为是“新写实”的经典文本。作品围绕印家厚一天的一些生活片断里进行精彩的组装,通过角色的不断转换,将这些生活的碎片穿成一串珠子,本真又形象地描摹出一个普通人的那种既尴尬又无奈、既希望又失望、既超越又务实的两难处境下的“烦恼人生”图。与“先锋派”小说相比,故事因素增加,可读性增强,在印家厚一天生活流的展示中,笔触自然而然地随时间的流动而伸出。
但是,有一点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文本中除了那些故事性很强的几个精致的片断外,余下的便都是印家厚在“当下”生存境遇中的内心感受和内心独白。萨洛特笔下的“潜对话”和“内心独白的前奏”在这篇文本中也不乏其例。例如关于发奖金一事。
以往是“轮流坐桩”,人人都有份,只是时间的早晚有别而已,人们的内心却也较为平静,一种等待中的平静。偏偏天不遂人愿,等轮到印家厚“坐桩”,规矩却被打破:严禁“轮流坐桩”。虽然他加班加点地为大检修出力最多,却因迟到一分半钟(车间主人却只言迟到而不说时间)没拿到叁拾元的一等奖,而得了个最低的三等奖:伍元!于是,不但印家厚内心有了矛盾和张力之下的“潜对话”:外表没有大的变化而内心却波澜起伏,思绪绵延,即使他与人之间的对话也充满了“潜对话”的意味。如他与二班长之间,表面的对话只有两次,且非常简短。一次是在评奖会上,二班长说:“喂喂。小印,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得了。”印家厚低低吼了一句。二班长说:“……咱俩是他妈什么狗屁班长,干得再多也不中。太欺负人了!就是吃亏也得吃在明处。”印家厚说:“象个婆娘!”其实,二班长的处境与印家厚一样,也是“在劫难逃”,他本想找个同病相怜的安慰,但内心里却希望印家厚是一只“枪打出头鸟”,自己好借此渲泄一下情绪。印家厚的对话表面看似乎都与二班长无明显的矛盾,但内心里却瞧不起二班长这个人的罗嗦、虚伪、怯懦。因此,在简短的表层对话后面却是深层的内涵相为丰富的两股相冲突的“潜对话”。还有一次是在评奖后的食堂打饭时的对话,二班长摹仿雅丽的嗓音说:“哦!行不得也哥哥!”“屁里屁气!”印家厚说。对话也极为简短,但仍有一个“潜对话”在后面,因为二班长在评奖后曾表白自己要好好干,还“谦虚”地说拿三等奖都是过奖了,所以印家厚的这一句话后面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只是掩藏在了下面。再如印家厚与徒弟雅丽之间,围绕着评奖金,表面看,他们的对话都是以“钱”为焦点,但在“钱对话”下面,却是他们俩人感情之流的“潜对话”的碰撞和相遇。
另外,“内心独白的前奏”在《烦恼人生》中也无不与萨洛特的《天像馆》有对应。在《烦恼人生》的结尾,当写到印家厚与妻子之间那种“情浅而缘深,失语却话多”的情感世界时,当印家厚说出“算了。睡吧”这句话时,他内心显的前奏是极为丰富的:即有对妻子的关心体贴,又有妻不如别人的遗憾;既有想以关心作出点补偿的愧疚,又有无可奈何的感慨;既有一个男人的宽容和怜惜,又有失望和内在的尴尬在其中……这一切,在“算了。睡吧”这句话出口之前汹涌而至,交融混合成这一句可作多种角度解读的符码。
萨洛特与池莉是相通的,尤在展示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方面。
三、“新表象”:罗布—格里耶的时代
人看着世界,而世界并不回敬他一眼。[⑩]
能展现为基本因素而不能压缩为含混的思想观念的东西,则都是动作本身,是物件,是运动,是外形,是形象突然恢复了它们的现实性。(11]
——阿兰·罗布—格里耶
著名法国作家萨特在谈到“新小说”派的创作特征时曾说:“我们这个文学时代最古怪的特征之一,是到处出现生机勃勃却具否定性的作品,人们可以称之为反小说……。反小说保留了小说的外表和轮廓,向我们介绍虚构的人物,为我们叙述他们的故事。但这样做是为了使我们更加失望:作者们旨在用小说来否定小说,在它产生时便在我们眼前将它毁掉、写一部关于小说的小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思考的时代,而小说正在进行自我反省。”(12]这一文学观念的变革实际上源于人们认识世界、感受世界的方式的变革。20世纪,随着科技文明和物质主义的极度发展,尤其是在人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过去人们极为熟悉亲切的世界变得陌生冷漠,由对“物”的崇拜和依赖人越来越多地成为“物”的附庸而难以自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变得难以理解和无法沟通,鲜活亮丽的生命个性也因机器文明的排斥而日益萎缩。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分离而导致的异化,使世界在人的眼里也越发地变得不可理喻,不可解释。
罗布—格里耶作为“新小说”派的主将之一,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有了前面的两段言说并认为,就世界而言,人只是一个见证者而已:“我们周围的世界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光滑的平面,毫无意义,毫无灵魂,毫无价值,不可捉摸。”[(13]所以,在小说中,他认为首先必须拒绝比喻的语言和传统的人道主义,同时还要拒绝悲剧的观念和任何一切使人相信物与人具有一种内在的至高无上的本性的观念,总之,就是要拒绝一切关于先验秩序的观念。基于这样的文学真实观,罗布—格里耶在叙事方式上采取了对“物”的纯客观的还原,借以达到或恢复“物就是物”的原貌。我们知道,“还原”在其现象学意义上正好是与“典型”对立的,因为“典型”的方式是依照一种思想观念去塑造人物,剪取生活,而“还原”要求像胡塞尔说的那样,“终止判断”,把现实事物“加上括号”,以最大可能地呈现生活的真实状态,以达到一种现象的而不是理念的真实。进一步,“还原”的目的意在消解“典型”对生活的肢解和歪曲,消解捆缚在生活现象之上的种种理性的缰索,让以往被肢解被润饰被扭曲的生活还原其本来面貌,不再受观念的施暴。
为了达到还原现实生活本身的纯粹性,罗布—格里耶还强调作家应站在一个“点”上去观察物,描述物,且仅仅要局限于这个点而不能去设想“点”以外的所感所闻。由此,罗布—格里耶被称为“客体”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那种有一定“社会”、“心理”或“记忆”的某种深度的经验消失了,主要画面是对世界表象的描绘。这种叙述模态被批评家称为“零度写作”、“冷叙述”、“削平深度”。自然,这种以“物”为中心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叙述视角和聚焦方式,所描述的毕竟仍然是有关人的言和事,不可能脱离开“人”这个聚焦点去观照生活,审视一切,否则作为文学创作便会失去它存在的寓所或者毫无意义。正如罗布—格里耶自己在1959年10月8日的《快报》上所说:“即使在我的某些小说中有许许多多的物体,但进行观察的总是人,而不是什么中性的目光,既然是人,当然就会深深卷进人的感情之中。”(14]
本文之所以将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表象”小说定位于罗布—格里耶发生影响的时代,主要因为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步步深入和全面展开,商品经济大潮对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各个角落开始渗透。知识分子以人文精神为中心的精英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并越来越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商品——物,堂而皇之地由以前的卑下地位一变而为生活的主人。既然是日常琐屑、细碎得以肯定和普遍认同,那么精英意识中的所谓深度、意义也就仅仅局限于它所特定的领域。“新表象”小说基于这样的一个创作背景,与罗布—格里耶的“物主义”、“客体”的纯客观还原具近似乃至契合也就不难理解了。
以文本为个案:罗布—格里耶的主要作品无疑是《橡皮》、《嫉妒》和《窥视者》等,其中《嫉妒》可谓是描述表象、描写“物”最经典的文本了。按理,在人的情感生活中,“嫉妒”是最复杂、且最具主观色彩的一种心理情感现象,作品既然名为《嫉妒》,就应该以描写人在某种暖味不明情境的刺激下所产生的复杂矛盾的心理感受为主。但是,罗布—格里耶却采用“纯客观”的叙述方式,一反传统叙述视角,而是把叙述视角的聚焦点放在了人对“物”的细致观照以及纯粹的“物自在”的本真还原上。于是,虽然内涵是情感,但叙述方式却是“物”自在的凸现。随着小说中视角的不断变换,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柱子、阳台、花园、房屋、种植园、远处的山坡与田地。所听到的仅只是主人公阿×和弗兰克时断时续的对话,谈话的内容也没有一丝一毫涉及感情的事,不过是弗兰克的妻子与孩子的健康,一本他们都读过的小说,阿×要搭弗兰克的车进城去办些事等等。所见到的中心事件似乎就是阿×和弗兰克之间的交往,但也只有一两个片断:弗兰克与阿×一起就餐,阿×搭乘弗兰克的车进城去办些事,另外再就是阿×如何梳头,如何整理物件、如何乘车回家……其他还有一两个略带形式意味和隐喻的情景:阿×在写一封不知寄给谁的信;在餐桌上,妻子发现墙上有一条蜈蚣,弗兰克走向前去用餐巾把它捻死;阿×与弗兰克进城当晚没有回来,到第二天才回到家里,原因似可信又不可信——车子抛了锚。于是,这些零星的谈话与情景再加上一两个疑团,就构成了文本的全部内容。我们本以为在文本中可能摸到丈夫嫉妒情感的内在波动与外在情态表现,但是,没有,文本并没有满足读者的这一阅读期待。相反,在这部写嫉妒的小说里,不仅没有嫉妒的感情变化、情绪起伏以及有关的任何心理活动,也没有与嫉妒这种感情相关的任何思想、观点与见解,更没有处于嫉妒的情况下对客观事态的考虑分析、意图打算。叙述者似乎只像是一架无生命的摄像机,仅仅把发生在他眼前的一切景象实录下来而已。若说这实录中还有一些人的“情感”和“精神”活动,那也只是瞬息闪烁而稍纵即逝的一些意象而已。而这尚须通过图像的变化与联系才能感觉到,描述者本人则没有对这些图像的任何说明。罗布—格里耶在写作中完全将人的任何思想感情、心理意念全部过滤干净,只剩下了一些也许在说明某一嫉妒事件的细碎的图景和片断。
自然,所谓没有嫉妒,只是就叙述聚焦点的特定空间而言,实际上,作品中嫉妒的感情依然存在,只是被压在了文字的背面而已。叙述者虽然没有一丝一毫感情的直接流露,但他在观察时那样关注、注意力那样集中,那些片断或表象的细枝未节的变化都被置于观察之内,犹如在加倍放大的显微镜下一般,一一得以自在地凸现,从而在客观上显示出了他因怀疑而产生的嫉妒。因为我们很难设想或想象一个人若没有强烈的怀疑和深深的嫉妒,会对妻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有那样的关注和观察。
在“新表象”小说中,这种“物化”、“非人化”、“纯客观还原”已由外在形式的探险涉足而成为作家的艺术自觉了。
北村在“新表象”小说中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生的婚姻》试图描述一个落泊的文人在世俗生活中历经波折、最终在宗教——《圣经》那里找到精神归宿的故事。但是,在文本中,北村并没有将叙述聚焦点集中在主人公在内在的精神痛苦和困惑中竭力挣扎寻找出路的矛盾、徘徊和苦闷上。文本中出现于读者眼前的只是一些生活的外形和各种表象片断:混乱沓杂的街景、饭店里的调笑和偷情、某些家庭的打闹以及一些未遂和已完成的凶杀场面……。这些现象之流蜂涌而至,以致于将哲学教授张生整个地淹没了。在这里,所谓叙事不过是一些表象的随意流动或任意拼贴;或者说,表象之流支撑起小说的全部叙事,而人的思想、情感、形而上等等统统被压在了表象的下面或者原本就已失去深度而无所谓掩藏。婚姻的失败从侧面拆射出张生的落泊,但却不是小说的中心画面。
著名作家吕新“新表象”的主要文本《南方遗事》从叙事动机看,是想重新书写晋北农业地区的形貌状态,创造一种关于农业地区的新型的人文地理学。但在本文中,叙事却成为语言追逐物象的任意流动,物象本身就构成了小说的本体。鲁羊的《洞酌》时空任意打乱,意象鲜明但没有深度,自动漂移。何顿的《弟弟你好》叙述视点几乎不带有任何先验性的观念,也不怀有发掘生活意义的明确动机,作者的兴趣显然仅只在表现这种生活的外在状态。西旸的《季节之旅》则更是对写作生活原生状态的彻底还原,那种无内在统一性,没有情节和整体感的叙事,实为对生活和事物进行的一次纯为表象的还原。李洱的《导师死了》就更是以对欲望化表象的处理为中心。
当存在的“深度”寓言被解构、当人们处于一个多元的、“当下”的、没有乌托邦性彼岸世界作出终极价值承诺的语境,生活原本也许就无所谓在“表象”或“物”的背后再去寻求意味乃至意义。于是,“物”、“状态”、“表象”成为聚焦点,并进而成为文本的主体,“只作描述,没有判断”抑或就是生活最大的真实?!就这点而言,中国的“新表象”与罗布—格里耶的“物主义”似乎是不谋而合、貌异而神似了。
注释:
①②④⑥⑦⑨⑩(11)(12)(13)引自《新小说派研究》,柳鸣九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88,90,144,31,497,57,73—74,65,480—481,84页。
③ ⑧引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柳鸣九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0,180页。
⑤ ④见米歇尔·雷蒙:《法国现代小说史》,徐知免、杨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346,3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