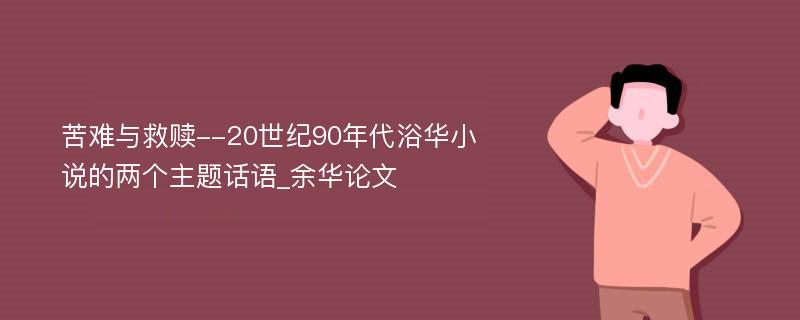
苦难与救赎——余华90年代小说两大主题话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苦难论文,话语论文,年代论文,两大主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1)02-0096-06
余华从20世纪80年代带着其处女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登上文坛开始,就以其独特的语言风格、个人感觉及所开拓出来的与传统不同的艺术天地而成为一位再也无法令人忽视的新生代作家。其后,他用如梦如烟的故事网络构置,循环往复的情节叙述,冷淡甚至冷酷的叙事语言表达了他个人对于生存的某种态度,表达了他所感到的世界的真实。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1]这种真实在余华笔下展现出来的是:弥漫于整个世界的无边无际的欺诈、暴力、杀戮、阴谋、荒诞;人性之恶的洪水滚滚而来,淹没了每一个人;苦难犹如一朵巨大的乌云,笼罩着整个人类生活。整个世界是黑漆漆的,阴森、恐怖,透不进一丝光亮,找不到一点出路。这幅世界图景为我们提供了余华80年代小说的一个主题话语:苦难。所有的暴力、杀戮、血腥及人性的罪恶共同交织成了一幅苦难图像。正是用这些难以自拔,而深陷其中的苦难,余华亵渎了传统的世界,颠覆了生活的真实。苦难与亵渎成了他80年代小说相互依存的主题。
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余华并不是一个按一成不变的风格写作的作家,而是一个逐步变化,并在变化中走向成熟的作家。正如他自己所说:“作为作家本人,主观上总是想往前走,总是想变化。”[2]90年代余华的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自1991年《呼喊与细雨》的过渡之后,1992年与1995年的长篇小说《活着》及《许三观卖血记》充分地显示出余华新的小说创作风格的形成与成熟。而其主题话语也相应有所变化,由80年代的苦难与亵渎转向了90年代的苦难与救赎,不仅对过去的主题话语有所延续,更重要的是有所发展,增添了新的意义内容。余华90年代小说的主题话语一方面在形式和叙述语言上与新的艺术风格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在深层次上体现了余华小说对人类的超验的哲学关怀。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余华90年代长篇小说的主题话语,由于《呼喊与细雨》是一篇过渡之作,所以本文主要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长篇为分析文本。
一、苦难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2]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疲地加以表现。在他90年代小说转型中,“苦难”这一主题被继承下来,但这并不是简单、低级地重复,而是在形式上显现出新的艺术风貌,在内容上体现了新的意义。
在余华90年代的小说中,“苦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悲剧和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这与80年代的小说创作有着明显的差异。
余华前期小说的“苦难”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罪恶,本质上的宿命。余华笔下显现出来的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恶的世界,这些罪恶包括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等等,因此,暴力、血腥、杀戮这些余华前期小说创作的典型内容也就共同体现了“苦难”。正是在对暴力、血腥等等冷静甚至残忍的叙述中,罪恶性的苦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人们对“我”的欺诈与暴行已经初步显露了余华对世界的看法。《一九八六年》从一个悄然而至的可怕的疯子开始展开了古代种种酷刑的实施。在《现实一种》中余华更是以冷观和审美的态度为“暴力”造型,向人们展示了亲人间骨肉相残的血腥场景。
弥漫在文字中的杀戮、暴力、血腥、欺诈、阴谋交织出一幅浓重的罪恶黑幕,它不仅让人感到恐惧和不安,更让人感到世界的黑暗和无边的苦难。这种“伤痕即景,暴力奇观”[3]式的苦难体现的是一个“与现实关系紧张的愤怒作家”[4]为着理想“给世界的一拳”[5]。然后他意识到“世界这么大,我的拳头那么小,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上一样,有屁用。”[5]进入90年代,当生活环境变化之后,在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余华对世界的感受也有所不同了:“我现在没有工作,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可能和任何人发生直接冲突,世界在我心目中变得美好起来。”[5]他开始变得心平气和。虽然余华始终没有放弃苦难这个主题,但这些变化却使余华90年代转型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
苦难不再等同于罪恶、杀戮、血腥、暴力等等。这些东西开始逐渐隐退,腾腾的杀气消散了,血淋淋的场景隐没了,无处不在的暴力收束了。苦难在他的转型小说当中开始沿着两个向度扩展,一是直指终极的生命悲剧,一是指向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甚至在他的转型小说当中得到了日常化的体现。前者以《活着》为典型范本,后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活着》的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然而在他所经历的一系列不幸当中,家产尽失也好.穷困潦倒也好,被拉壮丁九死一生也好,都抵不上那一桩接一桩的亲人的死亡和生命的丧失来得令人触目惊心,悲难自禁。正是死亡对生命的消蚀带给了福贵最深的苦难和最大的折磨。这个终极意义上的消散带走了福贵所有的生活希望和最低程度上可期待的幸福。死亡原本就是人类无可逃避的终极悲剧。死亡结束了生命,也终止了一切的价值和意义,当亲人一个一个死去之后,死亡对于福贵来说已并不可怕了,然而死亡却迟迟不降临在他的头上,让他活受这生的悲哀。《活着》上演的其实是一出由死亡连缀的生命悲剧。《活着》充满了作者的精巧构思,精心布置,他让一幕接一幕的死亡出现在读者眼前,把生命之苦渲染得无以复加,痛彻心骨。但是在这部充满死亡气息的小说中,我们却感受不到恐怖、阴森、杀气,看不到鲜血淋淋的惨状,生活的无常虽有,人为的暴力却淡然。人与现实的关系不是如紧绷之弦,一触即发,作家的叙述是舒缓而凝重的,甚至用“我”的插入的中介作用来使福贵的苦难减少直观性。《活着》中的苦难让人悲及骨髓,却决不像前期小说中的苦难那样令人对世界充满恐惧和不安。
须直面的生存困境。这是一个小人物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下的日常生活和悲欢离合,那些生活的坎坷和遭际不是可歌可泣,如泣如诉的,但却在深层里揭示了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苦难:每个人生活着,就必须直面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活着是不容易的。如果说《活着》充满了作者精心布置的偶合和命运无常,像一部人生传奇的话,那么《许三观卖血记》则更加接近于生活的真实。事实上,生活里的苦难恐怕更多的还是来自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不易和艰辛以及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许三观就是这样一个面对生存困境不断地挣扎并生活下来的小人物。尽管《许三观卖血记》在以“主人公不断丧失某种有价值的东西”[6]作为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上与《活着》完全一致,但福贵面对亲人的死亡只有无法挽回的锥心之痛,而许三观面对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困境则是痛苦地挣扎。为了结婚,为了付方铁匠医药费,为了渡过饥荒之年,为了款待儿子的生产队长,为了筹集大儿子的医药费,为了日常的正当的生活,这个一无所长的小人物只能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困境的解决和一家人的继续生存。在丧失与获取之间,苦难被铺陈了出来。在现实里,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卖血,但是每个人只要生活着,就注定要面对这样或那样的生存困境,要担负压力而生活。这也是无法逃避的苦难。在《许三观卖血记》里这种苦难没有变成玄而又玄的抽象之物,而是在与时代因素相结合的日常化体现当中变得愈发真实可感。正如评论所说:“这是一个寓言,是以地区性个人经验反映人类普通生存意义的寓言。”[7]在这个“寓言”里,有鲜血,没有血腥;有死亡,但不见暴力和杀戮。事实上,余华后期小说中的苦难一方面在现实层面上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又在本体论上进入了生命的终极。
在余华前期小说中,人性恶可以说是造成一切暴力、血腥和杀戮的根源,换言之,人性恶是导致苦难的重要因素。同时苦难也将人性恶凸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余华前期作品在贯彻苦难这个主题话语上,也大都可以互为阐释,共同叙述着苦难的重要根源——人性恶。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人们对“我”的欺诈和暴行开始,人性恶已露端倪。人生处处充满了不祥和危机,《四月三日事件》就是对这种情绪的集中揭示,主人公只能在无法排遣的焦虑中带着巨大的惊惧等待四月三日的到来。在这里,人性的险恶暴露无遗,亲生骨肉形同陌路之人,比别人更阴险地将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边缘。《现实一种》中人性的卑劣与残忍更是推动了一场亲人手足互相残杀的死亡游戏的上演。人性在这样的暴力和血腥当中早已跌落到兽性的层次,然而又比野兽多了一份狡诈。正是人性恶所带来的种种罪恶使世界如此可怕,使人们的生活灾难深重。
进入90年代,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依旧是深重的,并且更具有了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然而与苦难之中暴力、杀戮、血腥等等的隐退相对应,人性恶不再是一切苦难,一切罪恶的归结之所。作家的理想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4]
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4]事实上,《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都遵循了这种理想。首先,作品中的苦难的症结所在不再是人性恶;其次,作者也确乎站在了超越道德判断的立场上,对善与恶保留了最后的判断,而用同情的眼光注视一切。在《活着》当中,亲人生命的丧失可谓是福贵遭受的最大的苦难和最深的痛楚,然而在一系列的死亡当中,母亲和妻子的病死,儿子的失血过多而死,女儿的难产而死,女婿的意外身亡,孙子的吃豆过多撑死并不是人为的暴力、欺诈、阴谋造成,并不是人性恶直接导致的悲剧,更多的似乎是命运的不幸与捉弄。在《许三观卖血记》当中,无论是筹措付给方铁匠的医药费,还是度饥荒之年,或儿子的下乡染病,这种种的生活磨难也都不简单的归结于人性的罪恶,有时这些磨难甚至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民族整体的生存困境与生活状态。总而言之,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余华90年代小说当中,人性恶作为苦难之渊薮的地位逐渐失落了,命运的不幸与现实的甚至时代的因素加入进来。
从另一方面看,作者站在了超越道德判断的立场之上,只是平静而客观地叙述着一切,他包容了一切的善与恶,从不站出来大声指斥:看,那是罪恶。善与恶在他同情的目光下消融在一起。无论是《活着》中的龙二也好,还是《许三观卖血记》中的李血头也好,他们虽然让人感到不是好人,却从未达到令读者悲愤难平、千夫所指的程度。因为作者从来就不想利用他们为“人性罪恶”树立标本,他们只不过是在这人生苦难的故事之中出场的配角而已。
余华前期小说当中苦难的呈现基本上是带着一种宿命意味的:人活着就注定要受苦。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都闪现出宿命的光环。它笼罩在整个文本的上空,仿佛作者讲述的故事都可以归纳为一句简单的话:你们难逃劫数。每个人在命运的面前,命若游丝,毫无反抗之力,极力狂奔却又只能落入网中。这一切不是因果轮回的报应,而是人性的堕落。自我消弥于本我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人们在罪恶的本性驱使之下,相互杀戮、伤害、欺诈,生活在彼此制造的苦难之中而无法逃脱。在“苦难”这面“魔镜”的映照下,人性和生命的泥泞与沉沦状态终于彰显出来。人性和生命在苦难中堕落和沉沦,看不到任何被拯救的希望,而只是与接近死亡的最为黑暗的心理体验——绝望紧密相联。在80年代的余华笔下生存只是一个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到了90年代,在余华的小说里,苦难主题之中的宿命意义并没有缺席,“人活着就要受苦”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宿命已不再是绝望的温床,绝望也不再是人面对苦难宿命一无所为之后的惟一的必然的选择,黑暗的天空被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透进了一丝亮光,即使这一丝光亮也给人和世界带来了被拯救的希望。当余华用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亵渎了现实和人的生活之后,面对他所感受到和呈现出来的新的苦难,他选择了救赎。于是福贵在亲人尽丧之后,仍与老牛为伴,走向黄昏中那开阔的大地,而许三观也在历经磨难后,坐在饭店里悠闲地喝着黄酒,吃着炒猪肝,对老婆讲述着:“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的道理,作者实际上是借福贵和许三观的生活提出了新的直面苦难而不至跌入绝望深渊的在世态度,苦难的宿命不再是人只能沉沦于其中的无边汪洋。
二、救赎
余华的小说几乎篇篇是悲剧,在他把苦难这个主题一以贯之地表现下来的时候,同时也把苦难作为一种整体的生存境遇,使之生命化了。只是在前期小说中与苦难相伴的是深深的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命运的绝望,对人性的绝望。这种绝望用海德格尔的描述来讲就是“深渊时代”和“黑暗之夜”。它是人对生存意义的一种精神态度,是对自身价值的否认,是人的精神沦落和毁灭的一种极端境遇,是一个黑暗的牢笼和陷阱。然而当余华沉到绝望底部之后,我们却在小说中读出了“希望”,这就是“活着”。于是在绝望的边缘处,余华90年代小说中的救赎话语也就应运而生了。当余华把世界消解为虚无之后,出现的问题是人没有了,自我不存在了,于是重建人类心灵的任务又摆在了作家面前。克尔凯克尔认为:绝望是一种精神上的表现,它关系到人的内心的永恒性。人的内心存在着两个世界,每个人都有永恒拯救和永恒沉沦这样两种可能性,前一种是迷人的,后一种是恐怖的。无论是作家本人还是读者都无法在绝望的独木桥上一直走下去,作家的绝望的言说本质上正是为了最终摆脱绝望,在无意义的废墟上找到真正的意义。因此,当余华彻底地亵渎了现实,把传统的世界颠覆得支离破碎之后,他开始从最初面对世界的愤怒与困惑中走向了平静的思考,重新寻找生存苦难中的温馨,从而重新确立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并给出自己的回答。这样,救赎的主题话语就在他90年代的小说中展开了。这种救赎在形式上是对苦难的超越,在精神上则是对绝望的超越。
关于救赎的主题话语在我看来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
其一,对人的生活的拯救——提出新的在世态度。余华前期小说当中苦难与绝望紧密相联,当人的生活在苦难中毁灭的时候,绝望也就弥漫开来。然而无论是对现实的绝望,还是对命运的绝望,说到底都是对沉沦于苦难之中的生活的绝望。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生命的悲剧没有停止上演,生存的困境也并未消匿,然而余华所提出的“活着”的在世态度却无疑是向着绝望和苦难的深渊扔下的一根长索,这根长索的另一头连着的正是人的生活。毫无疑问余华是个抱着悲剧人生观的作家,他从未放弃过“人活着就要受苦”的想法,在他眼中人面对的是注定是悲剧的人生,是无情无义的世界。然而,进入90年代的余华不再把死亡作为绝望生命的透气孔,不再把死亡作为对生命的惟一解脱——否定性的解脱。他开始对生命进行肯定,对严肃的人生问题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要对生活回答“是”。这貌似平淡的答案——用“活着”的在世态度来面对苦难的生活,首先在《活着》当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仿佛是日出的光芒照亮了黑暗,贯穿余华小说的那种浓得化不开的黑暗天幕终于被撕开了一个口子,生命的光亮照了进来。
余华借《活着》表达了他认识的真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4]从这个意义上讲,《活着》就是一部人生寓言。福贵所持守的面对苦难人生而活着的在世态度绝不只是一个农民的个人生存体验,它所表达的是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面对悲剧的生存态度。《活着》所体现的面对悲剧的内在精神从本质上讲和充满哲理的西方神话“西西弗斯的故事”是并无二致的。风尘仆仆的西西弗斯受诸神的惩罚把巨石推向山顶,而石头又重新滚下山去,于是西西弗斯又走下山去,重新把石头推上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加严厉的惩罚了。但西西弗斯坚定地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努力不停,永远前进,他朝着山顶所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他生活得痛苦,同时也成就了胜利。西西弗斯经历的是无望而又无效的劳动的折磨,福贵经历的则是生活的大起大落,丧亲的接连发生。当他一次又一次忍受苦难,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生活和亲人身上时,最后却发现一无所有,孑然一身,所有的亲人都离他而去,他已失去了希望的寄托。但是福贵并没有放弃生活,他仍然以超越苦难的达观和超越绝望的平静悠然地生活着。当西西弗斯坚定的走向不知尽头的磨难,在对荒谬命运的反抗和诸神的蔑视之中获得救赎的时候,福贵也以穷尽苦难和穷尽生活的“活着”的在世态度拯救了生活。《活着》正因为这样的教赎而成为了沉重却令人振奋的作品。
《活着》告诉我们,尽管命运注定是悲剧,然而我们应该做的是穷尽现在,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关键是要活着,带着这种破裂去生活,只有这样人类的高贵才能在毫无意义的世界里重新获得其地位。没有一种命运是对人的惩罚,只要竭尽全力去穷尽它就应该是幸福的。面对苦难,面对悲剧命运而活着,对生活说“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反抗,就是在赋予人的生命和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活着”的在世态度是救赎这一主题话语之下的重要语码,在这种在世态度之中人原始的生命强力、对世界的乐观态度以及生命的质感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它们构成了绝望景象和苦难人生的现实性的正面救赎力量。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活着”的在世态度,人的生活才免于彻底的毁灭,并由此获得了终极期待的可能。
《许三观卖血记》的在世态度的精神实质可以说是对《活着》的重复,只是小说的表现更具有日常生活性,更接近生活的原生状态,让人感到更加亲切。就揭示的深度而言,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走向成熟和练达的“重复的诗学”。
其二,从人的危机走向人的复活,在余华前期小说所展示的罪恶、暴力、血腥、杀戮等等的背后,隐藏的是对人性本身的沉重的绝望。对于人性,余华同样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说到底,他对于现实和生活的绝望,对世界的绝望正是根源于对人性的绝望。可以说人性的罪恶造成了无边的苦难,人性的沉沦导致了生命的沉沦和黑暗的“世界之夜”的降临。余华笔下的人性畸变和人性丑陋事实上消解了人本身,展现的是人的危机。然而这种对人性的强烈绝望正是深含在对人性的热切呼唤之中的,绝望得越彻底,期盼得就越深沉。因而,在彻底放逐人性之后,也就必然引出对于拯救话语的讲述。与人的生活的拯救相伴随,人的危机开始转向人的复活,人性开始复苏了。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人性的光辉,人性的美好在字里行间闪耀着。家珍的善良,凤霞的贤淑,二喜的质朴,苦根的乖巧,哪一样不感人至深。而在许三观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的情景里,在许三观向方铁匠和何小勇女人借钱的情节里,在许三观赴上海途中卖血的经历里,我们更是读到人性的宽容与善良,人性的纯净美好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这两首旋律温和的跳跃着的民歌之中,人性的光辉终于穿透罪恶与绝望的阴云,照亮了人类生活的天空,被消解掉的人又重新复活,在天地之间站立了起来。
苦难与救赎这两大主题话语是自然的紧密相联的。它们共同的指向对象都是“人性”和“生存”。正如前期小说中罪恶性的苦难必然与深沉的绝望和全面的亵渎相联系一样,从横向上看,当苦难在余华90年代小说当中显现出新的意义时,救赎这一主题也就应运而生。而从纵向上讲,救赎主题的出现也是对余华前期小说中创作思想的水到渠成的自然发展。苦难和救赎这两大主题话语不仅使余华90年代小说在风格上有了回归古典和民族传统的倾向,在语言上变得简约和质朴,在叙述上向民间转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共同体现出余华90年代小说所具有的超验的哲学关怀。
三、哲学关怀
余华90年代小说当中超验的哲学关怀主要体现为两点。
一是对“存在”的回答。“存在”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哲学问题,余华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就是用文学的文本对这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作出的回答,因而使作品具有了超越性和哲学关怀。这种关怀不是世俗的,而是超验的;不是针对某一个体的而是面向整个人类的。
作家北村曾说:“艺术家作为一个人,他在实存的空间之上感到一种彻底的无力性,这是他‘逃亡’的终点,在这个关键环节中,作家应该回答‘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存在、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主式,也就是他的逃亡方式,从一个实在空间向艺术空间的逃亡,精神对原有价值观念的逃亡,由此确立他与世界的精神关系。”[8]余华正是用他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存在”这个世界性的话题,体现了他对“存在”的本真性和终极性的关怀。他讲述的是世俗的生命故事,但本质上却是为了超越世俗,指向人的“存在”这一终极,追求一种永恒性。人的整体生存境遇而不是人的个体遭遇成为了作家思考的中心,而思考的结果,就是对于“存在”作出的回答。这样余华90年代小说的主题话语也就被赋予了形而上的色彩和哲学化倾向。
第二点是作品所蕴涵的深刻的悲剧精神。余华作品几乎篇篇都是悲剧。余华把自己逼进一个极端的空间,在悬崖上观看人类生命痛苦的挣扎。但是前期的余华胶着于存在而对超越有所疏忽;胶着于现实的有限性、无奈性、被动承受性,而疏离了有限之中的无限,无奈之中的能动选择。文学中,终极意义、价值标准、自我实现的话题日渐淡去。可以说前期的余华是个悲剧作家,而不能说其作品具有了悲剧精神。只有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现以后,在苦难可以被救赎之后,悲剧精神才真正在他的作品中显现出来,并且通过这种悲剧精神才真正实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
绝不能把悲剧精神简单地等同于悲剧感,也绝不能一味地把苦难和绝望当作终极,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是能动的超越。从本质上讲,对苦难的反抗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意味着人在面对无法摆脱的困境的时候,并不是完全软弱无力的,每一个个体都能通过他自己的行为、生活和思维,走向一个较好的世界。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活在世上,还意味着超越存在以获取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福贵以“活着”的生存态度对抗痛苦的生命悲剧,许三观用汩汩的鲜血获取生存困境的解除便具有了最深刻的悲剧精神。
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悲剧世界观最为极端的扭曲畸变,就是真正的悲剧变成绝对,并且看起来仿佛是它构成了人类的精髓和价值”;“悲剧与不幸、痛苦、毁灭,与病患、死亡或罪恶性截然不同……它是问询而非接受——是控制,而非哀悼。”[9]事实上,悲剧和悲剧的解脱是绾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悲剧变成“唯悲剧”,那么悲剧精神也就丧失了。余华凭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重塑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曾一度失落的悲剧精神。正是这种悲剧精神向人自身的探寻和追索,把人从绝望和苦难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指出了更为美好的道路。它不仅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具有了哲学的高度。
苦难和救赎这两大主题话语的出现使余华90年代小说在前期小说的基础上迈向了新的境界,同时又凸现出其文本在精神品格上的绝对性与超越性。《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可以说是余华向90年代文坛奉献的扛鼎之作。它们超越了世俗,又不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历史小说,贯穿于其间的终极思考与超越的哲学关怀使这两部作品即使历经岁月风尘而仍能绽放出夺目的异彩。
收稿日期:2001-02-20
标签:余华论文; 许三观卖血记论文; 人性论文; 小说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文学论文; 十八岁出门远行论文; 活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