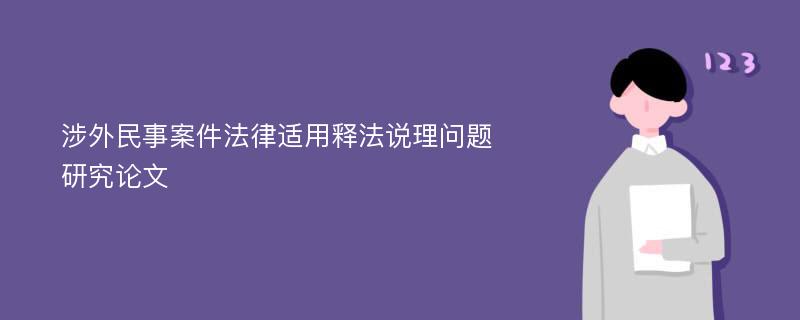
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问题研究 *
翁 杰
(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西安 710063)
【内容摘要】 在我国涉外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法官不说理或错误释法情况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热议话题之一。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法官释法说理的理由主要在于当定性时出现识别冲突或适用选择性冲突规范、结果选择性冲突规范以及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不仅是“找法”的过程,同时也是正当化的过程。为控制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法官有义务论证其法律选择的正当性。涉外民事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应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向度展开,法官在释法说理时应遵守合法性、合理性、客观性以及融贯性四项原则。
【关 键 词】 涉外案件 法律适用 释法说理 理由与情形 进路和原则
前言
相对于国内案件而言,涉外案件中的法律选择或法律适用是其最具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个方面,也是涉外民商事案件必须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1]P36然而,在我国涉外审判实践中,不同法院对法律选择过程和理由的说明情况差别很大,有的令人赞叹、堪为典范,有的不置一词、径行用法,而且后一种情形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2]P27-42正确适用法律是公平审判的前提和基础。涉外案件审判对法律适用过程和理由不作任何说明就直接适用法律容易导致错误适用法律,也难以令当事人信服,因此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合法性和权威性在我国都存在很大问题。[3]P14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2018年6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的发布,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如何规范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中法官的释法说理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国内探讨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文章比较多,但从涉外民事法律适用角度讨论释法说理的文章几乎没有。基于此,本文拟围绕《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和涉外案件的特殊性,展开对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若干问题的研究,以期为接下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有关涉外案件释法说理的细则性规定提供智力支持。
一、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特殊性
《指导意见》第2条规定,“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说明裁判所认定的案件事实及其根据和理由;要释明法理,说明裁判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以及适用法律规范的理由。”在我国涉外民事裁判中,一般认为,法官法律适用主要采用以逻辑涵摄为特征的推论模式,即将冲突规则作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并通过演绎推理得出准据法,最后根据准据法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推论模式的思想根源来自于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萨维尼认为法律选择应由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准据法的确定问题。依照萨维尼的理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析离出每类法律关系中能够实现整个法律关系场所化的法律事实,这些决定法律关系本座的事实的选择通常是比较固定的,常常集中在如下几个:法律关系所涉及的人的住所;法律关系的标的物所在地;法律行为实施地;法院所在地。我们可以将萨维尼理论概括成一个公式:“法律关系+连结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这就是萨维尼所构建的一切法律选择规则的基本结构。[4]P140依照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思想,我们可以将涉外民事法律适用过程转化为一个司法三段论的法律推论过程,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构成了一个完备、封闭的公理系统,而冲突规则又源自“法律关系+连结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体系”这一公式,由于前提的真,这就保证了法律推论的有效性。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法律适用模式试图借助司法三段论强制性的逻辑规则,来防止法官法律适用中的恣意,以维护法官对法律的绝对服从。在这一模式下,在涉外民事立法较为完备的情况下,法官似乎只需通过解释方法就可以获得据以作为推理前提的冲突规则。“由于法律推理乃直接自既定规则出发,无须触及那些具有不确定性的价值判断如正义等问题”。[5]P51法官的作用“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从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赋予法律意义”。[6]P39法官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中通过演绎推论,在冲突规则与事实之间往返、对接并获取准据法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涉外案件法律适用就是一个纯粹的三段论操作。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这一法律适用模式也遭到了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法学派学者的批判,他们从多个视角解构冲突规则完美确定的神话。美国学者布莉梅尔就认为,“冲突规则本身的形式主义特征及其过度抽象的性格,导致机械地适用一个封闭的规则体系的教义,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7]P509安特马认为三段论的演绎逻辑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司法活动实质上是一个情绪化的过程,法官首先得出判决的结论,然后用法律原则和逻辑阐述发生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逻辑和原则在其中只起到第二位的作用”[8]P480。弗兰克不仅怀疑法律规则的作用,而且也怀疑法官据以判决的法律事实,“因为法官作为证据的确认者听取证言和发现事实,他不仅有自由裁量权,而且也会犯错”[9]P28。
琵琶仙微微一笑,说:“这个你放心,庄翻译的底细我清楚,他跟刁德恒不是一路人。明天中午,你送香肠慰劳太君,去一趟北大营,但要避开姓刁的保安队长,庄翻译会悄悄来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即使法官能够找到相应的冲突规则,他在确定演绎三段论中的大、小前提时,仍须“一步三回头”地谨慎行进。正如拉伦茨所言,“裁判领域的实际情势往往是:每个法律都需要解释,单纯由法律条文的文字,并不能获得大前提;而通过逻辑涵摄就能获得小前提的个案,在实践中也只占有限的一部分”。[10]P152一旦演绎三段论的大前提无法确定(如冲突规则规定了多个或主观性连结点时),或者小前提——作为陈述的个案事实——如存在识别冲突时,那么演绎推论的运用就会受到限制。因为推论只是一种思维程序,单凭逻辑,并不能解决如何确定大小前提的问题。由此可见,司法三段论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反映出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特点,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司法三段论要保证结论为真,其中作为法律推理的小前提,即案件事实必须保证具有真值性。然而,我们知道法律事实的根本性质并不在于其具有真实性,而在于其具有法律意义,法律意义的获得是必须在法律规范的参与下才得以产生的。涉外案件中的事实也是一种制度性事实,正如塞尔所指出的,“任何事实都是在特定的制度(语境)中才成为该事实,并且是穷尽了认识事项后的事实”[11]P8根据塞尔制度性事实的理论,我们知道法律事实是根据具有主观性质的制度条件建构而来的,法律事实的意义来自于形成制度语境的法律规范,而不是依赖于作为物质性存在的客观存在。法律事实作为一种制度性事实,在制度的语境下才有意义,法律事实的获得必须借助于法律规范进行,法律事实因此具有规范性事实的特征。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中,法官所要处理的不是客观事实,而是制度事实。制度事实是与制度语境相关的。同一事物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其法律含义是不同的。例如在刘祥富与谭正敏、成都泰和电气有限公司、香港泰和电气有限公司、香港泰和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二审一案中①,有关董事对公司的忠实义务,香港和内地公司法律中均有规定,但两地法律对该忠实义务的具体内容、违反义务后的责任以及公司的救济途径作出了不同的规定。香港公司结构中没有专门的监督机关,而由公司董事会兼任,因此董事会成为了高管损害公司利益时的救济诉诸对象;而内地公司法中规定有专门的监督机构——监事或监事会,则股东在发生有董事损害公司利益、欲提起派生诉讼时必须首先请求监事或监事会提起诉讼,请求失败时才算用尽内部救济而获得起诉权。本案中,董事损害公司利益后的侵权责任法律关系应以公司香港《公司条例》还是以中国大陆地区《公司法》来定性,成为本案的焦点问题,因为适用不同的法律来定性,其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因此,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中,对于案件事实而言,法官所要处理的难点是应该选择何国法律进行定性的问题。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法官如果仅仅依据法院地法来给案件事实定性,而根本不考虑冲突规范所指向的外国法是如何定性案件事实的话,其裁判结果很可能得不到外国法的支持,认为错误地适用了其本国法。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司法三段论推论的小前提,我们无法以科学意义上的真实或者程序意义的真实作为检验法律事实的标准。在有些案件中,特别是如果当事人对于事实认定存在争议时,作为司法三段论的小前提只能是法官在案件事实与法院地法和准据法之间来回顾盼的往复中才能得以确定。实践中,就事实而言,法官在释法说理时所要做的就是要阐明他是用什么方法(根据)来确定识别依据的,其理由又是什么。
第一,在涉外案件事实的定性过程中,发生识别冲突的情况。识别冲突是指由于法院国法律与有关外国法律对同一事实构成作出不同分类,采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观念进行识别就会导致适用不同冲突规范和不同准据法的结果。识别冲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1.不同国家对同一事实赋予不同的法律性质,因而可能援引不同的冲突规范。例如,关于未达一定年龄的青年结婚需要父母同意的问题,法国法把这种事实识别为婚姻能力问题,英国法则视之为婚姻形式问题;2.不同国家往往把具有相同内容的法律问题分配到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去。比如,关于时效问题,一些国家认为它是实体法上的一项制度,另一些国家则认为它只是程序上的一个问题;3.不同国家对同一问题规定的冲突规范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各国法律都规定“不动产依不动产所在地法”,但各国对什么是不动产有不同的理解,如法国把蜂房看作动产,荷兰则视之为不动产;4.不同国家有时有独特的法律概念。例如,许多国家都有占有时效制度,我国则只有诉讼时效制度。[15]P127-128对于识别冲突该如何解决,各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主张不一,主要有:法院地法说、准据法说、分析法说与比较法说、个案识别说、折中说、功能定性说以及两级识别说等。正是因为理论界对识别问题存在着上述分歧,各国法院的实践也很难前后和彼此一致。因此,绝大多数国家的国际私法法规对这个问题都未作明文规定,它们认为,识别问题不能用一条准则规定下来,应留给法官去自由裁量。[16]P71对于识别问题,我国《法律适用法》第8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法院地法律。”但本文认为,一国法院在处理国际民商事案件时,不应局限于某一种方法,而应从有利于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保护民商事关系的稳定,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便利案件处理的目的出发,来确定识别依据。实践中,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到底采取哪种依据来定性,必须结合个案来处理,但无论采取何种标准,若当事人对此有异议时,法官须说明理由,并论证其合理性。例如,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诉瑞士工业资源公司”上诉案中,我国法院显然是依我国的法律观念进行识别,同时充分考虑了原告的选择权利,即在合同行为和侵权行为竞合的情况下,看原告提起侵权之诉还是合同之诉以决定案件的性质。从本案的有关事实来看,被告自始至终使用欺骗手段,利用合同形式达到欺骗钱财的目的,根本就没有打算履行合同;原告提起的也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因此,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将它识别为侵权行为是恰当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公报中予以公布,也表明了其支持和肯定态度。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涉外案件法律适用的特殊性在于法官运用司法三段论推理时,对于法律推理大小前提的确定仍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面临多种选择。在许多情况下,冲突规则并没有提供唯一的答案,法官不可能像机器那样机械地适用法律。在法官面前,存在着多种解决方案可供选择。自由裁量权设定了在数个合法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同时自由裁量权并没有预设从多个解决方案中选择某一个特定方案的义务。自由裁量权假定在数个备选方案中,法官有权从中挑选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方案。自由裁量权以立法面临着许多备选方案的存在为基础,以道路上分叉的真实存在为前提。[14]P20-21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是找法的过程,另一方面是法律适用的正当化过程。所谓找法的过程就是法官根据案件事实和冲突规范,经过演绎推理得出准据法的过程;而法律适用正当化过程则是指在找法过程中,当案件事实定性以及冲突规范面临多项选择时,法官要对其所做出的选择说明理由并证明其正当性的过程。找法只是为个案准备一个可证立的法律判断,验证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并将其转化为准据法的结论,则必须补强一个正当化过程。由于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以及存在识别冲突问题,因此,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案件事实和冲突规范之间并不是总能找到逻辑上的契合或对应关系,而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或悬置判断,这时法官须依托各自所处的法律文化和司法传统,针对个案所需考量的事实因素和参照规范,运用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法律论辩等法律方法,并以逻辑的、修辞的或对话的论证方式展开法律适用释法说理。
二、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中释法说理的情形
《指导意见》第7条规定,“诉讼各方对案件法律适用存有争议或者法律含义需要阐明的,法官应当逐项回应法律争议焦点并说明理由。”本文认为,在涉外案件审理过程中,在下列四种情况下如果诉讼各方对案件法律适用存有争议或者法律含义需要阐明时,法官应当说明法律适用所采取的依据,并且阐述或论证这样适用法律的理由。③
2013年5月9日星期四上午,东营天气阴有雷阵雨,气温13~20℃。阴雨天气,太阳能电池板仍能对电动车的蓄电池进行充电,只是充电电流比较小而已。充电电流测试数据见表3。
第二,司法三段论要保证结论为真,其中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即冲突规范也必须保证具有真值性。而我们知道,冲突规范具有不同于实体规范的特点。按照通说的观点,冲突规范是由范围和系属两部分构成的,范围和系属是由连结点连接的,连结点决定了应该选择何种实体法作为准据法。传统国际私法为了追求冲突法上的正义,通常在连结点的确定上会选择国籍、住所、行为地、物之所在地、法院地等这样的单一、客观连结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排除法官的主观判断,根据冲突规范的援引,实现判决结果的一致性。然而,从17世纪开始,国际上出现了对传统冲突规范进行“软化处理”的趋势。[12]P45冲突规范软化处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进行:1.对同类法律关系进行划分,依其不同性质规定不同的连结点;2.对于一个法律关系的不同方面进行分割,对不同部分或不同环节规定不同的连结点;3.用灵活的开放系属代替僵硬的封闭系属。4.增加连结点的数量而增加可选性。[13]P22-23经过软化处理后的冲突规范,一方面注重实现冲突法的实质正义,另一方面更关注冲突规范的社会效果。在形式上,各国立法在冲突规范的确定上多采用了选择性冲突规范或主观性冲突规范,由此增强了法律选择的灵活性和开放性。例如,在欧阳志初与李彩群、罗裕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中②,一审法院在判定受害人对其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的赡养义务时适用了《法律适用法》第29条的规定,且认为:具体到本案受害人对其父母的扶养义务,被扶养人生活费支付的法律适用问题,根据《法律适用法》第29条“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的规定,本案应适用有利于受害人父母索赔被抚养人生活费的法律。可见,冲突规范软化处理导致法律选择的多样性、多种可能性,法官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可能会面临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这就好像法律之路到了一个交叉口,法官必须在没有清楚明确的标准指引的情况下选择一条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司法三段论的大前提并非是确定的,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中,法官必须结合案件事实,经过比较衡量到底应选择哪一个连结点,在连结点确定以后,才能最终确定法律推理的大前提。
从形式向度和实质向度展开涉外案件释法说理再现了法官在法律适用释法说理时说了什么以及是如何说的,是评价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重要内容。在不同类型案件中法官释法说理的侧重点以及采用的论证方法不同。在简单案件(即事实清楚不存在争议或冲突规则连结点的确定也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中法官主要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侧重于证立案件事实与冲突规则是否相适应;而在疑难案件中则主要采用论题学思维方法,论证法律适用中各环节存在争议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也就是当点P(1,1)不变时,D换成y轴上除原点外的其他点,结论就不成立了,因此抛物线的方程是由点P(1,1)决定的,这说明D与P之间是有联系的.
第三,当法律适用援引结果选择性规范时。所谓结果选择性规范,是指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以追求或达到一定的判决结果为目的的法律选择规范。这种规范是冲突法中结果选择方法的规则体现和外化表达,是法律选择趋向从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衍变的一种表征和诠释。结果选择性规范可以分为结果定向的选择性选法规范、“有利于”模式选法规范和单方当事人选法规范。这几类规则在我国的《法律适用法》中都有所体现,其中,《法律适用法》第21条、第22条、第26条、第32条和第33条皆设定了多个连结点,或者是促进身份关系成立的选法规则,或者是促进法律行为成立的选法规则,皆属于结果定向的选择性选法规范;而《法律适用法》第25条、第29条和第30条通过规则借助“有利于”字眼,试图实现对父母子女关系、扶养和监护关系中弱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目的,是为“有利于”模式选法规范;而《法律适用法》第42条和第45条分别赋予消费者合同中的消费者和产品责任中的被侵权人单方选择法律的权利,法律选择天平向消费者合同关系和涉外产品责任关系中的弱方当事人倾斜,以实现法律选择上的结果定向。结果选择规范在我国的法律选择立法史上是全新的规定,也是《法律适用法》的一大亮点。[17]P10实践中,在适用结果定向冲突规范时,由于法律适用的结果某种情况下就是依据法官的主观判断来完成,因此,法官就有必要在审理中说明他这样做的理由,否则,其结果就很难为当事人接受,其结果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也值得质疑。例如在“陈某某与曲某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2013闵少民初字第104号)中,法院认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亲生活。本案中法院依照《法律适用法》第25条作出了判决,并认定曲亚某某随原告共同生活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其理由:首先,曲亚某某自出生后随原告共同生活至今,双方建立了真挚的母子感情;其次,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不动产权证、收入证明、个人所得税缴税单据、社会保险费缴费记录、学历证书,均能印证原告具有良好收入、居住条件,原告自身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充分具备抚养儿子的各方面条件;再次,曲亚某某目前尚不满两周岁,其随母亲共同生活,于法不悖。
第一,合法性。合法性原则的目的在于设定法律适用依据的有效渊源,以实现冲突规范对法律适用过程的约束或指引作用。合法性原则要求法官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展开。④我国《法律适用法》第1条规定,“为了明确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合理解决涉外民事争议,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这一条明确了涉外案件法律适用必须依照冲突规则的援引来确定准据法,并依据准据法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涉外民事裁判的任务是通过援引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并依据准据法来解决个案争议。不过,每一项司法判决均以一条或数条冲突规范为前提,并不意味着判决结果通过冲突规范的演绎推理就自然得出了,因为从规范评价到法律适用结论,尚须衔接一个具体化、现实化的过程[33]P25。如前所述,我国《法律适用法》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大量地采用了选择性冲突规范和结果选择性冲突规范。在实际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当援引这类冲突规范时,如何确定准据法,法官须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经过严格地论证,最终做出自己的判断。为了将法官的释法说理行为约束在冲突法体系之中,合法性原则要求上述具体化、现实化过程,除了须尊重冲突规范的字面含义之外,还须遵守冲突法上业已系统化了的各种法律选择方法。[34]P283当然,合法性原则并不等于抠着字眼适用法律的法条主义和机械主义。合法性要求也不是绝对的,如果适用某一冲突规范的结果背离了冲突法的立法目的且不可接受,就应允许法官变通个案规范。例如,《法律适用法》第44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从文义解释来看,假若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时,法官应首先考虑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只有当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时,法官才可以考虑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是在实践中,如果法官发现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其结果明显不合理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这时他能否考虑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呢?本文认为,从目的解释的角度看,这样做是可以的。这是因为涉外侵权行为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所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律适用法》也将涉外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法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定,不仅与当代各国关于涉外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相一致,也符合国际私法的发展趋势。《法律适用法》第44条规定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实际上是作为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基本原则的一种例外情况加以规定的,其立法初衷主要是考虑到当事人对本国法应该更为了解,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更有利于当事人共同接受,也有利于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但从法律适用实质正义的角度看,当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的结果与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结果相比显失公平的情况下,法官如果只能适用当事人共同居所地法的话,这种做法显然与《法律适用法》的立法宗旨相背离的。不过应当申明的是,倘若法官打算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那他就必须在释法说理时说明这样做拥有更好的论据,必须能指出并论证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的不足。法官不能以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与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同样好”为由,背离通常的做法而损害司法实践的可预见性及法的安定性。总之,对于侵权责任,在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情况下,法官应首先考虑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但这种做法并非不能改变的,只是这种改变必须以更多、更好的依据为基础。
三、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进路
《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目的是通过阐明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如上所述,由于涉外案件法律适用中双方当事人很可能在上述四种情形下产生法律争议,那么,一旦产生争议,法官又该如何适用法律和释法说理呢?换言之,法官应从何入手?又该采取何种方法来正当化这一过程呢?本文认为,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不能偏离冲突法的价值取向,二者密切相关。为实现冲突法上的正义,传统国际私法要求各国法官通过法律选择方法的运用达到价值无涉,客观中立地选择准据法。在法律思维模式上,传统国际私法认为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冲突规范和事实的逻辑涵摄过程,是事实适用于冲突规范的演绎过程,法官对于法律用语不能附加任何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冲突规范普遍意义确定的过程,而不是针对个案的解释,传统法律选择模式中准据法的确定是发现应该适用什么样的实体规范,而不是针对个案裁判规范的证成。传统法律选择模式主要表现为方法论意义上的法律选择理论,它将冲突法的意义世界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上,将冲突法视为一个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客观性、中立性和封闭性的自治系统,这是因为,传统法律选择方法论建立在以下三个假设的逻辑前提之上,一是各国在冲突规范的理解上应该相同,二是法律选择体系具有一贯性,三是法律选择体系完满自足。
仁里铌钽矿床位于幕阜山复式花岗岩体的西南缘, 区内出露地层简单,主要为冷家溪群坪原组片岩及第四系。区内断裂构造较发育, 主要为北北东向的天宝山–石浆压扭性断裂(F12)及其次级构造,黄柏山张扭性断裂(F75)贯穿矿床西部主要的含铌钽伟晶岩脉。天宝山–石浆压扭性断裂切割了整个幕阜山岩体,将幕阜山岩体分成东西两部分(如图2)。
在美国冲突法革命的背景下,美国现实主义法学者一边竭力否定传统法律选择模式,一边又积极地探索能够取代传统法律选择模式的理论体系。与传统的法律选择模式相比,美国现代法律选择模式体现了国际私法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的追求,强调个案公正、法律选择的实质性依据和社会效果,在思维模式上更多地采用实质推理。美国现代法律选择模式虽然对传统法律选择模式进行了突破,但同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美国现代法律选择模式强调法律内容(准据法)的正义性和法律选择过程中法官的地位,这种理论在彰显主体的意义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律选择不确定性的风险。另一方面,美国现代法律选择模式主张放弃构成国际私法基础的冲突规范,既不利于国际私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发展,同时还可能导致国际私法立法的搁置,那么基于人们对制定法的合理期待而树立起的法律权威就可能会被削弱,这对于多边主义观念下平等适用各国法的国际私法基本原则构成了冲击。当代冲突法在价值取向上从本质上说是两种正义,即“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要求,同时是对两种正义要求的平衡。两种正义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诉求,既“相克”,又“相因”[24]P353。因此,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应从以下两个向度展开:
第一,从形式向度展开释法说理。从形式向度展开释法说理的重点在于证明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是否相适应。如前所述,传统上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从形式上看就是一个司法三段论过程,即将冲突规范作为法律推理的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准据法一般被认为是从这两个前提演绎得出的。司法三段论一直是证明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相适应的论证形式,在简单案件中更是如此。法律适用形式向度的释法说理以演绎的形式展示了法律适用结论及其直接前提,对于法官来说,这是实现形式正义的重要方法。具体来说,形式正义要求“类似案件类似处理”,而要想把这个原则付诸实施,就需要一个可以将一般性的冲突规范普遍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工具,演绎推理正好迎合了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这一需要,它是联结结论与前提的最合格的形式之一,保证在运用适当的情况下,前提与结论的联结在形式上是正当的。基于其在保障形式正义上的重要作用,司法三段论的形式已成为法律规范普遍化的必要手段。应当注意的是,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相适应的问题,既涉及到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在事实上的相适应,同时也牵涉到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在价值判断上的相适应。在我国涉外民事裁判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法官比较注重从形式上证明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在事实上的相适应,往往忽略了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在价值判断上的相适应。比较典型的是多数判决书只是从事实层面,如住所、物之所在地、行为地以及法院地等来证明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很少有从价值层面论证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的结果往往很难令当事人信服。因此,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在价值判断上的相适应最终也应该用演绎推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可以用贝科克诉杰克逊夫妇案[25]P232-233为例,来说明法官如何从事实和价值两个层面来证明案件事实与价值判断上的相适应。本案中,如果法官适用了“侵权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这一冲突规则,从而得出准据法即加拿大安大略省法的话,那么原告贝科克小姐的赔偿请求是不能得到满足的,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律规定,除非为了盈利的商业性运载乘客,非营业性汽车的所有者或者驾驶者对同乘者由于身体所受到的损害以至死亡,不负赔偿责任。从形式上看,法官适用加拿大安大略省法得出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案件事实与冲突规范是相对应的,我们完全可以将法律适用过程演化为一个三段论推理过程,即案件事实+ 侵权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 安大略省法。但这样做,在价值判断层面却并不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因为加拿大安大略省《高速公路交通法》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乘客与驾驶者相互串通向保险公司提出欺诈性的索赔,显然,这一法律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安大略省保险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纽约州保险公司的利益。相反,纽约州的法律要求侵权人对因自己的疏忽而引起的伤害负赔偿责任,法院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以事故发生在本州以外而取消本州立法上给予本州居民的这种保护。因此,本案中法官如果适用了“侵权的损害赔偿适用当事人双方的共同住所地法”这个冲突规则,从而得出准据法即纽约州法律的话,则无论是在形式上,而且在价值判断上才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判断,这样才能够证明案件事实与该冲突规则是相适应的。由此可见,演绎推论可以用来重构涉外案件法律适用的论证过程,以证明或者检验其法律适用的合法性和形式有效性。此外,由于演绎三段论强调前提和结论间存在着“必然地得出”的关系,能提供“终极的说服力”,[26]P110因此对突出大前提——冲突规则——的权威性,进而对落实形式法治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该平台依托华山-五院-闵行社区医联体,通过互联网救治服务实现包括多学科远程会诊、溶栓取栓、评估随访、监护教育和大数据科研一体化的远程智慧卒中中心。据韩翔介绍,其中重点突破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预防(人群分类、智能筛查、风险预警)、干预(穿戴设备连续监测、个性化照护、O2O主动问诊与延方)和救治(多级联动、移动介入、远程手术)等方面的应用。从而满足患者普适就诊、提高诊疗质量、降低医疗费用、较大幅度降低脑卒中死亡率和致残率。
第二,从实质向度展开释法说理。从实质向度展开释法说理的重点在于说明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如果法官运用司法三段论进行推理,当法律推理的大小前提存在争议时,他是如何处理的以及如何论证这样做的正当性的。实质进路的释法说理从性质上讲是一个“论题学思维”的论证过程。“论题”的字源是希腊文“tópoi”和拉丁文“loci”,其字面意思是“场合(place)”,意指一种并非严格因循规则,但仍值得信赖的论辩的出发点,其内容包括命题、观念或观念群。[27]P331论题在论辩中可以用来支持或反对特定的意见,指示通往真实的途径,或者说像船锚一样起到“定位”的作用。[28]P60论题学思维是以问题作为定位的思维方式,在整个思考过程中,我们对资料的收集、推理论证和方案的选择都是围绕着问题展开,是问题对整个思维过程起到导向作用。论题学思维的特点,一是意在使人们面对多种选择,进退维谷的困境时,寻求到最妥当最合理的解决方案;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思维,围绕问题展开论辩探讨,在各个备选方案中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三是展示了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同一问题的所持的各种观点,并以此为起点,通过论证达致合理的解决方案;四是论题学思维过程是围绕问题,检验某一论题作为或然性观点是否符合当前情形需要的过程,是一种倾向于合理性判断的思维方式。[29]P23如前所述,在涉外民事案件释法说理过程中有时法官在某一问题上可能面临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这时他就必须围绕这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论证,最终从备选方案中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以证明这样选择的合理性。实质向度的释法说理采用论题学思维的目的在于旨求“有条件地成立”,认为单纯依靠演绎推理并不能解决法律适用多个环节中存在的争议,实践中到底采用哪种方法或连结点只能经由“论题学思维”方式得到结论,即经由一种“特殊的问题讨论程序”,为结论找出一些“足以”使其正当化的观点与依据,因而该种释法说理活动较富“论辩——对话”的色彩。在实质向度的释法说理过程中,论题在论证过程中的作用,可用“椅子腿”和“织成布料的丝线”的比方来描绘,即证明一开始从单个论题出发,这一论题的证明力可能很弱,但在积聚其它支撑性的论题后,力量逐渐变强。[30]P40例如,在前述“陈某某与曲某某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中,法官是从以下三个论题出发来论证曲亚某某随原告共同生活有利于其健康成长的,一是从母子感情角度证明曲亚某某随原告共同生活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因为曲亚某某自出生后随原告共同生活至今,双方建立了真挚的母子感情;二是从原告抚养儿子的各方面条件角度证明曲亚某某随原告共同生活有利于其健康成长,这些可以从原告在本案中提供的不动产权证、收入证明、个人所得税缴税单据、社会保险费缴费记录、学历证书,均能印证原告具有良好收入、居住条件,原告自身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充分具备抚养儿子的各方面条件;三是从现实生活角度证明曲亚某某随原告共同生活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曲亚某某目前尚不满两周岁,其随母亲共同生活,于法不悖。上述三个论题如果从单一角度看,其可能证明力较弱,但三个积聚在一起则证明力会逐渐变强,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可见,从论题出发的推理和论证,是一个开放的言说过程,整体上完全不同于从限定的命题出发的演绎推论,即便在言说过程中的某些阶段会用到演绎推论。相应地,论辩性论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证明”,它不追求“必然地得出”,而只寻求有条件的成立。法律适用实质进路释法说理的结构,呈一种层层递进、交互论证的枝型构造。这里我们可以借用图尔敏(Toulmin)的论证图式加以说明。[31]P41-42例如在上述贝科克诉杰克逊夫妇案中,法律适用实质进路释法说理形成步骤可解析如下:(1)提出一个具体“主张”(Claim, C),如本案应适用纽约州法;(2)提出支持这一主张的“事实根据”(Ground, G),相对于法律上的证据,如贝科克小姐和杰克逊夫妇的住所都在纽约州;(3)当某人质问如何能根据G得出C时,论证者必须补充一个前提或命题,例如一条法律规则或原则,是谓“保证”(warrants, W),如根据公正期望保护原则,纽约州的法律要求侵权人对因自己的疏忽而引起的伤害负赔偿责任,由于双方当事人长期生活在这一法律环境下,因此作为驾驶者的杰克逊应该了解在驾车过程中因自己的疏忽而引起的伤害负赔偿责任。这三个步骤构成了一个最为基本的论证形式,但如果W的可接受性受到质疑后,还需补充支持W的“基础依据”(backing, B),如传统上世界各国在对待双方都具有同一国家国籍的人的事务上一般都依其共同的本国法来处理。在某些场合,论证还会涉及作为例外情况出现的“抗辩”(rebuttal, R),如安大略省是事故的发生地,以及“限定”(qualifier, Q用来进一步说明W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系争个案),如除了双方当事人是纽约州人外,车辆的保险地也在纽约州。因此,在本案而言,法官适用纽约州法是比较合理的。[32]P120
第二,当援引选择性冲突规范时。所谓选择性冲突规范是指冲突规范的系属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结点,但只选择其中之一来调整有关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冲突规范。选择性的冲突规范分无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和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两种。无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是指法官可以任意或无条件地选择系属中的若干连结点中的一个来调整范围中的国际民商事关系。例如,《法律适用法》第22条规定:“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有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是指系属中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结点,但只允许依顺序或有条件地选择其中之一来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冲突规范。例如,《法律适用法》第4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我国《法律适用法》一个很大的特点在于大量地采用了选择性冲突规范。在具体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当援引有条件选择性冲突规范时,法官须证明条件是否满足,只有在不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采用另一个条件确定准据法;而在适用无条件冲突规范时,如果冲突规范条文里规定了多种连结点的情形,而案件只符合其中的一种情形,法官也必须说明本案符合该种情形,不能简单地引用条文了事。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告诉当事人采纳某一连结点的理由,并证明这样选择的正当性。例如,在徐艺雯诉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案(2015)佛顺法行初字第75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2015年10月20日)。本案中,原告徐艺雯诉称其与第三人严舜竞已定居澳门,根据《法律适用法》第26条,其与第三人的离婚协议应当适用澳门法律。根据《澳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子女抚养及抚养方式需要父母以协议确定之,该协议需经法院认可。由于涉案离婚协议中关于儿子的抚养方式未经澳门法院认可,违法了《澳门民法典》的规定,原告认为被告不应对离婚协议作出确认并作出涉案离婚登记,请求法院判决撤销离婚登记。法院在审判中,以原告申请离婚登记时使用中国身份证、未提及澳门非永久居民身份证,以及非永久居民身份证不代表经常居住地为澳门两个理由认为民政局适用中国法律并无不当,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开放使我们协会始终走在行业前列”,说这句话的时候,徐建国理事长语气中透着自豪。中国印工协成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5年,创立之初,首任会长范慕韩就明确提出了“大印刷观”的理念,并有一个经典的比喻:印刷,印刷设备、印刷器材如同一架飞机的机身与两翼,三个领域应紧密连结在一起,协同发展,才能推动中国印刷产业的进步。“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的定名亦由之而来。可以说,这个跨部门、跨行业、全产业链的全国性行业协会自诞生之初,就承载了推进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的厚望与重托。
四、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原则
《指导意见》第7条规定,“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处理案件时,应当坚持合法、合理、公正和审慎的原则,充分论证运用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并阐明自由裁量所考虑的相关因素。”如前所述,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在多个环节上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为了有效地控制法官在法律适用上的自由裁量权,本文认为,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应当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第四,当没有相应的冲突规范可以直接援引,需要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也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由于找不到相应的法条而陷入“无法可司”的局面,但基于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裁判原则,在不涉及法外空间的情形下,必须找到某类裁判依据进行裁判。[18]P7-8对于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我国《法律适用法》第1条第2款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这一条在学理上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兜底条款”,其含义是当没有具体的冲突规则可循时,法官可以采用最密切联系方法来确定准据法。最密切联系原则是20世纪中叶美国“冲突法革命”最卓越的成果,其一经产生便引起各国的瞩目,甚或成为判断一个国家国际私法立法是否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最密切联系原则并非是对传统国际私法的完全否定,而是扬弃。它是传统法律选择方法的更新与发展,代表了国际私法价值取向由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科学合理地实现了法律适用的目的,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P1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方法,我国国际私法学者也曾提出过许多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学者董作春认为“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透过各种连结因素的表层去分析通过该连结因素与该特定民商事关系相联系的法律的精神,以期找到与该特定民商事关系有着最真实的,即本质的、固有的、稳定的联系的法律”[20]P45;丁伟教授认为“不能拘泥于某一个或几个客观因素来决定适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而应从质和量这两个角度对与案件有关的各种主、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寻找法律关系的“重力中心地”,该重力中心地所属国的法律即为审理该案所应适用的法律”[21]P187;肖永平教授还提出了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五个步骤[22]P467-468。可见大多数学者认为法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应从连结点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入手来确定最密切联系地。但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完全是靠法官的主观判断完成的,因此,法官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时,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应充分说明是如何判断连结点的数量和质量的,并通过法律论证来确保裁判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例如,在香港美善公司诉香港同进公司案[23]P116-117中,本案中与合同有联系的地区是中国内地和香港,从表面上看,香港与合同的联系更多一些,因为当事人双方都是香港公司并在香港签订的合同,合同价金以港币计价和支付,而中国内地仅仅是该合同的履行地。但判断联系的密切程度不能仅考虑联系因素的数量,即不能仅仅因为与合同联系的因素较多地集中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就断言该国或地区与合同有最密切的联系,而还应该考虑联系因素的性质或重要性。在本案中,合同的特征性履行(即设备安装)所在地就比其他联系因素(如合同订立地等)重要的多,该所在地就是中国内地。在一般或大多数情况下,合同的特征性履行所在地或承担特征性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营业所或住所所在地可视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地方。从本案考察,无法看出香港或其他地区比中国内地明显具有与合同更密切的关系。因此,无疑应确定中国内地的法律是合同的准据法。
第二,合理性。在很多涉外案件中,法官显然不能仅依冲突规范就可以直接获得准据法。如前所述,遇有结果定向性冲突规范、选择性冲突规范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场合,法律往往只界定了一个一般性框架,框架内有若干种解释、选择的可能性,这时法官须结合个案另行探究、评价,才能得出确切的准据法。例如,《法律适用法》第29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该条规定了多个连结点,实践中,法官须根据案件事实在这些连结点所指向的法律中选择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的法律。然而,一旦涉及到评价,法律适用就存在主观、恣意和片面的可能。因此,为了防微杜渐,法官不能光找出一条或几条支持裁决的理由或依据就完事,他应当在考虑所有相关理由之后,再从中为个案拟定一个最合理的解决方案。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涉外民商事案件无论在数量、类型和复杂程度,还是在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选法方法和司法理念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仍存在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涉外审判实践中相当一部分法官的法律适用意识不强,相当比例的案件未说明选法的过程和理由,“恋家情结”过于严重且表现形式多样,同一法条运用不一,类似案件处理差别较大等,且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存在系统性、科学性和先进性不够的问题。[2]P52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这一问题,本文认为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推进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的公布,有关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问题的研究理应成为当下国际私法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研究应遵循《指导意见》的基本精神,深入而系统地揭示涉外民事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律和特殊现象,厘清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找法与法律适用正当化之间的关系,为进一步提高我国涉外审判水平,维护我国司法公正形象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第三,客观性。客观性原则要求法官在程序上应严格保持中立,平等对待各方当事人,不能有所偏袒,裁判结果应符合司法公平正义的要求。涉外案件法律适用的客观性主要关涉法律适用是否能以一种客观的方式解决争议。法律适用之客观性并不否定法官的评价因素,法官的评价并不等同于主观偏见或中立性丧失,评价的登场也并不意味着规范的出局。有些冲突规范包含一些主观性连接点或不确定的连结点,法官适用这些冲突规范时就存在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例如,《法律适用法》第6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外国法律,该国不同区域实施不同法律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区域的法律。”实践中,当法官适用该条作为法律依据时,他就必须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何地的法律是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客观的评价”这一观念,可以容纳法官的创造性活动。但创造不是自由发挥:(1)法官必须超越自己的主观偏好,法律适用释法说理过程应当是非个人化的、不偏不倚的,尽量避免出现所谓的“回家去的趋势”[36]P5;(2)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必须从一般性的角度考虑评价或价值问题,并且法官除考虑当下法律适用的可能结果外,还须考量判决对可能出现的同类案件所产生的影响;[37]P217-218(3)法官必须尊重相关的客观资料,并且在评判资料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时,还须受一系列职业和学科规则(例如合法性原则)的约束;(4)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结果不能抵触行业共同体(或曰解释共同体)的一般性意见。[38]P744
这里应当强调的是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目标的,是法官试图向败诉一方、向有可能接受“意见”的其他人、也向行业共同体证明他这样做是客观、合法的。因此法律适用释法说理不能像文学创作或艺术表演活动那样,可以完全是一种个人化的行为。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具有社会证明的因素,并且可以对其进行客观性检验。换言之,法律适用释法说理过程中即便有法官自己的评价或价值观的介入,也不应是法官个人偏好的介入,这些价值观应该是对社会有某种意义,并为其他人所广泛持有。
第四,融贯性。“融贯(coherent)”是任何说理性行为皆须遵守的一般性准则,其含义简要地讲,就是论证应尽可能以来源更广、数目更多的依据为基础,并且论证过程以及论据之间必须尽可能地排除矛盾,做到协调一致和前后连贯。⑤如前所述,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的多个环节,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如何处理时,必须阐述理由,并论证其行为的正当性,而融贯就是判断法律适用的衡量标准和证成方法。
在涉外案件的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常常需要通过评价来确定到底采用哪种方法或某一连结点来解决法律适用各环节中的争议。例如,在实践中,当出现识别冲突或适用选择性冲突规范时,因为供法官法律选择的方法或连结点不只一个,可能有多个,这样法官采用哪种方法或连结点的理由和根据就是可变的,因而也是可反驳的、可争辩的。由于采用哪种方法或连结点具有这种可反驳性,因此据此展开的法律适用释法说理和推论,也呈现为一种可反驳的论证。[39]P181在涉外案件法律适用过程中,释法说理融贯性的考察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看法律适用中某一争议点的论证是否融贯,不过这个层次的融贯明显是不够的,因为案件可能存在多个争议点;第二个层次是从整体上看各争议点之间的论证是否融贯,也即从案件整体的角度来把握和发现个案的最佳方法或连结点;第三个层次是倘若不同争议点之间的论证存在冲突,无法在整体上得以解决、协调,就必须求诸于法律外的标准,例如效益最大化的功利原则,以此来寻求更高层次的融贯。[40]P483-519就涉外案件法律适用释法说理活动本身来讲,融贯就是各个争议点自身论证及其相互之间能够相互支持,并构成一个连贯的“论证循环”。有学者认为,融贯性是一份细致周详的(full-fledged)释法说理所须具备的关键要素。因而法官在涉外案件释法说理时,皆应像德沃金笔下的海格力斯(Hercules)那样,以一种续写“章回小说(chain novel)”姿态,在法律选择依据和法律选择结论之间架构起条条“法律锁链(chains of law)”。锁链的结实与否,与论证的支持结构密切相关,即结构愈精致,支持愈深且愈广,那么论证就愈融贯。[28]P63
结语
合理性原则要求法律适用释法说理的理由应当符合某种法律之外的一般性原则和标准,例如宗教准则、道德规范、贸易习俗以及政治和经济的考量等等。合理性按其不同的实体取向,又可再分为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这两种合理性在法律适用中的投影,即为法律适用依据上的目的性依据和正当性依据。[35]P29由于合法性定向的法律适用论证有一个局限,即当一些实质性因素应当被考虑进来时,却无法将它们考虑在内,因此法官须审时度势,结合个案中可资利用的目的性依据和正当性依据,为法律适用行为提供合理性支持。鉴于合理性是一种实质性考量,因此探究“什么是合理的”,离不开设问时的语境或背景。如前所述,在遇有结果定向性冲突规范、选择性冲突规范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场合,法律仍然规定了一个一般性框架,法官的评价必须在这个框架内展开。而从另一方面来讲,框内到底包容了何种个案评价标准,其规范意图又作何解,也惟有通过个案事实、生活事实与通行的社会评价,才能予以把握。换言之,规范意图必须经过个案的“洗涤”才能呈现,个案评价惟有通过法范畴的“筛选”方能生效。与此相应,合理化个案法律适用的实质性依据与评价标准,必须接受三个维度的审查:一是“向上”审查,看其是否传达了法律秩序、尤其是冲突法的理念与价值;二是“向下”审查,验证其是否见容于具体规范的规范意图;三是“向外”审查,检视其是否符合国际社会通行的正义观和价值取向。
注释:
在出图时,只需定义出图区域,通过调用编辑完成的图纸模板,就可以生成相应区域的平面图纸。与传统设计方式相比,设计人员不再需要在CAD软件中手动编辑图纸、标注文字和符号,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Smart 3D软件支持多种编辑功能,可以根据需要定制图纸,包括仪表符号的替换、标注的形式、报表类型等内容,使用非常灵活。
①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川民终字第744号民事裁定书。
人工唾液(东菀科达胶黏剂);奥威尔牙膏(香港绿间道);碳酸氢钠、无菌去离子水(连云港云沂化工);绿茶(祁门祁雅茶叶);多乐氟护齿剂(高露洁,德国);齿科酸蚀剂(贺利氏,德国);单面片切砂条(微牙,巴西);低速切割机3180电磨(广州德美);精密电子天平MAX-C系列(苏州佰仕利);电热恒温培养箱HN-258(上海秋佐科学仪器);扫描电镜(SEM)(松下,日本);能谱分析仪S-4800(日立,日本)。
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06民终655号裁定书。
③ 这里应该说明,将法律规避和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在外的理由,因为两者涉及到强行法的范畴,这些领域不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
④ 近些年来,针对实践中如何认识冲突规范问题,国际私法学界围绕着冲突规范是任意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曾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但多数学者认为在法官依职权适用冲突规则的制度下,必须强化法官对冲突规则以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的释明义务。只有依职权适用而非任意性适用冲突规则,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依据国际私法体系所享有的法律适用的权利。相关讨论详见宋晓:《程序法视野中冲突规则的适用模式》,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5期。
⑤ 融贯性是有别于“一致性”(consistence)的。 “一致”是指具体的规范或命题之间“没有矛盾”,而“融贯”是指一组规范和命题在论证结构中,总体上而言是连贯的、“有道理的”,因而融贯性还存在一个程度问题。See Neil MacCormick. Coherence in Legal Justification[A]. Aleksander Peczenik. In Theory of Legal Science[C].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235-236).另外,融贯性也是一个相对选择的概念,它是在构成“冲突”和“竞争”的事物中选择更为合理的东西。由于系统是通过减少冲突来达到一致的,因此判定某种确信是否与某系统相一致,依据的是接受它比接受在此系统基础上任何与它相冲突或相竞争的确信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 肖永平.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A].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指导与研究[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2] 徐锦堂.当事人合意选法实证研究———以我国涉外审判实践为中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梁西,宋连斌. 法学教育方法论[M]. 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4] Savigny. A Treatise on the Conflict of Laws, trans. By William Guthrie, 1849.
[5] [美] 史蒂文·J·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M].张志铭、解兴权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6] [美] 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M].顾培东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
[7] Fred Schauer, Formalism, 97 Yale L. J.1988.
[8] H.Yntema,The Hornbook Method and the Conflict of Law,37,Yale L.J.,1928.
[9] J.Frank. Are Judges Human? 80 Pa. L.Rev.,1931-1932.
[10] [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1] 李力,韩德明.解释论、语用学和法律事实的合理性标准[J].法学研究,2002(5).
[12] 徐冬根.国际私法趋势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3] 肖永平.肖永平论冲突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4] 梁迎修.法官自由裁量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15] 韩德培.国际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6] 肖永平.肖永平论冲突法[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17] 陈卫佐.法律适用法的十大亮点[N].法制日报,2010-11-2.
[18] 胡仕浩,刘树德.新时代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制度构建与规范诠释(上)——《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2018(16).
[19] 马志强.国际私法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0] 董作春.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质初探[J].学术论坛,2011(2).
[21] 丁伟.冲突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2] 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3] 赵一民.国际私法案例教程[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
[24] 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5] 杜新丽.国际私法教学案例[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6] Aarnio, MacCormick.Legal Reasoning,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92.
[27] Julius Stone. Legal System and Lawyer’s Reason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68.
[28] A. M. Honore. Legal Reasoning in Rome and Today, Cambridge Law Review, 1973.
[29] 戴津伟.法律中的论题及论题学思维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30] 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司法论证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1] Stephen Toulmin. The Use of Argument[A]. Eveline T. Feteris. Fundamenta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 A Survey of Theories on the Justification of Judicial Decision[C].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32] 翁杰.论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模式的双重理性架构[J].政法论丛,2016(3).
[33] [德] 亚图·考夫曼.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吴从周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
[34] [德] 哈斯默尔.法律体系与法典:法律对法官的约束[A].[德] 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C].郑永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35] P.S.Atiyah and Robert s. Summers, 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al Reasoning, Legal Theory, and Legal Institution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87.
[36] 何其生,许威.浅析我国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回家去的趋势”[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37] Ota Weinberger. Objectivity and Rationality in Lawyer’s Reasoning[A] . Aleksander Peczenik. Theory of Legal Science[C].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38] Owen M. Fiss. Objectivity and Interpretation.Stanford Law Review, 1982.
[39] Aleksander Peczenik. Jump and Logic in the Law: What Can One Expect from Logical Mode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A]. Henry Prakken. Giovanni Sartor. Logical Models of Legal Argumentation[C].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96.
[40] Luc J. Wintgens . Coherence of the Law[M]. Archiv fur Rechts und Sozial philosophie V.79, 1993.
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 Application in Foreign -related Civil Cases
Weng Ji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Xi'an 710063)
【Abstract 】In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related civil law, the problem of judges not speaking of reason or misinterpretation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foreign-related law, the reason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w by judge mainly lies in the fact that when there is a conflict of identification or applying selective conflict norms, result selective conflict norms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closest connection to determine the applicable law, judges enjoy certain discre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 in foreign-related civil cases is not only a process of "find law", but also a process of justification.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the judge has the obligation to prove the legitimacy of his choice of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reign-related civil law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form and substance, and judges should abide by the four principles of legality, rationality, objectivity and coherence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reason.
【Key words 】foreign-related civil cases; application of law; interpretation of law; reason and circumstance; approach and principle
【中图分类号】 DF974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涉外民事法律选择模式研究——基于法律方法论的视角”( 14YJA820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翁 杰(1966-),男,浙江慈溪人,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法基础理论、国际商事仲裁。
【文章编号】 1002— 6274( 2019) 03— 030— 12
(责任编辑:黄春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