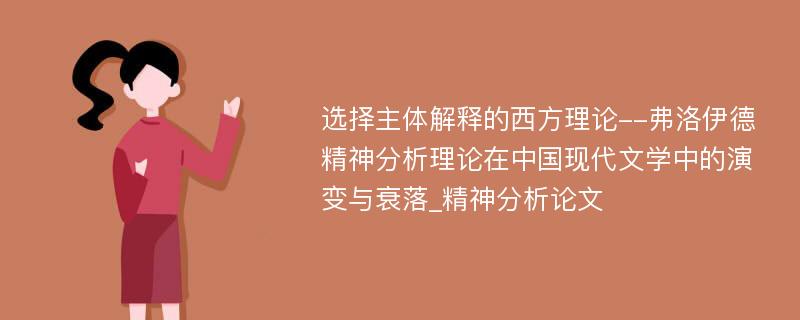
一种经由选择主体阐释的西方学说——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演化和消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说论文,中国论文,主体论文,精神分析论文,弗罗依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中国新文学作家对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选择和汲纳,其实质是对西方学说一次充满主观色彩的阐释。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目的引发了这一选择冲动,并经由创造性地运用和演化,使这一意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自然本能和无意识心理过程的西方学说,被诠释为一种充满理性精神的社会学说而最终同新文学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主题达成了冥契。
20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东西文化汇流中揭开自己辉煌的一页的。在这一新思潮呈百川汇流之势的时期中,一些新文学作家曾一度把眼光投注于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美学中影响极为深广的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并汲纳之,为其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所用。问题是:这种意在揭示人的非理性自然本能和无意识心理过程的精神分析学说,又是怎样同充满了理性精神的新文学反封建思想启蒙主题达成冥契的呢?对这一问题的思索,并结合精神分析学说在初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演化、消长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其走向进行多侧面、全方位的了解,更有助于我们去发现在两种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客体互择时,一种带有社会文化心理特征的内在规律。
一
首先,有必要对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出一些诠释。就总体而言,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可归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潮一流。人本主义作为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经过了它的古典主义时期,至19世纪中叶,已发生某些质的变化,其思潮流派虽同古典理性主义思潮一样,强调人的核心地位,但在其自然观上,把人抽象为生物学上的自然人,把人的各种非理性的生理、心理功能视为人的本质,并使其普遍化,上升到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衍变基础上的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学说。这一学说认为:人首先是一种生命存在,因而人的本质就是与存在原则相一致的生命本能。弗罗依德把这种生命本能解释为归属于无意识心理层次的性欲。“人类最深刻的本质在于初级的,自发的本能动力,这些动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同样的,它指向一定先天需要的满足。”①由于受现实原则(指社会意识,如伦理、道德、法律、习俗等)的制约,得不到满足的欲望被压抑在无意识领域里。如果这种被压抑的“力必多”(Libido,指性本能)得不到正常的宣泄或附加到别的活动中去,实行“强而有力的转移”,人的精神和生命系统就会遭到破坏。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言行被认为是无意识本能渴望得到满足的变相显现,梦即是一种在意识(指社会意识)监视松驰的情况下“实现了的欲望”。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一个很显著的贡献在于:它系统、完整地提出了“无意识”理论,并以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证了人的自然情欲“指向满足”的愿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
但这一强调人的自然本质的西方学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经由选择主体的阐释,被诠解为一种社会学说,并大量地应用于文学创作,成了一种弘扬人性并藉以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的武器。我们通过对一些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剖析,不难窥见这种主体的阐释过程。
一是这类作品往往用炽热的情感,大胆地袒露人的非理性情欲世界,活生生地写出人被压抑的自然本性,作为一种对现存意识的反叛。
在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中,主人公“我”为一个卖甜食的姑娘所迷恋。于是他的内心世界便交织着一场情欲和理性的酷烈搏斗。他“感应着一场无可名状的焦燥和不安”,一次次费尽心机寻找借口窥视姑娘的容颜。回到家就象走进一座森严的教堂,妻子就象“一幅中世纪的圣画”,处处使他感到一种社会理性的压抑,而那姑娘就象动人的“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霭”。他拥抱着妻子,就象“抱着圣母的塑象驰骋着爱欲的梦想”。这种近乎无奈的性格二重分裂,无不显示着无意识本能同意识中的道德观念的剧烈冲撞和抵牾。一方面是出自本能的渴求,另一方面是皈依道德的自责。灵与肉在欲念和理智的双重鞭打下痛苦不堪。“我”终于熬不住这双重的挤压,最终只能走向自毁肉体,寻求内心永恒平静的末路。在这里,作者借助自己的笔,敲开了一把传统道德的锈蚀的锁,向人们敞开了人类自我的另一个隐秘仓库——自然人性的我。而在郭沫若的另一篇小说《叶罗提之墓》中,主人公叶罗提在少年时代便对堂嫂产生的一种恋情,总是云缠雾绕般地控制着他,以致于他觉得“世间上的一切都好象逼迫着我,我自己也逼迫着我,我好象遭了饥荒一样”。和《喀尔美萝姑娘》不同的是,叶罗提终于在精神上获得了嫂嫂的恋情,而把肉体的情欲深深地压抑下去。当嫂嫂早夭时,本能欲望在精神上的实现亦随之溃散,最终是精神连同肉体的一起被埋葬。在这里,叶罗提之墓似乎是一个象征:它埋葬了一个尚不为人知的被压抑着的自然人性。
同样是大胆的暴露和渲示,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则更充满着情欲的震颤和自然人性被扭曲的苦闷:“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②,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主人公那压抑的本能欲求就象一个灰色的幽灵,在现实压抑的泥沼里徘徊、游荡。他那一系列孤苦、超常、变态的性心理过程,实际上是在非正常的封建原则钳制下人性的一种常态。
二是有意识地运用弗罗依德的学说来解释作品人物的行为动机,以闪烁着新人文精神之光的“自然人”来对抗封建原则的“社会人”;或是沿用这一学说的理论,揭示一类道德化人物的潜意识心理,以显示出道学家的虚伪。
鲁迅的历史小说《补天》属于前者。在这幅以重彩浓墨的浪漫色调绘制的神话图卷里,女娲一觉醒来,感到一种无端的烦恼和无聊。粉红色的天穹和嫩绿色的大地激发了女娲春意难遣的苦闷,她无聊地喟叹,并“猛然站起来了,擎上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膀,向天打了一个欠伸。”这些作者有意设计的系列动作,都暗示着女娲被压抑的本能欲望急待排遣的心理。最终,她找到了宣泄被压抑的本能的途径,即造人补天。女娲在这充满欢愉的创造中,使被压抑的本能冲动得到了“强而有力的转移”。这种以“性的发动”来解释人的行为动机,显然是受了弗罗依德的关于被压抑的性本能是创造人及一切精神现象的内驱力的论述的影响,并以此来对抗封建学说的“道的发动”和“道”化的人物。
鲁迅的《肥皂》和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属于后者。《肥皂》中的主人公,以道学家面目出现的四铭,他那一句不绝于口的“咯吱咯吱洗一洗”,实际上正是他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外烁。我们透过这一道德化的性格表象,窥见的恰是一种与之相反的逆道德的无意识本能。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则用幽默调侃的笔调,描绘出这位大圣人的情欲世界。孟夫子在想作圣贤的意识和情欲渴求满足的无意识的矛盾博斗中,不胜重负地叹息:“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三是在创作手法上,往往借助对梦境的描绘,来展示企图实现的人的无意识情欲世界,其内容主旨同以上两点殊途同归。
弗罗依德认为:梦并不是无意义的,荒诞的。梦是一种有充分价值的精神现象。它表示着一种未能满足的欲望,在意识监视松驰的状态下,获得的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他在《释梦》一书中说:“我们已经看到梦总是把欲望作为已经得到满足来加以表现的。……即在梦中,欲望的满足是不戴任何假面具的和可以认识的。”③
郭沫若的《喀尔美萝姑娘》中的主人公,被对卖糖食姑娘的情欲折磨得憔悴不堪。然而这一切都无意中在一个凄清的梦中得到了实现。日思夜想的姑娘向他走来,热烈地向他倾诉衷肠,并悲壮地为之殉情。于是,在幻觉中,被压抑的情欲得到了释放,近乎破碎的心得到了抚慰。梦使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本能得到了变相的实现,使在清醒时缺损的情感在幻境中获得了补偿。同样是作梦,郭沫若的《残春》则更体现了弗罗依德所揭示的那种奇妙的无意识心理过程。有妇之夫爱牟在探询友人的病情时邂逅美丽的看护妇,由此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这种情感远不如《喀尔美萝姑娘》中的主人公那样强烈、执着,一切都是淡淡的,一切都在隐隐中。然而在一个梦中,这一切突然象被放大了似的清晰起来,甚至对偕同探询友病的白羊君的一种无意识心理,也突然象得到提示似的呈现出来,变成他和姑娘交流情感的障碍。这一切无意识的心像流动,显然都是在日间思考中被意识压抑,控制着的本能活动,一旦入梦,意识的监视松驰了,便一泄无余地释放出来。
总之,借梦境宣泄一种对传统封建伪道德的厌弃情绪,从而完成这样一个反封建的结论:梦比现实生活更清醒,更合乎道德理性秩序,因而更能体现人性的真实的自我。
四是塑造一系列性格、心理变态的人物,使人见出封建原则的压抑对自然人性的破坏。
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中主人公那焦躁、敏感、自卑、自伤、自悼,以及各种卑琐的窥视行为,莫不显示出这种遭受现实原则残损的心理变态。至于《喀尔美萝姑娘》中主人公偷揭所爱姑娘写的字条,则类同于当代性心理学所描述的一种性变态行为——“恋物癖”。
这种带着强烈的主体阐释倾向的汲纳,不仅表现在他们的创作中,亦渗透在他们的一些言论中。郭沫若在他的文论《批评与梦》中曾对罗依德的理论作了剖析,并指出:“我那篇《残春》的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并且还在潜意识的一种流动……若是对于精神分析学或者梦的心理稍有研究的人看来,他必定另外可以看出一种作意来,另外可以说出一番意见。”④在另一篇运用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评论《西厢记》艺术及其作者性格的文章里,他则阐释为:“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职司礼教者固当因善利导,以扶助其正当的发展,不能多方钳制,一味压抑,使之变性而至于病。”⑤他盛赞以自然人性冲破封建压抑的《西厢记》“是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⑥。鲁迅则在他的《故事新编·序言》中明确地表示:创作《补天》是“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此外,他在为自己的译本《苦闷的象征》所加的引言中称赞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作者据伯格森一流的哲学,以进行不息的生命力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又从弗罗特一流的科学,寻找生命力的根底来,即用以解释文艺,——尤其是文学……弗罗特归生命力的根底于性欲,作者则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他又在其杂文《碰壁之余》⑦里认为:“偏执的弗罗特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都被撕碎了。”这样,一种意在揭示人的非理性的自然本能的西方学说,经由选择主体有目的的阐释,已被诠释为一种充满了理性精神的社会学思想,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被用作成一种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的有力武器。
二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新文学作家们在百川汇流的新思潮中选择了这一学说,并加以创造性运用和演化;精神分析学说同新文学时期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主题达成冥契的理论依据又在那里?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对两种异质文化互相交融、汇流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探寻。本文认为:可以从选择主体和被选择客体各自先在的内容结构中寻找答案。
一是被选择客体提供了自己的可选择性。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就其本质而言,是建立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一种“关于人的精神生活(人格、个性)的本质、结构和作用的理论,他最突出地强调了人的本能作用”⑧,并且弗罗依德本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科学家和医生,而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和思辨哲学家。故而一些评论家往往认为这一学说有着“抽掉了人与社会的重要关联的致命弱点”⑨,强调的只是怪诞、恐怖、神经质的心理变态和无意识幻想。其实这只是不完整地描述了这一学说的部分内涵,而远非全部,并又恰恰抛弃了作为这一学说的重要的外延部分——同社会的连结点。因为,尽管弗罗依德对人的被压抑之本能进行了深入、祥尽的研究,而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抑”的内容很少说明,但它既然以“现实原则的压抑”为依据构作其理论内容,就不能不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种“现实压抑”的具体内容,并发生联想性思考。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分析了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之后认为:现实原则的压抑可分为合理性压抑和非合理性压抑。他认为作为一般文明要求的现实原则的根据是“缺乏”这一基本事实。“由于经济上的贫困和克服这种贫困所需的劳动,要造就文化就必须对本能欲求作一定限度的限制、克制或延迟。这种基本压抑在一定意义上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物质资料(不管仍是缺乏的,还是已经丰富了的)分配方式与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组织方式总是强加于人的,它们代表了特定文明阶段的统治利益……它们对人的爱欲所强行施加的压抑是在一般文明要求的基本压抑之外的,为维持特定统治形式所必需的额外压抑”⑩。这是一种非合理性的压抑,这种压抑不消除,人的生命本能得不到解放,就谈不上对自己本质的真正占有。由于弗罗依德学说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石上:即认为人之本能和文明是对立的,这种本能来自人体的内部刺激,有其生物学上的必然性,而代表群体原则的社会制度总是对人的行为作出规范和制约,因此人的本能欲望本身就具有反社会的性质。由于这一性质的存在,使得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不可避免地同社会学纠缠在了一起。30年代的鲁迅对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重新认识时说:“但弗罗依德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11)这虽然是意在批评弗罗依德的学说离开社会内容而谈梦,其实,这恰恰在无意中泄露了选择主体的一种思想方法:一提本能之被压抑,就必须同社会内容相连接。这种经由主体联想桥梁的连接,一方面固然反映着选择主体积极的阐释过程,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由于这种易于联想性或连接的必然性的存在,使得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新文学时期的被选择成为一种可能。
二是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的目的引发了这一选择冲动。
这一充满主体精神的原发性冲动,在两种异质文化互构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新文学作家们生活在一个盘根错节的传统封建社会中。这一社会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以儒学为其正统统治思想。这种学说的负效应,在于巩固和协调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和内部人际关系。从孔子的“修身养心,克已复礼”到《诗大序》的“发于情,止乎礼义”,都主张克制人欲而去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这种以礼制欲的观念发展到宋明理学,进一步演化为天理和人欲的截然对立说。朱熹在《朱子语类·十三》中称:“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种天理和人欲两不相容的说法,在形式上颇似弗罗依德的本能和文明对立说。然而,后者强调的是人的本能客观存在,它的“指向满足”是事物发展的内驱力;前者强调的则是天理对人欲的压制,以天理取消人欲。这是两个在形式上相同却在内容上双向逆反的命题。“存天理,灭人欲”说,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为维持特定统治形式所必需的压抑”,其实质无非是力图把特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行为规范抽象为某种普遍的必然的“理性”或“天理”,并通过这种“理性”或“天理”对自然人性的压抑,来实施和加强社会对个人的控制。鲁迅以“吃人”对这种压抑的本质作了有力和形象的概括。因此,要建立一种更符合人性的文明,就必须摧毁极端束缚和压制自然人性乃至人的正当情欲的全部封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原先自立的,独立的精神过程已被主体在国家中的功能即公共生存同化了。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社会总失调的医治”。伸张人的生命原欲,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其结果是必然会导出反封建社会的结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新文学作家们就故意大胆地袒露被封建礼教压抑在人性深层的情欲世界,辉煌地表现自然人性的魅力,显示出一种坚执、顽强的抗争。自然人性的鲜亮色彩一旦呈露在人们面前,即同灰黯的封建道德形成强烈的对比。此外,用犀利的笔触揭示伪善道德和矫虚文明掩饰下的情欲世界,则能使“道学家感到作伪的困难”,使其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所以,意在揭示人的无意识本能,强调人的情欲活动的精神分析学说正好被新文学作家们汲纳过来,并“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以完成他们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的先在目的。
综合以上两点:一种理论之被接纳和运用,往往是主客体互构的结果。一是这种理论本身存在着可供选择性,二是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目的在汲纳过程中的先导作用。并且,这种理论在被汲纳过程中经由主体阐释,往往会生发出一种同其原始形态不尽相同的意义来,这或许就是使精神分析学说最终同新文学反封建思想启蒙的主题达成冥契的主要原因。
三
在主体的阐释过程中,其先在目的往往带有某种实用性质的偏向性,这种目的偏向性牵引着被选择理论朝着主体自我的轴心扭转并发展,一旦主体自我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及原生的思想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带有实用性质的目的偏向性亦随之转向。我们可以从一些新文学作家对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最终抛弃,来证实这种主体阐释过程中目的偏向性的存在。
当我们变换一个角度——从文学思潮流变的角度去追踪这一学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消长,可以发现,随着“五四”高潮的过去和革命文学口号的被提出,精神分析学说连同其他一些西方人本主义学说在中国文坛突然地沉寂了下去。沉寂得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还来不及对这一学说本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意义作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尽管它仍在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顽强地延伸着生命力,但它毕竟是被后起的革命文学冲淡了、稀释了,甚至遭到了贬斥和否定。我们可以从新文学初期的代表人物鲁迅的思想发展脉络中,窥见这种变化的轨迹。
早年曾对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进行热情的肯定,并把这种学说运用于创作实践的鲁迅,当他接受了阶级学说的观点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而对弗罗依德学说持批判态度。他在1933年元旦所写的《听梦说》里,批评了弗罗依德及其拥护者的阶级立场:“不过,弗罗依德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这里表明,鲁迅已开始用阶级分析的眼光评叛弗洛依德的学说,完全把其归之于有闲阶级的奢侈品。这种带有明显的阶级功利性的眼光,使他轻易地推翻了他早期所希冀的“即其力的突进和跳跃”,用生命原欲之烛光去照亮国民精神的初衷。此外,对深受弗罗依德理论影响的法国作家法朗士的长篇小说《泰绮思》,鲁迅在他晚期杂文《“京派”和“梅派”》里,也一反曾对之有过的热情赞赏:“《泰绮思》的构思,很多是应用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12)
其实,这种对精神分析学说由赞赏、倡扬转而批评或否定的逆转,说到底是因为选择主体在对这一学说阐释过程中,其目的偏向性发生了转移。
众所周知,新文学初期思想启蒙的内涵是“人的发现”,以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为其标帜。作为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前脉——西方早期人本主义思潮,宣扬以人为出发点和依归,主张个性解放、人格独立,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等人性、人道主义思想,曾在文化思想上对封建体系具有极大的摧毁力。法国18世纪那场震动全欧的启蒙运动,就是在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构造了一整套反封建的社会政治学说,诸如“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论。卢梭的“回归自然”说是典型的代表,它强调善良的自然本性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相对立,得出了必须推翻束缚和压抑自然人性的全部封建上层建筑的结论。人本主义思潮在进入20世纪时,虽然起了某些质的变化,但它依然带有这一思潮的基本质素。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某些成果,还可被看作是对早期人本主义思想的深化或补充,比如弗罗依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无意识”理论,就为早期人本主义的自然人性论进行了科学上的确证。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主旨既然在于进行反封建思想启蒙,新文学作家们作为选择主体,必然会把注意力投向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并通过自己的解释,使之适合于自己的社会政治目的。他们“用人性当作钥匙,相信能用它来打开道德上、政治上、历史上的一切门户”。(13)这种选择是由于选择主体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是由选择主体预先设计的目的决定的。只要目的明确,一切有用的皆可取来,那怕是对一种理论的误读。
这种在主体阐释过程中带有实用精神的目的偏向性,也往往决定了被选择理论的暂时性。当“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和实际中对个体的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1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地位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在学术界的传入和被广泛接受,使得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思想结构发生了巨变。社会历史环境和思想结构的变化,导致了选择主体的目的偏向性的移位,形成了与被选择客体之间的视觉逆差。故而虽是对同一种精神分析学说进行审视,得出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印象;或者说,是对同一种理论阐释出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因而,弗罗依德的理论在西方“人们几乎可以说,在我们时代,差不多没有一种美学理论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弗罗依德理论的影响”(15),甚至可以说,在西方,弗罗依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产生,引起了整整一场文学的革新。但是在东方的中国,其引发的热潮是十分短暂的。尽管在20世纪的80年代,人们又一次把热烈的目光倾注于这一学说,但很难说其中不带有一种实用性质的先在目的。关键原因就在于:这一理论,并非是出自选择主体自身的社会的内部机制(经济、文化)发展到相应成熟阶段的自然产物,只不过是一种拿来为我所用,并经由选择主体原生的思想结构和先在目的阐释了的西方学说,人们从中看出的更多的是选择主体的“自我”。
注释:
①③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26页。
②指《圣经》故事中的夏娃。
④载《〈文艺论集〉汇校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2页。
⑤⑥《〈西厢〉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文艺论集〉汇校本》,第239页。
⑦载《鲁迅全集》第3卷,第116页。
⑧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主潮》,载《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⑨《走向世界文学——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⑩参见《爱欲与文明——对弗罗依德思想的哲学探讨》[美]赫伯特·马尔库塞,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11)转引自《〈故事新编〉的论辩和研究》,李桑牧,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36页。
(12)《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304页。
(13)普列汉诺夫:《唯物论史论丛》,第24页。
(14)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版,第32页。
(15)参见《文明与它的不满》,韦兹编《美学问题》,第761页-763页。
标签:精神分析论文; 无意识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读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