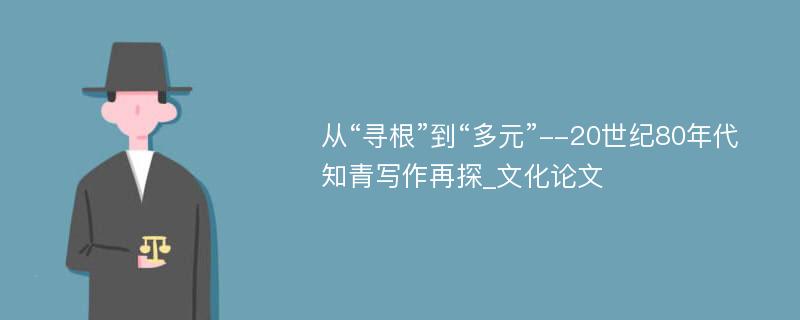
从“寻根”走向“多元”——20世纪80年代知青写作回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青论文,走向论文,年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6)02-0001-05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途程中,像“寻根文学”这样,由作家们执掌理论批评职事,而又以其独具魅力的创作实绩,在小说观念和形态方面对传统意义上的小说都进行了一次真正的革新与创造的,还没有其他文学思潮可与之相比。知青小说家是寻根文学的主力。在1983至1984年间,韩少功、李陀、郑义、阿城、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就围绕着文学寻根问题,交换过意见。1984年11月,杭州召开“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对话会,他们在会上又“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文化,尤其是审美文化的问题”,后来陆续成文,形成为自觉而明确的寻根意识。韩少功在会后发表的《文学的根》,以及郑万隆的《我的根》、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郑义的《跨越文化断裂带》等文章都对寻根文学潮流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表述上互有差异的文章,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文化岩层’,才能与‘世界文学’对话。”[1]
“寻根文学”思潮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评论界对此有过多种解释,每一种解释均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归结起来,“寻根文学”的潮涌一是导因于部分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换和文化民族主义情结,他们在当时汹涌澎湃的文化热潮中,以一种自觉的意识,明确打出文化寻根的旗帜,力图把传统文化从历史长河的积淀中发掘出来;二是导因于外国文学的刺激,特别是受到了 1982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拉美作家的启发和影响。国内1984年翻译出版了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这篇小说把野蛮的现实和印第安人的神话传说、现代物质文明的冲击和原始的巫术文化结合起来,再现了拉丁美洲百多年来被现代文明发展排斥在外的、孤独的历史悲剧。这种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对原始玛雅文化的探寻获得的巨大成功,强烈地刺激着我国的一批作家,他们企图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重建”中国文学和文化,并以此创造“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所以蔡翔后来回忆说:“《百年孤独》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足本土文化。”[2]
“文化”是寻根文学理论和创作中的核心观念。其主旨表现为从僻远、原始、蛮荒的地域和生活形态里,从不被封建主流体制规范的老庄哲学、禅宗哲学里,竭力发掘本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东西,以探求民族文化的“根”。正如李杭育所说的:“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之精华,更多地保留在中原规范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大多枯死了。 ‘五四’以来我们不断地在清除着这些枯根,决不让它复活。规范之外的,才是我们需要的‘根’,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土。”[3]“寻根文学”倡导者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形态以及它们依然作为现实关系的维系力状况,作出真实的确认,建立起民族文化心理上的自信意识,从而剔除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寻找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
知青小说家既承担了寻根文学理论批评的先驱角色,也是寻根小说创作的主要作家。以季红真的说法:“及至1984年,人们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的人文地理版图,几乎被作家们以各自的风格瓜分了。”[4]韩少功到湘西古老的习俗中去寻找他认为已经流失了的楚文化,李杭育努力开掘着他所认为的规范之外的、正宗的吴越文化,贾平凹立足于对商洛文化的审视,郑义固守着晋文化的营盘,王安忆眷恋着古风犹存的黄淮村庄,郑万隆漫话着东北山林中的“异乡异闻”,乌热尔图留恋于大兴安岭的原始风光,阿城盘桓于云南丛林,莫言钟情于齐鲁文化……一时间,知青小说家以各自的艺术风格,经营着各自熟悉的地域文化系列,寻根小说蔚然大观。
寻根文学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寻根文学几乎就等同于寻根小说。而在寻根小说中,韩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忆的《小鲍庄》是最有代表性的。《爸爸爸》以一种冷峻的笔调,叙述了鸡头寨一个畸形人丙崽,以及丙崽周围的各种人的生存状态。湘山鄂水,祭祀打冤,迷信掌故,服饰食品,乡规土语,构成了一幅民俗图,人性在这种生存状态和文化氛围里,以特殊的形态表现出来,卡夫卡式的变形与荒诞令人心悸。丙崽体残智呆、言行荒唐,他生来只会嘟哝两句忏语般的口头禅“爸爸爸”和“×妈妈”。他的出生本来就是一个误会,而社会居然宽宏地容留了他,养育了他,让他毫无价值地生活着。不仅如此,他竟然还得到了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被尊为“丙大爷”,成为指点迷津的神灵,而且在部落遭受生死劫难后,也独有丙崽不死,幽灵般喊着“爸爸爸爸”,继续丑陋的生存。人们将丙崽看作是远古以来我们这个民族愚昧、蛮荒、冥顽不化又充满神秘色彩的“集体无意识”和“生命自在体”的象征。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民族传统中积存得很深的小农社会文化遗存物的蛮性与蠢行的理性批判,进而引起人们对这种文化劣根、文化老根的关注和疗救。《小鲍庄》以多头交叉的叙述视角,通过对淮北一个小村庄几户人家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的立体描绘,尤其是捞渣这一人物具有象征意义的死,剖析了我们民族世代相传的以“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仁义之乡”的小鲍庄,因祖先治水无方,害死了许多百姓,于是命运老和他们作对,使他们的后代一代又一代地在沉重凝滞的不幸中生存。直到捞渣为救鲍五爷舍身而死,在命运神的祭坛上献上了一份礼品,小鲍庄人才渐渐摆脱了困境。捞渣的仁义之举,拯救了小鲍庄,因而生前的捞查和死后的捞渣是不同的,后者被偶像化了。当小鲍庄的大人们为这个孩子送葬的时候,他们褒扬的实质上不是捞渣而是他生前具有的和死后外加的传统道德素质。他们按照自己的道德理想塑造捞渣,又将依照这个偶像塑造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捞渣这个形象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象征着传统是怎样延续下来的,又将怎样延续下去,也体现了作者“仍保留着一切传统民俗中美好的东西”的愿望。《小鲍庄》被认为是寻根文学中的优秀作品,“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对儒家文化的经典叙述”[5]。
考察寻根作家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人们不难发现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寻根文学创作与其理论的悖论现象,即寻根文学作品所导致的实际文化价值判断大多与其理论旨趣相悖。寻根文学将其“文化”描述了出来,却并不能导致对这种文化的充分价值肯定。在寻根文学中它寻到的文化仍然不能不是“失落的文化”,仍然不能或没有理由改变其“失落”的历史命运。造成这种悖论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寻根文学”在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即它的文化价值立场实际上是犹豫和暧昧的,它并未坚定而明晰地处理好所谓“失落的文化”与当代文化、文明社会的关系。它只是单向度地企图对“失落的文化”予以理论上的价值肯定,而回避了或没有回答“当代文化、文明社会能否成为文学之根”这一必然的关联问题 [6]。实际上,在“寻根文学”理论提出的当时,就有人指出了它的缺陷。评论家周政保说:“无疑,文学的‘根’,应该深植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但作为当代小说,只能以当代生活作为自己的土壤,因为这土壤同样体现着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形态(也包括了悠久的传统)……我们应该澄清这样一种片面的创作意识,即认为描写现代文明比较发达的现实生活不足以表现我们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文化传统色彩,而只有描写了那种古老的、相对恒稳的、甚至是原始落后的社会生活,才有可能呈现某些富有民族性的文化传统特点。”[7]陈辽先生也说:“文化的‘根’是深深地植在人类的社会实践、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这块土壤里的;民族文化的根是深深地植在该民族的社会实践、社会活动、社会生活的土壤里的。既然如此,仅仅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文学的根,怎能不植在这块土壤里,而植在只是外延和内涵远比文学大的文化之中呢?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一棵树的干和枝,本来都植根于土壤里,却偏说‘枝’要植根于‘干’中一样不合理。”[8]客观地说,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寻根文学”是相当混沌、充满了矛盾和张力的,就是“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其意识也不是十分明晰,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一些概念在当时就比较朦胧、暧昧,后来才沉淀和变得明晰起来。
二是“寻根文学”的创作要比其理论(文化论)高明得多,也丰富得多。在实际创作中,“寻根”作家以清醒的理性精神来审视民族的文化传统,使新时期文学对人的认识进入到文化心理层次上。不否认有的作品在过分追求地域文化特色中,对封闭的生活形态作了孤立的反映,缺少一种现代批判意识,但这毕竟不是寻根文学的主流。其绝大部分作品并没有割断与现实社会和时代精神的联系,作家们突破或超越了地域文化形态的封闭性,更注重于展示不同质的文化的开放、碰撞和融会,剔除其腐朽的劣根,阐扬传统文化的精华,从而使我们古老的民族卸却沉重的精神负荷,抖落身上的灰尘,以清新雄健、底蕴深厚的身姿,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在审美意识上,寻根作家对民族艺术精神的认同,对传统的审美经验的重视,复活了我们民族历史的审美意识,给新时期文学灌注进我们民族特有的美学气韵和情致,也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艺术变革,使之在寻求与当代世界审美意识相一致的美学情致和审美经验中,以鲜明的民族色彩,独特的民族气质,对世界的文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9]。
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艰难、曲折的发展,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青写作则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作品关注点由“文化寻根”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人生。在这一时期和以后的“当代文学”创作中,知青小说家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创作了有广泛影响的作品。
1985年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有人甚至认为,1985年才算一个文学时期的开始。人们之特别看好1985年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不仅因为这一年知青作家们相继发表了提出“寻根文学”主张的理论文章,发表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小鲍庄》、《老井》和《爸爸爸》,一些后来被称为“先锋派”的小说家如马原、扎西达娃、莫言、残雪等也恰恰在这一年崭露头角;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的创作态势与理论动向形成了富有生长性与推动力的文学氛围,从文学观念到研究方法都出现了全方位的跃动。寻根小说的倡导者意在为文学建构一个文化的背景,使文学创作获得文化的深度,但先锋小说家对寻根文学所推崇的“文化叙事”似乎不抱有兴趣和热情,他们宁愿转向更为个人化的叙事;而不论文化叙事还是个人叙事,明显地都是对宏大叙事的颠覆或消解。作家叙事立场、叙事策略的转变,于是形成了80年代中后期多元并存的文学景观。如果说,80年代初知青小说家是知青文学创作的主力,那么在80年代中后期多元化文学格局中,他们仍然是异常活跃的因素,我们同样会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且不说寻根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几乎全是知青作家,就是在先锋写作中,1985、 1986年异军突起式人物也是有过知青经历的马原,马原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后来,当先锋小说遇到读者狙击,新写实小说应运而生时,知青小说家池莉又成为新写实小说代表性作家之一。1987年,她发表的《烦恼人生》,通过对主人公印家厚一天的生活流程的描述,将步入中年的知青生活的困顿和情感的麻木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被人认为它展现了知青文学的一种流向。
在新的文学潮流面前,面对新的挑战,活跃于80年代初期的一些知青作家也都作出了选择,调整了自己的叙事策略,知青写作很快由分化而汇入到多元化文学发展潮流之中。其主要表现在:
1.从“过去”回到“现实”,转而用理性的精神审视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问题。知青作家们不再是“追忆”、“远望”,不再是理想情怀,其创作风格逐渐转向现实主义。梁晓声后来写出《雪城》、《年轮》等作品,走的就是这一条道路。《雪城》写知青群体返城后寻找生存位置的艰难过程,这是一个求生的过程,也是价值体系崩溃和重建的过程。上集描写东北某城市的20万知青在1979年底集体返城,长期待业,在饥饿线上挣扎。下集写知青返城七年后各自不同的命运归宿,几乎没有一个返城知青能够逃避面临的新的人生困境。《年轮》是《雪城》的姊妹篇。这部长篇时间跨度大,写了几个知青从60年代初到80年代20来年的人生变迁。梁晓声说:“《年轮》于我,初衷并非是重操什么知青题材‘旧业’,而是写一些曾当过知青的城市中年人今天的生活形态。”[10]关注知青命运,描写他们返城后的当下生活形态,这是非常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一个主题。因而在《雪城》和《年轮》中,读者最感动的地方,不再像读《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样,是洋溢于文本中的一种浪漫的精神气质,而是隐含于写实性故事中的人文关怀。梁晓声的作品,记录了整整一代知青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信仰、理想乃至失落,代表了知青文学的最高水平。后来,梁晓声从他曾经有过辉煌成就的知青文学领域转移,创作了一系列经济题材小说,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转型期,物质财富追求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反差现象。这类小说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揭露以金钱为唯一目的,道德沦丧,精神堕落,以致走向毁灭的过程。长篇小说《泯灭》、《恐惧》便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中篇小说《又是中秋》、《表弟》、《顺嫂》、《冉之父》、《钳工王》、《荒弃的家园》、《黑纽扣》等,则把焦点对准转型期中的弱者命运,着眼于社会的中下层人民,为他们的宝贵品格讴歌,为他们的坎坷遭遇不平。它们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博大的人文关怀,也体现了作者深刻的洞察力和认识力。在当今多元化文学发展潮流中,梁晓声真正是一位具有个体精神特征的作家。
2.高举信仰之旗,用哲学思索或宗教精神来抗拒世俗的平庸和堕落。史铁生从个人生命体验出发步入宗教疆域,张承志公开宣称自己皈依伊斯兰教即属此例。史铁生是知青作家群中的异数,他在农村插队时得病导致双腿瘫痪,当时还不满20岁。从自身的残疾他“明白了人(类)命定的局限和终极的虚无,因而要把生的价值从追求终极、完美之类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上移开,移到人生的过程,给‘活着’注入一种意义”[11]。他以基督教牧师的生活为题材,塑造的是不懈追求的形象。《命若琴弦》中的说唱艺人老瞎子,50年来,为了重见光明不停地奔波,在他70岁时终于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当他打开琴槽取出师傅留给他的药方满怀希望到药铺取药时,人们告诉他那张药方是一张无字的白纸。他痛不欲生,不吃不喝躺在床上冥思苦想,终于明白了师傅的良苦用心:人生为目标而追求,生命的欢乐就在追求的过程中;即便目标是虚设的,也是激励人们活下去的力量源泉。于是临终前,他找到陷入绝望的小瞎子,为他指出了人生的路:只有弹断一千二百根琴弦再按方服药才能重见光明。并把那张无字的白纸封在小瞎子的琴槽里,在悲壮的气氛中完成了生命的传递。《山顶上的传说》中,拖着残疾之身的养鸽人,昼夜不停地寻着丢失的鸽子;《钟声》中的牧师,放弃宗教而接受社会理想,反而对原始意义上的宗教功能有了重新发现。这些作品都寄寓着:人的生命只有在孜孜不倦的追求过程中才能有蓬勃的生机。史铁生将宗教作为自己的精神信仰,以解决内心之平衡。当他把自己的信仰融合于小说创作传达给读者的时候,其影响也就具有了精神拯救的意义。张承志是真正在信仰上皈依伊斯兰教的作家,他经历了由早期的浪漫激情逐渐为宗教的虔诚所取代的过程。从80年代中期开始,他把个人理想和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并以回民聚集地西海固为基点,走进荒凉贫瘠、没有世俗干扰、远离现代文明与汉文化中心的“回民的黄土高原”,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黄泥小屋》、《金牧场》、《心灵史》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在《金牧场》扉页上的小传中,他已经公然宣称自己信仰伊斯兰教,“崇拜为保卫内心世界而不惜殉命的回族气质”。到90年代初出版的《心灵史》,他几乎成了一个撰经者、一个教主。《心灵史》冷静、客观地描述了回教中一个支教——哲合忍耶壮丽辉煌的历史,为捍卫自己民族信仰的神圣,面对绝世的饥饿、面对暴政、面对死亡、面对一切以排异除邪的名义发动的弹压,哲合忍耶人两百年来忍辱负重,历经苦难,甚至不惜牺牲50万人的生命,以维护民族的生息繁衍和信仰的神圣纯洁。这是张承志在中国人信仰危机越过临界点之后开始写作的一部关于人的信仰的大书。“张承志最终在伊斯兰教的民众中,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归宿,并且和自己的血缘之父和解,把革命的理想和宗教的理想融合在一起。进入九十年代的中叶,他又倾心于侠的精神,并且成为民族的代言人,写了一系列的散文。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而且是一个为了信仰而生活的人。”[12]
3.书写城市,展示都市人生,表现“市民精神”。在这方面,王安忆是最有代表性的。王安忆的文学写作原是从“雯雯系列”的“自我言说”起步的,这些作品以当代文学很长时间以来所没有的清新唤起了读者的审美感受。它们多以城市为背景,但作者此时的注意力并不在于此。其实,岂止王安忆,知青这一代作家就其个人来说,虽然一律生长于城市,但在他们那时所写小说中,拿得出来堪称力作的,竟主要是农村题材。王安忆有意识地向“城市”题材转移,是在90年代以后,诚如她自己所说的,“在90年代以后,我写上海比较有文化自觉性,但这自觉性却是来源于80年代中期的寻根运动。”[13]1984年王安忆赴美,后转道香港回国,“回国之后,经历了一个苦闷的停笔时期”[14],尔后推出了《大刘庄》、《小鲍庄》等本土文化小说。此次香港之行,“对王安忆意义重大,称之为个人写作史上的界石都不为过”[15]。一个作家创作上的显著变化,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某次旅行,但王安忆后来之被人们冠以“城市作家”,此次香港之行对她“都市感”的获得,“城市意识”的确立,不能说没有直接的或潜在的影响。1986年,王安忆写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一文,表明她对城市有独特的体认。1987年王安忆推出《流水三十章》,这个长篇的主人公张达玲就是一个生活在上海的当代女性,她与王安忆笔下大多数女性一样,属于“庸常之辈”,但无疑又是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市井中人。就此而言,《流水三十章》冠之以“城市小说”是贴切的。当然,王安忆作为海派传入和张爱玲之后的写城市生活的能手,更显示于90年代《香港的情与爱》、《长恨歌》、《米尼》、《妹头》、《妙妙》、《富萍》等城市小说的创作。在这一系列都市女性题材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攒足了在城市水泥的夹缝里、灯红酒绿的暗影里掏故事挖传奇的王安忆。只见她从容穿梭于香港、上海这样的商业化大都市,出没于最不起眼的街道弄堂,隐身于人家的厅堂、厨房,透过喧嚣尘世的满地尘埃,捕捉一个个都市女性疲惫的身影与灵魂。”[15]其中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尤其体现了小说“揭示了城市的全部秘密”。作品叙述上海“淮海路”上一个叫王琦瑶的女孩,以她一生的情爱故事,写尽了“上海”在20世纪后半叶的沧桑传奇。王琦瑶是个美人,她作过“上海小姐”,作过政治要人李主任的情人,她聪明过人,雅致周到,无疑是上海这座城市造就的,是这座城市生活的凡尘俗砾打磨出来的。城市为女性提供了面对公众的舞台和严守秘密的闺房,王奇瑶就在这舞台与闺房里长大、流转、迁徙与沉浮。她是世俗的,世俗性使她同时具备了代表性,因而她最能代表上海人和上海文化,她的魅力和价值即在于此。王安忆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懈地攀登着,她感受城市,书写城市,同时也没有忘记她曾经生活过的乡村。90年代后期,她相继推出了《姊妹们》、《文工团》、《隐居时代》等描写乡镇风情的回味性小说。在知青小说家中,王安忆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势头,是文学成就显著者之一。
在新时期文学形态的嬗变中,“寻根文学”无疑是一个承先启后的文学潮流,当它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让位于多元化文学格局便是必然的了。知青写作从“寻根文学”汇入多元化文学发展潮流,固然有艺术嬗变上一致的律动与顺势延伸的逻辑,但更体现了文学从文化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中分离出来,走向独立的内在要求。文学创作如同自由落体,没有中心,没有主流,作家处于自由独立的创作状态,才是它的正常现象。因此,从“寻根”走向“多元”说明,知青文学已经开始走在一条自由的、游离的,不为“潮流”所左右的、正常的路途上,这是一条合乎艺术规律之路,也是一条预示文学发展前景的广阔之路。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提出知青文学“这座富矿能否再开掘下去?”时,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不过,那也需要一代知青作家及其后来者们有新的审视眼光,新的描述方法。
标签:文化论文; 王安忆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小鲍庄论文; 寻根文学论文; 爸爸爸论文; 年轮论文; 雪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