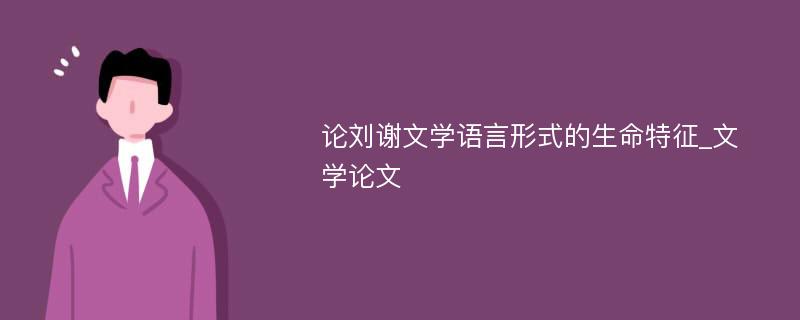
刘勰论文学语言形式的生命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形式论文,语言论文,生命论文,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01)03-0382-04
六朝是一个极重视艺术形式的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许多篇章专论文学形式,其中对我们今天的创作和美学研究有重要启发作用的是他对文学语言形式生命特征的论述。
生命美学认为,一切美的形式之所以美,归根结底就在于它的形式具有生命体的形式特征。从宇宙起源开始,万物便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优胜劣汰,不断更新完善着自己合规律又合目的的生命形式,从而使宏观如宇宙的运动,微观如一花一鸟,一草一叶,它们的生命机体和运动形式都暗含着、分享着美的形式。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正是把美的形式与天地万物生命形式的自然特征联系起来,他说:“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生命自然的形式就是美的形式。而且他更富哲理性地把美的形式与宇宙运行的大生命(道)联系起来,进而指出:“文(指美的形式——引者)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1](P.1)一切美的形式都是宇宙运动的最终本源——道的体现。声音美也是这样,不仅“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1](P.1),而且人的声音美也来自生命之自然:“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1](P.552)文学艺术中对偶(对称)的形式规律亦起源于生命自然:“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倾,自然成对。”[1](P.588)在刘勰看来,万物包括人的生命自然的形式是美的形式产生的根源。
刘勰从自然万物生命形式所具有的美的特征中感受到美的形式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同时,他又从哲学(道)的高度看到美的形式正是万物生命自然的本色和特征,生命形式是艺术形式的本源。这些都启发了他从生命特征的角度去看待、把握艺术形式。
在所有生命形式中,人是最高的进化阶段,所以,刘勰及南朝其他批评家、艺术家常常用人的生命机体的构造和名称来分析、称谓艺术作品的形式结构和组成部分。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说:文学作品“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种拟人化的比喻其实正是他们对艺术作品及其形式所具有的生命特征的初步认识和把握。
秦汉之前,人们更多注重艺术形式“和”人心从而“和”天下的政教功能,尚未把艺术形式美与人的生命形式相联系。魏晋以后,从曹丕《典论·论文》开始,许多表现人生命特征的语词被频频用来作为艺术批评的术语。曹丕的文以“气”为主,魏晋南朝文论家反复强调的“骨法”、“气韵”等就是例证。这表明,随着人们对艺术形式美感特征体验的深入,艺术形式的生命特征愈来愈为批评家(包括艺术家)所注意。而将人的生命姿态与艺术作品形式特征直接沟通的重要桥梁是魏晋玄学清谈中的人物品评。
从《世说新语》记载的清谈的场景看,清谈名士不仅以其对玄学微妙之理的领悟和美妙动人的语言词藻使听者获得美的体验,而且也以自身的意态神气与精神风姿使听众得到一种美的享受。玄学清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对人物风神才气和生命姿态的品评。这种对人的生命姿态、精神风貌的感受体验也启发了魏晋南朝文士对艺术形式所具有的生命特征的把握和领会。
《世说新语·赏誉篇》引《晋安帝纪》曰:羲之风骨轻举也。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玠别传》曰:“玠(指卫玠)颖识通达,天韵标令。”魏晋南朝艺术家、文论家以评判人物生命姿态的风骨、气韵来评价作品的艺术魅力,正是由对人生命风姿的鉴赏通向了对更虚灵的艺术生命形式的鉴赏。“骨法用笔”就是一例。“骨体”本来是指人的体貌骨骼。《世说新语·容止》篇注引《吴志》云:“……唯中弟孝廉,形貌魁伟,骨体不恒,有大贵之表。”这里的“骨体”就是指人的形体之骨骼。而上面所引的“风骨轻举”、“有正骨”,“骨”已虚化为一种对形而上的生命风姿的评价了。到了艺术批语领域,“骨”与“骨法”的内涵则是指一种形式的有机整体性带来的生命般遒劲、飞举、律动的力的美。它们是生命运动最重要的特征。所以,卫铄《笔阵图》云:“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2](P.2290)
魏晋南朝艺术理论中的“风骨”、“气韵”,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风骨”、“气”诸范畴,正是把玄学清谈中对人物生命风姿品评的术语移植于对艺术形式美的体验与把握的典型范例。《魏书·祖莹传》曰:“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这里的“风骨”是指作品应具有和人的生命一样的独特的风神体貌。“风骨”初步成为对文学形式生命意味的隐喻和概括。东晋葛洪也把文学形式比喻为人的皮肤与骨鲠。他在《抱朴子·外篇·辞义》中说:“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则患乎譬烦言冗,申诫广喻,欲弃而惜,不觉成烦也。其浅者则贵乎妍而无据,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鲠迥弱也。”早于刘勰的谢赫在其《古画品》中所论述的艺术形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气韵生动”和“骨法用笔”,这与玄学清谈中的人物品评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在刘勰等魏晋南朝艺术理论家对形式生命特征的体验中,他们明显地把艺术形式的构成区分为相互联系的两个层次,即文学的风骨与辞采,书法的骨力与媚趣,绘画的“骨梗”与雅媚。王僧虔《论书》云:“郗超草书……紧媚过其父,骨力不及也。”又云:“萧思诒书,全法羊欣,风流趣好,殆当不减,而笔力恨弱。”“谢综书,……书法有力,恨少媚好。”风骨、骨力是指具有情感意味的艺术作品形式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性所形成的力之美;而辞采、媚趣则更多表现为形式中较外在的、局部的辞藻、声色及笔画之美。有机整体的结构相当于人的骨架,局部的辞藻及笔画相当于人的皮肤、肌肉。两者相兼是完美的形式;若只备其一,多骨微肉优于多肉微骨,骨力劲健优于风流媚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风骨》、《熔裁》、《附会》等篇中集中阐述了文学语言形式具有的生命特征。具体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美的文学作品,其结构无不具有有机整体性。在《风骨》篇中,“风”是指情感的运动状态,“风”强调一种能打动人心的情感的力量。作品有动人心魄的情感就是“情之含风”,“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1](P.513)。“气”与“风”是艺术作品具有生命力的表现。“骨”则是潜存于语言文辞之下的有机整体的形式结构。它主要不是指作品中句、段安排,前后呼应等外在的篇章结构,而是指存在于每一特定作品中特定语言形式的内在结构,是一个与作品情感血肉相联、体现着情感要求的语言的结构系统。所以,刘勰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若瘠义肥辞,繁杂失统,则无骨之徵也。”[1](P.513)情感具有了感动人心的力度才有风,才有起伏振动的内在节奏;语言文辞形成一种与情感力度异质同构的完整而有机统一的内在结构才有骨。
风不等于情感,骨也不等于语言;风是情感运动的力度,骨是把情感运动的力度转换为语言形式内在的结构。“风骨”融为一个概念,就是把情感的运动状态化为语言内在的形式结构,这种形式结构具有与生命同构的有机整体性。孤立的辞采与声音是不能构成文学语言形式美的,它们只有进入与情感异质同构的形式系统之中,即进入风骨的内在结构之中,才能成为美的语言形式。所以,刘勰要求作品的语言形式必须具有“首尾圆合,条贯统序”、“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的有机整体性。“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而意阙,则短而非核;辞敷而言重,则荒秽而非赡。”[1](P.542)这是在语言的整体结构中求核、求赡,是以文骨的内在要求作为“删”与“敷”的依据,而不在一定一词上做文章。骨是与情感运动之风的内在节奏异质同构的语言的整体结构,它具有自然天成的有机整体性,但这种有机整体性的实现,又需要人力的功夫加以锤炼。人力的熔裁遵循着文骨的自然之势,文骨浑然一体的结构的内在要求会因人工锤炼而更加完善。
要造就真正具有生命特征的文学作品,必须造就一个具有首尾一贯、气脉流通的有机整体性的语言结构系统。“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1](P.570)“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统绪失宗,辞味必乱,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在这个有机整体的内在结构中,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夫画者谨发而易貌,射者仪毫而失墙,锐精细巧,必疏体统。故宜诎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寻,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此命篇之经略也。”[1](P.650)“附辞会义”,是对小到字辞,大到章篇的语言形式整体的结构与安排,是遵从着文骨的内在要求,将一个个语言符号构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生命整体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故善附者异旨如肝胆,拙会者同音如胡越”[1](P.650),善于构造美的形式,就可使异旨而彼此疏离的语言符号相亲如肝胆,产生高于部分之和的整体的结构效应。拙于构造语言形式,则往往使彼此密切的语言符号如远隔胡越,彼此产生对情感的离心和反作用,削弱了整体的结构效应。这就是语言形式结构所具有的巨大的审美功能与价值。
风骨的对立面是“丰藻克赡”,“思不环周,牵课乏气”、“瘠义肥辞,繁杂失统”,是“繁采”、“文滥”、“肌丰力沉”、“意乱辞黩”,是“空结奇字,纰缪而成经”,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1](P.513)。风骨理论的提出,正是针对南朝文坛上辞采泛滥无归的浮靡文风。刘勰不同于裴子野、颜之推等南朝理论家,他主要不是以提倡文学作品内容的惩劝讽谏、有助教化的政教功能,以牺牲形式美来拯救语言形式的浮靡华侈,流遁无归;而是在艺术形式范畴之中,提出一种具有生命特征的形式美的标准,即风骨,来矫正南朝语言形式的浮靡无归。风骨不是一个僵化凝固的金科玉律,而是一种动态的、开放的、与情感内容有机联系、异质同构的语言形式的标准。它是永远具有艺术生命的语言内在的、整体的形式结构。
其二,刘勰对文学语言形式美的另一要求是飞举之力与圆转流动之美。这是生命形式的运动性、节奏性与对称、平衡等特征在作品语言形式中的表现。
如上所述,孤立的词采与声音是不能构成文学形式美的,它们只有进入一个与情感异质同构的语言形式系统之中,即进入含“风”之“骨”的整体结构之中,才能成为美的形式。文骨是把情感化为语言符号的内在结构,是有情感意味的语言形式。进而言之,风骨强调着飞举流动的趋于动态的美。《文心雕龙·风骨》指出:“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夫翬翟备色而翾翥百步,肌丰而力沉也;鹰隼乏采而翰飞戾天,骨劲而气猛也。文章才力,有似于此。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鸣凤也。”所谓“意气峻爽”,“骨髓峻”,“风力遒”,都是强调一种强烈、充沛、坚实而快利的动态飞举之美。而那些无风骨的作品则“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了[1](P.393)。
对文学形式飞举流动之美的追求,也表现在他对建立在多样统一与变化基础上的形式的节奏性、对称性的提倡。《文心雕龙·声律》篇重点讨论通过人力调整,使语言声音的运动变化既符合沉响交错、飞扬回环、异音相从、同声相应的声律组合的美的规律,又与内在情感的运动节奏相统一,追求一种“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的回环流动之美[1](P.552)。在《文心雕龙·章句》中,刘勰强调句式参差变化带来的语言形式的节奏感:“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这就是要求语言的叙述与描写具有像舞蹈中的行列和进退、音乐中高低抑扬那样的节奏运动。所以,他说:“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也。”[1](P.570)
对偶与节奏一样,也是抽象的形式美的法则之一,它是对称与平衡之美在文学语言形式中的表现。但如没有变化,一味对称平衡,就会影响以至削弱形式的飞动之美,成为单调呆板的冗句。所以,刘勰一方面认为“神理为用,事不孤立”[1](P.588),一方面又提倡“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1](P.588)认为在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奇偶迭用,且内容充实的对偶之形式才是可贵的。
这种追求运动变化之美还体现在语言形式最小的符号单位“字”上。六朝人对语言形式美的极端热衷,从刘勰《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可窥见一斑。《练字》篇认为,写作中用字应避免“联边”,即同偏旁的字连续排列。如沈约《和谢宣城》中的“别羽泛清源”,后三字都是水旁。又如班固《两都赋》中的“鸟则玄鹤白鹭,黄鹄鹳,鸧鸹鸨鹢,凫鷖鸿雁”,连用十一个鸟旁的字。刘勰认为,这样用字单调繁复,“龃龉为瑕”,破坏了视觉在运动变化中形成的和谐与节奏感。汉人写大赋专门搜集同类字,造成繁富侈艳的美感,魏晋南朝人则更欣赏富于运动变化的清丽简约之美。两者相比,汉人美的形式更多是附着于形而下的物色形器之上,而刘勰等魏晋南朝人对形式的追求则是形而上的,它更富于抽象的形式美的意味。为了使语言形式获得运动变化造成的节奏与流动之美,刘勰提倡作品的用字应“权重出”,“调单复”,“单复”即字的笔划的少与多,它们构成了字形的瘠与肥。他说:“字形单复,妍媸异体”,“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1](P.623)。这是从字形的单复变化、错综排列中追求视觉的节奏运动和建筑美。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要求近乎苛刻,且意义不大,但其中所包含的刘勰关于文学语言形式应具有运动变化、飞举流转之美的思想却是有价值的。
收稿日期:2000-1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