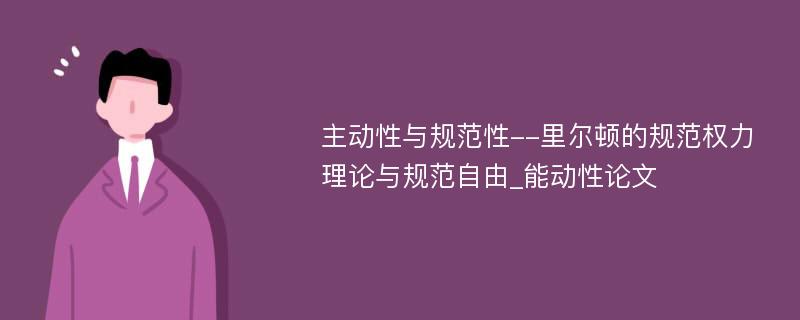
能动性与规范性——雷尔顿论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能动性论文,规范性论文,雷尔论文,力量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7 文献标识码:A
道德规范首先表现为一种强制力量。任何一个社会规范均可表述为“某一原则P具有规范特征N”。规范性N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应当”要求。而这种不可抗拒的“应当”特性因何而来,应如何理解,就成为了当代规范性(normativity)问题讨论的中心话题。(Finlay,2010)与当代其他学者只关注对于规范力量(本文用“力量”或“约束力量”来翻译force一词)的探讨不同,雷尔顿不但介入对规范性不可抗拒力量的解释,而且敏锐地把握到人们对于这种不可抗拒力量所存在的拒斥心理。所以他的讨论主题有二:规范何以拥有约束力量?规范面前我们何以能够保持相对自由?也就是说,他不但关注规范的约束力量问题,而且同时关注我们相对于规范的自由选择权问题。而后一关注维度直指我们对于规范约束力量产生畏惧的日常直觉。
雷尔顿的论证路径也有些独特。一般认为他是一个休谟路线的自然主义者,但是他自己认为自己兼顾了休谟与康德,而不是用休谟来反对康德。他的这种看法表现在他的论证主题中。在论及规范性时,雷尔顿的确持一种自然主义实在论立场,但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同情地理解康德的先验命题。与菲里帕·福特在“作为假然命令的道德体系”(Foot,1972)一文中所宣示的(当代伦理学研究中)对康德路线的强反叛不同,雷尔顿在自己的论证中一直注意不但要为道德规范寻找假然基础,而且要为其寻找非假然的逻辑基础。而且,他也主张,关于规范性基础的讨论,如心灵协调问题,我们同时可在休谟与康德那里寻找到相应的依据。
雷尔顿关于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的论证以自主(autonomy)、能动者(agent)与能动性(agency)等概念为基础。在他对这些问题的新解之中,这些概念的规范特征得以凸显,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存在着自主性缺失或选择性地放弃自主性的可能。在能动性的问题上,现实生活的人们其实有更多的表现形式。而这也正是人们在面对规范问题时得以可能自由选择的现实基础。
在雷尔顿看来,人们的规范实践并不诉诸系统的规范理论,因而我们不能把规范的道德理论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影响刻画成一种内在化的“决策程序”性质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评价图式。我们据此得以在实践中对我们的动机、策略、技巧、习惯、实践、规则等作出评价。(Railton,2003:p.xvi)雷尔顿还有一种观点,他认为:“不管先验的规范概念可能是什么样的,它们在行为中的指导作用则会变得非常后验。”(Railton,2003:p.xvii)
顺着这个线索,他建议我们从功能、作用的角度来看待规范问题。从功能角度,可以把我们通常所谈论的规范性拆分为“规范”部分与“指导”部分,或者是“规则”部分与“指引”部分。前一部分外在于行动者,它表现为一种独立于行动者意志的规范或规则。而后一部分内在于行动者的意志或意愿,但是遵守活动本身,表现为一种经验感受而不是人的意志产物。(Railton,2003:p.xviiii)雷尔顿认为自己的这种划分结合了康德的规范刻画与休谟关于规则遵守的道德心理学。通过这样一种区分,可以破除我们对于规范性概念的神秘感,我们不必再去把规范性看做是“伦理学中真的有这么样的一个东西”了。
雷尔顿在“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一文中区分了与规范相关联的三种权威力量。l.不可抗拒的外在强制(irresistible coercive);2.关联于自然律的自然力量(natural force);3.论证的力量(the force of argument)。(Railton,2000:pp.3-7)
卢梭曾对第一种力量提出过质疑:“如果以强力进行强制,那就没有必要诉诸可遵守的义务。”雷尔顿借用卢梭的这一质疑,表明第一种权威并非道德哲学意义上可以接受的权威。
自然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因而也是不存在争议的。不过在谈及第二种力量时,雷尔顿提醒我们不要把规范指导与自由意志相混同。理由有二:第一,许多规范行为的态度并不完全在意志范围之内。第二,我们无法用自由意志的概念来解释规范指导现象。因为道德律的神圣性谈及的是规范的“不可侵犯”,而不是实际的“不可侵犯”。“如果规范必须(must)在这个世界中有其独特位置的话,这种必须既不是自然律的必须,也不是概念必然性的必须。即便是我们倦怠、意志薄弱、懒惰、不服从、邪恶、无知,自然律与概念必然性也‘总是在起作用’。我们不必担心谁会违反自然律与概念必然性。但是规范指导要求我们有所作为,在这个领域中,在‘非规范’的意义上,自由要求一点必要的机警或努力。”(Railton,2000:p.4)
在谈及第三种力量时,雷尔顿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性选择”的概念。第一种是完美推理(well-reasoned)的观念。第二种是对于理由的合适反应(appropriately responsive to reasons)。规范概念存在着两种因素,一是自由因素,二是力量因素。“我们想发现解释规范性的自由因素与力量因素得以合一的秘密。或许我们可以通过理解论证的力量(the force of argument)模式来理解规范力量。”(Railton,2000:p.6)雷尔顿认为,论证的力量不同于外在压迫,也不同于自然力量。“论证的力量与信念之间的联系是一种规范必然,而不是一种普通的必然或一种概念必然。”(Railton,2000:p.6)
雷尔顿先是否定了外在压迫的力量,然后又否定了自然力量,从而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了对论证力量模式的考察上。而论证的力量又与我们的信念密切相关。当我们追问规范性时,首先是在追问一个规范陈述的约束力量是如何产生的。而当我们把规范陈述的约束力量转换为人们对于规范的认识与信念,进而通过论证的力量来向认识者与相信者证明规范陈述的约束力量时,我们已经是在围绕对于规范陈述的认识者与相信者来进行思考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里产生了一个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认识转向”。雷尔顿把问题的这一转向称作“认识的协调”(epistemic attunement)。
我们可以有两条研究规范指导的路径。第一条路径外在于行动者,第二条路径从行动者内部,由内而外展开。在内在路径中,“规范指导问题变成了这种指导如何在行动者之内发生的问题,是什么赋予了规范以生命,以及它们如何介入行动者的经验、思想、感情以及行为的形成及其意义”。(Railton,2006:p.3)很显然,在上述的三种规范力量中,我们只能求助于论证的力量,而且是由内而外的自我说服的力量。哲学研究倾向于寻求论证的力量。“在道德领域,人们经常诉诸推理和规则的至上权威。或许起码在道德问题上,我们会发现有可能借助论证的力量来说明规范的力量。”(Railton,2000:p.21)
雷尔顿建议从信念理由出发来考察行动理由。这一转换的好处是,基于信念理由,我们可以把问题转换为行动者与规范陈述的关系。在此基础上,雷尔顿先给出一个关于规范普遍性(非假然基础)的构成性论证。随后,雷尔顿分别用就高(The High Brow)与就低(The Low Brow)两个标准对此论证进行了限制性考察。
实践理性是人类因具体的实践目的而作出的理性推理活动。实践理性本身受特定时空和特定环境限制。但的确存在着作为一种理论理由的非假然理由。那么,在我们的实践领域,是否也同样存在着类似的非假然基础?雷尔顿认为是存在的,我们可以通过构成性论证(constitutive arguments)来证明其存在。
雷尔顿所设计的构成性证明的起点是假然的。在任一假然的实践活动评价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相对于行动者的实际裨益(benefits)之存在。这种实际的裨益构成了相信它存在者本身的实践理由。这种单独的个人目标与环境集构成了一种反认识的规范,它是依赖于具体环境的,因而是有时空差异的。但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很强劲的假然的实践辩护。不管怎么说,这种假然辩护并不能够被行动者自发地相信为是时空无差异的非假然理由。因是之故,我们得到一种极端的“摩尔悖论”:
(1)h是真的,但是我不相信它。
在这种悖论中,支持h的证据与能动者的信念几成反比。因此,我们得到一种反认识论的说法。
(2)我认识到支持h的证据确凿无疑,但是我丝毫不相信h。
这是两个奇怪的结论。
对这一现象,存在着一种伪装论的解释。
(3)h是真的(或者:我认识到证据h为真已确凿无疑),但是我假装它不是这样。
(4)进一步假设了对h的信念对应着h为真,如果h为假,但假装h不为假,则对h的信念就必然脱靶。据此:
(5)A相信h就必然支持:如果h本身是错误的,他对h的信念也就是错误的。
而这一结论显然已经是过分夸张了。雷尔顿指出,在这里,信念与真之关系其实在于“事情是什么样”与信念持有者认为“事情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因此,这一点也不奇怪:
(6)h是真的,但是我那时错误地不相信其为真。
雷尔顿指出,(1)与(2)的悖论“不是因为所述信念是错的或者它与世界的不一致,而是因为信念与能动者的一些既有想法不一致。”(Railton,2003:p.296)
我们的信念经常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这种不一致。雷尔顿通过上述分析表明,我们关于信念的命题态度不仅表达了命题内容为真的问题,而且也表明它不是对命题之真的迟钝或免责。“要想让命题态度成为一种信念态度,就不能让命题态度完全与真或证据无关。”(Railton,2003:p.297)
在这里,雷尔顿提出,我们需要承担“承认的代价”(price of admission)。就是说,相信某一命题,就得承担它与命题之真的关系。拒绝承担这一代价,就根本不能成功地相信这个命题。“信念与真的特殊关系构成了信念域,因而也就不再是信念者任一偶然目标的假然关系。”(Railton,2003:p.297)当然,“表明一个规范或理由是非假然的,并不是要表明它完全是无条件的。而只是要表明,无论其偶然的个人目标为何,这些规范和理由都可必然地适用于任一能动者。”(Railton,2003:p.298)
能动性的观念与信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能动者有意向有计划的行动本身就构成性地包含了行动,并且部分地是以信念为基础形成的。若根除信念,就无法形成有意向的行动。而且,我们作为能动者的这一观念的历时延续也构成性地包括记忆与期望。而这也同样包含着信念。如果从心灵图景中剔除信念,就不可能拥有可识别的身份(同一性)概念。也就是说,信念是能动性的前提条件。“在类似的意义上论证是非假然的:作为一个行动者,你必须拥有信念;作为信念,你必须表达某种可说明其为真的陈述态度,这种陈述态度必须(起码有限地)受制于真之导向的规范;因而,作为一个能动者,你起码必须这样表述你的一些态度,而无论它是否可能还服务于其它一些目标。”(Railton,2003:pp.298-299)
“为信念而付出承认代价对于形成能动性(的观念)是必要的。关于某种‘指向’真的态度的自我表述部分地构成了信念,而它转而又部分地构成了能动性(的观念)。”(Railton,2003:p.299)雷尔顿把他所表述的这种从信念到能动性的构成关系称作关于规范非假然特性的“构成性论证”。在构成性论证中,我们的信念指向了真。
不同于上述依赖于实际裨益的假然论证,构成性论证并不关注能动者对规范的实际遵守,它只提供了一种自我表述的结构。尽管它仍然只具有一种貌似的稳定性,但是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认识意义上的非假然情形。因而为我们提供了在理论推理意义上对于规范的忠诚。在《规范性的来源》(Korsgaard,1996)一书中,科斯嘉诉诸自我同一性论证,她追求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构成的稳定性。不过很显然,基于自我表述的自我同一性只是解决了行动者的规范诉求问题,却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规范的客观性问题。科斯嘉的论证就存在着这样的缺陷。
围绕这一问题,雷尔顿建议我们进一步从客观面和主观面来考察规范实践活动。如果一个行动者实际地成功遵守了规范要求,我们就说他在客观上遵守了规范。但是这也并不必然表明一个行动者在主观上认可这一规范。在直觉反应和经验推理之间存在着反差。也许我们通过实践推理的反思活动在客观上遵守了规范,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反思平衡并没有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反差。我们如何能够在实践推理的意义上证明我们对于规范的忠诚?
在这里,为了从哲学上说明行动者意向行为的性质,雷尔顿进一步提出了就高与就低两个标准来加以讨论。简单地说,就高就是看到行为之善,因而促使行动者择善而从,就低则是强调行动指向的是人的当前欲求(desires)的满足。前者可远溯至古希腊哲学传统,强调德性的吸引特性。后者以休谟理论为典型代表。休谟的理性与激情关系说可以说是当代道德行动理论的讨论母基。
雷尔顿没有简单地接受休谟的主张,而是对休谟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休谟认为人的能动性只不过是指向当前欲求的满足。休谟这种信念/欲求观被看作是就低说的典型表述。雷尔顿认为,休谟只是强调了就低行为在实践活动中的一般特征:行动者必有一目的,并依目的而行动。它既是表述的也是动机的,但是二者都不指向善。雷尔顿则认为行动者择善而从是天经地义的,人们并不会像休谟所认为的那样,永远只追求人的当前欲求的满足。“正如信念必然指向真,行动也必然指向善。”(Railton,2003:p.302)实践慎思识别善,行动接受善的指导。行动意味着给出选择对象以积极评价,并认为是值得选择的。
“信念指向真,行动指向善”的结构存在于我们的规范实践中。这相当于说我们有求真的意志(will to truth)和求善的意志(will to good)——如果你不反对使用意志这一词汇,并且能够对其保持适当警惕的话。但是意志这个词汇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对相关概念进行强化,当我们说有求真意志或求善意志时,我们几乎会把它们当作人的心理属性来看待。说它们是心理属性会让人认为是既定存在着的。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信念指向真,行动指向善”其实是人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心理属性。它不是既定存在的,但是它是我们常常展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相信某件事情为真,表达的是人的主观意愿。但是这个判断马上面临着一个是否能够兑现的问题。信念要落实为对真的客观认识,就有一个真之客观性问题,同时也有一个对客观真的认识兑现问题。因为如果相信为真的陈述并非真,而行动者如果也并不介意陈述非真,则相信为真的活动就会被锁定为信念(faith)。要想使相信某件事情为真这一点不单单是人的一种信念,就需要进一步追问真之客观性,以及行动者如何认识到真的问题。
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行动指向善”的行为中。在这两种行为中,我们都可以去说服行动者,如果不想让自己的认知活动和行动选择囿于主观信念的话,我们就需要进一步思考行动所指向的标准的客观性问题。反思均衡最终把社会规范的客观性问题收敛于社会生活本身,并且呈现为某种改良了的、温和形式的实在论。
尽管就高的内容有别,不过其一般特征是,能动者自己认识到自己所选择的行动或目的是好的。雷尔顿提出,这种“自认感”决定了能动性是否能够成立。动物和婴儿正是因为缺少了这种“自认感”,我们不称其为具有能动性。而且,即便是在成人中,如果一个人有潜在能力去辨识善,但是他却没有或者拒绝去辨识善,我们也会说这个人缺少能动性。尽管他们也是动机驱动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仍然是没有目标的。一个人的行动指向了善,但却同时声称他不承认善,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欺。
这样,作出判断与作出行动选择之间就有了某种关联。尽管作出判断并不必然意味着选择某种行动,但是选择某种行动则必然意味着作出了判断。对于善进行判断的慎思介入我们的行动,它部分地构成了我们的能动性。一个人如果完全无视善,毁掉的是他的行动慎思能力,他将仅仅依赖欲望而生活。雷尔顿把就高的择善而从的能力作为一种构成条件,我们据此来辨识我们规范推理中的非假然成分。
雷尔顿诉诸能动者的能动性,形成了一个关于规范性问题的构成性论证。在构成性论证中,能动性就其论证出发点来说是经验的,但是就其论证结果来说是规范的。构成性论证用我们所观察到的能动性实践来支撑起了一个规范的能动性概念。
这种论证的优点在于,能动性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已经见到的现象,也是我们日常实践的一部分。因此,规范以及规范实践是一个已经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基本事实。在诉诸人的能动性时,设定能动性的既成事实也就设定了规范性的既成事实。而另一方面,既然规范性是一个既成事实,则诉诸构成性论证就是一个对我们日常道德实践能动性加以理解的活动,而不是一个论证规范性之规范效力从何而来的活动。也就是说,构成性论证是一种说明而不是论证。如果运气不好,不排除这种说明仅仅提供了一种随附性的解释,也就是说,不排除它还有沦为貌似符合能动性实践的“伪”说明的可能。
另外,构成性论证诉诸自主性。其基本含义是:在如此这般被认可的完整自主的状态下,我们是这样协调我们的个人行为与规范关系的。而当我们把自主性看作是构成的,尤其当我们看到存在着自主性缺失或选择性地放弃自主性的状态时,我们会说自主性只是一个规范,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经验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雷尔顿提出,从一个能动者具有某种意愿,到其形成严格的自主性行为,这是一个开放的连续体。这种开放性的完整性只有由内而外观之(Railton,2006),才能得以充分理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某一规范持有怀疑立场者有权选择成为一个能动者,履行该规范;或者选择放弃,从而拒绝履行相应规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拥有了相对于规范的自由立场。即便承认了能动者的地位,一个人仍然有选择的权利。可以设想的是,他的一些非常规选择未必就不合情合理。在围绕能动性而展开的规范实践的问题上,人们的现实生活其实有更多的表现形式。(Railton,2003:pp.311-313)
尽管有如此种种担心,构成性论证所诉诸的能动性活动本身却似乎已为我们大家所承认。这样,我们对于构成性论证的担心也就仅仅局限在理论上,并不能够危及我们对于道德实践的观察。同时,这也牵涉到对于哲学活动目的的反思。我们总是想把规范性证明给人看,而并不满足于仅仅把规范性演示给人看。我们希望道德命令不仅是非假然的,而且应当是普遍无差异的。这一冲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笔者虽有质疑但并无定论,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思考路径。如B.威廉姆斯所言,循此路径,传统的道义论已经将规范性研究引入了“义务进,义务出”的狭窄胡同。现在,雷尔顿将规范力量与规范自由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他的论证有望为我们走出“义务进,义务出”的道德规范解释模式提供一种可能。
综上所述,在如何研究规范性的问题上,我们可以在雷尔顿这里获得某种告诫:“处理道德推理的规范性权威的过程,不在于去建立一种无可逃避的概念必然性或理性必然性,而在于理解我们道德实践的自由愿望。斯蒂文森对道德推理‘魅力’的认同是很恰当的——我们应当寻求道德推理对于我们的吸引力,而非其对于我们的不可避免的约束力量。”(Railton,2005:p.431)在规范面前,我们是自由的。但正因如此,规范是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善的特性本身吸引了我们,但是看来它并非一定要表现为我们无可逃避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