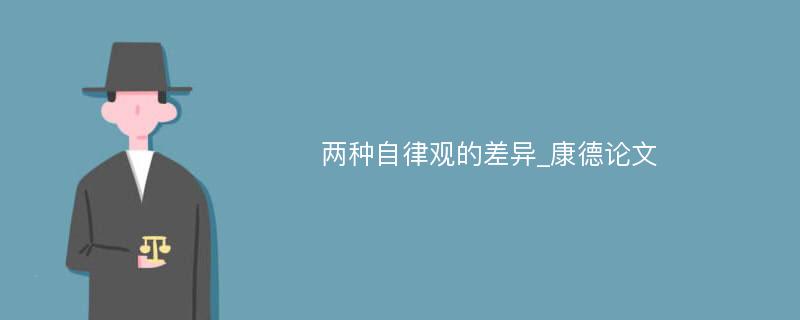
两种自律观的歧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异论文,两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问题研究
在伦理学研究中,不少论者强调道德具有自律性的特点。然而,不同论者所使用的自律概念,又往往具有某些不同甚至彼此对立的涵义。有的论者是按康德的思路解说自律;有的论者虽然把自律纳入马克思主义体系,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律概念的规定还不够明确、不甚严整。近些年来,对道德本身的不同理解以及对道德与市场经济关系的不同看法,有不少即是根源于自律概念的歧义。还有的论者显然是夸大了自律概念的操作价值,似乎把自律与否作为道德与不道德的裁量标准。为了有助于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避免自律概念的错误运用,本文专就两种不同的自律观作出初步考辨。
一
“自律”(Autonomie )一词源自希腊语, 由autos (自己)和nomcos(规则)二词合成,其原始涵义为:“法则由自己制定。”后来,尽管人们从不同角度丰富了自律的涵义,并因此而形成了对于自律概念的不同理解,但这样那样的理解都未能洗却自律的原始涵义的“底色”。如果我们在解析自律概念的不同变体时,还能够不忽略上述词源上的考察,那么,似乎可以把自律概念的基本涵义规定为:人做为主体自主地自己约束自己、自己限制自己。不同的自律观,对于这一基本涵义,一般都会取得共识。但在主体是如何实现这种自我约束、自我限制的,人的自律是否与外在因素有一定关系等问题上,却产生了分歧。
在西方伦理史上,康德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自律概念,并把它确立为伦理学的基础。
根据康德的理解,“自律”就是道德主体自主地为自己的意志“立法”——设定道德法则,而这种自主的设定排除了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外在因素,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异已意志”,包括他人意志和人格化的上帝意志;一是感性世界,包括人基于其自然本性而追求功利、利益等行为结果的感性活动因素,以及社会关系等历史条件。康德区分自律与他律(Ieteronomie)的唯一尺度, 就是看意志是否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而不论这种外在因素是什么。
康德认为,个体的人作为有理性的存在物,“在他立法时是不服从异已意志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6页)自律就是听命于每个人自己的意志所颁布的道德法则。因此,若服从他人意志的强制,就等于取消了自律。自律要排除的不仅有他人意志,甚至还包括上帝的意志。康德之前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道德律是上帝赋予人们的。而康德则认为,道德法则完全是意志的自律,“绝不需要宗教;它因纯粹实践理性而自足”。(参见[苏]瓦·费·阿斯穆斯:《康德》,孙鼎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就此而言,康德的自律原则,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宗教的批判的继续。虽然康德在论述所谓“至善”问题时,不得不把上帝的存在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悬设之一,但由于他的上帝已不是道德的立法者,不是道德的源泉,因而,康德的历史功绩仍然不能抹杀——他把他那个时代不仅为神学家而且为许多哲学家所承认的道德与宗教的关系颠倒过来了:人有道德,不是根源于上帝的命令;恰恰相反,人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因为道德需要宗教信仰。
康德的自律道德论,在消解外在意志影响的同时,也拒斥了影响主体道德的另一外在因素——以功利、利益为内容的行为结果等感性经验的影响。康德认为,如果把行为结果作为法则的基础,那么,这样的法则“永远只不过是意志的他律性”(《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98页)。康德视为道德主体的“有理性的存在物”,是一种纯粹抽象的规定,脱离了任何现实的社会关系,因而其自律也自然与任何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无关。
康德的“自律”,既排除了上帝的预定,又与感性世界绝缘,就只能先天地从纯粹实践理性的概念中去寻找根据。经过一番形而上学的考察,康德提出了一个“绝对命令”:“不论做什么,总应该作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30页)。康德把这一“绝对命令”,作为意志自律的总法则。康德的“绝对命令”,由于出自先天的纯粹理性自身,摒弃了一切感性经验的内容,因而仅仅是一种无条件的纯形式规定。在康德那里,意志自律就意味着意志只接受先天的、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即只接受来自纯粹实践理性的这种纯形式的规定;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不是看意志的对象或行为的结果如何,而是仅仅取决于行为的动机是否出自纯形式的“绝对命令”。
应当指出,康德之所以在道德立法领域忌谈功利、利益、行为结果,是因为他偏狭地侧重于从个体的角度理解它们。在康德那里,道德意志是个体的意志,道德行为是私人的行为。而功利、利益等等,也无不具有个体性、私人性。由于每个人各有其利益、功利,每个人对利益、功利有不同的理解,故如果以这样的利益、功利影响道德立法,就会使道德法则带上浓厚的主观性而丧失普遍性、客观性。康德企图通过排除带有个人主观色彩的功利、利益等行为结果方面的考虑,来求得普遍适用的、具有永久客观性的自律法则。
康德虽然主张排除感性因素对自律道德的影响,但并没有否定感性世界的存在。康德并没有取消功利、利益以及一般福利的实存性,而是把它们限制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康德的具体做法,是从人的两重性(感性与理性)出发,在感性世界(感觉世界)与知性世界(理智世界)之间严格划界。康德认为,在感性世界中,自然规律独立地起着作用;而在知性世界中,则是自由的规律起作用。人作为感性世界的一个成员,必须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和欲望、爱好等自然规律完全符合的,是和自然的他律性相符合的。人作为知性世界的一个成员,他的行动和纯粹意志的自律原则完全一致。这也就意味着,人在感性世界的活动,以幸福原则为依据。而人在知性世界的活动,则以自律的道德原则为基础。知性世界的纯粹实践理性“不受任何感性利益所影响”(同上书,第63页),而存在于感性世界中的“别的动机(如利益动机)”又不允许“与道德法则通力合作”(参见同上书,第73页)。二者互不僭越,界限泾渭分明!在康德所构想的知性世界中,不仅排除了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而且排除了非经济欲望的满足。这样看来,康德的上述划界,就维护道德的抽象纯洁性、崇高性而言,似乎比所谓经济领域与道德领域的划界更为彻底。
康德的自律概念,就其对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消解而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康德高扬了道德的主体性,使人从道德(宗德道德)的奴仆,一跃而为道德的主人(人为自己“立法”)。然而,由于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本质局限,康德的自律观步入了歧途:把主体的意志自由绝对化,把自律变成了与任何外在因素无关的、没有任何现实内容的空洞形式。于是,被康德推崇为“道德最高原则”、“唯一原则”的自律性,纵然是灿若星空,崇高无比,却也如遥远的星空般令人可望而不可即。
二
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了康德的自律概念,对之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性的改造,从而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自律观。
马克思指出,康德等道德家“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5页)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康德对于道德的宗教基础的消解,也就在实际上肯定了康德把他律性的宗教道德转变为自律性道德的历史功绩。然而,这里应当注意:第一,马克思首先是从“人类精神”而不是个别精神、个别意志的角度来规定自律,即把自律当作人类社会整体的内在制约(对比于他律即人类精神被神从社会外部制约),而不是仅仅作为孤立的个体意志表象;第二,马克思在这里仅仅着眼于从自律、他律的形式上来对比道德与宗教,而马克思主义对于自律的完整理解不限于形式,还涉及其丰富的、现实的内容。
康德谓之为“道德最高原则”的自律是无内容的,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先验形式。康德把自律原则的运用限制在知性世界,而与感性世界的功利、利益等等毫无关系。与之适成对比,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自律,不仅不排斥功利、利益等因素,恰恰还要调节人们的利益关系。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既然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那就必须使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7页)。虽然这里马克思引述了他人的部分说法, 但是马克思并不一般地赞成或反对“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这一论断,而是以“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来表明马克思自己是如何“正确理解”利益的,是以什么样的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排斥现实的利益关系,道德就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基础,就掏空了本应是道德题中之义的内容。因此,不能在道德与感性活动、利益关系之间截然划界。马克思倾向于把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康德则要在道德的基础中彻底清除利益的影响。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除了双方哲学观点的根本不同之外,还与对利益的理解正确与否有关。康德仅仅把利益狭隘地理解为个别的、私人的利益,而马克思则首先把利益区分为“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然后再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道德与不道德的分野,不在于讲不讲利益,而在于讲什么样的利益,在于以什么样的尺度来处理现实的利益关系。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只有在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时才是道德的。而与全人类的利益相冲突的个别人的私人利益,当然不能作为道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自律的观点,是与道德的社会功能即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不可分割的。自律本身不是目的,它要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在协调社会的利益关系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道德的自律就表现在对于利益关系的自觉调整之中。把自律本身当作目的,康德式的“为义务而义务”,就在根本上取消了自律的道德价值。由于自律因服务于一定目的才有价值,自律的道德行为总要对现实的利益关系产生一定效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总是主张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自律观,而不是象康德的“自律”那样,仅仅专注于行为的道德动机,不论这种动机能不能产生效果以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康德所谓自律的动机纯粹出自实践理性自身,与外在因素没有丝毫联系。马克思主义讲的自律动机则不是纯粹理性的先天产物,而是根源于一定的外在因素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脱离开现实的社会关系,个体的人就无法以人的方式生存下去。因此,个体的人注定要受到他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制约。既存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包括影响人的行为动机。人类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起最终决定作用的乃是经济关系。因此,人们“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3页)。不同的社会关系会产生不同的道德,也就会提出不同的道德要求,促成不同的自律动机。这就使得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地位上的人们的自律有了内容差别,导致了自律标准的社会性、历史性。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特定社会地位上的现实的个体,其“意志所遵循的准则”,往往难以为处于不同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地位上的所有个体所普遍认可,即难以“永远同时”“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康德所宣称的普遍适用于“一切理性存在物”的所谓“自律”,对于处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理性存在物”来说,恰恰是普遍不适用的。
康德为了说明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纯粹动机,不得不将意志设定为绝对自由的。康德看不到物质生产关系对于意志的决定作用,他清除掉“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使意志获得绝对自由,但这种意志也因此而“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康德的自律概念,即以这样的绝对自由的意志为前提。而马克思主义的自律观,则把个体的意志自由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强调这种自由总是要依赖于人对外部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总是要依赖于产生和深化这种认识的实践活动。人们在实践中越是深刻地认识了外部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就越是感到自由。基于对意志自由的这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律概念,就只能建立在对于规律性、必然性的认识的基础上。道德主体的自我“立法”,不能超越外部规律的客观要求,而应自觉地限制在规律性、必然性所允许的范围之内。遵循外部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不再被认为有道德他律的嫌疑,而被当作实现道德自律的前提。缺乏对于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自律就会变成盲目的。盲目的自律虽然也是出自道德主体自身,但因其“盲目”而可能违背规律的客观要求,最终会受到“铁的必然性”的惩罚,即不得不承受外部强制,不得不回归他律。
康德的自律概念,排除了主体以外的意志(他人意志或人格化的上帝意志)对于主体自己意志的强制,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自律概念有与之相通之处。但康德的自律概念并不止步于此,它基于意志的绝对自由,还要排除其它非意志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康德把不论是受到何种外在因素影响的意志,一概划归到“他律”的范围。而马克思主义的自律观肯定现实的社会关系、规律性和必然性对于意志的制约,仅仅把主体以外的意志对于主体自己意志的强制或主体完全被动地、机械地承受一切外部因素的限制,看作是他律的实质之所在。主体的意志自律,不是在幻想中摆脱一切外部限制,而是以对于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自主地、自觉地、自动地自己限制自己、自己约束自己。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自律观,自律性是道德的重要特征,但它又仅仅是道德的形式特征,仅仅可用之于在形式上区分道德与非道德(如法律、宗教等)。而道德的行为与不道德的行为都有可能出自意志自由,即都有可能是自主的、非强制的行为,都有可能是具有自律的形式特征的行为。因此,自律性不足以充当道德与不道德的有效评判依据。道德与不道德的根本分界线,在于是否以“个别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为根本原则。如果某种自律性行为在动机与效果上符合于这一根本原则,那么,这种自律就是道德的。反之,若某种行为虽然出自个人的自主决定,没有任何外部强制的迹象,但却将私人利益凌驾于全人类的利益之上,那么,这种具有自律的形式特征的行为也只能是不道德的行为。
